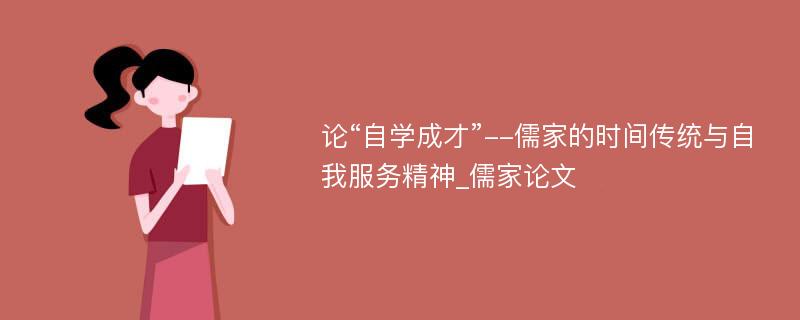
“己学”刍论——工夫传统与儒家的为己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为己论文,工夫论文,传统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3)06-0029-14
一、传统的为己之条贯
尝讲吾人与本体的肌理之分辨,其下遂讲吾人与工夫的肌理之分辨。专言工夫者,即以工夫为周遍论说的根本着眼处,其展现之尽姿、尽情与尽意,却无可能不兼做本体的论列。此是由儒家之传统的“为己”之条贯所决定。
(一)“为己”条贯的前后相续者,其大体的精神指向,乃在一个“仁”字:道德性境界面的“仁”与道德性本体面的“仁”;以明道“识仁篇”为案,做表象层与沉潜层的分说。
“为己”条贯的前后相续者,其大体的精神指向,乃在一个“仁”字。“仁”者,其作为道德性的内涵,无可置辩,只是需要吾人更进一步去做境界面与本体面的界说。故道德性境界面的“仁”与道德性本体面的“仁”,乃成为儒家之心性践履者(或谓“为己”者)必然趋向的二途。《二程遗书》卷二上载大程子答吕与叔之“识仁篇”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此则话有表象说与沉潜说之二层。一是所谓表象层,即是吾人信眼看去大抵是落于道德性的境界面去分说,譬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显是从浑然无物我内外之分隔言仁底境界。仁底境界之一体义,非系言建立于一本体,乃系言综括于一整体。整体之感通无碍,无所悬隔,照觉遍润,是明道由孔子奠立起的人伦日用之生活意趣的“仁”消化与转将出来。而孔子云“仁”,又复从周公确立“亲亲之杀”和“尊尊之等”的礼俗得到启悟。《论语》就“仁”之定义,以夫子教人之随机指点故,乃有就真实生命之实现法的工夫之仁,若《八佾》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里仁》云“观过,斯知仁矣”。又有就真实生命之跃动,虽可以由亲亲而至仁民,仁民而至爱物,其差等之分别极是明了,但此明了却不碍“亲”、“民”、“物”之间乃能作贯通一气、打成一片的实现。此实现,是全德之仁的实现,即,是全幅的道德性之境界面的实现,更说是凌越于一切德目上面乃为一切德目之综摄的实现。《颜渊》云“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其意思的描画,大抵与境界面的分说切近。二是所谓沉潜层,却非是信眼看去即是的东西,乃需要吾人做沉潜与突入的努力,去做道德性的本体面之分说。若得将“为己”做大体的工夫意义处着落,辄其对生命之真谛的涵养、照察、提撕、主一、无适、诚敬、慎独等等,而一旦能得开豁与朗现,其逻辑与条贯盖必以本体面为起点,以境界面为终点耳。即若仍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句为案。浑然无物我内外之分隔的仁底境界,其实是“终于”义,而非“起始”义。亦若阳明于《大学问》云“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只是言了表象层的意思。此感通无隔的一体之境界,之所以能实现整体义之一体,实际是根于本体义之一体。故吾人看阳明继前句的表象层说,又复直透至仁心本体去做沉潜层的条理:“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①以是,若复溯至孟子系“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句去看,其在后来的台卿、里堂之注疏里,只是较局限于一般的道德实践家的根柢去做工夫次第之讨论,而在朱子注,辄转到性理的道德实践家面上来。朱子做了理想(“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与现实(“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不待勉强(“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与勉强(“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的两层次境地之描画。吾人又复可以在朱子之理会的基础上做如下之分解:“强恕而行”“反身而诚”若意味吾人之生命性格的无限之实现,乃终有彻上彻下的两面之突破。一为彻下者,由仁心本体的通体光明为起始面去着落,故谓“近”;二为彻上者,抵至乐而忘忧,充实而有光辉的境界为挺拔的终于面,故谓“大”。
(二)工夫与践履的分辨与厘定:一重善的理想,一重人伦日用,能综合地涵括此两特质的实践之表现,儒家唤之“践履”。
中国哲学,总体言,系偏工夫的实践面的。“工夫”二字,略有殊致,其实践面之诸种表现,莫不与成就一理想人格有关。理想人格之实现的途径与方法,盖必从心性的涵养处着落,在西方若有稍契近的实践之照映者,譬如耶教流行的忏悔之救赎法也。返到儒家的实践义,辄其乃有两面向的特质之挺立:一重善的理想,一重人伦日用。故能综合地涵括此两特质的实践之表现,儒家通常唤之“践履”耳。“践履”者,其原意,可参看《诗·大雅·行苇》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又若焦赣《易林·明夷之乾》云“践履寒冰,十步九寻”,其衍义,辄必体现一道德性格及日用性格,故有司马光《再乞资荫人试经义札子》云“《孝经》、《论语》,其文虽不多,而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就使学者不能践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义礼乐”,又若朱子注《论语·宪问第十四》“蘧伯玉使人于孔子”条云“盖其进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践履笃实,光辉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亦复若龚炜《巢林笔谈·柴云章至孝》云“柴云章先生至孝,所著有《养亲说》,皆其晨昏践履之实”。以是,所谓“践履”,若详审地看,便是以德性气质的善之理想,周遍条贯于人伦日用生活里的思维世界与行动世界者。思维世界与行动世界非是悬隔无干,思维世界是“体”,行动世界是“用”。作为“体”的思维世界,盖独在意、念、思、虑、情、志、欲等方面,有其发明善之理想的表现故,或谓之心性面的,或谓之内圣面的;作为“用”的行动世界,其实质是思维世界的延续,亦盖独将其心性面或内圣面的善的理想普遍地运施于政治、社会、文化、人伦诸范畴,故能正德而利用,利用而厚生,或谓之事功面的,或谓之外王面的。故事功面或外王面的实践,亦必有一道德性格的挺拔。
(三)《论语》时代之奠基与儒家的为己精神之具体条贯:“为”的超融工夫义,道德世界的成立乃建立于“彼此交际”此宇宙之一以贯之的律则,生命实体所寓的若“灯”的能动显发方式及其若“镜”的所动显发方式。
道德性格显非悬空地讲,是始终以吾自己的生命本身为主体的。生命的根柢,非限于生理学意义上的,却更是提至心理学或伦理学的诸重意义上去说。故传统的为己之条贯以此道德实践的生命义为本根,乃其实是从肉体与情欲的躯壳突破出来,挺立一德感的精神。此一德感的精神,亦便是儒家之为己的精神。
儒家之为己精神的奠基,在《论语》的时代:
1.其《学而》章云;“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2.其《里仁》章云;“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3.其《公冶长》章云;“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4.其《雍也》章云;“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5.其《述而》章云;“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6.其《泰伯》章云;“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7.其《子罕》章云;“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8.其《颜渊》章云;“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9.其《子路》章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10.其《宪问》章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磐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11.其《卫灵公》章云;“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2.其《子张》章云;“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以上涉及“己”的诸条目,若做一综括地提纲挈领,便是一主体性精神的展现。此一主体性精神的总的旨趣,若加进阶地条分缕析,辄有如下几面向之意思:其一,有省云“己”者,系将“己”视为浑沦的自己的生命,以德性生命的性格,为自己全幅的生命的性格,若《泰伯》“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云(吾人此处的条目分解,未尝能与各注家一一相契,亦未尝求与各注家一一相契。底下各面向的分辨,亦然。《泰伯》条之所谓,是要吾人对为己的精神有一综括的认识:一是践仁成圣是吾人谓之“己”的生命不可辞之责任,反过来,践仁成圣亦必以吾人谓之“己”的生命为落定与发明的本体;二是吾人的生命之形貌,所以能郁然挺拔者,盖亦是以仁的境界与圣的气象之郁然挺拔者为底。而比照朱子、李光地、黄式三、官懋庸诸家注解,言语或纷纭,着重或略殊,其沉潜地体贴出来的为己之精神辄未相远。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可谓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谓远矣。”李氏《论语劄记》:“合而观之,以《能问于不能章》是弘,《可以讫六尺之孤章》是毅,但其根本则在战战兢兢以存心,而用力于容貌颜色辞气之际而已。盖心弥小则德弥宏,行弥谨则守弥固。《易》之《大过》,任天下之重者也,而以藉用白茅为基。《大壮》,极君子之刚者也,而以非礼弗履自胜。故朱子之告陈同甫曰:‘临深履薄,敛然于规矩准绳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虽贲育不能夺也。’可谓得曾子之传者矣。”黄氏《论语后案》:“仁以为己任,犹孟子所谓‘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官氏《论语稽》:“在常人视天下事无与于己,而士则任天下事如己事,倘非弘毅,何以胜之?”)。其二,有省云“己”者,其实是言德性生命之性格的建立,不单需作涵养之累积,且其涵养的日积月累之起始与根柢,便是吾人的血肉之躯,其中,累积亦名“加法”,肉躯亦名“己身”,若《公冶长》“行己也恭”,《子路》“行己有耻”云,又若《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卫灵公》“君子求诸己”云(“为己”的精神,非能一旦成就。此句话,隐含两层意思:一是纵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终于能豁然贯通者,乃奠基于吾人生命在日用生活的践履里之筚路蓝缕与劈荆斩棘。筚路蓝缕者,描画求趋为己精神的此生命之坚忍,劈荆斩棘者,描画求趋为己精神的此生命之刚猛。孟子“养浩然之气”说,五峰“戒谨于隐微,恭敬乎颠沛”说,朱子“涵养须用敬”说,盖是指此。二是豁然贯通,乃得近仁,近仁以后如何做,才是真谛。此一功夫近仁,非即意谓彼一功夫亦能近仁,此间若是有一丝毫的懈怠,便陡然有堕入不仁境地的忧虑。近仁是在内圣面庶几乎贴近善的理想,却是需要吾人将不懈的努力连绵地条贯于此一功夫、彼一功夫及彼彼功夫,直至生命陨落及安息刻,方止。道德性之于吾人生命的要求,从发轫于内在言,内在道德性之于吾人生命的尺度,从追求于无限言。故,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践仁之“践”,是永远的“践”,“成圣”之“成”,是永远的“成”。前面《公冶长》、《子路》、《宪问》、《卫灵公》诸条,故一是言此“为己”精神须涵养于日用的必要。贴着《宪问》条云“为己”者,在《论语》后较著名的代表性之言语,在《荀子·劝学》。抵及宋明,及其以下,乃有横渠《正蒙·大易》《经学理窟·气质》、二程《遗书·卷第六·二先生语六》《卷第十四·明道先生语四》《卷第十九·伊川先生语五》《卷第二十五·伊川先生语十一》《二程粹言·论学篇》《论政篇》、朱子《论语章句》《朱子语类·卷第四十四·论语二十六》、象山《陆九渊集卷六·与傅全美二》、南轩《癸巳论语解·卷七》、阳明《知行录第三·传习录下》《静心录之一·文录一·答王天宇二·甲戌》《静心录之二·文录二·与黄勉之·甲申》《静心录之四·外集三·答徐成之二·壬午》《静心录之五·续编二·与汪杰夫书》《悟真录之二·文录五·书王嘉秀请益卷·甲戌》、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卷第六·论语》,等等精当之议论。吾人以后面的章节将有专门的详细讨论故,乃不特在此将前面言及的材料一一罗列出来。此地只举出荀子、陈天祥、官懋庸、夏锡畴诸家之分说为案。《劝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陈氏《四书辨疑》:“欲得之于己,此为为己之公。欲见知于人,此为为己之私。两句皆是为己,为人之义不可通也。盖为己,务欲治己也。为人,务欲治人也。但学治己,则治人之用斯在。专学治人,则治己之本斯亡。若于正心修己以善自治之道不用力焉,而乃专学为师教人之艺,专学为官治人之能,不明己德,而务新民,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凡如此者,皆为人之学也。”官氏《论语稽》云:“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人无不学也。其入学也,自洒扫应对而极于修齐治平,皆切于日用之事,故曰为己。三代以后,惟士入学,其他则否。而士之为学,每以见知于人,博取富贵为心,较古人之学,名同而实异,故此章以为己、为人两言括之。”夏氏《强学录》云:“知为己,始能立得志定,始能做慎独功夫。不知为己,则毁誉荣辱俱足以为吾之累,而外物之加损于我者多矣。”又就《公冶长》、《子路》、《卫灵公》等条,可参看蔡清、李中孚、皇侃、官懋庸、汪垣诸说。蔡氏《四书蒙引》:“恭敬分言,则恭主容,敬主事。单言恭则该敬,‘恭笃而天下平’是也。单言敬则该恭,‘君子修己以敬’是也。行己恭主容说,盖出入起居升降进退见之一身者皆行己也。夫子温良恭俭让之恭亦主容说。事上敬不止拜跪趋走之间,陈力就列,乃敬之大也。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李氏《四书反身录》:“论士于今日,勿先言才,且先言守,盖有耻方有守也。论学于今日,不专在穷深极微,高谈性命,只要全其羞恶之良,不失此一点耻心耳。不失此耻心,斯心为真心,人为真人,学为真学,道德经济成本于心,一真自无所不真,犹水有源木有根。耻心若失,则心非真心,心一不真,则人为假人,学为假学,道德经济不本于心,一假自无所不假,犹水无源木无根。”皇氏《论语义疏》引李充云:“居正情者常迟退,必无者,其唯有耻乎?是以当其宜行,则耻己之不及;及其宜止,则耻己之不免。为人臣,则耻其君不如尧舜,处浊世,则耻独不为君子。将出言,则耻躬之不逮。是故孔子称丘明,亦贵其同耻,义备孝悌之先者也。古之良使者,受命不受辞,事有权宜,则与时消息,排患释难,解纷挫锐者,可谓良也。”官氏《论语稽》:“行者不得而反求诸己,则其责己也必严;违道干誉而望人之知己,则其责人也必甚,其始不过求己求人一念之别,其终遂至君子小人品汇之殊,人不慎之于所求哉!”汪氏《四书诠义》:“求诸己者,凡事只求自尽,见得尽伦践形皆己正当事务,不可不求,而穷通天寿俟之天,用舍毁誉听之人,于己无与也。然非勉为也,必求自尽,心始安耳。若著一念勉强,则故为隐晦,与求诸人者同。”)。其三,有省云“己”者,其实是欲在德性生命之性格的建立中,作更进一步的沉潜,即突入到血肉之躯的己身内部,最终着落于心性面去显发生命之道德性格的真谛之主宰,心性面是意、念、志、欲、情等的统合,若限于合理与允帖,是正意、正念、正志、正欲、正情之属,若离于合理与允帖,辄是私意、私念、私志、私欲、私情之属,前者需作涵养面的累积之“加法”,若《雍也》云能近取譬的“己欲立”“己欲达”,《卫灵公》“恭己正南面而已”云(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恭己者,修德于己也。正南面者,施治于民也。”),后者需作涵养的节制之“减法”,若《颜渊》“克己复礼为仁”,《述而》“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云(就《颜渊》“克己复礼”条,前贤注家多有激烈之讼议,所谓的汉学与宋学之诸辩难的其中一个纽结,便落在这一端。此可详参《汉学商兑》之具文。汉学系以“克己”之“克”只是“约制”义,“克己”之“己”只是“自己”义,宋学系辄将“克己”之“克”作“战胜”解,“克己”之“己”作“私欲”解。惠士奇、毛奇龄、阮元、陈澧及朱子各家之分说,可做参看。惠氏《礼说》云:“克为敏德,以己承之。孔子曰克己,曾子曰己任,一也。己之欲非己,犹身之垢非身。为仁由己,是谓当仁。仁以成己,惟敏乃成。训己为私,滥于王肃,浸于刘炫,异乎吾所闻。”毛氏《论语稽求篇》云:“马融以约身为克己,从来说如此。夫子是语本引成语。”“克者,约也,抑也。己者,自也。”《四书改错》:“马融以约身为克己,从来说如此。惟刘炫曰:‘克者,胜也。’此本扬子云‘胜己之私之谓克’语,然己不是私,必从‘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为私,称日己私,致朱《注》谓身之私欲,别以‘己’上添‘身’字,而专以‘己’字属私欲。于是宋后字书皆注己作私,引《论语》‘克己复礼’为证,则诬甚矣。毋论字义无此,即以本文言,现有‘为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阮氏《研经室集·论语孟子仁说》云:“颜子克己,己字即是自己之己,与下文‘为仁由己’相同。若以克己己字解为私欲,则下文‘为仁由己’之己断不能再解为私,与上文辞气不相属矣。且克己不是胜己私也,克己复礼本是成语,夫子既引此语以论楚子,今又引以告颜子,虽其间无解,而在《左传》则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对解。克者,约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尝有己身私欲重烦战胜之说?”陈氏《东塾读书记》云:“克己复礼,朱子解为胜私欲。为仁由己,朱子解为在我。两‘己’字不同解。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驳之,澧谓朱《注》实有未安,不如马《注》解克己为约身也。或疑如此则《论语》无胜私欲全天理之说,斯不然也。胜私欲之说,《论语》二十篇中固多有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处者,胜之也。原宪问‘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者,胜之也。‘根也欲,焉得刚?’欲者,多嗜欲。刚者,能胜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三戒:戒色,戒得。色与得者,欲也。戒者,胜之也。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皆欲也。明其为损,则当胜之也。”而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云:“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归,犹与也。又言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人皆与其仁,极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又见其机之在我而无难也。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此是于局促处言汉宋之异,若仄跃至开阔处,亦未尝不能见汉宋之同,即:此两系其实皆肯认“克己”乃是涵养的减法之路数。孔子时代言“为己”,固是奠立了注重“仁”与“礼”的基本之生命性格之追求,及至朱子时代的理学系统,辄是将“仁”与“礼”的性格追求转进为一个“理”的范畴去讲。以是,在朱子系看来,“己”乃须作天理之己与私欲之己的衡定,天理之己是要做加法的,私欲之己却是要做减法,正若《朱子语类卷四十一·论语二十三》言“礼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说个‘复’,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复礼。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复得这一分天理来;克得那二分己去,便复得这二分礼来”。故,愈是去做减法的,辄便是愈去做加法的。而“为己”的一个“为”字,其实是落定于“超融”义。此“超”是愈内在愈超越的“超”,此“融”是愈转圜愈圆融的“融”。超越且融合的明晰具细之肌理,辄是累积与节制的尺度之衡定,即若加法与减法之综摄,乃得“为”的超融义。以是看,朱子之分解路数,纵甚受责难,吾人则以其未尝不可,汉学之照着讲系有其可取,宋学之接着讲系亦有可取,如此吾人看其他若李恕谷《论语传注》、康南海《论语注》等著述,便亦有一弘博的包容心在。)。其四,有省云“己”者,其实皆要在人伦界之活泼泼底日用生活里面去分说,方有其笃定的意义,即,浑沦的自己的生命,非可能孤悬地于宇宙中挺立,乃必与人交际,与事交际,与物交际,以得彼此地扶依交结,呼吸互通,运命相牴。所谓善,是与人、与事、与物的交际故,乃得为善,所谓恶,是与人、与事、与物的交际故,乃得为恶。若此宇宙之苍茫无限,只是吾人为惟一的挺立者,辄吾人以为善,便可能是定论的善,吾人以为恶,便可能是定论的恶,但事实证明此只是不真实底悬想。吾人之有生存的可能始,便与其他的无计数的生命体盘根错节无以分隔,故所谓善,其实乃是与人、事、物作一定度量后的善,所谓恶,乃是与人、事、物作一定度量后的恶。此种相对相关的总体之轮廓的描画,辄在《论语》诸章便已豁然得烛照洞明的显现。若《颜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学而》“无友不如己者”“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子罕》“毋友不如己者”,《宪问》“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云云(言为己精神,其中的一个前提,不可不讲。亦即是说,由此前提的明朗,才使得此“为己”义愈是圆融与丰满。欲见到此前提,其实不难,只需吾人略作沉潜的心思,乃可得俯拾皆是的印证。譬若通过《颜渊》、《卫灵公》、《雍也》、《学而》、《子罕》、《宪问》诸章的材料,便可简易地证明一道德世界或价值世界的成立,乃奠基于彼此交际,此宇宙之一以贯之的律则。此律则,便是为己精神的枢纽性之大前提。每一生命之物事,盖以生命的显发能动之运力故,可喻为炯然之照体。照体者,非若生活里镜花水月的玄幻所指,却是此宇宙的彼此交际之一贯律则所当然已赋予的确实之存在义,故“照体”义蕴涵三层:首先是实体,其次此实体是一有显发力的东西,故得“照体”名。复次,此生命实体的显发乃能主动地将力量运施于他者,此种方式吾人喻为“灯”的方式,当然,此生命亦非只是能动的发起者,盖亦必同时担负着被动地接受并反映来自他者的力量运施之角色,此方式吾人喻为“镜”的方式。前者以“能动”实现其力量的显发,故谓之“能照”义的,后者以“所动”实现其力量的显发,故谓之“所照”义的。儒家传统的别爱义或推己及人的忠恕义,其实皆首先设定了彼此交际的人伦世界之事实,在此事实的设定之前提下,方着重讲生命的主体性之位置、功能及精神。故吾人参看以下诸家之注解,乃可能有更多的理会。若黄式三《论语后案》云:“主友俱以交际言,古义如是,故《集解》云然”,又云:“夫子以行仁之方,不论大小广狭。天子之仁,厚诸夏而薄四裔;诸侯之仁,厚境内而薄诸夏;递而推于卿大夫之仁,一介士之仁,凡己之所不得辞者,即施济之所及。仁者之于人,分有所不得辞,情有所不容遏,相感以欲而转责于己焉,所谓能近取譬也。”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云:“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譬,喻也。方,术也。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于此勉焉,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毛奇龄《四书改错》云:“博施济众不是驰骛高远,即此圣道仁道一贯忠恕之极至处。只圣道该忠恕,而由仁达圣,则必从强恕求仁,以驯至乎圣。此即子贡终身行恕之终事也。大凡圣道贵博济,必由尽己性尽人性以至于位天地育万物,并非驰骛,故《大学》明德必至亲民,《中庸》成己必至成物,《论语》修己必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独善其身必至兼善天下,即《学记》记学自九年大成后,忽接曰:‘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夫圣道未成,亦必先力推忠恕,而后可以成圣学。”官懋庸《论语稽》云:“子贡从广远处言仁,夫子从切近处言仁。子贡之言愿大难偿,故尧舜犹病。夫子之言则推己及人,只在尽己之心,由近及远,能立达一人则仁及一人,能立达千万人则仁及千万人,何病之有?‘能近’二句指出下手所在。方如治病之方,言近取诸己以譬人,即为仁之方也。”王夫之《四书训义》云:“夫子曰:凡人之情有求而不得,而不知所以可得之道,郁抑而不能自安,则患心生焉。患之则必思所以求去其患,而情乃适于此,而为己为人之别存焉。自君子而思之,则有其不可患者勿容患也,有其真可患者不容不患也。今人之所患者,己有德而人不知所尊,己有才而人不知所用,于是视天下若无所容身,而身亦无所自容。此不必患者也。能夺我名而不能夺我志,能困我于境遇而不能困我于天人无愧之中,不患也。乃若所患者有贤者在前而不知为贤,则出而无所可任用,处而无所可效法。有不肖者在前而不知为不肖,则信用之而为其所欺,交游焉而为其所惑。而贤不肖之情形非可以一端察也,疑之而又见其可信,信之而又有其可疑,将何所鉴别而不至自失其身?此则求之不得其术,裁之不知其要,所为惘然于身世之际,而自见其可忧者也。以患不己知者,反而自患其知,斯亦为为己之实学。”
二、儒家工夫论的性格衍绎:以《庸》《孟》的“内转系”与《学》《荀》的“外转系”为议论的基底
“工夫”二字,在《论》、《孟》、《学》、《庸》的原文,都无所见。但决不意味,此四文本盖全无“工夫”的旨趣。即若《论语》系以“忠恕”、“近取”、“勇直”以实现“践仁”之精神,乃成为奠立儒家工夫论之基本律则的肇端之说,其一贯而下,辄衍出四系之条贯:(1)或若《中庸》系以“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言“慎独”法;(2)或若《孟子》系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言“扩充”法;(3)或若《大学》系由“自新新民”云“止至善”法;(4)或若荀子系由“积学为圣”“仁义法正”云“起伪”法。此世系中,《庸》、《孟》二系偏于内转,故可统称之“内转系”,《学》、《荀》二系偏于外转,故可统称之“外转系”。所谓“内转”便是反抵到心性面去建立生命的内圣之性格,所谓“外转”辄是突破到事功面去建立生命的外王之性格。
(一)“内转系”经历了由《庸》至《孟》的自力性格之不断强化
无论是“内转”抑或“外转”,皆表明非能静而无动,内转系的“动”是由“上达天德”的超越之遥契面决定的,从《庸》的“至诚尽性,以尽物性,以赞天地化育”迄《孟》的“尽心,知性,知天”,《庸》是慎独此“性”,《孟》是扩充此“心”,性,或较天为近,心,或较人为近,《庸》言慎独,以吾人的“性”之隐微故,《孟》言扩充,以吾人的“心”之本善故。以是,内转系其实是经历了由《庸》至《孟》的自力性格之不断强化:(1)关于《庸》。《庸》言“性”的根柢,尚且依天命、天道的下贯讲,亦即,此他力的主宰性格乃基本形成《庸》的宇宙论性格,而此宇宙论性格亦必牵制并影响到其在人生面的表现,譬如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便典型地体现了《庸》的半他力半自力的性格。这句话可作两体段说,前体段“诚者,天之道也”,系讲宇宙面的,是就他力言,后体段“诚之者,人之道也”,系讲人生面的,是就自力言,宇宙面的本体在“诚”,故有“诚体”的说法,人生面的工夫在“诚”,故有“诚敬”的说法。这样一来,可能转出两个问题:一是“诚体”如何实现,一是如何实现“诚体”。此两问题,看起来只是次序的颠倒,却是两种迥异的路径之表达,一个是从宇宙面向下说的,一个是从人生面向上说的。云“诚体”如何实现,是云宇宙的创造或生化原理究竟若何,譬如“为物不二,生物不测”“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皆是描画宇宙生命的流行不息、创化不已的过程之实现。云如何实现“诚体”,是云人生面怎样能够上契到宇宙面的本体,亦即是须立定于照察、涵养、诚敬的所谓工夫面的努力,去做洞明地体贴。(2)关于《孟》。比照言,抵及孟子系的境地,辄焕然是全幅的自力性格了。此全幅的自力性格的实现,盖粗廓地有二面向之表现:其一在《孟子》卷十三《尽心上》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句,系将宇宙面的通盘地收摄于人生面来讲。纵然云事物的综罗万象非即可以与天命、天道的观念作等量观,即孟子系未尝将宇宙的命定义与必然义完全地收摄到吾人自身的生命中,并赋予吾人自身的生命以命定义与必然义的自由之衡定,却已然将宇宙之谓宇宙的实质义与内涵义(综罗事物之万象的事实)完全地收摄到吾人的生命之心性面的、条理面的或者功能面的来条贯。以是故,在后来的宋儒之系络中,乃有象山之着重于心性面的衍绎:“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见《象山语录(上)》严松年所录之条目),朱子之着重于条理面的衍绎:“万物之理具于吾身,体之而实,则道在我而乐有余”(见《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及龙川之着重于功能面的衍绎:“万物皆备于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具”(见《陈亮集卷之四·问答下》)。其二,在《孟子卷十三·尽心上》的另一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此话首先通彻地呈现了人生面之自力性格的建立,乃须将吾人的本心做根柢。所谓“根柢”,即云本心是乃能逻辑地连带出“性”、“天”诸范畴世界的生发处与起始处,孟子系此本心,非是空廓无物,却是将恻、羞、辞、是的“四善端”与仁、义、礼、智的“四善德”通融于一炉的,洞彻是此本心,光明是此本心,洞彻义与光明义便是“尽心”之“尽”的大体意思。其次,上提地概括言,孟子系的精神在“仁义内在”四字,环绕此四字,乃有“即心说性”的工夫面之表现。孟子素来主张“仁义”之道德尺度恒内在与自成于吾人的心中,非是外铄而得,此本心是不虑而知的,故可唤为“良知心”,此本心是不学而能的,故可唤为“良能心”。此个“不虑”、“不学”的存在前提,便已然充分地定义了孟子系的“本心”之性格及条理。故孟子系之扩充法的工夫论,无论其讲“反身而诚”、“养浩然之气”(或言为气的“配义与道”,或言为气的“直养无害”、“至大至刚”、“塞于天地”),或建立“勿正、勿忘、勿助长”的“三勿说”,皆必基于两个前提,一在云善之本心的天然自成,一在云善之本心的不证自明。天然自成者,是云吾人的善之本心并不需要一个外在的源头为根柢,乃是从来便如此地生于斯的,不证自明者,其实是天然自成的前提下所能衍绎出的命题应有之义,即并不需要一种外在的力量去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合情性,乃是吾人予吾人自己的本心世界以全幅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合情性。复次,“尽心”的一个“尽”字,只是孟子系工夫论之扩充法的粗廓的描画,其细处的分疏,辄在于“敬直”、“反诚”、“养气”、“三勿”、“收放心”诸说。此中,“敬直”、“反诚”为一路,偏就工夫的态度言,“养气”为一路,偏就工夫的方法言,“三勿”、“收放心”为一路,偏就工夫所当戒慎的注意事项言。再次,“心”与“性”的关系究竟若何?为何需要先即心说性尔后乃能说天?通例义的“性”,是“本性”义,物的本性谓之“物性”,人的本性谓之“人性”,然“性”却是宇宙与人伦间的转圜得以可能者,这是儒家系统的一贯之说。在孟子系中,“心”与“性”是两个既有分别亦无分别的范畴,若云无分别,便意味着,性若只是大体之性,即若只是道德义的纯善之性,辄此性当可与善的本心作等量观;若云有分别,辄大抵系于两层面的意思决定,一层是关乎“性”的理解,一层是关乎“心”的理解。关乎“性”的理解者,孟子系显然未尝否定自然(本能)义之性的存在(若《孟子》卷十四《尽心下》所讲:“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乃有“小体”之说,因而以“性”有“大体”与“小体”的分别故(若《孟子》卷八《离娄下》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又《孟子》卷十一《告子上》云“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其与纯粹意指“道德心”意思的“本心”义,盖有距离;关乎“心”的理解者,辄以孟子系亦未尝一律地将“心”作“本心”解,吾人即看其讲“心之官则思”的道理,便蘧然有“知觉心”的意思在,故以“知觉心”之“心”如何乃能与诸般的“性”之观念处理好关系,成一问题。以是,“即心说性”其实也隐含了“以心为性”的意思在里面,“上达天德”是所谓超越的遥契者,超越的根柢在“心”,遥契的介质在“性”,若“心”落在“本心”义,则“心”即是“性”,尽心便是尽性,故尽心也便能直截地与宇宙契。
(二)“知”的工夫与“行”的工夫之关系:辨思维世界的内圣性格与行动世界的外王性格,以阳明、近溪、及朱子为案
吾人云传统的为己之条贯乃必建立于宇宙面与人生面去讲,若论先后,恐以宇宙面为先,若论轻重,辄以人生面为重。人生面的工作,亦即是吾人在人伦日用生活里的点点滴滴之所感、所想、所行、所为。所感、所想是思维世界的,所行、所为是行动世界的,其实在吾人的此谓“己”的生命中,所感、所想即是所行、所为,所行、所为里亦未尝无所感、所想。亦即是说,吾人的生命并非偏颇于某一端,非能悬空地云思维世界,亦非能悬空地云行动世界。吾人知道外转系的“动”突出的是要建立生命的外王之性格,但此外王性格的建立,亦非能完全与内圣的性格悬隔起来讲,即,纵使若《学》、《荀》之属,吾人予其以外王性格的分判,但其根柢一是在于内圣面的涵养实践。儒家之谓儒家,其自始至终所需完成的功课,乃必是“体仁”的工作,若置“体仁”不云,便与儒家的为己精神相远。故,若自儒家的概括面往下细言,只是内转系可能更偏于讲思维世界的“体仁”,外转系更偏于讲行动世界的“体仁”。看孟子系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却绝非是只在内圣面着力而与外王面毫无干涉。以是,孟子系大抵是沿着孔子奠立起来的“推己及人”的“推扩法”之轨迹,综摄内外,却于内圣面的自力性格方面多所着力,乃转出一所谓的“扩充法”耳。
前云在吾人的谓之“己”的生命之学问条贯中所感、所想即是所行、所为,这里须进阶地辨明吾人的思维世界当下即是吾人的行动世界,以及吾人的思维世界如何乃能成就吾人的行动世界此两问题。前一问题之“当下即是”需要吾人作细细思量,“当下即是”可以是当下“本然即是”与当下“当然即是”两面,“本然”是本来如此,“当然”是应当如此,本来如此是讲吾人生命的素来的固有之状态,亦即是现实的样子,是就过去说;应当如此是就吾人的生命之未尝曾有、却未必将无的一种状态,所谓的理想的样子,是就未来言。这里其实牵涉到知行问题的分辨,是知本来就是行呢,还是知当然就是行?儒家惯讲知行工夫的合一,但知行工夫的“合一”二字如何理会却各有千秋。譬如阳明言“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见《阳明全书》卷三《传习录》下),更多的是偏于将“行”纳于“知”言。罗近溪云“当下即是”工夫,其条贯颇近于佛家“作用是性”的讲论,却是主张日用生活里的“行”当下便是“知”的发明,显是将“知”摄于“行”言,又若朱子云“知行常相须”(见《朱子语类》卷九)“知与行须齐头作,方能互发”(见同上,卷十七),看起来是直截地讲“知行互发”,其沉潜义却系云“知先行后”与“行重知轻”,故《朱子语类》卷九亦有如斯的说法:“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
故吾人若在此基础上作条分,阳明的知行论,系就“知”本来就是“行”讲,近溪的知行论,辄就“知”当然就是“行”讲。此一来,朱子系素所讲论的且知且行,亦复且行且知的所谓“知行互发”义,盖非是要吾人穷数载乃至穷数十载彻彻底底地知了才落于力行,此便涉及吾人的思维世界如何乃能成就吾人的行动世界之问题。若以吾人于上述的描画为根底,“知”乃能与思维世界及内圣面相应,“行”乃能与行动世界及外王面相应,又以是为基底作一有意思的推论,便是:阳明或讲“内圣本来便是外王”,近溪或讲“内圣当然就是外王”,而朱子或讲“且内圣且外王”,亦复“且外王且内圣”底。更将《朱子语类》卷九里的一则话作一词语的替代,辄便转成“致内圣力外王,用功不可偏废。……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内圣为先,论轻重当以力外王为重。”
吾人在此处更借己意去擅做词语与意思的替换,其表现盖非能为一般论家所接受耳。但知与行的观念在儒家之历来的传统中确是涉及多而含混亦多,吾人的努力只是欲将此层不必要的含混之盖子一并尽然掀去,而袒露出雪白玉润、晶莹剔透若珍馐的各种真东西。亦即是说,在吾人言,“知”的工夫便是思维世界的,更是内圣面的,着重于心性之涵养的世界的;“行”的工夫便是行动世界的,更是外王面的,着重于事功之致用的世界的。“工夫”者,非谓“知”才是工夫,“行”亦是工夫,反过来,非谓“行”才是工夫,而“知”亦是工夫。括言之,“知”所需凸显的是其内圣之性格,“行”所需凸显的是其外王之性格。
上面就“知”的工夫与“行”的工夫之关系的分辨,及为何需要就思维世界的内圣性格与行动世界的外王性格作特意的着重,其实是预为后面的工夫论与知识论关系的讨论,及“动中工夫”之条贯的具体辨析,作一基础性的铺垫,这大抵是此节辨知行工夫的一个重要意义与价值的所在。
(三)《学》作为“外转系”的工夫实现之一例:其本文予人以平铺面的廓然之直感;统摄地看,《学》的诸“本”义,盖以“物有本末”作为其总体意思的提拎;将《学》做三层肌理的条分;《学》所概言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之相贯义,首先系就宇宙面作广义的论说。
依上理会,吾人且去看《学》《荀》的外转系之“动”,便可得一更澄明更理性的照映。
直截看《大学》之本文,其得到平铺面的廓然之直感,当是极简易的。无论是言“三纲”的平铺,抑或“八目”的平铺,皆是由内及外、由本及末、由体及用、由始及终者,即若其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耳。《学》之云“本”者大抵有如是几条:1.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朱子注云:“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2.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朱子注云:“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而措之耳。”)3.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子注云:“本,谓身也。所厚,谓家也。”)4.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朱子注云:“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观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矣。”)5.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朱子注云:“人君以德为外,以财为内,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盖财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絮矩而欲专之,则民亦起而争夺矣。外本内末故财聚,争民施夺故民散,反是则有德而有人矣”)。统摄地看,《学》的诸“本”义,其盖以“物有本末”作为其总体意思的提拎当无甚疑问。其云“物有本末”义,具体的运思于八目里面,乃有如下之界说:格物系致知之本,致知系诚意之本,诚意系正心之本,此格、致、诚、正四条,亦复是修身之本,依此逻辑条贯下来,辄亦复可讲身为家之本,家为国之本,国为天下之本者。《孟子·离娄上》有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多有学者以为此是《学》渊源于《孟》之实际的证据,但以朱子明断的通行之说为据,《学》为曾子所撰,其早于《孟》,并开启《孟》的一些精神意趣当是极现实的。若由《大学》的“明明德”为其展延人生论之条贯的“本”、“体”、“始”、“内”的基础面,《孟子》亦未尝不是将善的心性之“明德”为其着重当去涵养、发明及扩充者,但这只是轮廓地看《学》、《孟》在心性面的“同”,若突入到各个更细处去穷究地追问,辄其“异”也甚明。《学》云心性面的善之立根,非是直截由心性言心性,由善言善,由涵养言涵养,乃是经历了先由外而后仄至内的条理。亦即是说,以外于吾人的“物”,为吾人的所感、所思、所念、所虑的根柢。此根柢作为主体界的吾人之照察(格)的对象,乃成为客体界的东西。即在主体界言,客体界是一被动,但此客体界之谓之“物”的东西却了明是主体界之各方面意虑情志的源头与契机。由是,吾人前面尝做的逻辑之条理,以为“格物”是其后各程序与步骤的起始者与本体者,其实仍不够谛当至精确面。易言之,“物”才是诸条贯的终极之本尔。此是从前看《大学》者皆可能无意间滑过去而不加着意者。故吾人看《大学》之道以“明明德”为三纲之首,此“明明德”三字直截地好像只是与内圣的心性面去做工夫便行。殊不知《学》的“明明德”之主张其实早就隐了“以物为本”的意思在里头。吾人讲宋儒的龙川水心之条贯,是素称为“主物”的一系者,以其思想的渊源盖近可以追溯至荆公系,远可以追溯至荀子系为柢,以为荀子系便是后来“主物”系的终极根柢者。若以吾人今之就《学》的各面向之照察看,其实其就以物为本的讲论与着重,方是真谛的根柢也。
以是,吾人盖可以将《大学》做三层肌理的条分:一层肌理谓之“形而上者”,一层肌理谓之“形而中者”,一层肌理谓之“形而下者”。此讲法看上去颇突兀,若案头昏沉泯睡之人一下子为窗外袭进的飒爽之雨的一片凉意所惊起者。且待吾人细细底费些工夫做品茗,辄乃终将或有丝丝之回味于心头绕转。此谓“形而上者”是就宇宙面去界说,此谓“形而中”及“形而下”者皆是就人生面去界说。吾人寻常以为《大学》是“纲”与“目”的二层肌理,其实只是限于人生面去做讲论的。即,此人生面的界说,只是言了中间的“三纲”之一层及底下的“八目”之一层,以“三纲”为“八目”的总领,以“八目”为“三纲”的明细。但此人生面的二层肌理,其实系奠基于宇宙面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肌理说,才能建立起来。吾人云《学》所概言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之相贯义,首先系就宇宙面作广义的论说,亦即,谓之一般的宇宙之生命,盖莫不有本与末、始与终的条贯在里面作动因。只是《学》的著者未尝将此一层最上面亦最根本的肌理作直截而明白的描画,乃是将其婉转且含蓄地摄入具体的章节里面,不易为读者所体察焉。既然宇宙面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之肌理乃成为人生面之纲与目的二层肌理之根柢者,故吾人看“明明德”、“亲民”以至“止于至善”,皆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动因在里面。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亦复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动因在里面。以物为本,以物为末,以事为始,以事为终,“明明德”是物之本的表现,“止至善”是物之末的表现,“格物”是事之始,“平天下”是事之终。本末是物的条理(理),终始是事的条理(理),即在纲与目的人生面之肌理言,物的本末之条理及事的终始之条理,莫不与吾人生命的心灵世界紧密地契为一体,于此契为一体中去显发其功能与活动,于是更乃有“物即理即心”的浑然一体之表现。
(四)比照孟子的内转系之着重理想性的工夫实践,荀子的外转系着重以现实性的深切体贴为建立的基础。即,现实性特质,周遍地体现于荀学各面向的哲学构造中,其现实性所以能挺立得起来,盖系于“物”的观念之彰明。
孟子的内转系之“为己”精神,以其着重于内圣面的建立,为吾人知。但孟子系乃得与《学》、《荀》的外转系之重外王性格的工夫实现,有分别的更深切之原因,辄恐在《学》、《荀》就“物”的观念之彰明:《学》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为其横贯的平铺义,《荀》以“裁万物,兼利天下”“得之分义”为其综摄的根柢义。由《孟子》讲论君子之“所乐”、“所欲”与“所性”(《孟子·尽心上》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又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及善、信、美、大、圣、神之成就德性生命的进阶(《孟子·尽心下》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乃可见出中国乐感文化的源头形式之一表现。中国非无悲感文化的条贯,悲感之义,重要的形式,即在“忧患”。而“忧患”,辄根于对现实世界之?混沌晦暗的茫然无措,若《书·大诰》云:“肆予冲人,永思艰。曰,呜呼!允蠢鳏寡,哀哉。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自恤”,对天命世界之神秘莫名的力量之诚惶诚恐,若《论语·八佾》里孔夫子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以现实性之照察,而转出一理想性之文学,其代表,楚《骚》也。但孟子所云的“乐”,却一是以理想性为始,又以理想性为止:其云“人性皆善”便涵括着些理想的意思在,待至其言“反诚得其大乐”及“君子三乐”辄纯粹是理想的境界。以理想性之照察,诞生一乐感文化,以现实性之体贴,诞生一悲感文化。中国文化之精神既有乐感面又有悲感面,乃因其底面的理想性因子与现实性因子作功能耳。
荀子的心理学、政治学、宇宙论、历史观乃至逻辑学,皆以现实性的深切体贴为其建立的基础。心理学面,若云“好利、好疾、好欲”的三恶端(《荀子卷十七·性恶篇第二十三》:“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②),政治学面,辄一是以“明分使群”的功利义为条分的基础,其意思大抵与《墨子·尚同》篇近似(《荀子》卷六《富国》篇云:“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为德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纷争之祸矣。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③),宇宙论面,以因物、思物、愿物的“制天命而用”作表现(《荀子卷十一·天论篇第十七》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④),历史面,辄荀子在《王制》篇、《非相》篇、《不苟》篇,大抵云“法后王”之说,乃与孟子“法先王”说相牴(譬如《荀子卷第二·不苟篇第三》曰:“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⑤),逻辑面,其辄以“制名以指实”去做“名”的缘起及功用之论列,其进路及廓然之大体,盖契于《墨经》所云(譬如《荀子卷十六·正名篇第二十二》曰:“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⑥又曰:“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异实者莫不同名也。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⑦)。现实性特质,周遍地体现于荀学各面向的哲学构造中,而其现实性所以能挺立得起来,盖系于“物”的观念之彰明。
譬如前面涉及荀子言“性恶”,看起来直是就心性面作一基本的分判,但其就“性”的理解,即首先有“本、始、材、朴”的认识,而此“本、始、材、朴”,若自其来源云,是“天之就”,就其内涵云,是“生之所以然”。此“生之所以然”,非是空洞无物,却有谓之“质”的好、恶、喜、怒、哀、乐,便可由“性”进一步界定为“情”。就其显发自己生命的着力之无限义,为可得而求之,便是性的“所欲”之表现。所欲可以是好利,可以是好疾恶,好声色。但荀子之所以将此些“所欲”定义为“性恶”云云,系因随顺好利之性将生争夺、亡辞让,好疾恶之性辄生残贼、亡忠信,又若随顺好声色之性,乃生淫乱,亡礼义文理。此一番界定,其衡准在于,乃可能对将来之现实有破坏之效果。若纠察破坏效果之实现的可能,其实际的根柢恰在吾人的生命无时无刻不没于对照、对反的关系之中。对照对反,是以吾人之生命之外,亦认识到别有其他生命的存在,吾人的此生命有其所欲,其他的生命亦复有其所欲,而现实界的物事之资源,在一定情境下乃是有限,辄以无限之所欲面对有限之物事,必将有破坏的功效发生。以是故,荀学言“性伪”,纵是以“性恶”为根柢,但其由“性恶”乃如何可能转出“性伪”之说,后来各家多有疑惑。唐君毅先生云“对较反照”。乃是以“性”若单言,直无恶可说,只是与辞让、礼义之事结成一对较反照的关系,才能见“性恶”。而其更沉潜的意思,其实是将辞让礼义界定为一理想面的物事。而以荀子由客观经验所抽出的种种人性恶之表现为现实面的物事。故理想面与现实面的对较对反之落差,以为“唯人愈有理想,乃愈欲转化现实,愈见现实之惰性之强,而若愈与理想成对较相对反;人遂愈本其理想,以判断此未转化之现实,为不合理想中之善,为不善而恶者”。⑧此地唐先生欲为荀子的性恶论作某种意义的“平反”,以荀子其实未尝云“性恶”之旨,只是因荀学预先已挺立一善的理想故,有对较对反之落差乃有“性恶”成立之理由。但吾人看唐先生之将“性”与“礼义”的对较之关系作为辨析荀子之所以言性恶的根柢之原因,此是唐先生突出的见地与可以允称为妥帖的方面者。吾人云将性与礼义置于对较关系中是一思想的突破之贡献,但惟将对较关系限于性与礼义的面上讲,则恐有些局限。“性”是人之性,“礼义”是人之礼义。若宇宙间惟一人存在,则此人之性盖可以作无数种可能之定义,另,人之礼义其实是人群之礼义,儒家的所谓“人伦日用”其实说的便是人与人之际在平时的生活点滴中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及社会秩序。故所谓对较对反,纵是云理想与现实之比照或性与礼义之比照,其基本的底线皆不可能逾出于人伦关系中所言之对较对反关系,而所谓善与恶其实是基于此彼此牵连、彼此作用的前提下去讲论。善是可能与实际的予人以利,乃定义为善,恶是可能与实际的予人以害,乃定义为恶。荀子之定义性恶,即在于随顺好利、好疾恶、好声色之性,乃可能或实际产生争夺生、辞让亡,残贼生、忠信亡,淫乱生、礼义文理亡的恶果,故定义人的“性恶”之旨。但“性伪”何以能够实现,《荀子·性恶》篇只是描画了性伪的事实,而未尝给出“性伪”之所以可能的依据,即如其《性恶篇第二十三》云:“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又曰:“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孰,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此二则说话其实皆有三层肌理,一层肌理是言饥欲饱、寒欲暖、劳欲休及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乃是人的真实之性情,此说法在《孟子·尽心下》里其实有“口之于昧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有可以对应比照者,言的是同样的天然之人性的各个方面之表现,只是荀子予此般的人性以性恶的论定,而孟子则根本未尝就此面的人性作任何善恶面的分断,只是表达了“君子不谓其性也”这样有一定价值偏向的论断。欲饱、欲暖、欲休、愿厚、愿美、愿广、愿富、愿贵,作为一现实之人性,仅就其自身来看并无什么恶意可讲,但荀子定义其为“恶”,其实是预见到若随顺此性条贯下去,辄将可能造成一与辞让、礼义的一种紧张、对反之关系,亦即是说,随顺其性则辞让礼义亡,这里的“辞让礼义亡”即意味着一种良好和通的社会之秩序将全盘打乱,具体的表现则在于人与人之间互相征伐、互生残贼的一些犯分乱理之行为。故只是就“性”自身讲,或可云无善无恶,但其将可能带来破坏性的恶面之效果,乃定义其为“性恶”也。第二层肌理是言,饥而不敢先食,劳而不敢求息,子让父,弟让兄,子代父,弟代兄,这是一层所谓“辞让礼义”的表现。
所谓对较对反之关系,即在荀子的哲学构造里已有显明之设置。若饥与饱、寒与暖、劳与休、父与子、兄与弟、薄与厚、恶与美、狭与广、贫与富、贱与贵,能看到此一层算是洞透了荀学隐而未显的整体格局。但是对较对反,乃是根柢于人伦日用的吾人之生命与彼之生命之关系整体去看,亦恰是将此对较对反之关系格局,落定于人伦日用面之真实的生活里去照察,才能见到荀学里周遍可见的功利义之重要。所谓“功利”,是以利与害的结果为衡准。其果不利于人,谓之“恶”或“害”,其果利于人,则谓之“善”或“义”。故荀子以为性与礼义是一恶与善之对反,其实是蓄涵着这样的计较在里面:此礼义面之“善”其实是“果善”,乃别于孟子系所云的“本善”或谓之“因善”。但从性到礼义之即恶而向善的发展之过程,何以要定义为“伪”呢?其实是以扭曲,而非随顺自家的本性,去做事情乃得。照荀子的原话,这一扭曲荀子唤为“悖”,所谓“反于性而悖于情”、“辞让则悖于情性”。正以此扭曲之根柢故,便非是随顺着说,乃是悖逆着说,此是作为“伪”的十分重要的一层意思。另外,性之向礼义面的演绎与过渡,即是由恶向善的进化,这样看起来即是从现实面向理想面转化的形式之表现,恐是“伪”的光可鉴人的另一层之意思。但吾人云,返到“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句,其实是言明性恶为根柢者,善为终极者,由恶而趋向善便是“伪”的作为。但吾人需要继续地沉潜去追问,“伪”是如何需要且是必须的,亦即是说,为什么需要而且必须由恶的方面向善的方面去发展去突进?此是在荀子的论证系统里边所可能欠缺的一环。这便牵涉到对较对反之关系,乃是植根于人伦面的互相关系去讲论并以之为基础。吾人之生命,系有智慧之生命,此智慧之生命,反过来,盖能够感知其利,亦能感知其害:感知其利之来自于其他之生命,感知其害亦来自于其他之生命,反过来,亦能感知吾人此生命之行为的结果可能将利于其他之生命,亦可能将害于其他之生命。易言之,利害的结果之实现,非需要完完全全落实于现实界的争夺、倾轧、毁坏、残贼而导致辞让不存、忠义不在,及礼义文理亡;对利害的计较,其实是涵蓄于吾人此生命的思维界自身之中。涵蓄于此思维世界中的此计较功能的思维活动,吾人唤其“计较心”。“计较心”的一大能事,非是真的要去做要去行,要有切实的利害之效果端于眼前才叫“见利害”。其实是未曾去做亦未曾去行,即预见到自己的可能的将来之行为,若运施于实际之行动界,乃可能会遭遇的利或害之行为的果实之反馈。譬如,后来的水心之主物一系云“弓矢须从的”说,盖其实是涵了此预见性的计较心在,即射箭是向着靶标的方向去,此叫“从的”,但吾人射出此箭时并不会不作瞄准便信意地射出去,乃是审慎再三地去预见自己的瞄准行为究竟能否击中靶标而最后定夺。故,后一层意思的表现,其实是“从的”的真实面之表现。以是,“计较心”是拟议的计较心,是智慧的计较心。将此拟议的计较心及智慧的计较心,条贯于荀子所云的“何以有伪”的作为之成因的剖析,乃可有清澈透明之文理可以见到。欲饱、欲暖、欲休、愿厚、愿美、愿广、愿富、愿贵,是吾人的本性之真实,但吾人此本性之真实,何以最后未尝能随顺其性而全面地显现出来,而是作扭曲变成了“见长而不敢先食、劳而不敢求息”,呈现父与子、兄与弟间之互相礼让及父与子、兄与弟间之互相替代的情形,皆是以此拟议及智慧的计较心故。即,预示到若只是随顺吾人生命中本来之性去作为,则恐引来征伐,引来残贼,引来道德之批判,引来伦理之唾弃,反过来未尝利于吾人此生命自身的发展。以吾人之生命的发展为有长远的未来计,故须将吾人的本性不得不作收缩,或作涵蓄,或作扭曲。如是,辄荀学的“化性起伪”之推理系统与工夫系统,乃得合理地建立。
注释:
①《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8页。
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34-435页。
③《荀子集解》,第176-177页。
④《荀子集解》,第317页。
⑤《荀子集解》,第48-49页。
⑥《荀子集解》,第415-416页。
⑦《荀子集解》,第419-420页。
⑧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