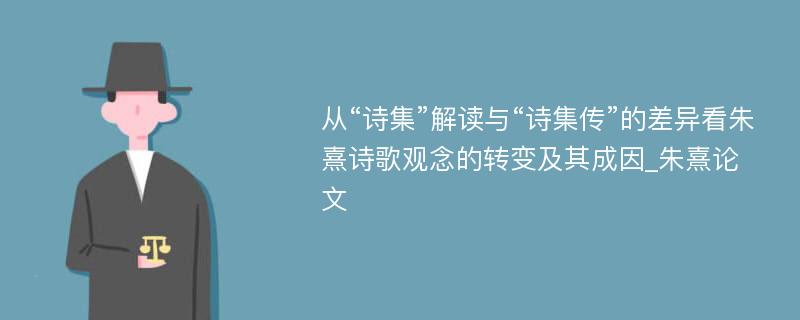
从《诗集解》和《诗集传》诗旨差异看朱熹《诗》学观念的转变及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集论文,朱熹论文,差异论文,观念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2)03-0096-05
朱熹是封建社会后期学问最广博、影响最深远的学者,他一生著述甚丰,其于经学,用力最勤者,首推《四书》,其次即为《诗经》。朱熹注释《诗经》是一件旷日持久的工作,乾道九年(1173年)所注《诗集解》是其注释《诗经》的第一稿,由于对《诗集解》颇为不满,朱熹不断地对其进行修改。今日所见《诗集传》当是朱熹晚年《诗》学研究的论断。朱熹为什么反复修改《诗集解》?是诗无达诂呢,还是朱熹注《诗》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
一
《诗集解》虽然早已亡佚,我们却可以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中见其概貌。在考察《诗集解》和《诗集传》所定诗旨的异同时,不得不提到《诗小序》,以做参照。
1.《诗集解》和《诗集传》诗旨相同例
(1)《诗集解》和《诗集传》皆从《小序》说。《周南·螽斯》,《小序》曰:“《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诗集解》曰:“螽斯聚处合一而卵育繁多,故以为不妒忌而子孙众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妒忌也,或曰古人精察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妒忌也。”《诗集传》曰:“后妃不妒忌而子孙众多,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前后稿所论《诗》旨皆从《小序》说。
(2)《诗集解》补释《小序》,《诗集传》基本从《小序》。《周颂·清庙》,《小序》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诗集解》曰:“《书大传》曰:‘周公升歌《清庙》,苟在庙中尝见文王者,然如复见文王焉。’”用《书大传》补释《小序》。《诗集传》曰:“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乐歌。”基本从《小序》。
(3)《诗集解》从《小序》说,《诗集传》以史补释《小序》。《豳风·鸱鸮》,《小序》曰:“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诗集解》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虽已灭之,然成王之疑未释,则乱未弭也。故周公作《鸱鸮》之诗以遗王,而告以王业艰难不忍毁坏之意,所以为救乱也。”基本同《小序》。《诗集传》曰:“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鲜、蔡叔度监于纣子武庚之国,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诛之,而成王犹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诗以贻王。”以史实补释《小序》。此类并不多见。
(4)《诗集解》和《诗集传》均依《诗》自立新说。此例在《诗集解》中亦不多见。如《邶风·谷风》,《小序》云:“《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诗集解》云:“此诗皆女怨之辞。”从文学角度解《诗》。《诗集传》云:“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进一步从文学角度解释诗意。
2.《诗集解》和《诗集传》诗旨不同例
(1)《诗集解》从《小序》说,《诗集传》从诗本身自立新意。《邶风·击鼓》,《小序》曰:“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诗集解》曰:“按《左传》州吁与宋、陈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出师不为久,而卫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众叛亲离,莫肯为之用尔。”对《小序》进行阐释。《诗集传》曰:“卫人从军者自言其所为,因言卫国之民或役土工于国,或筑城于漕,而我独南行,有锋镝死亡之忧,危苦尤甚也。”依《诗》自立新意。
(2)《诗集解》对《小序》提出一些疑问,《诗集传》依诗自立新说。《卫风·伯兮》,《小序》曰:“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返焉。”《诗集解》曰:“先儒以此诗疑此时作,然无明文可考。”对《小序》所作时间提出了怀疑,但不能径立新说。《诗集传》曰:“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是诗,言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执殳而为王前驱也。”依《诗》认为此为妇人思夫之诗。
(3)《诗集解》从《小序》说,《诗集传》定为“淫诗”。《郑风·遵大路》,《小序》云:“《遵大路》,思君子也。庄公失道,君子去国,国人思望焉。”《诗集解》云:“君子去其国,国人思而望之,于其循大路而去也,揽持其祛以留之曰: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遽绝也。”主《小序》而言《诗》。《诗集传》云:“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揽其祛而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遽绝也。”认为是淫妇留其所与私者之诗,与《小序》君子说截然不同。
(4)《诗集解》言刺某王,而《诗集传》或去掉刺意,或改刺他人。《小雅·小旻》,《小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诗集解》曰:“此诗刺王惑于邪谋,不能断以从善,将致乱也。”《诗集传》曰:“大夫以王惑于邪谋,不能断以从善而作此诗。”去掉“刺”意。《唐风·采苓》,《小序》曰:“《采苓》,刺晋献公也。”《诗集解》云:“献公好听谗。观骊姬谮杀太子及逐群公子之事可见也。”仍然认为是刺献公之诗。《诗集传》云:“此刺听谗之诗。”去掉所刺之人,改为刺听谗之诗。
从《诗集解》和《诗集传》所定诗旨的对比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诗集解》基本上尊《小序》说。
(2)《诗集传》中有一部分《诗》的解释仍然尊《小序》,一类是朱熹认为有史实根据者,如《豳风·鸱鸮》,一类为《小序》所言的“美”诗,如《螽斯》、《闵予小子》。对带有刺意的《小序》进行了改造。
(3)在《诗集传》中,朱熹把很多诗篇作为文学作品来解读,并提出了淫诗说。
二
《诗集解》和《诗集传》所论《诗》旨有很大差异,这是由于朱熹的《诗》学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那么,朱熹的《诗》学观有哪些转变,为什么会有如此转变呢?
首先,宋代《诗经》研究领域关于《小序》守、废问题的论争影响了朱熹的解《诗》思想。北宋庆历以来,在《诗经》研究领域出现了疑《序》废《序》之风,欧阳修和苏辙拉开了宋人疑《序》之风的序幕,同时,王安石、程颐等人则极力维护《诗序》的权威地位。南渡以后,动乱的社会现实,进一步降低了人们对圣贤经典的盲目崇拜心理,废序派对《小序》的攻击更为猛烈,南宋郑樵作《诗辨妄》,力诋《小序》,不遗余力;王质作《诗总闻》废弃《小序》而言《诗》。与此同时,守《序》派对《诗序》予以坚决捍卫,如范处义作《诗补传》,极力维护《小序》的权威。这样,朱熹之前,在《诗经》研究领域实际上存在着尊《序》与废《序》两条路线,这也使朱熹在说《诗》中面临着两种选择。朱熹写作《诗集解》当是受守《序》派的影响,以后作《诗集传》当是废《序》派影响所致。朱熹后来提到自己最初的《诗》学思想时说:“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从束景南说当去掉“到”字),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朱子语类》卷八十)朱熹写《诗集解》时心里就已很矛盾:既怀疑《小序》说,又不敢废《小序》,因此基本尊《小序》。在写完《诗集解》后,其解《诗》思想又向废《序》一派倾斜。他说:“《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同上)因此,朱熹也决定对刚刚成稿的《诗集解》进行修改。
朱熹对《小序》的怀疑态度,必然要受到守《序》派的坚决反对。当时守序派领袖吕祖谦便多次同朱熹以《小序》为焦点发生热烈的争论,由于朱熹坚定地认为圣人所放为“郑声”,而《诗经》所存为郑诗,为淫乱之诗,因此更坚定了他废《序》言《诗》的决心。在淳熙四年他再次修定《诗集解》,并在十月正式序定了修改过的《诗集解》,而朱熹对此仍然很不满意,他在淳熙五年夏给吕祖谦信中提到这次修订时说:“大抵《小序》尽出后人臆度,若不脱此窠臼,终无缘得正当也。去年略修旧说,订正为多,向恨未能尽去,得失相半,不成完书耳。”(朱熹《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书七》)此后,朱熹仍然不断对其进行修改。有人认为朱熹是由于不满吕祖谦太尊《小序》,所以才主张序弃《小序》而言《诗》,如清人朱鹤龄说:“朱子以其(吕祖谦)祖述《小序》,多所不满,郑卫淫奔之说,多用渔仲。”(朱鹤龄《诗经通义》)我认为,朱熹自变前说可能与吕祖谦有一些关系,但却不是主要的,废《序》言《诗》突出地表现了朱熹唯真理是求的精神,并不是刻意和某人赌气争胜。这一方面是受宋代《诗经》研究领域废序言《诗》风气的影响,一方面则是看出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
从文学角度言《诗》,是朱熹《诗》学观念的又一重大转变。《诗经》本是文学作品。汉代人把《诗》奉为经,汉唐的《诗经》研究多着眼于《诗经》的政教意义。从北宋中叶以后,很多《诗经》研究者注重从文学角度看诗,对前人《诗》注博览无遗的朱熹,或许从中受到某些启发而改变自己的《诗》学观。另外,南宋市民文艺已经相当发达,以言情为主的词盛行于士人学子之口,这也促使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质作出更多的思考。更重要的是,朱熹本是个文学家,朱熹现存《诗》就有10卷,1200余首。因此,朱熹能够更多地从文学角度理解《诗经》。《诗集解》已偶有部分《诗》从文学角度进行解释,在《诗集传》中,这样的解释更是随处可见。朱熹在平日教学中也常要弟子把《诗经》当成文章看:“义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风》,他只是如此说出来,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后,皆有次序。而今人费尽气力去做后,尚做得不好。”(《朱子语类》卷八十)“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的诗看。”(同上)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朱熹从文学角度解释《诗经》是很不彻底的,一方面,《诗集传》仍然采取《小序》说,另一方面,朱熹把一部分男女情诗说成是“淫诗”。朱熹为什么不把从文学角度说《诗》贯彻始终呢?这正是朱熹从理学角度说《诗》的必然结果。
朱熹《诗集传》对《诗集解》的改造是不彻底的,《诗集传》仍然保留了很多《小序》说,这些诗又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是朱熹认为有史实根据的,如《鸱鸮》一类,另一类即为“美诗”,如《螽斯》一类。朱熹对“美”诗《小序》说的保留,说明他反对《小序》美刺说主要是针对“刺”而言。朱熹为什么在《诗集传》中保留了《诗集解》中带有“美”旨的《小序》说,而对带有“刺”意尤其是“刺王”之意的《小序》进行了改造呢?这主要是他从理学角度解释《诗经》的缘故。宋代社会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宋代理学家把“三纲五常”纳入理学范畴,认为“夫所谓纲者,犹网之有纲也;所谓纪者,犹丝之有纪也。网无纲则不能以自张,丝无纪则不能以自理。”(《朱子文集·庚子应诏封事》)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对人们进行“三纲五常”的道德教育,社会关系才能理顺,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小序》所言刺诗,一部分转为他意,一部分去掉刺意,这正是“三纲五常”思想在解《诗》中的具体体现。因为《小序》所言“刺”诗,大多是刺某君、刺某王,这和宋代忠君的思想是有深刻矛盾的。因此,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必然要对这一部分“刺”诗进行合乎理学思想的改造,即去掉“刺”意,以合乎忠君思想。
朱熹在《诗集传》中已经把《诗经》的很多诗篇作为文学作品来解读,看出了《诗经》中存在着反映男女情思的作品。朱熹对其中的一部分直指为情诗,如释《陈风·东门之池》:“此亦男女会遇之词。”对另一部分则斥为“淫诗”,如:《郑风·山有扶苏》。朱熹所划分的情诗和淫诗,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不同,这正说明朱熹对“淫诗”与情诗的划分标准具有不确定性。这当是朱熹从文学角度言诗和从理学角度言诗的必然结果。从文学角度言《诗》,朱熹必然要发现《诗经》中的情诗,而从理学角度看《诗》,这些情诗又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不符,因此,朱熹把一部分情诗,特别女求男的郑诗,划为“淫诗”。为了支持他所提出的“淫诗说”,朱熹建构了完整的“劝善惩恶”说的理论,并进而对孔子删诗说和“思无邪”理论进行重新理解和改造,使《诗》之为经与《诗》之存在淫诗这一矛盾得到了完满的解决,但《诗集传》中却暴露出情诗与淫诗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诗集传》中是无法调和的。
总之,《诗集解》和《诗集传》所论诗旨的差异,反映了朱熹解《诗》思想的巨大变化,勾勒出朱熹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轨迹。《诗集传》代表了两宋《诗》学发展的新方向,预示了《诗经》研究向文学领域的有力渗透,赋予了《诗》学以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内容,因而体现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