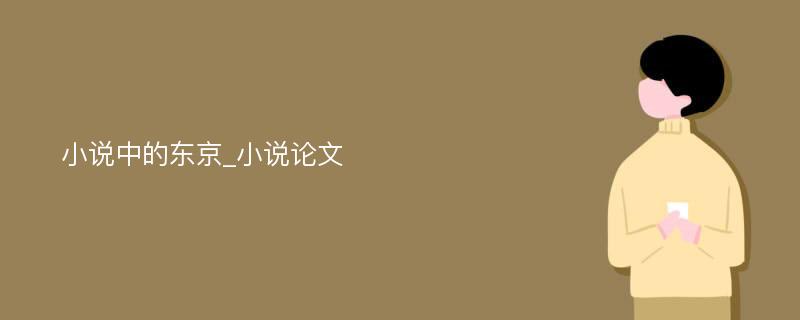
话本小说中的“东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本论文,东京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京”是宋元话本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完整呈现都市风貌的城市。作为话本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东京的作用与其特定的历史地位及都市特性联系在一起;而其都市风貌在话本小说中的演化,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宋元时期文学变迁的进程。在宋元话本小说中,以东京为背景或有关的作品自成系列,其中如《张生彩鸾灯记》、《红白蜘蛛》、《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简贴和尚》、《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金鳗记》、《勘靴儿》、《张主管志诚脱奇祸》、《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均为话本小说名篇,颇受学界关注。有关东京的研究论著甚多,如周宝珠的《宋代东京研究》①、刘春迎的《北宋东京城研究》②等;涉及话本小说与东京的论著也时有刊布,如庞德渐的《从话本及拟话本所见之宋代两京市民生活》③、葛永海的《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④,皆多精见卓识。但就小说所反映的东京都市文化面貌与地域文化特征及其在小说史中的意义而言,仍有可以申论的空间,本文即以宋元话本为主,兼与其他时期和体式小说中的同类描写比较,梳理“东京小说”的基本特点与价值。
一、“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都市特性与话本小说的产生
今天的开封是一座古城,历史上有过很多称谓,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序中,反复突出的是其“京师”的意义,也就是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受“开封府”支配的。《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开篇道:“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⑤这里包括了“东京”、“汴梁”、“开封府”三种地名,表明了“东京”不同层面的政治含义⑥。类似这样的叙述在其他的话本小说中也有,后世的小说也继承了这种写法,如《三遂平妖传》第一回:
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⑦
说话艺人笼而统之使用“东京”、“汴梁”、“开封府”,正揭示出“东京”作为一个都城与区域并不单一的意义。
对话本小说的产生与传播来说,东京首先是一个有着发达商品经济的都市,正是在繁荣的商业背景下,说话艺术蓬勃发展起来,也注定了话本小说商业化的文学品格。
《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有关勾栏瓦子为研究宋代俗文学的人所熟知: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⑧
据《史弘肇传》(《古今小说》卷十五题《史弘肇龙虎君臣会》)所叙,后周太祖郭威“因在东京不如意,曾扑了潘八娘子钗子。潘八娘子看见他异相,认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养在家中。自好了,因去瓦里看,杀了勾栏里的弟子,连夜逃走”。这或许是将宋以后兴盛的勾栏瓦子移植于五代时,或者五代时东京已有这样的场所。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叙包大尹差人捉盗墓贼朱真,“当时搜捉朱真不见,却在桑家瓦里看耍”。《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叙赵正“再入城里,去桑家瓦里,闲走一回,买酒买点心吃了,走出瓦子外面来”。这些描写都表明勾栏瓦子与市民生活关系的密切。
话本小说就是在勾栏瓦子中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学生成与传播的环境。我们在早期的话本小说中,还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说法:“这话本是京师老郎留传”(前引《史弘肇传》)、“原系京师老郎传流,至今编入野史”(《勘靴儿》,《醒世恒言》卷十三题《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京师老郎流传至今”(《拍案惊奇》卷二十一《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入话《阴骘积善》)、“这一回书,乃京师老郎传留,原名为《灵狐三束草》”(《拍案惊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这里所谓的“京师老郎”指的就是活跃于勾栏瓦子的说话艺人。而产生于上述环境的话本小说具有如下特点:它是一种商品化、表演性、娱乐性的文学活动;它的题材与人物往往为普通市民所熟悉,思想情感往往也为他们所认同;在艺术表现手法与风格上,迎合普通市民的欣赏习惯。
最简单而鲜明的事实是,东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社会阶层复杂的特大城市,不但造成了大批的文化消费群体,也为话本小说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大量的市民开始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所谓市民,是一个以工商业者为主的、庞杂的社会群体。由于古代城市的多重特性,它还包括在城市里长期居住的普通官员、文人、军人以及游民等。而话本小说描写了各色人等,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在书写角度与情感倾向上的重大突破。
《杨温拦路虎传》被认为是“现存宋代小说家话本中最接近原貌的一个标本”⑨,作品描写的是将门之后、“东京人”杨温的故事。他因去东岳烧香,病在客店中,无盘缠回京。“明日是岳帝生辰,你每是东京人,何不去做些杂手艺?明日也去朝神,也叫我那相识们大家周全你,撰二三十贯钱归去。”可见在一般人看来,东京人谋生本领强,精通各种“杂手艺”。
《错斩崔宁》入话中讲述了进京赶考的少年举子魏鹏举的故事。例行的科举考试吸引了大量外地读书人到东京来,他们是“东京”十分活跃的流动人口,也是最“有故事”的一个群体,屡为说话艺人称道。
《金鳗记》(《警世通言》卷二十题《计押番金鳗产祸》)的主人公计安在“北司官厅下做个押番”,属于禁军中略高于普通士兵的军士(“班长”)。
据《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记载:
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⑩
显然,“界身”是一以金银和高档品为主的市场。而《张主管志诚脱奇祸》所写正是“话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子里,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
话本小说中还描写了东京的各种女性,如《快嘴李翠莲记》的主人公李翠莲是东京李员外的独生女。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女孩儿高声自称:“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一派市井女孩无拘无束的态度。
《勘靴儿》描写了宫妃与贵夫人。
《皂角林大王假形》叙东京人赵再理,授得广州新会县知县。在任期间,其东京家室却为“皂角林大王”所霸占。
《简贴和尚》描写了一个“淫僧”骗占外出公差官员之妻的故事。从性质上与《皂角林大王假形》有相似之处,而从人物身份上看,此种“淫僧”,也另有现实背景。如《清异录》卷上记载:
相国寺星辰院比丘澄晖,以艳倡为妻,每醉点胸曰:“二四阿罗,烟粉释迦。”又:“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快活风流,光前绝后。(11)
如此等等,东京不同阶层、特别是普通市民在话本小说中都有所描写,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新的人物画廊。而这些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如《郑节使立功神臂弓》里有这样的描写:
只听得街上锣声响,一个小节级同个茶酒保,把着团书来请张员外团社。原来大张员外在日,起这个社会,朋友十人,近来死了一两人,不成社会。如今这几位小员外,学前辈做作,约十个朋友起社。却是二月半,便来团社。
市民们结成各种性质的社团,即是都市人际关系的一个新特点。
东京不仅是一个商业都会,更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这一特殊的政治地位,也为上层与下层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
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下曾载仁宗一事:
又一夜,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呜呼,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12)
且不说事之真伪,但它形象地显示出皇室与市井酒楼同处一个城市的情形。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辨证类》中说:“小说起于仁宗朝,盖时太平日久,国家闲暇,日欲选一奇怪之事以娱之。”虽然这一说法还有待考证,但皇室与市井有可能产生某种联系,自是情理之中的事(13)。仁宗曾率后妃、百官驾御宣德门看民间伎艺表演戏,司马光犯颜直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嘉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上)》称:
臣窃闻今月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各进技艺,赐与银绢,内有妇人相扑者,亦被赏賚。臣愚,窃以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赢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陛下圣德温恭,动遵仪典,而所司巧佞,妄献奇技,以污渎聪明。窃恐取讥四远。愚臣区区,实所重惜,若旧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诏有司,严加禁约,令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若今次上元,始预百戏之列,即乞取勘管勾臣僚,因何致在籍中,或有臣僚援引奏闻,因此宣召者,并重行谴责,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惧,不为导上为非礼也。(14)
这从反面印证了上层与下层的“文化交流”。
从话本小说看,帝王、包括本朝帝王,也是小说家热衷讲述的。而他们在讲述帝王的故事时,有时也有意识地将其与东京的都市背景联系在一起,这不但使话本小说带有了一定的政治性,也使得话本小说中的帝王形象更加具有一种亲和性,有时则反映出底层市民对皇权的一种戏谑。
由于宋元话本小说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源于下层社会也主要在下层社会传播的通俗文学,其中的描写也以普通民众熟悉的背景为主,有关朝廷的描写是有限的,如我们在宋代士大夫诗词中常看到的“御街行”书写,在话本小说中就不多见。《东京梦华录》卷二《御街》记载:
坊巷御街,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15)
这表明御街对普通人的活动、通行是有所限制的,这样的场所,很少作为小说的场景被描写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东京的多重特性,为话本小说的发展创造了各种有利条件,也使话本小说在吸纳不同方面营养后,成为一种很有包容性、也很有前途的文体。
二、“东京”在话本小说叙事中的时空意义
在话本小说中,东京是具体情节展开的背景。不言而喻,作为背景的东京必然与一个个特定的时空相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建立在此一时空背景有助于小说情节的安排与人物的描写基础上的。
与乡村小桥流水的田园风光不同,城市的住所、街坊是都市的日常生活场景,因而在话本小说中有许多描写。比如《简贴和尚》这样描写:
去枣槊巷口,一个小小底茶坊,开茶坊人唤做王二。当日茶市方罢,相是日中,只见一个官人入来。……
入来茶坊里坐下。开茶坊的王二拿着茶盏,进前唱喏奉茶。那官人接茶吃罢,看着王二道:“少借这里等个人。”王二道:“不妨。”……
那官人指着枣槊巷里第四家,问僧儿:“认得这人家么?”僧儿道:“认得,那里是皇甫殿直家里。殿直押衣袄上边,方才回家。”
巷口茶坊、巷里人家,正是本篇故事展开的特殊场景。有了这样的场景,简贴和尚才可能近距离的窥探良家妇女,并借助行走市井的小商贩,实现其阴谋。
实际上,客栈、茶肆、酒楼等人来人往的场所,有利于小说家安排人物的交流,而这些场所便成为引发情节冲突的常见空间。《赵旭遇仁宗传》(《古今小说》卷十一题《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叙成都书生赵旭来到东京:
遂入城中观看景致。只见楼台锦绣,人物繁华,正是龙虎风云之地。行到状元坊,寻个客店安歇,守待试期。……店对过有座茶坊,与店中朋友同会茶之间,赵旭见案上有诗牌,遂取笔去那粉壁上写下词一首。词云:
足蹑云梯,手攀仙桂,姓名己在登科内。马前喝道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队。
宴罢归来,醉游街市,此时方显男儿志。修书急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
后因狂傲,赵旭为仁宗黜落;失意时,店小二建议:“秀才,你今如此穷窘,何不去街市上茶坊酒店中吹笛?觅讨些钱物,也可度日。”“茶坊酒店”既是他谋生之所,也是他时来运转的关键。仁宗偶然也到状元坊茶肆吃茶,看到了赵旭的题词,怜才提掇,使其得以衣锦还乡。让皇帝与一个普通书生有缘相会的场所,只有茶坊这种空间才有一定的可能性,也比较贴近普通市民的想像。
在东京市民聚集的场所中,最具地标性和热闹的樊楼、相国寺和金明池,这些地方更是小说家热衷描写的重要场景,也构成了“东京小说”的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先看樊楼,樊楼又名丰乐楼,有关东京的文献中多有叙及,如《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
白礬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初开数日,每先到者赏金旗。……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16)
而小说中,《赵旭遇仁宗传》里有一首《鹧鸪天》词,也是咏赞樊楼的:
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
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栏杆彩画檐。
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酒店,写入话本小说,自然易为当时的接受者所熟悉而乐闻,《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更将其作为全篇最重要的场景。周胜仙与范二郎的初会在樊楼,她死而复生后来找范二郎,也是在樊楼。
不但如此,樊楼也与帝王联系在了一起。《宣和遗事》后集曰:
故宣和数年之间,朝廷荡无纲纪。刘屏山有诗曰:“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樊楼乃是丰乐楼之异名,上有御座,徽宗时与师师宴饮于此,士民皆不敢登楼。(17)
樊楼中居然有“御座”,不知出于民间传说,还是确有实情。前引《赵伯茶肆遇仁宗》也描写了仁宗出入于樊楼。同样说明了这种联系。
正是由于樊楼的商业地位的重要以及在民间叙事中与帝王联系在一起,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东京的一个符号。《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古今小说》卷二十四题《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便将故国之思与东京、与樊楼紧密联系到了一起。这一点应该是话本小说家的有意安排和渲染。在这篇小说的本事《夷坚丁志》卷九的《太原意娘》中,就没有这方面的描写。
再看相国寺。这同样是东京的一个重要场所。自唐代以来,就是开封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寺庙,至北宋,更成为东京的一个盛大的商业中心。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载:“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18)宋王得臣《麈史》卷下也记载:“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因号相国寺为‘破赃所’。”(19)《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内百姓交易》云:“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百姓交易。”无论民俗信仰活动,还是商贸、娱乐,东京市民都经常光顾相国寺,因而也就成为小说情节展开的天然场景(20)。《简贴和尚》在淫僧使阴险手段离间皇甫夫妻并如愿占有皇甫妻后写道:
逡巡过了一年,当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从休了浑家,在家中无好况……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两人,双双地上本州大相国寺里烧香。我今年却独自一个,不知我浑家那里去?”簌地两行泪下,闷闷不已,只得勉强着一领紫罗衫,手里把着银香盒,来大相国寺里烧香。到寺中烧香了恰待出寺门,只见一个官人领着一个妇女。看那官人时,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领着的妇女,却便是他浑家。当时丈夫看着浑家,浑家又觑着丈夫,两个四目相视,只是不敢言语。
一般而言,在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21),身份地位不同,生活方式有别,人生轨迹并不易交汇重叠,而相国寺却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因此,《简贴和尚》便合情合理地将相国寺作为了绾结情节、收束头绪的绝佳场景。
又如《张生彩鸾灯传》张生偶拾一红绡帕子,上有细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请待来年正月十五夜于相篮后门一会,车前有鸳鸯灯是也。”此“相篮”即相国寺,次年,张生“将近元宵,思赴去年之约。乃于十四日晚,候于相篮后门,果见车一辆,灯挂只鸳鸯,呵卫甚众。生惊喜无措,无因问答。”相国寺既是一个容易找到的地方,又是一个人山人海、不易被他人发现的地方,将其作为幽会地点,是十分合适的。
写到相国寺的宋元话本小说还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等,后世与宋代东京有关的话本小说如“三言”中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明悟禅师赶五戒》、《佛印师四调琴娘》,“二拍”中的《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大尉戏宫馆客》等,也都涉及了相国寺。
复看金明池。这是一处位于东京城外的自然景观(22),据《东京梦华录》卷七《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记载:
池在顺天门外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面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往日旋以彩幄,政和间用土木工造成矣。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河间云水戏龙屏风,不禁游人。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用瓦盆内掷头钱,关扑钱物、衣服、动使。游人还往,荷盖相望。(23)
话本小说中也有类似描写,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入话:“从来天子建都之处,人杰地灵,自然名山胜水,凑着赏心乐事。如唐朝便有个曲江池,宋朝,便有个金明池,都有四时美景,倾城士女王孙,佳人才子,往来游玩。天子也不时驾临,与民同乐。”这样一个游人如织的场所,理所当然的也成为小说家场景安排的绝佳选择。如《金鳗记》的开篇,描写计押番在钓得一条金明池“池掌”金鳗,并招至灭门惨祸;《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开篇叙“金明池游人赏玩作乐。那范二郎因去游赏,见佳人才子如蚁。行到了茶坊里来,看见一个女孩儿”;《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开篇叙“当时清明节候……满城人都出去金明池游玩。张小员外也出去游玩”,都是由金明池展开情节的。而《警世通言》卷三十《金明池吴清逢爱爱》更是将金明池作为爱情故事的大背景。《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的创作时间虽无法确定,但它依据的本事为《夷坚甲志》卷四《吴小员外》,很可能也有早期说话艺术的基础。
一个地区的民俗生活,还具有时间性。东京系列的话本小说与时间相关的描写,主要围绕元宵、清明、中秋等节庆活动展开,因为节庆活动也是人物交流最密切的时候,为情节冲突的展开提供了一种可能。
李清照的名词《永遇乐》有“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句,说明北宋东京元宵节最为隆重。《大宋宣和遗事》中从徽宗的喜乐,描写了东京元宵的盛况:
且说世人遇这四季,尚能及时行乐;何况徽宗是个风流快活的官家,目见帝都景致,怎不追欢取乐。皇都最贵,帝里偏雄:皇都最贵,三年一度拜南郊;帝里偏雄,一年正月十五夜。州里底唤做山棚,内前的唤做鳌山;从腊月初一日直点灯到宣和六年正月十五日夜……
东京大内前,有五座门:曰东华门,曰西华门,曰景龙门、曰神徽门,曰宣德门。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鳌山高灯,长一十六丈,阔二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长二十四丈;两下用金龙缠柱,每一个龙口里,点一盏灯,谓之“双龙衔照”。中间着一个牌,长三丈六尺,阔二丈四尺,金书八个大字,写道:“宣和彩山,与民同乐。”彩山极是华丽:那采岭直趋禁阙春台,仰捧端门。梨园奏和乐之音,乐府进婆娑之舞。绛绡楼上,三千仙子捧宸京;红玉栏中,百万都民瞻圣表。(24)
《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戒指儿记》也铺陈了东京元宵的热闹景观: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时值正和二年上元令节,国家有旨赏庆元宵。鳌山架起,满地华灯。笙箫社火,罗鼓喧天。禁门不闭,内外往来。人人都到五凤楼前,端门之下,插金花,赏御酒,国家与民同乐。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日止,万姓歌欢,军民同乐,便是至穷至苦的人家,也是欢娱取乐。怎见得?有只词儿,名《瑞鹤仙》,单道着上元佳景:
瑞烟浮禁苑。正绛阙春回,新正方半。冰轮桂华满,溢花衢歌市,芙蓉开遍。龙楼两观,见银烛,星球灿烂。卷珠帘,尽日笙歌,盛集宝钗金钏。堪羡,绮罗丛里,兰麝香中,正宜游玩。风柔夜暖。花影乱,笑声喧。闹蛾儿满地,成团打块,簇着冠儿斗转。喜皇都,旧日风光,太平再见。(25)
正是由于元宵灯节的重要,小说家热衷将这种年节风俗与情节安排、人物刻画结合起来。如《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中有这样的描写:
当日时遇元宵,张胜道:“今日元宵夜,端门下放灯。”便问娘道:“儿子欲去看灯则个。”娘道:“孩儿,你许多时不行这条路,如今去端门看灯,从张员外门前过,又去惹是招非。”张胜道:“是人都去看灯,说道今年好灯,儿子去去便归,不从张员外门前过便了。”娘道:”要去看灯不妨,则是你自去看不得,同一个相识做伴去才好。”张胜道:“我与王二哥同去。”娘道:“你两个去看不妨,第一莫得吃酒,第二同去同回!”分付了,两个来端门下看灯。正撞着当时赐御酒,撒金钱,好热闹,王二哥道:“这里难看灯,一来我们身小力怯,着甚来由吃挨吃搅?不如去一处看,那里也抓缚着一座鳌山。”张胜间道:“在那里?”王二哥道:“你到不知,王招宣府里抓缚着小鳌山,今夜也放灯。”
作品开始的这一叙述,其实就是小说家为情节发展埋下的伏笔。
由于节庆活动往往在特定的场所进行,所以,东京小说中的时间因素与空间因素也常相互关联。如前引《张生彩鸾灯记》的情节,时间上元宵佳节,空间上则在相国寺。
时空背景对于小说家来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与东京有关的时空背景有时也成为作品的一种结构性要素。《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开篇叙东京秀才陈从善得授南雄巡检之职,满怀恐惧凄惶地离了东京。在经历了许多波折后,终于又“回到东京故乡”。在这篇作品中,东京是作品的一个叙事框架。依靠这一框架,作者将陈从善人生、为官的起点和终点完整地展现出来了。而《错认尸》(《警世通言》卷三十三题《乔彦杰一妾破家》)叙主人公往来于杭州、东京之间,则显示出了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也造成了叙事空间的流动。
三、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中“东京”描写的异同
东京在话本小说中,是具体情节展开的背景。反过来,诸多作品也构成了东京的整体形象。前两节所论话本小说中的人物与时空背景就是东京整体形象的反映。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由于不同体式的小说关注的角度有所不同,即使同样以东京为背景的小说,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把握话本小说的特点。
相对于娱乐化、商业化更强的话本小说而言,文言小说更接近史书传统,也就是所谓“野史”。而说话艺人也把熟悉文言小说如《太平广记》、《夷坚志》等,当成必备的修养。与此同时,文言小说也成为话本小说重要的题材来源。
应当说明的是,文言小说之所以能成为话本小说的题材来源,与文言小说本身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宋代文言小说尽管颇受非议,但有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即在题材上,文言小说的作者与时俱进,也描写了宋代城市生活。这种描写使得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具有了某种同步性。虽然唐代文言小说也较多地描写了当时的大都会(26),但由于作者身份与趣味的文人化,相关描写也带有这样的特点或局限性。而宋代文言小说有所不同,在市井社会发展的事实面前,文言小说家们表现出了更开放的态度与眼光。
在宋代文言小说中,有关东京的故事有不少。其中有些为话本小说采为本事,还有不少没有被袭用。如《李师师外传》对东京的描写,颇具现实性和政治性:
李师师者,汴京东二厢永庆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比长,色艺绝伦,遂名冠诸坊曲。
徽宗既即位,好事奢华,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绍述为名,劝帝复行青苗诸法,长安中粉饰为饶乐气象,市肆酒税,日计万缗;金玉缯帛,充溢府库。于是童贯、朱勔辈,复导以声色狗马宫室园囿之乐。凡海内奇花异石,搜采殆偏。筑离宫于汴城之北,名曰艮岳,帝般乐其中,久而厌之,更思微行为狭邪游……
暮夜,帝易服,杂内侍四十馀人中,出东华门二里许,至镇安坊。镇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余人,独与迪翔步而入。(27)
又如《夷坚志补》卷八《京师浴堂》:
宣和初,有官人参选,将诣吏部陈状,而起时太早,道上行人尚希,省门未开,姑往茶邸少憩。邸之中则浴堂也,厮役两三人,见其来失期,度其必村野官员乍游京华者。时方冬月,此客着褐裘,容体肥腯,遂设计图之。密掷皮条套其项,曳之入帘里,顿于地,气息垂绝,群恶夸指曰:“休论衣服,只这身肉,直几文钱。”以去晓尚遥,未即杀。少定,客以皮缚稍缓顿苏,欲窜,恐致迷路,迟疑间,忽闻大尹传呼,乃急趋而出,连称杀人。群恶出不意,殊荒窘,然犹矫情自若,曰:“官人害心风耶!”俄而大尹至,诉于马前,立遣贼曹收执,且悉发浴室之板验视,得三尸,犹未冷,盖昨夕所戕者。于是尽捕一家置于法,其脍人之肉,皆恶少年买去云。(28)
外地人“乍游京华”,不知深浅,有时直如羊入狼群。《京师浴堂》就展示了东京极为凶险的一面。
《夷坚甲志》卷八《京师异妇人》则化实为虚,为现实生活涂抹上怪异的色彩:
宣和中,京师士人元夕出游,至美美楼下,观者阗咽不可前。少驻步,见美妇人举措张皇,若有所失。问之,曰:“我逐队观灯,适遇人极隘,遂迷失侣,今无所归矣。”以言诱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为他人掠卖,不若与子归。”士人喜,即携手还舍。如是半年,嬖宠殊甚,亦无有人踪迹之者。(29)
这一段描写与上节所论话本小说中东京元宵场景如出一辙。而接下来的描写,则颇类传统志怪小说。士人之友认定此女“非人类”,而葆真宫王文卿法师也看出士人身上“妖气极浓”,并以朱书二符授之,降伏此妖。虽然情节有类一般志怪,但描写此女“张灯制衣,将旦不息”和开封府初以为法师用妖术取民女,遣狱吏逮王师下狱等细节,仍具有现实性。
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四《龚球记》叙京师无赖龚球遭报应故事:
时元夜灯火,车骑沸腾。球闲随一青毡车走。车中有一女人,自车后下,手把青囊,其去甚速。球逐之暗所。女人告曰:“我李太保家青衣也。售身之年,已过其期,彼不舍吾,又加苦焉。今夕吾伺其便走耳。若能容吾于室,愿为侍妾。”球喜,许之。(30)
但龚球却卷其财物而去,此女被拷打致死,而其鬼魂则向龚索命。
与宋元话本一样,涉及东京的文言小说有不少也把情节的时间节点放在了元宵,上面两篇是如此,其他如《夷坚志补》卷八《真珠族姬》叙真珠族姬被拐,也在“宣和六年正月望日,京师宣德门张灯”之际,正因为“贵近家皆设幄于门外,两庑观者亿万”,歹人才便于乘乱下手。又有《夷坚乙志》卷十五《京师酒肆》、《夷坚乙志》卷十六《赵令族》、《夷坚志补》卷十四《郭伦观灯》等,都在东京元夕的时空背景下展开世俗生活的描写。
由于有的文言小说为话本小说所袭用,两相对比,更可见彼此的相互关系。如洪迈《夷坚支景》卷三《王武功妻》,叙一僧人施展诡计,谋夺去某官员妻。《简帖和尚》故事与相颇相类,或即据此改编而成。在《王武功妻》中,涉及背景性描写十分简单:
京师人王武功,居韈柪巷。妻有美色。化缘僧过门,见而悦之。阴设挑致之策,而未得便。会王生将赴官淮上,与妻坐帘内,一外仆顶盒至前,云:“聪大师传信县君,相别有日,无以表意,漫奉此送路。”语讫即去。王夫妇亟启盒,乃肉茧百枚。剖其中,藏小金牌饼,重一钱,以为误也,复剖其他尽然。王作声叱妻曰:“我疑此秃朝夕往来于门,必有故,今果尔。”(31)
其中仅“京师”、“韈柪巷”略示地域背景。而正如前文所引,《简贴和尚》中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东京市坊特殊的背景与人物,给读者的印象是,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情节的展开才有充分的合理性。且看其中僧儿传书一段:
……等多时,只见一个男女托个盘儿,口中叫:“卖鹌鹑、馉馉饳饳儿!”官人把手打招,叫:“买馉饳儿。”僧儿见叫,托盘儿入茶坊内,放在桌上,将条篾篁穿那馉饳儿,捏些盐,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吃馉饳儿。”官人道:“我吃。先烦你一件事。”僧儿道:“不知要做甚么?”那官人指着枣槊巷里第四家,问僧儿:“认得这人家么?”僧儿道:“认得,那里是皇甫殿直家里。殿直押衣袄上边,方才回家。”官人问道:“他家有几口?”僧儿道:“只是殿直,一个小娘子,一个小养娘。”官人道:“你认得那小娘子也不?”僧儿道:“小娘子寻常不出帘儿外面,有时叫僧儿买馉饳儿,常去,认得。问他做甚么?”
官人去腰里取下版金线箧儿,抖下五十来钱,安在僧儿盘子里。僧儿见了,可煞喜欢,叉手不离方寸:“告官人,有何使令?”官人道:“我相烦你则个。”袖中取出一张白纸,包着一对落索环儿,两只短金钗子,一个简帖儿,付与僧儿道:“这三件物事,烦你送去适间问的小娘子。你见殿直,不要送与他。见小娘子时,你只道官人再三传语,将这三件物来与小娘子,万望笑留。你便去,我只在这里等你回报。”
在《王武功妻》中,只是很突兀地写了“一外仆”的传信。而《简贴和尚》却极为细致地描写了僧儿的身份:“卖馉饳儿”的,这种身份为他走街穿巷,熟悉居民提供了方便。至于他卖馉饳儿时“将条篾篁穿那馉饳儿,捏些盐,放在官人面前”,见到赏钱“可煞喜欢,叉手不离方寸”等情态,都活画出一个油滑的小商贩的性格和心理。尽管这只是一个过场人物,但正是在这些细节上,东京的市井气息得到切实的加强。
宋代文言小说有关东京的描写是一个宝库,有的还为后世的话本小说所继承,如《夷坚志补》卷八《王朝议》记录了一个发生在东京的骗局故事,《二刻拍案惊奇》卷八《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就是据以敷演的。
总体而言,由于文言小说数量巨大,在有关东京社会生活广度方面,远远超过了宋元话本小说,不少题材内容与人物,都未见于话本小说。当然,受到语体的限制,文言小说的描写则相对较为简单,在对东京市民生活细节的描写与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方面,都稍逊于话本小说。
四、“东京”与小说中的其他城市异同
宋元时期的其他城市在小说中也多有描写,这种描写与东京的都市形象既有关联,也存在异同。《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的开篇是这样的:
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有个万万贯的财主员外,姓张,排行第一,双名俊卿。这个员外,冬眠红锦帐,夏卧碧纱厨;两行珠翠引,一对美人扶。家中有赤金白银、斑点玳瑁、鹘轮珍珠、犀牛头上角、大象口中牙。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所质库……
再看《警世通言》中的《万秀娘仇报山亭儿》(32)的开篇:
话说山东襄阳府,唐时唤做山南东道。这襄阳府城中,一个员外姓万,人叫做万员外。这个员外,排行第三,人叫做万三官人。在襄阳府市心里住,一壁开着干茶铺,一壁开着茶坊……
这两篇作品,一写东京开封府,一写山东襄阳府。我们无法确认这两篇作品产生的先后,但从二者叙述格局的相似可以看出,当年的小说家在描述城市时,确实存在着趋同甚至因袭的特点,如同小说家对人物外貌的描述。实际上,《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有如下一段描写:
万员外在布帘底下,张见陶铁僧这厮栾四十五见钱在手里。万员外道:“且看如何?”元来茶博士市语,唤做“走州府”,且如道市语说“今日走到余杭县”,这钱,一日只稍得四十五钱,余杭是四十五里;若说一声“走到平江府”,早一日稍三百六十足。若还信脚走到西川成都府,一日却是多少里田地!
所谓“市语”,指的某一行业的行话或隐语。此处所说的走到余杭县四十五里等距离,是以临安而不是襄阳府为起点计算,也就是说,这篇小说真正的产生地点可能是杭州(33),其中的背景描写可能也是以杭州为想像基础的。同理,东京也可能成为某些小说家书写其他城市的想像基础。
事实上,临安受东京影响巨大。对此,很多文献都有记载。例如吴自牧《梦粱录》卷二《清明节》:
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
卷四《七夕》载:
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罗”之状。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记也。
卷十四《东都随朝祠》:
惠应庙,即东都皮场庙,自南渡时,有直庙人商立者,携其神像随朝至杭,遂于吴山至德观右立祖庙,又于万松岭侍郎桥巷元贞桥立行祠者三。
卷十六《茶肆》:
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
同卷《酒肆》:
曩者东京杨楼、白矾、八仙楼等处酒楼,盛于今日,其富贵又可知矣。
卷十八《民俗》:
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盖效学汴京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食味亦不敢草率也。
卷十九《瓦舍》:
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也。
卷二十《妓乐》:
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也。(34)
民俗、信仰、娱乐,如此等等,无一不可以看到东京对杭州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深入到了话本小说对杭州的描写中,则有待进一步考察。
如果与杭州相比,东京小说与西湖小说在都市与地域文化的表现方面,有同有异。同的方面主要是市井社会日常生活以及风俗的描写,其中可能又微有差别,如以“时间”论,东京小说中元宵十分突出,而西湖小说似乎更重清明。在自然场景方面,东京虽然也有金明池,但它远远无法与西湖相比,更缺少后者的文化底蕴。因此,相对于杭州城而言,西湖小说更侧重于以“西湖”而非市井为场景,而东京小说即使描写金明池,也与市井社会联系更密切。在东京小说中,对酒楼、茶肆等的描写更为具体细致。换言之,东京小说的都市特点而不是自然、文化特点表现得更鲜明些。
至于宋元话本中的其他城市,如《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的“襄阳府”等,在描写上,与东京的市井其实并无差异。但缺少东京小说中那种因屡被描写而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标性场景与时序因素,也不构成自成格局的小说系列。
对于小说家来说,城市的异同同样可以作为情节安排的一种空间要素,《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极为突出。小说中,主人公有这样一段对话:
赵正道:“师父,我要上东京闲走一遭,一道赏玩则个,归平江府去做话说。”宋四公道:“二哥,你去不得!”赵正道:“我如何上东京不得?”宋四公道:“有三件事,你去不得。第一,你是浙右人,不知东京事,行院少有认得你的,你去投奔阿谁?第二,东京百八十里罗城,唤做‘卧牛城’。我们只是草寇,常言:‘草入牛口,其命不久。’第三,是东京有五千个眼明手快做公的人,有三都捉事使臣。”赵正道:“这三件事,都不妨!师父你只放心,赵正也不到得胡乱吃输。”宋四公道:“二哥,你不信我口,要去东京时,我觅得禁魂张员外的一包儿细软,我将归客店里去,安在头边,枕着头,你觅得我的时,你便去上东京。”
显然,这里是将东京与东京以外的地方作对比描写的,作品前半部分人物在东京以外地方的活动,成为他们进入东京的一种铺垫和预演。“这一班贼盗,公然在东京做歹事,饮美酒,宿名娼,没人奈何得他。那时节东京扰乱,家家户户,不得太平。直待包龙图相公做了府尹,这一班贼盗,方才惧怕,各散去讫,地方始得宁静。”“闲汉入京都”不但是情节发展的空间线索,也是国家太平与否的象征,随着北宋政权的南迁,东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发展也逊色于东南其他城市,其都市形象才逐渐淡出了小说的艺术世界。
余论:不完整的都市面相
《东京梦华录·序》描写北宋末期东京时说: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35)
这一概括性的描写,展示了东京的一个整体形象。这一完整形象又经《东京梦华录》诸多细节的补充,构成了东京丰富多彩的面相。比较而言,话本小说在描写东京都市整体形象方面,与《东京梦华录》及其他同类著作相比,可以说还多有欠缺。
虽然话本小说已经可以看到东京不同行业和不同阶层,但较之东京各行各业兴旺发达以及不同阶层同时并存的局面,还有很大距离。如《水浒传》中多处描写了东京相扑,这是东京广受欢迎的一项竞技活动,在话本小说没有这样的描写。
又如话本小说中涉及客栈的描写并不少,但与当时客栈的兴盛情况相比,犹有不足,如宋彭乘《墨客挥犀》卷七载:
参政赵侍郎宅,在东京丽景门内,后致政归睢阳旧第,东门之宅,更以为客邸。而材植雄壮,非他可比,时谓之无比店。(36)
这种官员退休后用自家豪宅开设客邸的情形(或被他人改造为客邸),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活跃的程度,在东京,出行有马、驴、牛等交通工具供租用。如宋王得臣《麈史》卷上载:“京师赁驴,途之人相逢,无非驴也。熙宁以来,皆乘马也。”(37)
除了繁华热闹的一面外,东京也有阴暗的一面,嘉祐四年,时任开封知府的欧阳修曾上书道:
今自立春以来,阴寒雨雪,小民失业,坊市寂寥,寒冻之人,死损不少。薪炭食物,其价倍增,民忧冻饿,何暇遨游?臣本府日阅公事内,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称因为贫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妇人冻死,其夫寻亦自缢。窃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胜数?(38)
在《夷坚志》甲志卷十八《天津乞丐》中,就记述了东京乞丐的居住之所。
此外,都市的发展,在管理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城市的卫生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较为严重的疫疾问题,史料多有记载(39)。
诸如此类事例,举不胜举,而话本小说中都少有相关描写。当然,有一个因素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的,那就是现存的宋元话本与《醉翁谈录》等书所记载的说话艺术的兴盛局面有很大距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话本小说中的东京,可能与当时小说家们的描写也有很大的距离。比如妓女的故事本来是小说家们津津乐道的,在不少文言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描写,如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二载“康倬”事,《青琐高议》后集卷四载《李云娘》等,均事涉东京妓女,情节生动,形象鲜明。但在现存话本小说中,此类形象不多见,应当不是小说家的疏漏,多半是作品失传所致。
总之,与史料及文言小说相比,话本小说对东京的描写还有所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宋元话本中的东京就是残缺不全的。毕竟,小说不同于史书,面面俱到也不代表着描写的深入。无论如何,宋元话本小说共同构成的东京形象,超越了此前小说对任何城市的描写,随着城镇商品经济发展,成为文学与时俱进的典型例证。
①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庞德渐:《从话本及拟话本所见之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
④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为宋元话本《红白蜘蛛》“增订本”,参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上册,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页。本文所引宋元话本小说,除另行注明者外,皆据此书,为省篇幅,以下仅注篇名。
⑥关于“东京”的名称之异与变化,参阅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六章第六节《关于北宋东京的几个名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7页。
⑦《三遂平妖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三遂平妖传》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宋元,《醉翁谈录》记南宋话本名目就有“贝州王则”,《三遂平妖传》中吸纳了话本内容,并非没有可能。
⑧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4—145页。
⑨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上册),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11页。
⑩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4页。
(11)陶谷:《清异录》卷上第一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12)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下第三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第3330页。
(13)有关北宋时期说话艺人与皇宫的关系,缺乏证据。南宋时期,据周密《武林旧事》卷七载:“是岁太上圣寿七十有五,……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则宫中有宣招“小说人”供娱乐之事。冯梦龙《古今小说叙》说得更明确:“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专。泥马倦勒,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但此史实,也有待考证。
(14)司马光:《传家集》卷二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8页。
(16)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4—176页。
(17)《新刊大宋宣和遗事》,上海: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85页。
(18)《默记·燕翼诒谋录》合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19)王得臣:《麈史》,《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4页。
(20)有关相国寺的兴废沿革,可参看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第228—237页的论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1)据《开封市志》,东京城人口应不少于150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册第396页)。另据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宋真宗天禧五年,开封府新旧八厢总计97750户,至北宋末年已达26万户,人口超过100万(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6页)。
(22)有关金明池的兴废沿革,可参看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第265—280页的论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3)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43页。
(24)《新刊大宋宣和遗事》第71—72页。
(25)程毅中:《清平山堂话本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83—384页。
(26)参见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第一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9页。
(27)出《琳琅秘室丛书》,作者不详。收入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程毅中编《古体小说钞》(宋元卷)、李剑国《宋代传奇集》等。兹据《宋代传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11页。
(28)洪迈:《夷坚志》,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25—1626页。
(29)洪迈:《夷坚志》,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页。
(30)刘斧:《青琐高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31)洪迈:《夷坚志》,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02页。
(32)本篇篇末有“话名只唤做《山亭儿》,亦名‘十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的说法,其本当即《宝文堂书目》所著录之宋元话本旧篇《山亭儿》。另外,《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提及“十条龙”、“陶铁僧”二目。诸篇作品间的关系,有待考证。
(33)参见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上册,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01页。
(34)以上《梦粱录》引文均据《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分见第10、23、119、130、132、149、166、179页,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
(35)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36)《侯鲭录·墨客挥犀·续墨客挥犀》合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8页。
(37)王得臣:《麈史》第二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6页。
(3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十四册卷一八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47页。
(39)参见包伟民:《试论宋代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0辑(2006年版,第235—266页),兹据网络检索(http://www.ihp.sinica.edu.tw/~wensi/active/download/active01/BaoWemi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