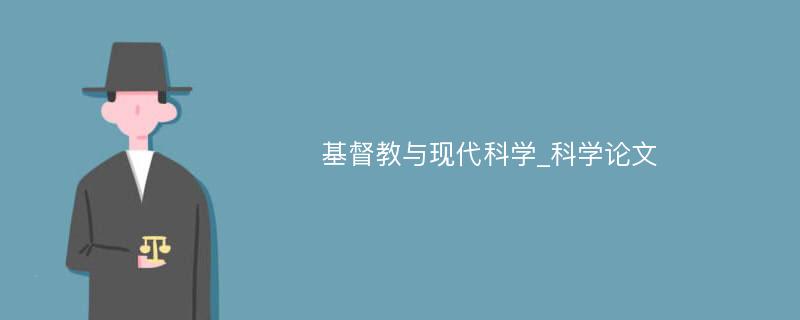
基督教与近代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论文,近代论文,科学论文,教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宗教与近代兴起的科学文化,一般流行的意见总是认为,它们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水火不容的。然而,不论验之以史实还是学理,情形远为复杂得多。
科学和宗教关系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为基督教与科学的混合阶段,科学从属于信仰,在伽利略—牛顿力学兴起,实验自然科学得到初步发展,其时宗教力量强大,新的科学思想往往受到压抑。
第二阶段是分化阶段,信仰在后撤,科学的地盘则在不断扩大,且声誉日隆。牛顿力学被广泛接受,科学通过艰难的斗争,摆脱了神学的束缚,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三阶段是对立阶段,科学的全面胜利,宣称牛顿力学已经达到最终真理,关于自然的基本知识构架已经完成,只剩下一些扩充、增补、运用的工作。在这个阶段,任何和科学不一致的学说、观点、立场,都被宣判为迷信,予以抛弃。这也就是科学主义的最早形式。
第四阶段,是二者各自独立发展又相得益彰的阶段。这一阶段里,科学和宗教都充分认识到了各自的有效意域,“科学并无权干预信仰,信仰亦无权干预科学。一个意域是不能干预另一个意域的。”“科学只能与科学相冲突,信仰只能与信仰相冲突;保持为科学的科学不可能跟保持为信仰的信仰发生冲突。这对其它科学研究领域来说也是如此,比如生物学和物理学。”“信仰之真理是不能以物理学或心理学的晚近发现来证实的,正如它也不能被这些东西所否定一样。”与此同时,科学和宗教又都意识到了人类在今天所共同面临的社会正义、安全、环境、道德以及心灵等方面的危机和困境,所以,它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更为深入和广泛得多的研究和探索。
二
关于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正面关系,一些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的意见值得注意。普朗克说:“宗教与科学之间,绝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对立,因为二者之中一个是另一个的补充。”培根把科学技术称为“向着上帝的荣耀而上升、为着人类的幸福而下降”的事业。受韦伯启发,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其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年)中,论证了清教伦理和科学精神之间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他注意到清教伦理的社会功利主义倾向,其中诸如宣扬自助、关心社会福利、敬仰上帝的作品,清醒、勤勉、对理性与经验的信心,关心实际和应用等等,都会促发科学实践的兴趣,为科学实践提供神圣合法的宗教依据,并为科学认识活动提供方法论支持。特别是清教摈弃权威使得理性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霍伊卡等人通过比较希腊因素和《圣经》因素各自在形成对待自然的科学态度时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以及中世纪尤其是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对自然所持的基本观念,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圣经》上帝造物的思想有助于破除希腊人对自然的神化,即把世界视为上帝的造物;严格区分造物主与被造物,自然本身并不具有神性。这种对自然的彻底的非神化的思想,还有助于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因为机械的世界必定由制造而来,这比有机世界观更加符合《圣经》的观点。
第二,现代科学得以发生的重要思想前提,除了“宇宙的非神化”以外,还有“宇宙的秩序化”一条。即相信宇宙万物是按一定的规律运作的,这种规律不随时间、地区和研究者而改变。这一前提被称之为“自然划一原理”。
第三,古典时代关于人不能胜过自然以及人同自然竞争乃是罪过的观点,被《圣经》关于人可以支配自然的观点所取代。这两条十分重要,它一方面表明人有能力研究、认识和利用自然,另一方面,则表明人有权力和义务去研究、认识和利用自然,为人类探索自然和利用自然提供了神圣的根据,人类可以或者说应该放心大胆地去发展科学和技术。
第四,希腊理性精神固然是现代科学产生的十分重要的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现代科学的根基是对事实的尊重。基督教在这一点上极大地支持了经验论和归纳法对唯理论和演绎法的突破。
第五,古典社会对手工工作的轻视,后来被犹太教、基督教对手工工作的尊重所取代,也为现代科学所必须的实验工作打开了观念的禁锢。
最后,霍伊卡详尽分析了宗教改革对现代科学的正面影响,其中最显著的是改革后的宗派林立,造成了相互宽容和自由辩论的环境,从而使新的科学思想很容易为那些作好了充分准备以接受任何类型变革的人们所接受。
正如有人所明确指出的:“第一,从历史的观点看,现代科学是神学的繁衍;第二,现代技术至少可以部分地被认为是基督教教义中关于人类统治自然的理论的西方化的实现。”
三
科学和宗教之所以并行不悖,康德在明确区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时已然说明,后来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划界”,更是另一层次上的申说。科学属于经验事实的领域,宗教属于超验信仰的领域;前者涉及的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事实,后者涉及的是个体生存的价值态度;前者属于可说者,提供事实判断,为工具理性;后者属不可说的神秘,它只诉诸于生存体验,为价值判断。在认知渠道上,前者切于逻辑和理性,后者则及于想象和灵性。
正因如此,在近现代,直至当代,科学的高度发达并不能取代和排斥深刻的神学研究和神圣的信仰生活,因为,对人与世界谋求理解以及在现世寻找安身立命的家园,乃是人之为人的永恒命题。鲁讯说过:“人心必有所凭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而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那么多大科学家在走出实验室时,能够走进教堂、虔诚敬拜上帝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爱因斯坦和汤因比亦有言:“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的赞颂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如果人类要保持自己的尊严,要维护生存的安全以及生活的乐趣,那就应该竭尽全力地保卫这些圣人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并使之发扬光大。”“高级宗教洞察事物的本质,这对于人类来说确实是思想文化的瑰宝。这种本质的洞察同宗教的传统表示形式不同,其区别在于没有时代的界限。即使我们的宇宙观会因科学而变化,这种洞察也不会不符合时代的节拍。从人的本质条件看,到目前为止,没有因科学、技术的影响而改变,看来今后恐怕也不会受其影响。这些洞察在提示时所采用的传统形式也许落后于近代科学。可是洞察本身仍不失为解决宇宙根本问题的唯一希望,任何人都不能置之度外。这是近代科学领域以外的问题。因而在我们看来,它比科学所能回答的问题重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