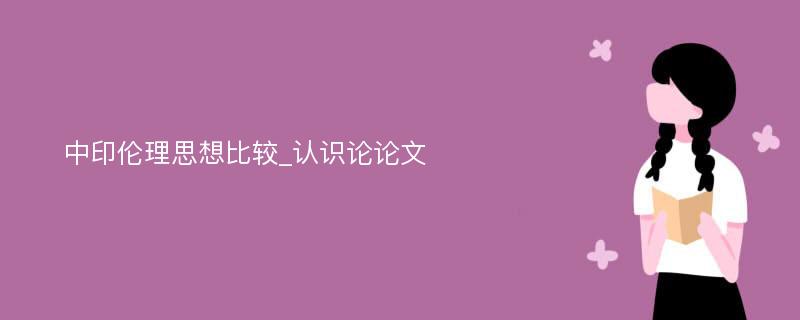
印中伦理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本文从与宗教的关联、与思辨哲学的关联以及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三个方面,对印中两国的伦理思想发展做了比较研究。
与西方国家相比,伦理思想在东方国家的文化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印度与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在这方面都很突出。两国的伦理思想在各自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有着广泛的影响。二者的相似之处是十分明显的。然而,本文所要侧重探讨的却是它们之间的差异点。以下围绕三个问题来进行比较分析。
一、与宗教的关联问题
在印中两国的文化发展中,虽然伦理思想都在各自思想史上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们的一个明显差别是:印度的伦理思想受宗教的影响较大,而中国的伦理思想相对来说受宗教影响要小得多。
我们先看印度的伦理思想与宗教的关联。印度的伦理思想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无论按历史或时间的顺序来划分,还是按哲学派别或教派来划分,以及做其他种类的划分,都可以明显看出,印度的伦理思想与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如从各派的学说上来看,这种关联就很明显。在印度各派中,只有顺世论的伦理思想不带宗教的色彩,但此派的伦理思想是在批驳其他宗教派别学说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应当说它与宗教也有着间接的重要关联。耆那教本身是宗教派别,它的伦理思想与其他宗教学说紧密相关,如该教主张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不淫、不执著世间事物(即所谓“五戒”)。但从耆那教的整个理论来看,这些还不是最高的道德要求。最高的道德要求是求取一种至善的状态,即解脱,而要达到这种至善状态,就需奉行该教的种种宗教修行规定。佛教重视伦理思想是其一大特色。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如“四谛”、“十二因缘”等学说中都包含了伦理思想。“四谛”理论认为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是人由于对世间事物的追求、贪恋而产生的烦恼及业,而要灭苦就应消除产生人的“业”的欲望。灭苦的具体途径有所谓“八正道”。“十二因缘”的理论认为,人生现象是互为因果或互为条件的,具体有十二个环节。在各个环节中最初的环节是无明,由无明起相续引生其后十一个环节。一旦按照佛教教义修行,斩断无明,则其余十一个环节便会自动消灭。这在佛教看来是一种至善的状态。“四谛”和“十二因缘”是佛教为出家信徒规定的较高的道德标准。对在家佛教徒则规定了较低的道德标准(如“五戒”或“八戒”等)。婆罗门教(或后期形成的印度教)是印度历史上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派别。该教伦理思想的核心部分在奥义书时期即已形成。奥义书中提出了梵我同一、善恶因果、轮回解脱等一系列哲学与宗教理论。认为梵是永恒的实体,唯一不变。“我”作为个体灵魂实际以梵为根本。梵通过自身的幻力,幻变出包括人类四种姓在内的世间万象。奥义书向人们暗示:社会上的四种姓是至上之神梵天创造的,因而是神意的,不可改的。遵守四种姓的生活准则,便是善因。善因将获善果。反之,便是恶因,恶因必获恶果。奥义书中的思想家教人不应满足于世上人间的善因善果,而应按更高的道德标准来积累善因,求取更高的善果。这更高的道德标准就是禁欲、冥想、认识梵我同一。婆罗门教的伦理思想还表现在此教的所谓“六派哲学”(胜论派、正理派、数论派、瑜伽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中。其中吠檀多派和瑜伽派的伦理思想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吠陀奥义书中的婆罗门教伦理思想。“六派哲学”中其余四派的学说中虽包含不少与婆罗门教正统观念对立的成分,但在伦理学说的具体内容上却大致与吠檀多派和瑜伽派一致,都主张维护种姓制,要求人们禁绝违背婆罗门教道德规范的欲望与行为。总之,在印度,伦理思想实际与宗教密不可分。顺世论这样的派别极少,而且它的伦理思想也不能说与宗教无关,而其他各派的伦理思想则完全地是在阐述其宗教学说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因此,印度的伦理思想的宗教色彩是相当浓厚的。
中国的伦理思想在这方面与印度有很大不同。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伦理思想不能说与宗教没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在程度上远不如印度的伦理思想与宗教的关系密切。中国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是儒家的学说。儒家学说从总体上看,重视的是对人的生活准则问题的探讨,把人的生活准则、道德规范与宇宙的根本实在相统一,力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真理。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内容是伦理方面的内容。如孔子的“仁”的观念,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程颢和程颐的“天理”思想、朱熹的“天理”与“人欲”观念等等,主要内容都是伦理性的。这些思想是其学说的核心内容,而它们显然与宗教没有多大关联。在中国思想史上,对神或超自然的实在的崇拜,对祭祀等宗教仪式的奉行,基本不曾占据主导地位。这自然也影响了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进程或特点,即一般来说,中国的伦理思想与宗教的关系不很密切。当然,说不很密切并不等于说没有关联。因为在中国思想史上,除儒家外,道教和佛教等亦在不同程度上起了作用。它们必然要影响到中国伦理思想。这是不能忽视的,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它的形成严格来说与中国古代的早期巫术、民间信仰有密切关系,但其在学说上显然吸收了大量道家的观点。它的伦理思想受道家学说影响是明显的,总起来说是有出世倾向,要人们按照道教的教义去修炼,去规范自己的行为。然而,无论如何,道教在中国古代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显然小于儒家。因此,尽管说道教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影响。但与儒家相比,它的影响要轻微得多。佛教在中国有重要发展,佛教及其伦理思想对中国民间的影响是不小的,如积德、行善、求取来世好的果报等思想,在中国老百姓中(特别是在旧中国)是很流行的。然而尽管如此,佛教毕竟自印度传播而来,带有深刻的印度思想的痕迹。中国佛教的许多理论,实际在印度就已确立,或说其思想来源还是在印度。因此,中国伦理思想中受佛教影响而形成的内容,就不能说是中国文化自身独立发展的结果。
二、与思辨哲学的关联问题
一般认为,有所谓世界哲学的三大传统,即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在这三大哲学传统中,西方哲学对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和伦理学问题探讨得相对专门化一些,即三者间彼此的独立性相对强一些,每部分的内容较为自成体系。这三者中的前二者因为探讨的是传统意义上(或按西方标准看)的哲学本身的问题,因而笔者称之为思辨哲学。如果这种划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应当说,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属思辨哲学的内容多一些,而中国哲学中属伦理学方面的内容多一些。然而这只是笼统地说,实际情况要更复杂一些。这里也需要具体分析印度的伦理思想和中国的伦理思想。
印度哲学的思辨性是很强的,就较早的奥义书来看,就有深奥的玄思(如梵我关系理论等);就佛教来看,大乘佛教中的瑜伽行派对世间现象的分析可谓在世界思想史上极为罕见(如关于“五位百法”及“识”的分析等)。然而,印度哲学的思辨性却并未限制其伦理思想的发展,因为印度思想家在细致地探讨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的同时,也将伦理思想掺进了他们的学说体系之中。如陀舍中的《原人歌》把“原人”视为世间事物的根本时,提到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其双臂,吠舍是其两腿,首陀罗是其两足。这里就暗示了作者认为社会中不同种姓的地位不平等有天然合理性。这种思想倾向在后来的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再如奥义书,其中两个主要理论是“梵我同一”和“轮回解脱”。在这两个理论中,思辨哲学与伦理思想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梵我同一”的理论认为,宇宙的本体(梵或大我)和人的主宰体(个我或小我)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我(个我或小我)有多种形态,但梵是其根本,是真正的实在(最高本体)。认识到这点即达到了至上的智慧,或至善的状态,而认识不到这点,把梵与我(个我或小我)看作是有差别的,则是无明。“轮回解脱”的理论认为,人的行为能产生一定的结果,即认为善行和恶行均产生业力,并有相应的果报,行善者成善,行恶者成恶。恶行按不同程度可使人转生成低种姓或成猪狗;善行亦按不同程度可使人进入好的(相对而言)轮回状态或获得解脱。善与恶的区分标准与行为者遵循种姓制度规定的情况有关,亦与人们对梵我关系的认识有关(二者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一致的)。一般的善可以进入好的轮回状态,而且善(认识“梵我同一”)则可使人达到解脱。佛教在这方面就更突出了,如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观念是“空”,认为虽然世间事物不是绝对的虚无,但却是没有主体的,无常的,因而事物都是“假名”。与这类哲学观念相对应,佛教在伦理学上提出了种种理论,如要求人们不执著于世间事物,要求灭除“三毒”(贪、嗔、痴)等等。佛教为教徒制定的行为规范与其理论体系中的思辨内容是一致的。
中国哲学有着自身的特点,它非常丰富、博大精深。自然亦有思辨哲学的内容。但相对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伦理学方面的内容更突出一些。在中国哲学史上,伦理学的内容往往是一个思想家或学派的思想体系中的主要内容,而思辨哲学的内容往往是从属性的,或是在思想家及思想流派阐述伦理思想时顺带论及的。如在儒家学说中,孔孟的理论主要是伦理思想,思辨哲学方面虽有些认识论的思想,但比重不大。宋明理学中当然也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想,但宋明理学家学说中的核心观念还是伦理学方面的。思辨哲学主要是为了说明伦理思想,或是在论及伦理思想时顺便提到的。这与印度的情况亦不同。道教学说中属思辨哲学的内容主要取自道家,而其思辨性及在民间的影响亦无法与印度的思辨哲学相比。道教或道家的伦理思想与其思辨性的内容有一定联系,但它(道教或道家)的伦理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远远小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中国佛教中的伦理思想就其实质性的内容而言,很难找出多少有别于印度佛教中的伦理思想。而中国佛教中的思辨性强的内容亦很难说与印度佛教的思辨哲学无关(倒是一些非思辨性的佛教学说所具有的中国特色更鲜明一些)。因此,中国佛教中伦理思想与思辨哲学的密切联系带有很强的外来性,即这种密切联系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中国之外,而中国之内的原因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却是次要的。
三、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这个问题在上面已有所提及,此处再补充一些具体内容,并作一归纳。
印度哲学中各主要派别在历史上大致是并行发展,因而相对比较容易考察。有影响的哲学或宗教派别主要是所谓“正统六派”和“异流三派”(顺世论、耆那教、佛教)。
数论派是印度的古老哲学,该派在哲学上的基本体系是所谓“二元二十五谛”的转变说理论,而伦理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其有关轮回与解脱的理论之中,该派要求获得“非我”、“非我所”等绝对认识,认为如果按此认识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可以断灭轮回,获得解脱。因此,数论的伦理学说与其哲学基本体系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但作为学说体系的主体思想还是“二元二十五谛”的理论。瑜伽派与一般的印度哲学流派不同,其学说的重点是宗教修持的理论,具体内容很复杂,较典型的修炼方式有所谓“八支行法”,而伦理思想较集中地体现在其“八支”中的前两支(即禁制和劝制)中,禁制包括不杀生、诚实、不偷盗、净行、不贪;劝制包括清净、满足、苦行、学习、敬神。胜论派在传统上被划归婆罗门教的哲学系统,但此派的实际理论与婆罗门教的主要哲学倾向有很大偏差。它实质上是一种自然哲学,基本哲学体系是所谓“句义论”,用“句义”来区分自然现象。该派在哲学上的侧重点是肯定世间事物的实在性,并对其进行细致的分析,而在伦理思想上则强调要遵守婆罗门教所规定的社会秩序,肯定种姓制所定下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与义务的合理性。但这部分内容在胜论派的整个学说中的地位是不重要的。正理派的情况与胜论派相似,所不同的是,胜论派侧重对世间事物的分析,而正理派研究的主要方面是辨论方式和逻辑推理。正理派在伦理思想方面亦接受吠陀以来婆罗门教的一般观念,要求对世界事物不执著,追求宗教上的解脱。弥曼差派以吠陀祭祀礼仪为主要研究对象,此派把吠陀奉为圣典,相信吠陀的正确性,相信祭祀行为的功效。与这一立场相应,此派在哲学上提出的主要理论是“声常住论”,后来还吸收改造了胜论派的句义论,并批驳有神论。该派在伦理思想上的基本观念是:凡吠陀上指明的行为就是正确的行为。而所谓吠陀上指明的行为主要是指传统婆罗门教的一系列宗教义务,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苦行、禁欲等方面的内容。吠檀多派是印度哲学中的主流派,或说是印度婆罗门教正统哲学流派中的“纯正统派”。该派在继承奥义书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主要理论有梵我“不一不异论”、“不二论”、“限定不二论”、“二元论”等。吠檀多派各主要思想家的伦理思想一般都与其梵我关系理论有关,但二者亦还是有各自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在各家总的学说体系中的地位有不同。如吠檀多派的主要思想家商羯罗在提出“渐解脱”和“真解脱”的理论时认为,渐解脱讲人死后个我(灵魂)至梵界享乐,它还不是彻底的解脱;真解脱则是通过对有关梵我问题的最上(最正确)知识而获得的解脱,这种解脱的实现虽然也要求遵从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种种规定,履行种姓义务,但主要则是依靠修行者直接证悟“梵我同一”,依靠修行者在梵我问题上坚持“不二论”。在商羯罗看来,真解脱就在于破除无明,认识真我唯一不二。由此看来,吠檀多派一般的伦理思想与其根本的哲学理论间虽有联系,但还是有层次高低的差异的。
在印度哲学的“异流三派”中,顺世论学说的主干是关于“四大”为万物因的理论、感觉为正确认识来源的理论。顺世论在伦理思想上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幸福生活,此派认为来世或前世不存在,因果报应和轮回解脱的理论不能成立,人们在世界上努力追求幸福生活是合乎道德的,它反对印度的种姓制度,主张人生来就是平等的。顺世论的伦理思想是该学说中的重要内容。但在思想史上,人们似更重视其有关“四大”的理论。耆那教在哲学上的重要理论是其对世间事物的分类(命我、非命我等)及关于“五种智”的认识理论。在伦理思想方面奉行不杀生、苦行、禁欲等理论,但对种姓制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有所不满的,与婆罗门教的态度不同。这种伦理思想与其对世间事物的分类等理论结合得较为紧密,但二者还没有达到密不可分的程度。佛教在各类宗教派别中,所包含的哲学理论是最丰富的,但这些哲学理论一般都不是纯粹的或独立性强的。伦理的成分一般都渗透其中。因此,客观地说,佛教的伦理学说与其哲学的成分都在该教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佛教的典籍为数众多。不少典籍在阐述该教理论时还是有所侧重的,有的主要对世间事物的种类和实质进行分析,有的重点探讨认识论问题,有些在伦理思想方面论述得较为具体或直接。伦理思想虽在佛教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还不能笼统地说佛教学说的核心是伦理学方面的思想。佛教学说中的其他非伦理性成分亦是极为丰富的,大量的,尽管它们时常与伦理性的成分融在一起。
中国哲学的情况与印度哲学不同。此处选择一些不同时期的主要思想家进行考察。
春秋时期较有影响的思想家是孔子和墨子等。孔子学说中有一些认识论方面的思想,如“生而知之”等,但核心理论显然是其社会伦理思想,如“仁”、“名”、“礼”、“中庸”等。墨子的学说中亦有认识论方面的内容,如经验论,但其伦理思想更为突出,他主张“兼爱”等,这显示了其学说的主要特色。战国时期的主要思想家有孟子、老子和庄子等。孟子的情况与孔子类似,伦理思想上的“仁”的观念和“性善”观念是其学说的核心。老子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均有建树,提出了“道”的思想和“玄览”的思想,但其在伦理思想上更为突出,主张与世无争、无为等思想,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不小。庄子在哲学上主张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与此相应,他否定一般的伦理道德。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伦理思想,是一种处世态度,对后世的一些思想家和学派有影响。
汉唐之际儒家继续发展,玄学、佛教、道教兴起,并在中国思想界迅速扩大影响,较著名的思想家有董仲舒、王弼、慧能等。董仲舒在哲学上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感应”等,但其有关“纲”、“常”的伦理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应说更大(更具体)一些。王弼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其理论体系有很强的思辨性,强调“以无为本”,但亦很重视伦理思想,他主要吸收了道家的思想,主张“无为”,以此反对或改造儒家提出的“仁义”、“忠孝”的思想。当然,他的“无为”实际上是有其特定思想内容的,“无为”不过是一种手段,用它来限制人的一些行为;最终还是要达到一定的目的,因而“无为”是形式上的。这种伦理思想是其理论的重要特色。慧能是禅宗的主要代表。他的伦理思想与其宗教学说密切相联。印度佛教及绝大多数中国佛教的出世性十分突出,要求人们远离世俗生活(当然,亦有一些不同情况),然而,慧能一系的禅宗则认为“运水搬柴,亦非妙道”,强调佛不在人身外,而在人心中,人不脱离日常生活就能成佛。因此,在慧能一系的禅宗那里,佛教的传统伦理观念是大打折扣的。他们实际变相地肯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的合理性。慧能等的宗教与伦理思想当然有其受印度佛教影响的一面(如受印度大乘佛教“实相涅槃”、“中道”思想等的影响),但更值得注意的还是他们在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中所受的影响,即他们必定受到儒家入世思想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或熏陶。
宋朝至近代,中国著名思想家极多,如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王守仁、戴震、康有为等。张载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有成就,如提出了“太虚即气”和“因物为心”等思想。他在伦理思想上则持“爱必兼爱”等思想。这种伦理思想与其本体论及认识论的思想有一定联系。程颢、程颐和朱熹的主要学说是所谓“理学”。“理学”既包含了他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观念,又包含了他们的伦理思想,但总起来看,伦理思想方面的含义或色彩更突出一些。陆九渊和王守仁的主要学说一般被称为“心学”。“心学”也同样是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思想的结合,但他们提出这种学说的最终目的是要“发明本心”和“致良知”。即他们学说的落脚点最终还是在伦理思想上。陈亮、叶适被称为是所谓“功利学派”,认为道德离不开功利。戴震的自然观、认识论和伦理学结合得亦很紧密,这与程朱的学说类似,但具体内容与程朱的学说是对立的。在伦理学上,他主张“理存于欲”。这是其学说的核心内容。康有力的主要学说是其“大同”思想,他的伦理观念是其“大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仁爱”、“博爱”等。这些思想的来源既有儒家的传统理论,又有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的伦理思想既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工具,也是“大同”社会应遵循的准则。
不难看出,印度伦理思想在该国主要哲学流派中虽然占有重要地位,但一般来说,这些派别中的其他非伦理的成分往往是其学说体系的核心或基本内容。而伦理思想则虽然常常与其他内容结合在一起,但它本身一般并不占主导地位(少数例外情况当然也有)。而在中国,情况则有些不同。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思想家大都把伦理思想作为其学说的核心或主体。非伦理思想的成分则往往是围绕伦理思想提出的,或是伦理思想的附属部分。这在儒家学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样,例外的情况也有,但亦是少数)。
印度的伦理思想与中国的伦理思想相比,差异点自然不仅仅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但这三个方面在笔者看来显得较为突出。
标签:认识论论文; 儒家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化论文; 伦理学论文; 读书论文; 婆罗门论文; 宗教论文; 国学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