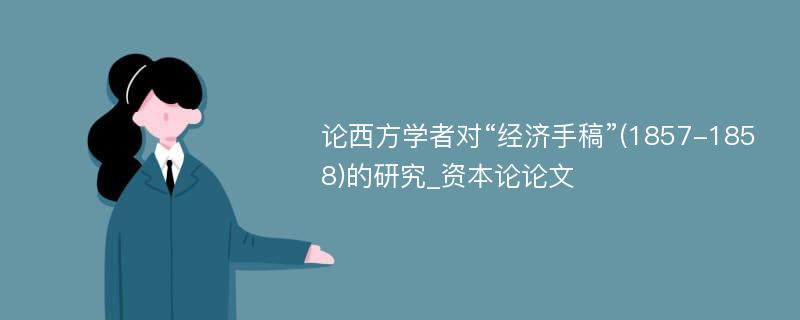
评西方学者对《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稿论文,经济学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下文简称为《大纲》)①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所阐述的许多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的重大发展。但是,与马克思其他著作相比,《大纲》被发现的时间较晚,西方学术界直到20世纪后半期才全面了解这一文本并展开研究。我们介绍和评析西方学者关于《大纲》的看法,对于我国学术界深化这一重要的经典著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学者对《大纲》的研究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对该著作的文本研究,二是对该著作的理论研究。本文前两部分分别介绍和评析西方学者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第三部分结合我国学术界对《大纲》研究的现状,就如何深化对该著作的研究谈一些我们自己的看法。 在马克思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大纲》一直不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了解。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恩格斯可能从来没有读过《大纲》。②1923年,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梁瓒诺夫发现了《大纲》。1939年至1941年,苏联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ǒkonomie(Rohentwurf 1857/1858)]为标题,出版了3 000本《大纲》,由于特殊的时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地点(在与西方世界相对隔绝的苏联),它几乎没有流出苏联国境。③1953年,东柏林再一次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④,这个德文版长达980页,“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对它不了解”。⑤1971年戴维·麦克莱伦翻译出版了《大纲》。⑥这里,麦克莱伦只翻译了《大纲》不到十分之一的内容,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他将该书以《大纲》为书名出版“是有误导性的”。⑦1973年,马丁·尼古拉斯首次将《大纲》全文翻译成英文,⑧“在《大纲》被翻译成英文后,它很快成为研究和评论的主题。”⑨西方学者从文本方面对《大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马克思的《大纲》在马克思整体研究中时期定位。悉尼·胡克认为马克思著作中的不连续性大于连续性。⑩于是,西方学者界就有“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之分、“不成熟的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之分等观点。阿尔伯特·G.拉利尔也认为,《大纲》是“成熟的”马克思的第一部重要的著作。(11)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著作分为四个时期,即青年时期著作、断裂时的著作、成长时期著作和成熟时期著作。在他看来,马克思在1857-1883年的著作为“成熟时期著作”,其起点就是“撰写《资本论》初稿”。(12)当然,有的学者指责阿尔都塞并没有充分重视《大纲》及其重大意义。杰夫·曼说:“各种非黑格尔的或反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从文本上关注《大纲》”,在阿尔都塞和艾蒂安·巴里巴尔的“具有重要影响的”《读〈资本论〉》英文版中,“只有一次提到《大纲》”。(13)安德烈·托塞尔认为,阿尔都塞并没有认真地把《大纲》当作一个整体来重视,而仅仅注意到了《导言》。(14) 法国学者汤姆·洛克曼将马克思的著作分为“早期著作”、“转折期著作”和“成熟经济学著作”,并将《大纲》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一起归为“转折期著作”。他说,早先马克思就像一个高年级的学生一样,常常喜欢详细地对引自某个特定作者的一系列段落进行评论,这种倾向在关于蒲鲁东的著作中仍有体现。而在《大纲》中,马克思的这种倾向基本上改变了,代之以努力综合一系列广泛的相关领域的为数更多的材料,包括引用的各种语言的材料。“在这里把该书纳入马克思的转折期著作,不仅是因为该书所属的时间顺序,而且还因为该书虽然像马克思后来所写的著作一样非常强调政治经济学,但它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哲学风格。该书导言中的方法反思是马克思所有著作中最重要、最精彩的思想,表明马克思仍然在仔细考虑关于如何阐明社会背景理论的棘手问题,这些问题在《巴黎手稿》中已经明确提出,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含蓄地提到过。”(15)针对阿尔都塞等人的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思想存在“断裂”的观点,英国学者特瑞尔·卡弗则认为《大纲》“瓦解了这种看法”,“《大纲》中的‘黑格尔’特征表明了早期和晚期马克思的连续性”。(16) 其次,关于《大纲》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比较。西方学者认为,《大纲》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具有连续性。汤姆·洛克曼认为,马克思先前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时候就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兴趣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非常活跃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导言中,他提请关注经济学和诸如法律、道德、政治等其他主题之间的联系,同时坚持认为他的结论是根据对政治经济学的仔细研究而得出的。“关于《大纲》并没有中断而是继续和发展了早在《巴黎手稿》中就明确关注的阐明现代工业社会观问题的看法,表明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之间的连续性。”法国学者汤姆·洛克曼详细分析了《大纲》与早期著作之间的“连续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黑格尔、蒲鲁东和李嘉图的持续关注中存在着连续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斯密的关注多于李嘉图。在《哲学的贫困》里对蒲鲁东的抨击中,马克思详细地专心于李嘉图的价值观点。“《大纲》就集中于对马克思早先就考虑过的这三个人的批判上。”二是语言上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表明在准备《大纲》的过程中,马克思参考了他还未出版的《巴黎手稿》”。“在《大纲》中关于资本的那一章,马克思一开始就几乎逐字重述了《巴黎手稿》中关于需要、类存在以及宗教异化和经济异化之间的相似性等众多的段落,也许是因为他曾经改写过这些段落。”三是“更深刻的连续性涉及对黑格尔的态度”。“关于马克思在这点上对黑格尔的关注或者他对费尔巴哈式术语的后效作用是纯粹表面的这一看法,跟他从导言开始一直贯穿于整个《大纲》中的对黑格尔的反复关注是相矛盾的。”四是“涉及异化的处理”。“通常认为在《巴黎手稿》之后,马克思就不再关心这个主题,这一看法显然跟马克思持续关注这一保持着它早期的所有细微差别的概念以及关于早期术语的后期著作中的持续性是相矛盾的。”(17)戴维·麦克莱伦认为:“在思想和风格上它都有着与1844年手稿的一致性,最明显地表现在黑格尔对作品的影响。异化、物化、占有、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的一般性质或社会性质这一切概念都在《经济学手稿》中再次出现。”(18) 同时,西方学者也看到《大纲》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的差异。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是第一个尝试将《大纲》的部分内容翻译为英文的学者,认为《大纲》是“马克思著作中的最全面的部分”:它阐述的主题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但是比后者更成熟,因为它揭示了他将哲学和经济学综合起来的思想。(19)后来,他进一步指出:“1844年,马克思已经读了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但还没有把这种知识融入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之中。所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却以《巴黎手稿》而为人所知)分成两个孤立的对等部分,正如该书的首批编者所加标题所说明的那样:‘经济学和哲学手稿’。1857年至1858年,马克思已经吸收了李嘉图和黑格尔的思想(有趣的是,在《经济学手稿》中没有提到费尔巴哈),而且正处于总结自己思想的时候。用拉萨尔的话说,他是‘把黑格尔变成经济学家,把李嘉图变成社会主义者’”。(20) 最后,关于《大纲》与《资本论》的比较。马克思并不打算出版《大纲》,而《资本论》是马克思准备出版的著作,并且他在生前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因此《大纲》与《资本论》相比在结构上“是极为不平衡的”,“大量的延伸是模糊的或冗长的,但是,它也不时有一些清楚的、甚至启发式的清晰之处。它可能比《资本论》更容易理解,但是它也更不引人关注和连贯”。(21)杰夫·曼说,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接触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大纲》等手稿开始的,而是从《资本论》开始的,“《资本论》处在优先的地位”,“对于我们先阅读《资本论》的人来说,很自然地通过后来的著作的视角来解读《大纲》”,近些年来一些学者脱离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长期争论的问题”,诸如“它们从根本上是不是独立或不同的著作?或者《大纲》仅仅是一个‘初稿’,一个错误的尝试,正如第一个编者(指的苏联最早编辑《大纲》的学者——引者)的著作标题所标明的那样?如果《资本论》中存在没有讨论的东西,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否认了他早期的分析?如果是这样,这如何对马克思思想有影响?”(22)安德烈·托塞尔概括了法国学术界关于《大纲》与《资本论》在理论地位上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以吕西安·塞夫为代表的学者坚持《大纲》和《资本论》之间具有同质性的看法,认为《大纲》是“马克思在为别人写作《资本论》之前为自己写的这本书”;以雅克·比代为代表的学者坚持《大纲》具有短效性和在理论地位上低于《资本论》的看法,认为《大纲》是“实验性著作”,其理论上的不充分性为《资本论》留下了空间;以亨利·德尼为代表的学者坚持《大纲》在理论地位上优于《资本论》的看法,认为《大纲》为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重建奠定了基础。(23) 麦克莱伦、尼古拉斯和其他的评论家都认为《大纲》提供了许多导致《资本论》产生的关键要素,这部未完成的《大纲》为《资本论》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框架。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几乎所有要素都在《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阐述。然而,既然这些要素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论述,那么对那些并没有再次展开的内容而言,《经济学手稿》对巨大著作的各个部分的完整性更感兴趣”。(24) 马丁·尼古拉斯也指出,尽管《资本论》的“内部结构”与《大纲》的主要方面是相同的,但是,并不能认为马克思将后者的许多内容搬到前者中。根据他的观点,在《大纲》中,不断成熟的马克思强调对科学思想的全面阐述,但是也考虑到那个时代的欧洲的现实。这种新的、广泛的方法体现在下面对主题的分析上:对黑格尔方法的批判性的评论,劳动价值和劳动力概念,异化理论,关于积累和自动化的趋势、利润率下降的相反趋势、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不断被动的地位的思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不断激化,对国家理论的讨论。(25) 《大纲》在西方被翻译出版之后,立即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杰夫·曼分析了《大纲》受到学术界关注的两个原因:一是“对广泛的问题的分析”。马克思在《大纲》中讨论的一些重要问题成为《资本论》等后来著作的主题,但也应该看到“马克思在《大纲》中讨论的一些问题再也没有大量提及过”。二是“《大纲》对许多主题的阐述是令人感兴趣的,因为它提供了洞察马克思思考的最清晰的窗口——他提出思想的方式,他接受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的强大动力”。(26)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2008年爆发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这一年又是《大纲》写作150周年,因此,《大纲》再度成为西方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西方左派杂志《对立面:激进的地理学杂志》2008年第5期发表一组探讨《大纲》的论文。由马塞罗·默斯主编的《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也于2008年出版。这些都表明“马克思再次成为令人关注的话题,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重新发现他的时代紧迫性”,而《大纲》“这一珍贵手稿将证明对于进一步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有益的”。(27) 西方学者对《大纲》的理论研究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涉及哲学、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内容。西方学者对《大纲》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纲》与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的思想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学者探讨的重要问题,近年来随着分析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式微,马克思与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唯心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28)我们在这里只关注西方学者关于《大纲》与黑格尔之间关系的看法。事实上,西方学者受到恩格斯和列宁曾经阐述过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资本论》之间的关系的启发,极为关注《大纲》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杰夫·曼说:“《大纲》在最近几十年里上升到突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关注黑格尔和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29) 阿尔都塞坚持马克思思想“断裂说”,提出马克思的思想可以分成两个大阶段,即断裂前的“意识形态”阶段和断裂后的“科学”阶段。如前所述,阿尔都塞将《大纲》归为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马克思思想的断裂“对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后果”,(30)马克思在这里关注历史和资产阶级社会,它所体现的是科学,但放弃了包括黑格尔辩证法在内的哲学。后来,德拉-沃尔佩、科莱蒂和乔恩·埃尔斯特和后来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所以,《大纲》在对马克思进行反黑格尔阐述中被省略掉了”。(31) 西方大多数学者并不认同阿尔都塞的看法,认为《大纲》不仅没有放弃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运用它进一步展开了对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麦克莱伦认为阿尔都塞没有认真研究《大纲》就得出结论,这在学术上是不诚实的。(32)尼古拉斯强调《大纲》中的黑格尔主义,认为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早在1969年,联邦德国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就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认为《大纲》中马克思的著作同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关系问题是非常重要和在理论上感兴趣的问题。“如仅仅在少数几个脚注中能够清楚地看出黑格尔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影响,那么《草稿》就必定会把它称之为对黑格尔的一部巨大参考书,特别是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而不问黑格尔是如何从根本上和唯物主义上被颠倒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出版,意味着不首先研究马克思的方法及其同黑格尔的关系,就将不可能写出关于马克思的学术性批判著作来的。”(33)于是,罗斯多尔斯基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中分析了马克思的《大纲》如何运用黑格尔的《逻辑学》。当然,日本学者内田弘认为:“罗斯多尔斯基在他的书中并没有完成证明这一点的任务”,“罗斯多尔斯基给读者提供的例子是武断的,与《大纲》的理论背景并不相关”。(34) 约翰·罗森塔尔既反对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来解读马克思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又反对批判“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力图提出解释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新康德主义”。他认为马克思在《大纲》中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他与罗斯多尔斯基相反,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是坏的思想方法,是一种产生最终谬误的非逻辑的神秘化的方法,“黑格尔的论述方式对马克思的诱惑在《大纲》中最突出”,从而使马克思在《大纲》中“反复进入理论上的死胡同”。在罗森塔尔看来,“尽管《大纲》是马克思努力脱离黑格尔的论述方式的依赖性,但是,他在理论上自立的成熟成果是《资本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与黑格尔的论述方式‘调情’”。(35)罗森塔尔的看法在西方左派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在2000年最后两期发表六篇讨论罗森塔尔的观点的文章。保罗·迪辛认为,罗森塔尔“对辩证法的理解是康德的;他想要非实验的推理过程”,实际上,“辩证法是一个好的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要成就的基础”。(36)托尼·史密斯在评论罗森塔尔的观点时说,《大纲》中的马克思的起点“也就是历史既定的总体”,“《资本论》和《大纲》一样是企图在思想上重构资本主义的本质上的决定,在体系上从它的最简单的和最抽象的规定到更为复杂的和具体的规定”。(37) 第二,对《大纲》中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早在《大纲》被翻译成英文之前,杰克·科恩就摘录和翻译了《大纲》中部分内容,出版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38)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为该书写了“很好的导言”。(39)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方学者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早于《大纲》其他部分的研究。霍布斯鲍姆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存在各种解读,甚至可能是马克思的“观察有误”或者“这些观点观察是基于片面因而误导的信息”,但是,他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理论只是要求存在一个各种生产方式的连续过程,并不必然要求存在某些特定的生产方式,而且也许这些生产方式之间没有特殊的预定顺序。”(40) 埃伦·梅克辛斯·伍德认为,马克思在观察历史时犯了重要的错误,这与“他写作《大纲》时的历史学术成就的存在状态有关”,具体到马克思所考察的三种前资本主义形式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形式“可能是最具争议的”;“古代形式结果是最成问题的”;“德意志类型由于一些略微不同的原因而是成问题的”。但是,伍德仍然维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在他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熟阶段中,从《大纲》开始,变得越来越少地,而不是越来越多地是一个‘决定论者’”。(41)当然,有的西方学者并不认同这种否定马克思是经济决定主义者的看法。(42) 乔尔·温赖特则比较了《大纲》和《资本论》第一卷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上的差异。他认为,《大纲》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也就是从时间上探讨了前资本主义;《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有一个小的离题”,讨论威克菲尔德的现代殖民理论,也就是从空间上探讨前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问题从时间上转向了空间”。同时,马克思在《大纲》分析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仍然坚持“欧洲中心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通过向欧洲的前社会关系扩散而出现,它还将其他地方的前资本主义关系转变过来”,(43)他在《资本论》中逐步放弃了这种看法。 第三,对《大纲》的经济学贡献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麦克莱伦认为,《大纲》在经济学上是马克思成熟理论的第一次阐述,它有两个“关键性的变化”:“第一,马克思没有分析市场交换的机制(像他1844年那样),而是从生产开始分析。第二,当时他认为工人交换卖出去的不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劳动力,正是这两点的结合导致了剩余价值学说的产生。”(44)1989年,阿尔伯特·G.拉利尔出版了《马克思〈大纲〉的经济学》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大纲》的经济思想,并给自己提出三个方面的任务:“系统地考察整个手稿,将这种研究落到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上:价值、价格、分配、国际贸易和金融,平等与非平等,生产流通和商品流通、经济发展和危机”;“分析马克思似乎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李嘉图关于地租、租金、对外贸易、黄金和危机;危机的原因和结果;黄金作为通用货币;贬值和重新估值;资本积累;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关系;价值和价格决定;交通成本”;“考察《大纲》中马克思总体上的推理”。(45)拉利尔认为,马克思在《大纲》中讨论工资发生变动,利润如何保持不变中存在“计算错误”。(46)但是,拉利尔在他的著作中似乎并没有完成他自己所确定的目标,有的西方学者指责拉利尔更多的是概括马克思在《大纲》的看法,“没有评论、没有比较”。(47) 《大纲》在经济理论上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写作《大纲》期间,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48)昂里克·迪塞尔说:“直到《大纲》,我们大家才发现对剩余价值范畴的确定形式的首次详细阐释”,而剩余价值理论的确立表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整体范畴体系的批判已经向前迈出了关键的步骤”。(49)尼古拉斯也认为《大纲》的剩余价值理论对马克思思想来说至关重要,甚至说“具有它的内容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共产党宣言》还不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在阶级分化问题上“《共产党宣言》中预测明显与后来的著作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预测不同”。(50) 第四,对《大纲》中资本主义生态和异化问题的研究。1982年,戴维·哈维出版了《资本的局限》,被称为“是第一个以英文从《大纲》角度来重新解读马克思整体思想的著作”。(51)哈维认为,人和自然构成一个辩证的整体,它们之间的分离并不是推理的而是历史决定的,资本积累必然对生态产生影响。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大纲》包括马克思的自然—社会辩证法或者说生态说辩证法,具体包括五个方面:试图构建一种既包括生产一般又包括它的特定历史形态的唯物主义批判;清晰阐明关于自然和社会的人类需求理论——指明超越资本关系的方向;分析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经济形态和这些形态由于原始积累而导致的解体,表明不断变化的通过生产对自然进行占有的各种形式;资本的外部边界/界限问题;在人口与土地问题上与马尔萨斯的交锋。(52) 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翻译成英文,西方学者对异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如果说早期的争论是以贝尔、胡克和福伊尔等为代表的一方与以奥尔曼和梅扎罗斯等为代表的另一方之间关于成熟的马克思是否放弃异化思想而展开的,那么,《大纲》在西方的出版使这种争论发生“重大转向”:双方都不再“将为不同目的而在不同时间所写的不同著作的段落进行比较”,而是考察《大纲》这么一部“能够将(青年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与(成熟的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资本、生产和交换的分析结合起来的著作”上。(53)麦克莱伦针对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放弃异化思想的看法,指出:“现在判断这是错误的”,(54)异化在马克思成熟思想仍然保持着核心地位。特雷尔·卡弗基本赞同麦克莱伦的看法,但是也指出麦克莱伦“在主张特别在《大纲》中主张异化是中心时有些误导”。卡弗认为,马克思一直没有放弃异化理论,但“存在着微妙的调整以应对学术环境、读者、结构方面的变化,最特别的是适应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及当代情况的相关资料的了解”。(55) 我国学术界全面研究《大纲》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主要与《大纲》在我国的翻译出版有关。我国早在1956年就以《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论资本主义关系形成以前或原始积累以前的过程》为书名,出版了《大纲》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生产方式的内容。1962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出版了《大纲》的“导言”。《大纲》第一个中译本是由刘潇然翻译、由人民出版社从1961年到1978年分五个分册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出版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在1979年和1980年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和下册,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大纲》的研究有了更准确的、更系统的文本依据。 我国学术界在过去30多年关于《大纲》的研究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56)但是,由于对《大纲》研究时间不长,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到我国学术界对《大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而对哲学、历史学甚至地理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深入。西方学术界在《大纲》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些观点由于受到研究方法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并不能为我们所认同,并且西方学者之间还存在着不同认识,但是,他们的研究视野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在我国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新的文献资料,深化对《大纲》的研究。 首先,正确认识《大纲》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西方学者认为《大纲》是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对于有些评论家来说,它甚至起到在马克思著作中把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普遍视为未完成的杰作《资本论》连接在一起的关键作用。马丁·尼古拉斯在英文版《大纲》的“前言”中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挑战或验证了任何一个设想到的对马克思的严谨的解读”、“记载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解决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成为这个手稿最有价值的特征”、“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发展和推翻黑格尔哲学的关键因素”、“是考察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不可估量的价值的重要来源”。(57)但是,也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大纲》“不仅是一部粗糙的草稿,而且存在着内在矛盾,语言也常常是冗长乏味的”,“这本著作未完成的特征是很清楚的:包括在书中的不同部分对同样的或者非常相似的题目进行反复讨论,对整个计划有不同的陈述,远远脱离了马克思当时感兴趣的题目,等等。”(58)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些偏颇之处。 我国学术界过去在对《大纲》的研究中,有些学者认为《大纲》只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初稿”、“草稿”等。显然,这种理论定位明显低估了《大纲》在马克思理论发展中的地位,也反映了学术界一度存在的“重理论而轻文本”的思维定势。我们当前应该加强和深化对《大纲》的研究的原因在于:一是《大纲》在马克思理论发展中的地位;二是人们对《大纲》研究的时间和程度。就前者来说,我们并不认为《大纲》的理论地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已经超越了《资本论》等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但是从文本方面看,《大纲》在马克思理论发展中具有自己独特的角色。1858年11月,马克思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说,《大纲》“是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59)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60)我们如果从马克思整体思想和整个文本的角度看待《大纲》,就会发现《大纲》中的一些理论(如资本积累理论等)与《资本论》相比还处于发展阶段,但《大纲》中的一些理论(如人的发展三个阶段理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思想等)是《资本论》所没有或不再充分阐述的,所以,笼统地说《大纲》在理论上不及《资本论》等著作成熟是不准确的。就后者来说,不管是我国学术界还是西方学术界对《大纲》的研究与马克思重要著作如《资本论》等相比相对较晚,《大纲》中蕴涵的许多丰富思想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 其次,将《大纲》的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尼古拉斯曾经指出,《大纲》“使将马克思的著作分为‘青年’和‘老年’、‘哲学’和‘经济’成为不可能”,“黑格尔的热情支持者和李嘉图支持者都同样在这部著作中找到兴奋点,或者相反,同样感到失望,因为《大纲》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前辈的相互交融的整体。它包括一些用黑格尔的语言来阐述李嘉图的思想的内容,也包括用李嘉图的语言来阐述黑格尔的思想的内容;两者之间的交融是直接的和有成果的”。(61)显然,尼古拉斯在这里正确地看到《大纲》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哲学著作。 1857年12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62)从出版的著作看,我国学术界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史或者说从《资本论》创作史的角度来研究《大纲》。这种研究路径是符合马克思思想的,《大纲》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大纲》是不够的。1858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63)戴维·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可能是偶然的,但毫无疑问黑格尔对他的影响却是深刻的。”(64)我们要准确把握《大纲》的经济思想,首先必须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马克思如何运用它来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曾经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65)列宁的看法不仅适用于《资本论》,而且适用于《大纲》。同时,马克思在《大纲》中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人的发展理论等科学理论。 最后,将《大纲》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保罗·沃尔顿曾概括了西方学术界关于《大纲》的争论,即“它应该表明在什么方面《大纲》不仅仅为解读马克思提供基础,而且这种重新解读对于现代社会理论有什么后果,或者意味着什么”。同时,他特别提到马尔库塞“从《大纲》中引用的证据被他用来支撑他的关于自动化作用,强调革命的无产阶级消失的看法”。(66)约翰·E.埃利奥特则将《大纲》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结合起来,探讨了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西方学者这种将《大纲》与现实结合起来的研究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尽管他们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马克思写作《大纲》旨在理论上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更重要的目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67)武装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我们当前深化对《大纲》的研究必须与我们当前面临的历史使命和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实际上,深入研究《大纲》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国情,更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本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旧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不可能在很短时间根除,《大纲》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大纲》对技术进步和工人阶级构成变化的分析对于我们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自动化和批判“无产阶级消失论”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①《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中文版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它也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在我国和苏联学术界中,有的学者将其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或“《资本论》第一稿”。它在西方学术界广泛被称为《大纲》(Grundrisse)。 ②参见John Hoffman.Review of Karl Marx's 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Science & Society,Oct.2009,Vol.73,Issue.4. ③参见John Hoffman.Review of Karl Marx's 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Science & Society,Oct.2009,Vol.73,Issue.4. ④参见Karl Marx Grundrisse de Kri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Frankfurt am Main and Vienna:Europaische Verlagsanstalt and Europa Verlag,1953. ⑤Mark E.Meaney.Capital as Organic Unity:The Role of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in Marx's Grundrisse,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2,p.2. ⑥参见Karl Marx.Grundrisse,trans.David Mclellan,New York:Harper & Rowe,1971. ⑦Shlomo Avineri.Review of the Grundriss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Jun.1973,Vol.67,No.2. ⑧参见Karl Marx.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Rough Draft),trans.Martin Nicolaus,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3. ⑨Mark E.Meaney.Capital as Organic Unity:The Role of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in Marx's Grundrisse,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2,p.2. ⑩参见Sidney Hook.From Hegel to Marx: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arl Marx,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4. (11)Adalbert G.Lallier.The Economics of Marx's Grundrisse:An Annotated Summary,Macmillan,1989,p.x x i. (12)[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页。 (13)Geoff Mann.Marx without Guardrails:Geographies of the Grundrisse,Antipode,Nov,2008,Vol.40,Issue.5. (14)参见[意]马塞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 (15)[法]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杨学功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16)Terrell Carver."Editor's Introduction",in Hiroshi Uchida,Marx's Grundrisse and Hegel's Logic,Routledge,1988,p.xi. (17)[法]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杨学功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46页。 (18)[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页。 (19)Karl Marx.The Grundrisse,ed.And trans.David McLellan,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1,p.15. (20)[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276页。 (21)Nathan F.Sayre.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the Grundrisse in Anglophone Geography and Anthropology,Antipode,Nov 2008,Vol.40,Issue.5. (22)Geoff Mann.Marx without Guardrails:Geographies of the Grundrisse,Antipode,Nov.2008,Vol.40,Issue.5. (23)参见[意]马塞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4~276页。 (24)[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25)参见Karl Marx,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Rough Draft),trans.Martin Nicolaus,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3,p.52. (26)Geoff Mann.Marx without Guardrails:Geographies of the Grundrisse,Antipode,Nov.2008,Vol.40,Issue.5. (27)[意]马塞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28)近两年国内学术界发表的研究和翻译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观点的文章主要有鲁克俭:《马克思思想的德国古典哲学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4期;[法]汤姆·洛克莫尔等:《再论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哲学动态》2009年第11期;[英]克里斯托弗·阿瑟:《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与马克思学的神话》,《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2期。 (29)Geoff Mann.Marx without Guardrails:Geographies of the Grundrisse,Antipode,Nov.2008,Vol.40,Issue.5. (30)[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0页。 (31)Geoff Mann.Marx without Guardrails:Geographies of the Grundrisse,Antipode,Nov.2008,Vol.40,Issue.5. (32)参见Karl Marx.Grundrisse,trans.David Mclellan,New York:Harper & Rowe,1971,p.2. (33)[德]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34)Hiroshi Uchida.Marx's Grundrisse and Hegel's Logic,Routledge,1988,p.2. (35)John Rosenthal.The Escape from Hegel,Science & Society,Fall 1999,Vol.63,Issue.3. (36)Paul Diesing.Comments on Roshnthal's "The Escape from Hegel",Science & Society,Winter 2000/2001,Vol.64,Issue.4. (37)Tony Smith.On Rosenthal's "Escape" from Hegel,Science & Society,Winter 2000/2001,Vol.64,Issue.4. (38)参见Karl Marx.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Translated by Jack Cohen,edited by E.Hobsbawm,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64. (39)Paul Walton.McLellan's Marx,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Sep.1972,Vol.23,No.3. (40)转引自[意]马塞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 (41)[意]马塞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123、124、126、131、132页。 (42)John Hoffman.Review of Karl Marx's 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Science & Society,Oct.2009,Vol.73,Issue.4. (43)Joel Wainwright.Uneven Developments:From The Grundrisse To Capital,Antipode,Nov.2008,Vol.40,Issue.5. (44)[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45)Adalbert G.Lallier.The Economics of Marx's Grundrisse:An Annotated Summary,Macmillan,1989,P.x x-x x i. (46)Adalbert G.Lallier.The Economics of Marx's Grundrisse:An Annotated Summary,Macmillan,1989,p.110. (47)James G.Colbert.Review of the Economics of Marx's Grundrisse:An Annotated Summary,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May,1992,Vol.43,No.3.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49)[意]马塞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120页。 (50)Nicolaus,Martin."The Unknown Marx." New Left Review,March-April 1968,p.48. (51)Nathan F.Sayre.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the Grundrisse in Anglophone Geography and Anthropology,Antipode,Nov2008,Vol.40,Issue.5. (52)参见[意]马塞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53)J.E.Elliott.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Evolution of Marx's Theory of Allienation:From the Manuscripts through the Grundrisse to Capital,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Fall 1979,Vol.11,Issue.3. (54)Karl Marx.The Grundrisse,ed.And trans.David Mclellan,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1,p.13. (55)[意]马塞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页。 (56)仅从出版研究《大纲》的著作方面看,主要成果包括汪水波:《马克思黄金时代的理论结晶:〈资本论〉最初手稿的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赵洪主编:《〈资本论〉第一稿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顾海良:《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7)Karl Marx.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Rough Draft),trans.Martin Nicolaus,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3,p.25. (58)[法]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杨学功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4页。 (61)Nicolaus."The Unknown Marx," New Left Review,March-April 1968,p.48. (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64)[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65)《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66)Paul Walton.Mclellan's Marx,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Sep.1972,Vol.23,No.3.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标签:资本论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巴黎手稿论文; 逻辑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