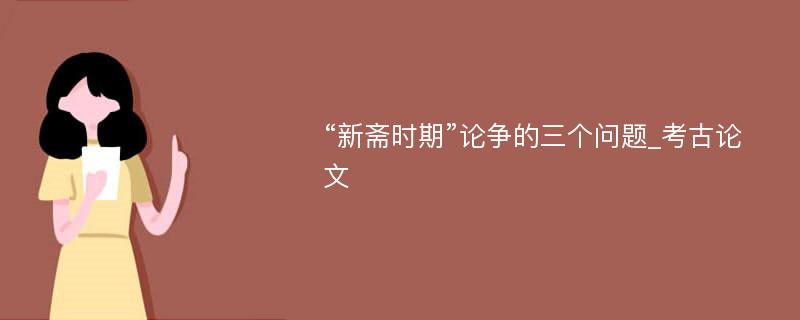
学风濯濯 学史昭昭——关于“新砦期”论证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风论文,新砦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02)03-0025-12
“新砦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的“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基础上,通过90年代末再次考古发掘,进一步认识的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的一种新的文化遗存,其学术意义在于把这两支考古学文化通过一种过渡遗存系联起来,以此作为探求早期夏文化和夏王朝起始年代的考古学基础。这一学术发现被作为夏代年代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载入《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0月出版)。由于早期夏文化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家与文明这样重大的学术问题,因此笔者对这一最新成果进行了认真学习。在研习过程中,笔者发现有关“新砦期”最新论证存在着诸多失误现象,致使这一学术成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受到影响。试就学习体会三题如下,供大家评判。
壹 “新砦期”论证缘何令人疑惑重重
拙作《来自“新砦期”论证的几点困惑》发表不久(《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11日,以下简称《困惑》),曾经参与“新砦期”最新论证的部分发掘者迅即联名著文作答(《关于“新砦期”论证的几个问题——兼答〈来自‘新砦期’论证的几点困惑〉》《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20日,以下简称《兼答》),该文在强调“新砦期”论证科学性不容质疑的同时,将《困惑》产生的主要原由推于笔者。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新砦期”论证的科学性分析
(一)研究程序倒置
运用考古学研究历史的一般程序是:以历史文献为线索,通过考古调查与发掘获取相应的实物遗存资料,通过考古学理论方法对其进行细致整理、分析后,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撰写出具有科学意义的发掘报告,以此为基础展开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学术目地的考古学研究。最终揭示其隐含的历史背景,探讨复原已经逝去的人类社会原貌及其发展规律。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是以客观实在性为主导,而主观臆断则应最大限度的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正是考古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
“新砦期”的最新论证程序则是主观意向在先,然后按需发掘寻找材料,结果证明设想正确。所谓主观意向在先指论证者首先以“新砦期”存在为假设前提。比如: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0月出版,以下简称《简本》)单方面提到“有学者认为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某些单位为代表的遗存,早于二里头一期,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80页),却不提学术界尚存不同意见。再如1999年新砦遗址发掘者在谈到此次发掘目的时,也只是单向强调“新砦期是否真的存在?如果的确存在,其文化性质究竟如何?……为进一步了解新砦遗址的文化内涵,1999年10~12月间,……我们联合对新砦遗址进行第二次试掘,……”(见《1999年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考古新收获》《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和《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4期,因前后两次发文内容、体例基本相同,以下凡出现《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即指两者)。而像“新砦期是否真的不存在?如果的确不存在……”这种假设前提却根本不予考虑。
这些迹象表明论证者与发掘者在发掘前已经导向明确并且胸有成竹。
因此,有了发掘目的十分明确的1999年度的新砦遗址发掘。结果,对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确认了“上承龙山文化,下与二里头文化紧密相连”的“新砦二期遗存”的存在。
故有《简本》(80页)所谓“1999年开始对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证实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文化一期,正填补了其间的空白”这一阶段性成果的介绍。“新砦期”论证获得成功。
另据《兼答》透漏,《简本》78页图十五《豫西地区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典型陶器形制演变图》(以下简称《演变图》)所列“新砦期”器物群,是在整理2000年度发掘资料期间,应邀提前把这几件器物选送发表的。
笔者按:“新砦期”论证采用特殊研究程序,从主观愿望出发,通过发掘证明预先设想的正确。从发掘者承认“1999年试掘新砦遗址之后,因发掘面积有限,复原陶器不多,我们对‘新砦期’的认识的确不够深刻”和在2000年度发掘整理工作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就能够作出结论和敢于“应邀”提前为《简本》选送标本的事实,表现出论证者的主观愿望和自信已经远远超越了科学研究必须履行的程序。所谓“应邀”者,即为自己违章操作提供了口实,也为日后推脱责任埋下伏笔。
(二)《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科学性丧失
研究成果能否成立,有关资料及其来源的科学性是关键所在。笔者在学习中发现,作为《简本》“新砦期”成果支持点的《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因存在严重失误而丧失了科学性和可信性。
1.对地层关系认识矛盾 主要表现为对有关地层介绍,多处存在文、图不一致的情况。比如:
H220,文字介绍开口于T6第4层下,而附图所示却开口于第5层下。(参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23页,《华夏考古》2000年4期4页)。
H444,附图显示于T1北壁剖面图上,却不见于文字叙述,而文字介绍开口于第6c层下的H144也不见于相应的地层图。(参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24页图二,25页文字,《华夏考古》2000年4期5页图三及相应文字,因《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明言发掘灰坑160多座,不知如何解释。)
T6第7层,文字介绍“仅(见)于T6(探方)中部,范围较小”,而T6西壁剖面图显示情况并非局限于探方中部,不知何故?(参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23页图一及相应的文字描述,《华夏考古》2000年4期4页图二及相应的文字描述。还有几例,不一一列举)乱葬坑,文字介绍其中一座在T6北部H220第一层中。那么,此乱葬坑与H220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是H220中的一处遗迹现象,还是两个不同的地层单位?(参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26页,《华夏考古》2000年4期6页)
在介绍T6西壁和T1北壁剖面时,文字对于图上显示地层单位叙述介绍有所遗漏。如T6西壁剖面:G1,T1北壁剖面:H35、H112、H120、H122、H123、H127、H444。(参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23页图一、24页图二及相应文字描述部分,《华夏考古》2000年4期4页图二、5页图三及相应文字描述部分)。
鉴于该发掘简报对地层的认识和介绍存在上述混乱不清的矛盾现象,所以笔者对于简报作者在介绍T6西壁和T1北壁剖面时,掺夹进去许多仅见于文字叙述却不见于相应地层图的地层单位,不敢轻易相信。(如在介绍T6西壁剖面的文字叙述中出现的H212、H214、H215、H216、H217、H218、H219、H221、G2、H224均不见于相应地层图;在介绍T1北壁剖面的文字叙述中出现的H8、H24、H25、H26、H29、H40、H47、G1、H71、H72、H125、H145均不见于相应地层图。(参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23页图一、24页图二及23、24、25页相应文字描述部分,《华夏考古》2000年4期4页图二、5页图三及相应文字描述部分。)
笔者按:在发掘者和简报撰写者对上述现象未作出正式更正声明和原因解释之前,笔者不敢轻易相信《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所称其成果“新砦二期遗存”得到了层位关系支持的结论。
2.器物纹饰特征、编号矛盾 主要指《1999年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考古新收获》《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和《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4期先后两次发表内容、体例基本相同简报多处出现对同一件器物纹饰特征、编号介绍不一致情况。
比如纹饰不一致:尊形器(H29:11),两次公布的图对其肩部纹饰特征描绘不一致(对照《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30页图七8,《华夏考古》2000年4期9页图八7)还有几例,不一一列举。
编号不一致:1件小口高领瓮编号分别为H227:7(《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28页图五·17)、H227:11(《华夏考古》2000年4期7页图六·11),类似情况还有几例,不一一列举。H147:18编号分别指代小口高领瓮(《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29页图六·7、32页图八·1)、鼎(《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32页图八·6)。1件带双贯耳小口高领瓮分别出现于H29(《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30页图七·18,编号为H29:7)和H6(《华夏考古》2000年4期9页图八·10,编号为H6:66)。
笔者按:在发掘者和简报撰写者对上述现象未作出正式的更正声明和原因解释之前,笔者不敢轻易相信《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所称分组器物组合及其演变的逻辑支持“新砦二期遗存”存在的结论。
(三)《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材料与结语不完全一致
1.《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报道材料不显示对其结语的支持
如《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结语明言“1999年,新砦遗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是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无论从地层关系还是器物组合及其演变的逻辑关系上看,新砦二期遗存上承龙山文化,下与二里头文化紧密相连。”(参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31页,《华夏考古》2000年4期10页)
但,该简报地层关系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混乱现象;所谓分组,或缺少直接显示的地层关系,或缺少相关联的器物群,或对于重要的遗迹现象不交代归于何组,结语中所谓“无论从地层关系还是器物组合及其演变的逻辑关系”不知在简报材料中何处得以体现。
2.《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对其材料的介绍与认识根本与结语中某些结论无关
如,《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结语明言“新砦二期介于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之间”,即“新砦二期遗存上承龙山文化,下与二里头文化紧密相连。”(参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31页,《华夏考古》2000年4期10页)。而《简本》正是根据“1999年开始对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证实新砦二期遗存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下连二里头一期,正填补了其间的空白”(80页)。
但《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对其材料的介绍和认识与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无涉,不知“下与二里头文化紧密相连”这样结论缘何得出。
(四)成果与《简本》要求不符
1.《简本》(11页)明确表示:“本报告为向社会公布阶段性成果所用,为求简明,未能一一注明引用他人之说的出处,有关内容将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繁本》中全面反映。”
事实是:收入《简本》中“新砦期”论证成果却连自己的材料出处都隐匿起来。
2.《简本》(95页)明文规定:“考古学的学者将对夏商周年代有密切关系的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建立相对年代序列和分期,为利用现代化手段测定夏商周绝对年代提供层位明确、文化属性明确、相对年代清楚的测年标本。研究重点是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考古文化,同时兼顾周邻地区与夏商周文化关系密切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事实是:《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因部分层位不明确和分组地层与器物脱离致相对年代序列和分期证据不足,收入《简本》中的“新砦期”遗存文化属性不明(这样对于其文化性质判断存在四种可能性: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介于两者之间一种新的文化遗存,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混合产物),对周邻地区其他关系密切的考古学文化也少有兼顾。
(五)成果目前得不到14C测年技术的支持
目前所见有关“新砦期”14C测年数据(参见《中原文物》2002年1期23页),难于突破二里头文化一期14C测年数据上限,表明“新砦期”目前还得不到14C测年技术的支持。笔者按:这涉及到在夏商周考古学研究中为什么要借助于自然科学测年技术问题。主要原因就是单凭有关文献记载无法解决像夏年这样的具体年代,而考古学本身又不具备解决绝对年代问题功能,借助于自然科学测年技术为解决绝对年代无疑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数据。
二、影响“新砦期”论证科学性的主要因素
随着《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科学性的丧失,“新砦期”论证可信性可想而知。事实上在“新砦期”论证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影响其论证科学性的因素。
(一)学术意义重大
按照“新砦期”论证者的话理解,只要“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下连二里头文化一期,正填补了期间的空白”的“新砦期”一旦成立,则早期夏文化可望“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或者“新砦期”本身“就有可能是大家苦苦寻找的早期夏文化”。
笔者按:这样重大学术意义使论证者只顾论证“新砦期”的确存在,而忽略了“新砦期”遗存如果不存在,是否还可以作出另外的解释(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或者作为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的一个地方类型),令人感到论证因情有独钟而失之偏颇。
(二)设定时间短暂
与20世纪70年代新砦遗址发掘者提出的“新砦期二里头文化”至今仍然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存在相比,1999年新砦遗址发掘者则幸运的多,其重要收获“新砦第二期遗存”很快被收入2000年出版的《简本》成为一个带有结论性的阶段性成果。
从1999年10月开始发掘,到2000年3月首次刊出发掘简报(《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完成“发掘--整理--分析研究--公布结果”全部过程最长才6个月时间;2000年春季发掘所获部分标本很快按时选入2000年10月出版《简本》。从1999年10月始,到2000年10月“新砦期”论证成果通过《简本》与读者见面,总共才12个月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具有如此“重大学术意义”的课题,在以往考古学研究中比较罕见。
笔者按:需要讨论的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是否能够预先设定时间。笔者以为完成一个考古学研究程序所需时间因受解决学术问题的大小,难易程度和客观条件的成熟与否等因素的限制而难以事先设定,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懈的努力探索和等待实践检验的耐心。在设定的时间内解决学术问题,只能是实事求是的能作到什么程度就作到什么程度,任何寄期望于主观热情和短期内一蹴而就的做法都很难凑效。
(三)前期研究基础薄弱
“新砦期”论证,必须在熟悉有关夏年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记载基础上,至少对有关河南龙山文化的分期与年代研究成果;有关二里头文化(尤其是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分期与年代研究成果;二里头文化早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相应年代关系及各自文化结构、文化属性拥有前期研究成果。然而,事实是以往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开展考古工作相对薄弱,公布材料也不甚丰富,研究并不深入。另外,部分论证者因涉足上述学术研究较晚,研究基础也相对薄弱。
笔者按:科学研究十分重视基础积累。因此,任何重大学术成果的取得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在前期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的。缺少基础积累的后果是论证者的研究视野和能力受到限制,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受到影响。如果不能够正确认识这一点,很容易走上急功近利的道路。
(四)论证成果没有经过充分的学术研讨和专家组全体成员的鉴定
《简本》(94页)明确规定对课题成果进行鉴定是专家组的职责之一。那么,即丧失基础材料科学性,又不符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要求的“新砦期”论证成果,是怎样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关专家组成员的鉴定和验收的呢?笔者在学习中注意到这样一些迹象:
1.1999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下属的9个课题、30多个专题已完成了预定的研究计划,提交了结题报告,并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稿》起草小组。至9月已经在初稿(起草小组)、讨论稿(经首席科学家审议后修改形成)和征求意见稿(经专家组会议审议讨论后修改形成)基础上形成了修订稿(《简本》117页)。而同年10月12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增设的《新砦遗址的分期与研究》专题研究人员才开始对新砦遗址实施试掘。
2000年春季,《新砦遗址的分期与研究》专题研究人员对新砦遗址实施较大规模发掘;3月,《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刊出《1999年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考古新收获》。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稿》相继形成修订二、三稿。9月15日,经专家组验收审查后形成修订四稿(《简本》118页)。10月,《简本》出版。
2.据《兼答》透漏,2000年10月出版的《简本》78页图十五《演变图》所列“新砦期”器物群,是发掘者在整理2000年度发掘资料期间,于2000年秋提前把这几件器物选送发表的。
3.查夏商周断代工程期间有关学术研讨会,与夏文化学术讨论有关的会议已于1997年11月和1999年6月召开完毕(《简本》8页),而此时1999年10月对新砦遗址的发掘还未开始。使“新砦期”论证成果失去了学术研讨的机会。
4.笔者就“新砦期”论证成果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负责人(专家组成员),得到的答复却是对有关论证情况了解甚少。
笔者按:上述迹象表明,“新砦期”论证成果很有可能由于专题设置较晚,时间紧迫,故来不及经同行学术研讨和专家组审议鉴定,就匆忙写进《简本》向社会公布。《简本》出版在即,匆匆将2000年度出土的几件器物提前放入《简本》《演变图》,结果造成《简本》文字介绍为“1999年开始对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演变图》上出现的是2000年出土器物。好在没有注明出处,否则《简本》这一处文、图不一致的现象就显现于世。
(五)部分论证者缺少科学研究的责任感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诚意
如果参与《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撰写的部分发掘者(笔者按:《兼答》的三位作者是该简报署名前三位作者),在1999年新砦遗址的发掘过程中,用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格把好发掘、整理和简报撰写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负责任的审核原始材料和校对出版材料,则《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中出现的诸多地层矛盾和器物错号现象本来是可以不同程度得到避免的。由于考古发掘简报是以发掘记录为依据,对发掘过程的总结性概括介绍,所以《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中众多错误现象应在发掘和整理过程中就已经发生。
如果参与《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撰写的部分发掘者能够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理解善意的批评和具有自我批评的诚意,那么原本存在的错误会早日得到公开更正,不致于因误导读者而引发种种困惑。然而事实却是,出于诚意笔者曾于2001年8月将情况面告《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作者之一(也是《兼答》的作者之一),至今未见任何形式的更正说明。更令笔者惊骇的是,《困惑》发表数天后,笔者曾将情况面告《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首席执笔者(也即《兼答》的领衔作者)。未料该作者在表示已经知道此事之后,当众告诉笔者:“郭沫若有时故意犯点错误,给同行提供一个挣稿费的机会。……”笔者愿请教此“典故”出处,可信与否,与“新砦期”论证有什么联系。
贰 “新砦期”论证随意性举要——以《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一文为例
笔者在学习“新砦期”研究成果时感到部分论证者的论证态度十分随意,由此引出一些有悖于科学与规范的错乱和矛盾现象。试以《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一文(刊载于《中原文物》2002年1期)为例,举要如下,以求严肃学风。
一、对有关学术观点介绍的随意错位 该文在介绍当前有关早期夏文化探讨主要学术观点时,举出两种代表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缺环。只有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才是夏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龙山文化不是夏文化,这实际上等于把二里头文化一期认定为最早的夏文化。……另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不能囊括夏文化的整个时段,因而主张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只是晚期的夏文化。最早的夏文化即夏文化的上限已进入河南龙山文化年代范围,认为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才是早期夏文化,……”(《中原文物》2000年1期21页)
笔者按:上述介绍两种学术观点似与实际情况不符。当前学术界有关早期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学术观点的确存在两种主要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在时间上已经紧密相接,根本不存在任何缺环。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整体,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龙山文化不是夏文化,最早的夏文化始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另一种意见认为,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缺环,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不能囊括夏文化的整个时段,因此二里头文化只是中、晚期的夏文化。最早的夏文化(即夏文化的上限)要在豫西地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去寻找。需要指出的是“新砦期”的论证者持后一种观点。
据笔者所知,主张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整体)的学者从未认为“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缺环”,而认为两者间存有缺环者恰恰是“新砦期”的提出和论证者,“新砦期”最新论证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缺环而设置的一个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0月出版,以下简称《简本》)80页,《1999年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考古新收获》(《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和《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4期)结语部分都表彰了自己填补了其间缺环(或曰差距、空白)的贡献,怎么能够擅自把“缺环”的发明权随意转让他人呢?
该文所举第二种意见实际上包括曾经流行的“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作为夏商文化分界”的学术观点和目前学术界流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不能囊括夏文化的整个时段,因而主张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只是中、晚期夏文化。夏文化的上限已进入河南龙山文化年代范围,认为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才是早期夏文化”的学术观点。但两种观点各自内部对于夏文化上限认识分歧和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以及前者已为多数学者所放弃的事实,在此却遭忽略。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学术研究具有完整的发展历程。每一位涉足特定学术领域的人,都应当实事求是地熟悉和尊重相关的学术发展史。只有尊重学术发展史,才能够理清学术研究的脉络,寻求规律,有所成就。
二、对有关概念和文化关系的随意混淆 该文首次公开承认初次发掘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新砦期”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的认识,却由此引出一些概念混同和自相矛盾现象:
1.对有关考古学文化概念混淆使用:
(1)《中原文物》2000年1期22页表述:“所谓‘新砦期’是指在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期,……”
(2)《中原文物》2000年1期22页表述:“1999年2000年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新砦遗址重新进行发掘,……其重要收获是发掘出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三叠层,……”
(3)《中原文物》2000年1期22页表述:“发掘结果证明在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确有新砦期将二者连接起来,……”
(4)《中原文物》2000年1期22页表述:“新砦期……,尚未跨入龙山时代,只是比二里头文化稍早。”
(5)《中原文物》2000年1期27页表述:“……二里头新砦期……”
笔者按:在同一思维论断过程中,同一概念或同一思想对象必须保持同一性和确定性,否则整个论断就会因含糊不清而出现混乱。
文中将“新砦期”视为存在于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一个过渡期,对其上连者使用了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不同概念;对其下接者使用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等不同概念,这些概念所表示的年代意义、分布地域和文化内涵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不能不加区分的混同使用。另外,文中不同地方出现的“新砦期”(或“新砦期遗存”)与“二里头新砦期”不知是否属于同一个概念,两种表述方式是否隐含着差别。
笔者注意到该文作者在另外一篇有关“新砦期”论证的文章(参见《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20日7版)中,强调对概念的区分和使用的准确性,不知在此却为何如此随意?明显表现出对概念理解与使用的双重标准。
2.对“新砦期”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判断混乱:
(1)《中原文物》2000年1期22页表述:“所谓‘新砦期’是指在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期,其文化性质属于二里头文化系统”。
(2)《中原文物》2000年1期22页表述:“果然如此,最早的二里头文化,就不再是原定的二里头文化第一期,而是新砦期”。
(3)《中原文物》2000年1期23页表述:“我们认为不宜将新砦期归入龙山文化末期,也不必将这一过渡期单列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而应归入势力呈上升趋势的二里头文化早期。
(4)《中原文物》2000年1期22页表述:“新砦期……只是比二里头文化稍早。”笔者按:按以上表述理解,不难得出如下矛盾的结论。
由二1(2)、二2(1)、二2(3)得出:河南龙山文化通过二里头文化早期过渡到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判断。
笔者不知该文中不同地方出现的“二里头文化早期”概念,是否属于同一个概念。
由二2(3)、二2(4)得出:二里头文化早期比二里头文化稍早的判断
由二2(2)、二2(4)得出:最早的二里头文化比二里头文化稍早,或二里头文化不包括最早的二里头文化的判断。
笔者不能理解一个不能包括其全部文化内涵的考古学文化,其命名的标准和存在意义是什么?
由二1(2)、二2(3)按文化性质只能得出王湾三期文化、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二叠层的判断。
笔者不明白,当该文将新砦期归入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之后,何来三叠层之有?
3.文中有关结论性认识的不确定
(1)《中原文物》2000年1期22页表述:“只要新砦期成立,它就有可能是大家苦苦追求的早期夏文化。”
(2)《中原文物》2000年1期21页、27页表述:“新砦期即使不是最早的夏文化,也是探讨早期夏文化的新支点,……”
笔者按:新砦期是早期夏文化还是探讨早期夏文化的新支点,其意义是不相同的。该文认识随意摆动,表明该文作者没有把握,只好采用脚踏两只船的做法,即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以便为日后更改留出余地。
三、对相关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随意估计
1.对有关14C数据使用不科学 主要指该文对有关14C数据表述不规范和使用的随意性。《中原文物》2000年1期23页表述:“新砦期可进一步分为早晚两段。……首批测定的14C数据有7个,其中,早段2个,晚段5个。其中早段的绝对年代早于公元前1850年,晚段的年代在公元前1850前1680年之间。”
笔者按:文中表述新砦期早段的绝对年代早于公元前1850年,不知有没有这种上不封顶的14C数据。这种做法只能表明该文作者对有关14C数据随意理解和使用,其目的是为其随意安置新砦期年代上限提供方便。
2.对新砦期绝对年代随意估计
(1)《中原文物》2000年1期23页表述:“新砦期可进一步分为早晚两段。……首批测定的14C数据有7个,……其中早段的绝对年代早于公元前1850年,晚段的年代在公元前1850~前1680年之间。”
(2)《中原文物》2000年1期23页表述:“从测年数据看,新砦期的绝对年代难于突破公元前2000年,……”
(3)《中原文物》2000年1期22页表述:“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绝对年代已被测定为公元前1900前1850年,距传说中的夏王朝始建年代不过100余年。”
(4)《中原文物》2000年1期22页表述:“如果新砦期能够确认,那么,新砦期遗存很有可能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数十年乃至100年,从而更加接近夏王朝始建年代。”(5)《中原文物》2000年1期27页表述:“如果认定新砦期是最早的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左右或公元前1850年左右,新砦期前后历时150年左右,已经接近夏文化的上限或距上限不远,……”
笔者按:参照三2(1),不知三2(2)是如何将新砦期的绝对年代与公元前2000年联系在一起的?
参照三2(1)、三2(3),不知三2(4)何以得出“新砦期遗存很有可能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数十年乃至100年”的结论?
参照三2(1)~(4),不知三2(5)根据什么得出“新砦期前后历时150年左右”的认识?对于任何一个论断,只有当它具有充足的理由时,才能够被认为是正确的,在逻辑上被认为是能够成立的。该文在没有举出夏王朝始建年代的前提下,无视新砦期14C数据难于超出二里头文化一期14C数据上限的事实,作出上述有关论断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可想而知。
四、对考古学遗迹现象与历史背景随意联想
1.大冲(水)沟与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联想
(1)《中原文物》2000年1期22页表述:“遗址……发掘出一条新砦期晚段的大冲沟,……”
(2)《中原文物》2000年1期27页表述:“这条大水沟……这样大的水流不禁使人联想到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
笔者按:根据:二3(2),三2(1)、三2(5)判断:属于新砦期晚段的此沟,形成时代应在该文判断夏文化产生75年之后(这还是按该文所说新砦期可能是早期夏文化而言,如按该文又说新砦期即使不是最早的夏文化,也是探讨早期夏文化的新支点说法,当距大禹治水时代更远),无论该文是否考虑史学界尚存夏王朝始于禹或启的意见分歧,都很难将此冲沟年代提早到大禹治水之时。
2.新砦期居民与东方民族发生了密切联系
(1)《中原文物》2000年1期23页表述:“大量的东方文化因素器物的涌入昭示新砦期居民与东方民族发生了的密切的联系。”
笔者按:在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对于文化性质进行判断的一条重要的依据是,对其内部所含不同文化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这种计量必须以文化分期科学无误、因素渊源清楚为基础,必须举出具体的数据才有说服力。希望该文作者能够明确出示具体计量数据(根据该文作者在研究中将超过10%的现象称作个别理解,该文中所用大量一词表明所谓涌入的东方文化因素至少在10%以上)。
(2)《中原文物》2000年1期23页表述:“以文化因素划分,新砦期的陶器群大致可分为三种:1.当地传统因素,……;2.东方因素,……;3.创新因素,……这三类文化因素中的前两类都可以在当地和东方的龙山文化遗存中找到具有渊源关系的同类器物,……”笔者按:根据四2(2)所说“前两类都可以在当地和东方的龙山文化遗存中找到具有渊源关系的同类器物”,不知该文作者能否明确说明文中区分、判断当地传统因素和东方因素渊源的根据是什么。因为文化交流和文化因素的传播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和过程,不知该文作者对此是否研究清楚。
3.对夏年随意择取与判断
该文以“夏王朝始建年代”(《中原文物》2000年1期22页)和“夏文化的上限”(《中原文物》2000年1期27页)为标准,抑制二里头文化一期绝对年代上限,抬高新砦期绝对年代上限。
笔者按:该文如此自信地使用上述标准,仿佛“夏王朝始建年代”和“夏文化的上限”已成定论。既然如此,又何劳苦苦寻求早期夏文化呢?
据笔者所知,有关夏年跨度研究认识在400~600余年之间存在十多种不同意见。按照该文所说归入二里头文化早期的新砦期前后历时150年,那么二里头文化一四期各自也必须均得150年,这样二里头文化所含五个期共历时750年(即使参照学术界认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已经进入商纪年的观点,则也有600年)。从《简本》86页看,“新砦期”论证者倾向于夏积年为471年,这样新砦期占去150年之后,留给二里头文化一四期只有321年(每期只能均得约80年)。无论该文作者如何解释,都难脱对各期年代分配厚此薄彼、随意估计之嫌。
对上述所举“新砦期”论证中的随意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现象,究其原因:笔者以为除部分论证者对于学术界有关研究状况和材料不够熟悉并由此造成学术研究视野十分狭小外,更多的是在“特殊需要”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学术研究中讲求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少有兼顾了。
叁 “新砦期”部分论证者是如何对待读者不同意见的?
作为一名“新砦期”研究成果的读者和学习者,以《来自‘新砦期’论证的几点困惑》(《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11日,以下简称《困惑》)为题谈了“新砦期”论证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希望论证者予以澄清并加以纠正。曾经参与“新砦期”最新论证的部分发掘者立即联合发表《关于“新砦期”论证的几个问题——兼答〈来自‘新砦期’论证的几点困惑〉》(见《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20日,以下简称《兼答》)一文进行辩解。该文在强调“新砦期”论证的科学性不容质疑的同时,对论证中存在的问题采用避重就轻、文过饰非和混淆因果关系等手法,把责任推委于笔者。现将《困惑》提出的问题和《兼答》的辩解会按如下,以正视听:
一、避重就轻 所谓避重就轻指《兼答》对《困惑》提出的关键问题答非所问。
比如《困惑》一提出:《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0月出版,以下简称《简本》)78页图十五《豫西地区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典型陶器形制演变图》(以下简称《演变图》)隐匿所列陶器群出土地点和地层单位,因看不出图上排列器物群出处和关系如何,令读者不免对其科学性和可信性产生疑问。
《兼答》:《简本》毕竟容量有限;《简本》并非考古报告或讨论分期之类的学术论文;同类出版物中不注明单位号者,比比皆是;请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读者等待将来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
笔者按:《困惑》只要求回答《演变图》隐匿所列陶器群出土地点和地层单位的做法是否科学,为什么?《兼答》对此未作正面回答,却推委于《简本》容量有限和等待以后出版的丛书。其实《简本》并不能成为对关键性材料任意删减的理由,所谓“麻雀虽小,五脏具全”就是这个道理。况且《简本》本身已经明言“为求简明,未能一一注明引用他人之说的出处”,《演变图》何以自作主张隐匿成果本身材料出处?至于说到“同类出版物中不注明单位号者,比比皆是”,笔者不仅要问“比比皆是”是衡量科学性的标准吗?能否如是为笔者举出一例:即在文、图介绍不一,又不举出材料出处的情况下,既能够被学术界同仁看懂并毫不怀疑的予以接受,又科学地解决了重大学术问题这样的陶器分期图。
那么,《兼答》作者为何越俎代庖替《演变图》的作者作答呢?原来,《演变图》上所列“新砦期”器物群是他们在未完成整理工作的情况下应邀提供的。事实上《演变图》隐匿材料出处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读者因看不懂“新砦期”论证的成果而对其科学性产生疑惑。
再如《困惑》三提出:在没有交代清楚新砦遗址编年、文化性质及其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一期关系的情况下,从广大的豫西地区4个不同遗址选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器物组织排定《演变图》的方法,有悖于学术界通常运用的考古学分期研究方法。
《兼答》:对于新砦遗址编年、文化性质及其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一期关系等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实在难于在容量有限的《简本》内的一张图中把这些问题全部展开并交代清楚。这些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问题只能在即将出版的新砦遗址专刊中展开讨论”。笔者按:《困惑》要求回答《演变图》是否具有搞清新砦遗址编年、文化性质及其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一期关系的研究基础,从广大的豫西地区4个不同遗址选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器物组织排定《演变图》的方法是否科学。《兼答》对此避而不答,而用“容量有限”为由将读者的视线引向未来。其实,从《兼答》“截止目前为止,新砦期的绝对年代如何,二里头文化一期上限如何等一系列问题尚须做进一步的工作”所言判断,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
二、文过饰非 所谓文过饰非指《兼答》作者对《困惑》采用或纠缠于概念,或轻描淡写,或任意曲解的文风。
何谓纠缠于概念?比如《困惑》二 按《简本》所言“1999年开始对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线索,查阅《1999年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考古新收获》(《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和《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4期)(笔者按:因前后两次发文内容、体例基本相同,以下凡出现《1999年新砦发掘简报》即指两者)。结果是,在前后两次发表的内容、体例大体相同的简报中出现:两次公布的相同器物编号不一致;分组或所举地层缺器物,或列出器物缺地层;重要的遗迹、遗物也未明确属于何组等一系列的问题。以这样一个欠缺科学性的报告作为“新砦期”论证基础,可靠性令人怀疑。《兼答》为此再三提醒读者注意区分小规模地试掘和大规模的发掘、简报与正式报告、通讯性质文稿与发掘简报、内部刊物与正式发表等不同概念。
笔者按:《困惑》只要求回答所提问题是否属实,这样的做法是否科学,这样的材料还能不能作为“新砦期”论证的基础。《兼答》对此未作正面回答,却推委于《困惑》对有关概念使用似不准确。事实上,无论小规模地试掘或大规模的发掘、简报或正式报告、通讯性质文稿或发掘简报、内部刊物或正式发表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其内涵的科学性和可信性是一致的。
至于结构、内容基本相同的发掘简报,怎么能够冠以不同的题目两次刊出,就变成通讯性质文稿和发掘简报两种不同题材呢?(笔者注意到《兼答》首席作者在有关“新砦期”论证的不同文章中署名并不完全一致,试问能否据此理解为不同的两个人呢?)只能是要么都是通讯性质,要么都是发掘简报。问题不在于题材是什么,而在于为什么两者对相同器物纹饰特征和编号报道不一致?读者若有兴趣,将两者对照以下就不难明白《兼答》作者纠缠概念的真正目的。从《简本》77页出现将“河南龙山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两个不同概念互换等同现象,不难体会其兴趣并非在于弄清楚概念本身,不过是醉翁之意而已。
何谓轻描淡写?比如,对于《困惑》二提出前后两次发表的内容、体例大体相同的简报中出现的相同器物编号不一致现象;《兼答》以自己假设前者是通讯性质文稿,后者才是正式发表的简报为正确前提,进一步写道:“该通讯性质的文稿刊载之后,我们首先发现其中个别编号(主要是同一地层单位中的器物小号)有重复和错编现象,因此,将1999年试掘资料正式刊发于期刊《华夏考古》2000年4期时,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我们主动对《1999年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考古新收获》中个别器物编号做了必要的调整和改正,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简报上的行文、插图和器物编号均更加规范。好在读者阅读和使用资料通常以正式发表的简报为准,不会以前此公布于内部刊物的通讯稿为准。”
笔者按:这段文字描述不仅看不出《兼答》作者(也即1999年新砦遗址发掘简报的部分作者)丝毫的愧意和歉意,反而明显流露出自圆其说的轻松感。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器物编号(主要是同一地层单位中的器物小号)重复和错编是个别现象吗?事实是,在发表的陶器中,器物编号被改动者不少于10%,对于器物编号改动现象也涉及不同地层单位。做了必要调整和改正的简报行文、插图和器物编号真的均更加规范了吗?读者真的可以以《华夏考古》2000年4期正式发表《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为准,而置《1999年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考古新收获》(《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不顾吗?事实是否定的,因为:在做了必要的调整和改正后的简报中仍然存在着比比皆是的错误现象,比如:
在公诸于世的简报中有关地层介绍中多处出现错误和遗漏。[见本文壹、(二)、1]在做了必要的调整和改正后的简报行文中,在谈到第二组时,却出现“第三组呈现出与第一组的不同”(10页);简报所介绍的一座乱葬坑在T6H220第1层中(6页),而出示的H220剖面图并未分层(4页图二);这些问题还必须分别参照《1999年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考古新收获》《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28页,23页图一才能找到正确答案。(诸如此类例子还有,不一一列举)
在做了必要的调整和改正后的简报线图中还存在更改遗迹分层和陶器纹饰特征的现象。比如H220原剖面图显示其内部分5层,更改后不分层(对照《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23页图一,《华夏考古》2000年4期4页图二)。编号H29:11的尊形器原图肩部明显有一道纹饰横线,改正后该线消失(对照《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30页图七8,《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第9页图八7)
在认真对照学习《1999年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考古新收获》(《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和正式发表《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4期)之后,不难发现《兼答》作者(也即1999年新砦遗址发掘简报的部分作者)“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对遗迹分层结构(如H220)、遗物局部纹饰特征(如H29:1)、器物所在单位(如H29:7改成H6:66)和器物编号等,都能够作到悄悄地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正”,难道不怕有按需篡改材料之嫌吗?
何谓任意曲解?就是指《兼答》作者在没有读懂《困惑》情况下,随意对《困惑》作出的解释与判断。
比如,针对《困惑》三“发掘报告对陶器分组出示依据地层关系及其中包含器物群材料并不充分,如发掘报告中显示支持所分三组地层依据是:T6(2b)(或2B)→H6(三组);T6⑤→H220(二组)→H227(一组);T6⑤→H220(二组)→⑥→H223(一组);《兼答》:《困惑》“罗列的3组地层关系,并非简报公布的所有地层关系,只限于T6之内,而简报公布的地层关系却不局限于T6。”
笔者按:《困惑》所举这三组地层,是笔者在对简报所列所有地层考察之后遴选出来的。因为,只有这三组地层最有可能直接或间接为陶器分组提供地层依据。这段话并没有说所举三组是简告中所有地层关系,不知《兼答》何以作如此曲解。
再如,针对《困惑》三“由于发掘报告中缺少不同地层单位相应关系介绍,致使三组与二组之间缺少有机的地层联系,如发掘报告谈到三组的代表单位H6时只是介绍其位于T6东北部(2b)层下,至于与H6相关联的地层单位以及与发掘报告介绍T6西壁地层相应关系均未交代。假设T6探方内地层一致,西壁地层③为唐代文化层,那么位于T6东北部(2b)层下的H6与③层关系怎样,如果其在③以上则应属唐代文化层,从其中包含物特征判断这种可能性显然不存在;如果在③层以下则又与发掘报告所称其位于T6东北部(2b)层下不符;假设T6东北部不存在③层,则表明T6探方内地层并非统一,那么离开地层相应早晚关系,怎么能够说明H6(三组)一定晚于H220(二组)呢?”(说明:由于印刷有误,将原文中③错印为⑧,《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18日已作更正声明)
《兼答》:《困惑》“作者原本应该清楚:即使H6不是在③层之上,而是开口于第③层下,那它的层位也比开口于第⑤层下的H220的层位晚。对于这一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困惑》作者却反问简报作者:怎么能够说明H6(三组)一定晚于H220(二组)呢?”
笔者按:事实是《兼答》作者所说的那样“再简单不过”吗?从简报对于地层的介绍,笔者只能作出T6东北部没有第③层的判断,那么H6与(2b)以下那一层地层发生关系呢?笔者实在不清楚,那么H220到底是不是在第⑤层下呢?由于简报文字将其开口提升到第④层下,致使该地层单位失去了可信性。《兼答》作者没有看懂这段话的意思,更不知道H220地层存在的问题,却毫无根据的曲解笔者“原本应该清楚”,实属强人所难。
又如,针对《困惑》三“还有发掘报告虽然举出二组晚于一组的地层关系,但不见有关二组代表单位H220包含陶器群材料的公布,那么区分两组的文化特征根据又是什么呢?其他作为各组代表单位因既缺少地层关系支持、也缺少文化特征系联同样缺少说服力。由于发掘报告对于乱葬坑、奠基坑、墓葬、房基、卜骨等重要遗存相应地层关系未有交代,因而不知其应属于何组,也影响了各组文化面貌的全面体现。”
《兼答》:“简报中虽然没有公布H220的器物,但却公布了与之层位关系一致、同属第二组的H147和H101的资料,并不影响读者对第二组文化特征的认定。”
笔者按:《兼答》作者再一次举出没有显示地层关系的H147和H101两个单位,表明对这段话没有读懂。笔者的意思是,在简报分组或所举地层缺器物,或列出器物缺地层;重要的遗迹、遗物也未明确属于何组情况下,只能以材料衡量其结论,而不是相反。
三、自以为是 所谓自以为是指《兼答》对于事实做出片面的理解和判断
比如《困惑》四提出:以往公布有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碳十四测年数据大体相接,“新砦期”何以楔进其间。
《兼答》:《困惑》作者否认“新砦二期遗存”存在的主要根据是凭自己以往对有关14C数据的统计分析;然而,仅凭14C数据是远远不够的。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从样本自身年龄、保存状况、到采集过程、测试过程等各个环节,都不能保证14C数据测定不出任何问题,不可能拿14C测年数据代替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何况,截止目前为止,新砦期的绝对年代如何,二里头文化一期上限如何等一系列问题尚须做进一步的工作,怎能仅凭自己以往对有关14C数据的统计分析即得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大体相接’的结论?”。
笔者按:这涉及到在夏商周考古学研究中为什么要借助于自然科学测年技术问题。主要原因就是单凭有关文献记载无法解决像夏年这样的具体年代问题,而考古学本身又不具备解决绝对年代问题功能,借助于自然科学测年技术为解决绝对年代无疑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数据。
《兼答》强调了许多因素可以干扰14C数据正确性,无非是要摆脱这样一个事实:目前有关“新砦期”14C测年数据难于突破二里头文化一期14C测年数据上限。表明“新砦期”目前还得不到14C测年技术的支持。
令笔者不解的是,《兼答》在责难笔者“怎能仅凭自己以往对有关14C数据的统计分析即得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大体相接’的结论”之时,自己却能够在“对‘新砦期’的认识的确不够深刻”,“新砦期的绝对年代如何,二里头文化一期上限如何等一系列问题尚须做进一步的工作”,有关“新砦期”14C测年数据也落入二里头文化一期14C测年数据范围之中,又没有举出两者相对年代早晚关系的地层证据的情况下,居然作出了“新砦期”下与二里头文化一期紧密相连的结论。
四、敷衍塞责 所谓敷衍塞责指《兼答》作者们为了开脱干系,采用混淆因果关系的手法,将《困惑》产生的原因推委于笔者。
《兼答》在其文最后依据三条理由将《困惑》产生的原因推委于笔者,三条理由中至少有两条成立,理所当然可以金蝉脱壳了。然而,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却不是这样:
第1条《困惑》“对2000年发掘的“新砦期”材料所知甚少”。
笔者按:由于有关2000年度新砦遗址发掘材料至今尚未公布,笔者“所知甚少”当然成立。但是请注意:笔者有关目前所见“新砦期”论证材料的困惑并非来自2000年度新砦遗址发掘材料,而是来自已经公布的1999年度新砦遗址发掘材料;笔者目前对于“新砦期”论证的困惑也并非来自发掘规模的大小和所获材料的多少,而是来自已经公布材料的科学性和可信性的丧失。2000年材料与由1999年度新砦遗址发掘公布材料给笔者造成的困惑根本无关。此《兼答》作者混淆因果关系一也。
第2条《困惑》对已经公布的1999年的试掘材料存在使用不当和笔误现象。
笔者按:《兼答》所谓“对已经公布的1999年的试掘材料存在使用不当和笔误现象”,是针对《困惑》三“已经公布的1999年新砦遗址H6器物群组合(罐、豆、钵、缸、刻槽盆、刻槽罐)”而言,《兼答》作者以“试掘简报中,无论是文字还是发表的线图当中,都找不到H6出土有什么‘刻槽罐’”为由,得出笔者“对已经发表的材料有所改动”或者是笔者“又一笔误”的判断,最后上升为笔者“对已经公布的1999年的试掘材料存在使用不当和笔误现象”的认识。
看来,在H6中是否存在刻槽罐成为问题的焦点。那么,事实是否如《兼答》作者所说的那样呢?文字部分的确没有(因为该简报文、图不一的现象比比皆是)。然而线图显示,在H6中存在两件内壁显示有刻划痕迹的器物,一件被称作刻槽盆,另一件即是笔者所谓的“刻槽罐”(H6:42),(请对照《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期30页图七3、《华夏考古》2000年4期9页图八3)
第3条以《困惑》“对以往公开发表的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某些重要材料也未能全部收集”为例,上升到“对已发表的材料收集不全”的认识。
笔者按:《困惑》一文对公开发表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一期材料核查存有疏漏。但此因却不能导出“新砦期”论证科学的结果。这里《兼答》作者再次混淆了因果关系。
由于《兼答》作者对亲自发掘整理的1999年新砦遗址发掘材料(已经公开发表)过于生疏和对自己文过饰非的本领过于自信,以至于在没有理解《困惑》作者的科学诚意,没有完全读懂《困惑》一文,甚至没有来得及依据《困惑》所提供的线索对自己撰写的简报材料再认真核查一遍的情况下,就匆忙聚众对《困惑》进行笔伐,以图用“假、大、空”的文风压制不同的学术意见。结果只能是在事实面前将其专断学风昭然于世。
最后,笔者想强调两点:
1.笔者无意否认“新砦期”的存在,不过是希望有关论证者加强论证的科学性,让读者看的明白,心悦诚服,以免“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2.科学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客观实在性及其发展规律;学术研究要以科学的材料为基础,作到论据充分,论证科学,其成果要经得起实践检验而富有生命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要具备高度的科学责任感,拥有追求和捍卫科学与真理的勇气。学术研究需要各种不同意见与建议交流,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需要营造百花齐放的环境和百家争鸣的氛围。
[收稿日期]2002-05-29
标签:考古论文; 文物论文; 中国古代文明论文; 二里头遗址论文; 中国文物报论文; 中原文物论文; 华夏考古论文; 龙山文化论文; 困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