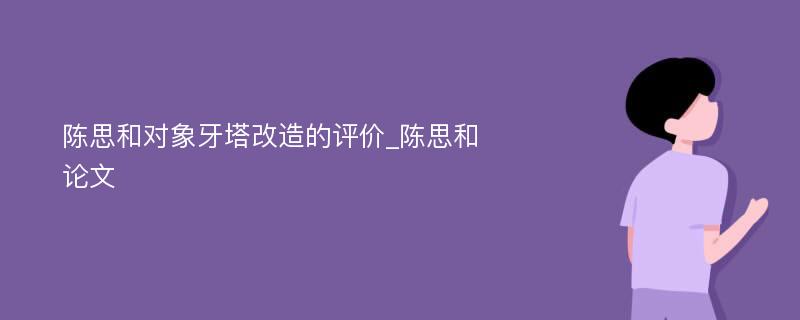
陈思和评论小辑——重建象牙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象牙塔论文,陈思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早就想写的一个题目,现在我把这个题目送给陈思和。
要去描写一个以文字和思想为生涯的人,是相当困难的。这种生涯几乎没有感性的一面。是静止的形态,还是孤立的形态。它完全没有可视性。它提供不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它活动的舞台是书斋这种枯燥又封闭的地方。有时候,是出于想让大家了解的好心,我们去描写他们的日常起居,个人性格,生活习惯,我们把他们刻画成人群中特出或者不特出的一员,可结果是,没有人认识他们。其实,性格于他们的生涯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不是社会大舞台上,性格演员的那一类人。日常生活于这生涯也无大的关系,甚至连皮毛都算不上的,这个日常的世界只是他们寄居的地方。我们不必强调他们作为“人”的那方面,他们的意义并不在于此。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人性大启蒙的时代,这个时代说实在的开始得有点晚,同时又延续得过长了。那是因为我们从无视人性的历史里走来,所以我们格外迷恋这个肯定人性的时期。我们曾有过几次走进这个时期,又走出这个时期,再又走了进来,爱不够似的,也叫做历史的重复。这是充满人道主义热情的世界,特别能够满足对人对己的感情需要。在一次文学会议上,有一位人士提出,作家不应扮演群众导师的角色,而只是群众中的一员,他所从事的职业和调酒师的职业没什么两样。调酒师,可说是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中找到的位置。这里确实有着对人性的普遍尊重,以及平易近人的谦逊,还有着一点审时度势的激流勇退。这觉醒的时代里,确实不再需要给大众上课的老师了。在这同一地平线,大家的视野都是同等的疆域。所以,我们确定会混淆一个以思想为生涯的人的特性。也因为,描写这特性于我们同样也以思想为生涯的人,是有难度的,这意味着一场思想的竞争和赛跑。谁能跑过谁呢?
像思想这种抽象的东西,大约只能用文字去操作它,只有文字才可使它物质化。而文字又是什么呢?白纸上的黑字,读它就有,不读它就没有,也是够抽象的。陈思和就是和这种抽象加抽象的东西打交道。我觉得他是那样一种人,他是隔着文字去触摸这个世界的,他面对的是一个后天的人为的世界,一个思想和审美的世界。这世界也是有骨血的,也是第二手的。他看起来像对现实缺乏热情,醉心于概念之中。可谁知道呢?概念也许要比现实更精彩一些,它炼取了现实的要点。好比原始人在陶罐上留下的雷电纹、云彩纹等等的图案,其实是证明了他们思维的飞跃,从具象到抽象。概念也是雷电纹一类的东西,它是经过总结的现实,虽然缺乏体温,可却包含着思想的能量。其实,这也是需要热情的,需要的是沉淀过的热情。如不是有加倍的敏感,他怎么可能透过文字的隔膜去受授于现实的生存?
从这个现实世界走进抽象世界的过程,就类似于蝉蜕的过程。现实有多少缠绕啊,你得一层层地脱了它去,才可自由。更多的时候是,你一旦脱去了那羁绊,便无可依托,无从抓挠。举个例子,许多研究文字作品的文章,需要依靠作者的生平材料,进行立论立据,这类文章其实都有些瞒天过海之术,论点缺乏说服力,就用现实材料去补充,现实材料不够用了,再上论点。哪一边的逻辑都不是完整的,说是互相补充,其实不对茬口。还有些,甚至需要你作者出来作证,要作者自己交代,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作者都这样承认了,还有什么不算数?或者干脆颠倒过来,用他作反证,有那么多现代心理学可作武器呢,弗洛伊德,荣格,谅他也逃不出这个证人席。
陈思和却不。表面上看起来,他评论的方式似乎有些孤立。即便是对我们这些近在眼前的人,他也极少去引用我们自己的说法,也不谈纯属我们个人的事情,他只对着我们的作品做文章。就是说,他只对写在纸上的感兴趣。他承认纸上的存在,是一种现实,这是他评论的前提。说起来是封闭自己,也是给自己出难题,其实却是严谨和缜密。不靠旁证,也不借助权威性的定语,是以逻辑的推理,让事实说话。似乎是没有人性的气息,把人文的产品当做机械的产品,可是对于一个以思想为工作对象的人,这却是负责的精神。你可以说他学院派,说他学究气,我倒情愿用俚语里“书虫子”这个叫法,我觉得很准确,也很形象。你想书虫子钻啊钻的,钻进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看陈思和写《巴金传》,会以为他要转变得具象一些,参与现实一些。这几年来,一些重要的评论家都在撰写作家传记,比如凌宇写《沈从文传》,王晓明写《鲁迅传》。你惊奇他们忽然对写人物这种写实艺术有了一致的兴趣,其实当仔细读过这些书之后,就会明白不是。他们是在寻找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的源。那是接受科学民主启蒙的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算得上源头的一类人。陈思和们是在对思想进行清理和清产的工作。陈思和的《巴金传》里确实使用了大量的生平履历材料,看来,他以往的那种就事论事的方法在此受到了挑战,这是由他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脉络,光是在纸上寻找是不会有结果的,他们的思想总是要受到现实的干预,同时他们也要干预现实。他们留在纸上给后人我们的,就显得那么不完全,需要配合他们的行为一起分析才可见其真相。所以,当陈思和面对着“人格的发展”这一个大题目时,不免会感到纸上的材料很不够用,他必须去寻找现实性的辅助材料。他这个书虫子,这一回倒真是有些钻出书本了,是不得已而为。由于前一代知识分子不得已走出书斋,后一代知识分子便也必得走出书斋寻觅他们的足迹。
中国这一百年真是动荡不安,知识分子常常悲叹:偌大个中国,却安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埋头于书斋的知识分子却被叫做“钻进了象牙塔”。我想,当陈思和收集着巴金先生庞杂的人生素材时,他一定会痛心于这一百年里有多少宝贵的思想流失于动乱之中。在这些生于世纪之交的敏感的头脑里,有着多少精神的萌芽,来不及生长便被扼杀了,要是由着它们成熟,将是如何辉煌的果实啊!这些果实的价值,有它的时候不觉得,没它的时候才知道。这都是一些脆弱的生命,有什么比思维这东西更容易倏忽而去?它们是需要悉心养植的,说象牙塔一点不为过。现在,陈思和要将知识分子从广场上召唤回来,是不是就是召唤进象牙塔里?他的声音很微弱,风一吹就吹散了,可总是有声音比没声音好。
中国人的思想工作,只注意到两极。玄的太玄,讲的是顿悟,一指头过去,就要觉醒;实的又太实,讲的是投笔从戎,知识分子下海。而中间的一段却被忽略了,这一段就是劳作的过程。什么不需要劳作?思想也是要劳作的。你只看到他们在读和写,却看不到这读和写里的思维紧张的活动,它们也是在奔跑和跳跃的,并且留下看不见的记录,给后来者作标高和攀援。你看见过图书馆吗?那是故纸成堆的地方,你也许终身不会进去翻一张纸看,可有它和没它就是不一样。就好比你一辈子不会走进森林,可它却改良着你的呼吸。说起来,我们都是思想的受益者,辛苦的是他们,思想的工作者们。可谁又知道,他们的快乐呢?
他们正处在蝉蜕的过程,脱去的是具象的外衣,一层层的,都是要以认真成熟的生命去挣脱。你可以说他们是避世,可其实他们避的只是时世繁复纷攘的表面,为要钻进那核里去,那里有着一些一万年也不变,一万里也不变的东西,叫它真谛也可以。它的不变不是指静止,而是恒动的意思。你说宇宙变不变?要进到这核里去,却是说时容易做时难,要避世,也是说时容易做时难,何况,像陈思和置身的是人文学科,研究的是现代和当代,难免要人在事中,怎么摆得脱干系。这一百年的人文史就好比是一部革命史,实践比文章多,陈思和想钻故纸堆也钻不了。这使得陈思和有时候会持一个战士的姿态,发出些呼喊,比如主持人文精神的讨论。在一个早已启蒙近百年的社会里,个人主义大膨胀的今天,这种战士的姿态多少有点像唐·吉诃德。这也是没办法,是一百年革命史的尾音,也是脱去蝉蜕的挣扎,是为铺平通向象牙塔的道路。
那确是处于塔尖的所在,是人的思想的顶端,那里也是须有一些劳动者的,为人们创造出一个精神空间。文字是它的砖瓦,也是攀援的阶梯。思想者们伏在书桌上写啊写的情景,看起来很现实,毫无浪漫可言,而他们所创造的那个领域,却是真正的超然物我。但对于陈思和们来说,事情似乎刚开头,却也不是新鲜事了,一百年里,这样的头不知已开过多少回了,现在就看他们,能不能走出历史的徘徊。
这就是我对陈思和的人生的描绘。
1995年4月20日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