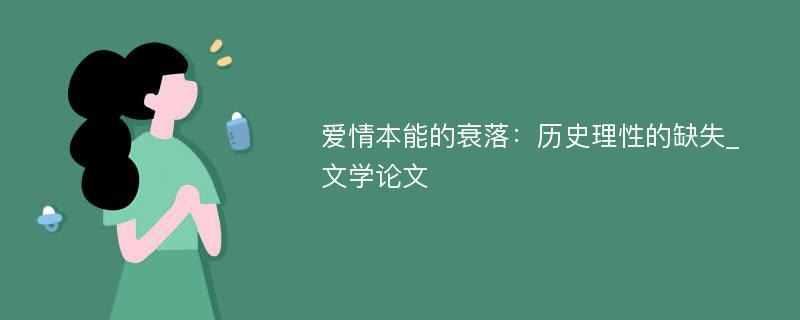
由爱情向性本能的滑落:历史理性的匮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向性论文,匮乏论文,滑落论文,本能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爱情,曾经被我们的文学遗忘过,或者说,被有意识地回避过,这是特殊的历史年代的特殊现象;进入新时期后,这个自古以来就吸引了无数文学艺术家的所谓“永恒的主题”,便成为我们解除了禁锢的文学家们再三表现的对象。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具有挑战意味的新视域,很快,爱情之花就洒遍了几乎每一个角落,文学中单纯的情爱描写在不几年中就有沦为陈词滥调的危险。于是,性描写这个兴奋点开始出场吸引人们的视线了。短暂的遮遮掩掩、欲说还休之后,赤裸裸的性暴露就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蔓延开来,从正常的性行为到变态的窥淫、乱伦等等,遍及性的方方面面,几乎到了无书不性的、无性不书的地步。性的诱惑淹没了爱情的光芒。成为很多作品表现的中心。于是人们开始哀叹:“爱情,这个人类生活中最超越的问题,在过去的时光里,都是支持我们向往诗意生活的基本信念,而在今时代却似乎成了奢侈品和梦想的产物。在文学世界里,爱情也正在褪下它那本应有的神圣光芒,显露出贫乏、苍白而不合时宜的面貌。”(谢有顺《重写爱情的时代》,《文艺评论》1995.3)“现如今,不再是什么性压抑,相反,性的无拘无束,大摇大摆,左奔右突,倒压抑了‘情’,是爱情压抑,爱情象洪水漫过的田野上的草木,奄奄一息,或荡然不存”,到处飘荡着解放了的肉欲,文学的兴趣集中到性上;也许是文学的无奈,你再深沉,就被人瞧不起,你再清高,就被人嗤笑为愚蠢,就无人理睬,现代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性感特征,红尘滚滚,物欲滔滔,谁还有功夫,有心思去爱呀情呀地绕来绕去?另一方面,文学中的杀戒大开,在一些发霉的故事里,常常是性与杀的二重变奏,美人爱土匪,土匪爱杀人,刀光剑影,动不动就人头落地。中国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此豪放,变得杀人不眨眼。性与暴力成为现代文化的两个支点,情感、道德、伦理等等人格精神好象成了古典的命题,随着历史一同变成了文物,变成了人类精神的昨天。现代文化仅仅剩下了物欲、原欲的释放,仅仅剩下了感性的膨胀与扩张。(以上引自石月《文学:在性与暴力的涡流中》,《小说评论》,1995.1)
那么,究竟该怎样看待文学创作中的这一现象?是仅仅在愤怒的道德谴责中做一番情感宣泄式的批判,还是理智而冷静地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恐怕后者更为可取。王达敏在《论当前小说性描写热与性描写艺术原则》(《当代作家评论》1994.5)一文中认为:是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酿成了性描写热的奇观,它的必然性潜存在作家意识中,也潜存在读者的意识中。他分析其中原因时写道:其一,世界范围大众性文化浪潮的冲击与启示。其二,文学商品化的需要。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被抛入市场。文学一旦进入市场,就必然要受市场经济的转换而被商品化,去尽力采取并非它本意想采取的方法去达到出版和赢利的目的。其三,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当代文学的逻辑演进及当代文学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开放性促使它必然要走到这一步。回顾当代文学在描写人的性关系方面由拘谨的情爱描写到自由的情爱描写、性爱描写,再到性行为性征性状描写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性描写热的出现,实是文学发展的必然。1992年大众文化大潮的滚滚热浪挟着多种驱力,更把中国当代小说的性描写推向了峰巅。
然而,文学发展的必然就一定意味着性爱描写的恣肆与泛滥吗?怎样评价、界定性描写的性质,王达敏在文中也认为这“历来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不确定因素之一,人们对性描写的看法,手中所拿的标尺往往不一样,加之因时因地因人之异,他们所掌握的尺度也绝对不一致。”“不确定因素之二。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性的标准对性描写的性质作以准确的界定。”“不确定因素之三,性描写是艺术问题,实际上,在如何评价性描写上,人们已不是把它当作艺术问题,而是当作道德问题来对待的。”道德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面对对象的,“道德评价只有融入艺术的审美评价之中,才能对性描写作出合理的评价。”因而,在怎样对待性描写上就形成了性开放与性保守对立的两极:“它们一为取消性描写,一为泛滥性描写”,过份地保守,不是办法,它将扼杀文学写作的活力与生气,而一任性描写泛滥开去则更不可取,因为“从心理学的观点分析,追求感官刺激,在刺激中过生活是一种精神变态。把感官刺激当作现实的代替品,不仅不能消除需要的焦灼,反而诱惑被压在无意识层中的原始本能苏醒并夺路喷发而出,它一旦喷发出来,就会危害受害个体以及整个社会。”(王达敏《第三价值——文艺的女性世界原则》)在此,性描写的审美尺度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杠杆,对待性描写,既不能单纯从社会道德原则方面考虑,也不能完全从纯艺术方面考虑,而应该从作品和作品的社会效应两方面出发,用整体性观点去看待性描写,将整体把握与具体分析结合起来。文艺作品中的性描写应遵循真善美的艺术原则,我们分析性描写,也应遵从这一艺术原则。石月也以为:性和暴力,完全可以是文学反映的对象,它们既是人的内容、也是社会的内容。然而,如何去反映,历来就是一个难题,完全陷入,顺流而下,肯定是歧途。因为,在这样的层面上,“连妓女的品位都在急剧滑坡,在众多的当代女妓中,再也升华不出一个李香君、董小宛、杜十娘、柳如是。”(鲁枢元《性与精神生态》,《上海文学》1995.2)
过份的性描写既造成了文学品位的滑坡,爱情的重写是否就是一剂最好的解药呢?事实上,爱情与性并不是两个能够截然分开的问题,正常的爱情必然包含有性爱的因素在内。恩格斯把爱情称为性爱,把性爱的最高形式热恋称为性的冲动,就是把人的自然属性作为爱情的起码条件。抽去性爱的纯粹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在现代社会中已难有立足之处。在此,怎样看待爱情与怎样写爱情则成为极为重要的了。在有的作家那里,“爱情的特质说到底就是浪漫主义。”(王安忆《无韵的韵事——关于爱情的小说文本》,《上海文学》1995.6)而谢有顺则以为,人性的自由与尊严是爱情赖以生长的基础。在长达数千年的支持中国人生存的思想传统里,并没有向神圣终极追问的勇气,而是寄生在儒家的务实原则与禅道的逍遥自适的人生信条里。一个缺乏终极参照的国度里,爱情永远都无法获得深情的品质,无法被神圣之光所朗照。在一个社会学或者文化学的层面上,爱情只能带上非本质的面具出现,因为真正的爱情不是被社会与文化这些外部条件决定的。一批不再担负明显社会使命的作家,就相继为爱情找到了两条最基本的消解途径。一是爱情的性化,一是爱情的日常化。文学与爱情之间存在着一种失恋,仿佛文学与爱情无缘,事实上,真实的原因是真正的爱情无法诞生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在非本质的境遇里,我们只能面对一片无情的天空。(以上引自谢有顺《重写爱情的时代》,《文艺评论》1995.3)
虽然将爱情的匮乏根由追溯到我们数千年的思想传统上是有失公允的,但当下文学中也的确存在着爱情理想的匮乏。对此,多数人的矛头指向的是现实物质化的“金钵”。事实上,人们对于重新提出“爱情”这一标旗来挽救被滔滔物欲所淹没的文学写作,已信心不足。爱情在这里被视作性的形而上、最后的精神堡垒,它与现实仍然相隔遥远。如果爱情被引入这一超凡脱俗的描写状态中,便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将爱情完全超脱于现实之上,与大众疏离,另一种可能便是迎合大众的阅读需要,泛滥为言情读物。而怎样将现实与超越把握好,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王安忆在分析《上海文学》1995年6 期所刊登的三篇爱情小说《背影》、《爱过》、《残红》时说:“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爱情竟成了一桩麻烦事。它本来应当是凡俗人间的一个超脱或者神游,结果却成了麻烦的焦点。”“这是一代成熟的爱情家,把它看了个透。他们对我们是有教育的,要我们不必对爱情抱有幻想,他们继承着鲁迅先生《伤逝》的传统,将人生的附丽进一步粉碎。他们对于认识人生,生活和社会,是有帮助的。他们确是要比言情小说家站高了”。然而,仅仅将爱情封闭在二人或几人的小圈子里作爱情游戏,仍然反映出写作者描述视线的局限。
面对性描写的泛滥与恣肆、爱情理想的日益俗化,纯粹而又“形而上”的“爱情”重写未见得是最佳途径。这里,需要我们的作家们放开眼量,以理性的精神反思我们所走过的道路,重新思考我们身处的时代,并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其中,“重写”的爱情才会具有永久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