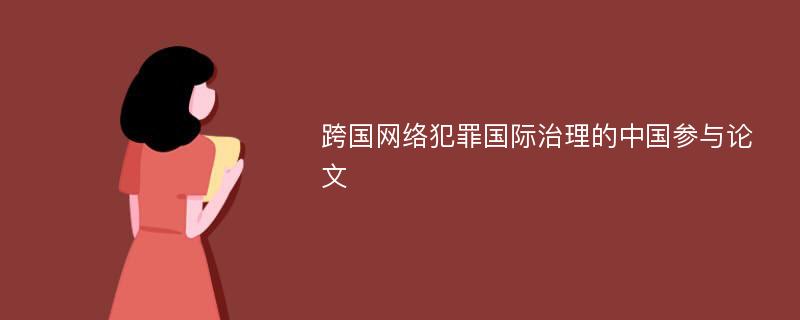
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中国参与
安柯颖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摘 要: 在中国传统刑法规则领域内,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面临法律机制失灵的困境,与信息社会蓬勃发展以及居高不下的网络犯罪率形成巨大落差。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困境归因于国内法的制度掣肘与发达国家治理跨国网络犯罪狭隘的外交政策,导致中国参与跨国网络犯罪全球治理进程中内忧与外患共存。鉴此,须站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以“中国参与国际治理”为主线,以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的现实需求为牵引,构建“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二元并重的法律归化方式,推进中国互联网法院能够拥有对跨国网络犯罪案件的审判管辖权,进而填补中国参与网络犯罪全球治理的盲区,改变“空想式”爱国主义的口号,促进中国刑法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实质融合。
关键词: 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中国参与
面对跨国网络犯罪蔓延,既有的国际治理规则形同虚设,国际社会呼吁构建新型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规则,但对于制定什么样的国际规则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分歧:前者主张网络主权;后者推行网络自由,借国际规则维护自身网络优势。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之机,中国无法独善其身。因此,我们基于治理跨国网络犯罪的立场提出“中国参与”,旨在塑造中国作为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规则设计的参与者和制定者,作为保障中国网络安全必要的补位。因此,面对中国深度嵌入全球化,审慎思考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以及如何构建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治理规则,避免任何过度代表区域利益的国际组织或国家单方面制定国际规则,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关乎网络安全保障与跨国网络犯罪治理,关乎网络强国战略与数据安全、网络安全法治建设的时代使命。
一、中国参与跨国网络犯罪全球治理的国际背景
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跨国网络犯罪治理层面的意识形态冲突非常严重。关于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规则的设计,谁主导制定、谁就能对规则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之机,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网络主权原则”影响下,网络空间的行为规范得到了高度的统一,“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渴望呼之欲出, “中国参与”成为了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标配,构建国际性的治理机制势在必行。
北京市海淀区东片区域教研联合体极大地促进了区域教师的专业发展,提高了区域教研联合体内七个成员校的校本教研能力,特别是教师的教学研究和教育研究能力。通过区域教研,教师们深刻意识到教育需要合作,教育需要分享。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和更多的优秀教研团体加强合作,通过横向拉动,实现教育共享。
(一)“网络主权原则”是跨国网络犯罪全球治理的基本立场
目前,在欧委会和联合国主导下的两种治理模式在打击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欧委会和联合国在推进打击跨国网络犯罪国际合作的同时,关于“网络自由”和“网络主权”国际治理规则的讨论日趋激烈。在美国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之后,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认可了以“网络自由”① “网络自由”旨在“将不受限制的网络访问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向全球“推广信息自由流动”。 为关键词的网络外交政策。随着“棱镜门”的爆发,欧洲各国开始追求独立自主的网络安全政策和国家治理权力。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俄等国提交的《信息安全国际行动公约》(草案)重申:“对与互联网有关的国际公共政策决策权是各国的主权。”从2014年以后,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四次②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巴西访问时首次提出“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能受到侵犯,网络技术发展不能侵犯他国的信息主权。”第二次:2014年1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向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词中重申“尊重网络主权”。第三次: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需要维护国家主权和网络安全。第四次:2015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致辞中提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遵循的“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强调确立主权平等原则应当适用于国际网络空间的治理。” 分别在不同的外交场合强调“尊重网络主权”。从上述国际文件和外交对话中可以看出,网络主权的核心在于不得利用网络技术干涉他国内政,不得利用自身优势损害他国网络利益。我国提出旗帜鲜明的网络主权观,目的是追求国与国之间的安全互信,摈弃以邻为壑的压制性安全理念。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完成了信息化转型的背景下,其倡导的“网络自由”无法与发展中国家的网络实力相匹配,其野心仍然是掌握全球的制网权。因此,跨国网络犯罪的国际治理规则是随着网络安全动态发展而调整的,只有在国家安全、主权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打击跨国网络犯罪的社会效益才能实现,网络安全法治全球化才能实现。
(二)网络犯罪的社会化进程加速了全球法律秩序的国际融合
在20世纪60年代,网络犯罪表现为对计算机系统或计算机信息数据而实施的侵害,关注的是对公民隐私权侵害。民事法律扮演了保护伞的角色,此时刑法处于陪衬地位。随着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20世纪70年代,网络犯罪聚焦于经济犯罪,如非法入侵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和间谍活动,以及这些犯罪的上游犯罪即黑客行为的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个体用户随着市场分工而细化,第一代信息技术标准化产品问世,侵权盗版行为的产生,尤其是音乐和自媒体的传播,呈现出侵犯知识产权的特征。时至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用户数量激增,网络平台服务商为增加网站点击率,非法上传儿童色情、过激言论和非法广告,使得该时期的网络犯罪类型增加了言论犯罪和色情犯罪。到21世纪,高度依赖互联网得以才运行的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军用设施和民用设施数量上升,出现了网络恐怖主义。此时,网络犯罪的社会化进程呈现出“旧瓶新装”的特点,呈现出侵犯公民信息数据权和人格权的犯罪群,入侵或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数据已不再是网络犯罪的终极目的,反而成为跨国网络犯罪产业链的初始环节,为后续的网络犯罪行为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尽管这些犯罪都与计算机信息系统相关,但是数字科技在计算机这个载体下释放了更多的潜能。可见,网络空间的开放程度和数字科技的迭代更新,改变了传统的社交方式、扩大了人类可以触及的空间、促进了国家在政治上的开放程度和国际法律的融合。
上述勾勒的网络犯罪社会化进程表明了数字科技是加速跨国网络犯罪国际融合的根本原因。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律的调整对象。正是这些调整对象的动态演变,迫使世界各国必须要对各自的国内法律规则做出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在刑事法领域,如果国内法的执行得不到国际法律文件的支持,那么“避罪天堂”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外空间,犯罪行为将得不到起诉或免于处罚。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国家的司法部门,会落入竞次陷阱① 这里借用经济学上“竞次”比喻人类文明“向低谷赛跑”,冲破道德底线。在全球化时代,与良性竞争相对的概念是竞次,在竞次的游戏规则里,比的不是实力,而是不择手段。 。这是因为,一国的刑事判决需要经过复杂漫长的刑事司法协助程序,加上世界各国的国内法的差异,仅凭一国之力是难以治理跨国犯罪的。因此,全球法律秩序的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在刑事法律协调下的国家间合作与区域合作是治理网络犯罪全球化的必由之路。
总之,当前中国参与网络犯罪全球治理的困境集中体现在国际治理规则的匮乏以及发达国家对制定新《网络犯罪公约》的阻扰。与此同时,国际层面的区域性法律文件和和国际组织在不同程度上的支持仍有优化、提升的空间。中国于2018年10月26日颁布并实施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和中国法院在治理跨国网络犯罪中的活力尚未充分释放,国内立法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外部实践在积累层面的问题同样存在。
(三)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跨国网络犯罪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
面对跨国网络犯罪形态迭代演进,传统国内法失灵,出现了来自国内犯罪的侵害和境外的威胁,打击跨国网络犯罪国际合作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面对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提出:“现有的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反映多数国家的利益和意愿;……网络犯罪、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公害”② 《习近平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2/03/c-1122050306,2018年12月22日。 。要解决这些问题,“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应成为国际社会广泛的共识”③ 《习近平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2/03/c-1122050306,2018年12月22日。 “建立开放合作,多边民主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④ 《向着网络强国阔步前进》,《人民日报》2018年4月20日第3版。 实现“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⑤ 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的致辞。 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国在网络命运共同体的相互牵制下,国际合作才能实现顺势而为。因此,在我国等发展中国家促推下,联合国网络犯罪政府专家组联合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亚非法协等国际组织对跨国网络犯罪国际合作机制的探讨日渐紧密,各方虽有分歧,但在共识层面开展了广泛有效的讨论。在金砖国家平台内,2017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强调了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的决心,对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治理跨国网络犯罪的国际规则达成了共识,由俄罗斯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联合国合作打击信息犯罪公约(草案)》。在上合组织平台内,成员国就安全合作领域达成了有效打击“三股势力、毒品贩运、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犯罪”的共识,并在2018年的青岛峰会中就网络安全合作的领域、具体实践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为各成员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法律咨询、指导法律实践,并于2014年设立了“网络空间国际法”工作组,专门讨论国家网络主权、和平利用网络空间资源和打击跨国网络犯罪等国际法层面的问题。因此,跨国网络犯罪的国际治理,非一国之责,应呼唤全球构筑网络安全防火墙,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变革,坚持多边参与、发挥政府与民间机构、互联网企业与个人、国际组织与技术团体的齐抓共治,既要推动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治理,也要发挥好各类民间行为主体的活力。
在净化网络空间秩序过程中,网络技术治理的优势对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治理网络犯罪提供了技术动力和约束基础。我们需用运用蕴含技术价值的法律治理手段,有效的实现信息化社会的法律归化。这是对技术应用进行社会选择和能力提升的过程,也是对法律规范进行信息化革新结果。一方面,技术治理的逻辑是自下而上的分权,法律治理的逻辑是自上而下的集权。从网络内部空间结构来看,它遵循的就是分权式层级逻辑,网络决策权分布在各个网络成员手中,允许网络主体多样性的存在。尽管“依靠技术形成的分权式网络管理模式,只能解决网络社会内生性的问题,而网络社会外生性的问题还需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法律治理手段。”① 网络服务者为增强在网络基础服务的控制权,采取流量限制、付费优先、信息过滤等技术,对途径网络信息流和访客实行差别对待。这些技术控制手段以网络服务者的经济利益为核心,侵犯了网民合法的基本权利。为改变现状,人们期待用法律对技术治理进行引导和归化。参见:Guo.H.,Bandyopadhyay,S,Net Neutrality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Content and Broadband Services,27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43-276(2010). 跨国网络犯罪不仅是书数字科技社会化的“恶”果,也是传统犯罪网络化的结果。随着数字科技治理的优势逐渐显现,例如:利用信息过滤、屏蔽手段控制数据跨境流动,为法律治理筑起了虚拟屏障。② 参见:DavidR.Johnson&David Post,Law and Borders,The Rise of Law in Cyberspace,5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389-391(1996). 另一方面,网络社会的法律治理更加依赖技术的结构刚性。从治理方式主体,网络技术的“分布式拓扑结构”③ 分布式拓扑结构的核心是多节点连接。即任何人无须网络授权能添加网络节点和链接,使网络形态发展为多个独立互联的共生状态。这种网络管理思想折射了弱化国家权力治理的理念,强调看不见的手干预和规范网络行为。 要求治理主体多元化,提倡网络服务主体与国家权力共同治、行业自律组织自治相结合。从治理效率来看,技术治理能够简化行政部门的层级审批、缩减中间环节。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网络犯罪中,还是应该坚持以国家主导,依靠硬性(法律治理)和软性(网络技术治理)的治理理念,让技术治理接受法律的归化,让法律治理发挥技术优势,从而形成一种技术型法律治理的格局。
为了实现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全球化,努力完善国际治理规则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传统法律规则的失灵和技术壁垒不可避免地会牵制跨国网络犯罪的国际治理效果,发达国家的狭隘的网络治理外交政策导致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规则形同虚设,面临制度掣肘和国际治理失灵的艰难处境。
二、中国参与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内忧外患
中国参与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归因于内在的国内法制度掣肘:传统的诉讼程序和法律规则难以适应跨国网络犯罪的罪情现实;另一方面源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治理跨国网络犯罪采取狭隘的外交政策,导致中国参与跨国网络犯罪全球治理进程中内忧与外患共存。
(一)内忧:治理跨国网络犯罪的制度掣肘与技术壁垒
一方面,发达国家以先占优势于2001年制定了《布达佩斯公约》,于2004年正式生效。时至今日,布达佩斯缔约国一直致力于将其设置为打击跨国网络犯罪的“国际标准”,反复多场合强调制订新公约将降低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标准。该公约作为区域性公约的确针对跨国网络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自身的缺陷也是存在的:缔约过程不公开、公约内容滞后、缔约门槛高、部分条款有侵犯国家司法主权等重大缺陷。《布达佩斯公约》缔约国表示,针对《布达佩斯公约》内容滞后性,可通过制定新的实施指南和签订新的议定书来修正上述缺陷,因而屡屡为制定新公约而设置障碍,导致会议谈判历时数年。
其三,发展中国家网络技术壁垒制约国际合作的层次。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模式以外驱型为主,这是发达国家的外部文明对发展中国家碰撞后呈现出来的被动反应,自主开发能力受限于发达国家的出口制约,网络人才流失严重。发达国家由于接触多元文化的时间长,在商业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技文明较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文明,具有接受新技术的产业基础、经济支撑和弹性发展机制。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治理跨国网络犯罪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拥有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的数量上。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计算机成和移动互联网成为了每个生活的标配,而发展中国家以非洲为例,每千人仅拥有16台电脑,最少的国家仅为8台,整个非洲人均拥有计算机的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占比不到1%。② David S.Evans and Richard Schmalensee,Matchmakers:The New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6 因此,发展中国家网络技术发展受限于薄弱的物质基础,就凭这一点,无论发达国家提供再多的技术援助,也是杯水车薪,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善。
其二,跨国网络犯罪提出了对“无形物”保护的诉求。传统刑事法律划定了对有体物进行保护边界,而跨国网络犯罪侵犯的通常是无形物。① 无形物在信息时代代表着重要的社会利益,如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在网络空间中,针对无形物实施的犯罪较传统犯罪而言,是视角上无法察觉的,也是难以监控的。 以犯罪主体身份识别为例,网络的虚拟性允许网络行为可以是匿名的,许多国家也都在其国内的宪法中规定了限制获取网络使用者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对于确定犯罪主体又是必须的,尤其是在跨国网络犯罪中,任何试图修改网络匿名的提议都会招致人权保护和数据保护主义的反对。因此,在《网络安 全 法》、欧 洲 《通 用 数 据 条 例》 和 美 国《CLOUD》法案密集颁行的今天,将对正当合法的获取境电子证据、跨境犯罪主体的身份识别以及涉案数额的认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二)外患:发达国家狭隘的网络治理外交政策
1.确立跨国网络犯罪案件的审判权:由互联网法院拥有
其一,传统诉讼程序难以适应跨国网络犯罪。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侦查取证难。由于网络的无国界特征与各国执法有国界之间的矛盾,跨国网络犯罪集团利用境内外法律的差异,通过网络遥控犯罪。例如:网络黑产集团在中国实行网络实名制以后,利用南东亚国家没有该项规定,大量收购和贩卖网络账号和手机号,为跨国网络下游犯罪提供了作案工具。在该种情况下,对刑事管辖权认定、证据固定和保全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在证据完整性方面,网络空间是一个开放性的传播媒介,电子数据跨境流动完全不受主权国家的领土限制。例如,执法人员在A地收集证据,行为人可以在B地轻易的删除或改变与A地相关的数据信息。这意味着,数据的完整性会基于网络空间的时空性被破坏,阻截了完整的证据链,这就加大了对电子证据取证的难度。尽管我国于2016年颁布了《关于电子数据收集提取判断的规定》,但是在信息时代,如何保护境外犯罪现场、提取域外网络犯罪的电子证据、远程勘验的标准化建设都是需要考验的领域。第二,管辖权难以认定。鉴于网络犯罪主体所在地与犯罪结果发生地分离的特征,与犯罪主体相关的嫌疑人、受害人及其它犯罪要素(计算机所在地、网络账号注册地、犯罪收益地)均呈现跨越多个国家、地区的现象。如在跨境网络赌博、儿童色情传播、网络洗钱等跨国网络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分散在世界各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了我国司法机关受理刑事案件的权限,但就跨国犯罪的立案管辖规则以“法律另有规定除外”一言蔽之,至今未见相关规定出台。该诉讼管辖规则的疏漏导致的问题在于我国行使刑事管辖权没有上位法依据,侦查取证的主体就无法落实。第三,境外执法难。法律的重要任务就是保证法律的适用和执行力,如果国内法的执行在外国得不到支持和保证,那么网络空间就成了网络犯罪的“避罪天堂”,最终被其他国家免于起诉或处罚。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我国《刑法》总则第九条规定了适用于跨国犯罪的普遍管辖原则,但这需要在刑法分则中设置相应的国际犯罪的罪刑规范接轨,否则该原则仅为一纸空文。① 以海盗犯罪为例,我国刑法总则设计了治理国际犯罪的刑法适用原则即普遍管辖原则,但是我国刑法分则没有关于海盗罪的罪刑规范。
另一方面,《布达佩斯公约》缔约国阻挠在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内制定 《新网络犯罪公约》。2011在中国和巴西倡议下,设立了联合国网络犯罪政府专家组,专家组与2011年2013年,召开了两次会议,并授权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网络犯罪问题综合研究报告(草案)》,该报告提出制定国际示范条款、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支持等方案。但因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布达佩斯公约缔约国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报告的结论和建议存在分歧,专家组讨论进程一度停滞了四年。这个分歧主要是来自两大阵营的利益设置没能谈妥:一方是发展中国家倡导在联合国框架内制定网络犯罪国际公约;另一方是布达佩斯公约缔约国,他们认为《布达佩斯公约》是治理跨国网络犯罪的“国际标准”,反对制定新公约。在金砖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网络犯罪政府专家组于2017年终于召开了第三次会议,讨论了关于网络犯罪的实质问题。2018年召开了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该专家组的远期工作计划。在专家组上述四次会议中,是否需要制定网络犯罪国际公约均是会议争论的焦点。
本研究对照组患者行急诊内科的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行急诊救治模式的护理干预,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至急救室后静脉通道开放时间、急救室停留时间显著较短,且入院10分钟后FPSR评分明显较低,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观察组患者采用急诊救治模式护理进行干预治疗后,提高了急诊救治的效果,缓解了患者的疼痛。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AS、SDS评分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的SAS、SDS评分较对照组明显要低,观察组家属的满意度比对照组明显要高,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急诊救治模式的护理干预对心绞痛患者的负面情绪起到了良好的调节作用,提高了患者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
制作方法:①选择肥膘适中、大小均匀的活鸭,宰杀脱毛去内脏洗净,并按不同需要将鲜鸭整型(并翅、弯头等),然后将鸭体均匀地抹饴糖上色,然后放入油炸锅中油炸,油炸后放入煮制好的卤汤汁内腌制1~2小时,捞出沥汁并冷却。②将冷却后的卤鸭于其腹腔内装入香米、板栗、枸杞等配方填料,直至填满为止。③将装有填料的卤鸭在120℃左右高温下蒸煮半小时,冷却后真空包装或直接上市。
三、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中国路径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法律的核心任务是应对并解决广泛存在的全球化产物(维护国际市场竞争和网络恐怖主义等,尤其是跨国网络犯罪)。这些全球化产物牵涉的已不再单个国家利益,而是在全球化视野中“面”上国家间利益的博弈。面对跨国网络犯罪的“内忧外患”,中国作为国际舞台中的核心成员,在“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使命下,理性研判、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突围之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法律归化的方式:法治与技治融合,
(1)投入指标。一般来讲,投入指标主要从资金、人力资源两方面来考虑。R&D经费支出和R&D人员投入常被用于表征创新投入。本文选取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来表征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选取R&D经费内部支出表征研发资金方面的投入。
(二)中国刑事法律的国际融合
网络犯罪行为的复杂性与传统刑事法律方面的紧张关系解释了尤其是(为什么)跨国网络犯罪是传统刑事法律的巨大挑战。当然,国际社会治理跨国网络犯罪所付出的努力对我国有很大的启发,为了应对跨国网络犯罪对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促进中国刑事法律与国际接轨的广度和深度。
除了治理跨国网络犯罪国内法制度掣肘,发达国家狭隘的网络治理外交政策是当下中国参与网络犯罪全球治理困境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为提高我国刑事法律的国际协同性,对我国刑事诉讼规则进行协调补遗是中国参与网络犯罪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刑事管辖权的实现首先见于管辖权的确立。我国司法机关在完成对跨国犯罪的立案侦查后,才确定审判管辖权,从而实现我国法院对跨国犯罪案件的间接审理。鉴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设定的审判管辖规则在跨国网络犯罪治理场合的缺憾④ 跨国犯罪案件不能在中国法院进行审判的原因基于两点:一是,犯罪行为地或结果发生地不在中国境内;二是,受害人不是中国公民等。根据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国际犯罪行使中国刑事管辖权,由被告人被抓获地的人民法院进行管辖。这意味着对跨国犯罪的审判管辖权,以被告人的被抓获地法院拥有,该规定在毒品类犯罪中可以实现。但在网络犯罪场合,犯罪行为的虚拟性和跨境性决定了犯罪行为的发生不需要专门进入中国境内实施,但“犯罪收益”一定会出现在中国境内,对在中国境外的外国人而言,由“被告人被抓获地法院管辖”的情形难以实现。 无论从法律原则还是立法技术出发,都需要在刑事管辖权制度中修正,遂本文建议跨国网络犯罪的审判应交由具有专业优势和技术优势的互联网法院管辖。该制度的确立可以通过我国刑法总则对分则中涉及司法管辖权的范围进行规定,以总则中法律原则的方式约束分则中的罪刑规范,建议在《刑事诉讼法》第28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对于网络犯罪案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法院管辖。”
2.填补中国刑事法律国际融合的盲区
德国和欧盟国家一直致力于实体刑法的更新以应对跨国网络犯罪,但这一过程仍有许多盲区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来填补。首先,在实体法方面,需要涵盖对信息社会无形物的刑法保护。其次,在立法技术上,针对信息社会无形物法益需要考虑刑法保护前置化,纵向体现为从公民信息数据权到虚拟财产,横向体现为刑罚权发动的时点前置。最后,在程序法方面,我们需要解决网络匿名、数据加密、数据鉴真、数据留存和披露、提存和保全等程序性规定和跨境数据刑事证据使用的采信规则。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正式赋予了刑事司法协助鉴定与调查取证委托程序的合法地位,为我国参与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提供了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桥梁,这意味着需要我国的实体法配合。遂本文建议将国际条约中的罪刑规范转化为中国国内法,可在《刑法》总则第9条中增加一款:“对本法没有规定的罪刑,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直接适用”。当然,有学者为援引国际条约进行审判涉嫌损害我国司法主权而担忧。但本文认为这种担忧是不成立的。理由有二:第一,中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必须经过国家立法机关论证审查,对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是不会成中国履行条约的义务内容。第二,中国刑事法律体系中缺乏与国际接轨的“实质性”罪刑规范,呼吁以中国刑法为准据法这样的“爱国主义”无异于是空想,这只会导致理论赋予我国刑法拥有普遍管辖权因无法实现审判管辖而被搁浅,公民权利反而得不到国家权力的保护。
2016年以后,国内旅游者行为研究发生了新的转向,研究内容呈现多样化的发展特点。在研究内容上,借鉴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深化了对旅游者不文明行为的探讨;对旅游者的风险感知、具身体验研究逐步深入;旅游流动性的研究新视角不断发展深入,朝着学科交叉、跨文化研究的方向推进。但是,对于旅游者与社区居民的互动、社区居民的心理变化等的相关研究一直停滞不前,研究成果较少。在研究方法上,逐步实现了定量与定性分析的结合,能够运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展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但是,旅游者行为研究的理论概念、研究范式和学科体系尚未构建完全,未来需进一步完善旅游者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
《道德经》的作者老子寿百岁,他说,“死而不亡者寿”,身虽死而不被遗忘的人,才算真正的长寿。这颇像“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现代诗句。
综上,网络空间开放辽阔,数字科技对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严峻的挑战。内在的国内法制度掣肘与发达国家治理跨国网络犯罪狭隘的外交政策,导致中国参与跨国网络犯罪全球治理进程中内忧与外患共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正在经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也正在进行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主基调,相互依存是大势所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主旋律② 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3日第2版。 的国际环境中,化解传统国内法应对跨国网络犯罪失灵的困境、扭转国际社会由发达国家主导制网权的局面、循序渐进的实现中国刑法规则的国际融合,为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网络空间的话语权,是网络强国建设的现实需求,也是中国参与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理性选择。在方法论上我们应当秉持务实、不必陷于削足适履的理论洼地。网络强国的建设,需要理论界砥砺前行,实务界齐心协力。我们相信,中国能力在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舞台上走得稳健、有力。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transnational cybercrime
AN Ke-yin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riminal law,the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transnational cybercrime faces the dilemma of themalfunctioning legalmechanism,which results in a huge gap between the booming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high cybercrime rate.The dilemma of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transnational cybercrime is attribu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f the domestic law and the narrow-minded foreign policy for transnational cybercrime in developed countries,which leads to the coexisten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blems i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control of transnational cybercrime.In view of this,we should aim at building a“community of shared cyberspace destiny”,take“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trolof transnational cybercrime”as the objective,take the real needs of data security and network security as the guidance,and adopt themethod of legal control and technical control,which can promote the Chinese Internet courts to have jurisdiction over transnational cybercrime cases,thereby filling the vacancy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controlof cybercrime,abandoning the dreamlike patriotism,and promoting the essential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riminal rules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Key words: transnational cybercrime;international control;China's participation
【中图分类号】 D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2019)03-0155-06
【作者简介】 安柯颖,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副教授。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信息化背景下跨国网络犯罪研究”(2017M621036)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王东昕)
标签:跨国网络犯罪论文; 国际治理论文; 中国参与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