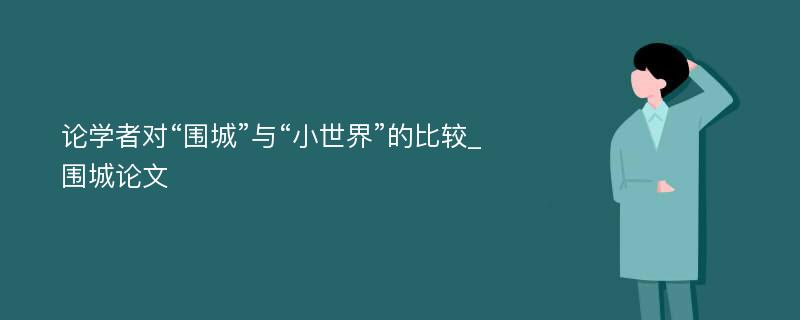
学者的罗曼司——《围城》与《小世界》比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围城论文,学者论文,世界论文,罗曼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身为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的戴维·洛奇于1984年出版了《小世界》一书。此书立刻在大西洋两岸引起强烈反响,不仅被评论界誉为“空前的杰作”,“最有趣、最卓越的小说”(注:弗兰克·克默德,参见中文版《小世界》封底书评,罗贻荣译,王逢振校,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而且还获得了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提名。有意思的是,汉学家们将其称为“西方的《围城》”,这一评价颇值得玩味。中外文学史上兼具评论家与小说家双重身分的不乏其例,但很少真正有人能既写出完整的理论著作,又取得出色的创作成就。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钱钟书先生自然属于少数“兼善”者之一。小说《围城》充分体现了他的博学、智慧与深邃。戴维·洛奇则是当代英国文论界顶尖级人物,尤精于小说理论研究,他总是交替出版自己的论著和小说,两类作品都颇受好评。
通常认为学者小说在字面上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当然是就创作者的身份而言;其二便是指小说人物主要由学者(知识分子)构成。学者小说家“不仅讲述一个故事,而且为了满足他们在知识和文学的其他方面的自我表现的要求而利用长篇叙述体形式”(注:茅国权,《围城》英译本导言,转引自《钱钟书和他的〈围城〉》,张泉编,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可以说,《围城》与《小世界》都是学者小说的典型代表。它们之间既有诸多相似之处,也存在某些有趣的差异,通过一番由表及里的比较,我们或许可以对这一类小说有更深的认识。
首先,不难注意到它们叙述模式的相似性。不少学者认为《围城》采取的是西方流浪汉冒险小说的模式,近于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夏志清就称其为“浪荡汉的喜剧旅程录”(注:夏志清《论钱钟书的小说》,转引自《钱钟书和他的〈围城〉》,张泉编,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这派小说有个特点,便是不大注重故事,因而无所谓结构。作者倒是利用主人公来贯穿全书,这主人公又天生是一副驴马病,永远不会安逸。作者便借了他到处漂泊的机会,来刻划社会各阶层的形形色色”。(注:林海《〈围城〉与〈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读书》,1984年第9期,第62页。 )主人公方鸿渐从国外留学回来,先在上海逗留了一年,结果失恋继而失业——情场角逐中,一组留学生的群像浮现;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进入内地——沿途见到内地社会的人物风气;在三闾大学再次受挫——见识了大学教授们的明争暗斗、丑态百出;从内地经由香港回到上海——结婚后的方鸿渐又要面对各种新旧社会关系。作者以方鸿渐的旅程为线索组接起不同时空,既不囿于一人一事,又不缺乏主干。实际上《围城》和《汤姆·琼斯》一样,不仅实写了旅行,而且备述主人公的心路历程,表现他们在精神上历尽艰辛,揭示了主人公与社会环境的种种矛盾冲突,以此“暴露整个社会的弊端和主人公性格上的弱点”。(注:林海《〈围城〉与〈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读书》,1984年第9期, 第62页。)
戴维·洛奇当初决定创作一部反映当代学术界“狂欢”状况的小说时,曾苦于找不到某种情节结构,将“不同国家各色各样不同类型的学者聚集在一起,使他们在不同地点,不同的聚会中彼此频频相遇,发生纠葛并保持不断的叙述趣味”。(注:戴维·洛奇、《小世界》导言,见中文版《小世界》,罗贻荣译,王逢振校,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第6页,第4页。)后来他受到《尤利西斯》的启发, 决定采取圣杯传奇的神话结构。圣杯传奇的主题是“寻找”,中世纪欧洲文学中曾有法国传奇诗人特洛亚的《柏西华或圣杯的故事》,英国作家马洛礼的传奇巨著《亚瑟王之死》,圣杯骑士们出于宗教动因历尽艰辛寻找圣杯,这种叙述模式恰好可以容纳一大批不同人物的漫长旅程,而且“从当代文坛各种折磨着作家和评论家的挫折与失败中,从在研讨会上得到的戏剧化表现文化生活中野心与情欲的张力中”,(注:戴维·洛奇、《小世界》导言,见中文版《小世界》,罗贻荣译,王逢振校,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第6页,第4页。 )洛奇发现了与圣杯传奇相类似的东西。《小世界》虽然时空变换频繁,具有明显的后现代小说的拼贴特征,但它以柏斯对安吉丽卡这位理想爱人的寻找为主线,让一群学者们顺理成章地在一个又一个研讨会上不断相聚,学者们有的寻求享乐,有的追逐名利,更不用说为谋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评主席这一诱人职位而展开的争斗。复调的“寻找”主题反映了后工业化社会中文人的普遍堕落。
流浪汉小说与骑士传奇的相似之处是明显的,它们都以主人公的游历来推动故事的发展,使叙述得以保持开放性,能不断引入新的角色和事件,便于人物群体的刻画。主人公在每一段历程中都会遇到新的危机的产生与化解,所以全篇时有高潮,并不因结构的相对松散而令人感到冗长或杂乱。其实,《围城》除整体采用流浪汉小说的框架外,亦包含罗曼司的特征。比如有的学者就认为故事一开始苏、鲍二位小姐都戴着墨镜在船头出现的场面即预示全书是“引诱与追求”的戏仿罗曼司,而后来赵辛楣与苏文纨,方鸿渐与唐晓芙,方鸿渐与孙柔嘉,乃至赵辛楣与汪太太之间的分分合合也确乎不脱这一模式。
学者小说的特征还体现在文本的互涉表现得十分突出。解构主义者认为,互文性是文学的根本条件,不存在任何独创性的作品,所有文本都是用其他文本的素材编织而成的,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用一种文本去指涉另一种文本的形式多种多样:模仿、戏拟、附合、暗指、引用等等。无论钱钟书还是戴维·洛奇,作为一流的文学评论家,他们对文学史上各类文本的了解超过一般作家,先前的一切文本都是他们可以利用的素材,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利用文本的互涉,大大扩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丰富了小说的意味。
《围城》中使用较多的手法是暗指和引用,书名就是一种象征,借用了法国成语“被围困的城堡”,与这一成语相呼应的是书中还提到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注: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这两句西洋谚语概括了人生的困境:爱而不得,得非所愿——这是小说的基本主题之一。方鸿渐的名字似乎也很有讲究。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有过一番“圆方论”:西方古称有定力而不退转之人为“方人”,后称骨鲠多触忤者为棱角汉,现代俚语则呼古板不合时宜为方。(注:参见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21—930页。)小说中的方鸿渐虽然怯懦,但总与环境格格不入,又不肯“磨合”,每到关键时刻都不能圆滑变通,以至屡屡陷入窘境。另外美国学者胡定邦指出,“鸿渐”一名出自《易经》“渐卦”,该卦辞中含有六“变象”,“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注:参见赵一凡《〈围城〉的隐喻及主题》,《读书》,1991年第5期,第33 —41页。)一只水鸟由海上飞来,渐次栖于滩头、岸石、陆地、树木、山陵与水边,仿佛经历一场犹豫不定的寻觅,这与方鸿渐香港——上海——内地——经港返沪的人生旅程暗合,主人公就像一只居无定所的水鸟,总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钱钟书先生自己在《管锥编》中曾多次评点《周易正义》并引用“渐卦”,也可作为佐证。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唐晓芙之间的多角恋爱,更是锻炼集约了多种西式小说特征,仅在英国文学中就能寻到多处踪迹。既有类似莎翁《皆大欢喜》、《仲夏夜之梦》等剧的青年男女捉对笑闹,误会不断的情节,又有简·奥斯丁的沙龙闺秀小说遗风,而作者在叙述进程中不时穿插冷峻而睿智的评论,且从不放过讥讽每一个人的机会,这一做法与从萨克雷《名利场》到赫胥黎、伊夫林·沃的学者讽刺小说似有一脉相承。至于《围城》中其他或明或暗的引经据典更是举不胜举,仅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董斜川等人在饭桌上的谈话,对各种文本的征引就令人眼花缭乱。这种文本互涉的效果倒是可以借小说中那位专写“杂拌儿”诗的曹元朗的话来评述:“诗有出典,给识货人看来,愈觉滋味浓厚,读一首诗就想到无数诗来烘云托月。”(注: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如果说由于钱钟书先生很少谈及自己的小说,对他作品中互文性的分析有较多揣测的成分,那么戴维·洛奇则不止一次以自己的作品为分析对象,并明确提醒读者注意文本的互涉。洛奇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素有研究,他承认“因为我把写小说与学术生涯结合近三十年了,毫不奇怪,我自己的小说越来越间涉各种文本”(注: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而在《小世界》中,他对互文性的利用则达到了一个高峰,有的评论家干脆称之为“关于小说的小说”。副标题“学者的罗曼司”表明他借用了传奇故事的文学形式,“罗曼司”一词有多种涵义,它既指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故事,冒险故事或爱情故事,也指传奇文学,风流韵事或夸大的描写与虚构。洛奇选择这一文学体裁显然是有用意的,《小世界》的情节确实包含了上述多种要素。主人公柏斯的名字是圣杯骑士“柏西华尔”的简称,姓氏“莫克加里格尔”意为“超级猛士之子”,柏斯执着地寻找安吉丽卡(与《疯狂的奥兰多》中奥兰多疯狂追逐的对象同名)正像柏西华尔寻找圣杯一般虔诚。文学评论界的元老金·费舍尔(Fisher King)不但失去了创作的冲动,也失去了性能力,恰恰对应于圣杯传奇中那位统治着一个了无生机的国度的渔王,渔王贫瘠的土地由于圣杯骑士问了必要的问题而丰腴起来,《小世界》的结尾处,柏斯在批评功能小组会议上的提问使金·费舍尔忽然找到灵感,恢复了青春。这样的戏拟指涉的不仅是中古传奇,还有同样利用这一素材的其他文本,如艾略特描绘现代人性生活和精神生活之萎顿贫乏的长诗《荒原》,以及杰西·韦斯顿《从祭仪到神话》中对圣杯传奇的重新阐释,从而提醒读者圣杯传奇“荒芜与拯救”的主题正在重演,当代文明萧条衰败,渴望救赎。书中还经常提及《亚瑟王之死》、《疯狂的奥兰多》、《仙后》、《圣爱格尼斯之夜》等传奇性长诗,这些传统罗曼司中充满的浪漫与激情无疑构成对当代社会肉欲横流的反讽,骑士们胜利的征服更与柏斯永远失败的追寻形成对比。
洛奇对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推崇备至,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包含多种话语的交流和冲突,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其他人的语言,小说家应在其中调整自己的方向,并细心倾听那些最富特色的言谈,将他们引入自己的话语”,(注: David Lodge,After Bakhtin:Essays on Fiction and Criticism,London & New York,Routlcdge,1990,p.7.)作为小说家的他面对过去文本的海洋,“注定要进行拼贴、戏拟和模仿,而对象恰恰是我作为学院派批评家提出的那些话语。”(注: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小世界》是多部文学作品和各种新潮文论的大举拼贴。洛奇以一种狂欢的精神来处理形形色色相互竞争的文评理论,他把精神分析、女权批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等拼贴到一起的同时,又对它们加以夸张和戏拟,使之无一不显得荒唐可笑。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部小说写作技巧之高明和独特,充分体现了创作者与众不同的一流学者身份。但我认为,真正优秀的学者小说还应不止于此,学院与社会息息相通,作家应当通过揭示他最熟悉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而批判地反思当时的社会现实;应当通过考察知识分子的人生旅程,进而反映整个人类生存状况,这就不是任何一部学者小说都能做到的了。《围城》与《小世界》则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深入的开掘,或许这也是它们更深层次的可比性。钱钟书先生在《围城》序言中明确指出:“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注: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所以“《围城》的思想批判意象始终是指向整个人类存在的,它的审美概括是涵盖整个人生——当然事实上主要是现代文明中的现代人生。”(注: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第74—78页。 )而《小世界》的书名本身即意味着在当代西方社会,学院以外的广大天地已成为供学者们自由来往的“小世界”,正如书中人物扎普教授所说:“最近二十年有三件东西——喷气机、直拨电话和静电复印机——使学者生活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注:戴维·洛奇《小世界》,罗贻荣译,王逢振校,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洛奇对这种变化并不持乐观态度,他要表达“环球大学的学者们从中国到秘鲁的喷气机旅行中所显现的人类追名逐利的欲望”(注:戴维·洛奇、《小世界》导言,见中文版《小世界》,罗贻荣译,王逢振校,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第6页,第4页。 )而这当中蕴含了从社会批判到文化批判的多重主题。
两位作家对小说中的人物都极力嘲讽,表现了对当时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强烈批判。方鸿渐一行从上海到三闾大学的旅程中碰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寡妇、妓女、司机、汽车站长、下层军官,他们构成了当时腐朽堕落的社会图景。在这样的社会中,知识分子也无一正面形象,卑鄙无耻的李梅亭,谄媚逢迎的顾尔谦,老奸巨滑的高松年,这些社会的“精英”们或可鄙可恨,或可笑可怜,既没有崇高的价值追求,也没有完善的道德品质,他们所受的教育似乎只是让他们更虚伪、更阴暗、更善于勾心斗角。一所三闾大学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其中复杂的派系斗争,错综的人际关系,足以令人生畏。作者的讽刺无处不在:方鸿渐等人在咖啡馆关于教育的谈话,对三闾大学推行导师制的描写,是对当时教育制度的猛烈抨击;说方鸿渐以三十美金从爱尔兰那里骗得文凭,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写曹元朗婚后托丈人的门路在“战时物资委员会”当处长,则揭露了国民党外交上的无能和政治上的腐败;对方鸿渐那位患有“语文狂”的老父亲的刻画,更是无情地嘲弄了传统文化观念。钱钟书以他敏锐的洞察力看穿桩桩表象背后并不光彩的本质,将世态种种一一剖析,使读者看到,当“世界从理想化的道德秩序结构向经验化的无道德秩序结构过渡之际……把现实世界的道德类型描绘成一幅讽刺画,比它在这种讽刺里所针对的理想化艺术和观念中所呈现的图景更真实”(注:胡志德《钱钟书》,张晨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小说《围城》因而具有了广阔的容量和深刻的内涵。
《小世界》“狂欢化”的写作方式和“复调”的主题也为我们展现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普遍危机。“校园中那些在性爱和学术方面放纵的游戏,正是绝对价值标准遭到轻视的范例。”(注:D.J.Taylor,After the War:The Novel and England Since 1945, London,Chatto & Windus,1993,p.183.)我们看到学者们走火入魔一般乘着喷气机飞来飞去,参加名目繁多的研讨会,可他们并非被探求真理的愿望所驱使,相反“他们的行动是出于职业上的嫉妒,他们希望的不是从运用自己的才能中得到乐趣,而是在权威杂志上发表文章或在现代语协的会议上作一次演讲,同样,他们进行文学研究的方法也不是依赖于诚实的评价,而要看什么技巧最时髦。”(注:戴维·洛奇、《小世界》导言,见中文版《小世界》,罗贻荣译,王逢振校,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 5页,第6页,第4页。)在这里,学术界的种种被充分曝光,学者们为“专业上的自我表现和性爱机会”而争斗不休,为了研讨会后丰富多采的消遣才忍受着枯燥的讨论,在争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评主席的过程中更是丑态毕露。出版商、作家与评论家相互勾结又相互诋毁;老学阀对青年学者的排挤压制;弄虚作假,剽窃之风盛行……所有这些,“形成了对当代文坛不留情面、一针见血的实况报道。”(注:转引自杨济彧,吴立平《多重译码:游乐于〈小世界〉话语的张力场》,《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第75页。)不仅如此, 我们从书中对“少女无限公司”的描写及史沃娄、温赖特教授诱奸女学生、扎普教授遭绑架风波等情节中,还可以看出整个西方社会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极度发达,另一方面却是精神生活异常空虚。人人奉行享乐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原则,金钱成为驱动一切的力量。
除了在写作手法上对互文性的利用以及通过学者圈子反映社会风气的共同特征,钱钟书和戴维·洛奇还分别在各自的主人公身上凝缩了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思考,这就使得两部学者小说更具典型性。《围城》和《小世界》都是以一位男主人公的经历为线索,贯穿起各个片断,只是前者仍严格遵循时间顺序,后者多采用空间并置手段。总的说来,方鸿渐和柏斯都是与现实无法融合的“局外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总是与实际生活不断发生冲突。方鸿渐始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买假文凭、被鲍小姐引诱、与苏小姐周旋、对赵辛楣的依赖,这些暴露了他的虚荣、玩世而又怯懦、无能;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与丑陋的外部社会同流合污,正直、认真、清高、善良这些品质在他身上仍留有印记,他在给高松年的信中并未填写假博士学位去换取教授头衔;他嫌恶李梅亭和顾尔谦,觉得与他们为伍是“可耻的堕落”,他两次被动陷入感情纠葛,部分原因也是他的善良。如果他能像苏文纨或李梅亭那样相时而动,不避污俗,或许不致处处失意,如果他能接受孙柔嘉那一套精明而实际的处事态度,或许还可以守住家庭这最后一方避风港,但方鸿渐的心理时空和社会历史时空始终存在错位,不管处在什么情境下,他都是个无从把握自己社会角色的局外人,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却对已经得到的一切都不能满意。他不是没有过爱情和事业的追求,可现实逼他不断妥协,他也只能委屈求全,以至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与他人越发隔膜,直至连婚姻也无可挽救,以彻底的失败和幻灭而告终。
如果说《围城》到了最后几章,对方鸿渐人生幻灭的描写越来越带有悲凉的调子,戴维·洛奇在《小世界》中则始终以充满喜剧色彩的调侃语气叙述柏斯的不合时宜。他的存在与方鸿渐一样是一个“错位”,他在生活观和学术观上处处与他人发生话语冲突。在肉欲横流、享乐主义盛行的后工业社会,只有他还信奉“婚前的贞洁”,视安吉丽卡为纯洁爱情的化身;在解构批评已成时尚的学术讨论会上,他却向人询问究竟何为结构主义;在人人忙于追名逐利的时候,只有他还写诗,固守心中那一份古老的浪漫。如此种种使柏斯看上去简直像一个不小心闯入当代社会的陌生人。但他远非古代传奇中的圣杯骑士,而是一个和方鸿渐一样不能正确把握现实世界、处处失败的“反英雄”形象,即使他最后对文学评论界的“拯救”,也纯属门外汉的歪打正着,洛奇对他的态度与钱钟书对方鸿渐的态度相似,兼有同情和嘲讽。最大的嘲讽当然是他追求安吉丽卡的失败过程,他为与安吉丽卡幽会而偷偷去买避孕套,却错买成婴儿食品;他担心第一次约会缺乏经验,红着脸去看色情电影,结果深感纯洁的爱情被亵渎;作者偏偏让柏斯在几近绝望时候,误将从事色情业的丽丽认作孪生姐姐安吉丽卡,与之春风一度后,他“感到老了十岁,也聪明了十岁,他品尝了甘露,他饮过了天堂的琼浆”(注:戴维·洛奇《小世界》,罗贻荣译,王逢振校,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525页。),这一极具反讽意味的结局无疑表明,表面上看, 柏斯有着比方鸿渐更坚定的目标,可他所追求的安吉丽卡仍如镜花水月,十分虚幻,并不见得是唯一的真正的幸福。实际上丽丽说得不错,他“爱的并不是安吉丽卡,而是一个梦”(注:戴维·洛奇《小世界》,罗贻荣译,王逢振校,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528页。)。
方鸿渐与柏斯从追寻到失落的人生经历,反映了人类生存的某种普遍困境。他们两人都置身于历史转型和文化变迁的背景下,却不明就里或不甘随俗;他们都有尚未泯灭的理想主义,却不能适应现实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话语的断裂、差异、冲撞、颠倒中无所适从,屡屡碰壁。从与唐晓芙的恋爱失败,到丢掉三闾大学的工作,直至婚姻生活成为新的战场,方鸿渐良好的初衷,认真的努力从未给他带来如意的结局。“他的人生经历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的收获而是失败的总和,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幻灭。”(注: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第74—78页。 )这正是对现代文明中,人在种种异己力量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状况的揭示。方鸿渐让我们看透了“人生万事如围城”——“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注: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2页。)——得到了, 却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柏斯对安吉丽卡永远失之交臂的寻找过程,则象征人生注定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追求,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要的总也得不到。这正是同一种生存困境的两个方面。但人却还是要不断被引诱,洛奇有意让柏斯在小说结尾又开始了新的寻找,其结果可想而知。洛奇在《小世界》中引入西方语言学关于所指和能指理论,也是为了阐明:“现实生活尤如语言本身,在表意与实际意义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差距。”(注:申慧辉《曲高未必和寡——谈戴维·洛奇和他的〈小世界〉》,载《文艺报》,1991年6月29日“世界文坛”版。)
经过由表及里的层层剖析,我们不难看到,《围城》和《小世界》既各有特色,又殊途同归。对叙述模式的选择和对其他文本的或明或暗的指涉,体现了作者过人的学识和开阔的视野,若非两位一流学者,很难有如此手笔。但如果仅限于这些,还不足以成为堪称典范的学者小说,钱钟书和戴维·洛奇更在各自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从他们最熟悉的学者群体入手,批判地反思当时的整个社会状况和人的普遍生存困境,正是在这后一个层面上,他们的作品取得了更深刻的一致性,从而也对学者小说这一名称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