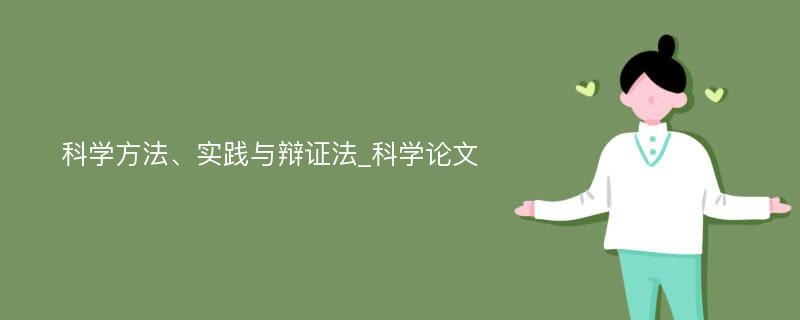
科学方法、实践和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科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笔者原治工程和科学,坚信科学方法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现虽改治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仍以科学方法研究哲学,认为研究哲学和研究科学的方法并无不同,研究两者都应该用科学的方法。
笔者曾听大陆的友人谈起,毛泽东的“实践论”曾经脍炙人口,为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经典之作。(注: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136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也屡次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于此可见实践之重要。对此笔者深信不疑,并且认为实践也是科学方法之一。
又马克思主义中,辩证法唯物论为其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者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可见辩证法也是科学的。
然而,科学方法中传统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与实践以及辩证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是否三者为不同的科学方法?应该用于不同的问题或不同的场合?或者三者应该用于同一问题的不同层次或不同的情况呢?本文试图讨论此三者间的关系并予以诠释。
二、传统的科学方法
传统的科学方法主要有二:一为归纳法;二为演绎法。另外还有统计的方法,可视为归纳法的旁支。
归纳法从实际情况中归纳出几个变数间的关系。如果每次实际情况中变数间的关系不变,即可获得一定律(law)。举一最简单的物理学的例子:如加一力F于一固定质量M上,其加速a与所加之力F成正比。用数式表示如下:
F=Ma
这是物理的力学中最基本的加速定律。
物理学的研究,分理论和实验两种。任何新的理论,开始时都是一种假设。假设经推导而并不发生矛盾,即可初步成立,但尚须经过实验的证明,才能完全成立,而成为一种定律或理论。换句话说,定律或理论必须用实验证明。一旦证明以后,就可以相信其为几乎永远可靠,笔者用“几乎”二字是因为物理科学中也有基本观念的改变,例如从牛顿的古典物理学发展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另有一种统计的方法,可视为一种独立的方法,但也可视为归纳法中之旁支。当个别的现象太多而不可能研究或不值得研究时,我们往往舍弃了个别的微观现象而用统计的方法去研究集体的宏观现象。因为统计的方法用的仍是据于实证的归纳法,所以可以视为归纳法的一个旁支。
至于演绎法,则是用于逻辑和数学的推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集合理论。我们定下了一个包含几个元件的集合,几个运作的方式和几个公理,那么就可以导出集合和次集合间的许多关系,亦即是证明出许多定理(theorem)。逻辑和计算机科学中用的波林代数理论,与集合理论是同形的,其情况也完全相同。
通常演绎法除了用于逻辑和数学的推理以外,也用于自然科学理论的延伸、扩张和普遍化。我们往往从重复的实际经验中用归纳法归纳出一套粗糙简单的理论,然后再用演绎法延伸和扩张这套理论,使其精化、深化、复杂化和普遍化。
归纳法和演绎法二者不可偏废。过去重视经验或归纳,易流于哲学上的经验主义。过于重视推理或演绎,则又易流于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二者之间,应取得适当的折衷或平衡。
此外,哲学的思考中有一种所谓的内省法,系用自觉或形上学的推理去悟出宇宙、生命和人生的道理。这是一种非常唯心的说法。笔者不认为是一种科学的方法。用内省法去发现宇宙和生命的起源或是诠释宇宙和生命对笔者而言是一种不可思义的事。现在哲学的宇宙论已经演化为科学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和地质学等。至于知识论中的哲学部分也在逐渐减少而由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所代替,因而产生了认知科学。当然,在研究价值论、人生哲学以及道德哲学时,内省法仍有它的用处。不过笔者认为内省法并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科学方法,所以也不在讨论之列。
三、对实践的诠释
实践的重要性,早已被毛泽东和邓小平提到、说明和强调,毋需多赘。笔者这里要提出的,是个人对实践进一步的诠释。任何知识都与哲学有关。上面曾经提到,过份重视经验,发生哲学上的经验主义;过份重视理性,又发生哲学上的理性主义。除此之外,任何知识,都具有知识或真理价值(epistemic knowledge),这就牵涉到了价值论。但我们在做研究工作时,平常很少想到所追求的新知识究竟有多少价值,所以这知识或真理价值,可暂时撇开不谈。但是有几种哲学,与知识的追求、理论的建立和实践的定位有密切的关系。这几种哲学是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以及讨论到知识于应用时所发生的效用之价值论。这其间的关系复杂,必须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开来看,也须把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分开来看。
先看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
大部分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都与时间有关。不用说动植物的生长离不开时间的因素,物理学中速度和加速度的概念以及电子的流动、电磁波的传播等都是动态的,也因而都与时间有关。与时间有关都有历史的发展,都需要研究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但是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动态研究不十分需要历史哲学,因为这些历史发展都是显而易见的,很容易从观察中发现。除了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我们还可以作人为的实验,在设定的及排除不相关因素情况下做实验,因而很容易找到许多因素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的最终目的都是在应用,亦即是研究的结果可以应用到人生中,对人类或社会有效用或价值。但是人类对研究学问有一种天生的好奇或兴趣,在研究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时并不一定会想到其将来的应用。例如最初研究核子科学的人并不一定会想到将来的核子炸弹和核子发电;波林发现波林代数更没想到它会成为计算机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虽然最后可以应用而对人类社会发生重大的价值或效用,但这种纯学术的研究并不需要价值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作为必不可少的一部份。
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时常需要实验来证明理论,这可以说是实践。但是严格而论,实验是研究过程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说这实践不是我们平常所指的社会科学中的实践。
至于应用方面,则情形就不同。物理科学的应用是工程,生命科学的应用是医药和农林。例如土木和机械工程是力学和热学的应用,电机和电子工程是电磁学的应用,化学工程是化学的应用,矿冶工程是地质学和化学的应用,医学是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应用,农学是动物学和植物学的应用等。
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也并不十分密切,也可以说这方面的应用并不十分需要历史哲学,但是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应用与价值和效用则密切相关,因为任何事物的应用,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对人类社会的效用。效用与价值有关,所以应用与哲学价值论相关,也与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相关。道德哲学中的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旧译功利主义),尤其是笔者所改建的统合效用主义(unifiedutilitarian theory)(注:盛庆著,顾建光译:《功利主义新论——统合效用主义理论及其在公平分配上的应用》第二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则是基于笔者的效用主义一般性价值论(注:C.L.Sheng,A Utilitarian General Theory of Value (Amsterdam and Atlanta:Rodopi Intrnational Publisher,to bepublished in 1997)),并包含一种效用理论(utility theory)的道德哲学,最适合于诠释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哲学观。目前西方的道德哲学,效用主义衰退而道义论盛行。但道义论为唯心的,虽为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所相信,理论上却缺陷甚多(注:盛庆著,顾建光译:《功利主义新论——统合效用主义理论及其在公平分配上的应用》第二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90-296页。),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过度的自由主义和人权论以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幸的是,还有许多经济学家是自然的效用主义者。笔者深信统合效用主义理论除了最适合于诠释物理哲学和生命科学的应用之外,还足以驳斥资本主义并支持社会主义的一种学说。
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应用也可以说是理论的实践,但其意义还不及社会科学的应用那样明显和强烈。
社会科学与物理科学及生命科学间有几点基本的不同。这些不同点笔者认为主要是内容上的而不是方法上的。彼德·柯索(Peter Kosso)最近曾为文表示同样的看法。他说:
那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何不同呢?人们为什么称社会科学为软性的呢?这并不在于社会科学的知识结构或基本方法。以显微镜作为类比来讲,并不是社会科学使用异于自然科学的造像装置,不是这些装置有些软性而对标本造成模糊或不可靠的形象。每个人均用同类的显微镜。任何不同必在于标本之性质本身或透镜之品质。社会科学中被用以赋与社会科学的意义的理论或许与自然科学中者不属于同一种类。这是所声言的内容之问题而并非这些声言的方法论形式之问题。(注:Peter Kosso,"Scientific Metho and Hermeneutic,"The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34,No.2(Summer 1996),pp.169-182.)|柯索并未明确指出内容的不同究在何处。笔者则认为基本的不同点是:(一)社会科学研究难以做实验。(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中常有许多无法预知的因素。(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应用或实践相互依赖和影响。
现将这三点相异处分别说明如下。
(一)社会科学研究难以做实验。
社会科学研究难以做实验,是因为实验(社会实践)不能在实验室做,而必须在社会中做。如果实验的范围很大,会影响到很多人民,甚至整个社会。如果实验成功,固然很好;但如实验失败,会使人民受到很大的损失,并会引起社会的不安、混乱甚至崩溃。举个现实的例子,俄国听信了美国经济学家的话,想用震撼治疗(shock therapy)来改善经济,结果经济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引起物资奇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弄得民不聊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败。这样的实验,当然应该审慎,不可贸然从事。事实上在社会科学方面,理论的应用就是实践,也就是实验。如果有可能失败,而失败的结果又可能十分严重,但又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那么应该从小规模的实验做起,万一失败,则立即用从实验结果获得的知识来修改理论。这样从小规模逐渐推广至大规模,方可不引起严重的问题。
(二)社会科学中所研究的对象有无法预知的因素。
现在研究社会科学,大多应用一般系统理论,将社会视为一个系统,研究许多变数间的关系。任何有关社会的系统都包含了许多未知的因素。即使在理论上我们掌握了所有重大的因素而建立了一个系统或模式,理论也未必完全无误。而且,即使在第一次的实践中未考虑到的小因素未起作用而实践成功,在这个特例中证明理论无误;但也许在第二次的实践中某个或某些小因素起了作用而使实践失败。如果那样的话,理论如果不被完全推翻,至少要加以修正。所以社会科学的实践不是一次就够的,而需要继续不断地用实践来检验理论中的真理。
关于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之所以没有不可知的因素或可以建立一个能避免次要小因素的影响之模式,可以用简单的物理科学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实验主要是将环境维持恒定或将其他的变数消除,专门去寻求两个或几个我们已经知道其存在的变数间之关系。因此,如果实验正确无误,这些变数间的关系即可确切求得,并可据以建立一个模式、一个定律或一套理论。
严格而论,社会科学里的实践也可以说是归纳法的一部分,因为它和实验一样,也是根据实际的经验的。但是,由于社会科学的对象是社会,理论的实践是政策、制度的建立,法令规章的制定,或是对某一重大计划的整个实际执行,我们既无法将环境和其他变数维持恒定不变,也根本不知道除了已经考虑到的变数以外还有些什么未考虑到的其他变数。从某一实践的结果,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一些前所未曾考虑到或被忽略掉但是足够重要而必须加以考虑的新变数,据此我们可以修改理论,但也许从另一实践的结果,我们并未发现值得重视的新变数,因此也无法据以将理论加以修改。这是为什么每一次实践,都要注意其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任务,若有新的发现,可据以修改理论。
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句话,虽然对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并不显著,但对社会科学则是非常重要。传统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是科学的方法。用实践来检验真理也是科学方法。二者相辅相成,都是必不可少的科学方法。
其实真理之需要检验并不限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也是如此的,不过自然科学中一旦理论建立之后,维持不变的时间较为长久而已。例如牛顿的古典物理理论因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建立而必须加以修改。又如几年前我们只知道原子中最小的单位是核子和电子,而现在已经有顶垮克了。说不定在未来还会发现更新更小的颗粒。物理科学理论之所以可以维持较久时间不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能影响理论的小因素较少和较易被发现,二是新的理论主要系在较高的层次而并不完全否定旧理论。
(三)理论与实践相互依赖和影响
在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中,理论研究的对象往往受到应用的影响。例如在IBM公司中有庞大的基础科学研究,但是这些基础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应用在计算机上。因此,在整个社会中,能有应用的基础研究远较缺少应用的基础研究为多,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理论研究所得的结果则并不受应用的影响。这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研究所获得的真理不受应用的影响:二是研究不需要有关应用情况的资料作为研究的材料。
在社会科学中,则理论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正在被应用或实践的事物。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如风俗、习惯等,比较自然客观,但是即使风俗习惯,有一部份也是有心人士具有目的而刻意造成的。动物中也有社会,例如蚂蚁和蜜蜂。它们的社会可以说是完全自然的。人类的智慧水准和理性远较动物为高,因而社会的形成具有人为的成份。至于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则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典章制度。政治学研究政治制度,经济学研究交易行为和经济制度,法学研究法律。这些制度或法律都是人已经或者可能建立制定的事务,也就是实践。由此可知,理论和实践是相互关连而逐渐发展出来的。实践要依据理论,但理论要有实践的事物作为其材料或对象。二者必定同时发展,而并没有自然存在的社会事物作为纯粹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理论和实践二者密切相关而不可分割。物理和生命科学的理论研究是发现,而应用则是发明、创造和设计。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不单是发现,也包含发明、创造和设计在内,是一种综合的思想。
因此,社会科学和哲学密切相关。因为要考虑这些社会思想的历史发展原因,所以与历史哲学有关。在历史哲学中,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最为透彻和明确。实践要考虑效用或是社会成员的福利,所以与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有关。而在许多不同学派的道德和社会哲学中,笔者认为统合效用主义是最适宜最理想的学说,因为(一)统合效用主义是目的论,因而是经验的而无需形上学作为理论基础,也就不会成为唯心论;(二)统合效用主义用决策的方法,因而是科学的并且量化的;(三)统合效用主义包含效用理论,因而与经济学相容。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知道,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实践必须有理论指导或作为依据。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理论有时又必须赖实践来加以修正。
四、辩证法的特质
辩证法源自希腊哲学,到康德和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而形成了第二个形态。(注: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页。)但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错误的。他说:“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顺过来,才能从其辩证的外壳中发现合理的核心。”(注: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页。)恩格斯又详细说明黑格尔唯心论辩证法的错误之所至。他说:
这样,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引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而已。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从量转化为质和从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所有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以其唯心论的方式只当作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分中,在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是整个体系构成的根本规律。错误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硬加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面,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注:恩格斯:“辩证法”,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39页。)
此外,英国的罗素也曾对黑格尔的绝对现实有甚为严厉的批评。(注: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tenthimpress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82-88.)
本文不谈辩证法的历史发展及唯心唯物的问题,而只将辩证法作为一个科学方法来加以讨论。作为一个方法,辩证法的原义是,当处理一个问题时,必须考虑正、反两方面的理由,权衡利弊得失,以达到阶段性的了解、结论或决定,然后准备向较高层次发展。
笔者认为,辩证法有两大特质:(一)它对社会科学和哲学比对自然科学更为重要。(二)它是一个无所不适,无所不包,最高层次的一般性科学方法,可以应用或延伸于任何场合。
关于第一个特质,前已在第三节中予以讨论。自然本身也有其系统性、层次性、历史性和辩证性等,并且反映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方法中(注:钱学成:《自然与科学技术论》,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0页。)。但是自然科学的未知数较社会科学为少。而且一个理论成立以后,它可以解释现有的一切。至于社会科学,则旧的理论可以在某一时期或在某一情况下看起来很对,但在另一时期或另一情况下变成大错。旧的理论也许未考虑一个在当时并不存在、尚未发现或未起作用的因素。所以旧理论可以解释当时的现象,但不足以解释新现象,而被新理论所取代。在社会现象中,因为因素太多,我们非得忽略掉若干无足轻重的小因素不可,但是这些被忽略掉的小因素是否的确无足轻重,则极难预知。因此,我们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未被考虑却值得考虑的因素。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用实践来检验真理,也要继续不断的应用辩证法的缘故。
现再从质量间的变化来说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间的不同。恩格斯说:“到这里为止我们所讲的只是关于无生命的物体;对于有生命的物体,这个规律也是通用的,其情况非常错综复杂,现在我们还往往不能进行量的测定。”(注:恩格斯:“辩证法”,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40-41页。)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注释,“质量互变的规律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毫无疑问,它也完全适用于生物体。”(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编:《自然辩证法简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1页。)
笔者认为就质量问题的变化而论,物理科学最明显简单,生命科学较为复杂,而社会科学最为复杂。举例说,在物理学中,水吸收热量使温度上升到100℃时水就变成蒸汽,热量的增加是水变蒸汽的唯一因素。再举一社会科学中相当的例子。如果一个政府腐败和暴虐到人民所不再能忍受的某种程度,那么人民就会起来造反或革命。这个腐败和暴虐的程度是否能确切量度呢?又即使腐败和暴虐到某种可以引起造反或革命的程度,人民是否一定造反或革命呢?这还难说,因为造反或革命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关于第二个特质,笔者认为辩证法的正、反两方,不一定是相互发生矛盾并具有无可妥协的敌对立场,而是可以延伸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选择或不同的程序。而且其间的冲突可以消解,或是两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因此辩证几乎可以应用于任何场合,笔者提出几种重要的可能延伸,并简单说明如下:
第一种是决策中的可能选择。假定透过节选,只剩下两个可能选择。每个选择有其优点和缺点,必须反复推敲。
将辩证法延伸于决策,是相当适切的,因为辩证法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是量的变化可以导致质的变化,例如水加热后温度增高,是量的变化,但到摄氏一百度,水从液体的状态变为气体状态的蒸气,就是质的变化了。决策有时也有相似于从量变到质变的特征,兹举一个例子以说明之。假定两个重要城市之间的交通量增加,需要增建一条高速公路或铁路。又假定一条公路或铁路的功用已经足以应付增加的交通量而有余,而且经费也只足够修建一条公路或铁路,而不够同时修建二者。因此问题是在公路和铁路两者之间选择,这就需要一个可行性研究来决定二者的利弊得失,也就是比较二者的总效用作为决策的准则。假如二者的总效用相差无几,并假定原先是公路的效用比较稍大,倾向于兴建公路,但是有人提出了一个原先未曾想到的铁路的优点,例如目前已经研究成功的高速火车可以提前获得实践。这增加了铁路的效用,使最后的决定为兴建铁路。从兴建公路改变为兴建铁路是一个质变。但是这质变的决定却是系于效用的量变,而且是由于许多因素中间的最后一个因素之加入。这个决策的例子不一定需要用辩证法来解释,但笔者认为将其视为辩证法的延伸,似乎非常贴切。
第二种延伸是上节所谈实践中所需要的历史哲学和道德哲学效用主义间的往复。历史哲学是考虑时间性的因果关系,是动态的;效用主义则是考虑某一状态下的最大效用,是静态的。这两者间的反复推敲也可以解释为辩证法的延伸。又社会主义的理论无法预先定出每一实践中的每一个细微末节,这些细微末节必须由实践中决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即是历史的必然性,也可说是宏观的看法。但是历史的必然性只是宏观的大概趋势,细微末节太多,而且其中包含了许多偶然的因素。笔者前曾讨论并说明要将这些偶然的因素筛去只保留必然的部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注:C.L.Sheng,"On the Basis of Social Philosophy,"inRevolution,Violence,and Equality,ed.Yeager Hudson andCreighton Peden(Lewiston,New York:The Edwin Mellen Press,1990),PP.381-398.)因此,提出了将统合效用主义加于马克思主义作为辅助而以决策理论的方法去完成实践。(注:盛庆:“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心得”,《纽约侨报》1995年9月23、28、30日。)从这点看来,决策理论也可以说是微观的看法。二者相辅相成,可以获得较大的期望社会效用。
第三种延伸,也是我们最常遇到的情况,是宏观立场与微观立场间的差异。这种立场间表面上看来似乎有矛盾或冲突,而事实上我们处理事务时需要有这样两种不同的立场,由于这两种立场之相辅相成才可以完成任务。
第四种延伸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间的往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理论初步建立以后,指导实践并应用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是否真理,也就是检验理论中有无错误,如果没有错误,我们可以继续用理论指导并应用于新的实践。如果有错误,则根据实践的结果去修正理论。于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修正理论,这两者间之往复作用也可视为辩证法之“正”“反”两面,而这两者之反复辩证也自然提高了理论和实践的素质和层次。
依笔者看来,辩证法的目的,其实就是运筹学中的求最适化(optimization),或是科学的决策方法中的求最大期望效用。
但是运筹学和决策理论是静态的,而辩证法则是动态的。笔者曾在另一篇小文中用三种科学理论来诠释“摸着石头过河”这句名言。这三种科学理论是:(一)统计学中的贝氏定理;(二)运筹学中的动态规则;(三)控制学中的适应性控制(注:子东:“从科学观点谈‘摸着石头过河’”,《经济评论》总第78期(1996年第2期),第38-39页。)。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个具体例子,正好作为辩证法的历史和动态特质的例证,也说明了为什么辩证法是一个无所不适、无所不包的最高层次的一般性科学方法。
标签:科学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实验物理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生命科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