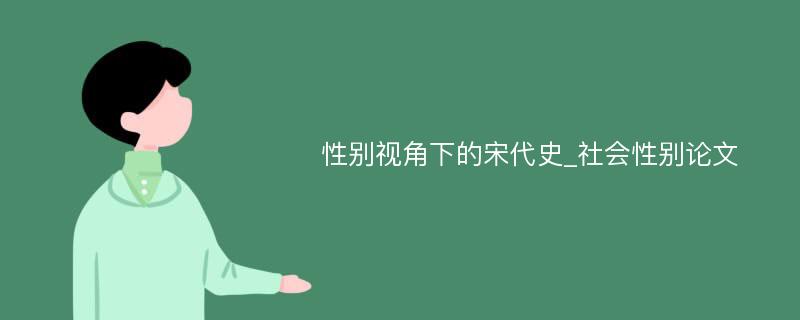
性别视角下的宋代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视角论文,性别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常荣幸在这个特别的季节来到久负盛名的吉林大学,来到美丽的长春市。我今天要和大家交流的是“性别视角下的宋代历史”。实际上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否换一种视角,或者说多一种视角来看看我们的历史。因为历史在我们的心目中都是有固定的影像的,说到宋代的历史,比如我们会说它是“一个士大夫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文人政治的时期”,是“一个科举繁荣的时代”;我们也会说它是“一个商品经济特别繁盛的时代”,是“一个文化造级的时代”,或者说“对外是一个积弱的时代”等。不管是什么,我们内心都有某种固定的影像。但如果说我们多一种视角,把那种非正统的、非主流的、边缘群体的视角加进来,换一换,特别是把我们过去忽略的、女性的视角放进来看一看,也许我们看到的宋代历史和我们心目中已有的成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这里提出能不能多一种视角,用新的视角来看待宋代历史,这就是所谓的“性别的视角”。 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问题,大体上从三方面来展开。首先要大体上了解一下什么是性别视角,它的由来、内涵,它在研究上的意义;第二是择要地展示一下从性别视角来看待宋代历史,大概可以看到些什么样的景象;最后简要地思考一下从性别视角来研究历史可能会面临哪些问题、哪些挑战。 首先简要说一下性别视角的由来和它的意义。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话题。所谓的性别理论内容非常庞杂,这方面的著述也非常丰富,我们这里简要地梳理一下。我们这里说的性别全称是“社会性别”,这个社会性别在西方(英语里)有一个原词“gender”,这个大家可能多少都听说过,那么提出“gender”这一词汇实际上是要和“sex”这一词汇做严格的切割,它和“sex”的含义确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过去熟悉的性别“sex”,指的是生理的性别,是解剖学意义上男女的差异;而“gender”强调的性别,它是社会文化的生成物,强调这种跟“sex”完全不同的由社会塑造出来的性别,认为这个性别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在后天的文化中形成的,是由文化塑造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这样来对二者做出严格区分。 那么这样一种社会性别的理论是怎样产生的、什么时间产生的呢?大体来说,是在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西方学术界开始产生的。在当时,实际上是对传统的生物性别决定论进行挑战形成的结果。这个“生物性别决定论”大家非常熟悉,就是说男女的性别差异,男女的性别特征,是与生俱来的,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同男性相比,女性在生理上,天生就有缺陷,天生就处于劣势;这样一种女性生理的低下,就导致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所以说,男女不平等在生物性别决定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是不可以改变的。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针对这种生物性别决定论,女性主义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解构,这个解构利用了很多当时的科学研究的成果。比如说,利用当时心理学家对两性人心理研究的成果。简单地说,就是当时的心理学家通过心理实验的一整套研究发现,我们说的那种所谓两性人,即生物学意义上的两性人,“TA”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和“TA”本人自己认同的性别并不完全一致。其实今天拿变性人来看更是例证。变性人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是某一性,比如生物学上就是男性,可是在心理认同上他就认为他是女性,所以他就固执地要改变自己的性别,如果不改变这个性别他就没法生存。这就更好理解了。在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时候,对两性人的心理研究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学者安·奥克利就利用了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提出来说人们认同的这种性别,它表现出来的这种性别特征、性别差异、性别行为其实并不是先天决定的,不是生物学意义上决定的。这样就做了一个区别。这是利用了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还比如说,利用了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当时也是女性主义学者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来解构这个生物性别决定论。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有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她有一部著名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可能有的同学接触过、读到过,叫《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实际上这个很早就有中译本。她的研究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成果了。她长期在新几内亚的几个部落里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主要调查了三个部落,即阿拉佩什、蒙杜古马、德昌布利。这三个部落在地理上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她的调查结果发现,这三个部落的性别特征却是很不一样的。阿拉佩什这个部落表现为我们主流文化认为的阴性社会,也就是说在这个部落中间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都比较倾向在家庭里面照看孩子,比较谦让,比较愿意从事家务劳动,男人和女人都表现出主流社会说的阴性社会特征。蒙杜古马部落却是完全相反,走到另一个极端,表现为主流社会说的那种所谓的雄性社会的特征,无论男人和女人,都是强调进取、外向好斗,这个文化里面最推崇的就是勇猛刚强,谁的地位高,不在于“TA”的性别是什么,而在于谁最勇猛、最好斗。德昌布利这个部落,它和主流社会的男、女差异确实很明显,这个很一样,但是它不一样的是,它这个部落的男性像主流文化中的女性,而女性却像主流文化中的男性。所以经过长期的人类学调查,米德就发现这虽是三个比邻的部落,民族也是一样的,可是他们却在性别特征、群体特征上完全不一样。在这样一个人类学调查的基础上,米德得出了一些基本认识,她就觉得所谓的先天的性别气质都不过是人类气质的不同变异。我们说性别之间有一些标准化的人格差异,其实她觉得这些都是文化监制出来的,性别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生成物。这也就是说,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在米德这里,把它理论化了,把这个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即把“sex”和“gender”区分开来,提供了一个人类学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丰富的,在此我们只做简要说明。我们当然也知道在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有一位学者为社会性别理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就是波伏娃。她的《第二性》,号称是“女性主义的圣经”,在她的《第二性》这本书里,她提出了一句名言,也是女性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 所以总体上来看,这个社会性别理论就是在肯定男女两性的生物学差异的基础上,它特别强调两性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在多种因素的建构下,体现出来的社会特征和性别差异;它强调人的社会性别角色不是与生俱来的,男女性别角色甚至是可以在变化的文化中间加以变化的。这是我们简要地说明社会性别理论的由来和主要内涵。 当然我们也知道,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性别理论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范畴。我们看到的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学界的一些著名的论著,包括西方的一些重要学府里面的博硕士论文,都可以看到他们在运用这个分析范畴,然后才进行开篇分析,几乎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这样一个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为社会科学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研究维度,也就是说在过去已有的那种社会的、阶级的、文化的、心理的,我们熟悉的政治的、经济的等这样一些范畴之外,又确立了一个新的范畴,就是社会性别这样的一个视角。实际上,它真的是有利于人类对自身进行重新的身、心的这样的一种审视,这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话说回来,社会性别理论的局限性也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有一些东西是值得警惕的。它的局限性在哪里呢?典型的一个表现是在社会性别理论这里,把女性看作是一个普遍的整体,它特别强调所谓的“姐妹情谊”,在它看来,所有的社会文化中间,只要是女性,就普遍受压迫,就普遍地比男性权利少,普遍地受制于父权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社会性别理论企图构建一个具有同一性、同质性、普遍性的,跨文化的、宏大的理论话语。这样很容易陷入我们所说的本质主义,或普遍主义的理论泥沼。显而易见,大家都知道,妇女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等很多不同背景下的女性当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差别其实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情况就像对传统的社会性别理论提出挑战的一位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学者贝尔·胡克斯说的,“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相比较的话,她们两者几乎是完全不同的性别歧视的体验。”她说,妇女中间本身就存在着压迫,存在着剥削,所以她认为白人的女性主义者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观察社会的方式呢?是“性别—种族—阶级”,她觉得这种方式是不成立的,她主张用“种族——性别——阶级”的方式来观察社会。也就是说,她认为,首先是种族的差别,造成一些妇女受压迫的处境,她说黑人妇女和黑人男人的共同之处远远要大于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的共同之处,因为首先黑人都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胡克斯提出的这些质疑和挑战确实是对女性主义传统的社会性别理论有了一个很大的质疑。的确,这样的局限性还是很明显的,它过于执着于单一的性别视角,忽略了和性别相关的其他一些分析范畴,很容易造成理论上的盲区,造成一种狭隘性。所以我们说那些非常尖锐的理论往往可能是深刻的,但很可能会是狭隘的。 所以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女性主义学者在西方又开始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把后现代的一些强调多元化、差异性的理论引入到社会性别理论中间,然后进行了对旧有理论的改造,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新的差异性的社会性别理论。这方面的论说也非常丰富,我们可以介绍一种在当前来看最有阐释力的论说,即美国的女性主义学者苏珊·弗里德曼的“社会身份疆界说”。那么“社会身份疆界说”强调什么呢?就是认为这个社会身份是什么?它是一个主体在多维社会和文化归属中的集合体。也就是说,社会性别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一个主体往往应当是多重的存在,它拥有多元化的个性。甚至她认为这个主体的身份是动态的,它经常在流动,甚至有时相互矛盾,它就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整合体。弗里德曼的“社会身份疆界说”内容非常丰富,至少包括了六种身份,她把这多种的话语体现用她的学说整个涵盖起来。总之,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以后,就开始出现这种差异性的社会性别理论,进一步地探讨性别在人类文化中的作用。它的好处是打破了过去传统的社会性别理论给男性和女性划定一个非常清晰的、稳定的,甚至是对立的界限的局面,开始考虑以性别为基础,其他的因素综合考虑,这当然就有了一个新的超越。所以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社会性别的视角,应当是一种多元化、差异性的视角。 我们要强调说这种视角首先是女性的视角,因为长期以来,无论从哪一学科来看,女性都处在边缘。特别是在历史学里,特别是我们说的文本的历史,精英编纂的历史,在这些历史中间,女性是处于边缘地位的。我们基本上很难听到女性的声音,很难看到女性的身影,所以我们这个视角特别强调首先要从女性出发,把过去被遮蔽的这些东西揭示出来,所以它首先是女性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来看历史,在开始的时候也被称作是发现妇女的历史,它要从中来挖掘女性的身影。这个视角首先是女性的,但又不仅仅是女性的,它应当是包括男女两性的。它强调的是社会性别意识,而不仅仅是女性意识,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异的。二者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都强调男女两性性别平等,都致力于去追求这种平等,但它们也是有区别的。我们知道女性意识就是从女性出发,它容易狭隘,容易偏执,容易造成两性之间过大的张力;而社会性别意识要从两性出发,这个就是不同之处,它真正能够导致人类性别的和谐,人类的和谐。我们之所以说不能仅仅从女性出发,而要从两性出发,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明白,因为单纯的女性意识很容易把男女两性对立起来,但事实上无论说女性从男性那里受到多少压迫,始终都不能改变两性共存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两性相依并存的,没有哪一性能够脱离另一性而存在,而且事实上来说,造成女性受压迫的局面,并不仅仅是男性单方面造成的,这个文化实际上是男女两性共同参与、共同塑造的。何况这种几千年来男女的不平等不仅是伤害了女性,同时也给男性带来了伤害,因为男性同样受到了限制,同样要受到文化的压迫。有很多的统计已经表明了这一点,男性作为社会压力的主要承受者,是非常辛苦的。不光是古代,就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两性关系的不平等还是相当程度地存在着。所以说男人不能解放其实还是因为女人不能解放,女性的问题说到底不光是女性的问题,其实是两性的问题,男人只有解放女人,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所以说性别意识,我们强调的是社会性别意识,不单纯是女性意识,有了这样的出发点,我们就很容易看待今天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摆脱当今学术界在谈女性问题的时候常常出现的局面,多半是女性学者在谈,造成了所谓的“公婆论战”,女性主义在女人那里大声疾呼,男性学者要谈女性问题甚至被讥笑为“变态”。要突破这一点,就要强调这是一个两性的问题,用这样的性别意识来看待问题。现在在西方学术界我们看到的妇女史已不单纯是妇女史了,而被称为“妇女-性别史”,或者叫“妇女/社会性别史”。我们把过去那样的妇女史称作是“发现妇女的历史”,现在更多地是称之为“发现性别结构关系的历史”,这是有所进步的。 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性别视角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强调性别的作用,强调两性结构,两性关系中体现的权力,权力的关系。用这样的视角来看待以往的历史文化,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无论任何一个制度、组织、文化构成,都具有不可回避的性别倾向,尽管这种倾向被消解在众多主导性的官方议题中间,常常不被承认。性别视角在历史研究中实际上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想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除了我们已有的一些分析维度以外,还必须分析性别在其中发挥的潜在的作用。这种性别视角也应当是一种多元化、情境化、开放性的视角,是把性别视角和其他的研究范畴联系在一起来看的。事实上也没有完全脱离其他范畴的所谓统一性的、单纯性的、普遍性的性别,所谓“女性问题”,永远和阶级的、地域的、文化的、民族的等问题的维度交织在一起来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说的性别视角的意义大体有哪些。 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视角的,依照这样一个视角,我们有可能揭示出和以往我们心目中的历史不一样的一些面相,有可能实现重写历史的目标。以上就是我们梳理的第一个问题。 下面我们就举例来看。用这样的性别视角来看待宋代历史,看看跟我们心目中以往的成像是不是有所不同。我们看看宋代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这些都是非常宏大的话题,我们分别举例来看。 首先是宋代的政治史。政治史上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女主的问题。这也是宋史研究中的一个老话题,现在仍然争议不休。可以说千年以来在主流精英那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没有大的突破。为什么没有突破呢?我觉得就是没有性别这一维度,如果我们引入性别这一维度,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因为我们知道宋代是一个非常强调男女大防的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强调男女的区隔,比任何时代都对女主政治有高度的警惕。但是恰恰就在这个时代,女主政治也在不断地出现,两宋十八朝,女主政治先后在九朝都出现过,时间长短不同,但确实出现过。传说中“狸猫换太子”的刘太后,执政近12年,是事实上的皇帝,威权几近于武则天。“女主”现象虽经常防范,但依然出现,这是为什么呢?用性别视角来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和性别制度中的婚姻家族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女主的身份、归宿究竟是什么?她的身份归宿在她嫁入皇室那天就已经明确了,即:她从出生时的父权家庭转移到了出嫁以后的皇权-父权家庭,她的身份在本质上是没有变化的,当她登上政治舞台来代表她的皇权家庭执政时,她实质上是被社会性别制度造就的皇权-父权的代言人,她不是真正作为主体的女人在执政,所谓“女主的权力”实际上仍在皇族手中,并未发生向女性的真正转移,她仍然是代表着父权,代表着国家的最高层面,即皇权。女主政治说到底只是父权制(提升到国家层面就是皇权)自身维持继承断裂和权力危机的一种调节和平衡。换句话说,执政女主是以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代表着文化政治意义上的男性在行使权力。所以说,女主政治的出现并不奇怪,它实质上也与“性别平等”没什么关系,宋代的整个性别制度与格局并没有因为女主政治的出现而发生什么改变。以刘太后为例,尽管她主政期间比较强势,也有意无意流露出一些女性本能,比如,在一些狱讼中,刘太后会做出有利于妇女的裁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圣六年(1028)“开封府言:‘有民冯怀信,尝放火,其妻力劝止之。他日,又令盗摘邻家果,不从,而胁以刃,妻惧,告夫。准律,告夫死罪当流,而怀信乃同日全免’。上曰:‘此岂人情耶?’乃诏怀信杖脊刺配广南牢城,其妻特释之。”显然,这里是刘太后借仁宗之手,重责冯怀信而释放其妻。后来,天圣八年(1030),在开封又发生了贵戚殴妻致死的案件,刘太后知道后大怒曰:“夫妇齐体,奈何殴致死耶?”“夫妇齐体”一语,是刘太后发自内心的,她认为,夫与妻应是平等关系,在法律上不应当重夫而轻妻。但是,刘太后并不能对当时女性地位的改变起什么作用,在这个贵戚殴杀妻子的事件中,仅是权知开封府寇城说了一句“有司不敢乱天下法”,就使得刘太后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想法,这个贵戚最终得以免死。平心而论,刘太后是宋代有作为的女主,但当时一些士大夫,包括后世一些进步思想家,对她批评很多,比如王夫之在《宋论》中即对刘太后大加鞭挞,说:“刘太后以小有才而垂帘听政,乃至服衮冕以庙见,乱男女之别,而辱宗庙。”文人还编造出《狸猫换太子》这类故事,塑造刘太后的刻毒形象,诋毁刘太后。 传统史家对女主政治的批评,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还是合法性问题,把女主政治等同于“牝鸡司晨”,即违背自然法则,必然带来祸乱。其实,从性别视角来看,对这所谓的“合法性”不难发出这样的质疑:“法”为何法,“法”从何来,“法”是否善“法”,是否应当遵行?回答这些问题应该是不困难的。 在女主政治方面,传统的批评还集中在女主执政的层面,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外戚专权。一般认为,女主政治素质低下、文化素质低下、执政能力低下,她们短视,她们狭隘,她们只会重用娘家人,所以重用外戚,那么结果就必然带来所谓的政治的黑暗。千年以来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批评。同样,如果我们在这里加入性别的视角,也不难发现,女主倚重外戚,实际上正是性别制度、尤其是性别隔离制度的产物,外戚专权从根本上来说,是性别制度的一个必然的派生物。如果我们一味地只是满足于对女主个人的品格、能力的批评,显然不能够很好地解释问题。这是我们拿女主问题举例来看宋代政治史。 接着我们来看宋代的经济史,看看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时代女人确实是可以经商,可以买卖,可以参加一些社会生产劳动。一般会认为,商品经济发展会有利于女人地位的提高,在宋代看来似乎的确如此,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宋代的妇女(无论城市妇女,还是乡村妇女)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文献中记载,不少妇女经营商业,有点本钱的,往往自己开店营业,当女老板。如开旅店,《水浒传》孙二娘开店不是虚构,类似的事情不少。有开饮食店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有王小姑酒店、曹婆婆肉饼;《都城纪胜》里有李婆婆羹;《武林旧事》和《梦粱录》都记录了皇帝喜欢吃的名店小吃宋五嫂鱼羹。有开药铺的,如开封有丑婆婆药铺,杭州有陈妈面具风药铺。有开茶坊的,《梦粱录》中,王妈妈开了茶肆“窟鬼茶坊”,是士大夫聚会的场所。经商贩卖的妇女很多,有些人甚至成为富婆。如前面提到的宋五嫂,《东京梦华录》说她因鱼羹“尝经御尝”,以致“人所共趋”,“遂成富媪”。北宋后期,在当时的商业大潮中,本应“超凡脱俗”的尼姑们也加入了世俗社会的商业竞争:《东京梦华录》记载相国寺“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乃至于一条“绣巷”都是“师姑绣作居住”。在商业方面,妇女参与的范围的确相当广泛。女子有了收入,就会享有家庭的一些支配权,甚至可以说享有了家庭的某些主导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女子有主动提出离婚的,这些都是事实。 但问题是,我们如果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也就是加入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的话,我们会看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的经济参与,对女性地位的提高其实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影响的。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第一,妇女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并不会单纯地随着参加社会生产劳动而自然提高。因为我们知道决定一个人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高低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因素,还有其他的如文化的、社会的因素,都在共同起作用。在实际生活中,古代劳动妇女没有不参与经济活动的,但她们的从属地位并没有因此有什么改变。而在当代社会中,成功女人被称作“女强人”,这并不是什么褒义词,她们在工作中容易受到猜忌,在家内也往往要扮演“弱女子”的角色才能换得家庭和谐。其实,当今的所谓“剩女”问题,实质也在于此。第二,经济上的参与,可能并不意味着身心健康的发展,甚至可能意味着身心健康的受损。因为妇女不得不承担两副重担,即家庭的和社会的。这在当代社会更加明显,有提高、自主的一面,但也有负担过重的一面。在宋代亦是如此,妇女要担负社会生产和家务劳动两副担子。以《清明上河图》为例来看,日本学者佐竹靖彦写过一篇文章《〈清明上河图〉为何千男一女》(据统计,《清明上河图》所绘人物共约500多人,女子不超过10人,“千男一女”是形象的说法),这是一篇以画证史的论文,作者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对女性的描绘,发现其中有少数几位女性,一位是在大声指挥众多男性从事将船向虹桥靠近作业的女强人,这与《水浒传》中的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属于同一类型,是一种与男性有同样的力气而参与男性社会活动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她的身边,可见她的孩子。此外,图中还有少数几位妇女以消极的身份参与都市生活,她们也都在照看孩子。佐竹靖彦把《清明上河图》与同一时期日本的绘画相比较,指出《清明上河图》中没有把男女一视同仁地加以描绘,反映的是“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女性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外出的,为了育儿不得已才外出。其实说到底,只要家务劳动不被计量,只要生育不被看作是人类最伟大的生产,妇女要想得到“社会地位”,就不得不担负家务劳动和社会生产两副重担。第三,宋代的女性参与了很多的商品经济、社会生产,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被局限在传统的性别分工认为女人合适的行业,比如服务业,更重要的在于,主流价值对于男女共同从事的一些行业中的女性,仍然是存在歧视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行医,男子行医被称作“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所谓“不成良相便成良医”;而女子从医多半被看作是“三姑六婆”,被看作是走街串巷、搬弄是非,甚至是唆使奸淫、唆使盗窃的一些祸害,《南村辍耕录》说对她们要“谨而远之”,避之如蛇蝎。说明这个社会分工和性别制度还是联系在一起的,妇女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她参与经济而自动地提高。所以对于经济发展、妇女参与、妇女地位相互之间的关系,是要做多方面考量的,其影响是相当复杂的。 再来看看宋代的文化史,我们以科举制度为例。科举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文人政治的兴起与发展,被看作是宋代历史的一个积极特征,甚至被看作是唐宋变革的一个主要指标。这几乎就是公论,但如果从性别视角来看,可能对科举制度又有新的认识。第一,科举制度是干什么的?为统治阶级选择人才,是选官制度和与之相联的教育制度。显而易见,女性被排斥在科举之外,被剥夺了参与公共政治的权利,不仅如此,也被剥夺了受教育、个体发展的权利。尽管宋代有过女童子应举,像《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的女神童林幼玉,但那仅是极个别的点缀、消遣,其结果也不可能进入官场,林幼玉就只能是被特封最低一级的妇女封号“孺人”回家而已。传统社会普遍认为女子是不必受教育的,反对女子读书识字。到宋代,宋人似乎比前人进了一步,看司马光《居家杂仪》的内容,他还是主张女子读书受教育的,但是,他所主张的女子教育的内容与男子不一样,其实质上仍与前人相似,女子教育只是限于“女学”。所谓“女学”是些什么?用清朝学者李晚芳《女学言行纂》的概括,女学之道有四:“曰事父母之道,曰事舅姑之道,曰事夫子之道,曰教子女之道”,四者自少至老,“一生之事尽矣。”男子教育讲究全面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女性教育的内容就很不相同。甚至于女子学文、吟诗作赋是“可耻”的事情,南宋杰出的女词人朱淑真是个典型,她聪慧异常,却为社会所不容,她死后,父母将她的诗词作品一把火烧掉,因为女儿的才华为社会所不容,女儿的形象在当时人心目中不健康,属于“无德”。虽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正式提法出现于明末,但这种价值观念在宋人那里是很明确的。这是第一,从性别视角来看科举制度,女性被排斥在科举之外,被这个制度剥夺了参与取士的权利,与此同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个体发展的权利。第二,从性别视角来看科举制度,我们也认为它是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性别分工,强化了女子的依附性。女性的命运与丈夫、儿子的科举前途直接联系在一起,女性人生的荣辱以及她自身的自我体认,都和她男性亲属(如夫、子)的功名成败联系在一起,女性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助夫、子博取功名,女性自身被进一步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从根本上来说,科举制度是性别等级制度的体现,扩大了两性之间的张力。如果是这样的视野,就和传统的视野有所区分了,这是我们拿科举制度为例来看。 其他更多的话题都可以这样来看。宏观来说,比如“唐宋变革”,我们常说的有很多很多的指标,但我们有没有人仔细地追问一下这些指标有哪一些是和女性相关的。所谓“士大夫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女性的生活状态、她们的感受又如何?又有多少人关心?在这样一个被日本学者称为“东方文艺复兴”的时代,女性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呢?这种情况有点像西方学者对文艺复兴提出的质疑,“女性有文艺复兴吗?”欧洲史上的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进步,可是从女性视角来看又怎么样呢?美国学者琼·凯利指出,尽管文艺复兴给男性为主体的西方社会带来了进步,而对女性的影响恰恰相反——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妇女被剥夺政治权利、性压抑的开始。宋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其实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宋代作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号称“东方文艺复兴的时代”,也恰恰是女性缠足的开始,是女性极端“贞节”观的强化时期。用性别视角来看待历史,我们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得出一些和我们以往心目中的成像不同的图像。 最后我们简要看一下性别视角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性别视角经过了在西方三四十年的发展,国内学术界也有一二十年的引进,应当不陌生,但仍然处于边缘,在国内甚至可以说是在起步阶段,很多问题仍需要探讨。首先,比如说学术术语的问题,“gender”到底怎么翻译?学术界也很犯难,它是西方学者用来区别“sex”的一个学术话语,可是在中国,在汉语里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对应词,我们就把它翻译成“社会性别”,可是“性别”一词是有它特定的内涵,没有找到更适合的翻译,只好权且如此。像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还有就是,用西方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的问题吗?显然不能。中国的很多问题它没法很好地回答,中国本土的性别关系比起西方来说更加复杂、曲折,可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还太少,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甚至是严峻的挑战。另外,我们也应当有高度的警惕,要注意性别关系的多元化、差异性,还有就是要注意古代中国女性尽管在“男尊女卑”的框架下生存,但她仍然有很大的主动性,或者说是协调性,甚至往往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利用一些自己的生理特质,突破女性被压迫的基本框架,而凌驾在男性之上。最典型的如乳母。台湾学者李贞德研究汉魏六朝的乳母如何藉由女性的生理特质——健康的乳汁,以及比之于母亲的照顾之情,突破阶级与性别的双重限制,自婢仆而列登官家,身受封赏并泽及子孙。这类情况历朝都有,宋代也不例外。例如仁宗的乳母林氏“预掌机密”;仁宗张贵妃的乳母贾氏,“宫中谓之贾婆婆,威动六宫,时相(宰相贾昌朝)认之以为其姑。”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都需要我们来认真地思考。当然,研究历史最大的挑战还是史料,因为遗留下来的历史文本主要还是精英编纂的文本,特别是那些官方的文本,男性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使得有关女性的史料受到了更多的过滤和加工,我们要怎样从中进行辨析、取舍,这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加上,我们习用的分析框架,包括现在历史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也是一个传统的框架,这种框架实际上还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未见得适合解决两性共同的问题,更不用说女性的问题了。但现实就是个悖论,我们既不能够脱离历史、脱离传统,我们也就只能用现成的话语来言说,这就使得我们想要真正突破传统的框架,想要重写历史,真的是非常艰难。 有人说我们过去的历史是“他”的历史,即“history”;现在的西方学者很多都说何不来个“herstory”,“她”的历史?但不管是“history”,还是“herstory”,都是一性的角度,我们应当追求的是那种真正能够从两性出发,能够共享两性的经验,追求两性真正和谐的历史,我把它称作“bothstory”或“wholestory”(这是我自己生造的词,表意而已)。要实现这一目标,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寄托于在座的各位,谢谢! (录音整理:关聪)标签:社会性别论文; 清明上河图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东京梦华录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宋代绘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