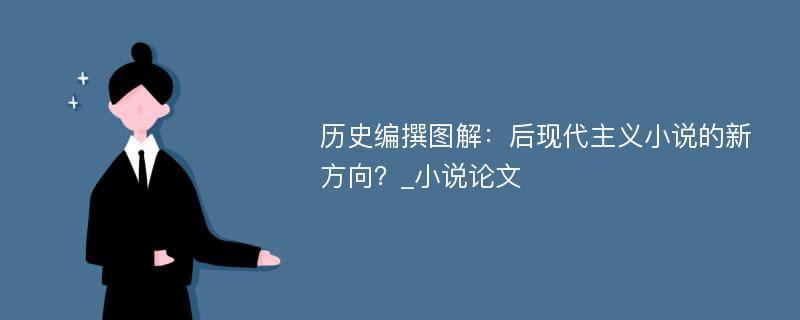
历史编纂元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新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小说论文,方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6)03—0055—06
一
在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及文学创作的讨论中,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林达·哈琴提出了“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概念。在哈琴的定义中,“历史编纂元小说”是指那些“众所周知的流行的小说,它们具有鲜明的自我反映的特征,同时又悖论式地宣称拥有历史事件和真实的人物。”[1](P5) 被哈琴归入此类的作品包括: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们》《耻辱》、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鱼鹰湖》、《但以理之书》、库弗的《火刑示众》、艾柯的《玫瑰之名》、克里丝达·伍尔夫的《卡桑德拉》、里德的《可怕的两岁娃娃》、普维格的《蜘蛛女之吻》以及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国佬》等等。可以看到,这些小说都是“历史编纂学”和“元小说”的有机结合。它们既具有自我反映、自我指涉等元小说的特征,同时又穿插借用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使作品虚实相间、亦真亦幻,甚至使人很难将其准确归类,不知该将它们归入传记、历史小说还是虚构作品。这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欧美文坛涌现的作品受到批评家和普通读者的一致好评和欢迎。在批评家的眼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理论上对历史与小说均属人为建构物具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从而为它对过去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加工奠定了基础。”[1](P5) 这批作家对历史与小说虚构的关系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在创作中不仅体现了自己的思考结果,而且运用了新颖独特的写作技巧。其作品熔深邃的思想、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精彩好看的故事于一炉,因而深得批评家青睐。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中通俗的故事、起伏跌宕的情节、生动幽默的描写又吸引了大批普通读者。正如拉里·麦凯弗雷所说:“这种小说就这样成了当代作家创作的一种模式,它对于自身的文学传承和摹仿的局限性了然于心,……但仍然试图重新使它的读者和书页以外的世界联结起来。”[1](P5) 正是历史编纂元小说这种通过在传统与历史语境中的写作来质疑传统与历史的叙事的悖论式特征,使哈琴将其视为唯一一种圆满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诗学”的小说。
“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在欧美批评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批评家们在接受这个概念的同时,也对哈琴的某些论断(如历史编纂元小说是唯一一种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诗学”的小说;历史编纂元小说是具有范例作用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等)提出了质疑。
但总的来说,批评界对这一颇具创见的概念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如英国著名文论家马克·柯里主编的《元小说》一书,就有一章题为“历史编纂元小说”。其中收入了林达·哈琴、苏珊娜·奥列伽和海登·怀特的三篇文章。奥列伽的文章标题是“不列颠的历史编纂元小说”,概括介绍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的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创作情况。柯里并且在此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从元小说到历史编纂元小说,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或从文学研究演化为文化研究,这些变化代表了20世纪思想演变趋势的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而这种演变趋势曾经看上去是毫无前途地指向自我分析和自我沉醉的。”[2](P14—15) 在思考历史编纂元小说是否真的会成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方向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它的发展脉络进行一番梳理。
二
历史编纂元小说作为元小说的一种,可以说是元小说的新发展。“元小说”是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由威廉·加斯用来指称当时出现的一些“关于小说的小说”的。帕特里夏·沃这样定义:“所谓元小说就是指这样一种小说,它为了对虚构和现实的关系提出疑问,便一贯地把自我意识的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人造品的自身的位置上。这种小说对小说作品本身加以评判,它不仅审视记叙体小说的基本结构,甚至探索存在于小说外部的虚构世界的条件。”[3](P2) 元小说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自我意识、自我反省和自我指涉。它通过各种方式在作品中有意暴露写作技巧和创作过程,暴露其自身的虚构性。在有的元小说中,作者、叙述者和小说主人公同为一人,他常常自由出入作品,对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等品头论足、发表评论,从而使小说叙述的真实性、作品的统一性等都受到质疑和挑战。一般认为,元小说是一种跨越了小说和批评之间界限的小说。因为它将批评视角融入小说,使文学批评与小说创作不再泾渭分明。由于清醒地意识到并有意凸显自身的虚构性,再加上作者在作品中频繁现身,使元小说中有大量对自身创作情况的说明和评论;戏仿和互文性手法的运用则反映出了它对前文本的选择和评判;作者对作品的开放式处理使小说的阐释和最终完成需要读者的参与。因此,无论是元小说的写作还是阅读,都需要一种批评的视角。这些都使元小说同时具备了批评文本的特征,并且使作者和读者、小说和批评、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变得界限模糊。如果说元小说就是将作者与读者、小说与批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内在化于文本的创作,那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文学史上找到它的先行者。如莎士比亚的戏中戏,菲尔丁和理查森作品中的侵入式叙述者,《项狄传》、《堂吉诃德》和《诺桑觉寺》中的戏仿等。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当代元小说的先声。
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自我反省特征可以说是对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传统的叙事形式、统一性原则和透明的表述语言的反叛。在元小说中,可以看到的是陌生化的创作技巧、戏仿/互文性的运用、多重叙事视角以及一种不再透明的语言。传统作品中透明隐身的动词结构变成了清晰可见的创作技巧,从而挑战了传统的小说观念。文学叙事的真实性受到了嘲弄,从而凸显了叙事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如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这部小说对经典童话故事进行滑稽模仿,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生活在当代美国,七个小矮人的职业是清洗建筑物和熬制婴儿食品,白雪公主则替他们管家。在小说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有一份读者意见问卷调查表,其中一个问题是:“在叙述过程中,胡诌八扯太多吗?胡诌八扯还不够?”作者用种种类似的荒诞可笑的手法对小说的虚构性进行自我暴露和调侃。
当代元小说发展到一个极端,就成为一种被哈琴称之为“晚期现代主义激进元小说”的语言实验。如美国的“超小说”和法国的“新新小说”。这种激进的元小说完全将小说自我封闭起来,脱离现实,也远离历史,自说自话地沉迷于文字游戏。这也正是马克·柯里所说的那一类“自我分析”、“自我沉醉”的“毫无前途”的元小说。如库弗的《保姆》。这部小说一共分为108节,每节之间用星号隔开。 每一节都好像是一个孤立的片断,和前后两节完全连接不上。读者在断裂和跳跃的片断中前行,仿佛是在猜谜一样。只有开动脑筋,将可能有关的情节片段和人物连接在一起,才能模模糊糊地拼凑出故事的大概轮廓。但这也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每个片段的内容都充满歧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人称代词“他”、“她”也可被认为是指称不同的人物。因此,每个读者都可能会对小说的情节发展和最后结局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对批评家来说,这样的小说固然有其研究价值。但对读者来说,读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是在参加智力测验。除非是对文字游戏感兴趣的读者,大多数人恐怕是会对它敬而远之的。哈琴认为,这一类极端的元小说使文学被边缘化的程度更加严重。因为这样的文学作品是注定没有读者,也没有前途的,它只能使文学脱离现实生活和历史语境,走向孤立,走向边缘。
历史编纂元小说和热衷于语言实验的激进元小说的区别,正在于它和历史语境的重新联结。这种联结不仅是形式的,而且是主题的。如汤亭亭的《女勇士》和《中国佬》。作者通过追忆自己家族的女性和男性先辈移民美国的经历,对华裔美国人的历史提出质疑,并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加工。作品的主题始终围绕着历史在被记录的过程中被选材、被剪辑,最终不可避免地变形、扭曲乃至湮没。在形式上,汤亭亭大量运用真实历史材料,将家族往事、童年记忆、移民史实全都收入作品。甚至在《中国佬》中专辟一章“法律”,罗列出美国历史上排华法案的条文。作品从主题到形式都体现出“重访”历史语境的特征。
三
历史编纂元小说是历史编纂学和元小说的有机结合。历史和小说的关系是这类小说探索的主要问题,也是我们解读这类小说的关键所在。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历史和文学分属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历史学家只能谈论已经发生的事和过去的细节。而诗人则谈论可能或将要发生的事,因此与大千世界的联系更加繁杂。诗人的创作可以不受历史书写的线性演进的限制,因此其情节可以发展成不同的统一体。然而,历史和文学的分离并未妨碍众多的历史学家运用文学虚构的再现技巧来创造他们心目中的历史上的世界的想象性版本。在历史上,历史的书写和历史小说的写作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如麦考利对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借鉴,狄更斯《双城记》对卡利尔的历史著述的参考等。关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20世纪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家和传统历史学家认为,二者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他们认为,文学或艺术是虚构的,因而是不真实的;文学或艺术创造了它们自己的世界,和外在的现实是无关的。历史则全然不同,它是对外在世界的最全面的、最深邃的真理的探索,拥有获取过去事件的终极真相的最大权利。文学是虚构,历史是真实,它们是截然相对的。然而,在当代的文学理论和历史哲学中,文学和历史的截然分离受到了挑战。当然,这种变化是和20世纪形式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对立抗争紧密相关的。自从20世纪20年代新批评在和文学历史主义的论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以来,形式主义理论一直占据着理论舞台的中心位置,直到1980年代晚期,解构主义被看作形式主义的一种让位于重新联结历史的理论流派。今天的批评理论更多地关注历史和文学的共同之处而非它们的差异。从海登·怀特到保罗·维因,理论家们认为,历史和文学这两个术语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它们的定义和相互关系是历史地决定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当保罗·维因将历史叫作“一种真实的小说”时,他是在示意历史和文学这两种叙事类型共享着下述规则:选材、组织、轶事、时态的调整、情节化等。它们还共享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语境以及形式技巧。除了那些极端的超小说,文学作品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形象化地表现社会和政治的历史,虽然表现的程度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历史编纂学和所有叙事性小说一样,是精心结构的、带着价值评判的、人工制成的文本。当代理论家们将历史和小说看作两种叙事类型,它们都是文本的建构。它们都依赖于以前的互文,同时不可避免地负载着意识形态的内涵,因此都是“非原创”的叙事。虽然在圣经和古典史诗以来的文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界限的模糊,但在哈琴看来,正是历史编纂元小说在宣称历史和文学界限的同时又公开地跨越了这道界限,凸显了它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当代批评家、《玫瑰之名》的作者埃姆伯托·艾柯曾提出,有三种叙述过去的方式:第一种是罗曼司——传奇故事。艾柯认为,传奇故事除了爱情故事以外,还包括哥特式小说和大量的科幻小说。第二种是侠义小说,或称“斗篷与短剑”故事,如大仲马的作品。第三种是历史小说。艾柯说自己就是想创作历史小说。[4](P176) 但在哈琴看来,艾柯的作品如《玫瑰之名》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第四种叙述过去的方式:历史编纂元小说。因为它在建立和承认了历史和小说的差异之后,又模糊和质疑这种区分,并利用自我意识等元小说技巧对它做的这一切进行揭示和暴露。这是和传统的历史小说根本不同的。那么,历史编纂元小说和传统历史小说究竟有哪些区别呢?首先,根据卢卡契的论述,传统历史小说的主人公是类型化的,他是共性和个性的合成物,他的身上带着所有的人和社会的最本质的决定因素。这样的人物才能承担起再现历史风云的任务。而历史编纂元小说的主人公决不属于任何类型,他们是虚构的历史中的去中心化的、边缘化的角色。即使是这些作品中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如《火刑示众》中的尼克松、《拉格泰姆时代》中的亨利·福特、J·P·摩根、弗洛伊德,都处于一种与真实情况完全不同的、特殊化的、彻底地去中心化的状态中。《火刑示众》涉及了1953年罗森堡夫妇遭美国政府迫害,被以出卖美国国家机密的罪名处以死刑的真实事件。在作品中,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被描写成一个极度荒谬的人物。他在行刑前偷访罗森堡夫人,想得到一些情报,又试图和罗夫人做爱。正在这时,狱吏闯进来通知行刑时间已到。尼克松未及束好裤带就匆匆赶到执行死刑的时代广场发表演讲。他说:“我要清楚地表明立场!我们没有任何秘密!……我请求你们支持我们发展出国家精神,一种为完成我们的世界责任所需要的信心!……今晚我请求你们每一个人站出来——立即!——为美国脱下你们的长裤!”这样的描写和传统历史小说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毕竟,历史编纂元小说认同的是后现代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差异,“类型”在后现代主义小说这里已失去了意义,除非是被当作反讽、颠覆的目标。
其次,卢卡契认为,在传统历史小说中,细节的真实和准确相对来说是不太重要的,因为细节只是获取历史的可信性的一种手段而已。在历史编纂元小说中,有两种处理历史细节的方式。一种是对历史记录的真实和谬误的游戏式处理。如在麦克尔·科依策的《福》等小说中,作者有意弄错一些人所共知的史实,以此表明历史记录可能发生种种记忆上的失误,并且始终存在出现有意的或无心的差错的潜在可能。另外,历史编纂元小说在实际运用历史细节和资料的方式上也和历史小说不同。历史小说往往具体地体现并完全吸收这些历史资料,以此给虚构的小说一种真实感。而历史编纂元小说很少完全吸收历史资料。相反,试图吸收历史资料的过程常常成为它有意凸显的对象。读者往往能清楚地看到收集资料的过程以及将这些资料组织到叙事中去的努力。也就是说,这种小说承认,确实存在某种过去的现实,而要使今人能够接近这些过去的事实,必须将其以某种方式文本化。而文本化的过程就是一种“遮蔽”事实的过程。历史编纂元小说正是要在作品中凸显这种悖论。
第三,传统历史小说把真实的历史人物降级为二等角色,在小说中安插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只是为了证实小说的真实性,即历史人物在小说中只是起辅助作用的角色。而大部分历史编纂元小说不是这样的。在很多作品中,历史人物就是主人公,或是重点描写的对象。如威廉姆·肯尼迪的《莱格斯》,这部作品记叙了美国历史上的著名匪徒杰克·莱格斯·戴蒙得的生平故事。另如约翰·班维尔的《科帕里克斯医生》和《开普勒》,都是以历史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此外,在历史小说中,安排一些历史人物是为了加强小说的可信度,历史人物仿佛是被用来掩盖历史和虚构之间的连接处的。而历史编纂元小说正好相反,它有意将历史和虚构的连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我们是怎么了解过去的?我们现在对过去了解或可能了解些什么?历史编纂元小说往往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虚构加工促使读者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如“我们应当如何接受已经被接受的历史版本”、“是否有必要质疑已经记录在案的历史”等等[1](P113—115)。
总之,历史编纂元小说以其独有的方式质疑历史和虚构的区分。它试图重新定义历史和文学的关系。不同于保罗·德·曼和解构主义者取消事实和虚构的界限,将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合二为一的观点,哈琴认为,历史编纂元小说在指出历史和小说的对立依然存在的同时,强调话语原则对二者的适用。也就是说,历史和小说虽然有各自的领域和叙事规则,但它们都要遵循共同的话语原则,因为它们都是一种叙事文本。读者在阅读历史编纂元小说时具有两种意识:既意识到小说的虚构性,同时又意识到小说中的历史材料是基于真实事件的。这种阅读体验使他们进入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无法解决的矛盾状态之中。也许这就是历史编纂元小说力图做到的,使历史和虚构始终处于一种既对立又同一、既相互矛盾又互为补充的不确定的关系中,并通过元小说技巧促使人们看到并面对这一悖论。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对过去的绝对可知性的质疑,以及它对历史再现的意识形态内涵阐明。在海登·怀特和多米尼克·拉卡普兰等当代历史编纂怀疑论者对历史和虚构的关系进行论说以后,人们对历史的真实可靠性已经不再确信无疑了。尤其在美国,越战后对当代历史的官方版本的不信任感更促使理论家和作者去思考历史与虚构的关系问题。过去的绝对可知遭到了质疑,历史则不可避免地背负着意识形态的重担,对过去的再现必定浸染着今日的意识形态色彩。历史编纂元小说可以说正是这种思考的产物。
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叙事方式也是和它对历史与虚构的相互作用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历史编纂元小说往往喜欢采用两种叙述方式:(1)多重叙事视角;(2)一个公开的控制一切的叙述者。可以看到,在这两种叙述方式中,我们都无法找到一个确信他/她有能力了解过去的主体。这并非对历史的超越,而是将描写历史的主体性变成了一个问题。多重叙事视角使作品中没有一个稳定的、连续性的主体存在。而一个公开的控制一切的叙述者往往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他可能是一个自我忏悔的说谎者(如威廉姆的《星弯》的叙述者),也可能是一个对叙述的事件的真实性没有承诺的人(如博格斯的《尘世的权力》中的叙述者)。这样的叙述方式带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因为后现代主义正是把试图通过回忆去把握过去的稳定的叙述声音和叙述人离散化。它设置然后颠覆传统的主体观念。而历史编纂元小说通过这样的叙述方式达到了这一目的。[1](P117—118)
戏仿/互文性是历史编纂元小说最重要的叙事技巧之一。在这里,戏仿/互文性是将文本化的过去编织进今天的文本的一种后现代方式。如在汤亭亭的《孙行者》中,戏仿的互文有文学的,也有历史的。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前文本是五花八门的。有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惠特曼的《自我之歌》,也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有1960年代反战的嬉皮士,常青藤学校的嚎叫派诗人,伯克利的激进传统,还有好莱坞电影、功夫片、唐人街的梨园。作者通过对文学和历史的前文本的戏仿,对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和身份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加工。
四
正如马克·柯里所说,历史编纂元小说植根于现代主义,而它之所以能够在后现代主义的土壤中开花结果,是因为哲学、语言、文学及文化批评这些相关领域为它创造了有利的新的理论视野。它使文学作品重新联结了历史,但又并非回到对历史真实性的传统的确信中,而是对其提出质疑。因此,历史编纂元小说是对关于再现的天真的现实主义观念的挑战,也是对同样天真的文本主义者或形式主义者对于艺术与世界的截然分离的确认的挑战。
林达·哈琴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矛盾的文化事业,被它力图反驳的东西纠缠其中。它运用并滥用那些正是它自己试图批驳的结构和价值观。例如历史编纂元小说,它鲜明地保持着形式上的自我再现及其历史语境的特征,并由此把历史知识的可能性变成一个问题。这里没有调和,也没有辩证——只有未解决的矛盾。”[1](P106) 在哈琴看来,这种“未解决的矛盾”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也是历史编纂元小说的特征。
在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论争中,理论家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后现代主义,有积极拥护的,也有大加挞伐的。应该承认的是,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充满歧义。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因此,反对者和支持者对它的理解也许是迥然不同的。但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在林达·哈琴看来,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都应该建立在理论探讨和具体艺术实践分析的基础上,而不应当空谈理论,玩弄概念。因为这只能导致在这一问题上的无休止的混乱和迷惑。哈琴以伊格尔顿在《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文中对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为例,对某些广为流传的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和看法进行了批驳。如伊格尔顿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提出,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特征包括“没有深度”、“缺乏历史记忆”、“没有风格”、“没有政治内容”等。哈琴认为,这些标签在具体的文学作品面前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有深度、有思想、对历史记忆进行重新思考和加工、极具个人艺术风格并直面政治事件的创作。例如在冯内格特的《五号屠场》中,作者将二战、德累斯顿大轰炸等历史事件和科学幻想结合起来,对战争、死亡及人类的命运等严肃的问题进行思考。多克特罗的《但以理书》、库弗的《拉格泰姆时代》等作品通过将真实的历史、政治、文化事件和人物引入作品,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特点还包括“赞美媚俗”。也许在伊格尔顿看来,所有运用了非高雅艺术形式(如间谍小说、侦探小说、西部小说等)的作品都是迎合低级趣味的媚俗之作。但他显然没有看到,在通俗小说的外衣下,这些后现代主义作品运用戏仿、反讽、幽默等手法对所谓“严肃”艺术的矫揉造作的反拨和颠覆。对伊格尔顿等人以一种绝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后现代主义当作现代主义的反面和对立物的做法,哈琴认为这是否认了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复杂性。她认为,不能以一种“规整”的理论来简单化地概括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一种后现代主义诗学,必须立足于对所有后现代主义话语形式的分析和把握,而不能仅靠部分例子就进行简单化的理论断言。例如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后现代主义艺术并不像有的理论家断言的那样是反历史的或幼稚地怀旧的。这一点从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创作中就能得到证实。后现代主义是面对并且挑战现代主义以未来的名义对过去的抛弃或挽回。它并不否认过去的存在,而是质疑我们是否可能知道那个过去,如果不依赖于它的文本存留物的话。[1](P18—20)
对历史编纂元小说来说,除了与历史的特殊联系以外,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有着通俗小说的形式。如多克特罗的《欢迎来到哈德泰姆》采取了西部小说的形式,德里罗的《天秤星座》则使用了推理小说的手法。包括《法国中尉的女人》、《玫瑰之名》、《女勇士》在内的这些作品一出版就立刻成为流行的畅销书,并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究其原因,历史编纂元小说作为反映了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矛盾的文本,戏仿地运用通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传统,也就是说,它既运用这些传统,又在传统之中对其进行挑战和颠覆。这种杂交的小说是制度的和话语的复杂网络,囊括了后现代主义运作其中的精英文化、官方文化、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历史编纂元小说的这种包罗万象的万花筒式的创作使不同的读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如《法国中尉的女人》,批评家将其作为后现代主义文本来研究,普通读者则完全可以将其当作通俗爱情小说来读。这是这类小说得到广泛欢迎的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编纂元小说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种样式,但它并非唯一样式。例如在一般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中,元小说往往被当作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品,而并非所有元小说都有重新联结历史的特征。除了元小说以外,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小说还包括黑色幽默小说、新新闻主义小说、法国新小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那么,历史编纂元小说是否如哈琴所说,是具有范例作用的后现代主义创作,代表着后现代主义小说发展的方向呢?在一个去中心化的后现代社会中,试图以一种创作模式来示范所有的创作,并引领小说创作的潮流,这是否与后现代主义的精神不符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标签:小说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法国中尉的女人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拉格泰姆时代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玫瑰之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