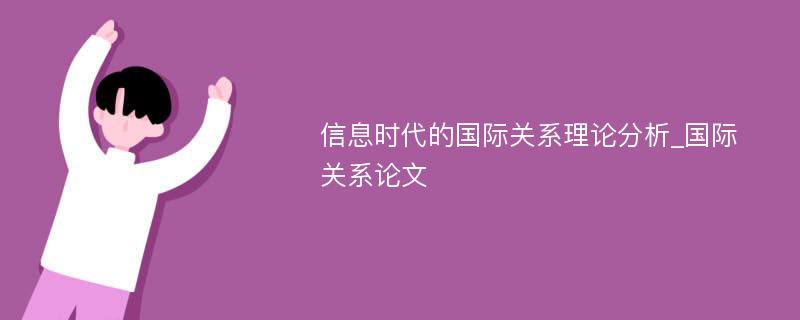
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理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国际关系论文,信息时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导言: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视野
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的跳跃式发展已经给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由于信息具有“第二媒介”的特点,其交互性、互连性、分权性、直接性、加速性、虚拟性、非地域性和非对称性的特性正在导致全球权力结构的微妙变革①。国际政治学家们在日益关注全球化时代各类新理论、新问题的同时,也开始将国关理论研究的视野拓展到这一新的领域②。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在世纪之交渐次成型。
总括而言,信息时代国际关系所出现的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特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1)由于信息接触渠道的开放为个人的权力扩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自然为信息时代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mance)提供了新的渠道,使得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非国家行为主体有可能跨越不同权力层次,以更加多样的方式进行稳定而可靠的交流互动;(2)文化、价值观等“软权力”因素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占据的重要位置日益凸显,在某些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有超越军事、技术等“硬权力”的趋势;(3)信息的加速性与非地域性特点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它加剧了各国政治主权事实上的不平等,限制和让渡了各国的经济主权,并且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捍卫“信息主权”的新课题;(4)信息国力的优劣日渐制约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与地位,而信息国力概念的介入使得传统的战争与和平理论面临“或改写,或淘汰”的挑战;(5)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实质性的拓展,信息安全成为国际斗争的新领域;(6)“数字鸿沟”成为南北关系中又一个重要的不平衡因素,由它所导致的“马太效应”将对构筑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形成新的挑战。
根据各种理论本身的流派渊源和立论特点,本文认为迄今为止的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均可纳入“新自由主义/乐观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批判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分析框架之内,前者从理想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蓝图出发对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的变革持乐观态度,次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社会理论出发对此持悲观主义的预测和批判分析的态度,而后者则坚持以权力和利益作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变量,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对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的变革作出了实用主义的考量。
二 新自由主义—乐观主义流派
以基欧汉与奈在70年代提出的“相互依存”理论为滥殇,新自由主义历经20多年的论战和发展,业已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并列的西方国际关系学两大主干之一。概言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点在于:注重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认定军事实力的作用相对减弱;国际合作领域明显扩大;提升“低级政治”的作用以纠正传统上对于“高级政治”领域的偏重;更加重视国际制度与规则;主张以“绝对收益”替代“相对收益”观念,等等③。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在秉承这些理论要旨的基础上有了新近的发展。
在权力结构方面,新自由主义论者普遍关注信息时代权力分散化或曰“非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趋向,认定国际权力结构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力正日益向个人及非国家行为体下放。麦克卢汉和殷尼斯在其著名的“地球村”理论中提出:无论在任何社会里,通讯媒体都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组织形式,经常会导致权力中心的转移④。前花旗银行主席兼里根政府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瑞斯顿提出了“信息本位”理论,认为信息革命正深刻挑战着世界权力结构,改变着全球的势力均衡,导致全球的权力转移。随着权力的基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信息时代的变革已经创造出一种“信息本位”,它要比旧的金本位残酷得多,同时也运行得更加高速有效⑤。
在权力方式方面,新自由主义将信息时代权力考量的重心,从“硬权力”转移到“软权力”之上。约瑟夫·奈指出,硬权力系指军事和经济力量,具强迫性,是一国使别国“做其所想”的能力;软权力主要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以及国际机制的制度与规则,是使别国“想其所想”的能力⑥。奈认为:在信息时代,“知识就是权力”,软权力的作用正日益凸显。谁能领导信息革命,拥有“信息权力”优势,谁就将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据领导地位⑦。
在国际格局方面,新自由主义强调: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以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体系”在国际政治中的支配地位开始削弱,而以全球相互依存为特色的“多中心国际体系”的地位日益彰显。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罗斯诺教授提出的“两枝世界”理论认为,二战以来世界政治经历了从“两枝”到“两极”的演变,出现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体系”与“多中心国际体系”相结合的“两枝”格局,并将在信息时代中向后者过渡⑧。
在政治倾向方面,新自由主义—反现实主义对于国家的关注,将目光投向形成中的市民社会和非国家行为主体。麦克卢汉提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与通讯系统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电脑正将我们移向‘世界意识’;与此同时,它还消除了具有集权化倾向的等级制度”⑨。威廉·杜顿的“电子接触权”理论指出:在构成民主的“永恒的三位一体”亦即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被信息和通信技术所动员起来的市民社会能够抵消全球化时代市场权力迅速膨胀、中小型国家面临主权侵蚀的失衡状态,在更大范围内形成新的平衡。
在国家主权方面,新自由主义认为传统民族国家治理国内外事务的操作主权在信息时代正经历着合乎逻辑的侵蚀过程,信息革命带来的贸易、金融、人口、文化和思想的自由流动将突破一切传统国家边界的界限,使僵硬的民族国家主权让位于日渐成形的“全球社会”。以美国学者奈斯比特和福山为代表的“全球社会”论者提出,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系统的演进,随着技术与人类互惠性的增强,一个“全球社会”正在出现。这个社会正日益通过全球通讯网络和全球化经济合为一体,出现了一整套新的、“后牛顿主义”(post-Newtonian)的价值观及社会组织原则,正取代着原有的“牛顿主义”等级控制⑩。
鉴于新自由主义—乐观主义流派在信息时代国关理论中的主流地位,本文将择要介绍其中3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分支:
“信息革命大引力区”理论 兰德公司信息革命未来研究课题组借用了天文学中“大引力区”(即二亿光年以远、正吸引银河系周边星系移动的一个中心吸引地带)的概念,认为信息革命的最终归宿将是所有地区与国家以不同速率、从不同距离逐渐被吸引向其靠近。这个“信息革命大引力区”(“Great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ttractor”)具有如下特征:
民族国家的权力与权威日益受到挑战;对于层出不穷的次国家社团、跨国家实体和超国家组织的权力增长,单个民族国家本身已经难以控制;
传统国家边界受到与日俱增的侵蚀和渗透,包括跨国贸易与金融的流动、人口跨国流动以及思想、文化和娱乐等的自由流动;
国际社会中的某些个人、集团、国家和地区将成为信息时代中权力、影响力和物质福利方面的获益者,但并非所有利益集团都能从中受益;
所有国家中享受信息特权、良好教育和物质财富的阶层和被信息革命边缘化的阶层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将导致民族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出现新的断层线。
兰德公司据此推断出信息时代中可能出现的8种不同的国家模型:信息革命的成功者(如澳大利亚);信息革命的驱动者(如美国);信息革命的奋争者(如韩国);信息革命的修正者(如新加坡);信息革命的虚饰者(如印度);信息革命的遗忘者(如扎伊尔);信息革命的抗拒者(如朝鲜);信息革命的落后失败者。各国在信息革命中的参与程度和成败取决于4种因素,即文化(Culture,包括语言、民族主义、法律框架、英才政治和信息观念)、能力(Competence,包括教育和通讯技术能力)、资金(Capital)和控制(Control)(11)。
“电子接触权”(tele-access)理论。英国经社研究学会信息与通信技术研究项目组(PICT)主席杜顿教授在继承马克斯·韦伯“接触权”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现代社会中的“接触权”和后现代网络社会中的“电子接触权”已经成为通往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主要阶梯。对新ICT(信息与通讯技术)的“电子接触权”使得处于边缘区的人们有可能不断挑战权力的中心。杜顿认为,从物理的“接触权”或“电子接触权”衍生出来的权力社会网络的存在或者缺失,将设置“网络社会”新的权力等级制度的基本参数;被电子接触权隔离开来的世界两极,正在促成一个“新封建体制”的形成(12)。
“广域信息政治”(Noopolitik)理论。美国学者阿奎拉Arquilla和隆菲尔特(Ronfeldt)提出,广域信息政治是一种信息时代的对外政策行为,它强调思想、价值、范式、法治和伦理的主导作用。该理论认为,现实政治将国家捆绑在利益的战车上相互对立,而广域信息政治鼓励国家以联盟和其他互助框架的形式发展合作;现实政治倾向赋权于国家,而广域信息政治倾向赋权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交错网络;现实政治的作用方式是通过人力、导弹、枪支、炮舰等“硬权力”,而广域信息政治强调的是吸引别国的“软权力”;现实政治声称实力造就公理,广域信息政治则认为公理创造实力。两者将在世界上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里、不同性质的议题上共存。因此,美国要在信息时代曙光初现时努力承担起新的“天定命运”:在全世界传播它的理想、伦理和价值观(13)。
纵观以上理论分支我们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在信息时代国际关系方面的理论线索,突出了国际权力结构中的权力分散化特点,凸显了从“硬权力”到“软权力”的权力方式转移、从传统国家主权到新型“全球社会”的过渡和从国家到市民社会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变迁。迄今为止,这种新自由主义—乐观主义的论点在信息时代国关理论中仍然居于主流地位。然而,该流派对于信息时代国际政治不平等本质的无视和过分乐观的理想主义论调受到了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判。
三 马克思主义—批判主义流派
新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致力于沿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经济社会基础、冲突与革命等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研究方法批判、分析、揭示当代国际关系中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掩盖的矛盾冲突,在信息时代国关理论上亦已有所建树。新马克思主义否认信息革命给国际政治的根本问题和基本变量带来了实质性变化,强调指出国际关系中被新技术乐观主义掩盖的实质性不平等。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必然是“你得我失”的零和关系,信息时代的国际关系不可能仅仅由于新技术的介入而走向和谐,国家主权也不会最终让渡于所谓的“全球社会”。信息时代的国际格局仍将是核心地区与外围地区的多层次国家体系,其权力结构仍将是植根于资本扩张本性的核心区域中心化与外围区域边缘化两重结构。
沃伦斯坦最早在其“世界体系”理论中批判了那种认定技术进步必将改变世界体系性质的技术决定主义论调。他指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它始终保障的是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和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14)。没有理由认为这两个过程将由于信息技术革命而改变。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韦伯斯特教授进一步提出了“资本主义延伸”理论,认为信息时代的到来与其说标志了一个新型社会的开端,毋宁说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延续、巩固与拓展,是一种向全球蔓延的“新圈地运动”。尽管信息劳动的“灵活性”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只是代表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要求。在把信息时代出现的新阶级结构描述成“信息社会的铁笼”之后,韦伯斯特指出:国际社会和该阶级结构的多变性不应归因于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动荡,而是源于作为资本主义内在特征之一的永不满足的动力机制(15)。
澳大利亚学者哈桑的“空间危机”理论指出:信息革命的渊源是由“空间危机”所驱动的全球化过程,以及由“空间危机”直接导致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由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无限度地积累资本,而地理空间却在同时迅速递减,这种永恒的“空间危机”迫使晚近资本主义全球化形成了两种相互关联的空间维度:外向全球化(地理上的外向扩张)和内向全球化(文化和社会上的内在空间侵蚀)。通过外在全球化和内在全球化的双重过程,资本主义的市场力量正裹挟着跨边界、跨文化的信息大潮,将原本独立的“认同空间”湮没。哈桑认为所谓“赛柏空间”和“虚拟社区”都是极为虚幻的空间,为信息科技所虚拟化的其他网络乌托邦式的梦想无非是天真的童话而已,因为信息革命是从某种特殊类型的全球化过程中演化而来的,它驱动技术发展的主要考虑,仍然是利润、生产率、节省劳动和逃避主义。因此,信息技术的主要功能,实质上是获取利润和支配的手段。哈桑强调,只有当生产方式的支配民主化之后,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全球电子“民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16)。
四 新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流派
肇始于肯尼思·华尔兹1979年完成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新现实主义思潮,在新形势下努力克服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局限性,开始了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兴时期。在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中国家中心思想、利益驱动理论、自助学说和权力核心等理论基点的同时,新现实主义也更加强调国际结构对互动单位的影响,注重结构层次与单位层次的体系结构分析;更加关注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之间日益不对称的相互依存;更加注重经济因素的作用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更加认同国家对于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主体控制力减弱的观点;更加致力于将权力与道义、秩序与霸权、冲突与合作、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研究(17)。信息时代国关理论的新现实主义流派秉承了这些特点。
在权力结构方面,新现实主义流派强调仍应将国际政治视为一个定义精确的结构体系,考察信息时代权力在结构层次和单位层次的双向互动关系。在承认信息时代的国家已无法垄断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力的同时,新现实主义并不赞同夸大个人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作用,更反对后者将逐渐取代前者的新自由主义观点。他们相信,信息革命给国际体系结构带来的巨大冲击,必然与系统中单元层次上的国家产生互动的因果作用。这样,信息革命本身不仅成为了促成国际体系结构变动的关键因素,而且也对现存国际政治权力互动的本质产生了“乘数效应”。
在权力方式方面,新现实主义将信息界定为提升传统权力效用的媒介,实质上扩展了“权力”的传统定义和作用方式。卡尔·多伊奇曾经将权力的基础分为权力的资源、权力的结果和权力的领域范畴等3个层次,强调知识积累和沟通作为外交决策过程的要素作用,实际上体现了将知识和信息作为权力内涵的思想。多伊奇还进一步将沟通理论运用于外交决策分析,提出国家行为者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为了达到既定的国家利益目标,必须不断通过信息沟通渠道,一方面从社会精英、政府部门、大众传媒和普通民众的经验记忆中学习教训,另一方面从环境中吸收新的信息,逐渐调整形成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决策(18)。因此,信息不仅是外交决策中增强反馈—自我矫正能力的有力媒介,也是国家提升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的有效手段。
在国际格局方面,新现实主义认为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将继续支配信息时代的国际格局,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轨迹,将最终取决于信息革命所造成的权力转移过程。吉尔平指出,国际秩序是国家配置物质财富的基本能力,新的国际秩序将反映新的国际力量分配格局。各国加紧制定国家信息政策,实施信息战略,正是为了让本国在信息时代的国际力量角逐中赢得优势,争取在未来的国际格局中获取更大的权力份额。
在南北关系方面,新现实主义指出:国际社会中“信息穷人”和“信息富人”之间的数字鸿沟将逐渐扩大,南北的不平衡将由于信息国力的介入更趋严重。诚如新现实主义的“强化理论”(Reinforcement Theory)所指出:社会公正从来都不可能是机器的自动产品。信息革命不仅强化了现有的权力序列位置,而且阻碍了原有权力关系的根本变革——它导致的将是现存结构的一种“固化”(19)。
在政治倾向方面,新现实主义坚持认为国家仍是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主权国家的中轴地位不容挑战。科普林提出的“新中世纪主义”(Neo-medievalism)理论从“空间、地理与边界的淡化”、“权威的模糊化”、“多重效忠”、“公共领域与私有领域的无区别化”以及“大一统的信仰体系和超国家的集权化”等5个方面探讨了信息时代国际关系向中世纪时代回归的相似现象。他坚信,尽管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革正使得国家经历蜕变的过程,信息时代的超国家力量与主权国家的核心作用将并行不悖,民族国家和国家体系将不会走向凋萎(20)。
在国家主权方面,新现实主义承认信息时代的国家主权不再是不可分割、不受限制的,但主权的合理核心必须坚持。罗斯诺在其“分合并存”(fragmegration)理论中指出:信息时代的国家主权将同时受到冲突—分裂与合作—整合的影响。面对国家主权正受到侵蚀、走向“空洞化”的情势,国家开始从过去的强调国家自主性和生存权的最高价值,逐渐朝国际合作、区域合作和建立制度化机制等方向调整。但即使在信息化与“分合并存”时期,国家仍发挥着一定的角色功能,充当着国民的主权代表(21)。
“信息时代权力与相互依赖”理论。基欧汉和奈将“复杂相互依存”理论中的假设与概念进一步运用于信息时代,在努力维护其理论完整性的同时,也深化了新现实主义者对于信息流动性质的理解。他们认为:尽管世界正日益变得“在信息上相互依存”,民族国家仍然主导着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效忠,控制着大多数的人类资源。自由主义并没有充分考虑信仰的延续性、制度的顽固性和信息世界与传统世界之间相互重叠和彼此依赖的关系,就直接从技术变革演绎出政治后果,从而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渊薮。
基欧汉与奈认为:信息革命通过指数级地增加世界政治中沟通渠道的数量,改变了传统的相互依存的模式,然而信息革命本身是存在于现存政治结构的背景之下的,其主要受益者注定仍是大国、强国,而小国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并不会显著增加。所谓“信息革命将导致国家权力的分散化和平等化”的新自由主义论调,无非是玫瑰色的理想主义梦幻而已。他们强调国家是有弹性的概念,基于地理分布的传统国家将继续塑造信息时代国际政治的主要结构,但是面对信息来源多样化的时代趋势,各国将更多地依赖公众可信度和统治合法性等“软权力”,更少依赖物质资源等“硬权力”。由于拥有信息技术、网络语言和标准规范方面的优势,美国将有能力运用“软权力”(在下世纪将主要是信息技术带来的权力资源)实现预定的现实政治目标(22)。
“资讯化政治”(Cyberpolitik)理论。哥伦比亚大学的罗斯科夫教授认为:信息时代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即“资讯化政治”,这种国际政治中的行为者不再仅仅是民族国家,原生权力(raw power)可以为信息权力所加强或抵消。由于信息能力的展现将成为权力形成的第四大因素,信息时代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定义已经增添了新的内涵。在信息时代,无论是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可以借由信息权力这一“第四权力”的媒介而获得提升。国家机器将试图通过信息能力加强控制,而非国家行为者也可以通过信息能力发挥其虚拟社区整合、宣传和影响政策的功能。罗斯科夫批评了克林顿政府将权力的中枢系于美国价值观体系的“理想政治”(idealpolitik)主张,指出信息时代国际关系在总体上仍将为现实政治主导。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国家仍将是唯一有能力解决国际关系中所有为全球市场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权力中枢;国家不仅不会从国际关系的视野中消失,还必将通过寻求界定新的角色来对抗权力的分散化趋势(23)。
五 几点评价
1.无论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流派都承认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国际关系中增添了许多新的变量,而这其中有许多领域是从来没有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论及的。在充分估量到信息时代国际关系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的特点和影响的基础上,各理论流派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各构成要素或进行了解构、或进行了补充。但笔者认为仍有必要重新界定“权力”、“主权”、“行为体”等国际政治中的基本概念,以适应变化中的国际关系。
2.这3个流派各自秉承了其理论渊源的要旨和基点,业已形成本流派在信息时代国际关系问题上的鲜明立场,其日益清晰的发展脉络,标志着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理论正走出混沌、日臻成熟。笔者尝试通过下表对这3个流派的不同主张作一对比归纳(见表1)。
表1.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的对比分析
新自由主义流派
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新现实主义流派
权力结构
权力分散化使非国家 核心区域中心化和外围 信息革命对现存国
行为体受益 区域边缘化两重结构
际政治权力互动存
在“乘数效应”
权力方式
从硬权力向软权力方 获取利润和支配的手段 提升传统权力效用的
式转移 “第四权力”媒介
国际格局
以国家为中心的无核心地区和外围地区
信息革命造成国家
政府体系走向式微的多层次国家体系 权力转移,将塑造
未来国际秩序
南北关系
南方国家可以借助“新圈地运动”:新技 南北的不平衡将由于
信息后发优势改善术乐观主义掩盖了南北信息国力的介入更趋
处境 关系的实质性不平等 严重
政治倾向
关注形成中的市民 信息时代仅是资本主义坚持主权国家的
社会和非国家主体 国家体系的延续、巩 中轴地位
固和拓展
国家主权
主权受到信息流通侵
国家主权是至上、不可
灵活坚持主权的合理
蚀,让位于“全球分割的 核心
社会”
3.新自由主义流派对于信息时代国际关系作了过于理想主义的描述,却忽略了许多严峻的问题,很容易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信息霸权和文化侵略、侵蚀发展中国家信息主权的理论工具。
4.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体系,揭示了信息时代国际关系中深层次的问题,指出了信息时代不平等的症结所在。但是其分析方法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于信息时代国际关系也抱有悲观主义的倾向,有的理论甚至根本否定信息时代的革命性本身。
5.新现实主义流派紧紧抓住“国家行为体”的核心作用,以“权力”和“利益”作为分析的焦点,体现了国际政治的延续性和国家作为历史沿革的坚韧外壳。但是其实用主义的观点仍然是“现实政治”的延伸,实际上肯定了现存国际体系的合理性,甚至认为信息革命只会导致现存国际结构的固化。
6.面临信息时代国际格局的重大调整和信息国力提升的严峻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们亟需跟踪西方理论研究的成果,创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为我国在新世纪国际信息国力的角逐中制订实施前瞻性的外交战略作出理论贡献。
通讯地址:100037 北京展览路24号
电子邮箱:champson@263.net
----------------------------------------
注释:
①David J.Rothkopf,“Cyberpolitik:the Changing Nature of Power in the Information Ag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1,No.2(Spring 1998),p.339.
②在国内,信息时代国际关系也成为近年来国关学者们关注的新焦点之一。代表性论著可参见龚文庠:《信息时代的国际传播:国际关系面临的新问题》,载《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3期;薄燕:《信息技术革命与国际政治》,载《国际论坛》2000年第4期;彭慧莺:《资讯时代国际关系理论与时务之研究》,载台湾《问题与研究》2000年第5期第39卷。但在系统介绍西方既存理论和构筑中国特色理论方面,国内研究仍缺乏力度。
③Joseph Nye,“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World Politics,January 1988.
④Philip Marchand,Marshall McLuhan:The Medium and the Messenger,Cambridge MA:MIT Press,1998,p.350.
⑤Walter B.Wristen,“Bits,Bytes and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Vol.76,No.5(Sept./Oct.1997),pp.172—182.
⑥Joseph Nye,“Hard Power,Soft Power,”Boston Globe,6 August,1999.
⑦Joseph Nye and William Owens,“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1996.奈认为,在信息时代中,美国可以运用软权力战略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影响世界各国制定它们的战略议题和主题,使其与美国的利益吻合,“不战而屈人之兵”。
⑧James Rosenau,“Normative Challenges in a Turbulent World,”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1992.
⑨Philip Marchand,ibid.
⑩John Naisbett,Global Paradox,NY:Avon Books,1994;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London:Hamish Hamilton,1994.
(11)Hundley,Richard O.,Robert H.Anderson,Tora K.Bikson,James A.Dewar,Jerrold Green,Martin Libicki,and C.Richard Neu,The Global Course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RAND,CF—154—NIC,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CF/CF154/,Santa Monica,California,2000.
(12)William H.Dutton,Society on the Line:Information Politics in the Digital A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416.
(13)John Arquilla,David Ronfeldt,The Emergence of Noopolitik:Toward an American Information Strategy RAND/MR—1033—OSD,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033,1999;John Arquilla,David Ronfeldt,Swarming and the Future of Conflict,RAND/DB—311—OSD,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DB/DB311/,2000.
(14)王正毅:《世界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评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载《中国书评》,1996年5月,第136—158页。
(15)Frank Webster,“Information,Capitalism and Uncertain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3:1 2000):pp.69—90.
(16)Robert Hassan,“Globalizat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within the Space Economy of Late Capitalism,”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3 1999):pp.300—317.
(17)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学派、论战、理论》,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1期,第19页。
(18)Karl W.Deutsch,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78,pp.185—199.
(19)Christine Bellamy and John A.Taylor,Gover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PA:Open University Press,1998,pp.208.比尔·盖茨本
人也承认:虚拟世界的平等要比现实世界的平等更容易实现。
(20)Stephen J.Kobrin,“Back to the Future:Neo—medievalism and the Postmodern Digital World Econom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1,No.2(Spring 1998),pp.361—386.
(21)James N.Rosenau,“New Dimensions of Security:The Interaction of Globalizing and Localizing Dynamics,”Security Dialogue,Vol.25,September 1994,pp.255—282.
(22)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Volume 77,No.5,1998:pp.81—94.
(23)David J.Rothkopf,ibid,pp.325—359.
----------------------------------------
标签:国际关系论文; 新现实主义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信息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世界格局论文; 政治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全球化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家主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