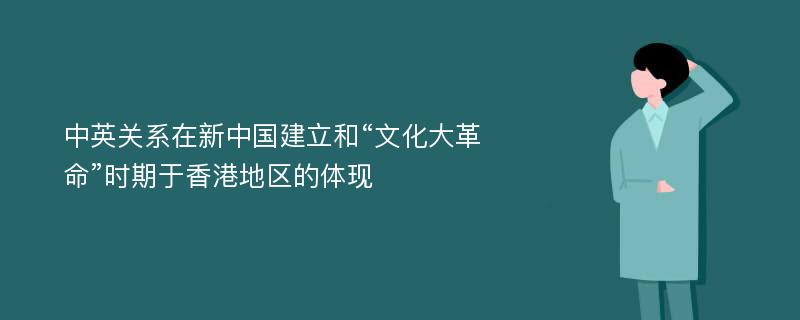
关怀广[1]2000年在《中英关系在新中国建立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于香港地区的体现》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前后,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可说充分体现和反映出中英两国关系中的种种矛盾、斗争和妥协,在“两航事件”,“加强社会控制”、“三·一事件”、“大公报案”等事件上,中英之间的角力既有激烈的一面,也有协调的一面。本文以解放初期香港发生的种种重大社会事件为主线,分析中英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和斗争,除了探索中英的既定政策,本文也从种种社会事件的动态发展中阐述该等政策在事态中的变化发展。 此外,解放前大批中国著名文化人停居香港,一俟解放便纷纷回国为新社会服务,从而对香港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国内也有不少著名知识分子在解放时南下香港,并在香港掀起了新的文化潮流,而新亚书院也是由钱穆、唐君毅等南下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底创立的。 本文就新中国建立震荡和影响下的香港文化变迁,进行深入探究和剖析,从中找出香港在中西(美元)文化交汇下的演进轨迹。 1967年“文化大革命”高潮时,香港也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英抗暴斗争”,其后在八月下旬更导致中英关系出现史无前例的危机——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在“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的策动下遭到群众放火烧毁,其导火线是港英政府查封了香港的三家爱国报纸。 本文详尽叙述了国内“文化大革命”同香港“反英抗暴斗争”之间的互动关系;英国和港英当局的不当政策如何激起了严重的社会冲突以及它们如何回应“中央文革小组”在香港掀起的“反英抗暴斗争”。此外,也详尽地剖析了中英在香港交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并且从动态的视角阐述了香港的社会动荡同国内局势发展的互动性,二者之间息息相关和相互作用。 总之,中英关系在1967年文革高潮时跌入谷底,经历了彻底破裂和骤然缓和的两极阶段,而这种极端反向的转变正是中国国内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结果,因此在香港的中英交锋同中国的外交路线之争可说是紧密相连的,而本文在这些方面有深入的阐释。 另外,“文革”对香港的报界和文化界也有极大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是透过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造成的,有些则是直接由“文革”的批判造成的(如朱石麟之死),本文对此均有详细的叙述和认真的探究。
王永[2]2011年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研究(1979-1984)》文中研究表明英国在19世纪后期,利用坚船利炮开启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朝签订有关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三个条约,强占了中国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租借新界。新界租约的签署,对未来的中英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界租约的“威力”在香港和英国都明显的表现出来。英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要求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英国的殖民情结促使它想继续呆在香港,并对其抱有很大的期望。撒切尔夫人访华之后,双方开始关于香港九七安排后长达两年的谈判。谈判期间,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硬立场,英国的立场步步后退,从秘密谈判阶段坚持香港主权到正式谈判前四轮坚持香港的治权再到第七轮至第十二轮正式谈判期间,坚持“九七”后英国保持香港的联系,直到最后被迫同意“九七”后完全退出香港。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简述香港问题的由来和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收复香港的努力及新中国成立后对于香港的政策。近代史上,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低下和国家实力的不济及内部不断出现的纷争,中国收复香港的希望屡屡破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从香港对中国的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出发作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保持香港现状不变”的方针政策。第二章描述了新界租约对香港和英国的影响,迫使英国政府就香港问题要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对香港未来的作出明朗的安排。在20世纪70年代末,新界租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香港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香港的混乱对英国的影响十分严重,英国政府感到有必要向中国政府询问其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但是鉴于香港之于英国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兼之英国的殖民心态,英国不愿意退出香港,从而作出继续留在香港的决定,因此对香港准备施行非殖民化策略,维护英国在香港的利益。英国政府并且开始对中国政府进行诱导,以稳定香港为由头要求中国延长新界租约,解除九七大限对英国的禁锢,使谈判向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鉴于英国在其他殖民地的作为,中国政府对此极为警惕,防止英国的非殖民化策略在香港问题上施用,对于英国政府不断要求延长新界租约表示坚决的拒绝,在香港问题上,中国逐步掌握了主动权。第三章,撒切尔夫人访华,两国政府在最高层级就香港问题进行交流。由于双方对于香港问题的立场迥异及两人强硬的个性,双方的交流处于极度对立的状态。撒切尔夫人的访问将两国的差异摆在世界面前,开始严重影响香港社会信心和香港经济。大英帝国情结浓厚的撒切尔夫人把中国作为耻辱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作为讨价还价的武器。激起包括香港在内所有中国人的愤怒,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撒切尔夫人的访问,并对以后的中英谈判产生负面影响,曾经影响了谈判的进展。第四章,中英谈判关于香港问题的秘密磋商和正式的谈判。由于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差异,使谈判几度陷入僵局。但新界租约的局限性和中国力量的强大及形势的差强人意使英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手段只有谈判一种方式,英国在谈判中的劣势注定它无法与中国强硬。谈判的过程,英国谈判人员试图利用其丰富的外交经验和熟练的外交技巧要求中国答应英国继续呆在香港。同时,英国为达到继续呆在香港的目的,利用“经济牌“信心”牌“民意”牌,向中国施压。在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坚持原则问题的坚定性和非原则问题的灵活性相结合的高度统一。香港社会的一部分人士对中英谈判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过去的三年里,因为中国过去政治运动的影响和意识形态差别及已经适应了香港的管理模式等各方面,香港社会出现了不愿回到中国的心态,他们希望英国继续治理香港。更重要的是,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过程中,华人议员向英国提出与中国谈判的建议,使中国政府非常的尴尬和愤怒。他们要求英国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正式谈判进行到第五轮,英国被迫同意中国收回香港治权的立场,他们承诺要退出香港1997年英国完全。香港社会特别是香港的华人议员对此极为愤怒,认为是中英两国联手背叛了香港,从而对英国的感情由原先的依赖信任转向怀疑猜忌。第五章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着重讨论了在英国坚持主权换治权的原因。本文认为殖民心态是促使英国不愿意退出香港的主要原因,另外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认识上的偏差及香港社会对英国的依赖也是导致谈判多次陷入僵局的因素。
翟石磊[3]2016年在《当代中国政府“西方观”话语的变迁——基于中央政府历年报告文本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东方主义”文化话语下的“西方”渗透着西方主义的支配性与霸权思维。但是在中国政治语篇分析中,“西方”却经历了作为“革命”的对象、“合作与对话”的对象以及日渐“平等的他者”等三个阶段。中国政治话语中的“西方”是对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西方”的解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解构而不断建构一个政治话语场域的“革命的东方”“发展的东方”以及“大国东方”。这类话语逐渐摆脱了“东方主义”对“我者”与“他者”二元对立关系的框定,进而实现了不同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发展阶段的国家话语之间的对话与融合,也符合中国作为一个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向“半边缘”,并逐渐进入世界体系“核心区域”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中国政治话语视域下的“西方”形象的嬗变恰恰印证了中国世界观与自我中国观认知的发展;中国的“世界观”话语也逐渐走出“冲突与对抗”的二元体系,走出了具有排外倾向的“本质主义”话语,进而塑造了中国特色的“批判性世界主义话语”。
参考文献:
[1]. 中英关系在新中国建立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于香港地区的体现[D]. 关怀广. 暨南大学. 2000
[2].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研究(1979-1984)[D]. 王永.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3]. 当代中国政府“西方观”话语的变迁——基于中央政府历年报告文本的研究[J]. 翟石磊.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 2016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文革论文; 中国英国论文; 香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