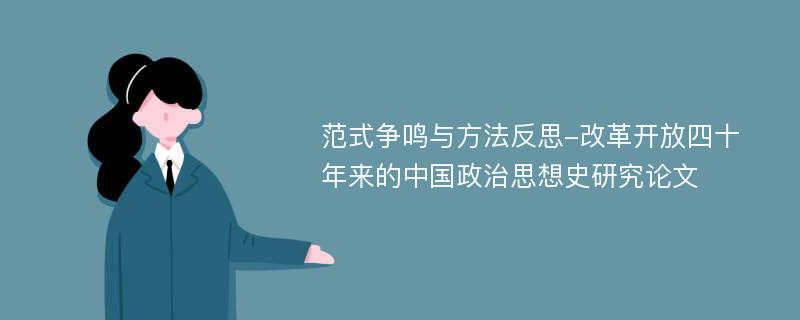
范式争鸣与方法反思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张师伟
摘 要: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曾一度近乎中断,改革开放后才渐渐恢复和发展,它在研究范式与方法上受民国时期相关学术成果的影响相当有限,而更多带有浓郁的时代性特征。这种时代性特征,一方面体现在改革开放时代反思传统以走向现代的启蒙范式与自五四以来一以贯之的历史分析方法;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渐热背景下,提倡回到传统以实现个性化现代的经世范式与中国传统哲学史研究所惯用的哲学分析方法;另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和方法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改革开放;范式争鸣;方法反思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无疑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和极为丰富的理论资源。但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却只有大约百年历史,其间还有近30年的时间不绝如缕,晚清民国时期的相关学术传统近乎中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得以恢复,但其知识体系的锻造却几乎要从头开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化知识体系在改革开始时期的恢复和发展,都以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为依托,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体系的锻造。有的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传统出发,梳理中国历史上各个阶级及其思想代表关于国家与法的观点与理论等,形成了一种以运用阶级分析和文本分析见长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这就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学范式。(1) 参见徐大同:《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线索与特色》,《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第3-15页。 有的研究者则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基础,坚持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原理,立足于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梳理基于中国独特国情的政治意识,将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与政治观念等贯通和结合起来,形成了学术界所称的“王权主义学派”(2) 参见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文史哲》,2013年第4期,第5页。 ,这就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学范式。有的研究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反思和批判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等(3) 参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2页。 ,其中有些新儒家的批判者后来站到了新儒家的行列中,如罗义俊就“公开站到港台新儒家的立场上”“批评大陆马列派”(4)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615页。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文化保守主义渐趋合流,孕育和形成了大陆新儒家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大陆新儒家当中有学者自觉地将他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归纳为“古典史学范式”,它“以承认中国古代之政治思想之永恒和普遍属性为前提”,“五经和经学将成为政治思想史研究之核心”。(5) 姚中秋:《重建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第21页。
(2) The function of the Ultralab experimental management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不同范式具有价值方面的巨大分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中,反封建和启蒙的价值主要集中在王权主义学派等历史学的研究范式中,文化保守甚至是政治复古的价值主要集中在经学研究范式中;不同研究范式各自所推崇和惯用的研究方法也差异很大。政治学研究范式比较推崇和惯用阶级分析方法与理论解释方法,并辅之以现代政治学的一些方法,但又常常在历史方法运用上有所欠缺。历史学研究范式比较推崇历史方法与命题分析方法,并辅之以政治学的一些方法,其长处是批判分析到位,比较实事求是,其不足则集中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化研究方面。经学研究范式惯于使用抽象哲学分析方法,并辅之以一定概念分析,其长处是饱含深情,聚焦于寻找当代中国何以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依据,其不足则是缺乏历史方法的必要应用,存在着太多的主观投射和过度解释,在政治上拥有太强的政治复古诉求,许多观点及主张等被包裹在国学中,直接冲撞了现代价值的底线。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多样价值与多元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领域,它自产生以来就不仅广受哲学、历史学及政治学等学科的关注,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聚焦领域,而且还受到不同价值倾向学者的共同关注。有的学者试图从中发现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所在,寻找所谓中国文化的“常道”(1) 参见李存山:《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载《光明日报》,2015年08月24日第16版。 ;有的学者试图在历史上发现现代中国的“源头活水”(2) 参见许苏民:《“源头活水”与“中国特色”——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建设》,《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3年第3期,第1页。 ;有的研究者试图将明朝中后期以来的历史进行一以贯之的解释,以便发现中国走向现代的内在逻辑,强调“理在经由清代的过程中,从封建的秩序原理自我转变为清末的共和的秩序原理”,这体现了中国近代相对于欧洲的“相对独立性”(3) 参见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索介然、龚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页。 ;有的学者试图从中发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传统文化之累,以便从历史中走出来。(4) 参见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自序》,第2页。 不同研究者在哲学立场、价值倾向、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上的明显差异,造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多种范式并存格局。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中国大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寄身于历史学及哲学学科,在价值倾向、哲学立场、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上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也仍然存在着不同范式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1) 参见张师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东南学术》,2009年第2期,第5页。 这个时期的港台及海外学者间也存在范式上的明显差异。(2) 参见葛荃:《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文史哲》,2006年第5期,第144-145、147页。 学术界已经存在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多元范式,作为一种既有的学术资源,势必会在范式选择上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恢复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其中就包含着价值选择方面的主要影响。不仅如此,实际上,当改革开放开启的思想解放洪流滚滚而来时,价值认识上的多元化也广泛影响到了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政治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恢复并获得初步发展,哲学、历史学研究逐步摆脱了教条主义羁绊,两者都提供了各自的价值倾向及学科方法,共同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多元学科的价值倾向与学术支撑。这个多元学科的价值倾向与学术支撑,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产生了直接的决定性影响。(3) 参见张师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第8-10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等通过作用于政治学的概念选择及理论建构影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学范式。中国哲学摆脱教条主义影响后的概念解释及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并最终孕育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经学范式。中国历史研究摆脱教条主义影响后,注重历史事实梳理和社会生活内容的呈现,产生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学范式。
改革开放后西学再次进入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中国近40年价值多样化的外部理论资源,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的利益分化与阶层多样化则提供了价值多样化的社会基础。每一种具有社会凝聚力和思想吸引力的价值体系,都有其确定的核心价值,并且也都有各自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根本看法,这种根本看法在研究实践中表现出来就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特定范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恢复之初在价值上以反思和批判为基调,虽然都在反思和批判“文革”的错误思潮,但反思和批判的具体对象又各不相同。有的研究者聚焦于批判和反思教条主义,积极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如徐大同先生等于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即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史知识中的政治知识内容。(1) 参见徐大同、陈哲夫、谢庆奎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6页。 有的研究者批判和反思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历史残留,注重运用历史方法来呈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的基本事实,分析传统政治理论的内在逻辑等,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传统,以便从中国传统的封建历史中走出来,如刘泽华先生于1984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就是如此。他强调,“不能把政治思想都装入阶级的口袋”,政治思想还具有“超阶级的内容”,还有“社会性”,“政治思想本身并不都是阶级的”,“不能把每一种思想命题统统还原为阶级的命题”。(2) 刘泽华:《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三联书店,2017年,第270-271页。 有的研究者批判和反思20世纪的文化激进主义,在实质上延续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试图从中国传统中寻找到现代中国的文化源头及核心要素,并由此而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一个支撑点,以此为基点,中国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经过儒学热及国学热逐步在价值上递进到了政治保守主义。有的研究者则在批判和反思中国传统中走向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价值上走近了全盘西化,追求以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来理解和评价中国政治思想,彻底否定中国政治思想还具有现代的价值,即使它在现代中国还有诸多影响,也被他们解读为一种妨碍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教条主义与僵化方法的批判和反思较大地影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恢复之初的研究范式,如徐大同等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朱日曜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桑咸之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等,即是如此。与此同时,历史学家运用历史研究的思维和方法,贯彻了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原则,也建立起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最重要的代表是刘泽华先生,他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堪称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典范之作”(3) 参见杨阳:《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百年典范——评刘泽华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32页。 ,在体现政治思想通史的贯通性和整体性上有相当代表性。(1) 参见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贯通性理解与整体性呈现》,《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63页。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撰述体例以列传式为主。不论是断代史内容的撰述体例,还是通史内容的撰述体例,均以思想家的列传体为主。该撰述体例聚焦于一个又一个的思想家个体,既注重对每个思想家个性化思想内容的呈现和剖析,也注重对思想家之间相互关系或联系的梳理,将每个思想家的个性化思想按照他们在思想上的相互关系,同类或同一时代的思想家连成一章,异类或异代的各章连缀起来,形成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通史或断代史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通史类或断代类著作大多采取列传体的撰述体例,徐大同等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朱日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都采取了列传体的撰述体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首先需要进行的是按思想家或代表作进行列传式的研究”,“列传式的研究是基础性的研究”,“对思想家和代表作研究不够,也就难于进行其他方面的研究”。(4)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第87页。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些专著在撰述体例上将列传体和政治思潮、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政治哲学等融合起来,形成了列传体的改良版。这种列传体的改良版既是以时代先后为线索,也以时代思潮来充实时代序列,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发展线索上表达为一个政治思潮接着一个政治思潮的前后连续,处理了不同时代思潮之间在内容上的批判与继承关系,不仅使人们看到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过程中在内容上的新陈代谢,而且也给人们展示了中国政治思想在理论上渐趋于成熟的发展过程。这种改良版也在撰述每个历史阶段政治思想内容的章节中进行列传体的撰述,一方面展现某个特定历史阶段政治思想的内容深度和理论高度;另一方面也以比较纯粹的理论逻辑来展现特定历史阶段政治思想的框架结构和思维特征。(1) 参见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贯通性理解与整体性呈现》,第65-66页。 刘泽华等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典范,在撰述体例上就采取了这种列传体例的改良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题性研究在撰述体例上有别于列传体,它们一般以特定的政治思想问题为研究对象,或者按照特定政治思想问题的发展顺序来撰述,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就是按照时序撰述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各阶段及主要内容,其中包含很多列传体个别研究;或者深入分析特定政治问题的各个方面,刘泽华等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就是如此。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恢复后,就受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知识论取向及实践论取向的双重影响,两种影响都具有明显的启蒙价值导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论取向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它的首要研究目的,就是呈现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社会科学知识一部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其次还体现在它的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并强调了阶级分析方法的决定性地位;再次还体现在其知识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上,即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不仅以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为线索,而且也以阶级、阶级斗争、阶级更替的历史进步为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为一种进化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它在知识论层面上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指导,在价值上体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思想的启蒙取向,虽然它的结论是在阶级局限性、历史局限性的名义下作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论取向,要求它所指导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要立足中国现实,并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妥善处理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依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都要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发挥有助于解决实践问题的资政经世作用,但也只限于古为今用的批判继承,与启蒙的价值诉求并不矛盾,从而与复古派所强调的复古经世迥然不同。一些研究者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理论,通过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历史哲学的研究,试图在明清之际的政治理论中寻找现代政治的“源头活水”(1) 参见许苏民:《“源头活水”与“中国特色”——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建设》,第1页。 ,或者试图找到传统与现代在明清之际的政治思想结合点(2) 参见冯天瑜:《文明近代进路的共通性与特异性——从〈明夷待访录〉“新民本”诉求说开去》,第8页。 ,或者试图在中国传统中找到所谓的“常道”,并以此“常道”贯穿中国政治的传统与现代(3) 参见李存山:《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载《光明日报》,2015年08月24日第16版。 。他们在研究的旨趣及结果上无疑体现了知识论取向,但也不排除他们因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延续性联系,从而与启蒙的价值诉求有些偏离,并在价值诉求上更接近复古派的经世追求。
一般来说,近40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科范式有五方面。其一,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范式。这个视角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的逻辑为依托,以特定政治学基本理论所关注的政治问题为关注点,注重分析历史上不同时代思想家对特定政治问题的解答,并在分析其解答的基础上来总结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民族性特点,强调西方政治思想的内容特点是组织国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特点是“注重治国之道,而不注重制度的研究”,“中国古代就把政治理解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2) 徐大同、高建:《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第5-6页。 ,其代表人物是徐大同教授。其二,中国历史学的学科范式。这个范式坚持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思想传统,以历史性地分析和呈现中国政治思想的概念含义与思想逻辑为立足点,比较关注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批评、批判和超越,强调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特质是“王权主义”,其主要的代表就是以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为标志的“王权主义学派”,“这个学派的学术旨趣集中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而王权主义历史观是其解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分析工具”(3) 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第5页。 。其三,历史哲学的学科范式。这个范式以线性历史哲学所揭示的人类政治生活的发展逻辑为立足点,比较关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整体性文化解读,或试图从中国政治思想主流的概念、范畴及理论中搜寻出现代法治等思想因素。有学者提出“先秦儒家提出的民本、公平、慎刑、预防犯罪等思想,与现代法治精神高度相契合”(4) 范高社、高阳:《先秦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契合与冲突》,《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66页。 ,或试图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其“常道”,并为儒家在现代立“新命”,其主要代表就是李存山。(1) 参见李存山:《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光明日报》,2015年08月24日第16版。 其四,儒家价值哲学及宗教建构的范式。这个范式坚持了近代中国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以儒家价值哲学及政治哲学为主要关注点,试图在儒家经学传统基础上,复活并重构晚清康有为以来的儒教政治理论,并力主以传统儒家经学为主要思想资源,来建构现代中国的政治儒学及儒家的宪政,“以王道仁政为基本特征的儒教宪政,建立在‘天人合一’的人性假设上,以贯通天、地、人的圣王统治为前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以中和为天下之达道,以贵民、富民、教民为核心职责,以人性的自我完善和实现天下大同为目标”(2) 包万超:《天人合一与儒教宪政的哲学基础》,《学术研究》,2013年第3期,第31页。 ,其代表就是现在颇有些走红的大陆新儒家。其五,政治哲学的范式。这个视角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概念、命题及理论体系分析为媒介,既强调分析具有民族特色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建构,呈现其理论建构的阶段性特点及最终成果等,也注重对传统政治哲学所体现的民族共性的发掘,分析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及转型的经验过程,其代表性观点集中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张师伟等。(3) 参见张师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进程》,《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67-74页。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和撰述体例的选择与调整
随后的一个多月,艾莉和男人就像两只难舍难分的蛤蚧。也许肉欲终于上升为爱情,也许爱情只为未来的肉欲存在,艾莉想不明白。想不明白,便不再想,每天有一位高大英俊的中年男人陪她吃饭喝酒聊天做爱,艾莉很满足了。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旨趣和目的上,存在着启蒙与经世的并存与竞争,两者根源于同样的历史传统及时代条件,均谋求以学术影响政治实践。现代社会科学理论首先在西方建构起来,并在西学东渐中传播到中国,其中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概念和知识的传播都曾以日本为中介。晚清末年,中国青年学生大量赴日本留学,既在接受日译现代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启蒙,又因自我启蒙而开启了为救亡而学习和移植日译现代社会科学的时代潮流,“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侵入我国”(2) 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化的政治知识体系,就孕育和开始于这个时代潮流中,并伴随着日译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及法学等学科概念在中国社会的流行,而开始了它的百年学科历史。(3) 参见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回眸与学术省思——本土政治理论的概念检视与话语梳理》,第15-16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从一开始就承担起了批评和批判旧政治、旧文化和旧伦理的时代使命,发挥了启蒙与救亡的思想作用;另外一些研究者站在维护中国政治传统立场上,维护传统的政治价值、政治权威与政治秩序,所谓“至于纲常礼制、国俗民风,西国远逊中华者,不得见异思迁,致滋流弊”,“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此则鄙见断断不能苟同者”。(1) 苏舆:《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52、167页。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流突出了实践取向,在具体的价值倾向上又分为启蒙和经世两类。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有了一种知识论取向的零星研究,这种研究虽然在学术上有重要影响,但并没有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实践论主流取向。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民国时期体现了明显的知识论取向,在著作的篇章结构上“体现出作者努力遵照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勾勒中国历代思想变迁的意图”(2) 朱政惠:《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贡献论》,《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1期,第32-33页。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绝大多数知识论取向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价值倾向上更接近于启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刘泽华先生开创的王权主义学派,就“是围绕着对王权主义的历史批判而展开的”(3) 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第28页。 ,而这方面的典范之作就是刘泽华先生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4) 参见杨阳:《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百年典范——评刘泽华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第37页。 。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经世诉求,主要体现在研究旨趣、研究方法及研究结果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经世诉求,在观点上集中地表现为主张复兴儒家政治哲学,不仅提倡以儒家政治哲学来指导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更主张以儒家政治哲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1) 参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424-429页。 ;在研究方法上则主要使用了抽象分析概念的哲学方法和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进行概念格义与解释比附的比较分析方法,试图在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中,找到与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相同或相似的关键概念与核心理论(2) 参见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回眸与学术省思——本土政治理论的概念检视与话语梳理》,第15页。 ;在研究范式上则表现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经学范式,该范式强调中国传统儒学中存在一套完整并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哲学,它既适用于传统时代,也适用于现代,认为“五经乃是中国政治思想之开端,确定了中国政治思想之基本词汇、话语与范式”,“揭示、展示乃至于实现中国源远流长之固有政治思想永恒性和普遍性”。(3) 姚中秋:《重建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第21页。 有的学者试图全面复兴儒家政治哲学,不仅注重从儒家经学著作中寻找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纲领性概念,西方现代社会流行并成为现代政治基础的纲领性概念,如民主、自由、法治及公民等在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物,而且也注重从儒家经学著作中寻找现代政治仍然需要遵循的普遍政治原理,比如从《周易》中寻找“中国式启蒙观”。(4) 参见姚中秋:《中国式启蒙观:〈周易〉“蒙”卦义疏》,《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3期,第40-65页。 有的学者站在现代公民宗教的立场上来研究传统儒学,并以公民宗教的视角来分析和认识儒学,将儒学当作一种普遍的公民宗教,既是希望儒学在现代中国发挥公民宗教的作用,也坚持认为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就发挥着公民宗教作用,从而希望更进一步深入发掘作为公民宗教的儒学内容,并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公民身份的普遍宗教基础。(5) 参见陈明:《公民宗教:儒教之历史解读与现实展开的新视野》,《中国儒学》(第九辑),2014年第00期,第311-335页。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经世诉求,当然不局限于大陆新儒学复兴儒家政治哲学的经学范式,还包含其他一些诸如新法家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经世诉求,新法家的研究方法与新儒家并无不同,主要是对概念进行抽象分析,它在研究结论上,混淆了先秦法家的法治概念和法治理论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概念和法治理论。(1) 参见喻中:《法家第三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思想史解释》,《法学论坛》,2015年第1期,第13-19页。 经世诉求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明显地走向了政治复古,但是他们对中国之古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古”只是“托古”之“古”,因此所谓“古”不过是一种用“古”包裹着的“现代”。他们作为认识主体,用自己的“现代性认知替代传统认知,把自己的观点,甚至是当下流行的现代理念或观念,投射到古人身上”,形成了研究者不应有的“主观投射过度”,其结果就是在概念体系的理解和理论的解释上以己度人,将自己的概念与理论强塞给了古人。(2) 葛荃:《立场、方法与禁忌: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研究断想》,《政治思想史》,2016年第3期,第8-9页。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多样价值倾向及跨学科特点,在根本上决定了她在研究方法和撰述体例上的多元特征。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学再次进入中国并深度丰富了中国政治学的概念体系,拓展了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内容的现实,也在研究方法和撰述体例上影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比如西方学者关于政治文化方面的概念与理论就对刘泽华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产生了研究方法与撰述体例的影响。(4) 参见杨阳:《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百年典范——评刘泽华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第32-38页。 西方学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方法与撰述体例,如剑桥学派西方政治思想史著作,就直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撰述体例。(1) 参见张师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第7-8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撰述体例,虽然在改革开放40年来也有相当大的变化,但其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主流的撰述体例却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即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大量研究者都在应用晚清民国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流方法和撰述体例,其中尤其以中西之间政治概念的格义解释方法和以西方为参照系来解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方法最为稳固,撰述体例上则大多采取流行的列传体。中西政治概念的格义解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孕育时期就开始流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各个阶段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研究者的不同价值倾向并不妨碍他们使用这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抓住一些西方政治学中有公共舆论价值的核心概念,以政治常识的理解水平为基础,以西释中地进行格义解释(2) 参见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回眸与学术省思——本土政治理论的概念检视与话语梳理》,《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第15页。 ,如把孟子“民贵君轻”比附民主思想(3) 参见汪荣祖:《中国政治思想史·增订版〈弁言〉》,载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增订版《弁言》,第3页。 ,陈天华将黄宗羲比附为卢梭那样的民约论者。(4) 参见陈天华:《狮子吼》,载《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7-128页。
本组研究对象为2016年7月~2017年6月期间在血站无偿献血的2063名献血者,根据《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以上献血者的身体条件与之符合,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以及血液病患者均不在研究之列。将2017年上半年无偿献血的1063名无偿献血者作为观察组。观察组献血者男女比例为545/518,最高龄55岁,最低龄20岁,平均年龄(32.4±4.1)岁。将2016年下半年无偿献血的1000名献血者作为对照组。对照组献血者男女比例为511/489,年龄22~54岁,平均年龄(31.5±4.7)岁。两组无偿献血者的基本资料对照相仿(P>0.05),本研究具有可行性。
三、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批判启蒙和经世济用的并存与竞争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恢复以来,格义解释和比附理解仍然为多数研究者所使用。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是在现代政治知识不充分和不普及的情况下进行的。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在中国实现西式现代政治而开始以西方公共舆论中的核心政治概念为依托,一方面批判中国旧政治文化中的君主专制主义成分;另一方面又从中寻找新政治在传统中的同类项,开始了格义理解和比附解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运用进行政治概念的格义理解与理论的比附解释,认为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原法》“诸篇明显地表现出民主主义思想”(5)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155页。 。虽然格义与比附的方法相同,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解释一般都立足于一套完整的历史哲学。这套历史哲学认为,因为民主主义启蒙思想普遍地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而中国在相应阶段上也必然有自己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所以黄宗羲等的批判性思想就被理解和解释为民主主义启蒙思想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恢复之初,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历史哲学还完整地保留着,政治学范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概念理解与理论解释上也都以五种社会形态为基本框架与线索,以对政治思想家及其思想进行阶级分析为主。(1) 参见徐大同、陈哲夫、谢庆奎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第2页。 每个社会形态都对应着一定的主导性进步阶级与反动阶级,而每个进步阶级或反动阶级都有自己的思想家和思想,政治不过就是各个阶级围绕国家政权展开的斗争,每个阶级的思想家都试图为实现和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本阶级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权而进行思考。因为每个政治思想家都隶属于一定的历史阶级,为本阶级代言,在历史上扮演进步或落后的政治角色,所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阶级分析就主要是给思想家戴上合适的阶级帽子。同时代,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格义与比附则主要立足于寻找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相同点,或者力求彼此间的直接贯通,有学者强调黄宗羲的思想“是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2) 李存山:《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兼评所谓“民本的极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页。 ,有学者则认为黄宗羲的思想在传统民本到现代民主的过程中发挥了“衔接古今、汇通中西的枢纽作用”(3) 冯天瑜:《文明近代进路的共通性与特异性——从〈明夷待访录〉“新民本”诉求说开去》,《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8页。 ,或者将学习西方的某些部分变相地转变为继承传统的某些部分,有学者认为,中国虽然没有民主的制度但却有民主的思想(4) 参见张岱年:《黄梨洲与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在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报告》,《浙江学刊》,1987年第1期,第4页。 ,或者试图以此证明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现代政治思想资源,有学者试图用格义和比附从中国传统中找出一个自己的现代政治思想谱系,并呼吁为此要展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古典政治思想史范式”(5) 姚中秋:《重建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第14页。 。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不同价值倾向的研究者,自然都有其独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们站在不同价值立场上,运用不同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自然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形成的各种影响要素中,价值倾向具有方向引领的根本作用。这是因为价值倾向不仅决定了研究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根本态度是批判和扬弃,还是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决定了研究者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等来进行理解、解释和建构等,并且还决定了研究者将获得什么样的根本看法,更决定了他们将如何看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与任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曾长期立足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激烈批评,并以阶级分析和社会形态分析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封建主义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批判。(2) 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1—5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其中第1、2、3卷均初版于1957年,第4卷(上)初版于1959年,第4卷(下)初版于1960年,第5卷初版于1956年。 20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所进行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立足于阶级分析和历史批判的价值立场,以批判封建旧政治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学为根本目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为分析视角,进行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概念梳理和理论解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与此同时,中国历史学研究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走出教条主义框架下历史研究的僵局,在完整陈述历史的追求之下,重启了历史学领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它的理论目的是恢复历史内容的丰富性和完整性,而实践目的则是要在文化上继续肃清封建遗毒,巩固民主与科学的现代价值。历史学认识方法的使用及历史认识论的自觉反省,体现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就形成了历史学的研究范式。有的研究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自觉拥抱传统政治,在价值立场上自觉地皈依传统儒家。这导致他们刚从一种教条主义僵化解释中走出来,就又进入了另一种教条主义解释中,其理论目的就是要论证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和教化之道比西方具有更高普遍性(1) 参见姚中秋:《可普遍的中国信仰—教化之道——基于〈尚书〉之〈尧典〉〈舜典〉的解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1期,第69页。 ,他们的实践目的就是要以儒家经学来指导当代中国政治实践。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很早就在研究方法上反思和批判了概念格义与比附解释,并形成了政治学视角和历史学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其在民国时期的最主要代表是萧公权。萧公权以研究西方现代政治多元论获得了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公开出版后广受好评,这充分展现了他对西方现代政治概念与理论的准确把握和深刻了解,并为他运用政治学视角研究中国政治思想提供了完整准确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他更以历史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政治思想史资料,关注政治思想家思考和解决的实际问题,依托历史背景进行思想家概念、命题的理解与理论的内容解释,客观呈现政治思想的历史内容,避免并批判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比附性解释。刘泽华先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坚持了历史学的研究传统,创新了历史学研究范式,开创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王权主义学派”。虽然如此,但刘先生并没有从萧著中继承什么,两者在历史方法应用中的相同属于殊途同归。刘泽华先生在进入历史学研究领域之前,曾从事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的学习和讲授(1) 参见刘泽华:《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第66-67页。 ,从而具备了比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基础,比较注重历史内容的完整性。这种对中国历史内容完整性的关注,既使刘先生注意到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又使刘先生倾向于将中国政治思想史放到中国历史的整体中进行理解和解释,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在矛盾中陈述历史”(2) 李振宏:《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王权主义学派方法论思想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66-67页。 ,还使得刘先生能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关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有学者认为,刘先生继承了侯外庐先生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传统(3) 参见陈寒鸣:《刘泽华与“刘泽华学派”》,《衡水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84-85页。 。刘泽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的研究,南开大学注重历史资料分析和历史事实呈现的传统治史方法,使得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得以另辟蹊径。他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历史学方法,不仅特别关注完整准确地解读史料和呈现政治思想的历史事实(4) 参见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再版弁言》,载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再版弁言》,第2页。 ,而且还注重从历史过程中发现和分析大批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原始政治概念、命题与判断等(1) 参见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84-87页。 ,还细致剖析了概念、命题与判断间的思想联系,划分了概念的层级,从中识别出了纲领性概念与核心命题(2) 参见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第263-279页。 ,呈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命题的理论结构,提出了阴阳组合结构的判断(3) 参见刘泽华:《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33-35页。 ,更在进行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之后,从中国历史内容整体性出发,完整呈现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等背景,深入分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以贯之的君主专制主题,得出了一个总体性解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王权主义结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复古经世诉求,立足于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社会大变革和大转型,他们之所以强调复古经世,就是因为西方来的概念和理论,特别是激进主义等造成了中国政治现代性发展的中断,而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继续发展则需要以“古”来经世,因为中国之“古”具有远超西方的普遍性。(3) 参见姚中秋:《可普遍的中国信仰—教化之道——基于〈尚书〉之〈尧典〉〈舜典〉的解读》,第69页。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启蒙诉求,同样也立足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和大转型,但在中国现代性政治发展所以遭遇挫折经历及现实困顿的归因上,却迥然有异于复古经世派,从而强调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发展在根本上就是一个从过去的“封建主义中走出来”(4)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自序》,第2页。 。既然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发展就是从过去的历史定势中走出来,那么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旨趣及目的就是科学地发现过去的历史定势。价值上的启蒙诉求在这里就顺势变成了一个知识论上的科学发现。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科学上的认识目的是发现各个历史时代的政治概念、命题、判断、理论及思维等,所以它在研究的方法上就必须要兼顾政治学的理论观点和历史学的分析方法。这种兼顾开创于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5)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凡例。 ,具有相当的科学认识论指导价值。如果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罔顾政治学的理论观点,研究者就不能准确理解各个历史时代的政治概念,并客观呈现其完整的政治理论结构和特定的政治思维方式;如果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忽略了历史学的分析方法,研究者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将思想史变成了博物架或博物馆。(1) 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00-301页。 萧公权先生所开创的政治学视角与历史学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虽然追求的是科学认识,但其在结果上却不能不产生启蒙的结果。
式中:M是与开关d在同一个环网中的所有开关集合。小部分粒子按规则一进行更新,大部分粒子按规则二进行更新,保证粒子多样性的同时使其跳离局部最优确保粒子快速地收敛,提高算法搜索效率。
祝庆英版:“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现在给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都通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改革开放以来,刘泽华先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既重视了政治学的理论视角,将政治学理论上的新概念引入研究工作,不断开拓和丰富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理论视角,也重视了历史学分析方法的充分应用,以历史认识论的自觉来进行思想史史料的处理和历史社会学分析。他不仅否定了研究对象的超历史普遍性,而且还呈现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联系的复杂整体性,并且还通过对话题、问题及命题等的研究,呈现了中国政治思想在理论结构上的阴阳组合的复杂性(2) 参见刘泽华:《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第33-35页。 及在宗旨上的君主专制主义特质。(3) 参见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0-121页。 刘泽华先生认为,从过去的“封建主义”中走出来,就是从君主专制主义的“定势”中走出来,否则这个“相当稳定”的“定势”就会“死的拖住活的”,成为“前进的绊脚索”,必须要用“极大的力量进行清理”。(4)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三卷),《弁言》,第1页。 这个结论在价值上显然具有十分明显的启蒙诉求。有的学者将刘泽华先生的史学研究归结为“启蒙史学”,强调刘泽华先生“作为启蒙史学的杰出代表”,“在他的专业研究中自始至终贯彻了启蒙思想和观念”,他关于“王权主义论述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仍是启蒙”。(5) 王学典、郭震旦:《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32-133页。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化知识的地位得到了恢复,但在怎样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什么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问题上,仍然缺乏知识论取向的科学研究。绝大多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都还带有“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不仅受到了学术思想界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诸多讨论影响(1) 参见张师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演绎》,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 ,而且也普遍突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为政治现实服务的宗旨,启蒙和经世只不过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为政治现实服务的两种不同方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启蒙方式,较多地体现了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以思想事实呈现的方式,突出了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及思维的非现代性整体特征,在知识论的角度上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经世方式,继承和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较多地采用了抽象分析的方法,突出强调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特别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普遍超越性,在民族自信心的提升上颇有影响力。两者的并存和竞争由来已久,并将长期存在,但在近年来两者的对比中,情胜于理的经世方式在舆论上处于上风。知识论取向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方面立足于呈现作为历史事实的政治知识,但又难免在研究中贯穿启蒙的情结,而只有避免了体现启蒙情结的诸多“假言判断”(2) 参见雷戈:《从简单本质到复杂本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开放出的思想境域》,《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第100-101页。 ,才能呈现政治思想历史事实的客观样态;另一方面立足于将历史上的政治知识,融入中国现代政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成熟(3) 参见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定位及学术使命——一种基于知识论视角的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30-131页。 。
作者简介: 张师伟,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15BZZ01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项目编号:16ZDA10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刘学斌)
标签: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论文; 范式争鸣论文; 方法反思论文;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