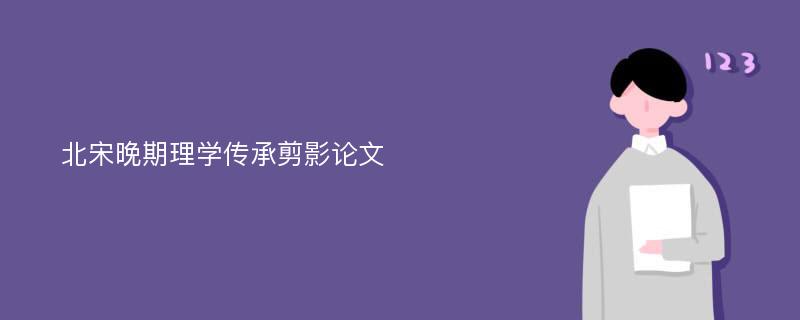
道南文化研究
【主持人语】 “道南文化”狭义上当是指我们所说“道南之学”或“道南学派”之文化传承。“道南”指程颢在送别杨时之际的临别语,《河南程氏外书》有言:“明道在颖昌,先生寻医,调官京师,因往颖昌从学。明道甚喜,每言曰:‘杨君最会得容易。’及归,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注]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8-429页。 杨时是程门四大弟子之一,其在学成南归后“独门沉浸经书,推广师说,穷探力索,务极其趣,含蓄广大而不敢自肆”[注] 朱衡:《道南源委》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被誉为“得伊洛之传,为闽中道学正宗”[注] 朱衡:《道南源委》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页。 。因此其创立的学派也被称为“道南学派”。“道南学派”自杨时创立以来,一传至罗从彦,二传至李侗,三传至朱熹,由朱子集其大成,创立了闽学并将其发扬光大,被称为道南学派正传。道南学派另有一著名人物,即与谢良佐、杨时同为程门高第的游酢。伊川初见游酢时赞言:“其资可与适道。”[注] 徐公喜主编,李清馥撰,徐公喜、管正平、周明华点校:《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而后游酢成为伊川喜爱的弟子,而杨时则成为明道喜爱的弟子。游酢作为程门高第,平日里不仅与程门诸弟子多交好,亦与胡安国等人交往颇深,胡安国说:“吾于谢、游、杨三公皆义兼师友,实尊信之。”[注] 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页。 言辞中可看出他与游酢亦师亦友的深厚感情。但游酢“在程门鼎足谢、杨,遗书独不传,其弟子亦不振”[注]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廌山学案序录》卷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93页。 ,故其在理学史上影响较小。在《儒林宗派》中游酢仅有曾开一名弟子,在《宋元学案》中也仅记载四名门人:吕本中、曾开、陈侁、江琦。另外,考察程门弟子,多半是南方人,这为伊洛之学的南传和道南学派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文化背景。因此,“道南文化”在狭义上指伊洛之学在闽传衍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明确师承特点的“道南学派”及思想文化。
在朱子集理学之大成创立“闽学”以来,道南学派大体已经转变成了以闽学为主体的新理学。与此同时,陆九渊创立心学流派,其与朱子的“鹅湖之会”就“为学之方”,包括“道问学”“尊德性”等问题展开论辩,促进了理学与心学的交融发展。陆九渊在理学和经学的发展史上另辟蹊径,以心论道,提出“心即理”“六经皆我注脚”,从心学的角度改造了以往的理学和经学,与朱学形成了对照,促使经学和理学思想向心学方向发展转变,并对王阳明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理学与心学的联系并不为陆九渊首次涉及,二者的联系早在二程门人中就有显示。王蘋字信伯,福清人,程颐之门人,因王蘋较程门其他弟子为后进,早年曾事杨时,因此也有王蘋得之于杨时的说法。全祖望评价王蘋时说:“颇起象山之萌芽”“象山之学……兼出于信伯。”[注]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震泽学案序录》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47页。 他认为陆九渊的心学受到了王蘋的影响,其后心学之集大成者王阳明也对王蘋较为推崇。王蘋曾说:“人心广大无垠,万善皆备,盛徳大业由此而成,故欲传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扩充是心焉尔。”[注] 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页。第128页。 他认为人心广大,具备世间的各种善,只要能将此等本善之心扩充开来,便可完成盛德大业,传万世之道。王蘋此等重视心之作用的观点与陆九渊心学的主要观点较为相似,而王蘋大陆九渊50多岁,陆九渊受其影响在时间上也是允许的。除王信伯外,二程弟子中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尹焞等都有论心之言论,虽然他们仍以道体、性体为重,但因此酝酿而生的学术环境,无疑对象山之学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噪声污染物监测点布置:在北、西南及西面厂界共布设6个厂界噪声监测点,在民居窗户外1米布设1个环境噪声监测点,在西南厂界外布设1个噪声衰减断面。监测频次为每天昼间和夜间各监测1次,连续监测2天。
王蘋有弟子施庭先,后传至林光朝。林光朝字谦之,世称“艾轩先生”,其后学林希逸曰:“在昔隆、乾間,士之師道立,浙有東萊呂氏,建有晦庵朱氏,湘有南軒張氏,江西有象山陸氏,莆有艾軒林氏,皆以道師授,并世而立名者也。”[注]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81页。 从林希逸之言可见当时理学学派分立且各有代表:浙江一带有吕祖谦所创“东莱学派”、福建有朱熹创立的“闽学”、湖南有张栻集大成的“湖湘学派”、江西一带有陆九渊创立的“象山学派”。虽各地学派人物、思想各不相同,实则都是义理之学的传播人。全祖望云:“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晦翁、南轩、东莱皆其所自出。”[注]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龟山学案序录》卷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44页。 吕祖谦与朱熹同为胡宪弟子,胡宪承其叔父胡安国之学,胡安国与二程门人相交密切。杨时之道南学派除经罗从彦、李侗传至朱子外,还经胡宏传至张栻,因此张栻为杨时之再传弟子、二程之三传弟子。而陆九渊多少受到程颢之学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南宋晚期,伊洛之学已经在包括闽、浙、赣、湘等南方多地传播开来,此时的“道南文化”不仅局限于游酢、杨时一脉的“道南学派”,从广义上讲是指伊洛之学在闽、浙、赣、湘等地区传播以来形成的各学派及由此促成的文化盛况。
本期“道南文化研究”专栏,选载三篇论文,均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伊洛之学在宋明时期的广泛影响。王建生的《北宋晚期理学传承剪影》,主要依托北宋晚期陈瓘写给其侄孙陈渊的书信——《责沈文贻知默侄》,显示了范祖禹作为陈瓘了解程颢的点拨者、中转者,给予了程颢极大的肯定;陈瓘与二程弟子杨时在元祐党禁的高压态势下对修道门径等讨论,显示出了程氏之学的生命力;文中勾勒出了由程颢→杨时→陈渊的谱系,并指出程颐直承孔孟之道,显示出程氏门人构筑道统、梳理谱系的努力;陈瓘的修养工夫论中言“物格而不二”,显示出他的思想受到程颢深刻的影响。周接兵的《陆九渊君子人格思想述论》,系统梳理、阐发了陆九渊的君子思想,认为陆九渊的君子人格思想从本体上借助了“心即理”的心学理论框架,强调了君子应顺天理、重本心的人格架构;从心性上说,君子应闲邪存诚,至于正道,将心学本体论融入到“诚”中;从工夫上说,应当去除各种逐物的妄念,减少各种繁杂的知识建构,并正确处理德才关系;从价值和政治上看,君子志于义,心系国与民,为官应当以克己奉公、抑恶扬善为政治理想。王佳、蔡方鹿的《从气之动静看王阳明的善恶观》分析了王阳明心学中恶的思想来源,认为王阳明延续了北宋以来以气解释恶之来源的传统路径,这与伊洛之学的人性论有关。在王阳明看来,气之动静是产生恶的根源,但这一说法与其“气即是性”的观点产生了一定冲突。因此文章结合了牟宗三、陈来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提出应当从体用关系和区分气之善恶两方面理解:性之本为静,为善,性又须通过气显现出来;气之动有善有恶,应循性之本原为善,去后天气质习染之恶。这三篇论文从广义上讲,是对道南文化源流的阐述,细致深入地论述了各自所探讨的问题而值得一读。
(四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朱子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 蔡方鹿)
北宋晚期理学传承剪影
王建生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责沈文贻知默侄》是陈瓘向其侄孙陈渊传授治学心得的一封书信。作为北宋晚期家族长幼间学术交流的文献,它在两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神宗朝时二程之学在社会上的影响相当有限,程氏亲友圈不约而同地对程颢生平事业予以总结概括。杨时与陈渊间的私相传授,体现出官方高压态势下程氏之学的生命力。陈瓘作为程门圈子外的士大夫,他对程氏之学的认知、评定、推服,既显示出程氏之学发展中的向上一路,也体现了陈瓘对未来思想界的预见之明——程氏之学方兴未艾。
[关键词] 北宋晚期;理学;陈瓘 ;陈渊
陈瓘南剑州沙县人,青少年时期在家乡读书,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23岁时中进士;是时程颢48岁,任开封府属县扶沟知县[2]227。《责沈文》中明确交待:元丰五年(1085)夏,陈瓘为礼部贡院点检官,与范祖禹同舍;恰在本年六月,程颢以疾终于汝州[2]276。陈瓘与程颢之间并无政治、学术思想上的交集,故从未听闻程伯淳为何许人,遑论知悉他的学说、理念!在陈瓘的追忆式的自述中,范祖禹成为他接触程颢及其学派的点拨者、中转者。范祖禹自熙宁六年(1073)始,随司马光在洛阳书局修书(即后来的《资治通鉴》),在洛阳长达12年[3]。而在熙宁五年(1072)至熙宁十年(1077)间,程颢以监洛河竹木务的身份居住洛阳[2]189-201。司马光、范祖禹、程颢、邵雍等居洛名士的交游唱和、诗书往还等,铸就了宋神宗变法时期西京洛阳文化史上的再度辉煌。也正在洛阳修史时期,范祖禹对程颢、程颐的学术旨趣、人格性情有更深入、更透彻的了解。所以,当论及颜回在儒学中的地位及人格价值时,范祖禹很自然地将程颢比附为颜子,这也是对程颢极具历史定位性的概括。
一
予元丰乙丑夏为礼部贡院点检官,适与校书郎范公醇夫同舍。公尝论颜子之不迁不贰,惟伯淳有之。予问公曰:“伯淳谁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谢曰:“生长东南,实未知也。”时予年二十有九矣。
适越而北辕,越不可至;徙越人而置于齐里,则越语可易而为齐。然则气质一定,不能易其习者,非以其不学欤?气质之用狭,道学之力大,习其所自习者未尝察也。天气而地质,无物不然,人藐乎其间,亦一物耳,物与物奚以相远?或哲或愚,不系其习乎?思诚之道,莫先于学;务学之要,在于求师。颜子之不迁不贰得于孔子,希颜之人将孰师焉?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夫叶公有知人之明,有谋国之忠,爱贤而得民,慎微而忧远。其事皆有可指,其遗语之记于《缁衣》者亦可观焉。楚国之贤,谁出其右?子路非慢贤者也。鲁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则于其问也,何足对哉?陈良楚产也,而能使北方之学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为豪杰之士,为其能悦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则虽贤如子高,亦孔门之所不对也,为士而稽古者可不鉴哉!
5.福娃妮妮是人和雨燕风筝的结合体,头部造型来自于雨燕的形象和北京传统沙燕风筝的装饰纹饰。中国风筝年代久远,它是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天使,除了娱乐,还成功的用于军事中。中国风筝是世界文化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很久以前,古代的科学家就已经懂得利用风筝进行科学实验,探索人类和自然的奥秘。[3]北京传统的沙燕风筝在造型上夸张了燕子展翅的动态,在形象上丰富了眼睛和爪子的形状,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装饰性。
《责沈文》是陈瓘向其侄孙陈渊传授治学心得的书信,现摘录于下:
据陈瓘所言,崇宁初因侄孙陈渊就学于杨时之门,他才与杨时建立直接的学术往来。清人张夏编《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崇宁三年(1104)的事目中,列“答陈莹中论华严书”,结末又说:“又和了斋自警六诗,并书寄之,陈公读之,深喜所言中其病。乃复书称以先生,先生更答书逊谢。”[2]152杨时鞭辟入里地论述儒家君子之道迥异于佛教宏旨,以《孟子》辟《华严》,故陈瓘在《责沈文》中云“内讼改过,赖其一言”,所指正是陈、杨二人关于修道门径的讨论。
《责沈文贻知默侄》(以下简称《责沈文》)作为北宋晚期家族长幼间学术交流的文献,其内容、价值绝不囿于家族一隅,在两宋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可能为流量计内进入脏污,导致浮子抖动或卡顿,此时需对流量计进行清洗。对于金属材质的浮子,可按顺序将水、无水乙醇、丙酮、乙醚注入流量计内将赃物洗净,对于塑料材质浮子,则可用洗洁精、水、无水乙醚进行清洗。待管内溶剂干燥后再装回原来位置。
医保办成立投诉管理小组,日常监督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对实施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将进入下一轮PDCA循环中予以解决。定期召开质量管理会议,评估执行效果,将整改效果好的措施予以提炼,使其制度化,规范化。对薄弱环节和新发投诉执行不到位的措施,在下一阶段的整改措施进行补充和完善,形成PDCA循环的依据和动力,并不断持续改进。
据程颐所撰《明道先生行状》,程颢卒于元丰八年(1085)六月十五日[4]637。范祖禹向陈瓘推介程颢时,程颢已经去世。范祖禹将程颢比为颜子,可谓是对程颢儒学史地位的盖棺论定。巧合的是,元丰八年(1085)八月八日,也就是程颢去世后50余天后,程颐撰写了《明道先生行状》,其中有这么几句高度概括的语句:“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此理也。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4]638这段文字被反复引用,旨在证明程颢直承孟子、开启儒学的新时代。在这点上,范祖禹与程颐声气相应,从中可看出程颢亲友圈对其生平事业予以总括的共同努力。
二
陈瓘在《责沈文》中,用援古证今的叙事手法,预见学术思想界的未来走向——程氏之学方兴未艾。叶公沈诸梁不识孔子,自己却不闻程颢,皆非贤者所为,宜为后世有识者深诫。至写作此文时,即政和三年(1113)八月,陈瓘57岁,因《尊尧集》被贬台州,老病相侵,勉励侄孙陈渊一心向学,持守学脉正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主体性意旨之外,却包含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自程颢→杨时的儒学谱系。这一谱系并非陈瓘有意构筑,他本意是要用来说明文末的主旨:期望陈渊能学有所成,在程氏之学的体系中终有所立。不意这一谱系却明显地附着于文章的浅表层,这样明显的附着折射出多维的思想史光棱。
自是以来,常以寡陋自愧。得其传者,如杨中立先生,亦未之识也。崇宁之初,兄孙渐就学其门,时予在合浦,始获通问。予之内讼改过,赖其一言。渐于是时,亦以所闻警予之缪。予始忽其言,久而后知其为药石也。今渐来天台,考其学益进,闻其言益可喜。陶染薫铸,有自来矣。举修步于南溟,观洪澜于北壑,此可远之基也。始之不谋,何以得此?古之善学者,心远而莫御,然后气融而无间;物格而不二,然后养熟而道凝。山上有木,其进也渐,合抱之干,岂一朝一夕之所可俟哉!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于彼乎?物之终始,可不严哉!始识而终成,同乎一默,非言语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祸,尚未诛殛,戴恩自幸,不知岁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简编笔砚,殆将捐弃。今于渐之行,不能忘言,作《责沈》以贻之,喜渐之能谋其始,而笃之使有成也。政和三年八月九日。[1]111
若以崇宁三年(1104)为时间点,是时杨时任荆州教授,陈瓘谪居廉州合浦,曾作《了斋记》[2]40-44、446。是时陈瓘48岁,上距初闻程颢之名已过去20年;崇宁三年(1104),对元祐党人及元符末年上书人的党禁,才刚刚开始。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追毁程颐出身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崇宁三年(1104)六月戊午,诏重定元祐、元符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309人,刻石朝堂,余并出籍,自今毋得复弹奏[7]367、369。无论是屏居洛阳龙门止四方学者来问学的程颐,还是身在荆州的杨时、陈渊师徒,以及编管廉州的陈瓘,都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责沈文》作为亲友间私人性的寄语,却传达出官方高压态势下程氏之学的生命力。杨时乃程门高弟,他在北宋晚期对程氏之学的坚守,已充分体现独立不羁、不趋时、不冒进的品格;陈瓘作为程门圈子外的士大夫,他对程氏之学的认知、评定,更显示他的洞察力以及矢志不渝的笃行精神。
陈瓘行将而立之年,却不知当今儒学之巨擘,深感惭愧。他并未停留在惭愧、感叹中,而是用切实的行动来弥补视界的短缺,用恶补的方式来“立”起一己之学,“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带然后读之”[5]837。在《责沈文》中,陈瓘还介绍了他倾心程氏之学的其他努力,比如与程门高第杨时的交往。
陈瓘并非理学中人,更非杨时之门人,但南宋以降便有淆乱事实者。吕本中为杨时所作《行状》中,说“邹、陈以师礼事龟山,胡公实传其学”[8]卷十,邹指邹浩,陈指陈瓘,胡公指胡安国,这种有关陈瓘师事的说法很快就被澄清,胡安国、胡宏等人有详细的辩白,即《龟山志铭辩》[8]卷十。直至南宋中后期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仍采用了这一说法:“至大观以后,(杨)时名望益重,陈瓘、邹浩皆以师礼事时,而胡安国诸人实传其学。”[9]200从《责沈文 》可看出,陈瓘乃私淑洛学者。全祖望的概述很有道理,称“私淑洛学而未纯者,陈了斋、邹道乡也”[10]1205,而纵览陈瓘与杨时之书信,或曰杨时乃陈瓘敬重之学侣较妥。
陈瓘私淑洛学,并未与程颢有直接的往来。他对程颢的尊崇,源于君子三省其身的自律以及对程氏学说的折服,故以为程颢是当代儒学贤者,又可谓是儒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由此勾勒由程颢→杨时→陈渊的谱系。无独有偶,比陈瓘《责沈文》早一年,即政和二年(1112),程端中在程颐文集的序中说道:“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圣人虑后世不足以知之,载之六经,丁宁教告,纤悉具备;宜若人见而知之,然自秦汉以下,泯没无传。惟伊川先生以出类之才,独立乎百世之后,天下学者士大夫翕然宗师之。圣人之道蔽曀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复明。”[4]后序指出程颐直承孔孟之道,秦汉以降,扬雄、韩愈不足挂齿。两个事例放在一起,可看出北宋晚期程氏门人圈构筑道统、梳理谱系的努力,而明乎是时之思想文化语境,更能理解新思想的生命力。
陈瓘、程端中各表一端的谱系,不自觉地引出理学史上的千年公案,程颢、程颐学说思想之分别,牟宗三等认为大程的心体“即存有又活动”,而小程的性体则“只存有不活动”[11]。他们的各表一端,恰恰反映了程氏之学在北宋晚期党禁中传承的某些特点:纷乱无绪、各自为政。也正因为散在四方的无绪状态,为其蓄势待发提供了良好积淀。在《责沈文》中,行将而立之年的陈瓘因没听说过程颢深以为愧,而二程中的小程似乎并未进入他的视野,多少有点不合陈瓘本人的学行。
深入生活,深入自然,这是我们细致认真地观察,一花一草,一山一水,一江一河,一树一林等特征,我们在俯仰向背之间,或高或低,或远或近,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了它的特征。全面地把握了山山水水的地貌特点,以及此时此地自然的独特性。只有对其特征的全面了解和把握,作画才真正能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
《责沈文》中“古之善学者,心远而莫御,然后气融而无间;物格而不二,然后养熟而道凝”可视为陈瓘学术思想的纲领,意在将平生体悟所得金针度人。要之,此论融合了《孟子》《大学》之精义。陈瓘箴言从根本上来讲属于修身养性的实践论,构成其内在理路的四种要素:心、气、物、道,在原始儒家孔、孟以及陈瓘之前的宋儒周敦颐、张载、二程等都有阐述。《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向公孙丑辨析过心、志、气三者关系,并形象地概述了“浩然之气”的特征、功能:“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12]62就目力所见,程颢曾在《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专门论述心性问题:“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4]460程颐也在《颜子所好何学论》说过:“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4]577在修养论方面,二程皆主张从心开始,起点相同,门径略异:大程“心”为本体,观照万物,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其思想导源于《孟子》养气论;小程则遵循《大学》正心诚意的门径。陈瓘还曾引述过张载论“心”之见:“六经之道,心物混一,则象亦心也。心自心,物自物,则象岂心乎?心物合则诚明一,诚明一则天地良知不见乎小大之别。此横渠先生之说,而学者之所宜信也。”[1]103
留给ofo的时间已经不多。11月14日,久未露面的戴威在已经很久没有举行的ofo公司大会上表示:除了破产,其他都有可能。
陈瓘这段学术思想的剖白,特异之处就在于明心→养气→至道中,横插了“物格而不二”。《大学》中八条目的顺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于“物格”的解释,朱熹说的比较透彻:“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13]4“物格而不二”也就是大程所谓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综合陈瓘这段文字的内涵及渊源,可推断他的思想更多地受《孟子》、程颢的影响;《大学》“物格”论亦有影响的痕迹,所插入的“物格而不二”,无意中打破了《大学》八条目的井然有序。说到底,“物格”在其思想体系中,如同“气融”“道凝”一样,只是“心远”结果的表现之一,同属于第二层级的范畴概念。因此,我们可以说,陈瓘的思想与程颢的心体论是一脉相承的。
三
陈瓘煞费苦心向侄孙陈渊传授的心经,在陈渊那里是否有回应或思想的印痕?陈渊曾在《与胡少汲尚书书》中满怀深情地追述问学经历:“渊少时学于叔祖了斋,其后二十五六岁,始获承教于龟山杨先生,因授室焉。凡出入于两公之门者,盖莫如渊之久也。”[14]卷十八在学术思想上,陈渊对陈瓘、杨时可谓兼收并取。他在《答晦之叔书》中曾说:“故惟止而求定者,乃期于虑而得也。至于虑而得,则洒扫应对之际,莫非妙用,而天下国家盖不足为矣,而况于一身乎!”[14]卷十五所谓的“定”“得”,主要源自《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存诚斋铭并序》中的一段文字直接表明陈渊学术渊源:
余尝问所以为道之方于龟山杨先生,先生曰:“《大学》之书,圣学之门庭也,是可读而求之。”余退而学焉。观其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本在于诚吾意而已。其说简而尽,其理直而周,其用要而博,虽不敢疑,而未知其必可行也。已而质之先生,先生曰:“是固然。”又辱教之曰:“《中庸》之书,大道之渊源也。是可读而知之。”余又退而学焉。至其论至诚不息,其极至于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则作而叹曰:“呜呼盛矣!诚若此,天下国家其不足为也已。”又从而考之,则天之所以高明,地之所以博厚,山岳之所以峙,江海之所以流,莫不以此。盖尝收视反听,一尘之虑不萌于胸中,表里洞然,机心自息。既自以为知之矣,又以谓其致之也不凝,则其居之也必不安;其养之也不熟,则其发之也必不粹。斯道也,其可须臾离哉!以其不可违也,而莫之违之,故吾诚尝存焉。[14]卷二十
杨时所授至道之要,正是《大学》《中庸》。杨时同时代的胡安国在《龟山志铭辩》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杨时所见在《中庸》,自明道传授。”[8]卷十值得强调的是,杨时对陈瓘学行文章有极高的评价,《题了翁责沈》云:“了翁以盖世之才,迈往之气,包括宇宙,宜其自视无前矣。乃退然不以贤知自居,而以不闻先生长者之名为愧,非有尊德乐义之诚心,而以自胜为强,何以及此?高文大笔著之简册,使世之自广而狭人者有所矜式。”[15]266从中可看出儒学内部成员间相互推许:陈瓘敬重杨时,杨时对陈瓘虚怀如谷、尊德礼贤、克己诚心,何尝不礼重有加?“以不闻先生长者之名为愧”,虽为概述文字,若联系上文反复论及的《责沈文》,可断定先生长者名字中一定有程颢。陈瓘《责沈文》本来是写给侄孙陈渊的,而从上引题跋可看出,《责沈文》显然得到杨时的积极回应。
除了《责沈文》,陈瓘还曾为陈渊“默堂”写过箴言——《默堂箴》[14]卷十八,勉励他劬劬正道,发扬儒学。陈渊的《赠别杨至游三首》其三,颇能体现他的思想宗尚,诗云:“应悟濂溪真古佛,始知伊洛是醇儒。”[14]卷六坚信伊洛之学乃儒学正宗;该诗真可谓陈渊笃信理学的庄严宣誓。陈渊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践行理学精神,如《看论语四首》其三:“陋巷从容一事无,不因邻斗出吾庐。箪瓢岂是忘忧物,自是从容乐有余。”[14]卷五从中可看出他对孔颜乐处的追寻;汲汲于圣学工夫,在日常践履中识得从容之乐,这也是理学家的基本素养。
北宋晚朝的思想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除了官学即王安石新学外,儒学尚有其他派别,如陈瓘、司马光后学、邵雍后学,等等,也在思想界发生着影响;二程之学只是非官方学术中的儒学的一个支派而已。陈瓘在《责沈文》一文中,通过自述他对程颢由无知到推尊的思想历程,说明二程之学逐渐获得有识之士的认同;他向侄孙陈渊度以金针,希望陈渊能将程颢伊洛之学与陈氏家学融会贯通,成长为洛学传承序列中的节点人物。陈渊果不负乃祖陈瓘所望,尽心修为,成为杨时门下首座弟子[10]1264。
2)从浮标站风速的日变化看,存在很明显的波动规律,夜间和上午风速值相对较小,午后到傍晚出现风速大值区,峰值出现在16时左右,也是日极大风速出现频率最高的时间点。日常监测预报预警工作要尤其关注午后到傍晚时间段浮标站风速的变化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责沈文》的影响并不囿于陈氏家族一隅,在两宋理学思想的传承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张栻在《跋了翁责沈》中盛称“虚中克己,皆可以为后世师法”“斯文之传,诚有补于世教”[16]710,所以,张栻将此文刊刻在桂林学宫,让万千学子瞻拜学习。据朱熹《跋陈了翁责沈》一文,可知在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桂林、建业、延平及沙县等地皆有《责沈文》的石刻,后人观瞻此帖,能感受到陈瓘“克己尊贤、虚心服善之意”“尚足以为激贪立懦之助”[17]3882。张栻、朱熹等作为南宋理学大家,极力彰显《责沈文》有益世教,更充分印证了它的价值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曾枣庄 ,刘琳.全宋文:第129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2]池生春.明道先生年谱[M] //宋明理学家年谱:第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3]施懿超.范祖禹年谱简编[J].文献,2001(3):84-104.
[4]程颢, 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M]//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于浩.宋明理学家年谱续编:第2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7]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朱熹.伊洛渊源录[M].丛书集成初编本.
[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0]黄宗羲 ,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陈渊.默堂先生文集[M].四部丛刊续编本.
[15]曾枣庄, 刘琳.全宋文:第124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6]张栻.南轩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7]朱熹.朱文公文集[M]//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An Epitome of the Inheritance of Neo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NG Jian-sh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 :Ze Shen Wen is a letter written by Chen Guan to impart academic experience to his grandnephew Chen Yuan.As a document of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senior and the junior of the family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content and the value of “Ze Shen Wen” are not confined to one aspect of the family.It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between the two Song Dynasties.The influence of Cheng brother’s learning on the society is quite limited at the Shen Zong Dynasty.The Cheng’s relatives and friends unanimously give their summary of Cheng Hao’s life and career.The private teaching between Yang Shi and Chen Yuan reflects the vitality of Cheng’s study under the official high pressure situation;Chen Guan,a scholar bureaucrat outside the circle of Cheng’s fiction,whose cognition,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of Cheng’s ideology not only manifest the upward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eng’s ideology,but also reflect Chen Guan’s foresight of the future ideological circles that Cheng’s learning is in the ascendant;.Chen Guan’s practice theory of self cultivation is direct successor of Cheng Hao’s theory of mind and soul.
Key words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Neo-Confucianism;Chen guan;Chen Yuan
[收稿日期] 2019-03-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BZW093)
[作者简介] 王建生(1981—),男,河南泌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宋代文学及文学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B 244.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889X( 2019) 02- 0011- 07
(责任编辑 杨中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