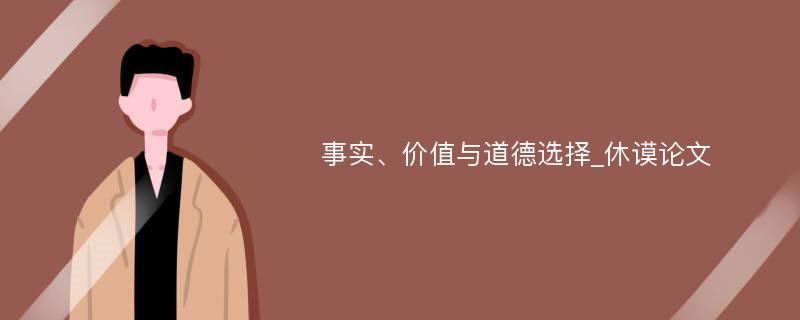
事实、价值与道德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实论文,道德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7)06-0134-04
美国著名学者J·P·蒂洛曾断言:“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要同道德这样的价值问题打交道。”[1](P205)所谓道德价值,就是指“道德事实与人之间特有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道德事实对人的本质之确证和完善。”[2] 道德价值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影形相随,人们只有选择这种或那种道德价值的权利,而没有选择或不选择道德价值的自由。“道德选择,就是在事实上的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重与轻、利己与利人、保全与牺牲、高尚与低下等等之间进行取舍。”[3](P104)即在不同的道德价值之间的取舍与选择。因此,道德选择的理论与实践中必然遇到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或者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也即所谓休谟问题。本文拟对道德选择中如何处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予以分析说明。
一、事实与价值的内在统一性
在西方哲学史上,英国哲学家休谟首先将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认为事实知识有真假之分,并可由经验来证明,而价值知识则无真假可言且是不可由经验来证明的,从表述事实的语句推不出表述价值的语句,亦即从“是”推不出“应该”。休谟谈道:“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4](P509-510)休谟认为,“应该”是“趋善”尺度,“是”是“求真”尺度,“趋善”尺度不能从“求真”尺度直接推导出来,二者绝对地对立,两个尺度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他对事实与价值即“是”与“应该”之间的一致性提出质疑。
休谟的发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价值哲学的诞生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他发现“求真”与“趋善”两个尺度的区别后,并没有同时看到二者的联系,相反,把“求真”与“趋善”两个尺度之间的区别绝对化,以致形成了思想史上有名的“休谟逻辑鸿沟”,或叫“休谟问题”。
正是由于休谟人为制造的这一逻辑鸿沟,遭到了后来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马斯洛即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写道:“从根本上说,一个人要弄清楚他应该做什么,最好的办法是先找出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达到伦理的和价值的决定、达到聪明的选择、达到应该的途径是经过‘是’、经过事实、真实、现实而发现的,是经过特定的人的本性而发现的。他越了解他的本性,他的深蕴愿望、他的气质、他的本质、他寻求和渴望什么、以及什么能使他真正满足,他的价值选择也就变得越不费力、越自动、越成为一种副现象。”所以,“发现一个人的真实本性既是一个应该的探索,又是一种是的探索。”[5](P112)也就是说,“求真”与“趋善”两个尺度不仅不矛盾,而且还相互匹配,相得益彰。“求真”是基础,只有通过“求真”,才能实现“趋善”;“趋善”是关键,它保证“求真”具有正确的出发点和归宿。两个尺度对于“人的真实本性”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求真”与“趋善”两个尺度的内在联系总是客观存在,并发生作用的。一旦脱离道德事实,就不可能科学地阐释道德价值。诚如梯利所言:“照我看来,那种在道德领域里认真而彻底的考察,将鼓舞我们对道德更加尊重,加强我们的向善心。当然,那些对道德事实的匆忙和肤浅的判断是和所有别的‘半瓶醋真理’一样危险的。”[6](P16)
解决道德价值与道德事实之间的内在矛盾,并不在于两者本身,而在于两者的架构者——人。人既是道德的主体,也是价值的主体;任何道德都是关于人的道德,任何价值也都是对于人的价值,脱离人,把握道德、解读价值都无异于缘木求鱼。人既是道德事实的轴心,又是道德价值的轴心;既是道德价值的创造者,又是道德价值的受益者;既是价值活动的认知者,又是价值存在的评价者。
因此,事实与价值是统一的,统一于“实际活动着的人”自身;人类之探索“是”、事实、真理,或者说人类之“应该”、之追求价值,都源于人的内在本性和人的生活与实践活动的需要。价值评价与关于事实的认知一样,都是在人的实践基础上,人对对象的能动反映或认识。而且,同是作为人对世界的反映或认识,价值评价与事实认知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在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中,与不存在纯粹表达事实的语言系统或概念体系一样,也不存在纯粹表达价值的语言系统或概念体系;正如关于事实认知的科学在根本意义上并非价值中立的,关于价值评价的理论与实践也不能脱离事实或事实认知活动;而且,人类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一再证明,事实认知与价值评价具有内在统一性。
二、道德选择: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
价值判断即意义判断,其功用在于区分和把握善与恶、美与丑,体现人的精神需求和德性水准。事实判断又称科学判断或真理判断,其功用在于辨明真与假、是与非,体现人的智慧水平和认知能力。选择都是在判断的基础上发生的,道德选择也是这样。正确的道德选择,其基础应是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统一,然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进行道德选择的实际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的。
自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逐渐感到,“学雷锋”在许多情况下正在走向形式主义,甚至正在起相反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初,在某个中学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宿舍的某位同学因专门为其他同学洗脏衣服而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其他同学因为身边有“雷锋”而个个变成了生活不愿自理的“懒鬼”。某年3月5日,一个人在街头“学雷锋”——无偿地给别人修补铝锅,忙得浑身是汗的“雷锋”的身后站了十几个等待修补锅的人,甚至还有一个人随便地在垃圾堆上捡了一只破铝锅,也加入到那十几个等待修补锅的行列。
发扬“雷锋精神”的人,从善良意志的价值判断看无疑都是“替他人着想”,期待着促进助人为乐的伦理关系的形成。但是,其选择是否合理,行为是否得当,结果是否能转化为善的事实,却成了另外的事情。上面例子中的“学雷锋”造成的后果是:一人学雷锋,必然会“培养”一批批的不学雷锋的人,这些人都是爱占别人便宜的不劳而获者;这与社会主义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是相悖的。
以上现象说明,主体的道德选择过程包含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两种判断不一致便产生“道德悖论”:雷锋精神的价值趋向在客观上是以众多的“非雷锋精神”为基础和目标的,而大力提倡雷锋精神的逻辑走向必定是雷锋精神的失落。
主体进行道德选择的关键是其自身和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进一步说明其过程存在着价值判断与逻辑判断的矛盾性,我们不妨再以“帮助乞丐”为例作一下具体分析:
“我”在做出“帮助乞丐”的道德选择之前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前提性判断:(1)从事实判断的角度:“乞丐”是否真的需要“我”去帮助。这一判断客观上存在几种不同的实际情况:第一,“乞丐”是真的,而且真的需要人给予帮助;第二,“乞丐”是假的,他是为了做“万元户”或出于别的什么动机,并不真的需要人给予帮助;第三,“乞丐”所需要的“我”的帮助,也可以通过其自身的努力来实现;第四,“乞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会对其造成某种“损失”,但对“我”、别的人乃至于社会却是有利的。概括起来,第一个方面的判断在客观上存在两种实际情况:一是客体的需要有真假之别,二是满足客体需要的方式不同会造成两种不同的结果。(2)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我”应该帮助“乞丐”。这一判断客观上也包含如下几种不同的实际情况:第一,“我”应该帮助“乞丐”是因为“乞丐”有此需要;第二,“我”这样做只是出于“乐于助人”的德性习惯。
通过以上几个事例的分析,可以得出在现实生活中,主体在认识和把握道德选择中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关系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道德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必须是一致的、不可脱节的。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选择,若不注意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就会发生类似我们上面所讲的事例中的“悖论”,主体只有在“确实需要”的情景下发扬“雷锋精神”,实施“助人为乐”,才值得称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行为选择实现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
第二,道德的价值判断必须以事实判断为前提和基础,即必须以分清科学意义上的是与非为前提和基础。例如,一般情况下,“诚实是美德”,根本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但是不是“某人讲了实话”这一道德事实就必然具有道德价值呢?或者说,是不是“某人撒了谎”这一道德事实就肯定没有道德价值呢?回答恐怕就不能简单从事,必须进一步弄清楚是何人、何故、对象是谁。倘若“撒谎者”是一名职业医生,出于同情、爱护一位绝症患者,那么这一道德事实就具有道德价值;如果这名医生信守诚实美德,讲了实话,致使病人受到严重精神刺激,病情恶化,甚至危及生命,那这一道德事实反而会失去道德价值,成为道德负价值。
第三,道德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脱节、忽视了事实判断的基础作用,都必然会最终导致对道德价值自身的否定,使主体由道德价值判断出发的道德选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失去道德价值。因此,在道德生活中,主体必须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统一起来,并且以事实判断为前提和基础。
中国传统道德是一种义务论、主观论道德,在道德选择上注重的是价值判断而轻视以至于忽视事实判断。它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人生在世要尽自己的道德义务,凡事须从自己应有的良心出发。今天,我们无疑要吸收这种珍贵的精神遗产,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在道德选择中,应当具备把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统一起来的意识,社会应当提倡这种统一的价值观,并以此来评价人们的道德思维方式和道德行为方式。
三、道德选择:德行与智慧的统一
我们上面所讲的道德选择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的过程,客观上也是个体人格的不断完善的过程。所谓人格的完善,不应被解释为越高尚越无私越好,而应该被理解为既是高尚无私的,又是充满智慧的,高尚与智慧的统一才是真正完善的人格。因此,道德选择从个体人格完善的角度来分析,又是德行与智慧的统一。这里我们集中讨论道德选择中的伦理智慧问题。
有学者认为,道德选择的“实践不应当是教条式的照搬道德原则,而应当是一种生活智慧。任何一种道德原则和规范,任何一种信念与道德理论,都无法教给人们在具体场景下的具体道德选择方案,它们所能做的只是教给人们一种生活的原则与态度,只能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人类、社会、生命、存在的负责精神。具体情境中的道德行为究竟应该如何选择,须当事人根据这种生活原则与生活态度,出于高度负责的精神,仔细分析权衡具体时空对象,相宜而行。这就是列宁曾说过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7](P368-369)
人类的伦理文明史表明:新建立的伦理关系总是需要维护,固有的伦理关系总是需要创新,维护和创新又总是需要与其相适应的道德,这里的相适应的道德往往是学理化道德。当道德主体运用道德维护和创新伦理关系的时候,道德还只是一种关于善与恶的知识,需要对其进行思索和转化。这一思索与转化的过程已不是原质的道德,而是演变成了与道德有关的智慧,即道德智慧。如敬业奉献是公民道德的一项基本规范要求,在其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就需要主体回答诸如“什么是敬业奉献”、“怎样才算敬业奉献”的问题,这种回答所凭借的就是道德智慧。相对于一定的伦理关系,道德只有转化成智慧形式,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伦理智慧表现在主体面对不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能够做出合理的选择,并将所选择的伦理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内化为自我意识,以指导自身的行为。“我们之所以说‘伦理是一种智慧’,就是因为伦理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只有内化为个体的主体自我意识(即通常我们所说的‘良心’),才能真正成为个体认识世界并指导个体行为的观念平台。人们在不同的道德选择面前也才有可能充分表现出伦理智慧。”[8] 马克思认为伦理道德是人们掌握世界的一种“实践精神”方式,康德把伦理道德看成是一种“实践理性”,其实都是试图表明伦理道德是一种在理性基础上的自觉,而这种理性基础上的自觉在常识生活中就是伦理智慧的表现。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孔子“仁”“智”并举,孟子把人生的最高境界定义为“尽心、知性、知天”,佛教主张“顿悟”,道教提倡“全身保真”等思想,其核心就是高扬这种伦理智慧。
当然,面对着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全球交往体系,仅仅依赖于个体伦理智慧的发挥而进行道德选择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作为社会,也有责任为个人的道德选择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即通过群体的智慧为个人的道德选择提供帮助,而且个体伦理智慧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依托社会整体的智慧,社会整体的智慧应该是个体伦理智慧得以实现的智慧。“对于个体行为来讲,怎样不偏不倚、处事合宜是一种伦理智慧;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怎样建立和完善一种整体性的机制、结构,使伦理道德的要求在这种结构中得以体现,从而使个体行为者经常面临的道德悖论得以化解,使每一方的利益都得以保障,这可以说是一种使伦理智慧得以实现的智慧。”[9](P10)
道德作为“对生活本身规则的总结”是伦理智慧的结晶,包含着人的智慧,但其本身不是道德智慧,在道德教育和道德活动中它仅仅是道德的“教条”。道德教育和道德活动是否遵循“一份耕耘便有一份收获”的规律,关键在于怎样“选道德”、“选对象”、“选方法”,这种“选”就是道德智慧。在实际的道德建设中,道德“思想”比道德知识更重要。当我们遇到道德建设事与愿违的情景时,首先应反思的不是道德知识的“灌输”是否“加强”了,而是道德思想的有无与多少,这种反思本身也是道德智慧。“从事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人,不应当是只会记忆和传播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的‘颂经者’,而应当是善于将道德要求转化为道德智慧,用道德‘思想’塑造人们心灵的智者和艺术家。”[10] 一个社会,与其重视它的伦理关系与道德体系,不如高扬它的伦理智慧和道德智慧。
标签:休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