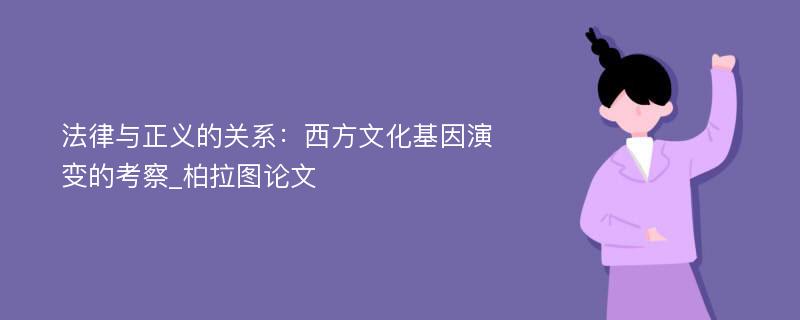
法与正义之关联:一个西方文化基因演进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因论文,正义论文,西方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思想家和法学家们,在许多个世纪里从种种角度对法与正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这种不懈的研究,表明了西方思想家所具有的一种“重视法与正义的关联性”的态度。考察西方文明源头古希腊的法律思想史可以看到,这种态度在古希腊就已产生,是适应了当时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一种态度,因此其中包含了某种必然性。而且,这种态度从此积淀在西方文明中,潜移默化,成为西方后世思想家思考时的“前见”,成为一种可以遗传下来的思维惯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自古希腊起就在文明中奠定了一种“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文化基因”。(注:基因:生物体遗传的基本单位,存在于细胞的染色体上,作直线排列。)以至于,在西方后世,即使是那些否定法与正义有关联的思想家们,也仍要重视、研究这一问题,而不能漠视和回避之——可以说,“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这一文化基因,实际上在对它的否定者们身上表现了其否定环节。
因此,本文试图从这一文化基因的奠定和演化的角度去对西方思想史上关于法与正义的关系研究作一考察。在行文的思路上,首先将考察这一文化基因的奠定过程,然后分析此基因是如何在后世的思想家研究那里表现了它的肯定环节、否定环节以及否定之否定环节的。同时,在具体内容上,我们不求面面俱到地把这些思想家对法与正义的问题观点都罗列出来,而将特别注意各时期的思想家们是如何根据时代的种种不同的需要而添注的那些新鲜有启发性的因素。
一、“重视法与正义关联”文化基因的奠定:古希腊罗马时代
在奠定了西方文明基因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源头,可以看到与中国古代有所不同,古希腊罗马人是十分重视法与正义的关联的。因此在西方文明的源头之处,我们不仅关心当时人们关于正义与法的思想的产生、发展的具体内容,而且更关注西方“重视法与正义关联”之“基因”的奠定过程和脉络。这将为我们理解以后西方近代和现代在此问题上的研究思路和态度提供根基。因此在本节多花一点笔墨,以求探幽发微,应该说是值得的。
(一)“正义”从宇宙论的概念到与“法”密切相关
人类对正义的观念,从顺序上说要比对实在法的观念发生得早。(注:宇宙大爆炸后,各种元素就是依次序先后出现的(参见[英]霍金:《时间简史》,许明贤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113页),而在所有文明的开端,造就文明的种种因素的出现,也有着一种类似的顺序性:从采集、狩猎到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从石器到青铜器、铁器;从社会分工到私有制、阶段和法。这种顺序性可能是有意义的。)它起源于远古的人们对自然、宇宙的混沌的感觉和思索中,最初是一个宇宙论上的概念。最早书面表达了希腊人从混沌中萌发的正义观念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公元前9世纪左右写成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荷马史诗中的"dike"一词,后来就一直被译为英文的"justice"(即“正义”)。(注:参见[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版,第19页。)对于"dike"一词的含义和使用,无论是荷马本人,还是他所描绘的那些人,“都预先假设了一个前提,即宇宙有一种单一的基本秩序,这一秩序既使自然有了一定的结构,也使社会有了一定的结构,……要成为正义的(didqios),就是要按照这一秩序来规导自己的行动和事务。”(注:同上注书,第19-20页。)
公元前8世纪,希腊各城邦普遍进行了立法活动。(注:参见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以下。传说,公元前8世纪曾有过《吕库尔古斯立法》、《卡恩达斯法》、《费洛劳斯法》等,但内容不传。从现有文献看,希腊最早的一部成文法是公元前621年的《德古拉法》。)成文法产生后,就此习惯法更容易引起人们对正义和法的关系的思索。同时期,海希奥德(约公元前8世纪)的长诗《劳动与时日》里,正义和法律开始有了联系。(注:据博登海默介绍说:“海希奥德认为,法律乃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一种和平秩序,它强迫人们戒除暴力,把争议提交给仲裁者。”(E.Bodenbeimer,Jurisprudence: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 of the Law,Harw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4.))然而在智者们出现以前,希腊人思考问题的重心毕竟只在宇宙论上而尚未扩展到社会、法律、人生等多个方面。“正义”,是作为一个宇宙论的重要概念而被一再提及的,它常被看作是一种有衡平能力的必然性或自然律,规定着万物之间的永恒的分寸、界限、比例或关系,使它们不互相逾越,米利都学派的重要人物阿那克西曼德(Anaksimandros,盛年约在公元前570年),在论述他所假设的宇宙本原“无定”时说的话,就通过“不正义必须互相弥补”的思想,来透露出这种界限:“万物所由之而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正义,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偿补。”(注:《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页。)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盛年约在公元前504年)则通过斗争来阐释这种界限。他说,正义就是斗争——通过斗争找到彼此的界线与和谐。假如没有高音与低音的存在,就没有和声;如若没有雄性和雌性的对立,也就没有生物。相反的力量造成和谐,就象低音和高音形成和声一样。(注:同上,第19页。)在专门研究数的毕达哥拉斯(Puthagoras,盛年约在公元前532年)那里,正义也与关系、比例的和谐存在某种联系。他建立了神秘的数的宇宙论,把整个宇宙秩序都显示在数与和谐之中,各种现象都可归根于数与和谐,并且他宣布,数的某一种特性是正义。(注:同上,第37页。)至于“法律”概念,在古希腊早期有时也会被作为自然规则的一部分而不多地提到,比如赫拉克利特说,“……人类的一切法律都因那唯一的神的法律而存在。神的法律从心所欲地支配着,满足一切,也超过一切。”(注:同上,第29*
。)比较可以确定的是,当时正义和法的关系还未成为人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与早期的智者几乎同时的德谟克里特(Demokritos,盛年约在公元前420年),对正义、法律的论述较他的前贤有增多之势。(注:据笔者根据同上注书《古希腊罗马哲学》进行的统计,德谟克里特的残篇200余条中,直接论及正义和法的只有6%。这两个相差将近一半的比例是从两人的一二百条言语中统计出来的,也许能够说明一点问题)很遗憾这位“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6页。)的原著,流传下来的极少,从其留存下来的、有争议的原著残篇看,他已经倾向于把正义看成是人的一种德性,而较少把它作为宇宙论的概念来使用了。
正义从宇宙论的概念演变成为与法密切相关的概念,是古希腊思想家为西方奠定“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文化基因的第一步。真正从思想上启动这第一步演变的“主体”,是智者们(Sophistes)。
回想中国古代尽管有“义利之辩”,却极少有对“义法之理”的探究,为何在古希腊,正义概念却会演变为与法密切相关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难以完全讲清的问题。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从表面上看,这种演变是一些思想家偶然完成的,但深入一点可以看到,这是古希腊当时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的:在古希腊,由于希腊泛海殖民活动而导致了众多的殖民地,所产生的希腊殖民城邦制度又反馈到了希腊本上,这种城邦制度具有自治的特征。众多的殖民地又事实上成为希腊人的海上贸易网,从而使多数希腊人走向重视商业、农工商兼营发展的道路。(注:参见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这种对海上贸易的很大程度的依赖,也意味着在经济生活中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土地的限制,如许多史学家指出的,这在古代亚细亚各国是没有的;从政治上看,航海活动最重要最深远的后果,是为了打破原始氏族神授王权的以血缘为基础的政体,为建立“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作了历史的铺垫。(注:参见崔之元:《比较历史研究的一个尝试》,《读书》1984年第4期。正如崔之元先生在该文中分析的,航海的艰险,需要船上的人们打破身份的界限,同舟共济,需要人们选择有能力的领袖,而不是通过血缘的继承产生领袖,从而“神权王授”必然衰落。最初代替王权的是贵族政治,后逐步发展为民主政治……。)而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度尤其成为这种演变的直接原因。“事实上希腊世界进入‘主权在民’的时代始自梭伦立法”,(注:参见注[13]引书,第125页。)梭伦于公元前549年立法后逐步创立的雅典民主制度,恰好为古希腊人以后在意识中逐渐重视法与正义的关系在制度上作了准备。公元前478年,雅典在反波斯的提洛同盟中成为盟主,并率同盟取得了希波战争的胜利。胜利中得到优越性证明的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度,从此迅速发展,而至伯里克里(Pericles,公元前495-429年)执政时期(公元前443-429年)达到了极盛,(注:参见注[13]引书,第146-174页。)并在希腊文明中举足轻重。
当其时,雅典的公民在决定城邦大事的公民大会和裁决生死的陪审法庭上,主要是靠成功的演说而不是地位和财富来对听众施加影响,于是,通过训练,提高公民的修辞、论辩和演说等方面的才能而谋生的“智者”便应运而生。公民们需要学习的,主要是对政治、法律等实际问题而非对宇宙、自然等形而上学问题的论辩技巧,这样智者们的思考从宇宙观转向“人事”是很自然而然的事。同时,伯里克里的立法富有技术上的弹性,陪审法庭可以不受雅典原有法律的约束,依公正原则和推理,创立新的法律。因此在法庭审判中,法官(由陪审员选举产生)和陪审团的注意力和兴趣往往不在于分析和适用法律条款的内容,而旨在发现正义和法律的关系,以求具体案件的公正判决。(注:参见注[13]引书,第50页,第56页。)于是智者们也顺理成章地把正义和法律的关系作为论辩的重点。后世研究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学者,常把这些转变称为“价值观的转向”,但却很少有人提及“民主制度←→智者的谋生物段(注:从智者的代表普罗泰戈拉的重要著作《争论的技艺》、《为收费辩护》的篇名中,我们可以对智者通过培养他人的论辩技艺以收费谋生一窥端倪。)←→雅典法律←→智者的思考←→价值观的转向”之间的关联。
智者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派。他们对正义与法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说法”,然而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这些“说法”代表他们各自的真实思想,具有诚意。因为智者或他们的“门生”在法庭上的辩护大致类同如今律师之所为,而在其他场合进行辩论时的角色也可用今日种种“辩论赛”中的学生来比拟。同此,同一个智者完全可能对同一命题视需要的不同而有相异的说法。事实上,“智者”后来几乎成为“诡辩者”的同义词。但要老用“诡辩”一词去评价他们在思想史上的成就是不公平的,拿“正义与法的关系”这一问题来说,至少,正是智者们第一次对此问题进行了多方探讨,栽培出了那么多种思路的萌芽,如: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90-410年):正义只是人们得以联合、建立秩序的政治技艺而不是宇宙的必然——尽管在寓言中它是由宙斯送给人类的——因此正义是人的一种德性,人人都有它,但又要通过学习和努力得到。不正义的人应受法律的惩罚。(注:同注[7]引书,第136-138页。)
吕科费隆(Lykophron):正义可以是一种约定,而法律只是“一种互相保证正义的约定”,并没有使公民善良和正义的实在力量。(注:同注[7]引书,第144页。)
安提芬(Antiphon):正义可分为遵守自然法的正义和遵守国家法律的正义。人在公众场合应遵守国家法,而在私下场合应遵守自然法。(注:《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第30-31页。并参见严存生:《论法与正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加里克利斯(Callicles):自然的正义和法律的正义不同。自然的正义是强者比弱者应得到更多的利益,而法律的正义是一种约定,是为了维护弱者的利益。(注:同注[21]引书,第27-30页。并参见严存生:《论法与正义》,第21-22页。)
其他的论述还有很多,尽管智者们对正义和法的论述各异,但形式上却有共通性,即都把“人”作为正义和法的尺度,并强调在这一尺度下对正义和法进行评价的相对性。同时,他们对正义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已经出现了意见分歧。
(二)从“德性与正义”到“法与正义”的重新定位:柏拉图
德性与正义的严肃结合,是由苏格拉底(Sokrates,约前469-399年)提倡的。他不同意智者们的“此亦—正义,彼亦—正义”,他认为要以理性为基础严肃地对待正义问题。由于苏格拉底的“述而不作”,而柏拉图(Plato,前427-347年)在其对话集中又喜以苏格拉底为对话主角,对于所有研究者来说,想要在思想观点上区分开他们两人是困难的和要冒风险的。(注:对此,罗素说:“我们很难判断柏拉图究竟有意想描绘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到什么程度,而他想把他的对话录中的那个叫苏格拉底的人仅仅当作他自己意见的传声筒又到什么程度。”[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9页。)但至少以下的几点是确凿无疑的:苏格拉底的确在雅典被判处死刑并于公元前399年就刑;他拒绝了逃跑的机会,因为他认为一个公民服从法律才是正义的。(注:苏格拉底认为一个公民服从法律才是正义的;而同时显然又认为判他死刑是不正义的。这两点事实已经给了我们研究的材料,对于苏格拉底,我们至少可以对他在正义和法律问题上的观点得出如此推论:或者,苏格拉底认为,公民必须遵守法律才是正义的——尽管法律本身也许并不一定正义;或者,在苏格拉底的意识中,公民必须遵守法律才是正义的——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而正义的法律也有可能被不公正地适用,也就是说法律是否正义与法律的适用是否正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柏拉图对话集的内容看,苏格拉底持后一种想法的可能性要大一点。)苏格拉底以他之死无可辩驳地向世人昭示了他把德性、理性与正义结合的严肃态度。
在其他问题上,请允许我们把“区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一史家们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悬置”起来,且以“柏拉图”来代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柏拉图也持重视德性与正义结合的态度。他批判智者们以辩论术迎合群众需要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不严肃的伪哲学,是“治国技术的幻影”。(注:见《高尔吉亚》463D-E。转引自王宏文、宋洁人:《柏拉图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页。)他反对正义是相对的,认为正义的基础是理性,对于个人来说,灵魂由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组成,个人要达到正义必须让理性统治灵魂从而借助激情抑制欲望;对于国家来说,“理想国”由统治者、军人和人民组成,统治者的美德是智慧,军人的美德是勇敢,人民的美德是节制,如果三个等级各自拥有了其美德,国家就达到了正义。(注:《理想国》428-432;同上,第285-289页。)故正义就是每个人只从事最适合他天性的职业,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不互相越位。(注:《理想国》433A-B;同上,第289页。)可见,在柏拉图那里,理性、德性、正义是三位一体的。但前期的柏拉图理想化地认为,要实现正义,美德是本,法律是末;懂哲学有美德的统治者所拥有的政治智慧的权威,要高于法律的权威,“……在政治秩序不良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是无济于事的,而在秩序良好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有的不难设计出来,有的则可以从前人的法律条例中很方便地引申出来。”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嘲讽那些想通过不断制定、修改法律来杜绝社会不正义的人,如“砍九头蛇的脑袋”(注:《理想国》426E;同上,第292页。九头蛇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种怪蛇,有九头,其头斩一则生二、暂二则生四,层出不穷,砍不胜砍。)一样徒劳。
然而这种与中国古代儒家“重德轻法”有相通之处的理论,并不适合古希腊氏族血缘关系早已土崩瓦解的城邦。现实使后期的柏拉图痛苦地认识到,他的正义理论必须在希腊城邦现实中重新定位——必须重视法与正义的关联,于是他在《法律篇》中批评人治的弊端,强调法律的最高权威。“当法律缺乏最高的权威,受制于其他权威,城邦就要遭殃。但如法律在统治者之上,统治者成为法律的仆人,城邦就会安全,并享受诸神赐予城邦的一切好东西。”(注:柏拉图:《法律篇》715C-D。转引自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仅如此,柏拉图还一反他早期对人们细密立法之努力的嘲讽,在《法律篇》中,从第4卷720E开始一直到第12卷,柏拉图为他设想的(Magnrsia)新理想国拟定了详尽的法律条文。当然,立法的目的没变,仍是为了实现正义。“我们的法律必须把一切不断地仅仅引向一个目的,……这唯一的目的就是把称为善的东西叫作正义。”可见如博登海默所言,前后期的柏拉图,正义观基本未变,而法律观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注:参见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我们进一步说,在柏拉图前后期理论体系中,是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有了重大的改变:前期,相对于有哲学智慧的王来说,法律只是实现正义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而后期,法律已成了实现正义的最有权威、最不可少的手段了。柏拉图这一改变,对西方奠定“重视法与正义的关联”的文化基因影响巨大。这不仅是由于柏拉图在西方思想史的地位,更由于这是一位在正义理论上曾经著名地“重德轻法”的思想家,在多年深思后严肃选择了“重视法与正义的关联”的路途,因而就有了别人不可替代的感召作用。如果要说苏格拉底的影子的话,在后期的柏拉图身上是已渐渐消退了。
(三)“基因”的基本奠定:亚里期多德
基本上完成对西方“重视法与正义的关联”的文化基因之奠定的思想家,是亚里斯多德。
阅读亚里斯多德(Aristoteles,前384-322年)的著作,今天的学者几乎都无法抑制自己敬仰的心情,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知识广博,见解深刻,为古希腊哲学最杰出的代表,更因为我们今天的很多优秀的思想还都渊源于他。在法与正义问题上,他也构建了第一个较成熟的思想体系。
亚里斯多德第一个建立了伦理学。(注:亚里斯多德在他的学园里开设了一门叫"Ethos"的学问,即伦理学,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伦理学。参见张海伦主编《西方伦理学家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他对正义的分析一直受后世的推崇。他把正义(公平)与德性联系起来,认为每一种德性都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比如说节制是对快乐的放纵和冷漠之间的中道,庄重是自傲和顺从之间的中道),(注:亚里斯多德:《大伦理学》1191b、1192b。(由于亚里斯多德理论的艰深,本文参考了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的《亚里斯多德伦理学》和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的《亚里斯多德全集》两个版本。在两个版本中,“公正”和“正义”两词应是相当的,只是译法不同而已。)参见《亚里斯多德全集》第8卷,第271、275页。)但中道并非是指与两极的距离都相等,而是由理性根据具体情况所找到的相对中道。正义是百德之说,也是中道。(注: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92a-b。同上,第94-96页;及《亚里斯多德伦理学》,第95-97页。)
亚里斯多德首先把正义分为普遍正义和特殊正义两类。普遍正义是指人拥有完全的德性。我们认为亚里斯多德的意思是:人如拥有了完全的德性就具有了为任何中道之事的可能性,因而就有了普遍的正义。特殊正义是普遍正义的一部分,它又可分为分配正义和纠正正义。分配正义表现在国家对荣誉、财物等东西的分配中,这种正义是一种按比例的平等,即指根据各人的真正价值来按比例分配与之相称的事物。这与柏拉图的正义是“人各适其天性、各安其位、不非分越位”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但理论上更明晰深刻;其缺陷是在现代人看来其中包含有人与人并不平等的思想。而纠正的正义是当人们在交往(又分为自愿的交往如商品交易和不自愿的交往如被盗)中受了损失时,裁判者(如法官)对所有的人一律在数值上平等地按所受损的同等数值进行弥补。(注:此段所述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同上,96-103页。)分配正义和纠正正义的提法被后世的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所沿用。正义的原则——中道,在特殊正义中主要的含义无疑是平等,不管是数值上的平等还是按比例的平等。
从法学的角度来说,亚里斯多德的最重要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对正义的分析,更在于他重视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法而不是有道德的人来实现正义。与柏拉图不同,亚里斯多德始终把法看作是实现正义的最高的权威。他说:“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欲望就有那样的特性。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枕,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因此,法律……可以被定义为‘不受主观愿望影响的理性’。”(注:《政治学》,1287a,《亚里斯多德全集》第9卷,第133页。)正如众所周知的,他又最先提出了法治与正义的法的联系。他认为法律有正义和不正义之分。法治不仅意味着公民恪守业已颁订的法律,而且意味着公民们所遵从的法律是良法,是正义的法律。(注:《政治学》,1294a,同上,第135页。)
亚里斯多德还最先明确论及了法律正义的概念。他专门从另一个角度又把正义划分为自然正义和法律正义。“自然的正义规则,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同等效力,而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接受它。”(注:E.Bodenheimer,Jurisprudence: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 of the Law p.11.)而法律正义,则是人们自己制定和规范的正义。这里,法与正义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从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中看,特殊正义也可以说就是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注:同注[29]引书,第35页;及严存生:《论法与正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亚里斯多德认为自然正义是具有神性的,它比法律正义更好。(注:亚里斯多德:《大伦理学》1195a。参见《亚里斯多德全集》第8卷,第282页。至于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关系,在亚里斯多德的著作里不甚清楚。在《尼各马可伦理学》1134b中,说政治正义,或者是自然的,或者是传统的。而在《大伦理学》1195a中则说政治正义是依据法律的,不是由于自然的(参见注[32]引书,第108页、282页)。)但人只能具有理性而不能具有神性,用法来实现正义已是人类最可取的方法了。
亚里斯多德是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文化基因,到他这里已经基本奠定,西方从此受益无穷。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西讨横扫天下时,可能没想到他的武功却没有他的老师理论思考的不朽力量来得大。
当然,古希腊对法与正义的研究并未就此止步,还有一些重要因素将补充进来。
(四)“普遍平等”、“契约”因素的补充和“怀疑”思路的出现
在重视研究法与正义关系的文化氛围中,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分别为法与正义的思考补充了一个“普遍平等”因素和“契约”因素,而希腊怀疑主义却对“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古希腊主流思想持怀疑态度。
斯多葛派的历史大约从公元前308年起至公元180年止。(注:同注[23]引书,第305页;及苗力田主编:《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页。)其创始人为芝诺(Zenon,其生卒年有几种说法,(注:如张宏生、谷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为:芝诺(前336-270);及同注[30]引书,第13页为:芝诺(前350-260)。)大约为前4世纪中期到前3世纪中期)。他们明确提出和论述了自然法的概念——该概念的意义恰是正义和法的复合,明显表现出这个学派对法与正义关联之重视。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对自然法的阐释认为奴隶和外邦人也有理性,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普遍平等观。(注:参见苗力田主编:《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认为正义要求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们至少都有维持人的尊严的起码权利,同时正义要求法律认可和保护这些权利。(注:[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2页。)这就超越了亚里斯多德“按比例平等”说中歧视奴隶的看法。这几点,对后来的古罗马法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注:同注[30]引书,第18页。)
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2-270年)是亚里斯多德后的古希腊的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在法与正义问题上正式地补充了一个“契约”因素。他认为,正义是出于功利的契约,(注:这是对智者吕科弗隆的“正义可以是一种约定”观点的更理论化的发展。与智者提出的类似观点时不同的是,他是在感觉主义和原子论的哲学基础上建立了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和正义契约论,他认为人们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和快乐,而感觉是判定善恶的标准。因此,他是最早把契约因素体系化地引入法与正义思考的人。)“公正是人们相互交往中防止互相伤害的约定”,他论证了正义作为契约的可变性,认为它也可随环境而变化。(注: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44页。)他还首次明确地分析了环境变化时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如果由于环境的变化,法律不再有利了,那么,当法律有利于公民们的相互交往时是公正。随后,当它们不再有利时就不公正。”(注:同上,第645页。)
由皮罗(Purron,约公元前360-270年)奠基的希腊怀疑主义因为对“重视法与正义关系”的古希腊主流思想持怀疑态度而值得一提。怀疑主义认为一切独断论都是不能成立的,不相信任何事物,不作任何判断。在正义问题上,他们认为,“很显然,对同一件事情,有些人认为是公正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公正。……至于谁正确,我们还是别作判断而存疑吧。”(注:同上,第654-655页。)这当然是一种挑战性的思路,开辟了后世西方怀疑主义的思考方向。
(五)文化基因在古罗马的制度实现和再传播
在古罗马从一个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城邦国家发展成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的雄奇过程中,原来盛行于小小城邦中的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文化基因,第一次以恢宏的规模、精密的设计转化为以巨大国力为后盾的实体性的法律制度。这一基因在影响、造就了名震后世的罗马法的同时,也在制度实现中证明了它自身的合理性。
如果说古罗马西塞罗,并不因他的思想具有独创性而流传千古的话,却因他系统地整理了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的学说并把它传给了罗马的法学家,而真正获得了法律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西塞罗明确地说:“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即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适应,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用人类的立法来抵消这一法律的做法在道义上决不是正当的,限制这一法律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容许的,而要想完全消灭它则是不可能的。”(注:西塞罗:《论共和国》。转引自注[43]引书,第204页。)他倾向于认为不合正义的法律是无效的。(注:同注[29]引书,第64页。)
通过西塞罗的重要中介,古希腊法律思想在古罗马法律制度中结出了硕果。罗马法学家一般并无系统阐述法律理论的兴趣,但没有一位罗马重要的法学家会否认在人定法之上存在着更高的自然法,法学的灵魂是正义。正是他们大力推动了法和正义的关系从伦理道德层面向法律层面落实,文化基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精密性获得了其制度实现。当凯尔苏斯说:“法学是有关人和神的事物的学问,是有关正义和非正义的学问。”(注:《民法大全选译:正义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0页。)这里的“正义”,“它的表达形式已不再是哲学的和道德的,而是政治的和法律的。”(注:胡旭晟:《法的道德历程(论纲)——法律史的伦理解释》,博士论文第74页。)罗马法学家通过法律把正义具体化:比如包含于罗马法中的平等因素、对约定之诚实的规定、法律程序日益摆脱单纯的形式而合乎公正的要求等等,都说明正义已不单是观念和精神,它也在罗马人的生活中通过法律得到前所未有的操作和实现。
制度又成为传播思想的中介。随着罗马法发展成为西方法制中上最伟大的法律制度之一,重视通过法来实现正义的治国思想和模式在当时和后世被广为传播。这一文化基因通过古罗马的法律,较好地实现了与制度的契合,这种契合以后一直成为西方法治文明的一个流光溢彩的因素,一个巨大的精神变物质的力量。
二、重视正义与法关联之基因的肯定环节
重视正义与法关联的文化基因在奠定之后,开始在西方思想史上演化其矛盾运动的轨迹来展现它自身。首先展现的是它的肯定环节。
(一)肯定环节的潜在状态:中世纪压抑中的巧妙显现
在中世纪的欧洲,一切知识都被纳入神学的轨道。如果我们把中世纪在法与正义关系问题上的不多收获,(注:在阿奎那之前,这不多的收获主要表现在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年)那里。他是中世纪前期教父哲学的代表,对法与正义的关系也是“有所思”的。他认为正义在于“使肉体归顺灵魂,使灵魂归顺于上帝”(《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8页)。奥古斯丁提出在国家和法律之上还有一种由神所制定的自然法,这种自然法是刻划在人类心坎上的。世俗法律如果与上帝的永恒法相悖,就是无效的。但对于自然法与永恒法的关系,他语焉不详。自他以后,从总体上看,从公元5世纪到13世纪把持着文化的神学家们思想上的创造性微弱,主要限于借助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派的观点来阐发圣经,制定和阐述教义。)去与近10个世纪的漫长时间相比,就会从一个角度发现人类的创造性思维受到既定神学框架的压抑程度。但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基因终于巧妙地显现于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中。13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us,1224-1274年)是中世纪后期的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既包含着奥古斯丁神学思想的影子,又追奉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渊源。他的关于法与正义的思考,既体现了上述两者的结合,又显露出他的创造力。第一,他把法明确分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定法。永恒法是上帝创造和统治世界的范本;人作为理性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可分享神的智慧,“这种理性动物之参与永恒法,就叫做自然法。”(注:《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7页。)故自然法已明确地不再是最高的法。第二,其自然法“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变性。……引起了相对自然法思想的萌芽。”(注:吕世伦主编:《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6页。)第三,他关注“人法”与正义的关联。如果一种人法在任何一点上与自然法相矛盾,它就不再是合法的,而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污损了”;(注:《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并认为“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注:同注[54]引书,第116页。)他把正义解释为“某一内在活动与另一内在活动之间按照某种平等关系能有适当的比例”,(注:同上,第138页。)其目的“在于调整人们彼此的关系”。(注:同上,第139页。)这又秉承了亚里斯多德的思想。第四,他采用了亚里斯多德的“法律正义”概念,“用‘法律
正义’这一术语来表达为了整个社会利益而给个人设定责任和义务的制度。”(注:同注[30]引书,第254页注4。)这种提法对现代比利时的达班很有影响。
如果只从法与正义研究者的角度去评价托马斯·阿奎那,可以说,尽管他在出发点上带有神学的偏见,但他巧妙地调和了神学框架的挤压和他创造性的张力之间的矛盾,使重视正义与法关联的文化基因得以在中世纪传承,并使它几乎最大限度地在神学框架中释放出异彩。
(二)肯定环节的高潮: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的盛行
17、18世纪,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古典自然法开始勃兴和盛行,这标志着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基因已进入了它肯定环节的高潮。为这一肯定环节极尽铺垫的,先有13世纪末14世纪初从意大利开始的人文主义思潮;随后有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其中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注:15至16世纪,许多希腊罗马作者、作品第一次为人所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希腊文、拉丁文全集相继出版,见注[42]引书,第205-206页。)成为该文化基因在其后的古典自然法学派中得到淋漓渲泄的正式“引言”;复有16世纪初发端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背景和重视法与正义的关系的浓烈氛围下,对法与正义关系的学术研究,通过原有的自然法观念与一些新因素如社会契约论、国家主权论和分权论等以种种方式所进行的理论组合,而在两个世纪内辉煌灿烂地发展,许多思想家为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进行研究。
1.格老秀斯在法与正义关系问题上的主要贡献
近代最早在法与正义上作出重要贡献的,是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年)。他揭去了托马斯·阿奎那披在自然法理论上的神学外衣,还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理论以世俗的本来面目,并加以对人性之于自然法作用的论证,从而奠定了古典自然法的基础。他认为自然法是通过人的理性和社会性为中介内容,而与正义相连通的,故自然法与正义具有同一性。“自然法是正当的理性法则,它指示任何与我们理性和社会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道义上的公正的行动;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注:同注[56]引书,第143页。)自然法和正义是意志法(即人定法)的基础。
他把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联系起来,是社会契约说的创始人之一。并且,他体系化地把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说由一国之内推至国际之间,认为自然法在国际交往中的体现即为国际法,由国际社会的契约组成。“公然违反国际法不仅是非正义的而且是不虔诚的。”(注:同上,第156页。)另在《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他认为法和正义不但适用于国际间的和平时期,也适用于战争时期。通过对法与正义的研究,格老秀斯也成为现代国际法的奠基者。
2.法与正义关系的三种崭新的构建方式
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在古希腊罗马自然法学说的“根”之上,依布丹最早提出的主权学说(注:依通说,布丹在1576年发表的《国家六论》中所提出的主权学说为最早的成系统理论。)及格老秀斯的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新的生长方向,茁壮地生长出了对法与正义关系的三种崭新的构建方式。霍布斯、洛克和孟德斯鸠、卢梭的学说,分别是这三种构建方式的代表。
先说他们各自对自然状态的看法。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持性恶论的观点,提出自然状态是人人互相为战的状态,这种状态下,“是与非以及公正和不公正的观念在这儿都不能存在。没有公共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注:[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6页。)而卢梭(Jc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持反对意见,他认为霍布斯本应这样说:“由于自然状态是每一个对于自我保存的关心最不妨害他人自我保存的一种状态,所以这种状态最能保持和平,对于人类也是最为适宜的。”(注:[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8页。)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也认为自然状态是美好的(如拥有完备的自由、平等),此时存在维护和平和保卫人类的自然法,“……每个人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以制止违反自然法为度。”(注:参见注[56]引书,第220-221页。)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年)则作出了另外的推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自卑感,几乎没有平等的感觉。……人类感觉到软弱,又感觉到需要。”(注:[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正文第4页。)
从不同的自然状态说出发,他们各自对正义与法的关系作了新的构建。霍布斯认为正义是由自然法产生的。有些学者以为霍布斯持“正义源自法律”的观点,其实这是有所误解的。霍布斯的理论思路是“理性—自然法—守约(正义的源泉)—主权者必然正义—任何法律都是正义的”。可分析如下:(1)“正义源于自然法”是霍布斯正义理论的最初前提。他认为自然状态的人尽管是“性恶”的,但又同时具有理性,有能力去发现自然法:(注:同注[65]引书,第97页。)第一条是“寻求和平和自卫”;第二是“人们为了和平而必须互相转让一部分权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同上,第97-98页。)由此,“就产生了第三自然法——‘所订信约必须履行’。”霍布斯说:“这一自然法中包含了正义的泉源。……在订立信约之后,失约就成为不义,而非正义的定义就是不履行信约。”(注:同上,第108-109页。引文中着重号为原文所有。)(2)“主权者必须正义”是霍布斯正义理论的最核心的结论。他认为人们互相订约建立起国家,承当国家之人格者称主权者,他必然是正义的。“主权者所做的任何事情对任何臣民都不能构成侵害,而臣民中任何人也没有理由控告他不义,因为一个人根据另一个人的授权做出任何事情时,在这一桩事情上不可能对授权者构成侵害。”(注:同上,第136页。)(3)法律既然是由主权当局制定的,那么“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不正义的”,法律无正义不正义之分,只有良与不良之分。(注:此段的意思请参见同上,第137-138页及270页;引文请见270页。)这只是其正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论。后世的国家主义者和法律实证主义者深受霍布斯理论的结论(2)和推论(3)的影响,却往往忽视了其理论前提(1)。
当然也不可否认,霍布斯确有强调国家权力和国家主义的倾向,这从他把国家称为“利维坦”就表现出来:“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Leviathan)的诞生,——用更尊敬的话说,这就是一个新的上帝的诞生。”(注:同上,第132页。“利维坦”是神话中强大无比的怪兽。)但要看到,这种国家主义与他所处的时代需要一种以主权去对抗教权、以新的“上帝”取代旧的上帝的理论,从而去摇撼、摧毁欧洲封建制度的教会支柱不无关联。
洛克在法与正义关系问题上的最大的创意在于提出分析学说。他认为,由于自然法缺乏明确性、也不能为众所周知,而且缺乏有权裁判纠纷的公正的裁判者及判决的执行者。故此,人们需要缔结契约来建立政治社会、以成立共同的裁判机关。(注:同注[56]引书,第233-234页。)同样地,他认为自然法代表着正义,是规定法律及判断法律正义与否的标准,“……这些法律只有以自然法为根据时才是公正的,它们的规定与解释必须以自然法为根据。”(注:同上,第222页。)洛克理论与霍布斯不同的关键之处是,他认为人们在缔约时仅交出了对自然法的执行权以建立政府,而当政府的行为违背自然法时,人们是有权废除和重新订立社会契约的。于是就有了分权学说的主要观点:立法权与执法权应由不同的人掌管,以防止政府的独裁、专横及违反自然法——这一创意是对法与正义关系的思考的一大进展,意味着人民可通过设置法制的运行机制来主要用于预防政府的不正义而非主要用来被动地接受政府统治。另外,洛克还提出了人民有权反抗不正义的非法的政府滥用国家权力的观点。(注:此段对洛克思想的陈述请参见同上,第236-238页。)
洛克的分析思想为孟德斯鸠所很好地继承了。尽管孟德斯鸠的理论前提与洛克有着相当差异——他未进行社会契约论的前提假设,而认为真接从人的天性出发就可自然而然地推导出社会、国家和法律。孟德斯鸠在游历各国、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事物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注:同注[68]引书,正文第1页。)他认为由事物的性质产生了客观的法则,也产生了正义,人定法是在它之后并根据它创设的。他说,“在实证法律建立正义的关系之前,已有正义的各种关系。”(注:转引自注[29]引书,第109页;该句在中文版《论法的精神》(商务印务馆1961年版)正文第2页,译作“……在人为法建立了公道的关系之先,就已经有了公道关系的存在。”)因此,“孟德斯鸠是古典自然法学派中唯一否认契约论的思想家。”(注:同注[29]引书,第111页。)他认为从事物(这里是人)的性质来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注:同注[68]引书,第154页。)而为了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必须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这种思考使他接受了洛克分权说,并在其基础上创立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与制约的学说。在法与正义关系问题上,他从事物的性质出发的思路,影响了以后的社会法学派;他从各国法制历史出发的方法,又对后来的历史法学派有很大启发。(注:梅因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本书虽然有缺点,却仍按‘历史方法’进行研究。”见[英]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9页。)
由洛克创立、孟德斯鸠加以发展的分权理论,对后来美国宪法制定者创制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有直接的影响,也成为以后西方法治思想的精华之一。
卢梭在他的著作中很注意对法与正义进行论述,而且文采飞扬。他的契约理论“起初好像和洛克的类似,但不久就显出比较接近霍布士(斯)的见解。”(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7页。)他认为真正的正义观念产生于社会状态之后,而不是在自然状态。“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注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代替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页。)他创造性地提出主权者是缔约者全体,而不是个人和大多数人;主权在民,国家统治者只不过是人民公仆,民主是实现正义的保证。在法与正义关系上,卢梭的观点基本类似霍布斯的见解,他说:“……我们无须再问应该由谁来制定法律,因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也无须问法律是否会不公正,因为没有人会对自己不公正。”因此他也是强调正义对法律的依赖性的。
卢梭的法哲学理论对后来许多伟大的法哲学家(比如康德、黑格尔等)都有重要启发,也一直被众多的学者评价为是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的号角和理论先声。但也有学者认为卢梭从契约导出的“公意说”(注:公意不同于众意。卢梭阐述他的“公意”道:“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之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见同上引书,第39页。))有消极意义,比如黑格尔尽管赞成卢梭“提出意志作为国家的原则”,但在评价“公意说”时,认为它偏执于“单个人的任意性、意见和随心表达的同意”,说雅各宾专政的恐怖政策就是这一理论实践的结果。(注: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4-255页。)
3.肯定环节的尾声:康德与黑格尔
康德、黑格尔的理论精深广博。但从时间上说,当他们在法与正义关系问题上进行理论建树时,“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肯定环节已经由高潮转向尾声。这两位大思想家主要分别为法与正义关系问题的研究系统地增加了“自由”因素和“国家”因素。
康德(Kant,1724-1804年)对公共正义的三种形式的划分(保护的正义、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只是对亚里斯多德的观点略加演变。显然,这种划分远远比不上他对正义的新定义所产生的影响。经过艰难思考,康德以他的哲学的一个基础概念“自由”重新定义了正义。
在近代强调“自由”这一概念的思想渊源,至少可追溯到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年),他在《神学政治论》中说:“实在说来,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注:[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72页。)把自由作为哲学的基础概念加以“最早的详彻论述,见于洛克的著作”。(注:同注[83]引书,第129页。另参见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页。)而“自由作为人的实质”观念的首先提出,按黑格尔的看法应归功于卢梭。黑格尔在其《哲学史》中就说,“自由的原则已按卢梭的观点逐渐为世人所理解,给予了人类无限的力量,……康德哲学按一种理论的观点把这个原则作为它的基础。”(注:转引自[英]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36页。)康德之深受卢梭影响,无论是康德本人还是后来研究康德的学者都是承认的。但终于第一次明确地用“自由”去定义“正义”的思想家,是康德。
康德说:“任何一个行为,如果它本身是公正的或者它依据的准则是公正的,那就是:根据普遍法则,这个行为和每一个人以及和所有人的意志自由在行动上可以同时并存”;(注:《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第399页。)康德又说:“如果一种行为与法律的法则一致就是它的合法性;如果一种行为和伦理的法则一致就是它的道德性。前一种法则所说的自由,仅仅是外在实践的自由;后一种法则所说的自由,指的却是内在的自由。”(注:[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页。)比较和体会上述两段话,康德用来定义“正义”的“自由”显然既包括了法律上的“外在实践的自由”,又包括伦理道德上的“内在的自由”。可见康德的正义概念的范围,是既包容道德上的正义又包容法律上的正义的。
原先,正义的主要而明确的价值内涵是平等,霍布斯虽然倾向于把安全作为正义的价值,但他并未有明确的“说法”,康德现在以“自由”去定义正义,为人们以后揭示正义在价值领域的总括性作了重要的铺垫。
法与正义在黑格尔(Hegel,1770-1831年)那里属于客观精神阶段研究的对象。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伦理有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环节,国家是伦理的最高环节。(注:参见注[86]引书,第三篇第三章。)近代的国家主义倾向,由霍布斯而卢梭,到了黑格尔这里则发挥为极致。因此强调正义与国家的关系,是十分吻合黑格尔一贯的思维逻辑的:“……正义的实在性和真理性只表现在国家里。”(注:[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3-244页。)因为黑格尔认为,“正义的真正概念就是我们所谓主观意义上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要得到实现须通过国家和法。他说“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所以一般说来,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注:同注[86]引书,第36页。)“法律是自由的具体表现,……国家是法律的客观实现。”故在黑格尔那儿,“正义—自由—法律—国家”有着必然的联系。
康德用来定义正义的“自由”,是既包括了法律的自由,又包括伦理上的自由的,康德的伦理上的自由与国家并无必然联系,因此康德的正义也就并不一定是在国家里才有的;而黑格尔的正义却离不开国家,他持的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正义观。应该说,康德的观点更与事实相符一些:人类的正义观念,从顺序上说要比对法、国家的观念出现早,从范围说,则不被国家所限。黑格尔并非不明白这一点,只是从他的体系出发,认为事物发展的高级阶段才真正表现出“真理性”,故他有一种以事物发展的高级阶段去否定事物发展的低级阶段(高级、低级当然也是他判定的)的理论偏好。他的唯心的体系和这种理论偏好,是他国家主义正义观产生的根源。
三、从19世纪到二战前:“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否定环节
(一)从肯定环节到否定环节的过渡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事物的肯定环节之后转而有一个否定的环节。“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文化基因在展现它自身时也不例外。而转向往往是需要过渡的。在该基因的从肯定环节转向否定环节中起过渡作用的理论,从哲学上讲是怀疑主义。怀疑主义之萌芽可追溯到古希腊的皮罗那里,在近代,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是公认的怀疑主义哲学的发端者。他提出的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裂隙的“休谟法则”,已为后人在法学上否定正义与法存在关联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法学理论上看,历史学派的出现也是这种过渡的一个表现。古典自然法从理性中推出自然法的非历史的方法,受到了来自历史法学派的抨击。萨维尼(Fridrich Carl Savigny,1799-1861年)在1814年与蒂鲍(Thibaut,1772-1804年)的法学论战中率先提出,要把法学理解为一门建筑在历史基础上的科学。他认为古典自然法的观点只相信普遍适用的自然理性,不顾各民族具体情况和差异,因而是错误的。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德国的历史法学派,强调具有特殊性的历史经验的重要,试图通过对法律史的踏实研究,对那种无经验基础的自然法理论中的“历史虚构式”的理性提出质疑。但他们的理论立场相对于完全否定自然法理论的立场而言,仍然只是过渡性质的,可资证明的是他们有着从现实的法律历史中去寻找改头换面的自然法——“历史精神”和“法律规则和法的整体真实和自然的关系”的倾向。(注:萨维尼说“对于法学家来说必须具备的两种精神”,即“熟悉每个时代和每种法律形式细节的历史精神;从每一个概念和每一个规则来看它和整体的生动关系与合作,即唯一真实和自然的关系的系统精神。”萨维尼:《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方面的使命》,转引自注[56]引书,第536页。)正如萨维尼在《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中说得明白:“……从各方面困扰我们的法律历史问题将为我们所用,成为我们的财富。我们将拥有真正的自然法……。”(注:转引自注[56]引书,第541页。)同样,英国的历史法学派的代表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年)之所以着力批判古典自然法为“‘自然平等’的教条”、“幻想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梦呓”,(注:参见注[82]引书,第4、5、9章。)其主要意图在于批判古典自然法与经验割裂的无历史性;但对于从历史研究中得出客观的法则,使经验和理性达到统一,梅因自己也是很感兴趣的,他提出的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步公式,表明他仍认为存在着一种客观的价值和进步标准。
(二)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否定环节:另一个片面的深刻
经过一段过渡,西方法学于19世纪在法与正义的关联问题上有了一次重要的反思和转折,即从重视正义对法的实质内容统辖,转变为强调法的形式因素的独立性,隔离正义与法律的关系。在法学流派上反映为自然法理论的统治地位被法律实证主义取代。一般认为,这在政治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从需要高扬自然法理论去推翻封建制度夺取政权,到需要通过法律实证主义理论强调实证法的权威,以巩固其既得政权的转变。
对于实证法学派奠基,笔者不赞成有些学者所附同的萨拜因的有关观点,认为奥斯丁所作的工作“只不过是把边沁多卷的而并不是总是非常容易读懂的作品中散见的系统思想归纳起来”。(注:[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55页。)因为,我们从时间上看,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要比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年)晚生50年,其学说几乎不可能来得及对边沁发生影响;再从边沁的法理学看,其中也一直贯穿着对法律制度的目的与价值的研究。只有到了英国法学家奥斯丁(John Austin,1790-1859年)那里,才把霍布斯、边沁以来强调“法律是主权者命令”的思想和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糅合起来,在实证法的逻辑分析和价值分析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奠基了实证法学派。
奥斯丁把法律分为“应当是这样的法律”和“实际是这样的法律”。依他看来,在法外寻找正义标准和根据的工作是伦理学家和立法学家的事。而法理学家所研究的对象则是不必考虑其是否合乎正义的“实际是怎样的法律”。他说,“法理学科学(或者,简单地称法理学)只涉及实在法,或严格意义的法律,而不考虑这些法律的善与恶。”(注: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p.96.转引自注[29]引书,第184页。)不顾及法律的好坏、正义与否等价值判断,而只关注法律的形式,奥斯丁所找到的法律的基础和依据,结果是“国家权力”。他认为法律包含了三要素:主权者、命令和制裁。
正义与法的关联被奥斯丁作了某种程度的否定,这是在法理学研究范围上的否定,但为以后凯尔森在此“片面”上追求“深刻”打下了基础。
更实质意义上的否定来自凯尔森(Hans Kelsen,1881-1973年)的纯粹法学。它可以说是对正义和法的关系攻击最力的法律学说。关于纯粹法学的“纯粹”一词的含义,凯尔森解释道:“之所以称之为‘纯粹’,就因为它设法从对实在法的认识中排除一切与此无关的因素。……特定的法律科学,通称为法学的学科,一方面必须同正义哲学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同社会学,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区别开来。”(注: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页。)对于正义,凯尔森说:“人类理性只能达到相对的价值,就是说不能使一种价值判断来排除相反的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绝对正义是一个非理性的理想,即人类永恒的幻想之一。”(注:[奥]凯尔森:《什么是正义?》,《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8期,第9页。)故纯粹法学是不研究价值判断和相应的正义理论的,而只研究实在法。在他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休谟的怀疑论和康德的不可知论对其法学思想的影响。在论证了原先人们的“非理性理想”式的正义观念必须放弃以后,凯尔森提出了“法律下的正义”概念:即“正义”便是指合法性:“将一个一般规则实际适用于按其内容应该适用的一切场合,那便是‘正义的’。”(注:[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凯尔森还提出了一个“相对正义—容忍正义”的概念:即对不同的价值判断,尽管不接受它们,也不阻止它们的自由发表。“在我看来,正义是那种社会秩序,在它的保护下人们能够自由地探索真理。所以,‘我’的正义是自由的正义、和平的正义、民主的正义——容忍的正义。”(注:同注[101]引书。)
“假定某个人把‘促进人类之最大限度的痛苦是应尽的义务’的原则或把‘尽可能多地杀人是应尽的义务’的原则当作一个基本的不打折扣的原则来采纳,那么,我们可以肯定,会把他看成是一个疯子,而不管他来自什么文化群体。”
尽管我们不同意凯尔森的结论,但他的这种对正义与法关系的反思和诘难,是原先注重从“实质”一极去研究法,向注重从“形式”一极研究法的彻底转向,消解了古典自然法的形而上学“泡沫”。他的研究可以说同样为法与正义关系的研究作出了贡献,是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文化基因从肯定环节到否定环节的合规律发展。他以形式逻辑方法对法律规范的研究成就,也为西方法学界所公认,达到了另一“片面”的深刻。
四、二战后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对立面在互相争论中的统一
以二战后纳粹政权的覆灭为契机,“重视正义与法关联”的基因开始较明显地发展到了它的否定之否定阶段。这一阶段,人们对正义与法关联的重视,已吸收了前面肯定环节和否定环节的积极因素,从而展现出它在对立中的统一性和互补中的完整性特征。而在吸收和整合原有因素的基础上,新的因素又开始加入到对法与正义的研究中来。
如果要找一位在二战前后,在对待自然法学说和法与正义关联上有着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之立场转变的法学家,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年)是十分合适的。拉德布鲁赫在二战前是个相对主义、实证主义法学家,他坚持现实和价值之分,主张当法律的确定性和正义发生冲突时,正义应服从法律的确定性。纳粹政权对国家权力的滥用及其覆灭的现实,使他在二战后重新反思自己的观点,转而侧重强调“法律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现实”,(注:See Kurt Wilk:"The Legal Philosophies of Lask,Radbruch,andDabin",Harward University Press,1950.p.52.)其普遍正当性的形成总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客观价值;在实在法和正义的关系上,如果一种法律规则对正义的侵犯已不可容忍时,这种法律就已是非法的法律,人们必须服从正义。(注:参见注[100]引书,第49页。)一般认为,他的这一转变,及其后联邦德国司法部门援用自然法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对于二战后西方法学和司法实践中自然法观点的复兴有着重大影响。
(一)新分析法学和新自然法学的互补
二战后,新分析法学和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在法与正义问题上共同走向了否定之否定环节,他们的观点具有互补性是很明显的。
比如新分析法学代表人物——仍坚持法律实证主义基本命题,划分“实际是这样的法律”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律”的哈特(H.L.A.Hart,1907-1992),实际上在与新自然法学派的富勒的学术论争中,向一直被传统的分析法学视为对立面的自然法学说作了相当程度的靠拢。哈特说:“不参照任何特定内容或社会需要而以纯粹形式的观点作出的法律和道德定义,会证明是不适当的。”(注:[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他认为,每一个现代国家的法律工作者都应承认道德对法律有影响,“这些影响或者是通过立法突然地和公开地进入法律,或者通过司法程序悄悄地进入法律”,这些都是任何“实证主义”者所无法否认的事实,“如果这就是指法律和道德的必然联系的含义,它的存在是应予承认的。”(注:同上,第199页。)哈特的这种说法是对传统的“凯尔森立场”的否定,而向肯定法与正义的关联靠近了一大步。更重要的是,他还认为根据五个对事实的简单判断和公理:(1)人的脆弱性;(2)人的大体上的平等;(3)有限的利他主义;(4)有限的资源;(5)人的有限的理解力和意志力,再结合“人的继续生存”的需要出发,认为人类必须有某些基本的行为规则,他称之为“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从而论证和强调了自然事实所给出的法律和道德规则之间所具有的理性联系。(注:同上,第9章第2节。)沈宗灵先生认为,哈特所列举的作为最低限度自然法所依据的事实或公理,实际上涉及到西方法律制度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特别是关于人身、财产安全和契约自由等原则。(注:参见同注[100]引书,第197页。)
对哈特来说,既然承认法与正义具有关联,接下来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在形式合法、而在内容上不正义的法律(比如在纳粹邪恶统治下制定的法律),应该如何看?哈特试图通过提出“广义的法律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认为恶法就不是法,只有良法才是法,是采用了“狭义的法律概念”,是把“法律是否在形式上有效”与“法律是否正义”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了;而他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可以分开的,可以存在一种形式上有效但却不正义的“广义的法律”,说:“这是法律,但它们是如此邪恶以至不应遵守和服从。”(注:同注[106]引书,第203页。)
但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富勒(Lon L.Fuller,1902-1978年)却针对哈特的观点反驳道,一旦具体地就在纳粹邪恶统治下的西德法院来说,哈特所谓法律的广义概念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引起混乱的结果:一个法院拒绝服从和适用它所承认是法律的东西。哈特的根本性错误在于,他忽略了法律的内在道德问题。缺乏这种道德的法律是根本不能成为法律的。(注:同注[100]引书,第72页。)富勒坚持说,法与道德的严格分离是不可能的。法存在道德性,而且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法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法的外在道德,是指“实体的自然法”,为法的实体目的;法的内在道德是“程序的自然法”,是法的制定和运行中程序上的原则(或称法治原则)——他归纳出八个原则:(1)必须制定能指导特定行为的一般规则;(2)这些规则必须公布;(3)这些规则必须不溯既往;(4)它们应通俗易懂;(5)它们不应自相矛盾;(6)它们不规定不可实现之事;(7)它们应有稳定性而不常更改;(8)规则及其实行应有一致性。富勒关于“自然法的实体与程序之分”的观点,较以往的自然法有了重大创新。他对程序自然法的研究,可以说是也吸收了作为自然法学说对立面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注重对法的程序性进行研究”的优点。
罗尔斯(John Rwals,1921-)的《正义论》是二战后对正义与法关联重新予以肯定和强调的一本重要著作。书中,罗尔斯也吸收了作为对立面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某些成果,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社会契约论的改造上。
订立社会契约的原始状态,在他的理论里不是作为形而上学的独断结果,而是作为一种理论假设重新出现的。他说,他的原初状态尽管是“相应于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中的自然状态”,但它“当然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实际的历史状态,也并非文明之初的那种真实的原始状况,它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用来达到某种确定的正义观的纯粹假设的状态”。(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这就回避了讨论它们“是否的确存在过”的问题,避免了实证主义的攻击。
在这种经过化妆打扮后的原初状态下,他假想了一种“无知之幕”(注:这是西方学者的把自然科学思维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的一种表现。)——假定人们知道有关社会结构的一般事实和人类心理的一般法则,但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阶级、天赋等足以产生个人偏向的一切因素。罗尔斯认为,这时人们会一致选择他提出的正义的第一原则和第二原则。他的第一原则注重一个在“自由”的基本量上的平等,内容主要是强调每个人都应平等地享有基本的自由权。他的第二原则是设计了在基本公平基础上的效率: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有(1)在对整个社会的所有人——特别是对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有利时,(2)满足机会平等的要求:所有的社会地位和官职对一切人开放或提供平等机会,这种不平等才不违背正义的要求。可见,他是试图以这种契约论来反对功利主义的正义观的。(注:因为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在实际上并不能保证一个基本量的平等。功利主义在产生最大利益功利的前提下,容许对一部分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基本的平等自由的侵犯。)
通过这种对社会契约论的改造,他建立了《正义论》一书的基础,而在该书第二编第四章,他认为正义原则的发展除了第一阶段(原初状态中对正义原则的选择)外,还要通过立宪、立法、执法和守法这其他的三个阶段,来进一步完成正义原则的发展,表明了他对正义与法的关联性的重视。
罗尔斯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成果吸收借鉴,还表现在他一改以往自然法学派学者常常具有的对法与正义关系中的形式方面、程序方面的轻视态度。他论述了形式正义的概念:“类似情况得到类似处理,有关的同异都由既定规范来鉴别。制度确定的正确规范被一贯地坚持,并由当局恰当地给予解释。这种对法律和制度的公正一致的管理,不管它们的实质性原则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形式的正义。”(注:同注[112]引书,第54页。)而他对程序正义(注:人类对程序正义最初的接触,甚至可以说早已隐含在法这个特殊社会调整器的最早的运行中,与迷信交织在一起。比如古人通过考察小鸡的内脏这样的程序,来决定当事人有罪与否。尽管当时的人们并未有“程序”与“程序正义”的观念,但他们的确相信那样的仪式(程序)的正义性。后来人们才逐渐概括出程序正义的观念,说起来这一观念可有两个来源,其一是“自然正义(naturaljustice,或译为“自然公正”)的基本原则。其二是英美法的“正当程序”(dueprocess)概念。早在古罗马时代,自然法观念就被应用于诉讼程序中,并产生了两项基本原则:(1)任何人不得审理关于自己的案件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nemo judex in parte sua);(2)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audi altermpartem)。但“自然正义”这一词,据说是由普拉特法官在1723年“国王诉剑桥大学案”中的判决书中最早使用的(参见彼得·斯坦等:《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第97页)。它后来在英美司法实践中实际上被倾向于用来特指应用于诉讼程序中的自然法观念——尽管从该词的字面意义上看不出这一点——即特指诉讼程序中应合乎自然法则而存在的正义。哈特就说:“‘听双方之词’、‘不许任何人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之类程序规则也被认为是正义的要求,在英国和美国,它们日常被归入自然正义的原则。”([美]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这种具有特定含义的“自然正义”为人们后来产生程序正义观念铸就了基础。后来的美国学者戈尔丁在讨论列出了程序正义的9个标准后就说,这些标准中“有不少或许全部都包括英国法学家称作‘自然正义’的东西里。”([美]戈尔丁:《法律哲学》,齐海滨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1页。)同时,据谷口安平认为,人们关于程序正义的观念得以形成和展开,又是以发生、发达于英美法的“正当程序”思想为背景的(参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
)。程序正义概念真正在西方法学界被广为使用和讨论,则是在本世纪6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后。)的研究,甚至达到了以往法律实证主义者都未达到过的学术水准。他的《正义论》一书,在总体上就具有“重程序设计”的倾向和特色,书中提出并分析了程序正义三种形态: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纯粹的程序正义是指:假设对通过程序运行而得出的结果是否正义的判断,并不存在任何独立的标准,但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只要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得出的结果就都可被认为是正义的,无论它们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完善的程序正义是指:对何为正义的结果既存在独立的标准,而且又有可能设计出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结果的程序。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是指:虽然具有一种对判断结果是否正义的独立标准,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这种结果的程序(比如说刑事审判)。(注:同注[112]引书,第80-82页。)罗尔斯对程序正义的分类充分表现了西方学者喜欢对问题“所指对象”的各个形态予以“模式化”的思路。这一分类被西方法学界广为引用和讨论,非常有学术影响力。在对(广义的)程序正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罗尔斯提出,法治的施行必须通过规定了正当过程的程序来实现,(注:同上,第225-233页。)并进而关注了法律上的(狭义的)程序正义的问题。而罗尔斯对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的不同论述,实际上也涉及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问题。(注:从理论上进,形式正义是和“实质正义”相对的概念,而程序正义则是与“实体正义”相对应的范畴。法律的形式正义,是指在形式上合法而产生的正义。故象法律的形式正义的标准,是通过就法律而法律,在法律内部就能发现的。法律的实质正义,是指法律的内容在实质上合理——合乎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正义。显然,在法律内部是无法找到这个“法律的内容在实质上合理”的标准的,标准来自法律之外的社会生活,看法律的内容是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却是从“法的程序与实体之分”这样一个另外的角度,去划分法律正义的。程序性法律规范及其运行中包含的正义为程序正义,实体性法律规范及其运行中包含的正义为实体正义。而从本质上说,程序性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是实体性权利义务如何确认和分配的法律过程。故法律上的形式正义的核心问题是“形式合法性”问题,程序正义的核心问题却是“法律过程”问题。正如季卫东先生所阐明的,“可以说,程序的本质特点既不是形式*
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季卫东:《程序比较论》,《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第10页。)因此,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是两种互为交错的划分。在这种交错中,从法理上至少可以产生出四组它们彼此的划分和互为的联系。比如说,当人们适用实体性法律规范时,如果从形式与实质之分的角度看,又可分为追求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理性两种方式,此时实体正义可分为形式上的实体正义和实质上的实体正义。同理,既可以有形式上的程序正义,也可以有实质上的程序正义,等等。)
(二)社会法学派在法与正义关系上的立场
从某种程度上说,重视正义与法关联的否定之否定环节也表现在社会法学派在此问题的立场上。社会法学派自它从19世纪末产生的时候起,就采纳了实证主义哲学的观点,以“社会实证”的面目出现。故在法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在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否“实证”这一点上,它与法律实证主义是志趣相投的,并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自然法理论持批判态度。布莱克是这方面的著名代表,他认为,法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就应当使事实和价值彻底分离,以事实为研究对象而摈弃价值问题。(注:参见朱景文:《现代西方法社会学》,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但另一方面,社会法学派的研究宗旨是以“社会实证”的方法研究法的社会目的与效果等等,这就意味着,它也是侧重“从法律以外”来研究法的,这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就法律研究法律”的态度是对立的,而与自然法学派的立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故也有一些社会法学派的学者对正义与法的关联持肯定和重视态度。
如产生较早的、在基本倾向上可归类于社会法学派的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年)的“目的法学”,认为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和为社会目的服务的手段。耶林讽刺分析法学那种认为法官只要根据逻辑推理就可从法律条文得出正确判决,而无需求助于公平正义观念,法律目的和社会需要的观点是“概念法学”的。又如埃利希(E.Ehrlihc,1862-1922年)的自由法学,主张允许法官可以根据正义原则和习惯自由发现生活中的“活法”。再如狄骥(Leon Duguit,1859-1928年)认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是以社会连带关系为基础自然产生的,社会规范又可分为经济、道德和法律三类。他说这种由社会连带关系而产生的法律规范不同于国家制定的实在法,而是一种“客观法”。(注:同注[100]引书,第254-256页。)尽管狄骥一再强调他的学说是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法学,但有些西方学者还是评论说他的那种“客观法”也是先验的,名义上是社会学法学,其实也只是自然法学说的一种而已。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法学派的代表庞德(Roscoe,Pound,1870-1964年)批评了自然法学只关心法律是否合乎抽象的正义,而不关心通过法律使正义发生实际效力的缺陷。他认为社会法学派应有所不同,应关心法律的适用,在研究如何使法的目的更有效地实现的过程中,研究正义如何在个别案件中得以应有的实现应是社会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注: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同时,庞德承认,普遍盛行的道德观念实际上经常在审判活动中频繁引用,只是人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这种道德观念是法律中的理想的价值标准,也是法律中的“连续性”的组成成分。因此,庞德肯定地说,“我们可以有一种内容正在起变化或形成着的自然法。”(注:见怀特:《从社会法学到实在主义法学的发展》,转引自吕世伦主编:《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现实主义法学(一种具有激进色彩的社会法学)的代表物卢埃林(Karl N.Llewellyn,1893-1962年)也很重视法与正义的关系。他指出,人们一般认为法官具有使判决结果合乎正义要求的责任。正义的意义尽管可能因法官的不同而被有差异地表达着,但公认的想法和说法可以减少这些差异。卢埃林认为正义有四种属性:第一,它是“良好”的一个方面;第二,它致力于消除、避免和调整人们的冲突;第三,它必须体现公正公平;第四,它是在资源稀缺的状态下使用的。(注:同注[100]引书,第319、321页。)卢埃林还较具体地分析了美国法律发展从19世纪以来的可看到的法院判案的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是形式风格,一种是庄重风格。(注:同上,第324-325页。)“形式风格”主要是指法官仅仅根据法律规则判案,判决意见是以演绎和单线形式来表述,法院认为政策仅与立法部门有关而与法官无关。(注:卢埃林这里说的“形式风格”,也就是19世纪很为法律实证主义者赞赏的所谓“严格的法治精神”:法官在案件中严格解释和适用法律规范,在审判过程上严格遵守合法性,以实现法律要求的形式正义。)而所谓的“庄重风格”,主要是指法官审判时不能仅依靠规则,死板地服从前例,而且要诉诸理性、智慧和正义感。“无论是判例法或制定法,没有理性,就没有规则,法院对制定法的正常任务不仅是阅读法律,而且要根据目的和理性来实施法律。”(注:转引自注[100]引书,第324页。)卢埃林赞成庄重风格,认为这种风格是防止不稳定性和矛盾从而寻求正义的最好的审判风格。
在二战以后,随着新自然法学派里“形而上学泡沫”的减少,社会法学派在法与正义关系问题上,与新自然法学派的立场就更为接近和相似。二战后社会学法学的代表塞尔兹尼克(P.Selznick,1919-)比庞德更重视和强调对法与正义关系、对法律价值问题的研究。他认为,社会学家将事实和价值割裂开来是错误的。当法律社会学发展到他所说的“智力自立和成熟”的第三阶段时,应该承认,对作为一种规范体系的法律,价值是其中心问题,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理想。当然第三阶段的法律社会学家研究这些问题时已掌握了社会学必要的方法和技术,研究水平也应该更高了。(注:同注[100]引书,第349页。)塞尔茨尼克还认为,法制只是正义的一部分,法制本身是一种可变的成就,而一些基本的正义规则是批评和改造法制的基准。他说:“把法律和政策中内在的价值抽出来,以这些价值作为基准批评既成的规则和创造新的规则,并使它们适合于不断变动的社会环境。”(注:Philippe Nonet and Philip Selznick,Law and society inTransition:Toward Responsive Law,Harper & Row.1978,p.79.)
从总体上看,社会法学派是非常重视正义与法的关联的,但他们通常的关注力并不在静态的包含在法律中的正义上,而是集中于动态的、在法的实现、法的运行中的正义上。可以说这正是该学派的创新之处,也是它最值得为我们今天研究法与正义关系时所借鉴的地方。
除了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法学家们,在“重视正义与法关联”基因的否定之否定阶段,还有许多法学家、思想家综合地吸收前面肯定阶段和否定阶段的成果,并在法与正义的理论上作了进一步创新,如佩雷尔曼的形式正义论、(注:法律上的形式正义与更为广义的形式正义有所不同。佩雷尔曼是对更为广义的形式正义作了系统的研究。在对思想史上的正义理论的类型进行分析后,他认为可以从中引出“形式正义”的概念,它可解释为“一种活动原则,根据该原则,凡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应受到同等的待遇”(转引自注[122]引书,第584页)。即佩雷尔曼的形式正义是抽象程度很高的正义概念,它没有具体规定任何“基本范畴”,而当人们一旦为正义具体规定了一个基本范畴,形式正义就会转化为特殊正义。关于特殊正义,佩雷尔曼举出了他认为至今最为流行的五种:即对每个人根据优点对待、对每个人根据劳动对待、对每个人根据需要对待、对每个人根据身份对待及对每个人根据法定权利对待(参见注[100]引书,第439-441页)。法律上的形式正义,则等同于本文上文中所举的罗尔斯的“形式正义”概念,而在佩雷尔曼的理论体系中它却恰恰是被列举的特殊正义的一种情况:“对每个人根据法定权利对待。”佩雷尔曼和罗尔斯其实是不矛盾的,其原因就在于形式正义也是个有着层次性的体系,佩雷尔曼的形式正义属最为抽象的层次,而罗尔斯所说的形式正义,与佩雷尔曼所指的形式正义相比起来抽象性要低,属特殊正义,但与法律正义中实质正义相比,却仍是抽象的形式,属形式正义。)博登海默的“法等于秩序与正义之综合”论、魏因贝格尔的分析—辩证正义论和诺锡克的资格正义论等等,本文不在这里一一赘述。
五、小结
请允许我在这里简要概括一下上文中对西方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文化基因之奠定和演化的考察:(1)在古希腊这一文化基因的奠定阶段,古希腊的智者们是真正把正义从宇宙论的概念转变为与法密切相关的概念的“思想主体”;柏拉图对法与正义关联从轻视到重视的转变,对“重视法与正义的关联”之文化基因的奠定影响巨大;而基本上完成了该基因之奠定的思想家,是亚里斯多德。(2)即使在中世纪神学框架的压抑中,该基因的肯定环节也在托马斯·阿奎那身上得到了巧妙的显现;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的盛行,是此基因肯定环节的高潮,原有的自然法观念与一些新因素如社会契约论、国家主权论和分权论等被以种种方式进行理论上的组合,从而使法与正义关系的研究得到了辉煌的发展,许多思想家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康德和黑格尔的有关研究,则是该基因肯定环节的尾声。(3)从19世纪到二战前这一时期,由奥斯丁奠基并为凯尔森所充分发展的法律实证主义,在西方法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但这一法学流派的思想家们仍重视和研究“法与正义关联”问题,而不是漠视和回避它(尽管在对此问题的研究结论上,他们是倾向于否定法与正义具有关联的)。可以说,“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这一文化基因,实际上在他们身上表现了其否定环节。(4)二战后,此基因进入了它的否定之否定环节阶段,前面肯定环节和否定环节的积极因素被吸收进来。表现为以新分析法学、新自然法学和社会法学派三大派为主流的许多西方法学家们,在互相争论中达到了一定的统一和互补;并在此基础上,许多思想家、法学家把一些新的因素注入到对法与正义的研究中来。
沿着上文考察中的思路而容易被提起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是否也具有“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文化基因”呢?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情况有相当的不同。一方面,尽管中国自春秋战国以降也讲“义”的概念,但这个“义”泛指道德仁义,它与西方的“正义”概念不完全等同:西方自古希腊起讲的“正义”概念,其重心之一,是以人们的利益为基础,这个“正义”,是围绕人们相互之间的利益划分和保护打转的,它适合用法来调整;而在中国古代,对“义”有代表性的阐释却常常是与“利”相对、相争的,(注:另据有的学者研究,西方的正义概念前提肯定了私利在正义面前的合理性,而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几种思想对义利之辩的不同论述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去私”。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153页,第160页。)所谓“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注: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对“义”的更为具体的解说也散见于典籍之中,比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慧、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注:《论语·礼运》。)这种“义”,的确是更适宜通过道德来调整的。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法”,尽管也有着“公平”、“正直”的内涵,(注:特别是中国古代法家,常常强调在法律的适用上,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古代思想家们还常以具有公正性、准确性的度量衡来比喻法,来说明法的公平之功效,如管子就把法比喻为尺寸、规矩、绳墨。)但遗憾的是这种内涵未被充分地挖掘出来。以家族伦理为治国之本的古时中国人,是强调以道德为主来解决纠纷的,讲“和为贵”,强调“无讼”,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法”在解决纠纷、实现公正上的功能和地位较低,有点不登实现公正的大雅之堂。在美国汉学家金勇义先生所著的《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中(第80页),我们可以看到康熙皇帝颁布的一道诏令,在其中,康熙公开向全国的官吏主张说:由于人易为自身利益所引诱,故用国家的这一半力量不足以平息另一半的争讼。因此,对那些求助于法律的人不要有任何的怜悯,这样的话,他们才会厌恶法律,发生麻烦、争议的人们应该象兄弟一样求助于长老或村长解决问题。(注:这段康熙诏令经外国人释译过,由于语气被翻译得太现代了,故这里不引用这段译文,而只取其意。)作为集立法权与司法权于一身的皇帝所颁布的这一诏令,*
露出中国古代统治者们的心态,也较能说明中国古代法律在解决纠纷、维护公正中的地位较之道德为低。因此,中国古代的“法”与“义”之间的关联,的确并没有西方的“法”与“正义”之间的关联那样受到重视。可以说,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传统中是缺乏那种“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文化基因”的。
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今的中国,自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社会越来越需要以法来实现正义——那种主要是对人们之间的利益进行划分、规范和保护意义上的“正义”——它与中国传统中那个往往与“利”相对的“义”,恰恰是有所差异的。但对于社会的这种需要,我们在传统上,又缺乏相应的系统而全面的文化准备。如今,这种被动已在现实生活中显现出来:国民(官员和民众)通过法来奉行和实现社会正义的意识之薄弱,与法律制度的迅猛发展之间,已形成了令人吃惊的反差。一方面,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本方面及主要问题上已有法可依;而另一方面,徒法不自行,现实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是有法不依。缺乏“重视以法来实现正义”的文化传统,影响了从官员到民众的价值评价和行为选择,国民对通过法实现正义的认识不足,主动性不够,这导致法律制度的实效不甚理想,是现实中“立法容易执法难,判决容易执行难”等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因此,考察西方重视法与正义关联的文化基因的奠定和演化,并作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创新,(注:“重视正义与法关联”的基因在古希腊奠基以后,经两次否定、三个阶段,在法与正义关系这一问题上,西方思想家的一些代表性的观点已经沿着许多思路作了研究,富积了精彩纷呈、观点纷纭的成果。然而,转用叔本华的一句话来说,我们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大脑只被别人“走了许多次马”。笔者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摸索在法与正义问题的研究上有所创新。因为在对以往的成果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人们以往一般只是从“法”与“正义是既相对独立,又互为交错两个范畴去研究它们的“外在关系”,当正义与法构成“内在关系”,即正义内化、制度化于法律,成为“法律正义”时,人们对它的有系统的专门性理论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因此,笔者集中力量从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一般与个别、形式与实质、程序与实体、立法与司法等几个方面系统地去研究了法律正义的特点和运行模式,力争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吸收以往那些关于法与正义关系的互相竞争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中的长处。今后,笔者还将把这一方面的探索进行下去。)将有利于我们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在国民思想中唤起和培养“重视法与正义两者之间关联”的法律意识,促成国民在精神气质上的超越和变革,这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得以良性运行的重要一步。
标签:柏拉图论文; 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法律篇论文; 古希腊论文; 理想国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法律论文; 哲学家论文; 伦理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