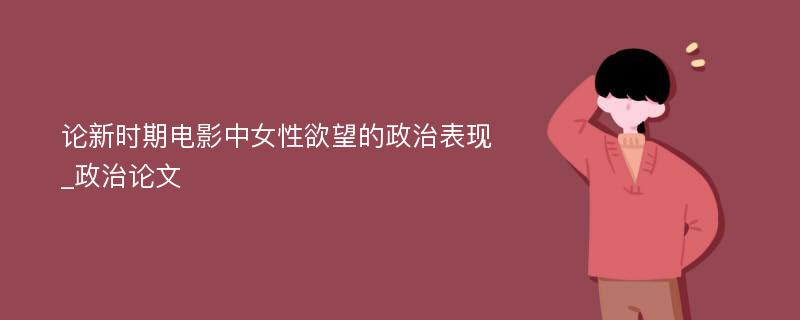
论新时期电影中女性情欲的政治表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情欲论文,政治论文,女性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开始之后,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激进“左倾”的建立现代乌托邦的革命狂热被现实主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化路线所取代,“解放政治”逐步转型为“生活政治”,“文革”时期清教色彩浓重的生产伦理退出历史舞台,尊重个体欲望、追求自我幸福的生活伦理庄严登场。政治文化的调整使得此际电影中的女性情欲终于摆脱了国家主义展演模式,迎回了私人情欲展演的广阔空间。由于新时期的主导政治所倡导的生活伦理在本质上依然是被纳入国家话语和民族复兴话语总体系中的生产伦理,电影本身亦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责任,这使得主导政治依然在谋划、监控此际电影中的女体情欲展演,以期将之完全纳入新的政治文化工程。另一方面,伴随着“文艺从属于政治”口号的废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方针,电影生产由计划经济的单轨制向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双轨制的转变,新时期电影终归还是获得了半自律性的生存空间,越轨的银幕女体情欲展演亦拥有其存活土壤。这些越轨的情欲展演虽然与新时期思想解放的轴心实践存在一定的共谋,但其对情欲力量的过分张扬明显偏离了主导政治所倡导的生产伦理轨道,故而与权威意旨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摩擦。
一 、情欲展演与政治神话
正如历史学家米歇尔?德舍陶所言“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会作祟于现在”,[1] (P37)“文革”电影中女性情欲私人流向的匮乏在新时期电影中得到了极大的弥补,这些重新浮现银幕的私我情欲展演比及“十七年”时期的含蓄式也更加奔放。首先,新时期银幕女性的情欲展演可以被任意置放在花前、月下、湖畔、街头等与社会主义建设无关的空间中,而不会被主导政治戴上“十七年”时期那般的污名帽子,《庐山恋》《漓江春》《三峡情思》这类“风光加爱情”影片的存在本身即是明证。告别公共政治空间、回归日常生活空间,使得此际电影中女性身体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属于个体生命的真实感受,其情欲展演不再仅仅是主导政治颁发给投身社会主义集体事业的优秀劳动者们的“随时”嘉奖。其次,新时期银幕女体情欲展演的尺度远远逾越了“十七年”时期的含蓄标准。《生活的颤音》让情侣在告别的时候有了接吻的意图,《庐山恋》中周筠在娇嗔埋怨耿桦不够主动之后大胆吻了爱人的脸颊,《不是为了爱情》中有了由意大利留学生裴兰·尼克莱达饰演的女主角同男主角三秒钟的接吻镜头,此后追逐、拥抱、接吻更一度成为银幕情欲展演的固定程式。[2](P38)《湘女萧萧》《红高粱》《寡妇村》等影片更是勇敢地突入长久以来的禁区,将女性身体对于男性身体的性渴望予以真实坦然的正面呈现,女人的生物学存在终于不再被歪曲丑化。总之,新时期的银幕女体情欲展演拥有了比“十七年”时期更多的自然元素——私密的、本能的、会对集体话语造成威胁的难以升华的元素。不过,这种“展演以往所不能展演”的表象并不意味着新时期的银幕女体情欲展演已经摆脱了主导政治的操控,事实上这些增添的低级元素正是国家政治在新时期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型所带来的新内容:个人主体得以从社会主义集体话语的普遍压抑中浮出水面,人情、人性开始得到承认,个人的世俗欲望(自然包括情欲)也得到了一定的尊重。银幕女体情欲展演的奔放表象,呼应了广大观众在卫生时代的压抑下所积聚的社会无意识,①对于点燃观众心中有关新时期创世神话的“原初激情”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辅助。
主导政治往往将银幕女性情欲的展演镶嵌入宏大话语的逻辑链之中,试图利用这样一种美学的自然效果来实现新意识形态的渗透。戴锦华曾经指出,新时期的电影生产与新时期的社会生活的重要相关之处,不在于一种经济/ 生产、再生产的事实,而在于“一个共同的记忆梦魇和心理参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表述”。[3](P23-24)在新时期电影对于“文革”的繁多表述中,将“文革”指认为压抑个体、灭绝爱情的封建法西斯,将新时期指认为解放个体、唤醒爱情的启蒙新时代,是主导政治利用电影话语进行自身合法性论证的一条迷人路径。在此,仅以《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和《大桥下面》为例,荒妹和秦楠均被剧情设置为在“文革”中遭遇重大事故变得对爱情异常冷漠,在新时期打开内心、寻回爱之激情的人物。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结尾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终于吹到了“角落”,农贸市场红红火火,父亲沈山旺被平反,沈荒妹从临近封建买卖婚姻的不幸边缘处逃脱,她一边挥舞着衣服一边高喊着“荣树哥”向心上人狂奔而来,绕过繁盛的桃花林,穿过明艳的油菜花地,脸上满是狂喜的神情。此时画外音响起:“让辛酸的往事永远过去吧!明媚的春天已经来了,美好的爱情还会远吗?”在《大桥下面》的结尾处,秦楠对高志华讲述了自己的不幸往事,高志华安慰她说:“要说命运,我只相信国家好了,我们就好了。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好的。”秦楠回答:“一定。”然后两人就默契定情了,秦楠先是娇羞地把头放在自己的手上,继而又抬起头微笑地凝视着自己的爱人,清丽的面容写满幸福。她们的身体变化反映出的正是新时期电影中女体情欲展演的一种惯用程序:政治的温暖春风唤醒了沉睡的女体情欲,政治的明媚春天成全了情欲的自然奔涌,新政治的无边魔术将她们从开始时的愁眉不展转换成收尾时的灿烂笑颜。饶有趣味的是,荒妹的姐姐存妮和秦楠本人都被设置为曾在“文革”时期闯入性禁区的角色。但是,两人的“类爱情”经历均不被指认为“爱情”:一个是愚昧落后所致的无知冲动,存妮与小豹子的仓促激情里掺杂着眼泪和巴掌,一个是在可怕力量推压下的彼此怜悯,秦楠与孟彬在一起的生活充满了冰冷面孔与唉声叹气。在此,“文革”段落的身体展演所运营的“畸形年代畸形情欲”的程序显然与上述程序同是新时期政治逻辑的衍生品,它们分别在“起点”、“拐点”与“终点”作用,以完美的封闭图形建立起了爱情神话与政治神话的同构关系,并将银幕女性身体转换成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政治寓言。新时期电影通过爱情神话的附丽将政治神话“情感化”,并以女性情欲的政治程序化展演直接诉诸观众的情感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主导政治(尤其是在新时期的前半期)对于强烈的情感感召力量的迫切需求。
政治神话的表述需要接通人们头脑中的既有思维以进行成功的价值转换,而爱情正是其可以借用“生子”的重要母腹。《白毛女》(延安歌剧版本、十七年电影版本)便是用爱情传奇扮演政治神话的绝佳范例,高喊“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的《王贵与李香香》(李季叙事诗版本、“十七年”歌剧版本)同样如此。经典社会主义文艺对于爱情传奇的使用,往往将其压缩为次要情节,约束在婚姻的前景或者背景之中,并且规约甚至放逐身体的情欲展演。而新时期电影在借用爱情神话表述政治神话时,则开始将之扩充为主要情节,并且进行奔放的身体情欲展演,将经典社会主义文艺中的潜动力彻底擢升为占据全景的主动力。甚至有时出现了政治神话完全隐身于爱情神话的表述方式,爱情神话成为一种去政治(表象)的政治(本质)。值得一提的是,新时期的主导政治在“文革”与“封建社会”之间建立了紧密的隐喻联系,因此此际电影中以个体情欲反抗封建统治的影像叙事在内核里同样是主导政治借情欲展演承载政治神话的表述方式。
二、积极情欲的时代变奏
新时期国家政治承认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乃是为了进一步疏导人的欲望并利用这种欲望进行国家的四化建设,其对主体的建构由民族国家向个人位移,却不是抛弃前者,它依然要将民族国家主体置入个人主体的目标之中。归根结底,此际的主导政治所倡导的仍然是一种生产伦理,这使其无法放弃对电影中的情欲展演的具体规划,尤其电影作品还需要“教育人们特别是青年,爱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爱我们的人民”,还需要“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激励和鼓舞人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身”。[4](P3)故此,新时期电影中的相当一部分女体情欲展演仍然被塑造成为主导政治的新文化工程,成为“十七年”时期银幕女体情欲展演的同工异曲。本部分将结合具体影片来探测新时期电影中女体情欲展演的政治参数,并通过与“十七年”电影的比较来勘测历史的变异与延续。
1.女体情欲的政治流向。在“十七年”电影中,女性身体的情欲流向遭到了主导政治的严厉规划,它只能通往那些担负着国家使命的男性英雄。优质纯洁的女性身体在事实上已成为主导政治颁发给男性英雄的另一枚勋章。在新时期电影中,这种国家生产伦理借用银幕爱情之名对广大观众进行的思想内化依然在持续。许多反映当时生活的影片都将新主导政治的理想镜像设置为银幕女体情欲的必然流向:《庐山恋》中清纯活泼的周筠爱上的是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的模范青年耿桦,《好事多磨》中典雅温婉的刘芳中意的是热心国防事业、刻苦钻研科学知识的优秀士兵沈志远,《快乐的单身汉》中苗条娟秀的丁玉洁爱上的是努力学习文化、积极研究电动锻打机的造船工人刘铁……许多反映当代历史的影片亦是如此:《天云山传奇》中的落难知识分子罗群虽然失去了宋薇但却有冯晴岚的爱慕与呵护,《牧马人》中的错打“右派”许灵钧拥有李秀芝的真心相随,《花园街五号》中真正的共产党员刘钊赢得了吕莎莎的一颗芳心……尽管同样是美女爱英雄的政治表述,但新时期电影与“十七年”电影在女体情欲的为何喷涌方面有着实质的差异。丁玉洁爱上刘铁是因为两人青梅竹马,李秀芝爱上许灵钧是因为他秉性的善良,吕莎莎爱上刘钊是因为自童年时便萌发的对大朋友的依恋,这些私人原因引导出的情爱使得新时期电影中的英雄镜像能够以个体男性的身份存在而不仅仅是被主导政治借用的空洞能指。在“十七年”电影中则连女体情欲的为何喷涌也被主导政治设定为英雄镜像对于民族国家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的公共贡献,伟大领袖所断言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在彼时银幕上得到了绝对精确的展演。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新时期主导政治对于银幕女体情欲的操控已经明显松弛,但基本方向的规约仍然存在,不管从哪个渠道入海都务必抵达英雄之海。
2.情欲展演中的政治残留物。新时期电影中的女体情欲展演比“十七年”电影更为自由、奔放,不过它依然没能完全清除政治的沉淀物。比如《甜蜜的事业》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爱情段落,唐招弟和田五宝躺在草地上畅想婚后生活,招弟很认真地表示要好好学习建四化,五宝闻此言论误以为招弟又不准备结婚了,招弟一脸甜蜜地说:“傻瓜,谁说结婚就不能学习了?”再然后,两人站起来欢快地转圈,你追我跑。在此于淑珍配唱的电影插曲响起:“并蒂的花儿竞相开放,比翼的鸟儿展翅飞翔,迎着那长征路上战斗的风雨,为祖国贡献出青春和力量。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这首插曲为画面中的情欲展演提供了完美的注释,即个人爱情要与四化建设融为一体,彼此互相促进、共荣共生。再比如《庐山恋》中的那个清晨,周筠和耿桦捉迷藏似的英文对话“I Iove my motherland,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在展演周筠对耿桦的好感的同时更展演了两人对祖国的深情表白,“爱人”与“爱国”、“庐山恋”与“恋庐山”被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尽管新时期电影不再如“十七年”电影那般时时处处保持着政治对女体情欲的升华引导,但是它依然在局部延续着经典社会主义的编码策略,依然需要以一个或者几个姿态醒目地标示出个体情欲的集体归宿。而当影片中个体情欲与国家、集体事业发生冲撞时,则必须舍弃“爱人”保全“爱国”,《归心似箭》、《沙鸥》等片中均有类似的关键场面,这些场面充分地凸显了主导政治所再三强调的“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烈爱慕应该排在第一位,两性之间的爱情只能是第二位的”。[4](P3)
总的来看,在新时期电影中源自女性个体生命的情欲初步具备了自足的合法性,它已不再被政治理性从自身所属的层次中生硬分离,但它依然被政治理性裁剪、重组和积极升华。就像枝叶自由舒展的绿色植物被修剪为精致盆景,就像天空自由绽放的烟花却被设置为有限的固定图案,尽管新时期的银幕女体情欲比及“十七年”拥有了相对色彩斑斓的呈现,但其“实然”与“本然”同样被改造成为表达主导政治意旨的“可然”与“必然”,此间政治参数的调整不过是依据主导政治的转型而做出的相应改变。“十七年”银幕女体的积极情欲展演曾经达成了高效意识形态效果,新时期则情况复杂。贺照田在《当代中国精神的深层构造》一文中指出,在“文革”这样的灾难和重大挫折之后,部分人群中的确弥漫着因狂信而虚无的社会精神状态,但在相当部分人群中,人应该对历史、对国家、民族、社会承担责任这一精神取向所构成的理想主义内核犹在。[5](P85)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犹强的精神局面,使得新时期初期银幕女体积极情欲中内嵌的“大他者”还能够对观众真正有所召唤而不致沦落为无效的政治摆设,并最终能够成功地将观众的利比多组织进新的政治文化建设中去。不过伴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展开,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浮出水面,整个社会的精神局面由崇尚理想渐转为崇尚务实,由此使得银幕女体积极情欲所能达成的意识形态效果也渐趋于低效。另一方面,新时期对“文革”电影的决绝否定和彻底批判在所难免地影响到了人们对“十七年”电影的评价,经典社会主义电影的一些惯用修辞和表达策略在不同程度上被“祛魅”,人们通常能够很轻松地辨认出赤裸裸的僵化“俗套”并自动拒绝其交际意图,这使得此际银幕女体积极情欲的建构必须不断吸收新的资源与技术才能完成自己承担的政治文化使命。
拥有半自律性生存空间的新时期电影,已经不再如“十七年”电影那般完整彻底地蜕变为主导政治的宣传工具,将女体情欲建构成新的政治文化工程也并不是所有影片的选择:对于侧重艺术探索的创作者而言,仅仅将情欲展演局限在政治表述的范围内不利于其进一步的文化阐释;对于渴求娱乐性的创作者而言,仅仅将情欲展演困囿于政治规划的区间内不利于其对大众趣味的投合。艺术片与娱乐片中的女体情欲展演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逾越了主导政治部署的既定轨道。当主导政治对电影的管理相对宽松时,这些越轨情欲便能得到从容的展演空间;当主导政治对电影的管理相对严厉时,这些越轨情欲往往会招致反复的批评、指责。(由于转型期的缘故,新时期的主导政治总是处于不断的松紧调整中。)在1980年到1983 年间爱情片一度泛滥,甚至到了不管什么题材、什么主题、是否需要一律塞进情欲展演的地步,这种泛滥引起了主导政治的重视并试图通过领导讲话、舆论引导来规范银幕情欲展演的具体标准,将所有展演重新统一到积极情欲的正轨之中。期间《亲缘》《白莲花》《幽谷恋歌》等影片中的越轨情欲展演成为错误典型,遭到了主导政治的大范围公开批评。此后,在电影界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银幕情欲展演又被主导政治再三整顿,积极情欲仍然是展演的正确方向。不过,新时期的运动性审查的威慑力和杀伤力都远逊于“十七年”时期,制度性审查更不用说,而新时期电影界对于脱离权威意旨、追逐艺术自主性的诉求则在不断增长,电影生产由计划经济的单轨制向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双轨制的转变所带来的市场压力亦不断加大,各种力量的消长使得积极情欲在具体影片中的露面愈来愈少,越到新时期后期则越是如此。
三、“大写”情欲:身体的意识形态
在新时期较早的影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存妮与小豹子带有浓重蛮荒气息的情欲展演是粗鲁而缺乏美感的,它有力地指称了人们处于贫穷封闭小山村中的愚昧状态,是该片进行社会政治批判的重要工具。而在新时期中后期的影片中,情况发生了翻转,赞美诗般的女体情欲展演开始成为主流,它们往往是个体生命颠覆封建伦理的大胆之举,是影片进行文化反思的重要工具。在《老井》中,巧英与旺泉再也抑制不住那蕴藏已久的奔涌情欲,两人热烈的拥抱、疯狂的亲吻叠映在滔滔黄河、巍巍太行的壮阔背景之上,再加上如歌如咏的激昂配乐,使得整个展演段落成为灵肉交融的赞美诗。在《湘女萧萧》中,萧萧快乐地牵着花狗走向磨房草丛中,然后是焦灼的激吻、愉悦的满足,镜头一转是随风轻摆的青草,郁郁葱葱的景致有力地衬托了美好的青春性爱。《红高粱》经典的“野合”段落中,我奶奶泪水满面,仰天缓缓倒下,被踩倒的高粱秆形成了一个圆形圣坛,我爷爷在一旁双膝跪下抬脸向天,然后是炫目阳光下红高粱狂舞的叠化镜头,高亢的唢呐声嘹亮响起……这些影片中女性身体的情欲展演几乎都是隆重推出的“大写”情欲,自然意象的铺陈、激昂配乐的辅助都是为了充分张扬“人”在情欲勃发时的旺盛生命力。如果在此对比一下“文革”电影中女性身体的国家主义展演,不难发现二者的展演方式竟然如此相似:自然风景、雄阔音乐、狂喜表情。虽同是浓烈的赞美诗般的“大写”情欲,但是展演方向却完全背反:一个是“最身体”的私我情欲展演,一个是“超身体”的国家主义情欲展演。或许,唯有前者才是能够彻底冲击后者的绝佳策略,一个神圣、崇高、浪漫的属己身体(刻意制造的纯粹自然,甚至有些只是诗意包装的“原始兽性”)才能战胜一个同样神圣、崇高、浪漫的属他身体(刻意制造的纯粹社会),一个同生活实存中一模一样的平凡、庸俗甚至有些许丑陋的身体显然没有力量,尤其是在新时期禁欲之风尚未完全扭转、人的精神尚在半空中高蹈的特殊语境中。
新时期电影大致经历了一个从直接揭露“文革”罪恶、遍数人民内心的伤痕,到对“文革”进行政治、道德维度的局部反思,再到追根溯源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反思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思想枷锁的发展历程。而诞生于新时期中后期的银幕女体“大写”情欲大都担负着反思民族文化的劣根性、重新再造国民性的热情的启蒙使命。谢飞、乌兰在《〈湘女萧萧〉创作随想》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比较自觉地将影片《萧萧》的创作同“再造民族灵魂”的使命联系在一起,将锋芒对准长久占据我们国民精神的“顺从天赋”,对准那毁灭人性、丧失自我的“群体无意识”,对准那个在愚昧、落后中原地踏步的“怪圈”,以期警世。”[6](P85)张艺谋同莫言一样有着“中国人活得太累”的感叹和“种的退化”的隐忧,企图借《红高粱》将生气勃勃的野性蛮力重新植入老朽民族的肌体之中。导演王进也直言《寡妇村》的主旨是“揭示封建婚姻习俗对人性的摧残”。[7](P6)这些影片或者以“大写”情欲被封建伦理的摧毁为悲剧,叹惋生命应有光彩的凋落;或者直接以“大写”情欲宣告“身体”的解放与胜利,高奏洒脱自由的华彩乐章。它们从正反两方面努力,对观众进行着一种被张英进定义为“身体的意识形态”的渗透:人应该毫不羞愧地直面自己的身体,按照自己最淳朴的天性生活,拒绝任何形式的灌输与压迫[8](P247);冀望以此彻底打碎人们头脑中那从两千多年来的“超稳定结构”中承继而来的思想枷锁。因此,这些影片虽然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的关于“个人”/“真人”的故事,却并非是纯粹的个体生命史的奇观,那些自由相好的男人和女人,“并非浪漫主义时代的遗世独立的个人,而是重构的民族神话中的中国的亚当与夏娃”[3](P47)。(民族内涵的注入,使得这些影片中的人物都是“大写”的人,或许这也是此间的女体情欲被“大写”的原因之一。)
必须看到银幕女体“大写情欲”所参与制造的“身体的意识形态”与新时期主导政治所推行的“思想解放”的轴心实践存在着深刻的共谋,即都有对尊重个体、张扬自我的强烈诉求,都致力于将人们从“文革”时期划一的生活方式和枯燥的思维方式分离出来、过一种活泼自由和更有创造性的生活。而这也是新时期电影中“大写情欲”能够得以生产的现实合法性依据。不过,两者高度的共谋并不能消除其内在的分歧。首先,在新时期中后期,主导政治的大方向转型已经尘埃落定,剩下的问题只是在新方向上如何前进,它已不再像前期那般迫切地需要进行“大转型”的自我合法性论证。而银幕女体的“大写”情欲将剑锋直接对向民族文化本身,不停地挖掘民族的劣根性,显然有间接通向“全盘西化”之虞,不利于建构观众的民族认同感,不利于主导政治在“大破”之后的“新立”,不能为四化建设制造积极的动员力量。在《湘女萧萧》的北京座谈会上便曾有人指出:“今年电影创作在注重反思历史时有偏执一端之弊,只强调揭示劣根性,对人性、社会中的善和美挖掘不够;如果我们民族没有向上的力量,岂能有今日?”[9](P19)其次,也是最为关键的,“身体的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个体的自由伦理,尽管它还有着人民伦理的外层诉求,但其内层叙事却在瓦解人民伦理的合法性,因为若要自由伸展个体的生命感觉便不会顾及来自人民伦理的动员与规范。“身体”还原回它的原始本初,身体只担当“身体” 的意象,这种完全自我的话语方式在颠覆凝固的封建思想、在颠覆“文革”同一暴政的同时,也在颠覆经典的社会主义理想与集体主义价值观,而这对于仍然试图维持经典社会主义的生产伦理的新时期主导政治(不管其怎样调整这一面向的诉求始终存在,也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言无疑是一种重大伤害。再次,新时期主导政治依然保持着对于银幕女体情欲之镜像功能的监管,担忧性爱在银幕上的过分展演会在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心灵上造成可怕的精神污染。贺敬之在1987 年3月2 日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明确指出:“我们不否认,现在的人们封建意识还是有的,这也表现在性的观念上,因此我们并不简单反对禁止在创作上做一定的试验,但完全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去年,我在广州时讲过,创作中不排斥表现两性关系,这类作品也有好的例子。但这毕竟不能在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精神生活里占主导地位,不能让弗洛伊德的泛性欲主义占据人们的心灵,那样的后果是严重的,对青少年的戕害尤其严重。”[10](P13)
不管银幕女体的“大写”情欲与主导政治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共谋又有怎样的冲突,它的崇尚自由生命其实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真切存在的时代无意识。伴随着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彼时中国渐被松绑的人们正充满了对自由甚至是狂浪自由的渴望、对自我甚至是绝对自我的扩展诉求,银幕“大写”情欲正为广大观众提供了“想象性的超越社会、超越文化、超越权力的欲望满足”,[11](P275)成功完成了其“身体的意识形态”的播撒。只是这种播撒保护、支持和强化的乃是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及相关结构,它所成功询唤的情感主体/ 政治主体是原子式的个体,而非共同体中的坚定一员。
注释:
①1979 年第5 期《大众电影》在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接吻剧照,结果一位新疆读者用异常激烈的言辞写了一封批判信,责问编辑部“你们在干什么???”。《大众电影》随后全文刊发了这位读者的来信,随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编辑部一共收到了一万余封来信,赞同该读者观点仅是少数。这充分表明了广大观众对于奔放情欲展演“久旱逢甘霖”后的衷心欢迎。《甜蜜的事业》《庐山恋》等设置了动人情欲展演的影片所引起的全国性轰动也有力的论证了这一点。
标签:政治论文;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论文; 庐山恋论文; 红高粱论文; 爱情论文; 剧情片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