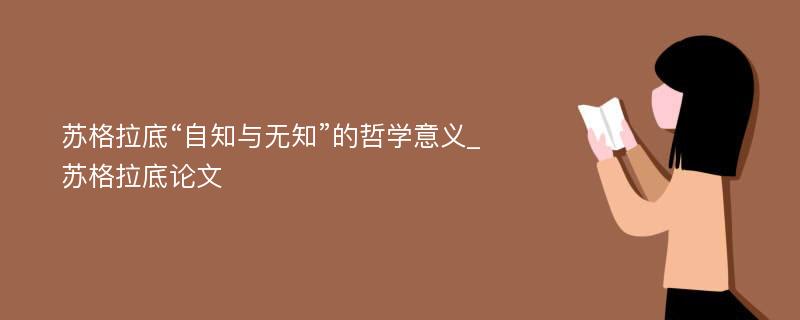
苏格拉底“自知无知”的哲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格拉底论文,无知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格拉底早慧,自从他还是“青年苏格拉底”起,他的超凡心智就为各国著名访问学者和国内哲学界看好。但是按照《申辩》中所暗示的,使苏格拉底享有“智慧”之名的智慧未必一直就是“自知无知”。当苏格拉底年届中年,“智慧”之名在雅典如日中天之时,一次“德尔菲事件”将他从自满中唤醒,令他过渡到这种“反思批判”类的智慧。这次事件的要旨是,那位以“认识自己”(自知)为训令的阿波罗神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加智慧了。这一能够让多少缺乏自知习惯的教条主义者无比骄傲、自豪、自信的神谕却让苏格拉底顿时感到迷惘,自信心全面崩溃,陷入痛苦之中年危机。在经历了紧张的思索、证伪实验和参悟之后,苏格拉底终于实现了他的“批判哲学转向”,从此他整个身心投入揭露人类的智慧等于无知、不含有真理之知的工作中去,直至最后开罪于众,招致杀身之祸。
柏拉图无废笔。纵观柏拉图的记载,苏格拉底的“夫子自道”构成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的一个浓墨重彩的写照。无论是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还是中期对话中,经常有人打断对话的流程而专门“批评”苏格拉底的这一否定性思维方式,数落他热心的就是把一切肯定的知识都加以推翻,却不肯定任何东西。大多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话录都是没有结果的;即使那些看上去“肯定性”的对话,也笼罩着一股“反讽”意味,使人不敢相信里面在宣布绝对真理。“自知无知”的批判性意识并不是枝节的、偶然的点缀,而是渗透在苏格拉底的所有思考之中,构成了他使命般地虔诚投入、并最后为此而被处死的事业。所以,这应当是解开苏格拉底哲学奥秘的一个关键。
一、一个个案:“拉刻斯”
苏格拉底“中年变法”之后是怎样进行他的说服大家“自知无知”的哲学使命的呢?让我们先从所谓“苏格拉底对话录”中选取一篇《拉刻斯》看看。
话说有些雅典公民找到了著名的雅典将军尼昔阿斯和拉刻斯,请教他们如何教育孩子、使他们获得美德——比如说:观看重装兵操演是否是一个好办法?两位将军推荐自己的好友苏格拉底(当时大约45岁左右)加以教诲。苏格拉底说:要想知道应该如何培养孩子的美德,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美德,如果连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是不可能找到实现美德的最好办法的。观看重装兵操演,应当是要学习“勇敢”这种美德;那么,什么是勇敢?
拉刻斯说:能够在作战中坚守阵地的人就是勇敢的人。但苏格拉底马上质疑说,那么追击敌人的人是不是勇敢的人呢?并指出,我所问的勇敢不是限于某种特殊情形下的勇敢,而是能够包括所有这些情形的共同的勇敢,不仅是抵制痛苦和害怕时的勇敢,也包括抵制欲望和快乐时的勇敢。于是,拉刻斯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定义:勇敢是灵魂的一种忍耐。苏格拉底却又反驳这一定义说:愚蠢的忍耐就不是勇敢,因为勇敢是高尚的,好的,而愚蠢的忍耐则是坏的,有害的。拉刻斯只好承认:只有聪明的忍耐才是勇敢。这似乎走向了苏格拉底喜欢的“知识德性论”,但苏格拉底依旧反驳说:一个精于算计而预知了自己能够完胜的人,当然“无所畏惧”,轻易忍耐;但是,一个对自己的胜算没有充分了解人如果也能坚强忍耐,他显然更为勇敢。
拉刻斯沉默了。苏格拉底建议说:也许我们应当请尼昔阿斯救我们脱离困境?尼昔阿斯发言从苏格拉底常说的“一个人的好在于他的智慧”这句话出发,认为,如果勇敢的人是好的,那么他也是智慧的,因此勇敢是一种智慧。苏格拉底打断他:这是什么智慧?总不会是关于弹琴的智慧?尼昔阿斯说,当然不是,是一种能在战争或其他事情中激起恐惧或自信的知识。拉刻斯插嘴反驳说,勇敢是一回事,智慧是一回事;农夫、艺人、医生最懂得自身领域内的危险,他们最具有激起恐惧与自信的知识,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更勇敢。但尼昔阿斯不认可这一挑战,说:医生只知道疾病和健康的知识,并不知道一个人患了病以后最好是活着还是死去,并不知道关于害怕和希望的理由的知识。苏格拉底对尼昔阿斯的这个观点作了总结:勇敢是关于希望和害怕之理由的知识,并非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知识,而没有这种知识就不可能勇敢。
讨论至此,看上去已经很美好了。但是,此时苏格拉底又提出了疑问:“可怕的”乃是关于将来的恶,“可期望的”乃是关于将来的善。如果勇敢是关于可怕与希望的知识,那么它就是关于将来善与恶的知识;但是没有一门知识是只关于将来的,任何关于事物的知识都包括它的现在、过去、和将来。因此勇敢必定是关于所有善恶的知识;但是如果一个人知道所有的善恶,他必定是完美无缺,拥有包括正义、虔诚、节制在内的所有美德。如果这样,勇敢就不是美德的一部分,而是全部美德了。但是这与我们的预设又是矛盾的。
结论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勇敢”。
二、意识在自我否定中觉醒
《拉刻斯》是一个典型,许多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话的结构都是如此。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的“自知自己无知”体现出了一种主观意识的强烈的自我反思精神。“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是苏格拉底的名言。这个意识的自我反思包含了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意识的自我决定原则。黑格尔敏锐地看到了在此出现了人类精神发展历史上的新环节。他称之为“主观自由的原则”。(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3页。)对于苏格拉底,一切权威和原则,都必须经过独立的个体意识的严格审查,才能获得肯定或否定。也就是说意识自身要求自主地决定一切观念和原则的合法性。
在人类精神的发展史上,意识的觉醒不仅只是发生在苏格拉底身上。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大约总会有这样的领悟者出现。但是他们大多被人淡忘了。也许有几个要素促成了苏格拉底成为代表这一环节的西方思想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中的标志性人物。第一,是他的使命感导致的热诚。他把这当作神圣使命,当作理性之神阿波罗(这不是一位“新神”)的命令。在“神”是人所坚信不移的最后依据的意义上,苏格拉底对主体意识的推崇乃是在人类精神史上引入了“新神”;第二,是他的充沛的意识力量和因此而来的极端化推导——直至不惜为之献身(事实上,许多现代学者指出苏格拉底在“申辩”中的表现似乎更像是在故意冒犯大众,招致直接冲撞和自我毁灭——为了震醒人的良知);第三,是有一个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重大意义并拥有精彩绝伦的文笔力量把这一切都富有魅力地记下来的柏拉图。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里觉醒的是意识。苏格拉底并不是在直接怀疑x(原则、德性等等),他是在质疑是否有人能够“认识(知道)x”。所以这是反思;所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十分关注人类的各种知识能力:修辞,技艺,经验,理智,实践理性……等等。追问它们各自包含多少真理?它们能否教授?对理性的极端关注使得尼采斥责苏格拉底是理性疯子。正因为苏格拉底的意识力量的充沛和强大,它呈现出一种显得悖论式的自我否定冲力。黑格尔说过,对个体意识合法性的肯定和高扬并非始自苏格拉底,而是始自持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立场的智者。然而,智者对个体意识的推崇当真像是在“引入新神”了,他们将其奉为神圣:“我认为真理就是像我所显现的那个样子,即我们每个人都是存在或不存在的尺度”。(注:普罗泰格拉残篇,见苗立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82页。)意识并不反思自身,而是无条件地肯定自身的合理性。苏格拉底与此相反,他并不偶像化个体意识;审查的火力毋宁说恰恰首先对着自己,是自我审查,其结果常常是推翻自身原有观念的合法性。
在《拉刻斯》等苏格拉底对话中,各种意识通过不同的对话者口中说出,一一受到严格的审查和否定。实际上,这一意识的不断自我否定的强大火力扫描还放大地体现在苏格拉底的一生心智所不断经历的“范式”性突破上。他几乎是所有希腊哲学家中唯一经历多次“转向”的人,他不害怕否定自己。前面说道:“自知无知”的批判哲学转向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向。但是人们应当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苏格拉底就已经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向了。(注:泰勒提醒我们注意苏格拉底的整个人生历程。参看A.E.泰勒、Th.龚柏茨:《苏格拉底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0页。)根据《菲多》的记载,苏格拉底在青年时期应当有过一次“目的论/理型论转向”。这对于他后来的思考方式具有很大的影响。苏格拉底青年时期正是雅典的鼎盛年代,他与许多时人一样,热心于传入不久的自然哲学。但是他的意识中的不满足冲动很快让他走到别人的前面:他感到自然哲学中盛行的还原论的因果观不能很好地解释世界,转而考虑“目的论”的模式。而这种目的论如果不陷入简单的外在目的论,必然会走向某种“理型论”的思路。(注:参看Plato's Phaido,edited by John Burnet,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1953,96aff.)但是根据《巴门尼德》的记载,大约在苏格拉底30多岁时,访问雅典的巴门尼德和芝诺已经用严密的论证推动苏格拉底反思“理型论”中可能蕴涵的种种问题,从而考虑某种“通种”转向了。大约35-40岁左右,苏格拉底为雅典国运的衰退和内政中私心的异常爆发所震惊。雅典人“专注于尽量积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而智者更是对此推波助澜。感到震动的苏格拉底将精力转移到伦理学上,关心人的德性和美好生活的本质,这不妨说是苏格拉底的“人文学转向”。最后,就是他在希腊人所说的“鼎盛年”完成了中年变法,实行了批判哲学转向。因为他是在将自己的思考推广到民众当中,四处出击当牛虻,说服大家承认自己在根本价值观上的无知,因此这次转向也可以称为他的“政治哲学转向”。
所有这些转向,都不仅仅是否定性的。它不仅体现了意识的破坏性,更体现了意识的自主力量。意识的自我决定与自我否定是意识自身变革的两面,一方面,没有意识的自我决定就不可能最终产生意识的自我否定,而没有意识最初的自我否定,它就只能停留在原初的不自觉状态,也不可能产生自我决定的意识。二者同时产生,互为前提。
三、普遍性与特殊性
意识的肯定与否定的紧密结合表现在对对立面的注意上。苏格拉底的自我否定意识并非全部都来自发现了意识中的对立面,但是确实有不少是如此。而他又并不因此就抛弃原有立场,完全接受对立面,这使得他的意识非常复杂,在各种对立面之间紧张地摆动。其中,一对具有典型意义的重要对立面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
苏格拉底的自我否定并非仅仅只是“摧毁性”的,并非只是对个体性的肯定。在这种意识的自我否定中可以辨识出肯定的、积极的东西。这首先恰恰是对“普遍性”的追求。
在《拉刻斯》的一开始,苏格拉底就把“勇敢”的含义限定在了某种普遍性的行动本质上,抛弃了勇敢在具体情形中的特殊性和偶然性。这一点可以说是整个苏格拉底道德反思的普遍特征,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苏格拉底的“伦理学贡献”:使用归纳推理。归纳推理正是苏格拉底扬弃认知对象之个别性上升到普遍性的主要手段,普遍定义则是苏格拉底式的追问的起点和目标。在苏格拉底的谈话中,可以经常看到苏格拉底反复纠正对方将个别道德行为和现象等同于一般的道德品质的做法,强调自己所要追寻的乃是存在于所有同类的个别道德行为中的决定个别行为之道德品质的一般性。这个一般性就是苏格拉底所探索的事物“是什么”的内涵。它决不因个别对象、具体环境或认知主体的变化而变化,它就其自身而言具有绝对性。所以,所谓柏拉图的“理型”意识,在苏格拉底那里就已经有了端倪。从认识论上讲,这是为了反对流变,确立知识对象的实在性和知识的可靠性。自赫拉克利特提出“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的观点以后,至克拉底鲁发展成极端流变主义,不承认事物自身存在的同一性,因而否认认识的可能性。这是苏格拉底坚决反对的,他坚信有真正的美、真正的善这样不变的东西,这些不变的事物正是知识之作为知识的真正的认识对象,它是实在的、确定的;始终能维持固有的本质,保持与自身的同一性和普遍性。知识的可靠性也正来源于此。
从这样的普遍性思维向前走,逻辑的终点应当走向巴门尼德式的“越普遍”等于“越具有真理性”,最终导向肯定唯有最普遍的“一”,而否定一切“多”。众所周知,巴门尼德也是由于反对赫拉克立特而强调真理之路应该远离“众人的经验习惯……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和舌头。”于是乎,普遍性成为真理的唯一内涵和标准。除了那个最抽象的“存在=一”之外,一切可能含有否定因素的“多”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显然没有昂首踏上巴门尼德的“真理之路”。他意识到在“一切皆一”的极端点上,巴门尼德与混淆一切的智者又殊途同归了。所以苏格拉底坚持“多”。“理型”正是“多”。在《拉刻斯》中,苏格拉底让拉刻斯说出勇敢与知识的关联。“知识德性论”实际上是典型的苏格拉底的立场。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满足这种一般立场,他立即追问是“哪一种”知识。并非所有的知识都能促进勇敢,有的时候它们恰恰是矛盾的。勇敢必定涉及到知识,但这种知识又有别于其他知识。我们看到,苏格拉底不仅指出勇敢是一种智慧,而且为它限定了范围:关于恐惧和自信的知识。而拉刻斯的两次反驳更加明确了此类知识与其他知识的区别:它并非是像技艺那样关于事物本身的知识,而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害怕或希望的知识。这是关于哪种行动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善的)的知识。
这种对“特殊性”的重视并非偶然。在苏格拉底对知识的理解和界定中,“普遍性”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则;与此相对应的,具有同等重要性却常常为研究者所忽略的另一个重要原则——知识的专业化或特殊化原则,在苏格拉底这里也已经被明确地表达出来即:知识必定是相关于事物的类的特殊性的,因而拥有知识必定是拥有对某种事物特殊性质的认识;就知识的对象而言,它承认每一种事物都具有作为其自身的特殊性,因而承认各种事物的内在差异性,由此导致知识的分类原则;就知识的主体而言,它主张只有经过学习和研究并充分掌握了对象的特殊性质的人才是该类事物知识的真正的掌握者,因而反对在知识问题上尤其是在涉及到知识的发言权和依赖于知识的行动权上实行平等主义和多数原则,由此导致知识的分工原则。分类原则和分工原则构成了苏格拉底知识特殊化原则的两个主要方面,它们的共同前提是承认知识对象存在的特殊性。认识特殊性就是掌握知识,特殊性作为知识的内容反而成为本质,普遍性则变成了无差异性的空洞的东西。
但是,当苏格拉底坚持特殊性,反对普遍性,坚持“多”,反对“一”时,他又在时刻注意反面意见,倾听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合法性要求了。柏拉图的对话录《巴门尼德》一般来说被看作是在讲本体论。但是我们知道对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本体论与政治哲学无法分开。他们之所以多次批判感性事物尤其身体,高扬心智,不仅是因为身体在认识论上的障碍效应,而且是因为它们是私心的根源,因为身体的特点就是相互不通——不能共通。心智则相反,是可以共通的。斯特劳斯在评说《理想国》时说:典型的“私”是身体,典型的“共通”是心灵——当然是纯粹心智。(注:参看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Rand McNally & Company,1964,p.115.)在《巴门尼德》的开头,巴门尼德对坚持“多”而且互不相通的苏格拉底“理型论”提出了几种批判,如“分有说”的困难,“第三人”的困难等等。归纳其要旨,我们不妨把其中的政治哲学涵义揭示为:如果理型世界也是各自坚守自己的领域、互不相通,宛如个体,(注:参看Parmenides,129b-e,131a.注意亚里士多德论“个体”与其他范畴的区别就在于不能“通”或表述其他个体。)那么就会出现物体界一身体界的政治中的典型私人现象。实际上,对理型的“分有”将显出“撕扯”、争斗、破裂、最终无法大家分享的零和博弈结果。提出理型世界,本应当是要为现象界做个好榜样,让它们“模仿”,怎么反而倒过来模仿身体世界的行为方式了?可以看到,在《巴门尼德》的第二部分,“苏格拉底”虚心接受了巴门尼德的意见,认真考虑了理型“相通”的一些可能方式。应当说,苏格拉底的思考总是在主体之间的“对话”进行,而不是像古代怀疑派或近代不可知论那样仅仅依靠“内省”,这就意味着他总是希望能从观念的差异中抽取出某种初步的共识,使意识的自我决定和自我否定尽量摆脱特殊性和偶然性,具有某种兼顾,具有某种普遍的有效性。
四、“厌恶论辨”还是不断追求善
在所有的对立面思考中,苏格拉底最关注的是追求“善”的知识。“中年变法”后的苏格拉底,所讲的自己的“无知”以及他的同胞们的“无知”主要指我们缺乏能够帮助我们的灵魂获得完善的价值知识——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好,什么是优秀,什么是德性。这是根本性的知识。如果人们在根本价值观上自满,认为自己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具有充分的知识,那么道德的和政治的实践改善就从根本上没有可能。所以,苏格拉底“自知无知”的主要工作就是试图震醒人们对现有价值体系的牢固的心满意足。对善的追求也充斥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来回辨证。
一方面,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柏拉图认真尝试在“普遍性”上规定“善”。在《普罗泰格拉》中,甚至提出了一个用“快乐”量度一切善的功利主义“技艺”模式。有人或以为这太粗鄙,太量化,不可能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真意。但是作为主体意识不休止的尝试之一,有什么不可能?更何况柏拉图思维中,数学占据重要地位(想想莱布尼茨对用“普遍算术”解决道德问题的可能性考虑),寻找一个能够像数学量度那样普遍的、公共的、共相的、超出特殊性的、精确解决问题的“德性技艺”,完全可能进入他的思考视野。(注:有关讨论可以参看Martha Nussbaum,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89ff.)
另一方面,《普罗泰格拉》并没有肯定性的结论,毋宁说以“一切都颠倒了”而结束。在《菲立布》中,我们看到思想的天平又摆向“多”、特殊性、不可通约性。在那篇对话中提出了5种“好”(善):尺度,比率,智慧,技艺,纯粹快乐。而且,最后的结论依然是不确定的。或许,苏格拉底是要在对立面中寻找某种“综合”?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就不仅揭示了不同美德之间的差异,而且揭示了它们背后更深层次的统一性,那就是无论哪一种美德都来源于理智统治下心灵的三个组成部分(理智,激情,欲望)的协调,没有任何一种美德可以孤立存在。然而,换个角度看,《理想国》是一部宣布绝对真理的对话录吗?书中对于“善”的“太阳比喻”不是语焉不详吗?“自知无知”没有在其中发挥作用吗?“早期苏格拉底对话”没有最后结论,“后期肯定性对话”难道就有吗?苏格拉底总是在认真听取对立面的意见,他会尽量综合它们,同时在最后他又不会忘记用“没有结果”或“摧毁一切”的极端化方式提醒人们:综合并没有“完成”,绝对真理远远没有被把握。
这样无休止的“自知无知”会让人厌倦或者陷入“厌恶论辨”(mislogoi)——对知识探求本身陷入悲观绝望。这是“苏格拉底智慧”的本意吗?实际上,后来的“柏拉图中学园”就宣布自己的怀疑论哲学继承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真谛”:证伪一切可以提出来的命题,从而证明追求事物“本质”的哲学是一种根本上不可能的事业。然而苏格拉底在《菲多》中苦心孤旨地告诫追随者:我们不应当因为意识所呈现出的辨证性而陷入“厌恶论辨”的境地,因为自己的坚固信念被摧毁而走向反面极端,从此对一切论证和信念都加以拒斥。(注:Plato' Phaedo,89d.)
事实上,坠入绝望者往往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多是思想的和行动的懒人。许多人习惯于批判苏格拉底/柏拉图是“乌托邦”,但是细读对话录,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处处为乌托邦式思维埋下解药,他们知道要在“洞穴”中考虑政治,他们并没有主张巴门尼德式的“大同”(绝对相通的“一”)。“自知无知”并非简单的“假谦虚”(“irony”的原义),而是明白真的有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比如德性能教吗?《理想国》给出了那么完美的教育法,苏格拉底一生在孜孜不倦地教诲学生,但是他的最亲密学生中不是就有品德败坏的政治家吗?
面对我们伦理实践的真正困难性,避免堕入普遍讽刺或者悲观主义或者乌托邦认真的方式,可能正是清醒认识到我们的现有价值观和价值“新知”都与真理有距离,从而保持对善和美好生活的永远探索的心态。而这,正是“自知无知”的真实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