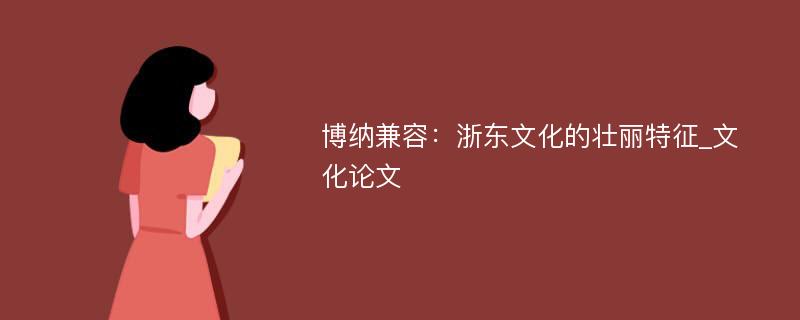
博纳兼容:浙东文化的恢宏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东论文,品格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24(2000)02-0001-05
浙东文化虽然衍展于浙东地域,但它却多元并茂,五彩斑斓,不象是或者说根本不是一种高纯度的本土文化,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在于它所具有的开放性运作机制,在于这种机制下逐步形成的海纳百川的开放态势和对待异体文化的应变能力,一句话:在于它博纳兼容的恢宏品格。
一、浙东文化的主体结构:兼容并茂
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变迁,不外乎有两个主要因素在发生作用: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
浙东文化之所以具有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势,首先在于浙东特殊的地缘条件。浙东背陆面海,伸向陆域的腹地并没有天然屏障的阻隔,而港口位置的优越和造船业的发达,又洞开着海上的门户。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浙东历来易于成为各种文化的登陆点和接收点,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其次,外部社会结构的变迁(包括政治、经济、战争、文化、人口等)也深刻地影响着浙东地域的对外开放,而且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呈现不同的开放特征。东汉以前,浙东社会结构单一,经济开发水平低下,导致文化的单调落后。东汉以来,浙东对外交往的频率相对提高,越人与汉人不断融合,促进了浙东从一个保持自身原始内涵的地域文化向与先进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同构的区域性文化的历史转型。这一转型的最重大的收获,就是播迁于浙东的北来士族移植了中原文明。他们主要聚居于山阴、上虞、余姚一带。但是,由于文化活动往往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因而北方文化在浙东的展开幅度并不是很大。而且汉唐时期浙东文化现象又与中国政治变动密切相关。晋室南迁,浙东地区聚居了大批文化士族,曾极一时之盛,然而随着浙东地域政治力量的绷紧,给予了文化士族以致命的打击,再加上继而中国政治中心北归,儒家文化对浙东地域的影响更加减弱。因此,汉唐时期,中原儒家文化对浙东地域的冲击强度是有限度的,浙东对北方儒家文化的接纳也仅仅是初步的,儒家文化始终未能深入人心,占据主导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浙东地区(尤其是明州、台州等地)所受的礼教桎梏比中原要轻些,表现在文化个性上,比中原地区要开放、自由和活跃一些。由于儒家文化的有限侵入未能使浙东民众获得普遍的启蒙,因而导致浙东在没有经过多少文化抵抗的情景下顺利地接纳了异质文化——佛教。当然,佛教从海路之所以能够传入浙东,并获得迅速的传播,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在浙东经济的剧烈分化和时代的动荡中,满足了地域主体对精神渴求的强烈需要。佛教劝人向善的教义,可以作为稳定地域社会的重要支柱,民众对佛教的信仰,也是平民在痛感自身缺乏保护、依靠和关怀时力求自保的一种精神姿态。于是佛教文化迅速占领了儒家文化由于有限传入而预留的真空,跃居为浙东地区的主流文化并渗透到每一个角落。隋代高僧智顗创立的天台宗,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最早的宗派。佛教文化与浙东原有的古越神巫文化、仙道文化合力作用,从而塑造了地域主体重神秘、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
约从唐代中叶开始,以丝绸、瓷器、造船为代表的手工业生产崛起江南,再加上浙东物产丰饶,水运畅通,因此浙东商业经济愈益发达,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海洋性。明州港在唐代就开始对外开放,从明州港出口的越窑青瓷成为我国进入国际贸易市场的最大宗商品。明代中叶以后,浙东地区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机户”和“包买商”,双屿港还成为16世纪中国最大的国际走私贸易港。由于浙东人多地少,且偏于一隅,为开拓生存空间,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形成了强烈的向外发展的冲动,于是相继出现了宁波商帮、绍兴师爷等职业群体。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中,浙东形成了比较浓厚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其显著特点是讲究实际,注重功利,重视工商,不尚空谈,这有助于得风气之先并形成开放型、创新型的思维模式。
有了一定的经济发展之基础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浙东学术文化究其实质,就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开放性的观念形态。浙东人重视实事实功,浙东学术强调义利合一,理欲相容。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就提出“功利与仁义并存”,陈亮提出“义利双行”,并肯定了人的欲望具有天然合理性,其批判锋芒直指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儒家正统思想。四明心学派的袁燮、杨简都很重视经济。明代的王阳明对商人予以相当的同情。甚至有人认为,在吴越文化的代表人物王阳明身上具有经济文化的特点。阳明后学则更有人提出“理在欲中”的思想。到了清初,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黄宗羲直呼“工商皆本”的口号,实在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地域经济文化的历史渊源。
浙东文化尽管包罗万象,但其主体是:宗教文化、商业文化和学术文化,这三者构成了浙东文化的三驾马车,民间的、世俗的与精英的马车并辔而驰,又相互涵摄,每一驾马车又往往涵载着相异的内容,并各自构成一个文化丛。如此组成了浙东传统文化多层面的丰富内容,予人以多元并茂、色彩斑斓的直观印象。
二、浙东学人的知识结构:博闻贯穿
积淀于民众社会实践生活中的文化精神,如果没有学者的提炼概括,很难跃升到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地域文化由自在走向自觉,由散漫走向独立,由低俗走向深度的精神体验,还必须靠学术来涵养,于是浙东文化的建构,最终会落实到地域精英的身上。这样,浙东学者的知识结构,也就会直接影响着文化创造的强度、高度和开放度。
知识结构是各种知识在人类大脑中的组织方式。知识的组织方式在理想状态下应该是纵横交错、井然有序的网络结构,因为支离破碎的知识很难提供一个创造性思维的广阔空间。浙东的学者历来以孤陋寡闻为耻,于是“博闻贯穿”就成为地域精英群体共同追求的目标。
浙东学者善于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知识,不断地充实自己。早在东汉,王充就博采古今,广泛地汲取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及自然科学知识,成为东汉最渊博的学者之一。“风光八朝”的余姚虞氏家族中的虞翻、虞喜、虞世南,均以博洽旁通闻名当世。南宋时代,“博闻贯穿”逐步形成为浙东的优良学风,只要翻阅一下楼钥《攻媿集》中的浙东人物传记,就不难发现浙东博学之士鳞接栉比,如王伯痒“贯穿经史,旁出入百氏”,楼弆“勤百氏之言,无不该贯”,赵善誉“考求世故,贯穿今古”,高元之“自天文、地理、稗官小说、阴阳方伎、种艺之书靡不究极”,宋晋“贯穿百家”,周之卿“博贯经史”。若再论博学名流,可以推出楼钥、程迥、王柏等,至于吕祖谦、王应麟则更是人所共知的博学大师。
明代士大夫束书不观、空谈心性是普遍的现象,从而造成明代学术的空疏。受这种时代氛围的影响,浙东学者追求通博的风气有所削弱,上不如南宋,下不如清代,但相对于当代而言,博闻贯穿之士还是迭有涌现。如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博及群书,于学无所不能,其弟子方孝孺,“凡理学渊源之统,人文绝续之寄,盛衰几微之载,名物度数之变”,无不通晓[1];杨守栋博求广取,实事求是;特别是胡应麟,为公认的学问精博的文献学大师。
清代的浙东学者勤学苦读,兼收并蓄,对知识的网罗之广,令人叹为观止。他们的知识结构网络之完善,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境界。浙东学派的鼻祖黄宗羲,“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为“自来儒林所未有”。其得意门生万斯同博闻强识,尤长于史,“自西汉以来,数千年之制度沿革,人物出处,洞然腹笥”。私淑黄氏的全祖望,兼有经学、史学、辞章之长,“其学渊博无涯,于书靡不穿贯”。至于邵廷采、章学诚、黄氏三父子、平步青、李慈铭等学者,虽学术成就高低不齐,但无不以兼综博学见长。
以上列举的众多事实,足以说明浙东学者知识结构蕴蓄富有的开放性向度,如果细加解剖,我们还可进一步发现:
1、浙东学者的知识结构往往是跨学科的。学科之间的互动、渗透和重构,实际上体现着认识向更高层次的迈进。浙东学人的博采虽以经史之学为重点,但又能兼涉人文学科的各个分支,同时也涉足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天文、地理、历算、水利之学。
2、浙东学者的知识结构往往是跨门户的。浙东学者对“门户”最为厌恶,明代黄尊素曾说:“门户二字,伎院名也。……今者国家动称门户,以此诱人,以此傍人,亦以此攻人,恐此二字与国运终始。”[2]浙东学者最反对门户之见,也最不守门户之见,他们多能平视各家各派,不私一说,不名一师,务求真旨,为我所用。所以浙东学者能够并蓄汉宋精华,淹取朱陆之长,也能折衷儒佛,兼探百家。正因为浙东学者超越门户,不存宿见,所以能够成功地进入前辈学术大师的创造性天地,充满兴趣地去探索他们的理论底蕴,感受他们对宇宙、对人生的观察与思索,从中汲取有益的汁液,获取宽广的思路和创造的张力。
知识结构的博闻贯穿这种开放模式获得的逻辑张力,不仅为创造提供出一个产生新知识的思维空间,而且也为浙东学术的兼综整合,提供了主体一方的内在条件。
三、浙东学术的独特风格:兼综整合
任何一种群体文化,一方面有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惰性,而且,对不同的群体文化存在着排斥的倾向,往往由此形成文化的冲突。另一方面,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具有融合吸收不同文化中有利东西的倾向,并且不断有着文化的整合。作为群体文化一种,浙东文化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浙东地域是一块文化相融的沃土,多元兼容的格局促使其更多的表现为后者而不是前者。特别是作为浙东文化最精致形态的浙东学术,其构建者是一群具有开放式高知识结构的地域精英,其知识的逻辑张力渗入潜意识的本能深处,往往积淀为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从而成为激活创造潜能的巨大力量,同时也为兼综整合提供了可能。又因浙东地域狭小,仅靠自身的努力无法达到构建学术的日的,客观上也必须借采它山之石来攻铸自家新玉。因此,浙东学术就其主流的变迁而言,实质上是整合型的高级文化形态。文化的整合,不是不同文化特质、文化因素等等之间的机械组合,而是在新的基础上的有机构成,文化的整合,往往意味着某种新质文化的产生,至少意味着原有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文化的分化与整合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和趋势,也是文化区域运动变迁的基本形式。但具体到浙东地域,文化的整合远比分化来得典型,越到后来,文化的一次又一次整合运动越是构成了浙东学术不断延续的发展序列,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文化的整合又具有不同的特点。我们不妨从文化整合的视角粗略地勾勒一下浙东学术不同历史阶段的运演过程:
(一)文化区域草昧时期的整合融流。汉唐时期,浙东学术未成体系,总的说来表现出“移植型”的特征。凡是学术上有贡献的浙东人,多为北方移民及其后裔,学术掌握在少数文化家族和僧侣手里,学术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驳杂和断裂现象。所以我们只能认为这一时期浙东有区域文化,但决不可以说浙东已形成了文化区域。即便如此,应该肯定的是汉唐时期的浙东学术,已初具善于吸纳整合的风格特征。最为典型的是王充和智顗。王充广泛地吸收了先秦以来各家的思想及自然科学知识,将朴素唯物主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隋朝的智顗是位杰出的宗教理论家,他既兼容并蓄,承认各种佛教流派的合理性,同时又以圆照的方式对印度佛教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中国式佛教,从而创立了第一个中国佛教流派——天台宗。
(二)文化区域自立时期的整合融流。文化独立是地域文化自立的重要标志,而文化独立的最核心的表现乃是学术的独立。引发浙东文化区域自立有两大原因:一是儒学的地域化进程波及浙东,明州杨杜五子和永嘉九先生率先切入了“新儒学”的文化精髓。与汉唐时期的“移植”有所不同,北宋地域精英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借采。在文化的借采过程中,任何一种被借采的文化模式都有可能被借采主体重新整合。由于明州杨杜五子和永嘉九先生所面对的是高元文化,消化和吸纳是主要任务,还无力进行整合。但是,他们的借采工作,使儒学在浙东地域的隐性存在转换为显性凸现,从而动摇了浙东佛教的“霸权”地位。二是宋室南迁带来的历史机遇。北方文化人大量涌入浙东安营扎寨,使得浙东人文骤盛,名冠全国,出现了世所罕见的文化繁荣景象。其突出标志是以地域命名,在全国范围内素有声望的学术共同体——浙东学派(包括“四明学派”、“永嘉学派”、“金华学派”和“永康学派”)正式成型。浙东学术一旦自立,文化区域也就正式形成。其时浙东学术虽然属于多中心的合成体,但粗略地看,又可分为心学和事功学两大系,心学一系以四明为大本营,注重主体的自觉,是致力于向内开掘的“内圣型”经世理论;事功一系强调实事实功和经世致用,是崇尚功利的“外王型”经世理论。浙东四派各有宗旨,又不同程度地作出了整合的努力,他们相互切磋,建立了文化沟通的网络,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交流场”。除了四派之间相互融合外,他们还把思维的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学术天地。其中吕祖谦的学术被后人称为综合之学,他继承了博采众家、泛观广接的家学之风,把朱熹的理本论与陆九渊的心本论融为一体,合为一炉,构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使之具有调和性、综合性、包容性的特点。“四明四先生”既取资于吕学和永嘉学术,也有得于湖湘学,尤其是杨简,公然援禅入儒,将陆派心学导向唯我论方向发展。尽管如此,南宋的浙东学术虽未形成统一的学术范型,但已勾勒出事功学和心学的两大形象,从而为下一阶段更高程度的整合融流进行了必要的铺垫。
(三)文化区域成熟时期的整合融流。南宋浙东文化的自立借助于宋室的南迁,此后不管政治中心如何变动,浙东学术文化已能按照自我发展的惯性驱动运演,这说明文化区域已趋成熟。自立和成熟是前后相续的两个文化阶段。南宋的事功学和心学分别倡导了近代理性所需要的现实精神和主体精神,因而对以后的中国启蒙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他们的启蒙还是十分稚弱的。“因为从人类思想发展的逻辑来看,近代理性要求思想的现实精神与主体精神的充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将思维对存在之关系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基础之上,并对关于自然与人生之近代的科学认识之形成与发展产生强有力的推动。因而只有将事功学的现实精神与心学的主体精神融合贯通,才能产生更大的启蒙力量。到了明代中叶,浙东的王阳明才真正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努力。”[3]王阳明的思想立场尽管是心学的,但却是更加开放的和包容的,他充分吸收和继承了元代以来各种思想融合的成果,建立起了“范围朱陆”并集心学与事功学大成的圆满而精致的哲学理论体系。阳明之后,王学产生了分化。浙东学派的鼻祖黄宗羲在其师刘宗周批判程朱、修正陆王的思想启发下,进一步表现出“宗王而不悖朱”和“折衷朱陆”的思想倾向。他站在心学立场上吸取了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的气本论,构建出理气合一、心性合一、心理合一和穷理者穷心之万殊的哲学体系,它源于阳明心学而又修正、改造阳明心学,同时还吸收了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知识。黄宗羲还提出了“会众以合一”的治学归纳法,他说:“士生千载之下,不能会众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达于海,犹可谓之穷经乎?”[4]由分析而走向归纳,便是求得真理之途,也是文化整合融流的重要方式。
浙东文化是吸收外来文化最为积极、最有气魄的地域文化。浙东文化的每一次整合融流,非但没有因此而解体,反而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和调适能力,而且其结果几乎都导致了文化的增殖。浙东文化就是这样地从弱势到优势,从自立到成熟,在不断的集长补短、博纳兼容中,释放出创造发挥新文化形态的潜力,并驱使自己走向辉煌的顶点。
收稿日期:2000-0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