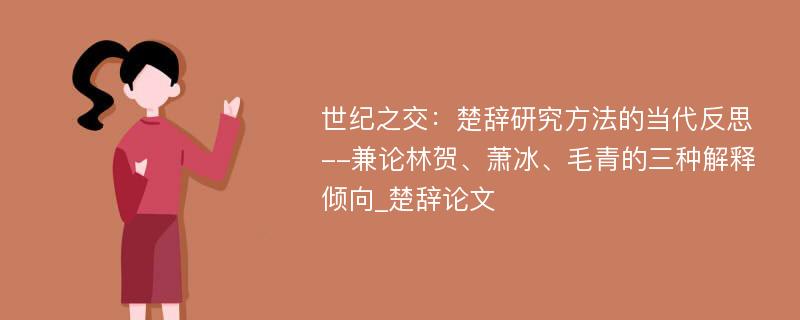
世纪末:楚辞学研究方法的当代反思——兼论林河、萧兵、毛庆等人的三种阐释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等人论文,三种论文,世纪末论文,倾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以来的学术视野中,楚辞学的繁荣昌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自八十年代以来,这个具有二千多年悠久历史,并伴随着当代人文科学规范化思维进程越来越趋向于严密系统的古典文学范域,在现代“文化热”潮流的激荡下一再成为显学。大量的研究力量投入其中,坚实的,富有理论意义的成果也纷纷问世。从1985~1995年的短短十余年间,楚辞学界推出专著80余部,论文三千余篇。①]这些论著,在学术方法上对传统有重大的超越和扬弃,并在国外理论的大量引进中吸取了传统楚辞研究中的合理内核,从不同角度、不同方法的追问中,系统地逼近楚辞本体,形成了一种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为宏大壮观的学术规模,呈现出新方法蜂起更迭,新思维汹涌而至的多元化局面。站在世纪末回眸这一奇观,并从研究方法上进行深入反思,对仍然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楚辞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内在意义。
严格地说,研究方法是一切学术探索的价值基础和透视基点。学术研究都是基于一定方法对研究对象所进行的分析、推理、演绎、举证和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方法规范着研究的视角、深度以及新发现的可能性。但是,对研究方法本身 ,在古代楚辞研究中却并未引起重视,一直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或者用儒家文化的价值判断强行阐释楚辞文化,惊异于弥散于楚辞诗歌中的浪漫特质,却不能给予确解和定位,或者以历史事象层面的琐碎考证取代对楚辞文本的审美提示和象征把握,简单地将楚辞世界纷繁灿烂的象喻艺术等同于具体的历史细节,从而使一部辉煌的诗歌文本沦为满载琐事的史书,这大概是文史哲混溶时代,缺乏文学研究方法的自觉意识所致。即使在文革时代,对楚辞的研究方法也一直悬而不论,大都以庸俗社会学方法进行一些大而无当的表面性争议,存在以概念取代艺术、用政治笼括一切的弊端,不仅无法呈示楚辞的本原风貌,反而用当代政治争鸣掩盖了楚辞文化原本真实的存在,这是楚辞研究方法走上歧途的又一历史表征。
必须承认,在八十年代开始的楚辞学方法自觉意识增加,一方面的确是楚辞研究历史发展的学术积累必然导致在传统学问基础上倾注于思维方法和角度的提炼和自省,另一方面,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文化理论的多元引进也具有极大的激化和促进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大批西方文艺理论家、文化哲学家的理性思维的指引,中国当代楚辞学界一批杰出的先导人才大量阅读和吃透包括《金枝》(弗雷译)、《原始思维》(列维—布留尔)、《野性的智慧》(列维—斯特劳斯)、《文化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马林诺夫斯基)、《批评的剖析》(弗赖),《新科学》(维柯)等大量范导型文化论著。从“原始思维”、“诗性智慧”、“文化原型”、“宗教神话”、“巫风仪典”等极富启迪作用的概念、描述中获得重新追索楚辞文化世界远古信息的理论准备。于是,楚辞的探索方法与路向在多元化的理论吸取中具备了多元化的倾向。虽然,在这个气势宏大的多元方法并进的格局中,每一种方法都自成一体,彼此兼容,相互辉映,相互发明,但是,最具独立品格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三种方法,它们分别是三重证据法,艺术审美研究法、人类文化学方法。
典籍·器物·民俗:三重证据法的融汇与勃兴
楚辞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在于文化还原,必须通过各种认识途径探视和描画楚辞文化世界的原貌,必须在时空的种种阻障中回溯楚辞文学存在的客观历史条件,这是楚辞学研究中一个基础,同时也是直接影响到文化问题追寻和楚辞审美蕴含揭示的一个前提。
古代传统的楚辞阐释者,抵达楚辞本质存在的方法大多是考据,即以典籍证典籍,通过典籍文字的引证与映衬,说明楚辞具体意象、人物、场景和事件以及它们所关涉的文化内容。由于作为史源的文史典籍的疏漏、掩盖、局限乃至曲解,致使以此为据的考据本身常常充满疑义,并未发明抉微、把握文化的本原意义。尤其因为楚辞生成的文化地域偏离于中原黄河流域中心文化,从中原中心文化视角对它进行的任何评价和说明,都可能因价值取向的不同而掩盖其固有的特殊性实质。因此,文字典籍之外的有关楚文化的大量文物遗存和风俗习惯的遗传成为楚辞学还原性研究的重要参照对象。
王国维在本世纪初针对那种独尊典籍的治学风尚,指明过文字考据不能作为唯一史源,还必须以出土文物来予以参照。这就是王国维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它经王国维的倡议,考据学由单一的文献引证发展到了“二重证据”,即以典籍,结合地下发掘的出土文物来考察文化存在,从而把文史典籍的考据学同文物发掘的考古学结合起来了。“二重证据法”使后来的楚辞学研究十分重视楚地丰富的文物资源对楚辞探讨的价值和意义,也使长沙马王堆墓、曾侯乙墓、包山二号楚墓等大量楚墓葬文物提供的文化信息及时地汇入楚辞学研究中,在具体文化事象的参照比较中,把握楚辞的内在意义。例如,正是从楚地文物所携带的巫风文化特质上,姜亮夫先生认定了巫风对楚辞浪漫诗风的本质决定作用,指出所谓文学浪漫主义界定用于楚辞的不确切性。”其实并非浪漫,盖其理想主义之中,含大量之历史文化教育思想,其触及浪漫故事之处,乃南楚民间所习闻之故事,非屈子自为创造也”。②]汤炳正先生的《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③]则更是侧重于将文物楚简所呈现的楚国占卜史录与《离骚》的艺术创造结合起来,得出了《离骚》时序结构与楚国这种卜筮程序相同的结论。这种使用文物考古材料研究楚辞的方法,使楚辞学者突破了儒家观念审视下楚辞注释的种种陈说和谬见,更清晰地透视到楚辞与楚国巫风文化深层的渊源关系。
在考据学的二重证据法之外,近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楚辞学文化考察方法,即民俗学方法。它与二重证据法一样,本来意义上与考据学有方法上的一致性,旨在发掘原生历史,只是作为考据二重证据之外的第三重证据。这种方法,实际上在典籍,文物这类“死”文化之外去寻找楚文化的“活”化石,寻找楚文化远古延绵的当代地域风俗,从楚文化延播地域及偏僻山区(如湘鄂西、川东、贵州、云南等地)所遗存的楚文化风俗习惯中寻觅楚文化遗踪,并用它来参证楚辞,这样可以发现新的思维路径。但在实际的方法运用中、则远远超越了楚文化风俗的遗存地域、甚至古代域外的风俗亦被作为楚辞文化研究的有力参照系。
从楚国地域风俗存留研究楚辞文化,尤其切合楚辞自身特性。楚辞从根本上说,是楚国民间文化的结晶。虽然楚辞是文人对楚国民间文学加工、修饰和提升的结果,具有雅文化的艺术魅力,但其内涵上却还保存着楚国民间文学的文化基因。无论是《离骚》、《九章》还是《天问》《九歌》,都充溢着鲜明的民间文化内容。诗歌中的神话传说,抒情方式、巫风民俗、占卜降神、遨游九天等等艺术情景无不映射着楚国民间文化的光泽,是这种神秘幽邃、精深博大的楚国民间文化本体向诗的艺术形态转化的表征。尤其是《九歌》,真可谓是由诗人屈原从民间直接收集而来的关于楚国巫风神灵的系列组诗,与民间口头文学、民间巫风文化习俗都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因此,从那些遗留和散布于南方民俗中的楚文化因子中考察这些源于楚文化本体的楚辞诗篇,不失为一种确切的学术思路,也是“三重证据法”在楚辞研究范域中勃兴不衰的基本根由。
在运用“三重证据法——民俗学”探询楚辞的学者群落中,侗族出身的林河的贡献尤为卓著。他说:“一些著名的楚辞专家,远者如王逸、朱熹,近者如郭沫若,胡适,都因缺乏田野考察,单凭书本考证,因而未能有所突破。”④]他认为田野考察对楚辞研究具有根本性意义,对楚辞学“案牍派”提出了批评。在具体涉及《九歌》研究时他说:“可惜,从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社会文化学等方面对它进行研究的人,却寥若晨星。”⑤]林河这些侧重于“三重证据法——民俗学”的观点与著名学者钟敬文所倡议的把民俗学引入古典文学研究的倡议是完全一致的。⑥]在研究实践中,林河更是将文字、考古、音韵等知识手段结合到民俗田野考察中,“到民间去寻找历史活化石”,他的《试论楚辞与南方民族的民歌》(《文艺研究》1984年第1期)、《〈九歌〉与沅湘民俗》(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7月),可谓成功地运用“三重证据法——民俗学”于楚辞的学术代表作。其他论文如《马王堆汉墓飞衣帛画与楚辞神话南方神话比较》(与杨飞进合作《民间文学论坛》1985.1)、《马王堆汉墓的越文化特征》(《民间文学论坛》1987.3)、《论侗族民歌与〈九歌〉的关系》《沅湘求子风俗与〈少司命〉》(均见长江文艺出版社《屈原研究论集》1984年5月版)、《从楚简考证侗族与楚-苗之间的关系》、《一幅消失了的原始神话图卷——马王堆汉墓彩绘与楚越神话和丧葬习俗的比较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4期),《两千年前的楚越佳肴——论马王堆汉墓亡灵里前的饮食习俗》、(东南民俗研究会议文,1989南昌)等等都将古籍文典、考古文物和田野民俗三者揉合起来,相互交叉、彼此融合,使“三重证据法——民俗学方法”在楚辞学研究领域的运用日臻完善,并最终从民俗学视域触及到楚辞,楚文化所包含的文化问题和多重文化关系。在林河的视野中、楚辞文化并非一个孤独悬置的文化范畴,而是与“侗族文化——越文化——楚越文化——沅湘文化——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都有着微妙而繁复的深层联系,他对楚辞诗歌所依托的楚文化有了相当客观的把握之后指出:“楚文化包括:楚民族本身的文化;中原华夏文化的深层影响;楚国境内外各民族文化的影响;楚国境外海上和陆路来自东南亚、印度甚至波斯等外来文化的影响”⑦],林河已由“三重考证据法——民俗学”研究方法上升到整体的文化关系审视,这是三重证据法在最终的融汇阶段的必然结果:揭示文化层面。
萧兵的楚辞学研究则可能是考据,考古和民俗三重证据法纯熟运用的又一例证。萧兵论著中,不论是考据、考古、抑或民俗资料,都是以一种文化遗存物的形式或线条出现的。因此,它们之间本身就具有一种映现楚文化本质的统一性和融合感。在文字考证,文物分析和民俗资料三者之间并不存在彼此间的分离或单向度的使用倾向。他不拘一格地在三重证据中自由运作,描述着他的楚文化原初景观和深层衬蕴,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性成就。在萧兵笔下,古今民歌,古今民俗,伴随着文物现象内容,以及甲骨文、金文、音韵、训诂、文献等相互协作的全面的技术性分析,而某一文字、音韵、训诂或民俗方面的新材料,则往往引致这种全面的技术性分析的投入,从而破解出某一文化谜底。例如,对《天问》以及《诗经》《史记》所涉及的周代女祖姜嫄生子“三弃三收”之迷,几千年聚讼纷纷。萧兵利用Bas on《图腾主义》等书所载的世界各民族民俗史料,以马达加斯加土著把新生儿丢在隘巷里让牛羊践踏或庇护的奇俗,证姜嫄弃子乃图腾考验仪式。他研究《天问》,诬以世界各地民族志、民俗学材料,上溯颛琐婚制、下考舜禹家庭婚姻形态,考释夏王朝建立的经济,政治、社会图景,也基本上是三重证据互相渗透,灵活多变、显示了一种研究方法上的成熟和园通。
作为一种楚辞学探讨方法,三重证据法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和一般性原则。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涉入楚辞学,三重证据都是新发现的基础,也是新观点阐释的前提。1991年12月湖北武汉召开的首届中国楚文艺研讨会结集的论文《楚文艺论集》(1991年12月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反映出“三重证据法——民俗学方法”在许多楚辞学论者思路中的作用和意义。能正明《巫·道·骚与艺术》、萧兵《〈楚辞〉里有没有“龙船”和“方舟”?》、王克陵《云·气——楚文艺形象与符号问题》,陈建宪《引魂之舟——楚人物龙凤帛画与日本珍原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颜新元《长沙马王堆汉墓T形绵画主题思想辨证》,林河《侗族傩戏〈姜朗姜妹〉试析》、唐愍《冲傩——古傩和楚巫结合的混血儿》,巫端书《荆湘歌谣的楚文化色彩探索》,萧园《楚人与巫觋文化》,刘城淮《南·北神话,传说的交融》,黄永林《论楚辞与古江汉民歌的关系》等论文无不透现着三种考察视角的相互交替和全方位观照。
但是,楚辞学的三重证据法的根本价值仍然在于楚辞文化的还原性追求,它是传统国学单向度文字考据法向文物层面和民俗层面的延伸。虽然考据视角由单一性转向多样化,然而其方法却表现了一种对历史事象和文化原貌的复述性本质。在这种复述程序中,由于典籍,器物和民俗“活化石”三个方面的共同参照而使楚辞学研究者拥有更加广阔和更为全面的思维视野。这大概是楚辞学界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三重证据法”的勃兴而生机盎然。巨著新说层出不穷的根因所在吧。
艺术审美研究
在楚辞学诸研究方法中,艺术审美研究方法所突现的是揭示楚辞诗歌的艺术审美层面,打开那个缤纷灿烂的浪漫艺术世界,呈现悲剧诗人内在的心灵情感。如果说,楚辞学存在着事实性和艺术性两重层面的话,那么,艺术审美研究则明显地不同于考察楚辞文化事实性层面的“三重证据法”,而把思维焦点对准楚辞艺术性层面,阐释艺术心灵的奥秘。在过去相当漫长的历史时间中,楚辞学者大都存在着一种以楚辞文化事实性考察取代楚辞艺术性透视的习惯,偏重于传统考据学方式,而忽略了楚辞的诗本体之揭示,导致了一大批人在象征性艺术情景中作事实考据的错误偏向,把整体性的浪漫象寓体系拆解为现实琐事或历史事实的隐喻和暗示,并进行逐一追询和索隐,结果使楚辞艺术世界坍毁为一个个彼此分离,无法缝合的历史事象的碎片。在这种片面的考据行为中,楚辞诗歌本体沉沦不现,而浮现出来的则往往是浮光掠影的臆想与猜测。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诗与历史的严重混淆,和诗的分析方法的缺陷,使楚辞学长期徘徊不前,停留于某些肤浅的争议层面,从而付出了巨大的学术代价。
当代楚辞学扭转了这一艰难的思维惯性,把文化还原和审美分析作为两种相对区别的研究方法;在“三重证据法”勃兴的同时,也十分注目于楚辞艺术的表达形式,审美情感,意象内涵,诗人心灵和艺术风格,用艺术审美的研究视角来观照楚辞文学,区分史与诗,事实与意象之间的界线,运用西方东渐的艺术心理学、美学、哲学和文艺理论等学科的思辩性方法和综合优势,集中探讨楚辞表现的艺术世界。
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突出并自成风格的是毛庆。毛庆说:“从开始研究楚辞,我们思想就很明确,重点研究楚辞的艺术性。”⑧]他要从二千多年来楚辞学那种注释、考证、辑集、评议的一般性工作中逃离出来,充分利用中西知识,“吃透两头”(传统方法和西方理论),寻觅自己独特的楚辞学思维路向:从楚辞的艺术审视角度重新研讨楚辞。这种方法的研究难度在具体的学术操作中甚至远远超过了包括三重证据法在内的其他思维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已经超越了一般认知方式,需要研究主体具有一种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整体思辨力。而所有这一切主体智慧却并不是一些知识或材料所能集合而成的,中外知识和理论著作也仅仅能提供某些思路;真正的研究必须独立完成。毛庆的《屈骚艺术新研》⑨]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艺术审美方法视角的严格要求,以比较纯正的结构形式成为中国楚辞学史上一本艺术论方面的拓荒之作。在这部力图剖视心理与象征等诸多复杂的楚辞艺术的著作中,毛庆辨析了一般冠予楚辞的浪漫主义概念的含混不清的词义渊源,指出英、美、日、俄、中五国对浪漫主义的界定存在巨大差异,认为楚辞浪漫主义具有鲜明的表现主义倾向。而在楚辞艺术的心理与象征的具体分析中,毛庆指出屈原性格气质上的男女双性化特征,这一特征是屈原在许多诗歌于多重矛盾(如“去”与“留”,“生”与“死”等)中犹豫徘徊,进入迷狂状态,情感跌宕起伏、悠久忽飘摇变幻的心理反映;“象征”的艺术创造,则不仅仅限于移情于景和寓情于景的一般诗歌外化表现,而且是屈原自我矛盾心理的独白的直接呈现。因《卜居》《渔父》实际上是自我心灵两种声音的对话,恰如《离骚》中女媭是“另一个‘自我’的独白”。这种自我抒情的诗体方式给予了诗人自我表现和自我假定的艺术空间。在楚辞的象征语境中,毛庆厘定出屈骚的象征系统,大致可分三个层次,即动植物系统、事物系统和人物系统,整个象征系统中心是彭咸,最高层次是屈原的自我形象。依据象征艺术的原则,毛庆指出《桔颂》这一古今赞喻的诗段的象征寓意并不成功。
金开诚、戴志钧、潘啸龙、赵沛霖等功底扎实的楚辞学者,在继承运用传统楚辞治学方法的同时,也呈现出精辟的艺术审美分析。
金开诚《论作为艺术思维经验的屈辞超现实想象》⑩]刊发较早,着力从艺术思维特质上指明屈辞内在的超现实意涵。从神话、《诗经》、屈辞的比较视野中,发掘出屈辞创新性艺术经验。这篇论文融汇了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的理论透视,因而具有一般局限于楚辞学的论者所缺乏的系统性、整体性和阐释深度。
戴志钧的屈骚艺术分析则透露着三重类型划分的模式。他在《屈骚意象·手法·风格——屈原艺术个性研究》[(11)]指出楚辞的艺术表达手法分三种形式:一是直抒式、一维构思,如《惜诵》、《涉江》、二是直抒与“比兴”混合式,二维构思,如《桔颂》、《抽思》等,三是直书其事,香草美人体系,神话故事系统三维构思,如《离骚》,又将屈骚艺术风格也罗列成三种类型:一、儿沉郁悲愤为主调,兼有缠绵悱恻之思,如《惜诵》、《涉江》等,二、儿缠绵悱恻的主调,而兼有沉郁幽怨之情,如《湘君》、《湘夫人》、《抽思》等,三、沉郁悲愤中见缠绵悱恻,互为表里、水乳交融,如《离骚》。而另一篇名为《论〈离骚〉的形象体系和抒情层次》[(12)]的论文则认为《离骚》提供的是一个虚实相间的文本形象体系,由三种意象体系构成:一是政治生活意象体系(君臣)、二是婚姻爱情意象体系(男女),三是神话传说意象体系(人神),后两个层次是对前一个层次的虚化和变形。[(13)]这些类型划分和基本阐述,虽然对屈辞的构成之艺术因子有所揭示,对屈辞繁杂多变的风格轮廓有所描绘,但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还是比较浅层的,粗糙的,并未达到艺术形式的深层构成和风格趋向上的形而上层面。
潘啸龙《论屈辞之狂放和奇艳》。[(14)]涉及到屈辞整体风格上贯穿始终的激烈抒情特色,从深层的文化背景和楚人的民族习性的考察和追索中,阐释了屈子文学中时时呈露出来的抒情“迷狂”状态,使屈骚艺术表现和诗的灵魂风格在文化、诗人,作品三者的相互参照中自然见出,是一篇楚辞学艺术审美分析方面的力作。这篇论文虽取社会历史分析之视角,但历史文化之引证并非目的所在,而在于为艺术审美分析作铺垫,因此,不仅没有踏入庸俗社会学方法的歧路,相反为揭示屈辞内在的艺术奥秘提供了确凿的论述前提。在另外两篇涉及《离骚》艺术的千古争议的两个问题(即求女和男女君女之喻)上,潘啸龙进一步体现了艺术与历史分析相互渗透的方法特点。《离骚“求女”辨》[(15)]认为“三求女”在《离骚》诗文中为迷离之辞,是屈原政治追求的艺术外化形式,《论〈离骚〉的男女君臣之喻》[(16)]则解决了与“求女”之谜相关的问题“男女君臣之喻”。潘啸龙认为,屈原自我形象在《离骚》前半篇映现为女性形象,象寓着诗人不被楚王信任却又孜孜以求的不幸政治命运;下半篇“求女”三次则指喻着楚国的黑暗和求明君的希冀,这些阐述取艺术分析视角、却又辅以春秋时期赋诗言志传统和当时普遍的比拟习惯的历史性考察,使这一分析见解既不限于史实考辨的事象性层次,又呈现出艺术分析的澄明性和历史感;这种阐述方式毫无疑问属于楚辞艺术审美分析中较为成熟和坚实的一个方面。
透过楚辞学艺术研究现状,我们发现,这种方法尚处于萌发状态;和悠久古远的楚辞学考据法相比,它毕竟还相当年轻。它从本质上超越了国学传统中的经验体悟法和纯事实辨析,更多地需要域外理论范式的滋养,加之楚辞学研究主体艺术理论之思辨力量的贫弱,使这种从楚辞学园地萌生的艺术研究方法尚处于发展壮大之中,操作中普遍地存在着不够踏实、较为肤浅和参差不齐的现象。唯其如此,在楚文化考察日益繁荣发展的当代,这或许将成为下个世纪楚辞学致力的主要方向。
人类文化学方法
人类文化学方法,具有鲜明的综合性,客观性特点,它表现在楚辞学上,则从渊源上承借了古典考据,原型分析、音韵训诂、文物鉴别等多种深厚的国学根底。但它不仅对国学方法兼收并蓄,更为重要的是,它并不限于国学方法,而将思维视野扩展到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事象中,从类似或相同的文化遗存,风俗习惯、典章文献中追寻楚辞文化的映证物和破译法码。或许它与“三重考据法——民俗学方法”存在某些相似与重叠,但其根本区别则在于人类文化学方法具有更加辽阔宏远的视野,在时空上和文化种族的多向性考察上远远超过了以楚辞文化本体生成发展,衰落及遗存的时空地域规定为前提的“三重考据法——民俗学方法”。
这种方法在一种比较的文化视野中倾向于世界各种族文化因子本身的类同性或同质性。这是楚辞学研究中思维延展、泛化、以彼证此,相互辉映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一前提条件的存在,世界范围内相异民族文化的广泛引证或互证则无法展开。
这一方法在楚辞学界的典籍代表是萧兵。萧兵在三十余年的楚辞学研究中形成了坚实而丰厚的传统学问修养,而学术界的“文化热潮”把他从旧学层次上升到人类文化学的方法论高度。这是一种相当自然的顺利转换。这种从国学到人类文化学的方法转换,给他的楚辞研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创造前景,不仅给他进行楚辞文化与中原文化混同性考察提供了契机,而且也使楚辞学不拘格式,极度自由地融入世界文化大时空,远远超越了楚辞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般界线。萧兵因而把楚文化因子作为环太平洋文化(或名“泛太平洋文化”)Pan-Pacific culture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彼此间的同理互证,比较或影响方面的研究。毫无疑问,他近十年来推出的近十部楚辞学巨著——《辞辞与神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楚辞新探》(天津古藉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黑马——萧兵民俗神话学文集》(台湾中国时报文化公司1990年版)、《中国神话传说》(台湾适用出版公司1990年版)、《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楚辞的文化破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傩蜡之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都是在这种人类文化学方法的客观审视中完成的。这种方法给楚辞研究主体提供了发挥学术创造力的自由空间,对研究对象显然也缺乏严格的视角限制,所得出的结论时常不免宽泛。另外,从一般所要求的方法的纯粹性与理论透视的深邃感而言,也因泛泛引据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人类文化学方法之进入楚辞学界,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和提炼,那种纵情畅游世界文化大时空的思路是不符合楚辞学对方法论意义上的人类文化学的精粹要求的。我们认为,楚辞学人类文化学方法必须向理论层次迈进,而衡量楚辞学理论水平的却并不是宏观与微观之别。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并不表现出理论性与非理论性的差异。理论首先必须体现出思维自身的深度感与推演的逻辑性与抽象性、概括力、弃舍了这些,仅仅依赖宏观视野(来寄寓学术价值)是根本无法建构楚辞学理论体系或形成楚辞学的理论性描述的。
理论性思考与思维的深化是与方法上的某种方向选择和思维限制互为关联的。我们必须看到萧兵楚辞学研究在取得斐然成就的同时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这就是他使用的人类文化学方法尚需深化和完善,在视野的拓展的同时也必须加强思维的限制。而事实上萧兵的楚辞学人类文化学方法拓展了视野、却并未深化思维。一方面,萧兵突破了楚辞学的微观研究模式,带来了廓大的文化比较情景和雄浑的运思气势,但另一方面,因其思维一再超越对象,泛化对象而显得缺乏思维凝集焦点,缺乏阐述深度和理论特色。
无庸置疑,楚辞学人类学方法和“三重考据法——民俗学方法”一样对二十世纪楚辞学追寻新的思路、开拓新的探索天地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这种方法虽然有待完善和深化,但日益推进的楚辞学研究对人类学方法的普遍吸收却昭示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我们预计,人类学方法不仅将使楚辞学园地视景开阔,形成累累硕果,而且它也会在新的世纪里不断被楚辞学各个研究方向的研究者运用,发展和提升。
匆匆巡视当代楚辞的领域,我们认为,研究方法与视角的拓展,对楚辞学的发展与繁荣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而当代楚辞学也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具备方法上的自觉意识和创新意识及更新能力。上面所概述的以林河、毛庆、萧兵为代表的三种新的研究方法,正是楚辞学在新的人文环境中调整阐释视角,更新思维方法的具体表征。诚然,从多元性,融汇化的当代楚辞学方法中抽样出三种方法及主要倾向,也并不标明三者间的彼此分离和绝然独立。实质上,目前的研究现状表明,纯然单一的方法在楚辞学范域是不存在的,因为在楚辞文化宏大的视景中,常常需要研究方法上的横向兼容性,并借此基础向纵向深度掘进。因此,在楚辞学术整个运作过程中,各种方法不仅可相对发展,而且还能够彼此兼用,取长补短,克服某些方法倾向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未来楚辞学方法远景趋向将是,一方面倾向于多重维度的整体观照,另方面不断提炼和调整上述三种方法自身。由此,我们预测三种方法的未来。
1、在“三重考据法——民俗学方法”中,将会更加自觉地运用三重维度、彼此参照、将纯“民俗学方法”中最易混同的真正楚辞文化遗存与被他文化影响或变异的因素拆离出来,避免“民俗学方法”泛化性引据过程中的误导和误读倾向,用“三重考据法”透视出楚辞文化本体及其历史视象形式。
2、楚辞艺术审美研究方法将会更多地溶入“三重考据法——民俗学”和人类文化学方法的宏阔视野,使艺术的直感阐释和历史文化的客观维度结合起来,使阐释过程既具有文化事象的穿透力和统摄性,又具有详尽充实的论证材料,并从艺术审美方法的特有视角限定和统一芜杂的纷乱史料,从而更呈现出方法操作上的纯粹性。
3、楚辞人类文化学本来是个视景廓大的领域,但在未来的世纪中楚辞学者将更注重方法运用中的限定性因素和特定目的方向,比如在时空界线上有意识地区分楚辞文化本体和非楚辞文化,楚辞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楚辞文化和异质文化间的影响与被影响,楚辞文化与他文化的类同及差异等等,这样才不致于泛泛而论,将存在于特定时空范域(先秦六—八百年、中国南方长江流域中部地区)与其他文化混同起来,既可借助于多重文化的比较性观照,破解因文化中断而丢失的楚文化线索,又不掩盖楚辞文化之本体内涵,这对进一步揭示楚辞文化的本真存在具有极为重大的价值。
注释:
① 参见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周建忠主编《楚辞学快报》.
② 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简论屈子文学》P230.
③ 《文学遗产》1994年第二期.
④ 林河《〈九歌〉与沅湘民俗》,P23.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7月.
⑤ 引自周建忠《当代楚辞学研究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P296.
⑥ 钟敬文《民俗学与古典文学》,见《文史知彼》1985年10期,《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82年10月.
⑦ 引见周建忠《当代楚辞学研究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版,P492.
⑧ 引自周建忠著《当代楚辞学研究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版P356.
⑨ 毛庆《屈骚艺术新研》,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⑩ 此文刊发于《北方论丛》1984年第2期.
(11) 载戴志钧《论骚二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12) 载戴志钧《论骚二集》
(13) 参见戴志钧《〈离骚〉的组织结构与构思艺术》《北方论丛》丛书第三辑《楚辞研究》1983年.
(14) 辑入中国首届楚文艺研讨会(1991年12月武汉召开)《楚文艺论集》1991年12月湖北美术出版社.
(15) 载《学术论坛》1982年第6期.
(16) 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2期.
标签:楚辞论文; 楚文化论文; 萧兵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九歌论文; 神话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天问论文; 楚国论文; 民俗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