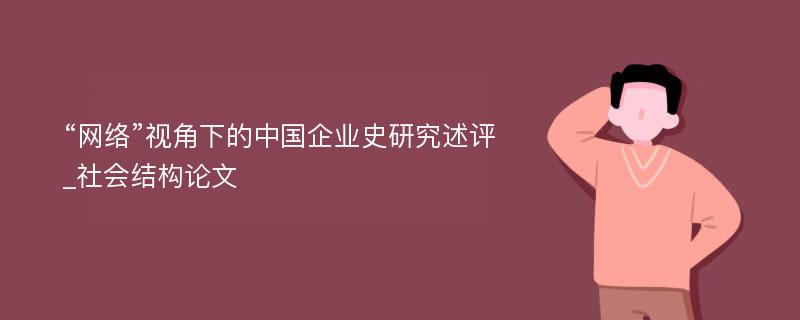
“网络”视野中的中国企业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国企业论文,视野论文,史研究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3(2010)01-0167-08
近20年来,“网络”研究成为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热门课题。90年代至今召开了多次关于中国商业网络的会议,同时有大量采用“网络”视角的论著问世。本文旨在介绍“网络”研究兴起的现实和理论背景,回顾“网络”视野下与中国企业史相关的研究,指出此类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研究方向。
一 “网络”研究的兴起
“网络”研究的兴起肇因于学术界探求二战以降亚洲经济腾飞的内在动因,而制度变迁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为其提供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背景,同时该类研究还反映出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蕴含着发现中国-亚洲自身历史的学术关怀。
1.缘起:亚洲经济神话探因
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苏,196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197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先后崛起,1990年代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一系列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神话引发了经济学、社会学学者对其原因的思考。
研究者很快发现,这些经济成功在外围现象上的共同点——以基于密集型劳动产业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为起点,不足以说明该地区各国间的差异以及经济高速发展的深层原因。对于亚洲的经济成长,继80年代盛行的儒家文化说之后,韩格理等人在90年代初进一步提出了“商业网络”的解释模式。①
1989年举办的“东亚、东南亚的商业网络与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此后关于亚洲商业网络的讨论奠定了基调。此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为考察不同华人社会中的商业网络提供了大的理论背景,并对亚洲商业网络进行了初步的个案和比较研究。这些研究以文化、信用、亲缘、地缘等概念为关键词,构筑起亚洲型资本主义的框架,形成了中西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并将“网络”确定为研究亚洲经济的主要单位。②此后,尤其是在亚洲经济泡沫破灭以后,华人网络对亚洲经济发展的功过问题,引发了学界长期激烈的争论。③
2.背景:制度变迁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所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突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式,揭示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④该理论激发了更多学者关注制度因素及其背后的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正式制度相比,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制度更加稳定,更接近于特定文化的内核,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也更直接。⑤建立在地缘和血缘基础上的网络正是由非正式制度安排所引起的非正式组织,因而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此外,社会资本理论也引起了研究者对网络的兴趣。该理论认为社会资本嵌入于社会网络中,是一种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这种网络结构观突破了资源只有通过占有才能加以运用的地位结构观的认识局限,凸显出利用社会关系来实现目标的重要性。⑥社会资本理论一方面为研究者以商业网络来解释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成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表明了凭借社会关系获取回报的普世性,进而提出了何为亚洲商业网络特殊性的课题,这也使中国-亚洲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商业网络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3.内核: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
19世纪欧洲率先完成近代化后,西方发展模式成为衡量世界其它国家、地区发展进程的标准。二战后至70年代海外研究亚洲史尤其是中国史的三种主流模式,即“冲击-回应”、“传统-现代”,以及“帝国主义”均植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抹杀了亚洲社会自身变化的能动性。⑦
20世纪后期,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迅速崛起,展现了一条与西方截然不同近代化道路。这一现象促使研究者对西方近代化模式进行反思,同时也开始在亚洲的文化传统中寻找亚洲近代化的内部动因。⑧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中心观”逐步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主要范式。与此相应,在中国商业史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西方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而以往被忽视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⑨
这种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使亚洲史和中国史的研究不再束缚于与西方相关的若干方面,也开始注意到难以用“传统-近代”二元演变模式来解释的一些领域,由此深入探究亚洲历史演进的内在脉络。在这一趋势中,“网络”研究成为挑战西方中心论、书写亚洲自身历史的有力工具。
二 “网络”视野下的中国企业史研究
“网络”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组织结构,也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视角。这一视角并未囿于对亚洲现状的探讨,也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⑩企业史以企业这一社会经济机构为切入口,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正因为如此,一些在“网络”视野下进行的研究虽不以企业为直接的考察对象,但也跟中国企业史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此将“网络”视野下与中国企业史相关的研究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对商帮、商会等商人团体的研究,不少学者都将网络视作商人团体成功运作的关键。李焯然分析了关系网和信用制度对中国近代晋商票号业兴衰的影响。(11)汪雷认为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的原因在于他们建立了基于血缘、地缘的商帮网络。(12)黎志刚通过对香山商人的研究,指出网络即资本,血缘及地缘网络的形成亦以减低交易成本为前提。(13)李培德考察了早期香港及粤籍买办如何利用既非市场、又非制度的人际网络来开展商业活动。(14)应莉雅的研究表明天津商会构筑的组织网络具有减少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经济功能;(15)天津商会的制度化对完善商人组织网络运行机制起到了积极作用。(16)
2000年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讨论会以“中国商人、商会及商业网络”为主题,对区域商人网络和商会的网络结构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对宁波、梅县、台湾竹堑、山东潍县、天津、上海等地的同乡网络、商业网络或个人网络进行了个案考察。滨下武志提出了近代中国通过“合股”这一新形式,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的新商业网络;冯筱才基于对民国宁波商人及其同乡组织的研究指出同乡网络对商业活动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胡光明认为商会组织网络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民间新生社会势力第一次合法地打破各个省区的分散隔离状态。(17)
二是对会馆等同乡组织的研究。顾德曼在1995年出版的《家乡、城市和国家》一书中不仅论证了同乡关系的生命力,也卓有见地地指出了其局限性。(18)2004年顾德曼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乡关系内涵的空泛性使其可被用于各种用途或与其它组织关系相结合,而且同乡关系并不会导致网络自动形成,只有当它能使相关人等共同受益时,才会形成网络,这主要依赖于同乡组织领袖担任多重公共领导职务,从而使其网络资源得以扩展。(19)
三是华商跨国贸易网络,与此密切相关的是1970年代以来滨下武志等人开拓的亚洲交易网络研究。滨下武志认为朝贡体系使亚洲内部形成了“朝贡贸易关系的交易网络”,尽管西方列强将这种亚洲交易网络与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但亚洲内部交易网络的特性在亚洲白银圈、契约劳工贸易和亚洲区域内汇款网络等方面依然得以延续。(20)在亚洲交易网络研究兴起的背景下,一批聚焦于华商跨国贸易网络的研究涌现出来,如古田和子考察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华商跨国贸易网络;市川信爱、戴一峰、廖赤阳讨论的福建商帮的跨国交易网络等。(21)
四是以某企业为研究单位,对相关的各种形式网络的综合考察。在2002年举办的“企业制度·企业家精神·城市经济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关文斌以永久黄企业集团为例,对近代中国企业家利用社会关系网从事企业经营活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柯博文考察了大银行家周作民如何利用与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网,保持企业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发展;戴一峰的研究则表明,侨批局借助侨民的社会纽带,将自身网络化,并使其商业活动结构性地嵌入于华人跨国社会。(22)另外,高家龙所著的《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与华商大企业(1880-1937)》也被列为会议参考文献分发给与会者。
在2007年举办的“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企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高家龙通过对刘鸿生企业与家族关系网的研究,质疑了父权在中国家族企业中的绝对权威。(23)关文斌考察了久大精盐有限公司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如何选择性地使用网络、层级与市场三种原则来克服它所面临的困境;(24)李培德分析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基于人际关系的分行网络被制度网络取代的过程;(25)王玉茹和张玮的论文将组织关系网与私人关系网区分开来,探讨了近代中国绸缎业流通市场的分级与上海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关系网络的构建过程。(26)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网络”这一视角在商业组织、同乡团体、跨国贸易和企业经营的研究中都受到了关注。而前三类研究所关注的商业网络、同乡网络、跨国贸易网络、家族网络、个人网络等也可以在企业史的框架中加以综合研究。高家龙的《大公司与关系网》一书围绕“企业管理层级结构”和“社会关系网”这两个概念,对六家大企业在华运营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是综合研究与企业相关的各种网络的代表作。高家龙认为他的这本著作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现状提出了三个挑战:第一,如何将长途贸易的研究理论化,重新绘制地图,并将人的因素引入19世纪企业史的研究之中?第二,如何综合研究中国企业史和政治史,以加深我们对20世纪初期企业-政府关系的理解?第三,如何才能解释在企业活动中中国社会关系网的活力而不过度夸大它的作用?
高家龙所提出的前两个挑战,旨在修正有关中国长途贸易和政商关系的一些既有结论。他在书中初步论证了20世纪初中国企业依靠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关系网,能够成功规避政府的控制,穿越施坚雅所描述的半封闭的经济大区,而且没有局限在罗威廉所描述的国内市场中,此外这种国际贸易也没有随着滨下武志所描述的朝贡贸易体系的完结而在1911年终止。(27)而该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质疑了以往研究对中西(包括日本)企业的本质界说一认为西方和日本企业采用“企业管理层级结构”,中国企业则注重“社会关系网”。(28)其结论是书中讨论的所有企业都同时依靠了社会关系网和公司管理层级结构,因而每一家企业中都产生了关系网和层级结构之间的动态互动。(29)
《大公司与关系网》对中国企业史研究现状提出的三个挑战都与“网络”密切相关,这充分说明了企业史综合各种网络研究的可操作性,也大大拓展了在“网络”视野下研究中国企业史的思路。(30)
三 存在的问题及一些思考
采用“网络”视角研究中国企业史,将修正关于中国长途贸易、政企关系及网络-科层关系的既有看法,并能突出人的能动因素,揭示出历史的复杂面相,使研究更加细致深入。但当我们运用“网络”这一研究视角时,仍有以下几个问题有待解决。
1.“网络”的概念界定
“网络”研究已经兴起了20多年,由于“网络”概念作为比喻或分析工具的方便、有效与弹性,使之在短期内迅速泛滥。许多人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并未加以思考和界定。因此“网络”的定义至今仍不甚明晰,而且有空洞化的趋势。
究竟什么是“网络”?韩格理等人的研究并未对“网络”这一概念进行严格的定义,仅表明中国商业网络的特征是依靠亲缘、地缘而结成,以信任和互惠经济利益为基础。(31)顾德曼的论著指出了同乡关系的局限性,并提出具有多重身份的同乡组织领袖所编织的社会网络并不仅仅依靠同乡关系。(32)冯筱才对“宁波帮”的研究表明血缘、地缘以外的业缘关系网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滨下武志提出近代中国通过“股”建立的商业网络不仅越来越普遍,而且越来越重要,成为宗族、行业之间经济活动的新连接点。(33)他还在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之外,提出了文缘和善缘。关文斌在对久大精盐有限公司的考察中指出网络“以亲属、家族和朋友为中心”,“加上同乡、同年、工作、相似的生活经验、政见,以及共同的敌人,使网络得到进一步加强,通过这些关系,创造出一个具有多层次的关系网。”(34)由此看来,结成网络的要素由亲缘、地缘扩展到各种关系。
这与费孝通所阐释的“差序格局”相符,即中国人重视社会关系,每个人都生活于一个以“己”为中心的、富于伸缩性的社会网络之中,人的行为也因在这个关系网络中的相对地位不同而表现出差异。(35)金耀基也强调了中国社会中,个人构建家庭以外关系网的自主性。他指出地域(籍贯)、亲族、同事、同学、结拜兄弟和师生关系等是建构关系网(即拉关系)的主要“归属性特征”,但作为群体认同基础的归属性特征是可大可小、灵活多变的。(36)不过这种构成网络的归属性特征范围之广泛,也逐渐模糊了中国关系网的特质与边界。另外社会资本理论证明了通过社会关系获取回报的普世性,这也质疑了亚洲或华人网络的特殊性。有人认为诸如信用、关系等人际关系模式,并非中国或东亚所独有,因此,至少没有理由将华人或亚洲网络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加以特殊化。(37)
正是由于没有界定“网络”的概念,英文中network一词翻译成中文的用词也尚未确定。Chinese networks通常被译为“关系网”、“社会关系网”、“人际关系网”等,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译者对中国人重视“关系”这一特征的强调。但是这些概念的内涵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应该区别使用?翻译的中文用词是否应该统一?这些问题都有待思考。
笔者认为要解决“网络”的定义问题并回答华人或亚洲网络是否具有独特性这个问题,尚需进行大量的实证和比较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人际关系网是否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社会关系网是否有什么不同,不同地区的企业关系网有什么不同,海外华侨关系网与中国地方关系网的联系等。(38)另外还可以关注不同的移民模式、贸易类型与网络结构之间的关系。(39)除了在中国国内各地区、各类型企业之间、华人关系网之间进行比较之外,还可以将中国企业的关系网与欧美企业的关系网进行比较研究。(40)在华外资企业有着自身的关系网,又与中国的关系网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因此也不失为一类较好的比较研究对象。
2.“管理层级结构”与“网络”的关系
高家龙在《大公司与关系网》一书中挑战了社会学研究认为西方和日本企业采用“管理层级结构”,而中国企业注重“社会关系网”的观点,因而颇具新意,但该书仍未完全摆脱原先中西企业本质界说的影响。例如书中在探讨英美烟公司的个案时,涉及到1921年英美烟公司与郑伯昭合资组建的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采用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并且英美烟公司也参与了其管理,但是作者仅仅因为永泰和是由中国人来实际运作的,就忽视了它内部的复杂状况,将其简单地划分到关系网一边。再者,前面已经谈到,欧美企业也有自身的关系网,但作者则忽略了这一点,将这些企业划归到了层级管理结构一边。书中所谓的管理层级结构与网络的互动无非是一家企业既采用了管理层级结构,又使用了关系网。这两者尽管在一家企业中,但仍是相互分离的。克服这个问题,就需要关注在华外国公司自身的关系网与中国本土关系网之间的联系,以及中国企业、商业团体自身的等级结构。
另外,高家龙没有定义“管理层级结构”与“关系网”这两个核心概念。(41)他只是在导言中借用鲍威尔的话对两者进行了一个模糊的界定,即管理层级结构有“清晰的部门界定、明确的权限划分、详尽的报告机制和正规的报告程序”,与此相反,关系网强调的是“各种横向的沟通和相互间应尽的义务”。(42)而在之后的个案研究中,作者自己也承认关系网本身就是等级制的,如郑伯昭和荣宗敬的关系网。(43)如果说“管理层级结构”的特征就是纵向的等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关系网中的等级制呢?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关系网中的等级在中国关系网与外国来华公司结合的时候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3.外国人与中国关系网
过去的研究都预设中国的关系网中不包括外国人。但是前面也已经谈到,结成网络的要素不断扩展,不再局限在亲缘、地缘的范围之内,那么我们能不能大胆地假设外国人也被包含进中国人的关系网呢?(44)笔者在考察1921年以前郑伯昭与英美烟公司的关系后,发现英美烟公司的首任中国地区主管唐默斯对促成永泰和与英美烟的合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与郑伯昭建立了良好的私交,并且双方都很好地利用了这种私人关系。在1917年,郑伯昭在面临失去“大英牌”专销权的危机时,利用与唐默斯的关系维护并巩固了自己的利益,而唐默斯则利用郑伯昭既有的经销网络销售英美烟公司的产品。1905-1919年间,唐默斯和郑伯昭的交往更多是为了英美烟公司的利益,1919年他离开英美烟公司之后仍然保持与郑伯昭的私交,并以此为自己谋利。唐默斯于1922年从英美烟公司董事的职位上正式退休后,开设了一家资本为500万元的孔雀电影公司。(45)他与在上海拥有大片地产的郑伯昭合作,1925年在北四川路开奥迪安电影院,1930年在汇山路开百老汇电影院,同年又在贵州路开新光电影院。这是否表明唐默斯也融入了郑伯昭的关系网呢?
4.在华外国企业与中国区域关系网
“网络”研究蕴含着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但是如果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情境中的网络时完全不考虑西方的因素,是否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矫枉过正呢?施坚雅、罗威廉、滨下武志都肯定了关系网在中国长途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罗威廉基于对汉口的考察认为在19世纪后半期和整个20世纪里,建立在祖籍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关系网所做的并不亚于“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内市场”。滨下武志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关系网不仅整合了中国国内市场,而且联系起了整个亚洲内部的“朝贡贸易体系”。高家龙的新作《中国药商》以中国企业在销售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药业为考察对象,进一步论证了中国企业利用血缘和地缘关系网,能够成功地跨越地理屏障及规避政府控制,在全国范围内从事贸易并进行市场整合。出于对西方中心论的戒心,上述史家均力图在中国历史的坐标中理解中国历史,强调较少受到西方影响的时空下(如1796-1889年的汉口)的关系网或较少被西方化的本土商人(如中国药商)在近代中国市场整合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但是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西方与中国频繁接触之后,中国人逾越地理壁垒、整合全国市场的方式是否发生了改变?例如驻华英美烟公司将中国分为东北、华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和华南的5个“部”、17个“区”、90个省属“段”和上百个“分段”来进行管理。(46)英美烟草公司在成功地设立了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它在全国范围的经销商之后,又开创了“督销”制度。横跨山西、河北两省的三和烟公司、北方区的王者香、四川的南跃公司、南京的久大、汉口的义记、河南的赵仲陶等都是较大范围的督销。根据1937年的统计,当时全国共有12个督销,其中以公司名义组成的有7个,以个人名义出面的有5个。(47)值得注意的是:英美烟公司一般在各地物色有现成销售网络的人作为督销;此外,有些督销原本并非商人,在担任英美烟公司的督销之后才利用自己的各种关系建立香烟经销网络。根据这种观察,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英美烟公司促成了中国区域性商业网络的形成和联合呢?(48)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认为“网络”视野下的中国企业史研究应该关注中外企业关系网的比较研究,进一步考察关系网中的等级制在中国关系网与西方公司结合时所发挥的作用,探讨外国人融入中国关系网的问题,以及在华外国企业对中国区域关系网产生的作用。
注释:
①亚洲商业网络的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80年代后期以降的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展开的。如1989年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的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1993年在意大利米兰举办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ercial Networks in Asia,(1850-1930)与1998年在新加坡举办的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sian Business Networks等。其他关于亚洲商业网络的会议可参见Lai,Chi-kong,"Chinese Business History:Its Development,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 in Franco Amatori and Geoffrey Jones,eds.,Business History around th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302.探讨亚洲商业网络的文献众多,可参见Nohria,Nitin and Robert G.Eccles,eds.,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Cambridge: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2; Fruin,Mark,ed.,Networks,Markets and the Pacific Ri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Richter,Frank-Jürgen,ed.,Business Networks in Asia:Promises,Doubts,and Perspectives,Westport:Quorum Books,1999; Chan,Kwok Bun,ed.,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State,Economy and Culture,Singapore:Pearson Education Asia Pte Ltd.,2000; Menkhoff,Thomas and Solvay Gerke,eds.,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nd Asian Business Network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Curzon,2002.
②Chen,Edward and Gary G.Hamilton,"Introduction: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ary Hamilton ed.,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Hong Ko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1,p.9.
③廖赤阳、刘宏:《当网络遇到国家》,《读书》2006年第9期,第128页;Kwan,Man Bun,"Managing Market,Hierarchy,and Network:The Jiuda Salt Industries,Ltd.,1917-1937." Enterprise and Society,vol.6,no.3(September,2005),pp.395-418;关文斌:《网络、层级与市场:久大精盐有限公司(1914-1919)》,张忠民、陆兴龙、李一翔编《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205页。
④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⑤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为方式》,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⑥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在林南等人强调社会资本正面效用的同时,也有学者揭示了社会资本的弊端,参见Gargiulo,Martin and Mario Benassi,"The Dark Side of Social Capitals," inTh.A.Roger,J.Leenders and Shaul M.Gabbay eds.,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and Liability,Norwell,Mass.:Kluwer Academic Publishing,1999,pp.298-322.
⑦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页。
⑧对西方近代化模式的反思,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⑨Lai,Chi-kong,"Chinese Business History:Its Development,Present Situation,and Future Direction,"Business History around the World,pp.305-311.
⑩高家龙曾对有关中国社会关系网的研究做过一个总结。参见高家龙:《对中国企业史研究现状的三个挑战》,张忠民、陆兴龙编《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注释1。
(11)马伟:《多纬视野中解读晋商——晋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史论坛》2006年第4期,第62-63页。
(12)汪雷:《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原因探析》,《学术月刊》2001年第6期,第81-87页。
(13)黎志刚:《近代广东香山商人的商业网络》,王远明编《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122页。
(14)李培德:《早期香港买办的人际网络》,朱燕华、张维安编《经济与社会——两岸三地社会文化的分析》,台湾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41-153页。
(15)应莉雅:《网络化组织于区域市场交易成本——以天津商会为个案(1903年-1928年)》,《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第61-66、70页。
(16)应莉雅:《近代商会研究新视角:商会网络运行机制——以清末民初天津商会网络为个案》,《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26-129页。
(17)朱英:《网络结构:探讨中国经济史的新视野——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80-182页。
(18)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宋钻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9)顾德曼:《民国时期的同乡组织与社会关系网络—从政府和社会福利概念的转变中对地方、个人与公众的忠诚谈起》,《史林》2004年第4期,第112-118页。
(20)朱荫贵:《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48-157页。
(21)古田和子:《上海ネツトワク中の神户:外国綿製品を運ぶ中国商人》,山川出版社1992年版;古田和子:《上海ネツトワクチークと近代東アジア》,東京出版会2000年版;市川信爱、戴一峰:《近代旅日华侨与东亚沿海地区交易圈》,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廖赤阳:《長華商と東アツア交易網の形成》,汲古書院2000年版;戴一峰:《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70-71页。
(22)参见陆兴龙:《“企业制度·企业家精神·城市经济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上海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第75-79页。
(23)高家龙:《企业与家庭关系——上海刘氏家族》,《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第188-193页。
(24)关文斌:《网络、层级与市场:久大精盐有限公司(1914-1919)》,《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第194-205页。
(25)Lee,Pui-tak,"Institutional Networks versus Personal Networks:An Analysis of the Branch System of the Shanghai Commercial and Saving Bank,1916-1937," 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企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上海,2007年7月,附页。
(26)王玉茹、张玮:《流通市场分级与关系网络的构建——近代上海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研究(1900-1930)》,《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第304-314页。
(27)高家龙:《对中国企业史研究现状的三个挑战》,《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第5-9页。
(28)参见"Review by Howard Cox,"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54,no.3.(Aug.,2001),pp.582-583.
(29)高家龙:《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与华商大企业(1880-1937)》,程麟荪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228页。
(30)高家龙的新作《中国药商》通过对中国和东南亚药商的研究论证并深化了他之前提出的观点。Cochran,Sherman,Chinese Medicine Men: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31)Gary G.Hamilton,"The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s of Western and Chinese Commerce: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pp.49-65.
(32)顾德曼:《民国时期的同乡组织与社会关系网络——从政府和社会福利概念的转变中对地方、个人与公众的忠诚谈起》,《史林》2004年第4期,第112-118页。
(33)朱英:《网络结构:探讨中国经济史的新视野——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80-182页。
(34)关文斌:《网络、层级与市场:久大精盐有限公司(1914-1919)》,《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第205页。
(3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36)金耀基:《关系和网络的建构—一个社会学的诠释》,《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3-111页。
(37)廖赤阳、刘宏:前揭文,第129页;Kwan,Man Bun,"Market and Network Capitalism:Yongli Chemical Co.,Ltd.and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Ltd.,1917-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9期,第97页。
(38)张忠民、陆兴龙:《前言:关注学科前沿、回应时代挑战,在比较中迈向经济史研究的国际化》,《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第3页。
(39)Chi-kong Lai,"Chinese Business History:Its Development,Present Situation,and Future Direction,"Business History a round the World,p.311.
(40)关于美国和欧洲网络的研究可参见关文斌:《网络、层级与市场:久大精盐有限公司(1914-1919)》,《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第205页。
(41)一般对儒家文化的研究都认为中国社会注重秩序,是一个等级结构的社会。Lapidus在一篇比较中国和伊斯兰社会的论文中就试图说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是等级,而伊斯兰社会结构的特征是网络。结构的特征是等级,而伊斯兰社会结构的特征是网络。可见在使用前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定义是很有必要的。Ira M.Lapidus,"Hierarchies and Networks: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Islamic Societies,"Frederic Wakeman,Jr.and Cardyn C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p.26-42.
(42)高家龙:《大公司与关系网》,第2页。
(43)有关“管理层级结构”与“关系网”的探讨,参见冯志阳:《一本书与六个大公司的中国故事——〈读大公司与关系网〉》,《史林》2007年第1期,第185-186页。
(44)关文斌也曾指出,忽视中国企业家与外国人的密切互动是亚洲网络模式的缺陷之一。Kwan,Man Bun,"Market and Network Capitalism:Yongli Chemical Co.,Ltd.and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Ltd.,1917-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9期,第97-98页,注释14。
(45)程仁杰:《英美烟公司买办郑伯昭》,《上海文中资料选辑》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9页。
(46)高家龙:《大公司与关系网》,第59-60页。
(47)陈曾年:《英美烟公司的销售网》,《学术月刊》1981年第1期,第19页。
(48)考克斯的研究表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最大的成就是监督一个在范围上超越以往任何中国国内贸易机构的经销网。它最终不是通过创立一个自身的充分发展的经销机制来做到这一点,而是通过建立一个将众多服务于传统中国经济的既有贸易机构引入其组织的行政结构,并容许这个经销机制中的某些部分相互竞争来做到这一点。Howard Cox,"Learning to do Business in China:The Evolution of BAT's Cigarette Distribution Network,1902-41," Business History,no.39(1997),p.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