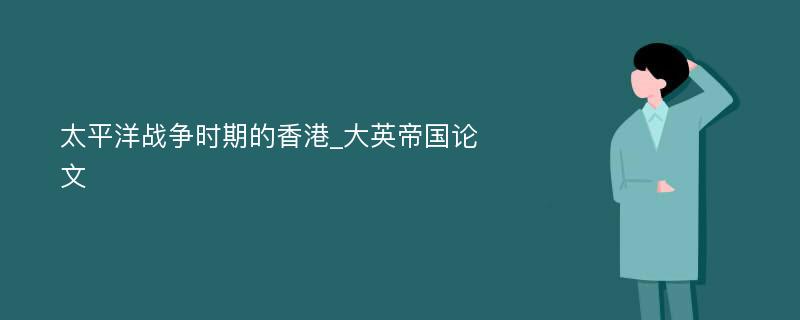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洋战争论文,香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格局,中国与美、英正式结盟。但太平洋战争没有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中国与西方大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关系,中国也并未取得与美、英等国真正平等的地位。中国与美、英既有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战争目标,又有各自的利益,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争执和龃龉,香港问题就是中英之间的一个突出问题。
“我不是英王为主持消灭大英帝国而设立的首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相继沦于敌手。日本军国主义者标榜自己是“东亚的解放者”,标榜他们进行战争“在于针对英、美、法、苏的侵略,解放东亚,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①,诚然这是欺编宣传;但英国在日本进攻面前一败涂地的现实却促使东南亚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美、英两国是联合国家中关系最密切的盟国,但两国也有各自的情况与利益。大英帝国是老牌的殖民帝国,美国则已宣布,菲律宾自1946年起实行独立,因此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英国那样沉重的历史负担②。美国政界和舆论界许多人认为,西方大国在东方建立的老殖民帝国寿终正寝了,印度支那、缅甸、马来亚等在战后不可能再回复到战前那种状态。美国报刊对英国的殖民政策颇多批评。一些报纸分别以《香港:生命死亡的一种方式》、《一个时代的终结》为题报道、评论香港和新加坡的陷落。著名作家赛真珠(Pearl Buck)撰文称,“不管白人知道与否,殖民主义的生活方式已经结束”③。知名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可以称作殖民地解放战争④。1942年10月9日的《生活》周刊登载了致英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其中敦促英国“停止为大英帝国而战,而要为胜利而战”,并说:“如果你们不惜以联合国家胜利的代价来固执坚持帝国,那你们将在战争中失败,因为你们将失去我们”⑤。在1942年6月的一次民意测验中,56%的被调查者认为,“由于英国从殖民地攫取不公正的利益”,英国人可以算作是压迫者⑥。一些政府官员也作了类似表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副国务卿、罗斯福的挚友韦尔斯(Sumner Welles)在阵亡将士日(5月30日)的一次讲话。他说:“如果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那么全世界各地人民的主权平等必须得到保证……帝国主义的时代结束了”,“《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必须适用于整个世界,适用于各大洋、各大洲”⑦。1942年秋,美国政治家、共和党领袖、1940年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Wendle Wilkie)经罗斯福允许访问非洲、中东、苏联和中国。9月下旬,他在莫斯科会见英国驻苏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时表示,他对访问途中所感受到的各地美国人的反英情绪甚为惊讶。他对卡尔说,如果他相信英国未来的政策是自由的和进步的,他将运用其影响使美国舆论充分赞赏这种政策;否则,必须坦率地说,他只能站出来反对英国。回国后,他在10月26日发表广播讲话说:“东欧和亚洲的亿万人民……不再情愿成为西方利润的东方奴隶。他们开始了解到,全世界各地人民的福利都是互相依赖的。他们决心……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不再允许帝国主义继续生存。”在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被要求对威尔基的讲话表态。罗斯福说,威尔基只是赞成《大西洋宪章》的原则适用于“全人类”而已。在英国,人们认为罗斯福的表态加强了威尔基讲话的力量。英国驻美使馆报告说,威尔基可能在共和党内号召对他“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这种运动很可能变成反英运动”⑧。
英国决策者对美国政要和舆论对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的批评十分反感。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认为,“美国对太平洋的态度……是要把别人的财产交给一个国际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美国占有1/3或更多的席位”。陆军大臣格里格(P.J.Grigg)对美国越来越凯觎大英帝国的财产“表示愤慨”。殖民地部大臣克兰伯恩(Salis-bury Cranborne)在议会上表示:“大英帝国没有死亡,亦非临终,甚至没有进入衰落。”⑨内阁中最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的是首相丘吉尔。11月10日,他在谈到英国军队在埃及的胜利时借题发挥说,英国对北非及世界其他任何部分都没有占有欲望。英国并不是为谋利和扩张参加战争的。他接着说:“然而,让我把这一点说个清楚,以免各方面对此产生任何误解。我们的意思是保持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不是英王为主持消灭大英帝国而设立的首相。”⑩
另一件使英国决策者十分恼火的事情是蒋介石对印度的访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署《联合国国家宣言》,接着蒋介石又成为中国战区(包括印支、泰国)统帅。蒋介石自认为应当在亚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时印度局势复杂微妙。甘地、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要求立即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印度成立国民政府。但是,英国拒不考虑印度独立的要求,双方矛盾非常尖锐。蒋介石希望说服英印当局和国大党都作出让步,实行战时合作。他认为他“可以作出有价值的贡献”(11)。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后,英印当局与国大党关系并未改善。年中,事态进一步恶化,英印当局于8月上旬拘捕甘地、国大党全体中常委和其他高级干部。8月12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向蒋介石解释这一措施。蒋介石表示,他没有料到英印当局这么快采取行动,他对印度人的志向是同情的,自然,要求英国人现在就撤离也是不现实的;但中国不能采取疏远印度人感情的政策,让印度人感到联合国家中至少有一个成员是同情他们的,这非常重要,不然,他们就会投向日本人的怀抱。他希望“仍然应该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并称“顺利解决印度问题对联合国家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他建议由美国出面进行调停,并保证战后印度独立(12)。英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建议根本不予理睬。丘吉尔于8月26日致电蒋介石说:“国大党根本不代表印度,像欧洲一样,印度是居住着许多人种、许多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大陆。”他还说:“联合国家应该遵循的最好原则是互不干涉彼此的内政”,他要求蒋介石像英国对待中国的国共分歧一样对印度持超然态度(13)。克兰伯恩认为,要打消蒋介石的念头,“似乎该由他来治理大英帝国或告诉我们如何治理”(14)。
面对亚洲民族主义的高涨,面对盟国的责难,英国决策者认为英国需要发表一项单方面的声明,既为过去的殖民政策进行辩解,以“教育美国舆论”,又对过去的某些作法加以修改,提出战后指导英国人与非白种人关系的政策,克兰伯恩在8月18日给艾登的信中说:“这是一个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采取坚定路线的问题。我们不能听任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摆布而落到公开认错的地位。”他认为英国过去治理殖民地的记录是值得骄傲的,英国对殖民地的沦陷固然负有责任,但“主要的过失在美国”,因为当英国忙于欧战时,美国没有对太平洋予以足够的重视。他提出,“英国将要作出的让步都不能是单方面的,而要取决于他方的态度。”艾登在这封信上批道:“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坚定。”(15)
殖民地部在8月中旬提出的题为《英国的远东政策》的备忘录中逐个分析了亚洲殖民地的状况,其中第一个就是香港。备忘录“承认,香港在地理上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备忘录指出,新界是香港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依靠新界供水;但新界租期有限,待中国收回新界后,港岛就要由中国政府控制的领土供水,港岛的生存和安全将因此大受挟制;且中国是个高关税国家,如果中国收回新界后在这里设置关税壁垒,港岛对英国经济上的重要性也将大大削减,因此,“维持英国主权现在对英国利益的重要性已经减少”,香港作为港口和市场能够对发展英国与中国及联合国家的关系发挥作用是战后重建计划中应予考虑的首要因素。但英国作出的任何贡献取决于联合国家的类似态度。殖民地部估计到,“在英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时,中国政府自然会期望考虑我们将来在香港的地位,那正是确保中国对我们的善意的时候,这可能为战后英中关系带来许多好处”。外交部顾问布雷南(John Brenan)读了备忘录后写道:“殖民地部在提出其主张时比较笼统、谨慎。据我的印象,他们的主要 意思是要有条件地将香港归还中国”(16)。
外交部对上述关于香港未来的设想展开讨论。1942年新设立的经济与重建司的吉布(Gladwyn Jebb)认为,在新界租借期满之后英国就没有理由再保持对香港的完全主权了。北美司的巴特勒(Newile Butler)主张,应当优先考虑政治—战略利益,如果英国要美国在新加坡及其他地方承担防务责任,那就必须达成一项使美国感到满意的一般性协定,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有条件地”归还香港,这“既是因为《大西洋宪章》,也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感情”。远东司司长克拉克(Ashley Clarke)和布雷南不反对有条件归还香港的主张。远东司次官彼得森(Maurice Peterson)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归还香港,其理由是:1.新界剩下的租期还有55年,“这决不是微不足道的,苏伊士运河的租期却只有24年了”;2.英国被日本人赶出香港时丢了脸,如不能重回香港,则永远不能赢得东方的尊敬;3.如英国和美国同样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实际上英国作出的让步比美国多,只要看一下上海和天津的情况就能明了;4.战后美国将得到日本的有战略意义的岛屿,“我看不出,为什么他们应该得到,而我们应当给予”;5.战后为了太平洋的安全和重建,英国将作出比美国多得多的让步;英国要谨防被美国排挤出去;6.如果战后法、美在中国市场处于比英国更有利的地位,那是“十分不能容忍的”。印度事务部大臣艾默里(L·S·Amery)支持彼得森的看法。他在9月10日的一次部际高级官员会议上说,他不同意殖民地部备忘录放弃香港的建议,主张对整个问题应采取的立场是:“我们什么也不放弃”,“如果建议我们放弃什么,那就应当确信,这对我们不是一种战略上的损失,我们可能放弃的东西将能用得到战略意义并不稍次的东西来加以补偿”(17)。应当指出,1942年8、9月英国在战场上的形势仍然险恶,在殖民地问题上又备受指责,殖民地部的备忘录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此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英国在战后处理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变得愈加强硬,在香港问题上也是这样,不管此时英国政府内部有多少不同意见,没有一种意见是主张在战争期间废除在华治外法权时就考虑香港问题的。中英新约的谈判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的。
“现在不可能考虑领土调整问题”
新约谈判提上日程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估计到,“中国人很可能会认为,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当然包括放弃租借地(如九龙),还可能包括归还香港”。他在10月16日给外交部的报告中特地引用了威尔基10月7日对重庆新闻界告别演说中的一段话:“我们相信,这场战争必定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其他国家的时代的终结。例如,从现在开始,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将只能由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治理,我们现在就该这么说,而不是等到战后。”他本人也对中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抱同情态度(18)。但外交部22日复电直截了当地拒绝考虑香港问题,称该“条约与香港殖民地和包括新界在内的香港任何部分均无关系”(19)。
10月29日,薛穆向中国政府提出中英新约草案。国民政府外交部经过研究,对草案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1899年6月9日在北京签订之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应予废止”,“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20)。国民政府在这里只提出了1899年条约和九龙租借地问题,没有提及186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和英国根据这一条约占据的九龙半岛,更没有提及1842年的《南京条约》和香港本岛,应该说,国民政府考虑到问题的难度,因此提出了比较克制的要求。
11月1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提出对案。薛穆对中方提出新界问题是有思想准备的,而且他认为,这个问题“一旦提出,他们就不大可能放弃,因为他们认为租借地和租界一样,都属于有损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的范畴。”薛穆还认为,中方只提新界,而未提港岛和九龙半岛,这实际上是默认香港和九龙是英国领土,这对英国是有价值的,因此或许可以考虑接受中国要求(21)。
但外交部却别有主意。远东司长克拉克在20日的备忘录中援引了香港总督1931年6月一份备忘录中的话:“不但九龙,而且新界的大部分地区……对香港在经济和战略上都是必不可少的。”克拉克完全同意这一结论。他认为“新界与英国领土是互为依存的”,“我们必须坚决抵制中国的这一建议:毫无疑问,中国的计划是要把我们一步一步地挤出香港。”但他顾忌到,如果完全拒绝中国的要求,英国就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拖延下去,由英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表明战后英国将致力于远东的重建并确保这一地区的和平,盟国应为共同利益精诚合作,英国也准备与中国政府讨论香港未来地位问题。如果盟国致力于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联合防御体系,英国将把香港作为该体系的战略要点之一;在经济方面,盟国之间或英中两国间应达成一种安排,使英国得以保留、增加和保护在香港的商业企业的特权。他认为发表这样一项声明可以使英国摆脱困境(22)。
布雷南大致同意克拉克的意见。副外交大臣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虽然认为中国没有理由在一项废除治外法权的条约中提出新界问题,但他还是同意了克担克的主张。议会外务次官劳(R.K.Law)主张把声明范围仅限于新界,并使用盟国希望英国为重建远东作出贡献这样的措辞。但艾登否决了发表声明的建议。他认为应答复中方:新界不属条约范围,但英国愿在战后讨论其未来问题(23)。最后,外交部的方针是:坚决抵制中国的要求,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11月30日的内阁会议批准了这一方针。12月5日,艾登指示薛穆,新界目前不属于条约讨论的范围,但可以通报中方,在战后盟国为重建远东进行合作的情况下,英国“会与中国政府共同考虑在现行租期内新界的未来地位”(24)。艾登就是否有必要这样做征求薛穆的意见。
薛穆7日回电说,中方提出新界问题,或许仅仅是为了尝试,或许是为了彻底解决,他认为后一种情况更有可能,“中国人不会同意战后继续保留租借地”。为此,他主张,如果“我们能够干脆拒绝在条约中写入新界问题,我们就坚持不变”,同时还要发表一项声明表示不会无限期搁置这个问题。但不能发表如艾登所说的那种声明,中国人会把它看作是英国打算继续保留租借地的表示;再则,也不能使用“在现行租期内”这类措辞。尽管如此,他仍然怀疑,中方是否会同意把新界问题留待战后解决。艾登没有立即答复薛穆这一封信。14日,薛穆在与宋子文的会谈中说,英国政府认为新界不在目前谈判范围之内。宋子文反驳说,中国公众都把租借地和租界视作一类问题,在国民参政会上也提出了九龙租借地问题,中国政府认为,即将签订的条约如不能保证解决这一问题,则不能消除引起两国人民间误会的根源(25)。
在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上态度最坚决的似乎是蒋介石。他坚持新约中要包括这一问题,否则,他宁愿不签订条约(26)。
14日晚,宋子文嘱杭立武造访英国使馆。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并兼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他深得蒋介石信任,与英国方面关系也很好,常常起到蒋介石与英国大使之间的联络官的作用。杭立武对英国使馆顾问台克满(Eric Teichman)说,宋子文拿不准是否能说服蒋介石和孔祥熙最终同意签订不包括新界的条约。杭立武以个人身份提出一项建议:中方向英方提出一份公函,承认新界与目前谈判无关,并希望在今后适当时候重新提出新界问题。他希望知道英方对此的态度。杭立武的建议显然是他与宋子文的共同想法,他是来为宋进行试探的。薛穆随即把杭立武的建议转告外交部,并再一次指出:“任何暗示要继续保留租借地的答复都不会使中国人感到满意”,“要理解他们的想法,我们必须想一想1898年各国纷纷索要租借地的历史,当时外国对中国的侵略达到了高潮”(27)。
杭立武的建议不要求英方承担任何义务,对于英国未来政策没有任何约束,艾登认为是可以接受的(28)。在12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丘吉尔再次强硬表示:“应坚持我们前此坚持的方针,即现在不可能考虑领土调整问题,必须把它留待战后……讨论。”(29)艾登随即于23、24日两次指示薛穆,新界未来的问题不属新约范围,但如果中国政府愿意,英国可在战后“考虑租借地的期限”,中英双方可通过换文表示这种意向。这实际表明,战后英国仍要保有这块租借地。25日上午,薛穆照这一指示向宋子文作出表态,遭宋子文拒绝。宋说:“租借地的期限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薛穆在当天给艾登的报告中建议,如果中方最终同意做出妥协,可将“租借地的期限”一语改作“租借地问题”。艾登接受这一建议,于26日指示说,英国虽极愿保留“租借地的期限”一语,但也可把“期限”一词删去,或改作“租借地问题”(30)。
25日下午,宋子文、外交次长吴国桢、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外交部条法司司长王化成及驻英大使顾维钧进行商讨。王宠惠等说,蒋介石对九龙租借地问题颇为坚持,如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中英谈判可能破裂。顾维钧认为,英国说战后解决领土调整问题是有诚意的。中国可以找到体面退让的办法;而如果条约谈判失败,英国发表声明解释理由,英、美舆论自然会采取现实态度,觉得首要之事是协同作战,而不是就现在还被敌人战领的领土进行争吵,那样可能反而对中国不利。在场的人一致认为,在今后对付苏联时,与英国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大家决定把问题呈报蒋介石,并由王宠惠起草一个方案,要求英国声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意愿,并同意在战争结束后6个月之内中英开始进行谈判。蒋介石批准了这一方案,并强调,英方应该承诺归还九龙租借地(31)。
27日上午,宋子文把蒋介石批准方案事告诉顾维钧,并嘱他立即去见薛穆。顾维钧奉命对薛穆说,中国政府不反对在新约之外解决九龙租借地问题,也不反对战后进行各种实际安排,但英国现在必须明确声明打算把该租借地归还中国,如果连这样的妥协办法英国也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将不签订条约。自然,他希望能避免这种结局。薛穆表示无能为力,说他已尽力设法提出折衷方案,如谈判破裂,不是英国的过错(32)。
谈判眼看面临僵局。顾维钧估计英国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不会再作多少让步,并主张“即使暂时牺牲九龙,也要签署条约”。宋子文建议一起去劝说蒋介石不要在此问题上继续坚持。27日晚,顾维钧在面见蒋介石时说,英国有意表示友好,建议缔结新约,这是英国“送上门来的礼”,中国应当先收下这第一份礼,同时暗示在等着第二份礼;中国应当先签新约,同时公开讲明,希望英国战后归还九龙租借地。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他决定先不把这一立场通知英方,而让宋子文翌日再告诉薛穆,九龙租借地问题解决后才能缔约(33)。
28日上午,宋子文再次与薛穆会谈。宋强调说,中方已对英国建议的换文讨论过两次,但不能接受这种解决办法,他强烈暗示情势的严重性,恳切要求英国政府重新考虑在新界问题上的立场,作出准备归还新界的表示。薛穆也感到事态严重,他相信宋子文所强调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新界问题上的感情,他担心如果英国不发表中方所要求的声明,中国真有可能拒签新约,那样,“英国可能陷入窘境,中国人在与美国人订约之后,会单方面宣布废除治外法权。即便不这样,也将出现很困难的状况”,中英“两国正在迅速改善的关系”将“严重倒退”(34)。
在28日内阁会议之前,克拉克在给艾登的备忘录中分析谈判形势说,如果内阁会议批准指示薛穆,除了把“租借地的期限”中“期限”一词删去,英国不再作任何让步,英国可能要冒谈不成条约的风险。这对英国议会和公众都能讲得过去,因为一则,新界不属治外法权范围,它是“英国领土香港的租借条件下的延伸”;二则,如果英国宽宏大量,条约对中国过于有利,中国将得寸进尺,要求对治外法权范围以外的事项进行调整。他指出,达不成条约虽有若干不利之处,但“事情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由于中国的压力而在这一重要问题上让步,那么我们使自己在其他问题上经受中国的严重压力”。艾登完全同意克拉克的这一说法(35)。
28日,艾登向内阁会议报告了谈判情况,表示不能接受中方要求,内阁会议同意这一立场。会后,艾登立即指示薛穆,除了26日电所示可将“租借地的期限”中“期限”一词删去,或改成“租借地问题”外,英国不能再作让步。”他说:“我们不可能接受顾博士提出的解决办法,如果中国坚持,我们只好不签订条约。”29日,艾登又紧急致函美国驻英临时代办,向他解释英国政府的立场,谈判开始时,英国政府没有料到中方会提出新界问题,现在,内阁已经议决,即使谈判破裂,英国也不能让步。他希望在谈判中一直与英国合作行事的美国政府运用其对中国的影响,不要使事情走到这一步(36)。虽然美国政要和公众舆论对英国殖民主义多有批评,但在这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支持的还是英国而不是中国。31日,英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电告外交部,美国国务院与美驻英大使怀南特(John G.Winant)“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向中国政府指出,他们对中方“经常节外生枝感到不快,虽然租借地问题是中英两国间的事,但美国也关心此事,因为提出这一问题可能影响顺利解决治外法权问题”。虽然在美国进行干预之前中方就已作了让步,艾登对美国国务院和怀南特还是深表感激(37)。
30日,薛穆、宋子文再次会谈,薛穆照艾登28日指示把英国立场告知宋子文。下午,宋子文、王宠惠、顾维钧又见蒋介石,劝他最后下决心放弃关于九龙租借地的要求。31日上午,蒋介石正式批准签署条约。中午,宋子文将此决定通知薛穆(38)。
由于条约文本翻译颇费周折,新约签字又推迟了若干日。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与中美新约同时签订。宋子文并向薛穆提出一项照会,声明: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21日,薛穆复照称,业已将此通知转达本国政府(39)。英国没有通过这次换文承担任何义务,作出任何承诺。可以说,中方在九龙租借地问题的谈判是完全失败了。
“除非踩过我的尸体,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版图中除掉”
英国政府在拒绝中方要求时,曾经侈谈战后远东的重建与香港的关系之类,其实,英国所谓的重建无非是恢复或变相恢复大英帝国,继续维持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是根本无意放弃香港(包括新界)的。1943、1944年间英国决策者凡有机会便重申他们的这一立场。
1943年11月,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亨贝克(Stanley Hornbeck)访问伦敦,作为对克拉克头年访问华盛顿的回访。亨贝克在与英国外交部官员的最后一次会谈中,以“完全由他个人负责”的方式表示说:“我们已经谈到了许多方面,探讨了许多问题,但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一不是在现在,而是在局势明朗时—一也许是我们应当加以考虑的,那就是……香港的未来。”在场的英国官员一听这话顿时像“触了电”似的。当晚,英方安排他去见丘吉尔。丘吉尔给他着着实实上了一堂课。丘吉尔说,香港是英国领土,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应该改变这种状况;战后也许可以与中国人做出某种安排,对主权做一些调整,但“政治控制与行政责任必须留归英国”。他再次提到他一年前的一个公开表态:他当首相不是为了消灭大英帝国。他说:“他对此确信无疑,他完全乐于对任何人这样坦率地说。”(40)
在11月下旬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表示,战后香港应当归还中国。在新约谈判中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碰过钉子,他知道事情棘手,因此,提议由美国先与英国商讨(41)。但在随即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当罗斯福提起香港战后归还中国的可能性时,丘吉尔甚至拒绝讨论。由美方起草的开罗会议宣言明确提出,战后中国将收复被日本侵占的所有领土,而对日本占领的大英帝国的属地却只字未提。丘吉尔对此极为不满,他在会上遇有机会便宣称:“战争结束时,我们并不要求给自己增加领土,同样,我们也不打算放弃任何领土”(42)。
1944年10月底,丘吉尔向他的内阁成员明白表示,“向俄国提供在远东的战争目标是绝对必要的”,其中包括了旅顺、大连,道理很简单:“俄国提出的任何牺牲中国利益的战争赔偿要求都将有利于我们解决香港问题”,因此,“英国不应对俄国恢复其在远东的地位表现出任何敌意”(43)。11月8日,在议会答辩中有人问首相,他在1942年11月关于“不是英王为主持消灭大英帝国设立的首相”的宣言中的“大英帝国是不是不包括香港”。属于工党的副首相艾德礼(C.R.Attlee)大概是为了表示在这一问题上的两党一致,抢着回答说:“大英帝国的任何部分都没有从宣言中除外”(44)。稍晚,12月31日,丘吉尔在致艾登的一份备忘录中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的格言是‘不许干涉大英帝国’,绝不许……玷污这个格言。”(45)1945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受罗斯福之命与英国决策者讨论香港问题,在途经伦敦时会见了丘吉尔,丘吉尔直截了当地向赫尔利表示,他将为香港斗争到底,他说:“除非踩过我的尸体,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版图中除掉”,大英帝国将不要求什么,也不放弃什么,“我们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旗帜下的一寸领土”(46)。
英国还为战后重新占领香港制造舆论,英国政府在纽约的官方新闻机构英国新闻社出版的《英国与日本》的小册子中,大肆渲染英国治理香港的政绩,其中心意思是说,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对英、中两国是同样有益的。
英国为重占香港及早着手进行准备。早在1943年,殖民地部就设立了一个香港计划小组,初时只有9人,全由曾在香港任职的资深官员组成。自1944年9月起,前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麦道高(S.M.MacDougall)出任组长,小组成员增至28人。小组的任务除了帮助殖民地部制订政策外,主要从事筹备战后重占香港的行政机构(包括人事安排)的工作,并研究如何保证提供足够供给的问题。该小组还负有帮助殖民地部制订未来政策的责任。它与殖民地部、英商中华协会等一起讨论了战后在香港进行“宪制改革”等问题(47)。
1944年8月3日,殖民地部、印度事务部和缅甸事务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解体的远东委员会,这是一个直属内阁的部际决策机构。11月15日,远东委员会召开恢复以后的第一次会议。23日,委员会秘书阿姆斯特朗(E.A.Amstrong)把艾德礼8日在议会上关于香港问题的表态印发给委员会,以此作为制订香港政策的指导方针(48)。
英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战后重占香港十分关心。新约谈判中的争论使它们十分担忧,“外部的压力可能错误地导致一种统一意见”,使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让步。1943年5月,英国在华利益的主要代表英商中华协会就向政府表示,鉴于“保持香港对战后中国与远东的贸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决不能放弃香港。1944年11月,协会再次致函殖民地部,对艾德礼在议会的表态表示“全心全意的拥护”,并说他们听到这一声明,有“如释重负”之感,他们上年提出的想法如今也“更有力量了”(49)。就这样,英商中华协会与英国政府互相影响,互相支持,坚定彼此在香港问题上的殖民主义立场。
“英国必须重新恢复香港原状”
使英国政府感到担心的是,香港不在东南亚战区司令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的管辖范围之内,而在中国战区之内。因此日本投降时,香港很可能为中、美军队所接收。殖民地部设想了扩充英军服务团(50)的兵力,利用它在日本投降后迅速在香港建立英国行政机构的计划。但薛穆、英国驻华武官卡顿·戴维亚尔(Carton de Wiart)及驻华英军司令海斯(J.Hayes)均觉不妥。他们认为:“我们现今在中国的军事地位如此困难和微妙,如要使任何这类计划有成功可能,则必须事先与中美最高层领导讲清”(51)。1945年7月23日,外交部、殖民地部、陆军部与香港计划小组四方代表的会商意见大体也是这样。与会者认为,既然香港在中国战区之内,必须事先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方能让一个英国的民政小组附属于参加接收香港的中国军队;而在向蒋提出之前,有必要先征得美国的同意。自然,英国政府完全意识到,“向蒋介石提出香港的民政问题可能把香港未来的整个问题提到显著地位”,因此迟迟疑疑,犹豫不决(52)。
战争形势迅速发展,8月10日,日本表示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在10日下午的内阁会议上,参谋总长汇报说,参谋总部已经拟定了在日军投降时向香港派遣一支载有海军陆战队的舰队的计划,该舰队司令将受命接受日军投降,并在香港建立军政府。新任首相艾德礼感到事关重大,应由他亲自致电杜鲁门商量,但国防大臣伊斯梅(Hastings Ismay)认为,由首相亲自出面会使美国人感到“我们不合时宜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原封不动地保持我们的殖民帝国方面”,因此改由英国参谋总部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英国参谋总部设想,英军占领香港分3个阶段:1.英国太平洋舰队的一支小部队尽早到达香港实施占领;2.此后数日内运送婆罗州的一旅澳大利亚军队抵达香港;3.在马六甲海峡通航后从东南亚战区派遣一支部队及空军战术分队抵香港,取代澳大利亚军队(53)。在此同时,8月11日外交部致电薛穆,命他通过英军服务团团长赖濂仕(L.T.Ride)立即设法与被日本人囚禁在港岛的前香港辅政司詹逊(F.C.Gimson)取得联系,授权他在被日本释放后“立即恢复英国的主权与行政”,直到英国海军到达建立军政府为止。13日,外交部再次电令薛穆,“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把外交部指示传达给詹逊。香港计划小组负责人麦道高将作为香港首席文官率领文职人员尽快尽往香港(54)。
蒋介石显然是估计到了在香港受降问题上会有麻烦,特地于8月14日下午召见薛穆,声明“中国政府承认英国在香港的权利”,只是希望最终能解决香港问题(55)。这实际上是给英国吃定心丸,表示中国近期内不会提起香港问题。
8月14日,裕仁发表“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16日,驻香港日军司令官将此消息告知詹逊。詹逊虽然尚未接到英国政府命令,但他自告奋勇,立即成立临时民政机构,当上了“事实上的代理港督”。23日,他又通过重庆的秘密渠道接到殖民地部的如下命令:立即成立英国的行政管理机构,没有政府批准,不得将权力交给任何人(56)。
8月15日,杜鲁门总统向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下达关于接受日军投降的第一号命令。其中说:“在中国境内(东北地区除外)和北纬16度以北的当属印度支那的日军向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投降。不言而喻,香港在中国受降地区之内。
英国不理会杜鲁门的一号命令。16日,英国驻华大使向国民政府提出一项照会,其中说,英国政府正在安排派遣必要的英国军队去重新占领香港并恢复香港行政。同日,国民政府复照英文指出,香港不在东南亚战区范围,英国的要求与杜鲁门关于受降的命令不符。照会说:“中国政府尊重英国一切合法利益,并准备给予充分的必要的保护,但是一项接受日本投降的协调一致的计划对于在亚洲重新恢复和平和秩序是至关重要的,兹建议英国政府按照联合国家的总规定安排接受日军投降。”(57)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吴国桢表示:这“仅仅是受降安排问题”,中国对香港没有领土要求,香港问题最终将通过外交渠道予以解决(58)。
19日,薛穆又交给吴国桢一份备忘录,英国在其中辩解说,“一号命令”规定中国将接受“在中国境内”的日军的投降,“英国政府认为这不能解释为包括香港”。又说,英国政府当初被迫弃守香港,如今英军接受日军投降,事关英国的荣誉。备忘录表示欢迎中国代表参加受降仪式(59)。
中国政府每接到英方照会,便立即将其副本送给美国大使赫尔利,并向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通报情况,无疑是希望美国支持中国的立场。魏德迈认为,“既然战争开始以来香港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战区之内的”,中国要求受降是理所当然的(60)。收到英国19日备忘录后,蒋介石亲自致电向杜鲁门求援。他在21日电报中写道,英国政府应当遵守“一号命令”而不能任意曲解,“现在对受降命令的一个改动都可能造成不良先例,从而在香港以外地区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他同时表示将邀请美、英代表参加受降仪式,“受降以后我将授权英国人将其部队登陆以重新占领香港岛”(61)。
国民政府在请求美国支持,英国也在向美国施加压力。8月18日,艾德礼致电杜鲁门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把第一号总命令解释为意味着香港包括在‘中国境内’的说法,香港是英国领土”。并称英国军方已通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支英国舰队已在赴香港途中(62)。20日,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在下院宣称,英国方面已为在香港受降采取了措施,但此事“可能还有困难”,中英两国军队正在展开一场竞赛,看谁先到香港(63)。
接到艾德礼的电报后,杜鲁门立即与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F.Byrnes)以及参谋长们进行商议,结果,美国在英国压力之下不惜修改“一号命令”,同意“在受降问题上明确把香港划出中国战区”。杜鲁门在21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美国“不反对由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受降”。杜鲁门尽可能降低他改变原先态度的意义,说这“主要是具体操作性质的军事事务问题”,“在任何方面都不代表美国对于香港未来地位的观点”,他希望蒋介石“以合作与谅解的精神看待此事”(64)。22日,贝尔纳斯公开表示,香港问题将在即将举行的伦敦四大国外长会议上进行讨论。英国政府对此颇感惊愕。23日,艾德礼针锋相对地宣称,英国已经拟妥在远东恢复行政的计划,并已做出由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的安排,它不准备对英国在远东的领土主权作任何修改(65)。
杜鲁门修改“一号命令”,美国拒绝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处于孤立无助的地位。蒋介石无可奈何,于23日复电杜鲁门,表示“同意授权一位英国司令官去接受香港日军投降”,并将派中、美军官各一人出席受降仪式。蒋介石这里所说的“授权一位英国司令官”云云,无非是作出实质性让步时一种保全面子的说法,杜鲁门自然明白,他立即回电,感谢蒋介石“体谅人的行动缓解了困难的局面”(66)。24日,美国方面宣布,麦克阿瑟已经向日本大本营发出命令,香港日军向英国军官投降。同日,蒋介石对香港问题作公开表态。他在中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白宣布:“中国决不藉招降的机会,忽视国际合作和盟邦主权”,“关于香港的地位,以前是以中英两国条约为根据,今后亦当以中英两国友好的关系协商而变更”(67)。从而明确表示,他无意在此时提出新界问题,他仅仅是要行使—一即使是名义上行使作为中国战区统帅在香港受降的权力。
但英国政府却无视这种权力。27日,薛穆奉命口头告诉蒋介石,英国不按受他的建议,“英国必须重新恢复香港的原状”,并已指派海军少将夏悫(C.H.Harcourt)主持受降。蒋介石反驳说,作为中国战区统帅,受降香港日军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但又顺水推舟地表示,既然英国政府已指派了夏悫少将,他从即日起就授权给夏悫。他还说:“如其不按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国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68)同日,蒋介石还召见驻华武官卡顿·戴维亚尔。该武官随即向国防部长伊斯梅报告说,在过去两年中他多次见过蒋,有时是在非常紧急的时候,“从未见他像今天这样激动”,他认为“如果我们坚持现在的态度,我们将严重损害将来的对华关系(69)。
英国外交部异想天开,于28日下午2时致电薛穆,表示希望蒋介石不要公开提出授权受降的要求,希望他“单方面地放弃这种权力以利于英军司令”。10分钟后,外交部又追加一电,称蒋介石现在的态度与他8月24日关于香港的声明不一致,并提出一项新建议:由夏悫代表英国政府、蒋介石授权另一名英国军官作为代表联合受降(70)。
次日一早,薛穆往见吴国桢,要求安排拜会蒋介石,遭到回绝。吴国桢说,蒋介石不会同意英国的新建议。薛穆立即电告外交部说:“鉴于蒋介石的态度,如继续讨论此事,除了徒增双方的敌意,不会有任何结果。”(71)
30日下午,蒋介石接见英国大使和武官。他对英国“践踏他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权力表示愤慨”。薛穆在当天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他与武官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接受授权”。他进而警告说:“除非此事得到解决,这个争端将可能损坏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而且正是在对我们的利益至关重要的时刻—一为了重建我们在上海等地的利益,我们应当得到中国合情合理的合作,如因香港问题而使蒋介石留下极为恼怒的感情,那么不但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会遇到障碍和恶意。”(72)
薛穆的这一警告显然起了作用,英国政府是不能不考虑战后与中国的长远关系的。外交部遂于31日下午致电薛穆,表示同意夏悫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受降,并欢迎中美两国各派一名军官出席受降仪式(73)。这样英国十分勉强地接受了委托受降的方式。蒋介石总算保住了一点面子,,可以自我安慰了:这“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明证”(74)。但十分明显,在受降权之争中,赢家仍然是英国。
8月30日,夏悫率领的英国舰队在香港登陆,恢复了对香港的占领。9月16日,夏悫以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双重代表身分,在香港督宪府接受日军投降。夏悫在香港成立军政府,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正式恢复。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得出下面一些看法。
在太平洋战争中,中国通过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成立中国战区、废除治外法权、列名于《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发表《开罗宣言》等一系列外交和军事举措,提高了国际地位。号称“四强”之一,但中国并未被其他大国视为平等的伙伴。如果说《雅尔塔协定》是美苏背着中国而将中国利益私相授受的交易(75),那么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交涉就是英国继续恃强凌弱的事例。不论是在新约谈判中,还是在受降安排上,国民政府都曾为实现理所当然的权力作过一些努力,但决策者仍然存在着半殖民地心理,缺乏自立自强意识,又没有审时度势地采取得力措施(76),常常知难而退,加之缺乏盟国的支持,以致把理直气壮的事情做得低声下气。美国政界和舆论界虽然对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有所批评,但美国政府到关键时刻仍然支持英国,而不是中国。这既表现了美、英传统的“血浓于水”的“特殊关系”,也表现了美国对中国的轻慢。总之,在有关香港问题的交涉中,处处可见一百年来中国与列强关系的延续。
英国对香港的立场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事例,它与英国对印度、缅甸、马来亚等的立场是一致的。对于印度,英国拒不考虑国大党的要求,坚持其殖民统治而不加变更。对于当时被日本侵占的那些原有殖民地,英国力图在战后恢复原状。也就是说,在太平洋战争中,一方面,英国作为主要盟国之一,与中国、美国以及后来的苏联,与亚太地区各国人民一起,进行着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殊死斗争;另一方面,英国又无时无刻不想着恢复其殖民帝国。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泰勒(A.J.P.Taylor)所说:“档案材料现在揭示,大不列颠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大英帝国,而且甚至还要给大英帝国增添点什么(如对利比亚)。”(77)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硬要把旧时代的做法搬到变化了的时代,其结果肯定是不美妙的。
*本文援引的档案资料,是笔者1993年下半年在英国从事研究时从英国国家档案局丘园新馆搜集到的,其中FO是英国外交部档案,CO是殖民地部档案,CAB是内阁会议档案,PREM是首相府档案,文中不再一一说明。在此,笔者谨对英国学术院王宽诚基金的资助表示衷心感谢。
注解:
①参见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
②关于美国决策者对战后世界的设想,见拙文《赫尔利使华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③《必须加以摧毁的种族障碍》,《纽约时报杂志》The Barrier That Must Be Destroyed,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42年5月31日。
④《远东在美国人的思想和教育中的地位》,《教育记事》The Place of Far East in American Thought and Education,Educational Record,1942年7月号。
⑤该公开信深受英国重视。英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E.R.Halifax)专就此信向外交部报告说,即便对英国最友好的美国人所反对的也只是此信的“形式和发表时间,而不是信中所包含的批评,即:一、我们曾有一个殖民帝国;二、我们曾拒绝给予其居民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自由”。见FO 371/31526。
⑥克里斯多德·索恩:《一定程度的盟友—一美国、英国与对日战争,1942-1945》Christopher Thorne,All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urtain,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纽约1978年版,208-209页。
⑦霍尔伯恩:《联合国家的战争与和平的目标》Louise W.Holborn,War and Peace Aims of the United Nations,Sept.1-Dec.31,1942,波士顿1943年版,第90页。哈利法克斯报告说,韦尔斯发表这一讲话是受到国务院战后重建顾问委员会鼓励的。在战后重建问题上,韦尔斯与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是总统的左膀右臂。见PREM4/42/9。
⑧《一定程度的盟友》,第221-222页。
⑨《一定程度的盟友》,第220-221、211页;刘易斯:《走投无路的帝国主义—一美国与英帝国的瓦解,1941-1945》Wm.Roger Louis,Imperialism at Bay: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1941-1945,牛津1977年版,第187、200页。
⑩1942年11月11日《泰晤士报》第8页。
(11)卡尔致外交部,1942年1月24日,PREM 4/45/3。
(12)薛穆致外交部,1942年8月12日,PREM 4/45/4。
(13)PREM 4/45/4。
(14)克兰伯恩在对哈利法克斯的谈话中如是说过,哈利法克斯在1942年8月25日给外交部电报中又以自己的口吻说出。见FO 371/31526。
(15)FO371/31777;并见《走投无路的帝国主义》,第189页。
(16)备忘录和布雷南8月25日批注均见FO 371/31777。布雷南批注后两点涉及婆罗州、马来亚,与香港无关。新界即九龙租借地。
(17)克拉克8月27日,吉布、巴特勒8月28日、彼得森9月1日备忘录和部际会议记录均见FO 371/31777。
(18)参见李世安《1943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36页。
(19)FO 371/31659。
(2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三)],第766页。
(21)薛穆致外交部,1943年11月17日,FO 371/31663。
(22)FO 371/31663。
(23)布雷南、贾德干11月20日、艾登22日对薛穆电报的批示均见FO371/31663;并见陈刘洁贞;《中国、英国与香港》Chan Lau Kit-Ching,China,Britain and Hong Kong,1895-1945,香港1990年版,第306页。
(24)FO 371/31663。
(25)薛穆致外交部,FO 371/31664。
(26)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171页。
(27)薛穆致外交部,1942年12月15日,FO 371/31664。
(28)外交部致薛穆,1942年12月19日,同上。
(29)CAB 65/28。
(30)外交部致薛穆,1942年12月23、24、26日;薛穆致外交部,12月25日,FO 371/31665。
(31)《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70-173页。
(32)《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73页;薛穆致外交部,1942年12月27日,FO371/31665。
(33)《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6-18、173-175页。关于顾维钧说服蒋介石的这次接见,顾的回忆不尽一致。他在对中英新约谈判全过程的叙述中讲到两次见蒋介石,一次是12月27日晚,一次是30日下午,两次都是与宋子文等一起见的(同上书,第174-176页)。他在另一处回忆见蒋没有说明日期,且说是单独见的(同上书,第17-18页)。从当时情况看,除了27、30日两次接见外,不会再有第三次。顾维钧没有说明日期的这次只能是27日晚的那一次。
(34)薛穆致外交部,1942年12月28日,FO 371/31665;《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75页。
(35)FO 371/31665。
(36)FO 371-31665。
(37)FO 371/35679。
(38)薛穆致外交部,1942年12月30日,FO 371/31665;《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76-179页。
(39)《战时外交》(三),第781页。
(40)《中国、英国与香港》,第312页。
(41)梁敬錞:《开罗会议与中国》,香港1962年版,第41页;埃辽特·罗斯福:《如他所见》Elliot Roosevelt,As He Saw It,纽约1964年版,第164页。
(42)1943年第169页内阁会议(12月13日)记录,CAB 65/40;外交部致薛穆,1945年8月23日,FO 371/46251。
(43)吉尔伯特:《通向胜利之路:温斯顿·丘吉尔(1941-1945)》Martin Gilbert,Road to Victory.Winston S.Churchill,1941-1945,米纳瓦1986年版,第1093页。
(44)FO 371/41657。
(45)PREM 4/31/4。
(46)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文件》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5年第7卷,第331页。
(47)曾锐生:《民主被束之高阁》Steve Yui-Sang Tsang,Democracy Shelved.Great Britain,China,and Attempts at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Hong Kong,香港1988年版,第13-14页。
(48)阿姆斯特朗备忘录见CAB 96/5。
(49)英商中华协会的两封信见CAB96/8。英商中华协会(China Association)以前国内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译作“中国协会”(如伯尔考维茨著、江载华和陈衍合译《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英商中华协会是该协会自己确定的译名。
(50)British Army Aid Group(China),成立于1942年5月,活动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任务是搜集情报,掩护登陆和空降人员,营救被日军拘押的战俘和平民。
(51)《一定程度的盟友》,第557页。
(52)7月23日会议记录、远东司司长史班纳(J\C\Sterndale-Bennett)7月25日备忘录,见FO 371/46251。
(53)8月10日内阁会议记录、伊斯梅8月11日致艾登礼函、参谋总部8月13日报告均见PREM 8/34。
(54)FO 371/46251;并见赖濂仕《英军服务团:1942年至1945年香港的抵伉》Edwin Ride,British Army Aid Group(BAAG),HongKong Resistance,1942-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290页。
(55)薛穆致外交部,8月15日,FO 371/46212。
(56)多尼森:《英国在远东的军人政府》FSVDonnison,British MililtaryAdministration in the Far East,1943-1946年版,第199-200页。
(57)《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500-501页。
(58)薛穆致外交部,8月16日,FO 371/46252。
(59)《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506-507页。
(60)《魏德迈报告》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纽约1958年版,第350页。
(61)(62)《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508、504页。
(63)卢亚德:《英国与中国》Evan Luard,Britain and China,伦敦1962年版,第181页。
(64)《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505-509页。
(65)《英国与中国》,第181页。
(66)《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511-512页。
(67)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台北1984年版,第174页。
(68)薛穆致外交部,1945年8月27日,FO371/46253;《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512、513页;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社译印:《蒋总统秘录》第14册,台北1977年版,第40页。其实,连薛穆自己也认为,中国是不会接受“指派代表作为证人参加受降仪式”这样一种解决办法的。见薛穆致外交部,8月26日,FO 371/46253。
(69)FO 371/46253。
(70)外交部两份电报均见FO371/46253。
(71)薛穆致外交部,8月29日,FO 371/46253。
(72)FO 371/46253。
(73)FO 371/46253。
(74)《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41页。
(75)参见拙文《1945年中美苏关系的一幕》,《美国研究》1990年第4期。
(76)如在受降问题上,国民政府虽为受降做了部署,但军队行动迟缓,远不如英国军队迅速。参见刘存宽《英国重占香港与中英受降之争》,《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第168-169页。
(77)《走投无路的帝国主义》X。泰勒教授接着说:“那些在战场上实际作战的人的目的是简单的,他们是为了把欧洲人民从德国统治下,把远东人民从日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笔者认为泰勒教授的评价是全面的。
标签:大英帝国论文; 美国领土论文; 英国殖民地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香港论文; 历史论文; 宋子文论文; 蒋介石论文; 大西洋宪章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一战论文; 历史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