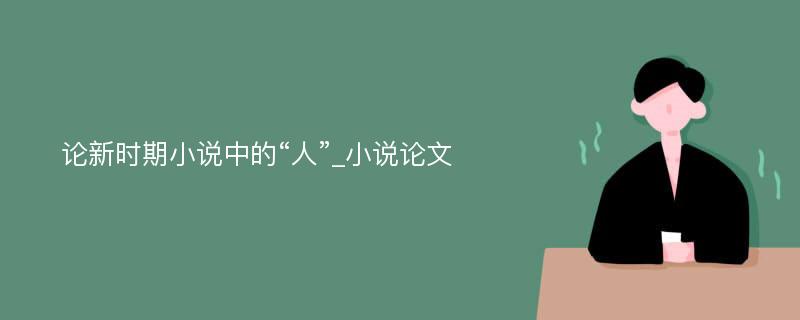
论新时期小说中的“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小说,从大红大紫滑向平淡无奇,从呼唤风云的社会中心流落到商品大潮的边缘角落,其间起伏,让人兴奋,也叫人担忧。然而,宁静以致远,在饱尝轰动效应与倍受冷落之苦后,文学开始显示出世人皆浊我独醒的人格力量与清醒的人学意识。从民族生活的里层,关心人的存在,人的命运,以至人的未来,已成为文学的基本走向与坚实的信念。无论外界喧哗与变幻,文学自有文学的步伐——“人”的步伐。
高尔基说:文学即人学。
这是一句为作家与批评家熟透了的警语。
但把这句喻世明言落实为文学的自觉行为,在我国,则是新时期以来的事情。新时期的小说家与批评家,在经历了许多次的“反思”与“探索”之后,开始把“人”推到文学的中心地位,使“人”成为文学世界中至高无上的“万物之灵”(莎士比亚语);成为“万物的尺度”(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语)。运用各种文化思想、各种艺术手段,观察人、分析人、透视人、再现人与表现人,使文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学”,使文学与人学达到较高的“人文合一”的境界,是新时期小说的一大努力,一项业绩,一个重要特征。
1.优秀的人文传统与历史局限
在我国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在漫漫数千年的文学传统中,应当说,有优秀的人文精神的流传,也有种种的锁链与限制。在先秦文学中,在我国文学童年那清纯的吟唱中,我们能清晰地回忆起那稚嫩而鲜明的人学的萌芽与闪光。“诗经”中,一首“关关睢鸠、在河之洲”,顷刻间把人带回到那原始质朴的人性世界,人们赞扬美女、表达对美女的爱慕与追求,洁白无暇、天真烂漫,且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多么单纯、多么可爱的“人”的声音。《离骚》,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句,便让人感到,那天地苍茫之间,唯“人”独行的辽阔境界。
在后来屡经发展的古典文学中,描写人,塑造人,仍是小说的一大精采。然,人类童年的天真纯朴、唯人独行的精神逐渐模糊与暗淡。人的光辉,人的形象渐渐被屡屡加深与巩固的“道学体统”、“礼教思想”所笼罩所淹没。明清小说《水浒传》,描写梁山一百零八将,个个栩栩如生,性格鲜明,可无一不可归入“忠义”与“造反”之轨道。《西游记》,谈天说鬼、写人写神,个个有花招,然,人变神、神变人,人有神性,神有善恶,无一不是德行轮回之化身。蒲松龄的《聊斋》,聊人聊鬼,言情言性,但最终也难逃“善恶有报”之说教。唯独清末曹雪芹,以辛酸之泪谱成的《红楼梦》,述家论事,言情说命,无一不以“人之性”、“人之命”为主笔,嬉笑哭诉,处处浸透曹君这一“世外之人”对人的关注、人的哀怜。
“五·四”以来,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标志,揭开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新纪元。鲁迅、巴金、丁玲、老舍、茅盾、沈从文等人,以“民主”为旗,以“现实主义”为笔,把“人”从千年压顶的“伦理”法网中解救出来,让人成为现实生活中种种“典型的人”。鲁迅笔下,人,或为仁义所欺而成为精神病者,如“狂人”形象;或为礼教所毒而成为活着的僵尸,如“祥林嫂”形象;或为外表无羁无绊,行为流里流气,而骨子里却渗透“国民劣根”的愚氓之辈,如“阿Q”形象。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一方面,把人从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带有“反封建、反礼教”的时代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封建、反礼教,依然是用某种高于“人”的思想尺度来评价人描写人。简单点说,在鲁迅这样一代宗师笔下,依然是“思想大于人”。“人”,在文学中,依然不是“独立的人”、“中心的人”、“全面的人”。
建国以来,小说的辉煌令人触目,在有限的题材中,表现出各式各样、千姿百态的人,不可否认,其间凝结着多少作家的心血与汗水。然而,在十七年时期,日益强化的“政治标准”,使得小说与文学逐渐失去应有的独立与尊严,而小说家也决不敢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之外探讨人,表现人。小说中的人,也必然被紧紧限制在某种思想,某种路线的范围之内,成为阶级的代表和政治的工具。人,有呼吸,却不能自由呼吸;人,有讴歌,却不敢为人之本性而讴歌。到文革,文学中的“人”为横行而苍白的“神”所取代,而此时的“神”正以人性的泯灭与“非人”的叫嚣为特质。“非人”的“神”横行文坛,“人”则可怜兮兮地被赶出了文学的伊甸园。
2、“人”的再生与前行
文革结束,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形势,为文学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与广阔的发展空间。文学回到了生活,“人”,回到了文学。文学家与批评家以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与文学自由谈论人、研究人、关心人、塑造人,使“人”在文学领域,不仅得以再生,而且以令人惊叹的步伐,把“人的研究”,推向吻合历史甚至超越历史的广度与深度。文学,成为“人学”研究中的皎皎者。
新时期小说,对“人”的关怀与研究,经历了两个明显的进程。首先是,在现实主义怀抱中,“人”得以苏醒与再生,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现实问题探讨文学”中,“人”开始了呻吟,开始了反省,开始重新审视人的价值与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与尊严。这时期,千军万马般的小说家与批评家,把“人”从僵化的思想说教与政治工具的囚禁下,一步步解救出来,使“人”在社会生活的海阔天空中得到自由地行动与再现,从而逐步确定了“人大于思想”的文学共识。然后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人”,不仅在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得到更广泛更深化的“反映”,而且,应运而生的,一系列具有现代意识的新潮小说,开始运用一些陌生的思想与新颖的表现手段,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人、探索人、表现人。如“寻根文学”,把“人”放进历史文化的长河加以巡视,使人成为“文化人”,“现代派小说”,把人投向“感觉世界”或“深层意识”中加以透视,使人成为“荒诞人”、“感觉人”、“意象人”。“新写实小说”则把人拽回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生存空间”加以观察,使人成为“生活流中的生存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非现实主义作家,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态度、运用什么手法,在关怀人、表现人这一问题上,取得了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一致:人,是文学的中心,文学,是人的文学。从此,文学中的“人”,开始成为“独立的人”、“中心的人”、“多方位和多层次的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一个新的标准,已基本确立。“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的外在与内在”、“人的灵魂与肉体”,不约而同成为小说家与批评家的“中心话语”。“人的关怀”、“人的透视”、“人的再现与表现”成为新时期小说家最热衷的“话题”。多么叫人高兴,高尔基的“文学即人学”的命题终于得到了真正的理解与自觉的把握。多么叫人欣慰,莎士比亚的“人是万物之灵”的呐喊在新时期的中国得到了最真诚的回音。
3、“伤痕”与“反思”的“思考人”
新时期小说,以覆盖全国的“伤痕文学”为第一拨浪潮,冲破了文革以来所形成的文学僵局,把“人”从伤痕累累的肉体与心灵的创伤中扶起,给以人性人情的滋润与慰藉,使“人”在浩劫后的血泊与废墟中重新站立。“伤痕文学”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在社会的众目睽睽之下,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向人们捧出一个个血淋淋、泪汪汪的历尽折磨饱受欺骗的“人”。如《伤痕》中的王晓华,就是在一系列的精神打击下,失去人的所有而心灵深处则伤疤累累的人。《铺花的歧路》中的女青年白慧,在“文革中”以极左的热情去横扫“牛鬼蛇神”,结果却发觉,这些无辜的“牛鬼蛇神”中有一个就是自己的母亲时,精神陷于痛苦与崩溃的边缘。知青作家竹林在《生活的路》中以自己的亲生经历为蓝本,描写了一个出身不好的女知青娟娟,在农材屡遭欺骗饱受凌辱的悲惨命运。“伤痕文学”的重要功绩,就是把“人”从种种的政治打击与精神欺骗中解救出来,使“人”在遍体鳞伤中,在受骗的耻辱中,得以苏醒与恢复,使人回到有血肉、有情感、有信念也有创伤的人性中来。人,开始了呼吸,开始发出时代的呼喊。刘心武的《班主任》就代表当时的社会人与文学人,发出了动人心魄的声音,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其实,何止是救救孩子,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救救人”。
接下来,“反思文学”掀起了现实主义小说的第二拨浪潮。“反思文学”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重新思考人的社会存在,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人的思想信念与人的命运。在回忆的空间,重新塑造与再现人,是“反思文学”的一大特色。“反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各式各样,但一般都呈现出“思考”与“寻找”的状态。如王蒙的《布礼》,主人公钟亦成在一系列的坐折命运中,反复思考后共产主义信念仍然不移。张贤亮的《缘化树》中,知识分子章永嶙,历经非人的歧视与毁灭,而在心灵上则升华为共产主义者。李国文的《月食》,老干部伊汝,在文革中受到冤屈与折磨后,重新寻找心中的恋人而已不可复得。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中,上海知青陈信,在结束知青生活回到上海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信念与位置。就连高晓声笔下的普通农民李顺大,这个无知无觉的农民形象,也在“造屋”成真后开始了作人的思索。“反思文学”笔下的“人”,或者思考后依然具有理想的光辉,或在信念失落后开始新的寻找,或在命运的捉弄之后进行人的思索。总起来说,“反思文学”一方面把人从种种“左”的迷雾中引导出来,使人开始新的历程;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把“人”放在理性的思考中加以再现与表达,从而使“人”成为“思考的人”或“思想的人”。
从“伤痕”到“反思”,“人”,从恢复知觉到进行思考。这意味着,人,又回到了文学的伊甸园,并在其中洗去身上的血污与耻辱,用新的姿态回顾自己,评价自己,使人恢复了应有的价值与尊严,从而伸展了人性,张扬了“自我”。一句话,人,回到了文学,文学,也还给了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此时的人,依然是停留于思想与理性的层面的“思考人”。
4、“现实问题”中的“社会人”
当人在“伤痕文学”中得以苏醒和站起,并在“反思文学”的思想空间获得恢复与调整后,人,很快就步向了现实生活的大地,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不同地方,从不同角落,展现出人的多种多样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特征。这一点,在具有广泛影响的、声势浩大的“现实问题探讨文学”现象中,得到充分的肯定与再现,“现实问题探讨文学”,或“现实问题”文学,其主要实绩体现在小说方面。“现实问题”小说,一方面,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得以恢复、深入后,进入全面开放时期的规模宏大的文学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活的多种多样,有轻有重,从而使“现实问题”小说分列出若干文学现象,如“改革文学”、“军事文学”、“青年问题”文学、“农民问题”文学,甚至包括“婚恋问题”文学与“性问题”文学等等。
现实问题小说中的“人”,不再是“伤痕”与“反思”中迷恋于回顾与思考的人,而是开始面对现实,在社会生活中勇于行动,具有明确的“人的意识”与“自我意识”的人。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面对文革后的残留的废墟般的现实,不是回避与叹气,而是立志改革,并将改革意识落实为大刀阔斧的实际行动的勇于进取的人。这时期的人,不仅具有敏锐的思想,而且同时拥有“人”的感情世界。这一点在《西线轶事》中表现得很是畅快醒目,革命后代、牺牲在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战士刘毛妹,在牺牲前,对女友陶坷那别开生面地强制性的一吻,充分勾勒出人的情欲侧面,不仅没有破坏人物的正面性,反而使“人”得以相对完整。这时期的小说,除表现出许多依然光辉的正面的人物外,还再现出许许多多的转变中的人物,如《花环》中的赵蒙生,《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解静。小说还对那些老的和新的反面人物也有极大的关注与描写。如《人到中年》中的“马列老太太”,《花环》中的要儿子临阵脱逃的“高千母亲”,《北方的河》中的自私自利、背信弃义、不择手段给别人制造一系列痛苦的“徐华北”,等等。另外,还有一种特别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就是这时期的小说在表现“人”时,那种高于“人”的“社会评价”开始出现模糊与淡化的趋势。最典型的是路遥的《人生》。小说中的中心人物高加林,是个新旧时代交替中的,处于城乡之间的“交叉人物”。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抱负的农村青年他勇于进取,选取中充满个人野心,他追求现代文明与新型爱情,追求时无情无义抛弃了挚爱他的农村姑娘刘巧珍而背弃了人生的初恋。对这一人物,无论是肯定与否定,都必然会陷入到“价值判断”的两难之中。而作者路遥,对他笔下的人物,充满关注也充满矛盾,有谴责也有同情,有理解也有憎恶。从而表现出对人的价值判断的模糊性与主题思想的“淡化”性。
现实问题小说,写“人”有如下进展:a、打破禁区,表现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人。b、张扬人性,充分表现人性的各个方面。c、对人的价值判断出现模糊与淡化的趋向,“思想大于人”的标准开始动摇。d、把人放在社会生活中加以描写,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加以考察,表现着人的或深或浅的或明或暗的“社会性”。一句话,现实问题小说中的人,开始成为不囿于“思想”的独立人,同时又主要是拥有“理性”色彩的“社会人”。
5、“寻根文学”的“文化人”
八十年代中期,关注人、表现人,已成为新时期小说的定局。接踵而来的是:如何写人。运用各种观点各种手段来写人,成为当时的热潮。“寻根文学”在如何写人中,展出了一幅貌似古老而实则别开生面的画卷。这画卷的基本含义是,在历史文化的寓言中表现人。明确点说,就是把人放进历史文化的深层次中加以考查,加以再现,从而表达出:人是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的产物。用西方的“洋话”说,“人是文化的符号”,“文化的动物”。用中国的“土话”说,人具有民族文化的“根性”。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可推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
阿城的《棋王》,旨在表现道家文化那悠远的境界与对人的影响。主人公“王一生”,在文革动乱时期,在尘世的疯狂与艰难中,闻目塞听,忘却了尘世的痛苦而进入了“棋”与“道”的精深高远的境界。王一生,顾名思义,说是“玩了一生”。而“玩”,却是一种充满哲学意味的严肃的字眼——为达到人生的某种高尚境界而“苦渡”。王一生的故事就是在说明,通过苦渡,方能进入民族文化的“天人合一”的道学境界。
如果说,阿城的《棋王》旨在宣扬我国的具有民族色彩的历史悠久的“道”的文化传统,那么,王安忆以其女性的、客观冷静的、细腻而又玩皮的笔法所写的《小鲍庄》,则完全摆脱她个人好恶的态势,从容而坦然地表现了“仁义”文化在我国的悠久历史与今日的换装和遗留。《小鲍庄》的主人公,是一个叫“捞渣”的小孩。捞渣,是个仁义的化身,他长相仁义,举止仁义,为仁义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仁义”之心与“仁义”之举,被新时代的人们更换为“共产主义思想”而广泛宣扬,捞渣最后也被迁坟立碑以扬名后世。在这里,小说家只是讲述而未置评价,给人一个很轻松的答案:“仁义”文化是我国有千年历史的民族性文化,在今天,它依然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依然影响并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
韩少功的《爸爸爸》,则与前两位作家有所不同,前面二位,一者宣扬,一者讲述。韩少功则具有一种严格地“审丑”态度,小说虚构了一个叫“鸡头寨”的地方,这“鸡头寨”是个毫无现代文明的、原始而又病态的、封锁于远山之中的“化外之地”。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个叫丙崽的精神痴钝的小孩。丙崽生下来就是个病态的“小老头”,对人对己,只有两句话,就是“爸爸”和“×妈妈”。“爸爸”为好为善。“×妈妈”为坏为恶。最后,“鸡头寨”必然地毁灭了,而丙崽却侥幸活了下来,无疑,“鸡头寨”那原始落后的文化习俗将随着“丙崽”的存活而继续着。小说中,由丙崽所代表的“爸爸”与“×妈妈”文化,使人很快联想起鲁迅先生曾致力揭示与鞭挞的“国民劣根性”。无疑,韩少功借用小说,揭示与批判了民族文化中“劣根”性部分,并启示,这一根性的东西,依然活着。
“寻根小说”在研究人,表现人时,不再拘泥于眼下的社会生活,而试图把人投入到民族文化的不息河流中去进行洗涤,进行裸现,无疑,这使文学对人的研究大大深化了一步,使人意识到,今天的人,仍然具有历史的牵联,“人”是具有民族文化的“根性”与“历史积淀”的“人”。人,在较深的层次上看,依然是个从历史中走出来的“文化人”。
6、“先锋派”的“变形人”
八十年代中期与后期,在对外文化的开放与交流中,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引进,使许多中青年作家与学者大开眼界,并跃跃欲试,以新的文化观点和审美方式来表现“本土”的现实与历史中的人,从而掀起了种种“陌生的”“不可思议”的文学现象。这其间,新名称的掘起与更换,常叫人跟踪不及消化不良。如“先锋派”、“现代派”、“探索文学”、“新潮小说”、“后现代主义”、“后新时期”等等。无论这些现象以什么命名,或者不间断的进行名称变幻,而在小说创作中,则显示出一种共同的创作态度,就是越过传统的、理性的思想方法和写作手段,以“新”的文化观和文学观来表现“人”,并因此而获得“反传统”、“反理性”的定性与共识。在这些文学现象中,其中一些作家作品引起较大争议,并取得相当大的影响。比如说,“荒诞小说”、“新感觉小说”、“意象小说”等。为方便起见,我们姑且将这些不完全相同的小说现象纳入到“先锋派”名下给以论述。“先锋派”小说笔下的“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人与理性人,而是一系列不易为人们所理解但又确实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的“陌生人”,如“荒诞小说”中的“荒诞人”,“新感觉小说”的“感性人”,“意象小说”的“意象人”。
“荒诞小说”的正式出现,当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为标志。在此之前,王蒙、宗璞等老一辈作家就引进与采用了“荒诞”的表现形式。但以“荒诞意识”作为小说的基本内容,《你别无选择》还是首次。《你别无选择》以荒诞的意识来观照人,描写荒诞的人,开新时期荒诞小说之先。《你别无选择》所表现的是:在新旧交替的社会格局中,无论是陈旧,还是新颖,都呈现着荒诞的色彩,人是荒诞的人,社会是荒诞的社会。“荒诞”,本是人生与生活中很特殊的一个部分,而小说将其扩大化、夸张化,使整个儿的人与周围的生活弥漫着荒诞色彩。或者说,小说以荒诞的眼光来看待人与周围世界,人便具有了荒诞的外形与内质,人也就成了“荒诞人”。荒诞的文化意义在于:让人脱离“理性”与“秩序”的约制,使人成为“反传统”“非理性”的人。
“荒诞小说”后,小说“怪才”莫言以他的“红高粱系列”震惊文坛,从而引起人们对“新感觉小说”的议论与重视。莫言笔下的“高粱地”与“高粱地人物”,一反传统的道德的说教,以“火红”的感觉世界与人物性格开拓出一个新的小说现象。在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当推他的中篇小说《红高粱》。《红高粱》所表现的好象是已经陈旧的“抗日题材”,但由于作者采用了全新的认知角度和反常的表现手法,结果是小说一举成名,成为“新潮小说”的重要代表作。《红高粱》的中心人物,是“我奶奶”,“我奶奶”最引人注目的性格当为她那不顾一切敢作敢为的高粱地一样的“火红的”性格。她风骚可人,义肝侠胆。她敢于并乐于一反传统礼教在高粱地与乡村野夫后成为土匪司令的“余占鳌”进行生命的野合,让婚姻见鬼,让生命发红。另外,小说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个小男孩——豆倌作为小说全过程的叙述人,见证人,甚至评价人。而作为“孩子”的豆倌,在叙述与评价中,则完全没有“成人”的那种道德与理性的包袱,而是以人的本真的“生命直觉”作为叙述与评价的根据。这种写法,在哲学与美学上可在“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那儿找到依据。生命哲学与直觉主义认为:传统的理性世界是“表象”或“假象”,人的生命意志才是世界的“真实”,以生命的直觉观照人的生命,方是艺术的真谛。莫言的小说在写作与创意上,正好吻合了这种“生命直觉”的文化思潮,而为新时期的小说界开辟了一种新的“写人”方法。在莫言笔下,人,不再是传统的理性的说教的人,而是生命的人,直觉的人,“感觉世界”中的“感觉人”。
九十年代初,苏童成为新潮小说中的一个焦点人物,他年纪不大,而他的多产的小说创作却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或者大力推崇,或者恶狠狠地批评。而苏童本人,作为小说家时而被纳进“现代主义”,时而被看成“后现代主义”。但有一点却取得了人们一致的认同,就是苏童是个编故事的“新手”与“老手”,“新手”,是说苏童以一种全新的方法编造着不同于他人的故事;“老手”,是说苏童在编造各种故事时非常老练自如。苏童的小说,名气最大的,也最能表现他的写作风格的无疑是《妻妾成群》。《妻妾成群》是在讲述女人的故事。女大学生颂莲,嫁给陈家花园的老爷陈佐千,在陈家开始了“为妾”的女人生活。在阴森的大院里,她很快就被剥夺了或者说放弃了女学生的清高与真纯,自觉与不自觉地陷进争风吃醋的妻妾争斗中去,随着时间的剥离,颂莲开始表现出种种的“生本能”与“性本能”,最后在“畏本能”与“死本能”的追逐下,终日湟湟而沦为疯子。颂莲这个名字本身就暗含着一种象征,莲之洁白无暇,为历代文人骚客所颂,可在人的实际生存中,“莲”很快就陷入污浊成为疯癫,实在是不值一“颂”。颂莲的故事无非在说,人,最终还是“生存的人”,“生命的人”,在模糊而阴暗的生命世界中,人必然呈现出种种本能,生、死、畏等等。苏童编故事,与人不同,他是运用“意象”来窥视人的本来面目。苏童笔下的人也就成了“意象人”。
总的来说,在“先锋派”笔下,“人”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不为传统与理性所能包容的质的“变形”。人,或为荒诞不可理喻的“荒诞人”,或为生命直觉中的“感觉人”,或为生存意象中的“意象人”。在“先锋派”笔下,人已超出人们已经习惯的“思想人”、“社会人”、“理性人”范畴,显示出新时期小说开始对人的一些潜在的本质、陌生的层次进行探索,进行透视,从而表达着“人是生命”这一主题。
7、“新写实小说”的“生活人”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代文学处于“低谷”状态时,“新写实小说”相继出现,使社会对文学的关注有所回升,并形成较长时间的“写实热”。“新写实小说”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推崇,在于它们采用了一种比较调和的创作方法,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一些不再拘囿于传统道德传统理性的新的“生活流”中的“生活人”。这一点,也引起争议,有人说,“新写实”是现实主义的一脉,是现实主义在九十年代的发展。有人说,“新写实”在根子上是接近“现代主义”的,是“探索小说”的一个新的动态。其实,归谁属谁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新写实小说以一种新的审美手段,新的文化内涵,从新的角度再现与表现了“人”,表现了“人”的又一个新的方面。“新写实小说”一开始并未打出什么旗号,而是以其创作实绩向人们推出一种新的写作态度,以客观冷静的、零度感情的笔法,再现现实生活中处于生存竞争状态下的“生活本相”的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该推方方、池莉、刘震云等。
新写实小说在写人时,一般暗含着两个步骤,一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进行“非传统”的消解,使人失去“意义”与“优美”,还原成生活现象中平俗无奇的“现象人”;二是对“生活现象”与“现象人”进行本质探讨,找出一些暗含在“生活本相”中的“生活本质”与“人的本质”,并对这些本质再次给以“现象”的再现。这种手法,与从西方现代文化中引进,并开始流行于我国的“生命哲学”和“现象学”有很大关联。
方方的小说《风景》,对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生活人,给以“传统意义”的消解,将其落实为真实的生活流中的现象人,具有独特的功力。《风景》发表于89年,其中三个主要人物形象——父亲、二哥、七哥,分别代表三种含义,父亲这个形象,表现出对人的“思想意义”的消解,二哥形象是对人的“美学意义”的消解,七哥形象是对生存竞争中生存人的还原。“父亲”是个码头工人,在传统意义上,是“先进阶级”的一员,是“英雄人物”中的一个。而实际上的父亲,除了喝酒、斗殴、欺凌子女妻子外,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崇高的思想与光辉的本质。二哥是这个家庭中唯一具有理想与美学追求的人,他向往文明优雅的生活方式,对拥有优雅气质的小姑娘杨朗给以儿时的爱慕与青春的钟情,为她,他任劳任怨,舍身忘己,可结果呢?杨朗为了生存,只好出卖女性的身体,同时也出卖了二哥的真情。杨朗还认为被人诱奸是个公平而二哥对他毫无实利的爱则一钱不值,理想与美同时毁灭。七哥则与二哥不同,他的口头禅是:“当你把这个世界看得一钱不值时,你才会活出滋味来”。这一真理是七哥无数次被人当“狗”踢后终于悟出来的。于是,七哥成了生存竞争中的强者,他走“狗屎运”上了可望不可及的“北京大学”,他利用与高干女儿的协议婚姻而一蹴为省团委书记,他见过场面,享受豪华,过着风光的人上人的日子,七哥的成功在于他看穿了世界与人生,领悟到在看不见的生存法则中,人必须顽强、冷漠,不择手段。
女作家池利在她的代表作《不谈爱情》中,把“生活还原”表达得更加自如,更加老练。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庄建非和吉玲,分别是两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庄建非出身于知识家庭,是个事业心很强的“正人君子”。尽管他在婚姻选择中,抛弃了形体干枯而知识型的“玉珞”,选择了惹人怜爱的世俗女性“吉玲”为妻,然而在骨子里还照样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格”。而“吉玲”则与之相反,这个从“花楼街”走出来的世俗女子,精巧、能干、性感、体贴,向往实实在在的温馨的家庭生活。在两人互感新鲜而结婚后,爱情消失了,“传统人格”与“世俗生活”显示出距离并发生着冲突。冲突的结果非常戏剧也非常真实,“人格”力量的代表庄建非连同他的父母都统统缴械投降,而吉玲和她的父母则以毫无文化体统的胡搅蛮缠获得辉煌的胜利。到这里,知识型的人格被逐步消解,代之以起的是更实际更平凡甚至是俗不可耐的“生活流”。
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把生活的琐碎与人生的尴尬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小林”和“小林老婆”,本来都是受人羡慕的大学生,没想到,进入实际生活后,光是被一些不起眼的鸡零狗碎弄得惶惶不安不值一文,比最卑微的小市民都不如,在经受一系列的尴尬之后,小林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琐碎阴暗的生活背后,有一种看不见的“权力网”,你或者被“它”压扁,或者与人相互利用,在“权力网”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小林选择了后者,从此,生活对他们张开满是金牙的笑脸。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现象学”的第二步“还原”。首先生活以一系列琐碎的现象出现,现象之中,有个“本质”,这本质就生存竞争中人人具有的“生存意志”与“权力意志”。而这“权力意志”依然以一系列“现象”表现出来。而人,就是这样一系列现象中的现象人。
新写实小说,写人,抛开了“历史的传说”,也取消了“理性的赞歌”,消解了传统人格中的崇高与优美”,落笔于实实在在、干巴枯燥的“生活现象”与“生存法则”。从而使人跳出了历史的空间与理性的虚构,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处于生活本相的,生活流中的“生活人”、“生存人”。
8.文学的呼唤:整体人
新时期小说中的“人”,在“伤痕”“反思”中得以苏醒回归,成为“思考人”。在“现实问题”中步向社会,成为“社会人”。在“寻根”中走进历史文化,成为“文化人”。在“先锋”的笔下和现代意识的观照中,步进各种生命层次,成为各种陌生的“变形人”。在“新写实”中又回到现实生活的现象中,成为“生活人”。这一步步,一层层,使文学对人的研究,由点到面,由外到里,由明到暗,由浅到深,使人的各种本质得到不同程度的注意与表现。
可是,作为“人学”,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人,究竟是个整体,而不是局部,也不是某一层次就能包容与概括的。单纯的“社会人”、“理性人”,固然不够,而单调的“生活人”、“感觉人”、“意象人”,这也不够。真正的人,该是传统与现代,理性与生命,文化与本能的“合一”。作为“人学”的文学,在对“人”的各种层面、各种本质进行了局部性探讨后,是否该对“人”进行一些组合与整合?换句说说,新时期的小说,是与能在一个“独立”“完整的”“文学世界”中,同时采用多种视角,多种审美手段,表现出一个“完整的人”或者“人的完整的世界”,这是否可以成为小说创作的一个目标或批评家的一个要求?从最近一段时期的小说创作看,新时期的小说家们已经有了这种认识,并在某些作品中出现了某种“尝试”,例如,九四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这部五十万字的著作出自老作家陈忠实之手,小说以“现实主义”为主笔,兼容与吸取了种种新的表现手法,如神秘象征,荒诞变形,文化追踪与现实描述相结合等等,借历史的题材表现了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的人,在写作手法上,有人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有人认为是现代主义的,能否看成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兼用?以笔者看,《白鹿原》其实是在根于现实主义,而兼用其他手法的同时,为新时期小说创造了——独特的写作方法——神秘现实主义!小说在思想内容上,有人认为揭示了民族历史与民族人的“文化之根”,有人认为宣扬了封建文化,评论不一。然,作为新时期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写人”这个问题上,小说确实显示出一种新的努力与尝试。第一,小说在表现人的世界时,兼顾包容了人的世界的两个重要层次,社会的理性的层次和暗含的非理性的生命层次。第二,小说试图表现人的世界中各式各样的人。小说中的人,有道义文化的人,白嘉轩和朱先生;追求理想与美的人,白灵和鹿兆海;为了生存不惜作恶的人,鹿子霖和黑娃,尤其是浪子回头转而欺世盗民的白孝文,还有以女人身体来换取自家生存与救活男人的母性人,娥儿。除人物以外还有一些既有文化含义也有生命含义的“神灵”形象,如“白鹿”“白狼”“白狗”等。看罢《白鹿原》,把其中的各种“人”相加,再把人的不同层次给以整合,就能取得一个相对“完整的人”。当然,如果不是把各种人机械相加使其相对完整,而是真正在一个“文学人”身上,给以“人”的完全整体的表现,那将是更加精彩,更加符合“人”的法则,然而,对新时期的小说来说,这也许是个更高的要求,是小说的未来。
最后一句题外话:文学,作为人的灵魂的探索者与引导者,是“人学”最敏感的触须,最中坚的实体,故:文学即人学。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理性人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你别无选择论文; 读书论文; 棋王论文; 小鲍庄论文; 荒诞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