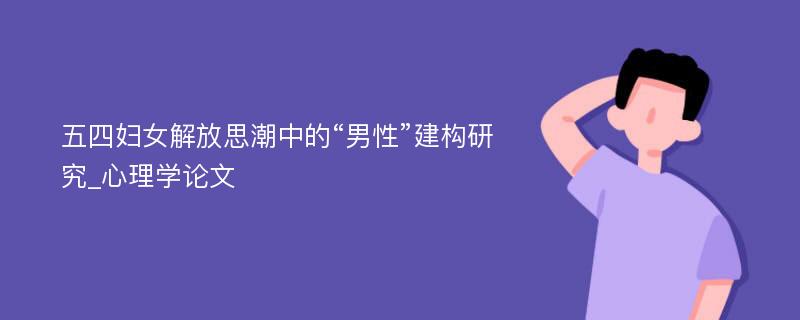
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中“男性本质”建构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本质论文,妇女论文,男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6-0034-07
在女性主义研究中,“男性本质”通常是与“女性本质”相对而言的概念,是伴随着解构“女性本质”的误区而被关注的。因而,对“男性本质”的研究似乎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
近年来,随着男性研究的渐兴,一些学者对男性气概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诸如男性气概的内涵、表现形态、其对男性地位及性别关系的影响,等等,拓展了人们对男性的认识。那么,回到历史中,探究“男性本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如何被建构的?是谁来建构的?为什么进行这样的建构?它与“女性本质”有着怎样的关系?它对男性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探索会对男性研究有一定的启发。
五四运动是妇女解放的源泉,各种思潮交融荟萃。此间,男性对妇女解放的参与是空前的,他们在建构着对女性的“解放与压迫的双重诉说”,那么,他们是如何自我建构的?这与当时的妇女解放有怎样的关系?本文主要运用文本解读的方法,探索五四时期人们运用生物学、心理学两大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男性本质”的“科学建构”。呈现它的历史功过,反观现实,窥见时至今日“男性本质”有何变化?与五四时期的建构有什么联系与区别?推进性别平等还要做出怎样的“科学”的努力?
一、建构“男性本质”的理论背景
“男性本质”一般是指以本质主义认识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理性、阳刚、粗犷等男性的个性特征。从文本来看,五四妇女解放思潮中并没明确出现“男性本质”的概念,但所谓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是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所认定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是泾渭分明的、而且被认为是由生理特点决定的,是“自然”的、“本质”的,否则就是“不自然”的。所以较为确切地说,应该称其为“男性本质”。
(一)比较、分析与溯源:“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
在五四妇女解放思潮中,许多人试图从两性的特点、差异、关系等问题入手来探讨妇女受压迫的现状、根源及其解放的途径等问题,这样的思路受到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启发,同时,这些学科理论也就成为解释这些问题的理论依据。金仲华在《霭理斯的“男与女”》一文中,谈到男女的特点及其优劣问题,说道:“上述几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的力量。生物学所作的是比较的工作,就是把男女的体格状态等等拿来比较,再把动物雌雄性的种种异状拿来和人类男女相比较。心理学所作的工作是分析的工作,就是把男女各种本能上的反映与心理上的特征详细加以分析,决定何者为二性所同具的,何者为一性所特具的?及其所具的强度与生活上的效用。人类学的工作是溯寻的工作,就是从古代原始的人类中和现在世界各处未开化的民族中探寻其二性生活的关系及其在进化中所经过的状况。这三种学问都是以科学为依据的;所以简括地说,男女平等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着科学的力量”。[1]在这段文字里作者谈到,生物学所做的是比较的工作,一是将“男女的体格状态”进行比较;二是将人类的两性差异与动物的雌雄异状相比较。心理学的方法主要是分析,即将“男女各种本能上的反映”与“心理上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一是发现两性共有的特征,比较在两性共有的特征中,哪些是女性强一些,男性弱一些,哪些是男性强一些,女性弱一些;哪些是两性独有的特征。人类学则主要是溯源,溯寻“古代原始的人类”和当时所谓“处未开化的民族”中,各个时期的两性关系及其“进化”的状况。作者着重指出:男女平等问题需要这些“科学”的解释。也正是依据这些“科学”概念和理论建构的鲜明的“男性本质”,成为五四妇女解放思潮的一股激流。
(二)两性差异是高等类属的特征:生物学的解析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严复的《天演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进化论的主要观点。五四时期有许多文章介绍达尔文的“遗传”、“分衍”(分化)、“天择”“三大理论”,并依据“遗传”、“分化”、与“性择”的理论解释两性的特征与差异。认为男女两性的特征是“遗传”、“分化”与“性择”的结果,是生物进化的规律,不可抗逆,因而是“自然”的、“本质”的。一些研究者依据进化论的“分化”概念,将两性的差异解释为高等类属的属性,从而赋予两性差异以人类标识的意义。Y·D所译日本学者富土川游的《妇女的精神生活》一文谈道:“从生物学上说:男女身体上的差别,个性的不同,都是从‘分化’而进步,因分化的能力才达到今日男女身体组织的极致。例如蜗牛、蚯蚓等低级的生物,雌雄两性在同一的身体里边,最下等的,(如原生动物传染疾病之麻拉列恶malaria)几全无男女之别,所以用生物学上的事实来证明,男女的所以差别,是分化到达极点的结果。”[2](P108)富土川游认为在生物界中,高等生物才有分化的能力,低等生物雌雄一体,无男女分别。人类男女身体上的差别是“分化”的结果,个性也是分化的结果。因此,两性差异是高等类属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两性差异在这里不仅指生理特征,也包括个性特征。可见,个性特征被解释为生物进化的结果。质言之,涵盖生理特征和个性特征的两性差异,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进化的结果,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这就为两性差异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前提。
(三)个性特征是铭刻的性别标志:心理学的概念框架
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男与女》晚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35年面世,是霭理士第一本关于两性问题的著作。五四时期,一些研究者直接运用霭理士的《男与女》中的“第一义性征”、“第二义性征”、“第三义性征”等概念解释两性的个性特征。金仲华在《霭理士的“男与女”》一文中指出:“男女在生殖的主要机能以外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区别即霭理士所谓的‘第二义性征’(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与‘第三义性征’(Tertiary Sexual Character)者:第二义性征乃是一性所特具的征状,其直接的作用可以使异性见了这种性征而受到强烈的吸引;所以这是辅助两性的主要作用的。第三义性征不一定是一性所特具的,但在一性中这种征状常较显著,而且发出来极具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常有一性对于某项事件特别擅长,一性对于某样能力特别短缺,就是这种特征的关系。就学理上说,第二性征是如此的简单,但实际所包括的范围及其表现于生活上的幅员却是极广大:在生理上人体各部器官的构造及机能都显示着这种自然的区别,在心理上从感觉,行为,意识,情绪,智慧,艺术倾向,以致环境适应等等都有着这种性征的或多或少的影响”。[1]作者根据霭理士的解释,将“第二性义性征”解释为性器官以外的生理特征,这些特征是某一性别所独有的;而“第三性特征”,则为两性共有,但某一性别在某些方面比较擅长,主要指感觉、知觉、意识、情绪、智慧、行为、艺术倾向、环境适应能力等等心理特质,即通常所说的个性特征。这里对第二、第三性特征的解释将生理特征与社会建构的特征混为一谈,统称为性别差异,并认为第二和第三性特征是两性差异在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的不同表现,即生理性别不同,心理和个性特征则殊异。显然,这种解释将两性的心理差异和生理差异等量齐观,忽略了心理差异的社会影响因素。虽然文本中也提到了社会环境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作用,但仍然将其解释为不可改变的事实,作为铭刻的性别标记。简言之,作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再次建构了两性的差异——所谓男性、女性的心理特征为不可改变的本质。
此外,一些研究者依据卫宁格尔的理论,认为个性特征是“微妙的内奥的实质”,“科学的男女区别”在“内奥的实质中”。默之在《妇女解放的原理——日本狄原朔太郎作》一文中指出:“卫宁格尔的理论所说,男女的科学的性的区别,决不仅在外貌和生殖器的外部形态,实际的男女区别很复杂,潜伏于性格内部的倾向气质等微妙的内奥的实质中。”[3]这里所谓“性的区别”是指性别差异,在五四时期的许多文本中“性”与“性别”同义。作者批评只从外貌和生殖器的外部形态认识两性差异的倾向,阐释只有从“内奥的实质”方面认识两性的差别才是科学的。所谓“微妙的内奥的实质”是指“性格内部的倾向性气质”。运用这一概念解释两性差异,呈现出智识与悖谬并存的两种认识。一方面,发现并驳斥了刻板的性别气质与角色,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默之在《妇女解放的原理——日本狄原朔太郎作》一文中说道:“世间实际有多少的‘像女子的男子’和像‘男子的女子’啊。关于男女的真正的区别,毫没有严格合理的批评,只依据了肉体的外观,作皮相的习俗的区别”。[3]作者认为只从“肉体的外观”,从“皮相”方面,认识男女的区别是表象的传统的认识。实际上有些人生理上是男人,但是具有所谓女人的特征,有些人生理上是女人,但实际上拥有男性的特征。这些人不是“本质上”的男人和女人。这里所谓男性和女性的本质特征指的是性别气质。作者进而批评基于生理性别的角色培养和分配,认为这是“不自然的,残酷的,荒谬绝伦”的事。指出:“例如,我们只因了某种表象的缘故,一生下来就被认为‘男’,被称作男子,被当作男子加以教育,而且还被强施着当兵的义务哩。我们如果真是本质的男子,性格上都完全男性,这样的境遇,不消说是适切的吧。倘我们是女性的性格者,是不能忍耐军事训练的柔和者,那我们就不适于一切的环境,先在世上无端要被斥为不是丈夫,受那毫无理由的排斥与轻蔑了。其实,我们的境域并不是自己选求的,我们自己并不要想编入男性的队伍里。”[3]作者认为,男性并非都拥有男性本质特征,也有具有女性特征的性格“柔和者”,他们不适合如军事训练等男性角色行为,常常被蔑视为“不是丈夫”,这种情况并非这些男性自己的选择。那么为何如此分配角色?作者认为是没有看到男人和女人“内奥的本质”,只根据生理特征培养和安排的缘故。“内奥的本质”和外表的特征之不同是如前所说的男人也有女性性格者。而作者为什么会如此反省?一是基于感同身受的现实的思考,二是受到自由主义理念的启发,认为人应该有选择的自由。此外,作者认为这种刻板的角色培养和安排对于女性来说,则“更加残酷”。指出:“假定这里有一个人,其性格全是男性的,几毫没有女性的成分,只因了肉体的某部分有着女性的外观的特色,生下来就被认为女子,强施以女子一切的教养,责备她具有女子的行为与情操,社会方面亦强制地硬责其为女子,这不消说是一种不自然的,残酷的,荒谬绝伦的事吧。可是,我们的社会却毫不客气地把这种野蛮残酷的事行着!”[3]作者认为,女性中有完全是男性性格的人,生下来却被强行施以女性的教化,培养女性的教养、情操与行为方式,这是不自然(违背自然规律)、残酷的、荒谬绝伦的事情。因为这是违背某些女性“内奥的本质”的。同时也可见作者对传统女性道德与行为方式的痛斥与鞭挞。此外,作者又依据这一认识发现了若深入“内奥的实质中”去看,男性和男性之间、女性和女性之间就有很大差异。男性和女性都有跨越其本质特征的。进而依据“第三性义征”的概念将男人和女人分为有男人本质的男人和有女人特质的男人、有女人本质的女人和有男人特质的女人。这样的划分,较之将女性和男性分别作为无差别的群体看待,无疑是个进步。
另一方面,所谓“微妙的内奥的实质”、“性格内部的倾向性气质”这一认识,已将性别气质作为不同性别的固有特征。研究者据此批评人们没有发现其“微妙的内奥”,是心理学启发了对这一“内奥”的认识。可见人们借助心理学将两性的社会性别特征还原为生理的派生物。这是一个微妙的转化。人们以为自己在性别的认识上依靠科学的力量前进了一步,其实却又设置了新的认识屏障,即,非但没有解释社会文化在个性特征形成中的作用,反而将其解释为生理特点的延伸。将生理特征与社会特征划为一体,统称为性别本质,这是一种“科学”的“结构”,加之没有科学的“解构”,而流弊颇深。
总之,以上将两性差异作为生物进化的“极点”和高等类属的特征,将感觉、知觉、意识、情绪、智慧、行为等个性特征作为本质属性,为进一步建构男性本质和女性本质作了基本认识和概念的铺垫,即赋予两性差异以科学的价值,为进一步建构两性特质解决了认识上的问题:两性差异不仅是存在的,而且认识两性差异才是科学的态度。心理学关于第一、第二、第三义性征的概念,为男性、女性本质的建构提供了概念框架:将个性特征作为“内奥的本质”,将本质特征从生理性别延伸为社会性别,将男女在社会中形成的差异也“收编”为“本质”,作为不可改变的事实。
二、“男性本质”的主要特征
五四时期人们依据生物学、心理学建构的“男性本质”与现在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阳刚、理性等特征有许多吻合之处。关于阳刚的内涵当时突出两点:一是身体的强壮,二是性的欲望。显然,这样的解释带有生物的特征,而社会特征则显不足。从五四时期的文本来看,一些研究者对男性特征的阐释,主要依据达尔文进化论的“性择”理论。此外,还有研究者依据作为19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的细胞学,解释两性地位的演变,集中为“男性中心说”与“女性中心说”,即为在生殖过程中,是以“娘细胞”为主,还是父细胞为主的论辩。据此,衍生出所谓“男性本质”与“女性本质”。
(一)“男性开花”的取舍:刚与强
“男性开花”是高希圣在《男性中心说与女性中心说》中提到的概念,指男性在“性择”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外观的美丽。文中指出:“一方面女性的选择是煽动了男性的嫉妒心,引起了男性间激烈的竞争,竞争使牠们的体格更有强大的必要。而女性选择的趣味性,不只在体格的大小,于是又激成了男性外观的美的特质,孔雀、极乐鸟、鸳鸯等雄者外观上的美丽是人所知道的。男性身体的强大美丽是女性淘汰的结果。——他们为了抵抗同种属的男性,遂使武器体格发达了,这些武器体格决不是用来征服女性的,而只是为了获得女性的选择。所以与其说是为了真正的斗争,不如说是使女性见到互相战斗的样子,以希求她们的选择,还有一半则带着装饰的意义。”[4]高希圣在这里运用了“性择”的概念。认为“男性开花”是男性在“性择”过程中,女性淘汰的结果。关于“性择”,达尔文曾经这样阐释:生物“在家养状况下,有些特性常常只见于一性,而且只由这一性遗传下去;在自然状况下,无疑也是这样的。这样,如有时所看到的,可能使雌雄两性根据不同生活习性通过自然选择而发生变异,或者如一般所发生的,这一性根据另一性而发生变异。——这种选择的形式并不在于一种生物对其他生物或外界条件的生存斗争上,而在于同性个体间的斗争,这通常是雄性为了占有雌性而起的斗争。其结果并不是失败的竞争者死去,而是它少留后代,或不留后代。所以性选择不如自然选择来得激烈。一般地说,最强壮的雄性,最适于它门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它们留下的后代也最多。但在许多情况下,胜利并不靠一般的体格健壮,更多地还是靠雄性所生的特种武器。无角的雄鹿和无冠的公鸡很少留下大量的后代——盾牌在获得胜利上也像剑和矛一样。——这样,任何动物的雌雄二者如果具有相同的一般生活习性,但在构造、颜色和装饰上有所不同,我相信这种差异主要是由选择所引起的:这就是由于一些雄性个体在它们的武器、防御手段或者美观方面,比别的雄性略占优势,而这些优势状况在连续世代中又只遗传给雄性后代。然而,我不愿意把一切的差异都归因于这种作用:因为我们在家养动物里看到有一些特性出现并为雄性所专有,这些特性分明不是通过人工选择而增大了的。”[5](P38-39)
达尔文发现在生物中,有些特征是一性所具有的,并且传给这一性的后代。他认为这种情况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因为另一性别的选择引起的。将其名为“性择”,并指出,“性择”不同于一种生物对另一种生物以及外界环境的生存竞争,而是个体之间的斗争。在“性择”中获胜者往往凭借“特别武器”。正是这所谓“特别武器”成为某一性别的特征。它既是“性择”的武器,又是“性择”的结果。达尔文的上述论述较为关注雄性的选择及其身体和个性特征的特点。高希圣依据“性择”的理论阐释“女性中心说”,称鸟类和哺乳类的雄性强大而美丽为“男性开花”,认为它是男性“性择”的武器,也是女性选择的结果,不是个体的生存竞争,而是为了吸引异性,繁衍子孙。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性别文化并没有将生物界的“男性开花”像女性美一样,完全转化为男性的本质特征,而只是彰显了“男性开花”中“强壮”的特点,隐去了色彩、美丽的特征,这显然是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选择。这种选择对社会性别特征和性别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见,女性本质或男性本质的建构对当时生物学观点的利用是有取舍的,是一种再建构的过程。即将强壮不仅作为男性的生理特征,而且转化为基于生理的不可改变的社会特征,舍弃了具有装饰意义的色彩和被看功能的美丽,凸显男性的强大,并将其解释为生物学的发现,使其具有无可置疑的科学意义。这样更有利于男性的社会权力、地位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二)“性择”的结果:理性
在传统的性别文化中,理性被视为男性的特征,女性则被认为更富于感性。在五四时期的一些文本中,理性这一男性社会性别特征也被解释为“性择”的结果,从生物学的角度给予科学的强化。高希圣在《男性中心说与女性中心说》谈道:“理性是指就最最单纯最最具体的事物加以推理考究的心的作用。这种原始的理性是从利己心出发的,在起初是单以更优良地确保欲望之目的物为他的目的。人类以外的动物都是以本能之力来维持女性的优秀,防止种族的破灭。因为女性是以育儿分娩等尽力持续种属的——男性和男性为了要求女性的选择,互相间发生激励的竞争时,体格强大而伶俐的男性当然是处于有利的地位,这又成了促进男性脑髓异常发达的原动力。人类的发达日益显著,于是遂脱离本能的支配,像其他动物那样会引起种族之灭亡的危险没有了。到这里,男性利用优秀脑筋与强大体格的活动以压迫女性终至连生物界最大特权之女性的取舍选择权也都夺取了。”[4]在这里,高希圣将“原始的理性”解释为“心的作用”,表现为“推理、考究”的能力,这种能力导致自我欲望的实现,是利己心的表现。认为动物界为了种族的延续,以本能的力量(非理性的)维持女性的中心地位,而人类在男性间争夺女性的竞争(性择)中,不仅发展了强大的体格,而且促进了脑髓的发达,即发展了原始的理性,并凭借理性解决了种族延续问题,从而走出自然界。拥有理性的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是进化了的人类,并代替了如同自然界的女性中心位置。文中还论及,理性的力量使男性产生了“父之意义的自觉”,即男性认识到了自己在人类繁衍中的作用,从而在男女间发生了“大革命”,即男性代替了女性的中心地位。五四时期,一些男性思想家一方面反省男性的自私,主要是针对压迫女性而言,另一方面又在界定男性由于理性而高于女性的性别等级,在高希圣的论述中也可见到这样的痕迹。同时,又可以看到这样的逻辑:理性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被界定为男性的特征,而在当时理性主义哲学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理性被看作人的本质特征,那么拥有理性的男性就成为高于女性的人类,而女性则为接近于自然的“他者”。质言之,女性作为社会中心位置被男性取代,是因为在进化过程中没有发展出理性。理性既然被作为生物进化的结果,作为“性择”的产物,就与生理特征结下不解之缘。从而,理性作为男性的本质特征就被生物学穿上了科学的外衣。“男性开花”被作为“浮游”的装饰而显得可有可无,甚至被舍弃。
(三)“大自然的命令”:性超于生存
五四时期的一些研究者,根据进化论以及细胞学中所揭示的动物、植物的生命规律,阐释了男女在两性“交合”中的不同角色,认为男性的性欲不仅强于女性,而且高于生命。心理学则推波助澜,将男性的性的力量解释为想象力、创造力的源泉。高铦在《性择》一文中指出:“在性欲一端说来,男性是主动,女性是受事。在种属女性是中心。”[6](P10)在这里,高铦谈到了男女在性的欲望与保存种属两个层面的不同角色,他认为在男女“交合”中,即在性的欲望方面,男性是主动的进攻者,与男性相比,女性是被动的接受者;而在保存种属方面女性是主体,即女性是生命的“蕴能”者。或者说,男性的性源自人的本能,是主体的巨大的欲望力量;女性的性源自“存种”,目的是孕育生命,自始至终是与主体(女性作为人的本性)相分离的。如此,女性同样作为人的性的欲望被隐去了。这其实是对生物学的文化建构,然而,却被作为生物学的结论本身。在此基础上,高铦又以自然界的生物现象为参照,进一步解释了上述观点:“异性相爱的性质和生命同在,就是本能,这本能是女性可以选择的根本:就是男性底性欲,超过生存欲。忘了痛苦,忘了生命,去忠实奉行大自然命令的原故。”[6](P10)在这里,高铦说明了两层意思:其一,异性相爱是一种本能,与生命同在。其二,男性的性欲可以超越生命,即男性为了得到了异性爱能够放弃生命,这是自然界的法则。高铦还以雄蜂和雄性螳螂“视死如归”的例子作为佐证,说明男性性欲的不可遏制,甚至高于生命。由这种观点又衍生出另外的一种解释,即男性的欲望需要女性来控制,男性的过错是女性的责任。因为男性的欲望具有多变性、无节制性、无方向性的特点。如果放任男性的特点,人类的种属将要全部紊乱。而女性的性欲具有沉稳、持重的特点。因而,人类的两性关系,需要女性的沉稳来控制男性的狂放。这样的解释,给女性的内敛乃至性压抑、男性的主动甚至攻击、男性的过错需要女人负责等社会性别规则提供了“科学”依据,将两性关系的文化规则再次转化为生物规律。
此外,男性性欲的奔放还被解释为“力的源泉”。霭理士认为男子的艺术能力产生于恐惧、欲望和疯狂,女性正是由于缺乏“各种冲动浮现到表面上来的心理作用”,所以“想象力特别缺乏”。霭理士举例说明,疯狂的男子具有奔放不羁的胡思乱想,“疯狂妇人完全缺乏对于错乱思想的创造力”。关于性欲力量对艺术想象力的影响,他认为:“妇女的性生活的幅员虽较男子广博而浩大,但其表现的力量则不如男子的强佛。在男子性的本能乃是力的奔放端的源泉,常泛于一切的通路。所以当春机发动期来临——艺术的冲动也已经发生。”[7]他认为,男子性表现力的强大,常常可以带来创造、想象的思路,所以男子“春机发动”时,艺术的冲动也随之发生。男子的性本能是“力的奔放的源泉”。霭理士的结论是“艺术的冲动是一种男性的副特征,正如胡须之于男性一样,虽然不能毫无辨别地承认下来,但似觉颇近于真理。”[7]这一结论与霭理士“第二义性征”的概念十分吻合。即将后天形成的个性特征转化为生理性别特征,并据此安排两性的社会分工、期待与评价。
三、结论与讨论
在五四奔腾激荡的妇女解放思潮中,“男性本质”的建构是一股激流和潜流,裹挟在许多议题之中,似乎并不令人瞩目。然而,在人们以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为背景的强力打造下,凸显出男性的强大、理性、“奔放的性欲”以及与此相关的创造力等特征,深嵌在性别文化之中。这其中,男女的性爱被作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建构的逻辑起点和内在标准。关于这一点,默之在《妇女解放的原理——日本狄原朔太郎作》一文中曾经谈道:“男子如果离开了柔美的曲线,美的貌,宛淑的性情,快活,绰约等等一切女性的魅力,对于女子怎能发生性的爱呢?人是一种本能的动物,性的关系是必然的电器的法则。”[3]从这里可以看到:作者认为性爱是人的本能。异性相吸是自然界的法则。虽然异性相吸犹如电器的两极,是双方的,但是,如前文所述,男性的性欲是主体的奔放不羁的欲望,而女性的性欲则由于存种而内敛、沉稳,所以,从尊重人性的角度上说,男性的性欲望更应该满足。女性要拥有美丽的容颜、优美的曲线、贤淑的女德这些所谓女性特征才能燃起男性的性爱之火。可见,性爱是构建性别特征的逻辑起点,能够燃起男人的性爱之火即是女性特征的标准。
此外,许多文本反映出,五四时期一些研究者热衷于运用进化论来解释两性差异,这一问题可以从进化论在社会思想史中的地位窥见一斑。众所周知,进化论是19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费孝通曾经对它的重要意义做过如下论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它作为新思想的先锋突破了旧有意识形态的封锁线。达尔文把人类也纳入了其他一切生物的统一发展系统之中,也就使人类成了可以作为客观事物来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8](P554)进化论在当时的意义在于挑战“神创论”的世界观,将人类纳入生物的范畴来研究。五四时期学术界运用进化论解释两性差异,显然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将其作为认识人类及社会的新思想、新方法。严复系统地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旨在使国人了解“物竞天择”的生物进化规律,“以唤醒中国人保种自强,与天争胜,变法图存”。[9](P9)五四时期是中华民族面临家国危亡、企盼科学救国的社会转型期。对封建传统的反叛和对科学的渴求,使人们拿起这一科学的武器,解释人类及其社会现象。当时的妇女解放思潮回应了富国保种的政治诉求,人们关注怎样的男性和怎样的女性才能担当起富国保种的任务,进化论便成为解析男女两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工具。
至于人们运用心理学的一些概念对于“男性本质”与“女性本质”的建构,最主要的特点是看似将生理特征与社会特征混为一谈,浑然一体,实际上将社会特征转换为生理特征。与此呼应的是严复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曾经纠正、改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将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论与人类社会关系、道德哲学分割开来,而主张自然与社会的统一,熔宇宙自然过程与社会伦理过程于一炉,即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5](P38-39)可见,当时学术界有些主张自然与社会合一的倾向。这对心理学将生理与社会差异融合一体有些微妙的影响。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五四时期人们对“男性本质”与“女性本质”的建构是对妇女解放思潮与行动的回应。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反对妇女解放思潮中男女平等的主张。认为男女平等就是“男女均等”,就是男女都一样。对此,依据心理学两性具有不同的“内奥的本质”的观点,对其进行批评,认为这是“不自然的”,违反自然规律的。换言之,“男性本质”与“女性本质”的建构是为了纠正当时妇女解放思潮中“激进”的主张。另一方面,是为了解释、支持妇女解放主张。认为既然有些女性具有与男性一样的“内奥的本质”,就必然要求做和男性同样的事,诸如教育、就业、参政,等等,强制她们做女性也是“不自然的”,是对自由的压制。
五四时期建构的“男性本质”特征与现今的男性气质有怎样的联系与区别?事隔将近百年,这些文化传统有哪些方面值得继承和扬弃?“解铃还需系铃人”,科学的结构还需科学的解构与建构,更何况进化论与当时的心理学、人类学、细胞学本身就有很多局限,到了现代又有许多新的发展,应该怎样运用新的成果重新解释两性问题?学术界应该对先进性别文化建设担负起怎样的责任?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