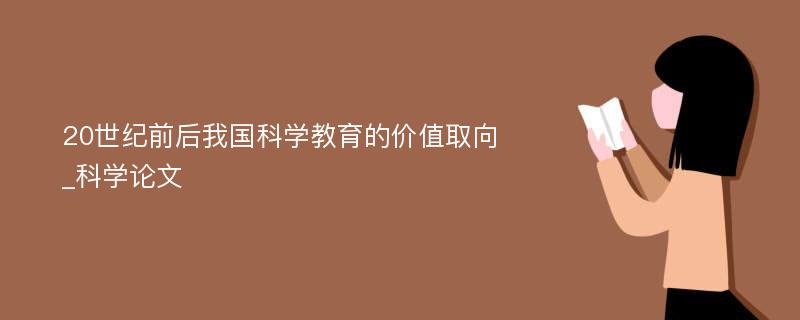
20世纪前后我国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取向论文,我国论文,科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地看,20世纪前后国人对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这一演变的路径如下:即从负向价值取向到正向价值取向,从物质层面的价值取向到思想层面的价值取向,从单一维度的价值取向到多元维度的价值取向,从社会救亡的价值取向到个人生活的价值取向。
从否定科学教育的负向价值取向到认同科学教育的正向价值取向。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被逐渐引入中国。以坚船利炮为前导的西方文明,首先以“器”和“技”的形态呈现于晚清士大夫的眼前。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的理解先从“器”和“技”层面开始。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中,西方的科学技术主要被理解为“器技”。在尔后的洋务知识分子中,科学逐渐由“器”和“技”提升为格致之学。在器与技的层面,科学技术的价值主要以物质文明的形态得到展示;随后以数学、电学、光学等为表现形式的格致之学则开始取得理论的形态。从“师夷长技”到“格致为基、机器为辅”,这已表明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己超越了器与技的物质层面,使科学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理论形态。对不依附于器与技的科学的认同,为科学教育价值的认同提供了历史的前提条件。顽固派极力否定科学教育,认为科学教育具有负面的价值,使当时的科学教育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他们“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注: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当总理衙门奏请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时(1866年),就遭到顽固派的责难,爆发了礼义之学与技艺之学的论争。顽固派从封建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出发,强调“立国之道尚礼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由此可见,科学教育在我国起步之际,顽固派以本能的抗拒心态否认科学教育的作用。但是,由于中西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冲突,出于富国图强的历史需要,洋务派终究占了上风。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教育突破了传统封建教育的框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使中国近代的科学教育获得了初步的发展。科学知识被引进科举考试,1887年,在科举考试中添设算学一科。1905年,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废止。在近代洋务知识分子看来,学习西方科学的价值在于“以利于用”,科学教育能提高制造军事武器的技艺水平,以消除外来的军事威胁。科学教育的这一正向价值取向,对于19世纪末的中国启动科学教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科学教育在近代教育领地中争得了一席合法的地位。《清会典》记载有京师同文馆的教育内容,其中格致之学包括七大部分: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通过教学,要使学生懂得力的吸压之理、水的动静之性、声的响应之微、气的蒸化之方、火的腾热之方、光的回返之理、电的触引之捷。此外,考动植之学,以教树蓄长地力,蕃物类,节人工,亦皆格致之属焉。
从物质层面的价值取向到思想层面的价值取向。洋务知识分子对科学教育价值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的制约,他们认为科学教育的价值在于物质层面。自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见孙培青、李国钧主编:《中国教育思想史》(第3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之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洋务知识分子的普遍思维模式,同时也是洋务派办学堂、培养人才不可须臾背离的指导思想,所谓西学,首先便指西方的科学(格致之学),而所谓中学,主要指儒家的纲常名教。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在洋务派看来,科学教育的价值在于它具有物质层面的“实用”的价值,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科学教育对人的思想与精神的影响。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被迫向日本割地赔款,紧接着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外患的不断冲击,引起了近代思想界的强烈震荡。19世纪后期,维新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较之洋务派,维新思想家更多地将目光由形而下的器与技,转向到形而上的思想观念层面。与之相应,对科学的理解和阐发,也往往与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相互融合。维新知识分子超越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念,开始认识到科学教育具有社会思想启蒙的价值,严复可以说是其典型的代表。严复认为,科学教育能够变国人的“心习”,变的方向是尚实求真。科学是“吾国所缺乏而宜讲求者”,学习科学是“当务之急”,“中国此后教育,在最宜著意科学”。它“不独于吾国变化士民心习所不可无,抑且为富强本计所必需”。严复认为,科学具有改变“心习”(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势)的作用。他说:“欲变吾人心习,则一事最宜勤治,物理科学是也。……一切物理科学,使教之学之得其术,则人人尚实心习成矣。乌呼!使神州黄人而但尚实,则其种之荣华、其国之盛大,虽聚五州之压力以沮吾之进步,亦不能矣。”(注:严复:《政治讲义》,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2页。)作为变的对象,“心习”主要是数千年来积累和沉淀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以严复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认为,科学教育具有“炼心积智”、“变吾心习”、“黜伪崇真”的价值。严复的科学教育价值观对于一向以伦理道德空洞说教为圭臬的封建教育来说,是针锋相对的。相对于洋务运动时期科学教育物质层面的实用价值取向,以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科学教育与人的精神世界有所关联。
从单一维度的价值取向到多元维度的价值取向。洋务知识分子对科学教育价值的认识,局限在单一的物质层面的维度上。自维新知识分子开始,科学教育的多维度价值就受到重视,如严复就区分了科学的两种价值。他认为,各门科学有“专门之用”,也有“公家之用”,前者指科学的实用价值,如“算学则以核数,三角则以测量,……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后者指科学的非实用价值,即他所讲的“炼心”的价值。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了科学教育的多维度的价值。20世纪初,近代国人对科学的认同有了较为普遍的思想基础,经过不断泛化的科学开始被提升为一种主义,并多方面地渗透到知识学术、生活世界、社会政治领域。科学趋向于在知识领域建立其霸权;以走向生活世界为形式,科学开始影响和支配人生观,并由此深入个体的存在领域。通过渗入社会政治过程,科学进而内化于各种形式的政治蓝图设计。在相当的程度上,科学已超越了学术领域而被视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胡适对这一时期的科学思潮有过评述。他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敢公然毁谤‘科学’。”(注:张君劢等著:《科学与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科学在文化领域似乎已成为一种主流话语,对科学的广泛认同为认识科学教育多维度的价值提供了宽松的文化氛围。20世纪初,人们对科学教育价值的认识呈现一片多元化的景观。科学教育的多维价值取向可从社会与个人两个主体、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维度来剖析。蔡元培在科学教育价值问题上的认识,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初国人的价值取向。蔡元培认为,科学以物质世界作为变革的对象,科学教育具有发展经济的潜在价值,同时科学以主体(社会主体和个人主体)的观念作为变革的对象,通过观念的转换而改变社会思想与个人的精神世界。科学教育具有多元维度的价值表现在:第一,科学教育立于现象世界,具有实利主义价值。面对民国初年百业凋零、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的现实,实利主义教育于国家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救时之必要”,促进国家的繁荣富强;于个人可以改善生活,使个人获得幸福。第二,科学教育于实体世界表现为改变思想观念,于社会可以改造传统宗法人伦文化,“打破两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于个人可以发达人的精神。“智育则属精神方面。精神愈用愈发达……盖人之心思细密,方能处事精详。而习练此心思使之细密,则有赖于科学。”(注:《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8页。)蔡元培对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他从个人与社会两个视角来审视科学教育的价值,既看到了科学教育的实用价值,又认识到了科学教育的精神价值。20世纪初,鲁迅、胡适、丁文江、陈独秀等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在科学教育价值取向问题上的阐述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科举教育具有发展生产力的实用价值。鲁迅说:“自然之力,既听命于人间,发纵指挥,如使其马,束以器械而用之;交通贸迁,利于前时,虽高山大川,无足沮核(即阻隔);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举工业之械具资材,植物之滋殖繁养,运动之畜牧改良,无不蒙科学之泽。”(注:鲁迅著:《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2页。)第二,科学教育能够影响人生观。唐钺就认为,人生观是因知识而变的。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影响到人生观的变动。唐钺的看法意味着科学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第三,科学教育可以克服人性的弱点。陈独秀认为,科学内在的理性可以克服无知与迷信的人性弱点。他说:“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尊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20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高举科学的旗帜,意识到科学教育的价值是多维度的,人生问题、道德问题、思想问题、人格问题、个性问题等无不与科学相关联。他们认为,通过科学教育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对个人和社会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从社会救亡的价值取向到个人生活的价值取向。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同样认同科学教育的社会救亡价值。如,丁文江认为科学能够促进物质文明,进而提升精神文明,发展科学可以避免国家遭受列强的侵害。他指出,“懒惰的人,不细心研究历史的实际,不肯睁开眼睛看看所谓‘精神文明’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肯想想世上可有单靠内心修养造成的‘精神文明’;他们不肯承认所谓‘经济史观’,也还罢了,难道他们也还忘记了那‘衣食足而后知礼节,仓廪实而后知荣辱’的老话吗?”(注:张君劢等著:《科学与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在丁文江看来,中国几个世纪的修身养性产生了一种虚幻的优越感,而对实际事物却毫不理会,终于招致中国被列强征服的后果。20世纪初有的思想家就认识到科学教育与个体生命、生存、生活的关系,反映出科学教育的个体生活价值取向。胡适曾分析当时的个人生活因缺乏科学而产生的种种恶果。小孩出痘出花,都没有科学的防卫。供一个“麻姑娘娘”,供一个“花姑娘娘”,避避风,忌忌口;小孩子若安全过去了,烧香谢神;小孩若遇了危险,这便是“命中注定”!胡适还意识到妇女生小孩时缺乏科学知识的落后现状,他说,我们今天还把生小孩看作最污秽的事,把产妇的血污看作最不净的秽物,这大概是野蛮时代遗传下来的迷信。但这种迷信至今还使绝大多数人避忌产小孩的事。所以,“接生”的事还在绝无知识的产婆手里,手术不精,工具不备,消毒的方法全不讲究,救急的医药全不知道。顺利的生产有时还不免危险,稍有危难便是有百死而无一生。就个体的精神生活来说,胡适甚至认为科学使人生充满诗意、美感和幸福。“空间之大只增加他对于宇宙的美感;时间之长只使他格外明了祖宗创业之艰难;天行之有常只增加他制裁自然界的能力……总而言之,这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里,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智慧’的机会。”(注:张君劢等著:《科学与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3页。)胡适已意识到科学与个人精神生活的关联性。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期间,胡适明确提出了“科学的人生观”,力图用科学解决人生问题。鲁迅也认为西方物质文明背后还有更为根本的“真谛”,科学的根本不是科学技术导引下取得的物质成就,科学“兴业振兵”的作用只不过是科学结果的应用而已,而科学的根本力量在“立人”。
综上所述,近现代国人对科学教育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否定到初步认同再到多元理解的过程。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对科学教育价值认识上有严重的分歧,顽固派否认科学教育在社会救亡意义上的工具价值,而洋务派则认同科学教育的这一工具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为科学教育的发端提供了价值依据。洋务派企图以科学教育的实用性来弥补科举教育的空疏无用。但是,科学教育一经兴起,就不但显示出工具性意义上的“社会救亡实用价值”,而且也对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产生了冲击。到后来维新派改革教育时,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已不再聚焦于“船坚炮利”的物质层面,而是上升到了思想启蒙的高度。他们已认识到科学教育在转换社会观念上具有思想启蒙的价值。20世纪初,科学被提升为一种主义,科学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政治思想、道德伦理与个体的存在,以及人生观、精神世界等领域,人们开始认识到科学教育多维度的价值。
标签:科学论文; 科学教育论文; 科学与人生观论文; 生活教育论文; 数学论文; 读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严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