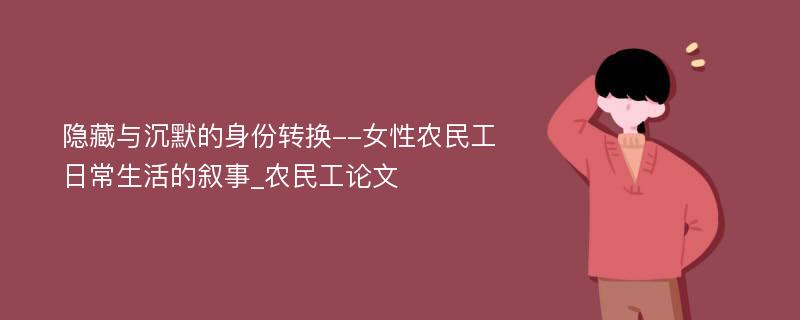
隐藏与沉默的身份转型——女性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常生活论文,农民工论文,沉默论文,身份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3)04-0055-07
一、问题的提出
“打工”简单说就是“为老板工作”,主要指在非公有制企业靠付出劳动力换取工资的情况,打工者群体主要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香港学者潘毅认为“打工一词意味着从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向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转变,打工仔/妹则是清楚劳动剥削、具有工人意识的新蜕体”[1](P12)。中国现今女性农民工的身份多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打工者。
在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中,女性农民工经常被简化成为抽象的数字和结构类型,甚至在一些主流经济学者的眼中,女性农民工就是商品或工具,她们代表了可以实现的价值和可能的利润,她们是可以被再重构和控制的“劳动力”,这些每天努力工作、忙碌的女性农民工很少被提到她们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付出的劳动和做出的贡献。但是,这些劳动着的女性农民工不仅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劳动力,还是中国社会基石——家庭的主要支撑者。特别是已婚、已育的女性农民工的打工经历、打工渴望、她们给予打工的意义、她们的打工和生活的压力、她们的成就感和挫折感等等,这些问题都远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作为女性,作为农民工,她们在打工中遇到的问题可能比男性农民工更多,她们当下的生活是明天的历史,如果不对她们今天的打工生活进行记录的话,她们很快就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变得无声无息。笔者试图尽力留下几个普通女性农民工的故事,关注她们的打工经历和生活是如何历史性地嵌入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
目前,关于农民工的社会学研究大都将农民工视为“工作主体或劳工主体”,他们往往被视为剥削(源于马克思理论)和规训(源于福柯理论)的对象,主体能动性通常在日常抵抗[1](P12-15)或是在消费领域[2]中显现。但是,这些思考忽略了“工作——通过合同或自愿交换自己的生产时间来获取报酬的活动——这一概念本身具有现代性,它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3]因此,理解农民工的“工作”不能仅仅从马克思、福柯的著述开始,而是应当将“工作”视为一个现代性概念,它本身是用来刻画一种现代性的遭遇的。同时,要理解农民工的城市工作体验,还需要将农民工的体验置于农村到城市生活史中来理解。何明杰在调查新生代服务业女工的打工生活时发现:“进城打工被新生代农民工视为人生的必经阶段,底层服务业的工作是他们转换自我的平台,具有改造合格劳动力、催化劳动者社会成人和支撑劳动者未来生活规划的三重意义。”[4]新生代女性打工者把打工视为一个“学习”与“自我提升”的过程,出生于1980年之前的已为人妻、为人母的中青年女性农民工,在从农村到城市的生活变迁背景下怎样叙述日常生活以及隐藏其中的身份转型,怎样突破主流研究的宏观叙事就是本文主要探索的内容。
二、研究立场与方法
法国人类学者皮埃尔·D.布迪厄针对结构主义人类学过于强调规则和结构而多少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倾向,提出了“实践”理论。受这种人类学取向的启发,笔者也从实践的视角出发,将中青年女性农民工视为是她们自己日常生活中具有能动性的实践者与行为者,视她们为实践着的个人。本文力求让女性农民工自己说话,突显她们的“主体性”立场:立场之一是倾听女性农民工“自己”的打工和生活故事,并把这种“自己”定义为“主体性”,一种对生活和打工的感觉、经验和意义的独立叙述和反思。这些叙述和反思表明女性农民工不是“市场”、“农村”、“城市”等结构因素下的被动者,她们的打工史反映着她们的个人能动性、选择的多样性和创造自主生活的潜力;立场之二是作为主体的女性农民工并不是抽象的个人,每个女工都是独立的个体,她们有特定的生活处境和生活策略,也正因如此,女性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和生活中的个体体验,对打工的不同叙述所暴露出来的社会含义,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生活轨迹所折射出的女性变化,正是本文力求探索的主题。
在写作的过程中,女性农民工的“主体性”更多地变为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从方法论角度看,女性农民工的“主体性”可以成为一种写作与叙述的手法,她们作为主体的叙述打破了传统“他者”地位的叙述,这种叙述本身足以明确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决定以女性农民工为主体,用她们的语言、经历和感受展示她们对打工的理解,将她们有关打工和生活的行动、观念放在她们自身经济条件、文化情境中去理解,力求对女工有一种符合她们生活经验的理解。本文就是运用叙事研究的质性方法,突出女性农民工的叙述/生活故事作为文本的分析。
三、女性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叙事
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笔者对一位女性农民工的跟踪调查。冰然(化名),女,1978年生于河南濮阳的农村,现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正上初一,女孩尚在幼儿园阶段,丈夫在服装厂做烫熨工。笔者是经工友NGO机构“家园”认识受访者的,在2012年7月对受访者正式访谈两次,时间共计3小时,访谈地点均在“家园”。笔者还去受访者的自租房进行了探访,并与她有QQ联系。本文就是建立在笔者实地考察与访谈的资料基础之上的。
冰然在初中一年级时就因为家庭贫困辍学了,第一次外出打工去的是青岛的冷藏厂。据冰然讲,冷藏厂加工鱼挺累也挺脏,睡的是地铺,而且是通铺,一个挨一个。冰然干了1个多月就逃跑回家了,因为扒鱼皮累得膀子疼干不了,最后发了300多元钱。回家后经亲戚介绍,冰然与同乡的丈夫订婚,见了两面后,19岁的冰然就结婚了,丈夫比她大4岁。婚后冰然在家种地,但时间很短,后与丈夫去北京打工,在儿子5岁时开始到青岛打工,一直到现在都做服装厂的普通缝纫工,期间因为女儿曾做过短暂的幼儿园保育员。冰然现在与丈夫、女儿住在10余平米的自租房里,儿子在老家读私立初中。
冰然对在城市的打工生活整体上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从农村到城市,冰然经历的是两种不同的生存环境、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体验到的是在城市打工的自由和便利,同时也承受着城市打工带来的母子分离之痛与紧张困顿。
(一)从农村到城市,感受自由与便利
讲到种地,讲到农村,冰然坚决的否定语气留给笔者很深的印象。从种地到打工,从农村到城市,笔者分明感受到冰然毫不犹豫地对城市的向往之情和对农村的排斥与否定。
1.从种地到打工,获得解放与自由
“种地累得哭了,再回去种地更种不了了。在这里打工挺好的,主要是种地又累又脏又热,也种不了,打药什么的,我干不了。在家里除了种地还得干家务,觉得出来还挺舒服的。”
从农村到城市,“进城”的最大转变是生存方式的变化,对于冰然,就是摆脱了在农村种地。从冰然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脱离种地带给她的“轻松”,在经历过农业生产、农村长期生活的冰然看来,农村绝非一个浪漫的场所,尚未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并不仅仅是与自然亲近,而是代表着又脏又累又热的农活,与这样的农活相比,“打工挺好的”。更深入地分析冰然对种地的态度不难发现,她对种地的排斥和反感不仅仅是对一种劳动方式的态度,更深层次的是对与种地相连的农村生活方式的排斥和反感。
英国历史学家埃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生动地分析了随着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一种新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概念的形成:“前工业”时期的劳动形式具有不规则特性,深受自然节奏的影响,时间感是以任务为导向的;而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新的社会分工、金钱刺激,一种精确的时间纪律开始形成,由此带来的是工作与生活的区分,时间和劳动力的商品化[5]。要理解冰然的城市打工体验,我们还需要将她的体验置于农村—城市的生活中来理解。
在农村,农民是根据冷暖晴雨安排劳作和组织生产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村落里的生活是单调的、简单的、重复的、轮回的。种地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工作”,在时间的体验中,也不存在工作时间和生活(休闲)时间的严格区分。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更不会有严格规定的劳动指标,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时间。但是,农民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不得不应对繁琐而无休止的劳作。这种劳动与生活界限的模糊让很多返乡的女性农民工抱怨“家里生活繁琐”。对于许多女性农民工来说,农村的家庭经济不仅意味着繁重的家务活动,而且她们的劳作经常被视为“自然”、“细微”的家务活,虽然在家有很多清闲时间,但这些清闲时间大多是分割的。这些支离破碎的“清闲时间”不是她们种地之余用来消费的“清闲时间”,而是需要消磨的时光,这让女性们觉得时间需要自己“混过去”。而城市打工的工业时间表划分出了一个人特定的工作时间,然后其他时间属于自己的个人生活时间。在城市打工,工作与生活的分离使工作之外的时间成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些自由的时间给女性农民工带来了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安排的主动性,并由此产生“被解放”的感觉。
进一步理解这种自由和被解放的感觉还需要与女性特殊的性别角色联系起来。在农村,已婚已育女性的角色定位基本上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意味着不仅要下地干农活,还要照顾家人和操持家庭事务,主妇的生活是忙完地里的活忙家里的活,没完没了的。而在城市的打工是有钟点的,下班意味着工作结束,城市便利的消费又使她们摆脱了在农村相对繁琐的家务。所以,相对于在农村的似乎干不到头的农活和家务,冰然“觉得出来还挺舒服的”。
2.享受休闲时间
“出来这么长时间没啥变化,见识多了,在这里,这里逛逛那里逛逛,还能上网。我上网看看空间日志,不看新闻,我也不大会写,会传照片,玩玩儿牌。我感觉我上网以后开心很多,所以我就光想买电脑,以前吧心里有什么事儿也没处说,有网就可以和别人说说,在空间里写写,我不经常写,也玩那个漂流瓶,有些能聊得挺好的,上网了我觉得找着说话的了。我很愿意和有文化的人聊天,因为人家有文化的人很有素质,我也很容易和他们沟通。”
从农村到城市,冰然不仅脱离了农活的脏累,开始享受便利的生活,而且工作之余的时间也让她开始上网聊天,与别人开心交流,享受工作、休闲相分离的多样休闲生活。冰然不仅喜欢使用网络,还经常参加“家园”的活动:周一电影放送,周三K歌,偶尔周末旅游,除此之外她还参与所在企业的车间聚会等活动。从冰然的叙述中可以读出她对从农村出来到城市打工所体验的自由:一是脱离种地和无休止的家务;二是打工的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分离,使冰然体会到工作之余的闲暇和自由。
休闲是一种自由和自我表达,它是潜在的一种革命力量,有着通过个人自由与赋权促进社会与个人层次的变革的潜能。同时,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休闲对女性的个人认同与社会交往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通过休闲,女性能认识到自己作为个人的价值,并对某些制约自己行为的社会限制与成见进行挑战[6]。
从女性主义与休闲的联系角度来看,休闲的正面维度正在改变着冰然的自我认识。休闲的正面维度包括积极地寻找自己喜爱和有内在动力要去从事的活动,以及对能表达、构建自我的活动的感情投入。“自我”包括对一种特定的休闲活动的参与,同时能积极地表现自己,并对这种自我有一种良好的感觉。冰然在讲述自己积极参与“家园”、车间聚会等活动时的开心之情溢于言表,她很兴奋地告诉笔者,为了按时参与自己渴望的这些活动,她如何“哄骗”孩子和丈夫,以争取他们的认可和支持。当冰然对这些充满情感交流和人际关怀的活动高度投入时,她体验到了自决自主的休闲,对这种活动的高度投入也许不仅关系到她个人的赋权,而且还关系到她的自我表达,自我效能感与自尊。通过这些自主与自决的休闲活动,冰然能从中获得一种独立、自主和赋权的感受。因为与丈夫的感情较淡漠,冰然在参与这些活动中体验到了开心,并获得了某种归属感、自主性和自我关怀。在积极参与这些休闲活动中,冰然实际开始了寻找有自主性的自我和自我赋权的过程,从女性主义角度讲,这是一个女性主体性觉醒的过程。
3.独立收入的骄傲与自信
城市打工不仅把冰然从农村繁重的家务活中解放了出来,让她有了属于自己的休闲时间,同时还凸显了她工作的价值。冰然的工资收入是维持家庭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仅是家庭的生存需求,还决定着她在家庭经济中的位置。
“出来还是不一样,出来接触人多,说话什么的不一样,和我以前不一样。在家的话肯定上网什么的都不会。出来干活学的也算是一门技术吧,在家什么也不会。村里像我这样的出来的少,年纪小点的出来的多,她们在家种个地,看看孩子,日子过得可紧巴了。”
“你像我们这个年龄段在家的(妇女),老的都不管了,自己过,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对象在外面打工挣钱,自己在家种地看孩子,很会过日子,什么也不舍得买,一个钱都掰好几个花,看看这个不舍得,那个不舍得。没出来的觉得出门的好,年纪大点吃过苦都觉得出来可好了,出来享福的,每个月都发工资,可以给小姑娘买吃的,买件衣服。出来,花钱便宜,虽然挣得不多,但每个月都有钱,在家里手里没钱,出来花钱这块好些。”
独立经济收入所产生的自豪感,就是能用自己的钱给孩子买衣服什么的,这让作为母亲的冰然感到满足和骄傲;同时打工还能学一门技术,有技术所带来的是能依靠技术自立的成就感和自信,相对于依然在农村种地的同龄女性,冰然分明感受到了外出打工产生的骄傲和自信。在冰然的叙述里,打工意味着收入,收入意味着她的生活可以继续,她可以给孩子买喜欢的东西,她可以学一样技术,没有工作就不会有这份自豪感和成就感。
同时,女性农民工的身份是个多元体,她们的职业经历、有关工作和性别的话语共同影响着她们身份的确立。在工作中,她们形成了有关自己是哪类人的意识,这是一种她们与自身的关系,她们通过确立自己是工人的身份认同而与他人建立联系。对于她们来说,重要的社会身份不是家庭中的妻子、母亲或女儿,而是工作中的职业角色。她们在自我介绍时首先介绍的是自己的职业身份:“我是服装女工”、“我在制鞋厂”、“我在箱包厂”,这种自我介绍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女性农民工首先认同自己的工作身份和与其相关的社会身份,其次才是女性的性别身份,即工作带给了女性超越性别身份的认同,并由此建立起自身的具有意义的世界。女性自信是一名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这样的身份认同是更宽泛的社会属性,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积极意义是它赋予了女性新的角色,她们不再仅仅是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而是服装女工、服务员,工作使女性第一次可以通过社会角色——职业角色确立自己的社会身份,而不再依靠父亲、丈夫或儿子来确立,这是女性从“无我”到“有我”的过程。由此,女性农民工在职业发展与其主体性之间建立起了稳定而多元的关系。
4.享受简单的人际交往
从农村到城市,冰然在获得了自由的时间和独立收入的同时,还收获了另一份自在。在农村,村落相对于城市,仍是一个充满规范的熟人社会,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受人瞩目,并受规矩约束。来到城市的女性农民工由于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空间,个人获得了更多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利,很多以前看似牢不可破的规矩都被逐渐打破,以前纠结的一些关系也从此断裂。
“公公帮着打药,嫂子还咬嘴,我就不愿意回去,就在这打工一天天过下去,过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也不用生气,老人给我们干了,她(嫂子)自己干得了也让公公再给她干,俺的地公公种着。反正我很不想回去,哪怕过得不好也不回去,家里的那些事儿……从我嫁给他(丈夫)就没有开心过,俺那个嫂子老多事儿,斤斤计较。”
“我现在也考虑不了那么远,回家也没有发展头,在家里要进厂子也挺累的,还不挣钱,在家上班比在这上班麻烦,在家事儿多。”
从农村到城市,冰然终于脱离了农村生活中繁琐复杂的人际关系,尤其与妯娌之间不愉快的纠葛,获得了简单快乐的人际交往,享受到简单的城市生活,没有妯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并通过网络开拓了自己喜欢的人际交往方式,生活空间更自由和宽松。笔者的另一位受访者阿梅,因为生二胎回家乡了,在与笔者的QQ联系中,阿梅抱怨在农村张家长李家短的,好烦,说道:“还是城市好,让人没压力”。笔者的另一位受访者环环在离开青岛准备回家结婚时同样提到:“还是在城市好,简单,在农村事儿可多了,结婚生孩子的,人情烦着呢。”
“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我感觉差别大了,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就说俺那个地方,农村也没啥好玩的地方,除了吃,就是地里有点活,其他没啥做的,能串门,串门就是和咱这样聊聊天,买东西也不方便,得骑车去好几里地赶个集去,有小卖部,就卖个烟酒糖茶什么的,它不跟这地方一样,有卖肉食的啥的,它就卖点小东西,酱油醋的,买菜还得赶集,没有什么活动之类的,俺那地方落后,我感觉在这里,这里也不算城里吧,算郊区,比俺那好多了,有‘家园’多好,一到过年过节就搞活动,感觉很开心。俺那边吃水还是用压水井,地下水,生活还是城里方便。什么时候我也买上个楼啊,我就羡慕城市生活,那么干净,我不喜欢看着乱呼呼的,不干净。城里人我就感觉人家有能力、有文化,说话办事都比咱强。”
从农村到城市,冰然逐渐形成了对城市的高度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的认同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自己出来这么多年,跟家里的妇女不一样,穿的差不多,懂的比她们多,说普通话什么的她们听不懂,出来后思想挺开放挺爱打扮的。”冰然已经将自己与普通的农村女性区别开来,对自己的定位放在了更具有城市人的特征上。
(二)从农村到城市,承受分离与紧张
从农村到城市,城市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毕竟与农村存在差异,在城市的生活对于像冰然这样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不仅意味着感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和自由,同时也意味着需要承受农民工身份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和困难。对于冰然来说,首当其冲的是必须面对工作与家庭之间的不协调,忍受生活的压力和紧张的节奏。因为女儿4岁还太小,而且经常生病,冰然不能晚上加班,而自己仅仅可以选择的工作就是服装业,服装业大多是加班的,冰然就只能选择允许请假的、晚上不加班的“妈妈班”。“妈妈班”工资低,正式工12元/小时,上妈妈班的冰然只能拿9元/小时。不仅工资低,妈妈班还不稳定,一旦企业订单减少,首先面临裁员危机的就是妈妈们,为此,冰然就处于不断换工作、找工作的奔波中。
“我是一没有活了就愁得慌,有个孩子不能整天在家,我也是尽力去挣钱,能找到不加班的活我就赶紧去干,现在刚找到这个厂子,没有找到这个厂子时我就去干临时工,有时我就觉得很委屈,他(丈夫)干烫熨,除了上班就是上班,我是一没有活了就愁得慌。去年那个厂子挺好的,不加班1小时给我9块钱,后来涨到10块,后来不忙了,女儿老感冒,老请假厂里烦了,就把我辞了,后来干临时工,也是闲的时候辞人,因为我不能加班,又给辞了,光忙着找工作,今年这一年还没真的安顿下来。”
对于女性农民工来说,家庭和工作都是她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别无选择地承担家庭的责任,而工作依然是她们重要的一部分,这就是她们的生活,别无选择的生活。
冰然在承受生活压力与紧张节奏的同时,在情感上还得忍受母子分离之痛。因为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对农民工来讲,过高的教育支出迫使冰然将大孩子放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而成为留守孩子。
“房租越来越贵了,住了5~6年,现在230元,刚开始120元,住这么长也不便宜,水电另算,小孩子另交15元房租。这是钱,那是钱,虽然俺们两个加起来4000多元,到月底就没有了,房租、孩子入托费,生活费,家里孩子寄点钱,到月底,不看病的话能剩1000多元,这个月买电脑就没有了,还有网费一年800元。儿子上私立初中,一上初中就交900多元。每个月几乎不剩,现在女儿看病在李家诊所可以打吊瓶了,以前不行,都得去人民医院,一去就得300~500元,还耽误我挣钱,感冒就化验血化验啥的,现在好了,在李家诊所打一吊瓶40块。”
“大的放家里,现在放暑假接过来了,十月一、春节回去,感情不跟我近,感觉跟奶奶近,5岁留家里,把小时候我对他的好都抹杀掉了,我老训他,怕我,奶奶宠他,挺伤心的,我们这些打工的,没办法。”(热泪盈眶)
忍受母子分离之痛对于作为母亲的冰然来讲无疑是沉重的,这也是像冰然这样的女性农民工不得已而付出的代价。除此之外,工厂的专制化管理也给冰然带来不小的压力。
“在厂里也没少受委屈,在厂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现在这个好点了,以前那个大声说话都不敢,这里还能听音乐,以前那个看得可严了,你去厕所,呆着过了10分钟,她就去厕所抓你。刚出来打工,觉得那一天可难熬了,时间那么长,现在都习惯了,觉得蛮快的。”
对于打工过程中的诸多紧张和困顿,冰然会为自己的某些不满进行自我安慰,具有很强的自我心理修复能力。某种程度上,冰然对生活的不如意抱着一种平淡与命中注定的口气,对许多困难常常是一笑了之。在冰然的QQ空间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自我安慰的留言:“简单生活,顺其自然”(2012-9-17),“日子再难也要笑着过”(2012-9-17),“有时候相信一下命运心里会好受一些”(2012-9-26)。对于冰然所讲的“相信一下命运”,我们不能简单地批判为“命中注定”的宿命论,冰然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归纳原因倒不如说是一种为自己寻找心理平衡的方式。这里的“相信一下命运”体现的并不是一种实际判断或指导行动的生活态度,而更类似于一种释放内心焦虑的方式与技巧,冰然很清楚生活中的种种限制,但她同时知道忍耐和等待,或暂时把问题悬置起来,以保持对未来的希望。
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转型
日常生活作为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是一个人时时刻刻以某种方式从事的最基本的活动,因此,日常生活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它是起点,又是终点,它完全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是最基本的细胞,由此将目光锁定于日常生活研究女性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可靠而且客观的研究策略。从学理的层面看,日常生活属于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在迪尔凯姆看来对社会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生活世界是最真实、最新鲜的社会镜面,关注日常生活的真实运行也是最可靠的。关注女性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出发,并不意味着她们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完全自主的领域。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制度设置是实践主体的行动背景,作为主体实践者的女性农民工受到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影响。从女性农民工打工的实践性层面不难看出,打工是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女性农民工通过工作场所的社会关系,重新创造工作场所时间,在城市的工作与生活的区分中寻找到了新的自由。从农村到城市,女性农民工在打工中、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悄悄发生着身份和自我认同的转型,她们隐藏在日常消费、日常交往和日常观念中的转型是沉默的,还没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我们也很少听到她们的声音。通过分析女性农民工这个群体在不同生活空间下的行为方式,可以认识到社会身份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形成的,中年女性农民工在这一转变中反映出了较积极的心理机制协调过程。或许是乡村艰苦生活的磨砺,或许是悠远历史传统积淀的智慧,女性农民工们的顽强、执著、坚韧、聪明、策略、机智、应变都令人感叹。
潘毅在《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中提出: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一场“沉默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角正是这些新型的打工者主体——打工妹。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连同女工们在“中国制造”的所有产品,必将遭遇强大的抗争与变迁力量[1](P22)。从农村到城市,冰然经历的城乡差异正在改变着她自己,这种改变也必将成为“沉默的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