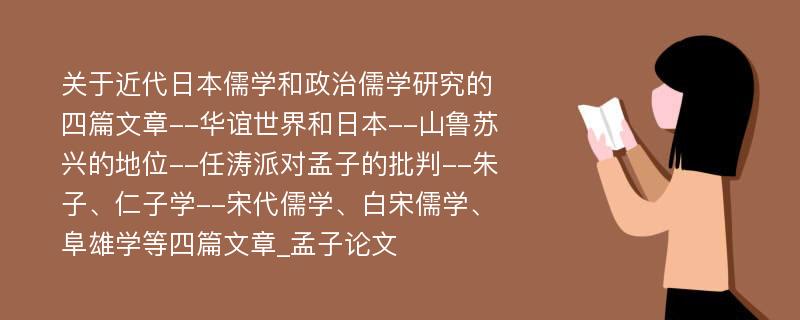
日本近世儒学与政治儒学研究四篇——华夷世界与日本——山鹿素行的地位——租徕学派对孟子的批判——山鹿素行的地位——朱子与仁斋——疑宋儒、排宋儒、复孔学——春台先生读损轩先生《大疑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日本论文,孟子论文,地位论文,近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华夷世界与日本
——山鹿素行的地位
信夫清三郎,
信夫清三郎,[日]
信夫清三郎(1909~1992),日本政治学者、历史学者,名古屋大学教授,曾任日本政治学会理事长等,著有《日本政治史》、《明治政治史》、《日本近代政治史》、《日本外交史》等。
[译者按]“华夷之辩”是个文化观与思想史的大问题。“华夷之辩”的问题,要重视“日本主义”的视角与立场,要吸收日本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要注意在江户时代、明治时代也即朱明时代以后,东亚有一个思想中心发生近代转移的问题,而这个近代性转移是同时伴随着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的。虽然很难说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逐一决定了思想格局的变迁,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上层思想的变化在潜伏性地引领政治经济的变革,思想通过人的行动,众人又通过上层的引领或制度安排……这就是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思想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或马克思·韦伯的所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类的问题。
日本近世思想家的新思想、新主张、新梦想,催生了近五百年来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大东亚主义”思想;尤其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军事的种种冲动与努力,无不与近代全球化浪潮下日本这一亚洲主义、大东亚主义思想主张密切相关。思想引领行动,格局孕育思想,东亚格局的变迁,总是与东亚思想的变迁结合在一起。今天,谋求东亚格局的前进,需要反省故有的东亚思想(它的流变),需要反省近几百年来东亚人民的努力与残酷的“内斗”血迹,需要重新检点观念的历程并在它那里汲取智慧。
近来埋头研究明治维新史,觉得理解维新史重要的关键之一是正确定位国学和启蒙思想的关系。维新是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争论,也只有正确理解了明治2-4年以国学为背景的神权专制向明治4-8年以启蒙思想为背景的启蒙专制过渡才能做出判断。启蒙专制的观念在日本思想史上得到了公民权,但在日本政治史上还没有。在日本,思想史和政治史之间有一个大的断裂。
国学与启蒙思想对抗的一个标志是:幕府末期启蒙思想家西周的《万国公法》和国学者大国隆正的《新真公法》的对立。前者主张国家开放,后者强调攘夷。大国隆正将视夷狄为禽兽、阻绝一切通路的武力攘夷论斥为“小攘夷”而加以摈弃,相反,他鼓吹的是“怀柔万邦”、“令西洋夷人生起尊王之心”的“大攘夷论”。他主张将“大攘夷”作为国际社会的原则,从而创作了《新真公法论》(1867年)。他认为:西欧各国主张“万国公法”是因为他们讨厌支那人将各国分为中华、夷狄,重自国、轻他国,将其作为一己之见,从而创立了“公法”;公法学创自西洋,我大日本创发的真公法学终将及于各国并超越之;并强调说:唯其推日本天皇为“世界之总王”,缔造“万邦臣服”的国际秩序,才是“普及各国的真公法”。
长久以来,中国在亚洲创建了特殊的国际秩序。要言之,以己国为“中华”、外国为“四夷”,令四夷朝贡,结成宗主与藩属国的关系。此即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琼·金格·菲尔班克教授所称的“中国的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或曰“支那中心主义”(Sinocentrism)等义(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rla's Foreign Relations,Editecl by J.K.Fair bank,1968),我国的中村荣孝教授则称之为“华夷的世界”或“华夷世界的秩序”(中村荣孝教授《日鲜关系史的研究》,1965-1969年;《日本与朝鲜》,1966年)。西欧的“万国公法”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开始破坏“华夷世界”的结构,接着要将日本囊括于“万国公法”中。大国隆正站在“大攘夷”的立场,认为“万国公法”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他将“万国公法”视为“新真公法”的前导即含此意。他进一步写道:“当将来‘万国公法’普及于世时,连支那人也必须沮丧地承认其‘华夷之分’、‘支那君主是世界的天子’不过是自己的僭称。”对他而言,“万国公法”打破了日本国内的“华夷”思想本身才是有意义的。他接着强调:“此学自舶来日本、迄于今日,举支那必褒称‘中华’,言我国必以为‘夷狄’,此固儒者之陋习,除之,亦攘夷之一端也。”但是,他宣称与“万国公法”分道扬镳时,又断言“复次将来,真公法兴于日本,挫败‘万国公法’,所有国家都臣服于我日本,方为真实之攘夷。”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此种“攘夷”是无法实现的。相反,倒是“万国臣服”的“新真公法”屈服于“万国对峙”的“万国公法”,相应地,国学也最终屈服于启蒙思想。
当大国隆正攻击“举支那必称‘中华’,言我国必以为‘夷狄’的儒者之陋习”时,日本同中国还没有正式的邦交,更没有宗主藩属关系,因此,在政治上国学对儒学的反抗并没有太大的价值。然而,回顾历史的前因后果,将日本与“华夷世界”相区别却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回溯历史,十五世纪初足利义满通过获得明朝皇帝给日本国王的册封,以朝贡的礼仪与明王朝进行往来,从而将日本纳入“华夷世界”的秩序。此后,丰臣秀吉因日明战争与明朝断交。德川幕府建立后,明朝更替为清朝,也没有复交,直到幕府末期的维新。以后,维新政府对亚外交开始着手将朝鲜和琉球从“华夷世界”的秩序中剥离出来。这样一来,日本与“华夷世界”相区分始于何时以及以何种形式的问题,这于政治史而言是很重要的。
18世纪后半期,这种区分在政治思想上具有划时代性。一方面,本居宣长的“国学”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兰学”形成。德纳尔德·金教授在《日本人发现西洋》(芳贺澈译,1968年)中说:“兰学派反击儒者们的非难首先采取了攻击中国本身的方式。”同时也介绍了大槻玄沢的《兰学阶梯》(1783年)的一节,指出:“现在,日本学者们对信奉了一千多年的所有东西的价值都开始怀疑。”并说:“国学者们扩张势力大致与兰学者们同时,他们受后者影响很大。”
从18世纪进一步上溯历史,寻找划时代的人物,结果可能会落到十七世纪后半叶的山鹿素行身上。已故林冈典嗣教授就素行的《谪居童问》(1668年)为先导的《中朝事实》(1669年)指出:“本书名之所符的‘中朝’非如当时的惯例指支那,而是如素行其人向来所说的‘我国’,这实际上表明他的思想向彻底日本化转变了。”(村冈典嗣《素行·宣长》,1938年)——山鹿素行“从周公孔子主义彻底转向日本主义”,同时不也是政治思想史上日本区别于旧“华夷世界”的最初标志吗?
思想史家素行的“日本主义”的全部内容为何?他怎样描述日本的实然和应然状态?後小松天皇(1382-1412)作为思想史对象,叙述皇统、武统交替的素行怎样阐明皇统和武统、朝廷和幕府、天皇和将军以及幕府末期御门对大君的“二元元首制”成为了关联内外问题的日本政治体制?武家的存在和武家的统治被赋予了怎样的理论?君臣上下的关系如何?要言之,素行是如何把握、拥护或改革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封建制度的?反过来说,通过素行所见的日本封建制度具有怎样的结构和特殊性?
对于一本书,读者的期待只有读者自己有数。当被问及你对下次发行的《山鹿素行》有何期待?我的回答是:政治史研究是眼前最紧迫的问题。
原载《日本思想大系月报》第3期第10-12页,岩波书店,东京,1970年7月。
徂徕学派对孟子的批判
——山鹿素行的地位
友枝龙太郎
友枝龙太郎,[日]
友枝龙太郎(1916-1986),日本著名的儒学学者、朱子学家,广岛大学教授,长期讲授朱子学,著有《朱子之思想形成》(1969)等重要学术作品,翻译出版有日文《朱子文集》。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被尊为“四书”始于宋代程朱学形成时,特别是朱子(1130-1200)《四书集注》的完成令“四书”的地位不可动摇,元明以降则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而成为士人的必读书。我国也在朱子学传来的同时,于镰仓、室町时代由五山僧众完成了朱子注的新释读。江户时代出现了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山崎闇斋(1618-1682)等人,朱子学大为倡行,重视“四书”的方向得以确立。此外,吸收了阳明学的中江藤树(1608-1648)、熊泽蕃山(1619-1691)对“四书”的援注也是朱、王混杂的,不过并未改变对“四书”本身的尊重。但是批判朱子学的伊藤仁斋(1627-1705)则摈斥《大学》,割舍部分《中庸》而特为尊崇《论语》、《孟子》,以此来提倡自己的古学。尔后荻生徂徕(1666-1728)接其踵而进一步摈斥《孟子》而专用《论语》与六经,且有别于伊藤仁斋地倡导起他自己的古文辞学。
然而,徂徕学派批判孟子的要点在何处?徂徕在《孟子识》中,将孟子定位为一种战国的游说之士,孟子的立场是以言说为主,而非以践行为主,其“性善”、“养气”、“仁义”并称等一切后儒以为有功于圣门者都被判为“好辩之失”;且他反击提倡古学的仁斋,认为仁斋把《孟子》视作羽翼《论语》的观点仍未脱宋儒樊篱。对于孟子以汤武放伐革命来说汤武是“圣人”或汤武的行为是顺应天人的“仁行”的观点,徂徕无疑是承认的;不过对孟子劝齐、梁之君“王天下”的王道论,由于无法判定孟子时代改换天命者究竟为谁,程子对这一章也没有说明,故徂徕对朱子《集注》所引的伊川之说表示存疑,且判定仁斋之说也不过是“回护之言”。由此可见,他是不完全认可孟子的言论的。徂徕表达过明确的立场:作为古代圣人的事迹,经书所示的汤武放伐是正确的,而作为游说之士的孟子向当时诸侯所游说的则与圣人之教的《论语》不合,因而是不对的。因此,徂徕主张将《孟子》同六经、《论语》区别开来。就汤武放伐问题,较之徂徕,仁斋《孟子古义》则高扬孟子之言为“万世不易之定论”,比如他将孟子劝齐、梁之君“王天下”解释为:“孟子所说的王,是从德性上讲的,未必居天子之位;齐、梁之君若行仁政,得天下民心,则虽为诸侯,亦堪称王者。”这就肯定了孟子的学说。这种解释虽被徂徕斥责为“回护之言”,但这里可以看出仁斋尊重孟子的立场。
要附带说明的是:朱子对于前者(汤、武),说“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此为赞同汤武放伐;对于后者(齐、梁),朱子借用程伊川之论——“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犹知尊周之为义,故春秋以尊周为本。至孟子时,七国争雄,天下不复知有周,而生民之涂炭已极。当是时,诸侯能行王道,则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劝齐梁之君也。盖王者,天下之义主也。圣贤亦何心哉?视天命之改与未改耳。”意思是:孔孟之时势不同,圣贤根据各自时代的情况做出了妥善的应对。对于这个视天命之改否的问题,徂徕曾作出了反驳。但程朱之说适应彼国国情,相应地不失为一种立场。总之,在尊不尊孟子这一点上,朱子与仁斋相近,徂徕则与他们相远。
却说继承徂徕学说的太宰春台(1680-1747),他在《孟子论》、《圣学问答》中是拒斥孟子。春台例举了孟子的两个缺点:其一,为了形成自己的学说,持论牵强附会,此于与告子争论人性本质处尤见;其二,为了劝化对手,不惜取悦于当事人,此于肯定齐宣王好货好色处见之。春台之意与徂徕同,主张将《孟子》与六经、《论语》剥离开来。春台特别以上述两个缺陷来歪曲孟子的理论,令生龃龉。他认为《论语》全通,而《孟子》多不通,从这个立场来论难孟子的是《孟子论》。另外,他用和文写成的《圣学问答》则破斥了以孟子为中心的宋学。在此,可就君臣关系来探寻春台旨意:他认为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通论,而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为不通之论,理由是“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人臣者,不得以夷险渝其心,即使君主无礼,臣于此生愤则非臣”。春台引用的“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一句出于由他刊行的中国书《古文孝经?孔安国序》,这与朱子学的合理主义不同。
虽然朱子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引用过孟子所讲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韩退之(768-824)也曾作有歌咏被纣王所幽禁的文王是何种心境的《拘幽操》。于君臣厚义,程、朱也都表达过赞赏之情。然阅读表彰《拘幽操》的闇斋跋文,闇斋注重君臣之分更过于程、朱而近于孔安国序。北宋李觏(1009-1059)的《常语》与司马光(1019-1086)的《疑孟》等都非难孟子的思想破坏了君臣关系的伦常秩序,然与此相反,为孟子辩护的是稍前于朱子的余允文《尊孟辩》,以及后来朱子本人的《读余氏尊孟辩》。翻开《朱子文集》第73卷,李觏、司马光与余允文、朱子的差别被鲜明地叙述出来。朱子的君臣论不象李觏、司马光那样严峻,比如朱子说:“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时措之宜异尔。此齐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义,不得不然。夫子笔之于经,以明君臣之义于万世,非专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则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隐之以孟子之故,必谓孔子不尊周;又似诸公以孔子之故,必谓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时措之宜,则并得而不相悖矣。”解释遵循君臣大义还是放伐革命以及是否应根据时势之变来作时宜时中,此中可以看出闇斋接受的朱子学和朱子学本身之间有一定的差异。
这里姑不过多讨论朱子学,单单就斥孟这一点而言,徂徕学派与司马光、李觏是近似的,仁斋与朱子是近似的。春台曾批评说:“仁斋虽不喜宋儒理学,然毕竟以心法之教为主故,但不知孟子之说异于孔子处而与孔子一同尊信,且云《孟子》一书为《论语》之义疏,此乃可悲之见。”又极赞徂徕:“至徂徕,求先王之道于六经,悟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孟子之言多悖于孔子。”春台对孟子批判是从徂徕那里承接过来的,而且这种批判更加详细具微。
对春台于孟子的“非议”,高濑学山(1668-1749)的《非圣学问答》和薮孤山(1735-1802)的《崇孟》,则站在朱子学的立场予以驳斥。另一方面,藤泽东畡(1794-1864)的《思问录》、伊东蓝田(1734-1809)的《汤武论》,则站在徂徕学派的立场上继续回驳。只是东畡、蓝田的否定汤武放伐论与藤田东湖(1806-1855)的《孟轲论》及吉田松阴(1830-1859)的《讲孟余话》中的君臣论有关,且东湖、松阴虽排斥孟子君臣论,却将浩然养气论作为主干内容加以接受。
以上以徂徕学派的孟子批判为中心,就他们如何看待君臣关系略作勾勒。在江户时代的社会组织中,怎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君臣关系——即藩主与家臣的关系,还有幕府与诸藩的关系或朝廷与诸藩的关系等——由于视角的不同,总会呈现出复杂之样相。必须考虑到,我国当时的社会已不同于宋代中国社会,如脱藩就会被勒令剖腹的特有封建制度,无科举制的士农工商的身份制等。这些问题,有俟于他日再来探讨。
原载《日本思想大系月报》第21期,第6-8页,岩波书店,东京,1972年3月。
朱子与仁斋
贝塬茂树
贝塬茂树,[日]
贝塚茂树(1904-1987),日本著名的东亚史、中国史专家,文学博士、京都大学教授,著有《诸子百家》、《中国的历史》、《贝塚茂树著作集》(10册,中央公论社)等。
伊藤仁斋的古学为其子伊藤东涯所宪章,子孙绵延,古义堂的家学一直传承至明治时代。孔子殁后二五五○年,孔氏家族倾注了极大热情予以祖述,一直持续到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仁斋自然无法与之比肩,但在日本却是罕有的学问世家。
距今三十年前,天理教主中山正善热忱地将伊藤家的藏书捐献给了天理图书馆。依据关西大学图书馆管理员中村幸彦教授的周密调研,昭和三十年刊行了《古义堂文库目录》。我等承蒙此《目录》之赐,得以掌握古义堂文库的全貌。每当参访天理图书馆,拜读古义堂文库,莫不仰承中村教授的恩泽。而欲认真学习仁斋之学,必然会反复参考此《目录》,并对中村教授的努力油然生敬佩之情。
据说伊藤仁斋通过自学通达了朱子学,并进而形成了古学学风。仁斋读了什么书?产生了怎样的思想呢?仁斋死后,其长子东涯著《先府君古学先生行状》将亡父的经历遍告诸亲友。东涯最理解仁斋,他所著的这篇《行状》可以说是我们去了解仁斋的最早史料。最近,我将古义堂文库的仁斋、东涯藏书与同时代朱子学书籍在日本的翻刻情况等做了一番比较,探究反映仁斋学风形成的《行状》早年记述是否真的可靠。
《行状》说,仁斋十一岁时(宽永十四年〈1637〉)开始跟从老师通过训读来学习《四书》第一部的《大学》,当读至著名的“治国平天下”章时他心中疑惑:有没有真正懂得此意的人?若有,当师事之。尔后学问稍进,即欲学做诗。其发想之奇,连成人也颇惊讶。仁斋这时的诗似乎没留传下来,但《行状》载有他十九岁时(正保二年〈1645〉)偕同父亲游琵琶湖时的诗作:
古来云此水,一夜作平湖。俗说诚难信,世传何其迂。百川流未已,万谷满相扶。天下滔滔者,应怜异教趋。(《古学先生诗集》卷一)
对琵琶湖于一夜之间形成的民间传说,仁斋断言其难信,其口吻虽是效仿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然采用此民间传说实是讥讽举世信异教(即佛教)。据说其坚持儒教立场的信念让长老们震惊,所以被记下了此诗。当时他正好在读购得的朱子之师南宋李侗(字延平)的《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复读了好几遍,连书都翻破了,据说这是他接受宋学的动因。
日本出版《延平问答》是在正保四年(1647),其时仁斋二十一岁。估计仁斋是弄到刚出的书,读得入了迷。然而,参阅《古义堂文库目录》的〈仁斋先生手泽本〉,却见不到《延平问答》的记载。年轻时就喜欢读且至翻破了的书,伊藤家没有留存下来实属正常。譬如我,大中小学时代爱看的书也差不多遗失了,手边几乎没有,想来仁斋也是这样的吧。
《行状》接着写道:尔后深浸于宋儒理学,一股脑儿地读了《性理大全》、《朱子语类》等书,昼夜钻研,极尽精微奥髓。这里有个疑点:既然读了《性理大全》、《朱子语类》等,为什么〈仁斋先生手泽本〉不记载这些仁斋早期爱读的书?其实这与《延平问答》的问题同理,并不是什么问题。明代胡庆奉敕编修的万历三十一年版(1603)《新刻性理大全》传入日本并由小出立庭加标点后,于承应二年(1653)在日本出版,当时仁斋二十七岁,所以不难想象仁斋是如何翘首以待,一上市就马上购得而醉心阅读。
但关于《朱子语类》有问题,由宋黎靖德编、明朱吾弼重编、汪国楠校正的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版传入日本时,林罗山获得、登记并写了跋语,此书现在还在内阁文库珍藏着。该书大部分是在宽政年间(1789-1800)由安井真祐标点,出版于江户,出版时仁斋死后至少已八十五年。而大明刊刻的原版书相当贵重,我想年轻的仁斋是没有财力购读大明原版《朱子语类》的。
假如仁斋购买了《朱子语类》原版书并加句读,那对仁斋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书,一定会永久保存在古义堂的。但不可理喻的是,纵观仁斋、东涯以下,古义堂藏书中既没有《朱子语类》的明版,也没有日本版。以明成化二年版(1466)由《朱子语录》摘编的《晦庵先生语录》为底本,正保三年(1646)京都二条鹤屋的町田原仁左卫门刊行了古活字本,古义堂倒是收藏有该书。此书由东涯校对、抄写,末尾有东涯的跋,作“从贞享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三年正月元日会读点校”云云。此时间为1685-1686年,仁斋在五十九至六十岁之间,大概是仁斋让十六岁的东涯读了这难懂的《朱子语录》之节录吧。《目录》收入了东涯这手泽本,而实际上它应该是以仁斋的句读为准的一个忠实的手抄本。
对此,有人推测:正保三年仁斋二十岁时,购得新版的《晦庵先生语录》埋头阅读,后来则用此书作教材训读于其子东涯。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那我认为仁斋年轻时一定没有弄到《朱子语类》的原书,只是读了该书的抄录本罢了。所以东涯的《先府君古学先生行状》记述仁斋读了《朱子语类》,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读了《晦庵先生语录类要》。
谈了这么多书志学上的考证,姑且按下不表。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对仁斋年轻时学风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与其说是朱子莫若说是北宋的程子兄弟。仁斋的手泽本中就有程颐著、朱子编的《周易经传》和《程子则言》。中村幸彦教授解释说:在《周易经传》上,仁斋从青年时代直到晚年,用墨黑、朱红、青蓝色批注了好几回,墨黑色是青年时AI写作入的朱子及其它训诂注释,朱红色是元禄初年撰写《易经古义》时尽抒己见而写的论说。而于《程子则言》,他又说:“仁斋所写《二程全书》的抄记,可以说是青年仁斋勤学的证明。”这个解释道尽了程子对青年仁斋的感化是何其深远。读仁斋《论语古义》等原文,详情自能明了,故中村教授的解释可为圭臬,暂就此搁笔。
原载《日本思想大系月报》第16期第10-12页,岩波书店,东京,1971年9月。
疑宋儒、排宋儒、复孔学
——春台先生读损轩先生《大疑录》
太宰春台
太宰春台,[日]
太宰春台(1680-1747),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学家,日本古学派代表人物荻生徂徕的弟子,著有《经济录》、《圣学问答》、《辨道书》等,对东亚儒学的突破与转型有重要贡献。
[译者按]本文采自《日本思想大系》第34册《贝原益轩·室鸠巢》之405-406页,日本国岩波书店1970年11月版,原题作《春台先生读损轩先生〈大疑录〉》,今标题系新录校者所加(文中粗体亦系另加),姑录之以作学人共享。(《日本思想大系》67册由岩波书店连续出版於20世纪70-80年代,收入了众多重要的日本古典思想学术文献。)
十七八世纪日本国的山崎闇斋(1618-1682)、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斋(1627-1705)、贝原益轩(1630-1714)、荻生徂徕(1666-1728)、太宰春台(1680-1747)等思想家完成了理学的突破与儒学的转型(实系复归孔学并维新儒学),是为东亚思想学术界的“文艺复兴”,其功厥伟,尤其山鹿素行《圣教要录》与荻生徂徕《辩道》、《辩名》等文,读来大快人心,可明理学之流弊。
十七八世纪日本古学家的思想学术工作已迈入了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并在“古学”中涌动着一种思想突破,为德川时代之后的日本奠定了众多思想基础,为日本思想走向独立自主奠定了基础,为接契近代西洋思想作了客观铺垫,代表十七八世纪东亚思想的最高成就。反观东亚大陆,明清时代只有戴震(1724-1777)其儒学思想的深度、广度及取向可与日本古学家媲美,然著《孟子字义》的戴震甚至比著《论孟字义》的伊藤仁需还晚出一个世纪……
戴震之后的清代,东亚大陆并未出现有勇气并有系统创见的儒学思想家,后之者无非多匍匐於“圣人”、“圣教”名下并顶着“理”、“道”等字鹦鹉学舌、鼓捣聒噪耳,相反日本古学家之后的思想家是群星灿烂并各有思想创发。德川时代/江户时代(1603-1868)日本古学家的新儒学思想,对于反观明清时代东亚大陆儒学的得失与反省今日东亚思想的来龙去脉,不可谓无有裨益也。
筑前贝原损轩先生博学洽闻、海内无比,生平所著书已刊行者凡数十部,皆有益于斯世;其未刊行者,犹有数十部云。盖先生少学程朱之道,以笃实之性竭力专精、至老弗怠,其所造宁浅乎哉!及晚年,忽疑二氏之言有异于先圣之道,反复思之,不得其解,卒成大疑,所录且二万言,分为二卷,名曰《大疑录》。先生谦恭,未敢示人。由美子善少逮事先生,幸得见之,因写而藏之。及子善之再游东都也,予与之有旧。子善尝见我徂徕先生而问古文辞焉,徂徕亦善之。今徂徕亡矣,子善视吾二三兄弟有加于往日,则犹以徂徕故也。于是,予就子善而求一见《大疑录》,三请乃见许予。而后得借而读之,始知损轩先生信程朱之道如斯其笃而疑之如斯其大。先生所疑者,自周茂叔著《太极图说》,以太极本无极、主静立人极,二程、朱氏继作,盛唱理气心性之说,其言曰“性即理也”,曰“有天地之性,有气质之性”,曰“理气二物”,曰“身有死生,性无死生”,曰“一阴一阳非道,所以一阴一阳者是道”,曰“明德虚灵不昧”,曰“天理冲漠无朕”,且教人静坐,此皆老佛之道,非我圣人之道也。又茂叔所云“无极而太极”,伊川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者,并释氏之言,二子取之以发明易道,非当行也。诸如此类,皆古圣人所弗言而宋儒言之,此损轩所以大疑之也。夫损轩以宋儒之徒而能疑宋儒,诚奇士也。然特疑之而已,未能排之。且其所论辩犹在宋儒范围之中,推崇孟子以配孔子如故,则未能及洙泗之流也。夫仲尼之道,至子思而小差,至孟轲而大差。所以差者,与杨墨之徒争也。轲之道性善,其实亦苟且教导之言耳,轲急于教导不自觉其言之违道也。宋儒又不知轲之违道,以为轲实得孔氏之传,遂以其书配《论语》。迨其解性善之言也,不能不置气质而别说本然之性,所以谬也。夫仲尼教人不以心性理气,心性理气之谈胚胎于子思,萌芽于孟子,而后长大于宋儒,则与佛老同其归何足怪哉!今损轩虽能疑宋儒,而未能疑孟子,则其所疑宋儒者何以释哉?易自有易之道,不可以常道论之,宋儒未始知之,损轩亦未之有见,则其所疑宋儒者何以释哉?佛之与老,其道相反犹水炭不相容也,其有相似者,特其末耳。宋儒之道,傚佛者十八九,傚老者十一二。今损轩疑宋儒,概以为老佛之遗愿亦未深考也。夫六经者仲尼所定,昭昭乎如日月之在天;孔子之言,如规矩准绳。是故凡天下之道,照之以六经,临之以孔子之言,则其是非斜正可立而定。自子思、孟子,不能逃其过差之罪,况其他诸子乎!而况后世诸儒乎!然诸子毁仲尼者,其非易见;宋儒似而非者,其非难见。自非善读孔氏之书而深信仲尼之言者未有能排宋儒者也,虽损轩犹坐是尔,悲夫!虽然,损轩之疑宋儒,由博览故也,何少其晚哉!若天假之以年,必有所发明焉,岂独疑之而已哉!近世朱氏学者流谓“仲晦贤于仲尼”、“非朱氏之书弗读”,所读不过数部书,则何从生疑哉?若然者,终身不觉悟,所谓醉生梦死者也,岂不哀哉!由是观之,损轩之疑宋儒,可谓天诱其衷也!纯之少也亦读程朱之书,弱冠见程氏二性之说而窃疑之,又因读《易》及《礼记》而得举错字,乃觉《论语》朱氏之解谬,自是遂大疑宋儒,卒至排之,然后仲尼日月无复云雾之蔽余生而见之,是幸也已,余故沾沾自喜以为得天之宠灵,岂不然乎!予观损轩先生其学不可及也,至排宋儒,予无畏于先生云。
原载《日本思想大系》第34册第405-406页,岩波书店,东京,1970年11月版。
林桂榛,字夷山,徐州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研究先秦思想史及东亚近世儒学;
刘春阳,成都某研究所(系保密性机构)副研究员,徐州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标签:孟子论文; 论语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国学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孔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