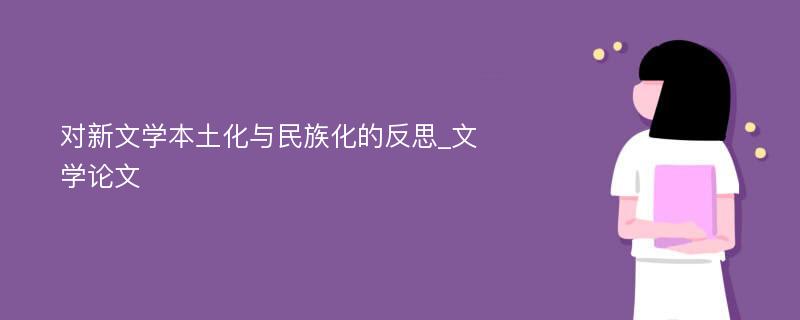
从本土化与民族化角度反思新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化与论文,本土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5-0085-06
主持人语:之所以选择这一话题来集中讨论,是因为我们深深感觉到:当前的新文学研究中肯定和褒扬性的成分太多,批判和反思太少。人们大都以仰视和崇敬的眼光打量新文学的历史和作品,却缺少必要的批判性审视。而我们认为,作为不到百年历史、中间又经历了种种束缚的新文学,它最需要的也许还不是赞美和崇敬,而是深刻的检讨和严肃的反思。只有在这一前提上,它才有可能进行自我超越,向着健康而宏阔的方向发展。当然,批判不是粗暴的否定,不是个人意气的简单表露,它是理性的检讨,是客观的审视,批判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新文学的发展,批判是另一种形式的建设。所以,我们的批判可能不是圆熟的,但绝对是严肃的;可能还存在某些遮蔽和肤浅,但却是真诚和坦率的。我们既欢迎同行学者对我们这些批判反思进行批评和探讨,也希望更多的学者参与到我们这个讨论中来。
(贺仲明)
一
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正全速向着全球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谈论“本土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似乎是一件与时代潮流相悖逆的事情。尤其是在文学界,绝大多数作家的创作和学者的理论都是带着浓厚的西方化(全球化)色彩,在直接或间接地向“世界化”靠拢,“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批评”的理论正席卷当前整个文学界①。相形之下,“本土化”和“民族化”的话题确实显得落伍和滞后。
但是,在我看来,新文学的“本土化”和“民族化”问题其实有着非常大的提倡和探索空间。这有三方面的理由:其一,全球化时代并不能排斥文学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在文学交流越来越普遍、人类命运越来越相互密切关联的情况下,文学当然不能狭隘地只关心某一族群或地区的利益,它应该追求普世人性价值,要有人类的整体关怀,但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文学的任何关怀都不是表现为抽象的理论,而是由对具体的人或物的关怀所构成,其爱和关怀的情感最终要落在具体的人或物上。而且,这些情感因素都是由具体的创作,由具体的文学场景、文学意象和文学情感体现出来,这些以具体生活为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会带有文学的本土色彩,其“世界主题”也必然会带有本土的痕迹。换句话说,没有具体的本土化、民族化文学场景和文学情感,也就谈不上有真正深入的世界关怀。
其二,文学的本土个性正是一体化世界文化的反抗者。在现时代,所谓的“世界化”其实就是商业化和物质化,这种文化虽然不能完全否定,但它对人类生活和精神个性的伤害是巨大的。文学的个性化,其中也自然包含着本土化和民族化的特征,正是对这种单一的一体化文化方向的批判和否定。正如著名学者弗莱所说:“文学艺术无论具有多大局限性,都可以在解放人类心灵中起到必要的作用。”[1](p.188)丰富的个性和精神特征是对抗物质文化潮流的重要基础,或者说,正是因为文学有独立的个性,有丰富的本土性和民族性为基础,它才能超越物质文化的羁绊和束缚,表现出其显著的个性和自由特征。如果文学真的失去了民族个性,被“世界化”了,它的魅力也就基本上荡然无存了。
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中国新文学有着这方面的迫切要求。因为中国新文学主要以西方文学为蓝本,是在对自我传统的否定和批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在事实上,这一否定不可能那么彻底,其内在精神上还保留着很深的传统民族文学因素,其发展历史中,也不时有着民族化文学潮流的出现,某些时候甚至还占据着文学潮流的主导地位,但是,总体而言,新文学的发展方向是以西方化为主体的,它需要经过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洗礼才能真正走向成熟。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新文学尽管已经发展了近一个世纪,但它并没有真正完成本土化和民族化的过程。
这典型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大众的日益疏离。虽然新文学一开端就以“平民文学”为旨趣,在其发展历史中,也多次寻求大众化的实现,但是,一个严酷的现实是,新文学始终没有真正进入过普通大众。包括在新文学已经发展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它依然游离于大众之外,甚至是更远地离开了大众。赵树理在半个世纪前曾经批评过“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和新诗一样,在农村中根本没有培活了”[2](p.1362),这依然是今天农村文学现实的真实写照。农民和大多数市民们喜欢的,依然不是新文学,而是言情和通俗故事——我们只要了解一下金庸和琼瑶等在社会中的受欢迎程度,再对比一下主流新文学作家的阅读状况,就会有清晰的认识。虽然大众接受不是评价文学成熟的唯一标准,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影视、网络文化的冲击等外在因素有关,但它还是反映了新文学与本土大众的距离,很有值得反思之处。二是新文学尚未形成真正具有民族个性的审美特征。一个作家创作是否成功,在于其是否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将它拓展到民族文学也是一样。一种优秀的民族文学,同样会呈现出显著的民族个性特征。从世界文学格局看,比如德国文学的哲学性,俄国文学的神性,美国文学的世俗性,等等。这些特点的背后是其民族的文化个性,或者说就是其本土特色。但是,新文学到底形成了什么独特的个性,使它能够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显示出别样和独特?我以为还没有做到,至少是还不充分。② 这不能归咎于我们民族文化和生活。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厚和独特的底蕴,传统文学也有鲜明的艺术个性。新文学未能形成独特个性的原因,显然与其本土化和民族化程度的不够、未能充分建立与本土文化精神的深刻联系有直接关系。
我们新文学研究界近年来比较热衷于讨论新文学传统,其实,新文学是否形成了相对稳固的、确定的传统,还很值得疑问。我更倾向于认为,即使在今天,新文学依然还处在一个探索和发展的阶段,它还没有真正从西方文学影响中独立出来,没有真正融入民族生活和文化中,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和价值系统。
二
在新文学历史上,并非没有对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努力,甚至可以说,自新文学诞生之日起,就有许多作家在努力探求着本土化和民族化的道路,寻求着新文学的独立与自我完备。就其主要的说,曾经出现过三个高峰:1.从1930年代初的“大众化”讨论开始,到19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新鲜活泼的、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p.500)和“工农兵文学”口号,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大众化讨论”和《讲话》形成的过程。这当中,1930年代的“普罗文学”、“大众语运动”都体现了明确的民族化(大众化)精神特征,本土化是其蕴涵的内在精神指向。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之余,更将民族化的口号付诸文学实践,产生了大量具有民族审美特点的文学作品。在这整个阶段中,鲁迅、茅盾、瞿秋白、赵树理等新文学作家都起了重要的推动和深化作用;2.“十七年文学”。这一阶段事实上是1940年代解放区文学思想的延续,或者说是在继承着1930年代的传统,不过范围更大,力度也更充分而已。这一时期产生的《红旗谱》、《林海雪原》等浓郁传统审美特点的作品,创作内容上也更为写实,与生活贴得更近。它与上一阶段的差别在于:虽然它也保留着民族化(大众化)的基本方向,但更注意与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与传统通俗文学的融合,吸收了较多古典文学传统的因素;3.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这是一次以知青作家为主体、带着这一代人精神印记的回归传统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在长期与传统隔离之后爆发的一次对传统的皈依和寻找过程。韩少功、阿城等作家提出的“寻根”主张,在理论上表达了将新文学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的愿望。不过,在创作实践上,他们没有达到理论的高度,甚至出现了与理论相悖反的情况,从而导致了“寻根文学”的昙花一现。不过,在“寻根”运动沉寂之后,还是有一些作家在持续着这方面的追求。比较典型如1990年代后莫言、格非、李锐等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他们创作的《檀香刑》、《生死疲劳》和《山河入梦》、《旧址》等作品,重新回归传统文学的形式和技巧,对本土化和民族化作了新的尝试。
这只是对几次潮流的概括,实际上,在潮流之外还有许多作家理论家作了不少探求工作。比如1930年代施蛰存、废名等人对中国传统小说形式现代化的尝试,比如在新文学历史中始终没有中断的诗歌格律化思想和实践,以及汪曾祺等人在1980年代对传统“笔记小说”形式的现代应用,等等。然而,尽管新文学作家们这种种努力非常值得尊重和肯定,但客观来说,这些尝试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限制了所能取得的成就。
首先是对本土化和民族化内涵理解过于狭窄,缺乏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一点最突出地体现在1940年代的“大众化”讨论中,向林冰等人片面要求回归传统,是极端的将民族化狭隘化的观点,也是将民族化内涵完全局限于现实层面,其内涵基本上等同于“大众化”。这些观点尽管受到胡风等人的批评,但是,它事实上却成为当时创作的主要方向,解放区的“民歌体”和“新章回小说”的复归就是典型的体现。并且,这种思想和创作方向一直延伸到“十七年文学”和1980年代文学中,以至于许多人一谈起文学“民族化”,就自然想到“大众化”,似乎二者是完全同一的。考虑文学与大众的关系,关注文学的社会效果,本身并不是错误,但是,完全单一地将它作为首要原则,自然会忽略文学的其他要素,甚至是最根本的文学要素,变成了文学完全为迎合大众的通俗化审美趣味而进行创作。民族文学中那些更深层和内在的因素就被弃置了,更丰富的内涵被单一化,形成了狭隘而局促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学来说,这种单一显然是不完备和不合适的。
其次,受政治影响太大,文学自身的考虑太少。这主要体现在1930年代和“十七年”时期。“大众化运动”最早兴起,主要是左翼文学群体出于宣传的功利考虑,为了让文学更多地适应现实宣传的需要,其讨论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与文学自身的关系不是太大,主要是为现实政治功利服务。因此,这一运动中提出的口号,基本上停留在实用的目的,很少考虑到文学自身的发展。同样,“十七年文学”的民族化方向,也有很强的政治主导因素。这种从政治出发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思考,自然不会真正深化对文学自身的思考,相反会影响真正本土化和民族化方法的实施和深入,会招致人们对本土化和民族化理论和实践的反感。
再次,受强烈的西方文化影响,未能真正回归本土和民族化。本土化和民族化的追求,需要明确的精神主体性,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建立在自我主体上的,独立的、客观冷静的回归。但是,20世纪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作家们很难摆脱其影响,许多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尝试也陷入了西方影响的窠臼之中。这一点,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有一定的代表性。作家们的“寻根”思想,与改革开放初追赶西方文学(文化)潮流的心态密切相关,这决定它不可能是真正冷静客观的。因此,“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们其实只是将“根”的内涵局限在表面或者说是概念化之上,缺乏对民族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学深层细致的考察,更没有将它与民族精神相结合起来。因此,他们的创作之“根”基本上没有落实到本土生活之上,没有扎到本土生活之“根”中。
正因为这样,新文学历史上的这些本土化和民族化潮流都只是暂时性和局部性的,它们尚没有完成这一关系新文学发展方向的建设任务,也直接影响到新文学创作的水准和实绩。更重要的是,这些多重束缚下的探索不只是“带着镣铐的跳舞”,而且还造成了本土化和民族化思想狭隘的印象,影响了人们对其进一步的思考。甚至可以说,新文学之最终走向西方化为主的方向,与新文学历史上民族化提倡的不成功,与其在策略和方向上的失误有直接关系。
三
在上述前提上来重新思考新文学的本土化和民族化问题,显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学“本土化”与“民族化”的内涵。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真正谈得上是对这一问题有意义的思考,也才可能进一步探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这一问题涉及的内容复杂,远非我这里能够论述清楚,我只能谈一些个人初步的思考。
具体而言,我以为文学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应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有较强的现实关怀意识,就是说要具有深切的本土关注精神。文学在题材上可以涉及古今中外,可以运用浪漫、虚构和想象的方法,但是,它应该是立足于对现实生活、具体说是本民族生活人民生活关注的基础上,它的爱和恨都应该从现实出发,源于生活——或者说它是在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中产生的。这是文学本土化的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作家的思想只能局限于现实,他完全可以将其主题上升到对整个人类的关怀,只是其起点应该是民族的、现实的。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其更深远的关怀才可能是真实的、深切的。
其次,是灌注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任何民族都有其独特性,尤其是像中华民族这么古老而成熟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是它立足的前提,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地方。它对世界、人生、道德的看法,虽然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也需要改变和发展,但其拥有相对稳定的基本精神,它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德国哲学家洪堡特曾经谈过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入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是因为,智能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4](p.52)。文学也完全一样。文学应该灌注民族文化的个性,是民族文化的体现。这既表现为外在的生活、语言和文化面貌,更是整体的世界观、价值精神。或者说,一个文学作品是作家在说话,同时也是代表着一个民族在说话,在传达着民族文化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审视和思考。德国心理学家荣格曾这样论述民族文化精神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除了德国人能写出《浮士德》或者《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我们能设想还有谁能写吗?这两部作品都利用了在德国人灵魂中回荡着的某个东西——一个‘原始的意象’。”[5](p.248)是很有道理的。
第三,是呈现独特的民族审美个性。文学由作家个体完成,当然最显著的是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但是,真正成熟的作家创作,他的个性应该是自然地融会于民族文学个性之中的。因为文学主要反映本民族的生活,自然、风俗和人物气质上的个性化会投射在具体作品的审美风格当中,更重要的是,作家的内在精神灌注了民族文化个性,它的思想、文化自然带了民族文化的特征。于是,一部具体作品所表现出的审美特征会自然带有民族审美的群体色彩,在其作家个性背后会蕴涵更深邃更广袤的民族审美特征。换句话说,民族文学的个性是由众多民族色彩显著的作品所构成,每一部优秀作品都是民族文学个性的组成部分。
上述三个方面是文学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基本要求。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作家来说,能够达到这三个要求,就应该是深入本土生活之中,很好地体现了本土意识;作为一种民族文学来说,能够在主体方面达到这一要求,也就标志着它已经完成了本土化和民族化历程,已经成功地融为民族文化和生活的一部分。
在谈论文学本土化和民族化内涵方面,还需要补充两点精神:一是文学本土化和民族化不是某一种具体的技术或方法要求,更不是局限于某一具体程式,它主要是一种精神方向,一种宽泛的姿态。它不是对文学僵硬的规定和限制,而是一种多元化的精神引导。当然,这绝不是说它是空虚无所指的,相反,它体现于文学的所有方面,涉及到文学精神、文学体裁、文学语言、美学风格等多个内涵,主导和影响到文学的发展方向。比如在对文学概念和文学标准的理解上,我们一般都强调文学的普泛性原则,认为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在主导我们。其实,这一看法只能说是部分准确的——如在文学评价上,强调其对人性的揭示,对人类命运和处境的关注方面,是有普泛意义的——但是,当文学表现到其他方面(毕竟,文学不可能总是表现普泛人性,它还有更广泛的表现空间),标准就应该是多元化的,其中民族的本体性是重要的标准。换句话说,文学不可能总是为全球化写作,它首先应该是为本民族大众写作的,它的评价标准也首先是民族大众。
二是文学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内涵是丰富的、宽容的、变化的,而绝对不是狭窄的、排他的、停滞的。在许多人眼里,本土化与现代化是相对立的,是自我封闭的表现。事实远非如此,本土化同样需要西方文学资源的支持和丰富。同样,我们很多人一谈到民族文化,就很自然联想到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就像一谈文学民族化就想到文学大众化一样。这其实也是不准确的。任何民族文化都包括有雅和俗、民间和主流两部分,传统文学的内涵同样包括传统古典文学,甚至说,中国古典文学发展更为成熟,成就更高,凝聚的民族文化更丰富,在新文学民族化中占着更重要的位置。我们吸收民族文化,应该两方面都有所关注,不能单一方向发展。从这一理解上说,文学本土化和民族化既需要立足传统和本民族生活,也需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和文学的营养;既需要关注大众审美,更应该借鉴传统古典审美精神。它的最后和最高目标是融会传统和西方、民间和古典两方面的影响,形成自己独立的个性,成为现实生活和民族个性最恰当的反映者和表现者。
四
新文学实现本土化和民族化是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它已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发展历史的背景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只有在更多人的理论探索和丰富的创作实践中,新文学的这一任务才能得到深化和完成。我以为,具体到当前文学,也许这几个方面是迫切需要加强的。
首先,是加强对生活的深入体察。深入生活的话也许已经被人们听厌烦,甚至反感了,这与人们以前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理解的狭隘有关,有可理解的原因。但是,生活对于新文学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建设确实是有非常的意义。其一,正如前所述的,生活是本土文化的最基本体现者,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蕴涵着传统文化的底蕴。以往我们许多人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理解,往往局限于书面上、典籍中,这其实是很不完备的。传统文化不是虚幻和僵化的,它以鲜活、自然、发展的姿态存在于现实生活,现实生活赋予它灵性与活力;其二,生活是民族审美最基本的体现物。民族的自然风情、人文风俗,更包括人的精神品格,都蕴涵在生活中。要想呈现出独特的民族审美品格,对民族生活的再现是重要的基础。当然,要求作家深入生活绝对不排斥他的独立思考,他完全可以在生活中寄寓更广阔更丰富更有个性的思想,生活只是帮助他深化思考和表现能力的重要基础。
其次,是对民族文化(文学)传统的深入体会。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古典文化(文学)传统。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古典传统长期被排斥于新文学的接受之外,新文学作家的传统文学素养呈现明显而严重的下降趋势,新文学与传统古典文学的关联越来越浅,距离越来越远。以新诗为例。长期以来,新诗发展都以西方文学为圭臬,谈民族化都只局限于民间文学。这一趋向,严重伤害了新诗与本土生活、本土文化的深在关联,丧失了其独特的民族个性审美特征。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学的优秀个性完全具有可以借鉴和深化的价值,可以为新诗和其他文学形式发展提供精神支援。如同艾略特所说:“传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6](p.2)强化传统文学资源的影响力,深化与传统的精神联系,是当前新文学发展的迫切方面。
最后,是寻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结合点。文学本土化,寻求与传统文学的联系,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形式,借鉴文学技巧,它更重要的是寻求一种精神,找到一种个性联系。在民族审美精神与西方文学风格,在民族风格与现代技巧之间要寻求一个平衡。因为传统文学再高超,想回到传统已是绝无可能,也无必要。它需要借鉴和吸取西方文化之优长,在丰富和创新中拓展自己。我们应该认识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在思想、形式上的巨大差异,认识到其中有些差异是完全不可融合、也没有必要融合的。它需要有所取舍,前提是创新和发展。以小说为例,中国古典小说尽管有《红楼梦》、《聊斋志异》这样的杰作,但是,其总体发展并不充分,因此,新文学小说家想要继承民族小说传统,不可能采用固守的方法,而是需要向西方文学大量借取,在丰富和发展中促进传统精神与现代技巧的结合。一味的固守方法,传统将会变得僵化,失去魅力和生命力。这一点已反映在当前部分创作上。1990年代以来,一些作家意识到加强与传统文学联系的必要,于是,在一些创作中,多方面地借鉴和仿效了传统小说的意境和技法,呈现比较浓的传统文学气息。这一努力显然是有意义的,但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③。我以为,最关键是作家们在两点上没有处理好:一是没有意识到传统最直接的体现者是现实生活,只有将传统精神与现实生活相融合,才能更深切地展示传统;二是没有意识到文学本土化的精髓是一种精神,而不仅是某些具体方法。方法需要发展和丰富,需要生活的鲜活与丰富。这是传统获得新的生命力的重要前提。如果能够在这两个方面有突破,我相信这一创作会有更璀璨的收获。
收稿日期:2009-06-07
注释:
① 当然,这种潮流也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深刻批评。参见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② 正因为这样,前些年人们一直谈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殖民色彩”。近年来人们虽然不太直接谈论这一话题,但实质其实并未发生改变。
③ 参见拙文《新时期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