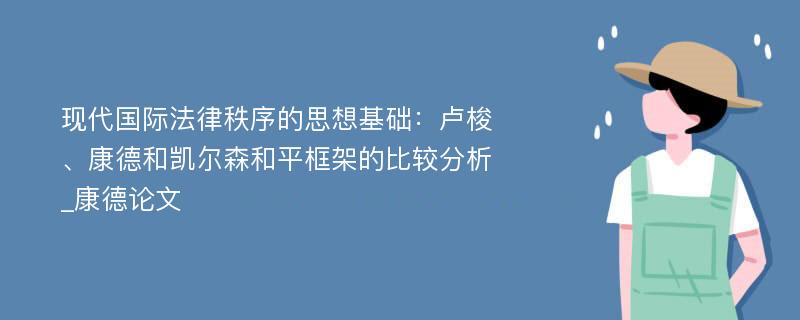
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思想基础——卢梭、康德和凯尔森之和平架构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梭论文,架构论文,尔森论文,秩序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2-0103-06
理解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一个上佳的出发点就是考察人们对世界秩序的追求,国际法可以放在世界秩序的框架中予以理解,因此本文的出发点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存在着世界秩序,而这种秩序表现为一种司法构造(juridical formation)。”⑴为了明确起见,本文称这种司法构造的秩序为“国际法律秩序”。国际法律秩序不同于国际政治秩序,前者乃是和平哲学的产物,其核心集中在作为维持和平的组织机构之构造上,具有规范性特点,后一概念基于权力、力量要素或其组合。本文所指的国际法律秩序主要是基于和平规范的组织架构,核心是其背后的构建和平的规范前提。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这些前提进行考察。
第一部分 作为永久和平架构的国际法律秩序构想
一、从开端到卢梭
国际法律秩序的谱系可追溯至在战争与和平的永恒冲突中欧洲人对永久和平的追求,是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人文主义者的一个“甜蜜梦想”[2]。卢梭的永久和平思想的起点就是那些欧洲人文主义前贤。
卢梭设想国际社会能像解决国内社会个人争端那样能解决国家间的争端,比照国家的模式来构建其维护和平的方案。他认为,国家间利益的一致就可以使国家联合起来。必须用某种强制性的权力来协调其成员,使成员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义务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而靠成员国自己是永远做不到的。[3]
这种联合的形式在组织架构上就是一个统一的欧洲联邦,这个联邦“必须接纳所有举足轻重的大国为其成员国;必须有立法机构,具有通过约束每个成员国的法律和条令的权力;必须拥有一支强制的力量,能够迫使每个国家遵守共同的决议,无论是用命令还是禁止的方式;最后,还必须十分坚强有力,这样才能制止任何成员国在看到自身利益与联邦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随心所欲地背离联邦”。[4]
关于这个欧洲联邦的宪法,卢梭建议要包括五个条文。第一条各个主权者立约建立永久、不可撤销联盟,并委任全权代表出席常设议会,通过仲裁或司法方式解决立约方之间的争端;第二条涉及议会的代表问题;第三条处理各个成员国领地之财产、继承和政府形式问题,以杜绝无尽的纷争;第四条规定毁约者应当被宣布为公敌的情形、成员国应当共同采取行动应对;第五条涉及全权代表在处理事关欧洲共同体最大利益时的常设权力和投票方案(简单多数和四分之三多数)。最后,这五条必须经过一致同意才能更改。[5]卢梭的呼吁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反响,但他对通过法律秩序追求和平的诉求通过康德继承下来了。
二、康德:和平的先验规定——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的联合
康德在一份虚拟的和平条约中表达了如何永不开启战端的条件,这就是以《永久和平》为题的论文,其行文的风格是一份和约式条款,分为预备条款和正式条款,前者规定了一些和平存在的技术性先决条件,后者为正式条款,也仅只三条,都是以典型的康德式先验判断提出。一个自由主义国际法学者总结说:“康德的观点是,没有民族国家的内在自由,就不可能取得永久和平。康德理论的主题就是,道义上合法的国际法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合之上,它们共同致力于对个人自由的道德承诺,忠于国际法律规则,通过和平交往达到共同进步。”[6]在《永久和平》中,康德的和平构建主要基于三个正式条款。第一条正式条款是“每个国家的公民政体应当是共和制”。此条应当同第二条结合在一起理解:“国际法应当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第三条正式条款为“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其条件”,着眼点在于永久和平的普遍性,而非隅于一地之数个国家之间。根据前两条的精神,国际法应当建立在共和制国家的联盟之上,在这是康德之和平秩序的核心。关于共和宪政,康德规定了三个要素:一个社会的成员作为人的自由原则、根据所有人作为主体对于唯一共同的立法的依赖原则、根据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平等法则。康德将社会中个体的自由放在首要位置。在《道德形而上学总导言》中,康德将自由作为人的首要属性。[7]康德和平哲学中首要的原则是一种自由主义原则。
这样一种共和政体如何导致永久和平?康德说,在这样的政体中,如果就是否发动战争问题作出决断,就要寻求作为自由、独立、平等的公民的同意,那么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就会深思熟虑,谨慎,不会贸然进行,因为公民要自己面对战争的种种后果。出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他们的一般决断就是避免战争。[8]另一方面,由于共和政体的分权和代议制特点,存在一种平衡机制,是战争之决断不那么武断。[9]
永久和平的第二条正式条款要求“国际法应当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盟之上”。该条中Federation这样的措辞使人容易误解为是建立一个具有权力中心的实体,或类似于世界政府。事实上,康德明确表示不支持世界政府的想法。何谓自由的国家?第二正式条款没有定义。第一正式条款首先要求每一个国家必须实现国内自由,即个体的自由、平等及独立,应当如此理解自由的国家。自由国家的联盟是怎样的联盟?康德说,“这一联盟并不是要获得什么国家权力,而仅仅是要维护与保障一个国家自己本身的、以及同时还有其他加盟国家的自由,却并不因此之故(就像人在自然状态中那样)需要他们屈服于公开的法律及其强制之下”,这种联盟中的国家“遵照国际法的观念来保障各个国家的自由状态”。[10]强调自由国家的联合,拒绝具有强制性执行功能的组织架构,这是康德之国际和平秩序理论的根本特征,其实也是先验规定的逻辑结果。
康德之永久和平的第一正式条款要求是每一个国家内部必须实现国内自由。以此为基础,成为民主和平论的先驱,[11]也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哲学所依赖的理论基础。[12]康德理论也被认为是当今各种争端解决司法机制的先声,这位哲人事实上也是“联合国制度的理论创始人”[13]。
三、凯尔森:集中性制裁条件下的和平
凯尔森提出的核心问题是,①“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只有在国际法的框架中寻求和平方案,也就是说,通过国际组织,而该组织的集中化程度并未超越国际法的本质。”[14]他进而解释说,“在国际法框架内解决和平问题,其实就是通过国际组织解决和平问题,该国际组织具有一定程度的集中化,但其程度还不至于达到要消除该国际组织之成员国相互关系中的国际法;该和平方案也就是建立一个国家共同体,同时调整成员国间关系的法律并不因此变得不再成为国际法的程度,也不是变成国内法。”[15]根据这个出发点,凯尔森花了很大的篇幅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国际法框架、国际法的特殊技术如何能保障国家间的和平?”[16]
凯尔森的国际法理论是其国内法概念的放大,国内法上的个人在国际法上就是国家。如果说国家对个人使用武力是对其不法行为的制裁(集中制裁),那么在国际层面上,武力的使用乃是作为对国家之不法行为的制裁。②但是,国内法中促成和平的独特要素是集中制裁这一特点,[17]而这一特点在国际法中不存在,后者的制裁是分散性的,也就是各个主权国家自己使用武力,或者奉行自助原则。[18]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在国际组织中解决集中性的使用武力以保障和平这一困境呢?
凯尔森认为最好由尽可能多的国家组成一个类似于联邦制国家那样的国际组织,特别是建立具有立法权的中央机构,只有这样才能使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具有充分的集中化。[19]在这样一个世界联邦国家中,其成员的政府形式无关紧要,无论它们是君主制、共和制皆可。[20]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联邦必须垄断武装力量的使用,它所确立的法律规范禁止成员国家之间使用武力。对成员使用武装力量的条件是作为对该成员不法行为的制裁。[21]具体而实际的问题是,在建立国际共同体的时候,如何体现集中性的制裁?凯尔森设想通过宪法性条约建立具有强制管辖权的国际法庭。所有国际争端必须毫无例外地由国际法院解决。[22]同时,也必须建立执行国际法院判决的中央执行机关,该机关要么直接掌控中央武装力量,要么在实施集体制裁时候在该中央机关的指导下由成员国自己动用其武装力量,但任何情况下都是为了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
我们看到,凯尔森在国际法框架中构建和平,主要就是通过具有行动能力的国际组织来保证和平,尤其是依赖于一种司法化的程序。所以他在多处强调了这样一种思想:更为有效的是通过集中适用法律、尤其是集中地实施制裁更能够保障和平。也就是说创立解决各个法律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共同体本身之间争端的法院;集中使用武力、建立中央执行机关。法律的适用不仅仅是由法院执行,而且也由行政机关执行。[23]
凯尔森之国际组织框架其实是建立在他的基础规范上,该规范决定着和平状态是一种法律秩序,使用武力乃是对不法行为的制裁。至于规范的内容,他并不涉及,或者说他在规范的内容上是中立的,[24]因而凯尔森的规范被认为是高度形式化的。尽管他没有暗示说由国际社会决定这样的基础规范是什么,但正因为其形式化特点因而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事实上,联合国的历史表明,凯尔森意义上的基础规范尽管内容狭窄,但可以被视为开放的体系,其内容在不断地充实。诸多国际法规范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发展起来,这可以为佐证。
卢梭限于欧洲范围,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联邦国家来消除战争。同卢梭方案相比,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则提供了另一极的国际秩序,即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的普遍联合,它立足于国家政体的形式和实质上的同质性。而凯尔森在和平状态本质上认同卢梭,认为和平的实质就是集中使用武力(作为对不法行为的制裁),但他们提供的和平秩序方案从各个方面来讲都相差甚远。凯尔森意识到无法达到卢梭版本的和平方案,所以他提供了一个中间阶段、最低版本的国际法律秩序,在康德视为必需的同质性前提的那些方面,凯尔森正好予以忽略,他满足于将和平定义为有条件地使用武力——作为对不法行为的集中性制裁,并作了许多国际组织建设方面的知识准备。如今的区域性、国际性法律秩序无不以这三种模式为蓝本,或多或少进行修正,或处于任何二者之间的中间状态,而与凯尔森最为接近。③
最高版本 最低版本 最高版本
卢梭← 凯尔森 康德
统一的欧洲具有集中制裁权能自由的共和制
联邦国家 ←的国际组织国家的联盟
说明:这是三者和平构架的简洁图示。凯尔森版本的和平方案在逻辑上可能向卢梭版本的和平方案演进(箭头所示),但却不能向康德版本演进。
第二部分 克服自然状态后的国际法律秩序(永久和平)
卢梭和康德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等同于战争状态,战争因其邪恶而应受谴责,和平是可欲的,故应当走出“自然状态”。④康德永久和平秩序可以简化为“各个共和制国家普遍性的自由联盟”,该和平状态具有永久性、普遍性和绝对性。说它具有绝对性,因为在康德的和平哲学中,战争被绝对地克服了。因为没有可能主动发起战争,所以连自卫战争的可能性也没有。鉴于康德永久和平在哲学上的先验性特征,故其在逻辑上存在一个先决条件,即克服国家间自然状态,进入和平状态:[25](1)国家,同没有法律的野蛮人一样,自然地处于一种无法律状态;(2)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强者的权利占优势;(3)依照原始社会契约观念,国家结成联盟,保护每个国家的自由;(4)联盟中的彼此关系不存在有形的统治权力。联盟可以随时解散,因而又必须随时更新。
从战争状态过渡到永久和平状态,是从一种绝对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绝对状态。自然状态-战争状态的本质是什么?康德在这个重要的逻辑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澄清,就完成了从自然状态-战争状态到和平状态的过渡。他从自然状态出发,通过“社会契约”使国家结成联盟,但这个联盟不具有卢梭那样的约束力和组织结构,也不存在有形的统治权力,仅仅因为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的存在,自然状态就被克服了,和平状态就降临了,在逻辑上缺少了一环。自由的共和制国家如果不在组织结构的意义上进行联合,仍然是自然状态。康德将卢梭的个人间的自然状态简单地位移到国家间的自然状态,但两种自然状态并不等同。克服个人间的自然状态是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国家,康德其实没有通过真正的社会契约来克服国家间的自然状态,在他那里,社会契约其实没有实质性内容。既然逻辑上少了必要的一环,康德仍然通过对国家属性的描述完成其和平方案,只能说,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的松散联盟是永久和平状态,这样的命题是一个逻辑上的先验规定。
一个国际法律秩序的可行性必须根植于对战争与和平根源的理解,并考虑政治上的可行性。有必要回头看看卢梭的构想。毫无疑问,卢梭欧洲联邦构想的出发点是国家间的自然状态,他对自然状态的克服是通过立约建立一个实体性的、有执行权能的欧洲联邦。他敏锐地考虑了这样一个欧洲联邦的可能性基础,“必须接纳所有举足轻重的大国为其成员国”;“将任何社会形式结合起来的是利益的一致,而使之分列的是利益的冲突”;各个君王的利益紧密相关;[26]欧洲各国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27]这里他谈到利益的一致和冲突,谈到国家的相似性,但非康德所规定国家必须是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的相似性对卢梭而言不是一个先决条件,而是这些条件已经具备,才使成立欧洲联邦有更大的可能性。但是,卢梭的欧洲联邦无论在当时还是近现代,都走得很远。他的欧洲联邦必须有立法权力、强制力量,还必须十分有力,这无异于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尽管卢梭隅于欧洲地理范围考虑世界秩序问题,但他的思想是统一欧洲的先驱,也是后世的“世界国家”的先声。卢梭模式是另一个版本的国际法律秩序,在现实世界同样难以实现。
在卢梭和康德失败的地方,凯尔森最低版本的国际法律秩序倒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国际社会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来约束各国的行为,这种状态被卢梭和康德视为自然状态,但凯尔森并非就此认为不存在规范,相反他认为国际法仍然存在,其特点是对国家行为的控制属于分散性制裁(针对国内法的集中性制裁),也就是自助。[28]一种可行性高的国际法律秩序的本质就是在这样的国际法框架内成立国际组织,追求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制裁(对国家行为的制裁从分散越来越趋向集中化)。如果说自然状态是卢梭和康德要克服的状态,那么凯尔森则是将其视为既存的基础纳入其法律秩序。如此一来,凯尔森理论对国际社会的现状改造的少,接受的多。他要行动的不过是建立某种具有相当执行权能的国际组织,规定集中制裁的条件,既不要求改造国家政体、政府形式,也不要求马上成立世界政府。而这正是后来联合国成立时的基本条件。
第三部分 国际法律秩序的先决条件——国家的同质性问题
康德规范性理论预设了一个和平前提:永久和平以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的普遍友好联合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中,国家的特性被简化为自由、独立、平等的公民组成的共和制国家,每个国家的文化、地理位置、宗教等因素不予考虑。因而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和平是否仅仅在同质的国家(homogeneous state)中才可能存在?康德之前的卢梭所构建欧洲联邦的宪法,其有效的条件并不以立约方的政府形式为前提。双方在这方面的差异根源于各自对和平状态的理解及怎样达成这样的问题有本质上不同的理解,因而其构建和平秩序的基础也就不同。
凯尔森对和平状态及如何达成问题的理解上,追随卢梭而非康德的理论。此外,他和卢梭的共同点有一方面比较突出,就是其拥有集中性制裁权能的国际组织不考虑成员国的政府形式和政体。[29]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法律秩序的发展历史有利于验证凯尔森而非康德的理论。尽管后世人们可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律秩序中看到康德的先验规定的影响,如人的自由、尊严、追求和平这些价值是联合国成立的宗旨,但联合国得以建立的政治前提正好是囊括尽可能广泛的成员国,而不考虑它们的国内政府形式;它规定使用武力的条件(单独或集体性自卫、安理会授权的集体行动)、和平解决争端(通过仲裁或司法)等等。如果把这些规定视为有效的规范,那么规范的内容在价值上是中立的。所有这些都能浮现当年凯尔森着力倡导的和平方案的影子,部分地也有卢梭的余音(必须接纳所有举足轻重的大国)。可以初步断言,在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国际法律秩序并不以国家政体的同质性为前提。
联合国作为高度形式化的国际法律秩序取得了成功,其具有的广泛性使它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法律秩序。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越来越多的法律规范发展起来了。如今看来,同质性国际社会最好视为一种渐进发展的结果,无法视为前提,这是我们当前多元主义的知识状态所能合理期待的。
第四部分 结论:不断扩展的利益、自由价值观和基础规范的内涵
卢梭、康德和凯尔森的理论探究永久和平的法律秩序的可能性基础是什么,三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卢梭的法律秩序表现为欧洲联邦,其基础是利益的一致。康德的方案是逻辑上的先验规定,表现为自由国家的联合,其基础是国家内部的公民是自由的,政体是共和制的。凯尔森的和平是一种特定的国际法律秩序,其等同于有效的规范,表现为在规范之下使用武力的条件仅仅是作为对不法行为的制裁。尽管他们都为当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了知识基础,但事实上,该秩序的可行性基础是二战结束时摆在人类面前冷峻的政治现实。
如果从三人提供的基础来考察二战后成立的国际法律秩序,可以明确一点,当时的基础非常狭窄。但经过冷战到冷战结束直至现在,这样的基础内涵事实上是扩展了,这就给国际法律秩序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当卢梭谈到利益的一致、康德谈到自由的共和制国家、凯尔森谈到基础规范的时候,国际法律秩序的建设于此有何教益?首先,现实表明国际法律秩序的成长、壮大有赖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内容的不断扩展,这有助于促进卢梭意义上的各个国家的联合。二战之后的数十年,国际社会发展了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这导致了海洋法、环境法、南极条约等国际性制度的产生;发展了人类整体利益的概念,这催生了反人类罪、反和平罪、战争罪等国际强行法制度的产生。其次,国际社会一体化进程加速,国家间的交往方式和国家行为越来越以规则为导向,这促进了凯尔森意义上的规范内容的扩展,国际条约法、国家责任法的实践和立法工作、《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国际法原则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及《行动纲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代表。其三,国家政体的同质性确实不是国际法律秩序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但是战后国际社会数十年的发展,人类的自我意识提高了,权利意识增强了。自由价值观越来越受到个体及群体的接受,国际人权法律体系内容逐渐充实、越来越获得普遍性认同,康德所谓人的自由这样的先验规范也逐渐具有了经验上的意义。其四,上述内容无论是作为康德先验自由规范的增生,还是凯尔森规范内容的扩展,若要在国际法律秩序中具有效力(validity)和有效性(effectiveness),必须要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性的同意,这样可以使规则达到合法性和正当性方面的同一,这才是国际法律秩序的坚实基础。否则,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分离将会使人类历经千辛万苦构建起来的国际法律秩序根基不稳。
雷蒙德·阿伦希望我们所处的国际社会可通过超国家社会进化到同质的国际社会。从国际法律秩序这个角度来说,这确实值得人类追求。不过这个进程可能十分漫长,对此有必要倾听康德的建议。他谈到当时的国内制度时曾说到,“最好的政体,就是在这个政体内,不是人而是法律去行使权力”,“有什么东西能比他们这种观念具有更多的形而上学的崇高性呢?……如果这个观念通过逐步改革,并根据确定的原则加以贯彻,那么,通过一个不断接近的进程,可以引向最高的政治上的善境,并通向永久和平。”[30]这确实是我们对待国际法律秩序成长时应当持有的态度。
注释:
①在1940-1941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敌我双方的殊死搏斗之际,凯尔森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了题为“国际关系中的法律与和平”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讲座”,对立足于法律秩序的国际和平作了充分的阐述。该讲座后来以“Law and Pea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为题出版:Kelsen,H.Law and Pea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以下简称“Law and Peace”。
②这个观点也是传统上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法战争的分界线。在凯尔森的国际法理论中,国家使用武力仅仅是对一国之不法行为的报复、反应或制裁才是合法的,从传统的意义来看也就是正义战争。参见Kelsen,H.Law and Peace,pp.36-48;汉斯·凯尔森《国际法原理》,王铁崖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28-39页,15-19页。
③凯尔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正值困难的时候对未来国际秩序作了上述构想。“在联合国形成的幕后,他是知识界的一位核心人物”。据说后来凯尔森参加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那么说他“看到自己的理论假设成为现实也就再合适不过了”。参见[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5页。
④自然状态是万民法、后世国际法的一个逻辑出发点,卢梭和康德也不例外。参见Aron, R.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labar:Robert E.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1981,p.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