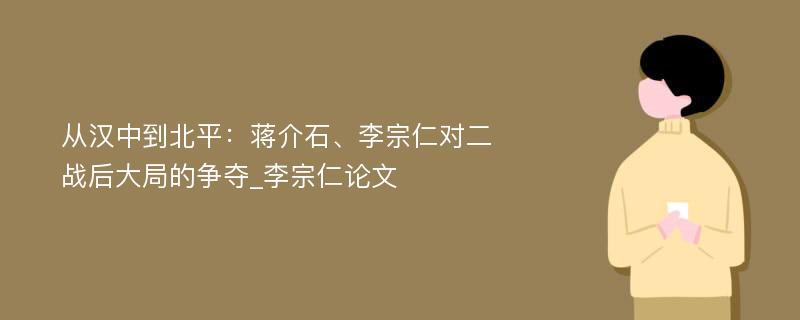
从汉中行营到北平行营:蒋介石、李宗仁对战后全局的角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营论文,北平论文,汉中论文,战后论文,蒋介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11)01-0073-09
随着抗战的胜利已成定局,蒋介石、李宗仁开始了对战后全局的角逐。汉中行营到北平行营的设置与演变,深刻反映了这一角逐。汉中行营设置于1945年2月①,撤销于抗战胜利之后。北平行营设置于1945年9月,1946年9月1日改称北平行辕②,撤销于1948年5月20日李宗仁就任副总统之后。由于学术界尚未探讨,下面就来探讨。
一、汉中行营的设置:蒋介石、李宗仁对战后全局角逐的开始
在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始终问鼎国民党政府中央大权的只有桂系。该系虽然多次为蒋介石所败,但终未瓦解,李宗仁、白崇禧到1936年6月还与广东的陈济棠一起发动了倒蒋的“六一事变”。随着抗战全面爆发,“以前内战中的重要领袖们,现在多少都有‘先困难而后私雠’的概念,认为内战实在不应再继续了”[1](p.460),因此蒋李公开对抗随之结束,但相互间的权力角逐并未消失。抗日战争进入1945年后,日本的战败只是时间问题,蒋介石、李宗仁对战后全局的角逐作了思考,这里所说的汉中行营,其设置就是两人较量的结果。
这个问题还需从安徽问题及第五战区的地位谈起。抗战全面爆发后,桂系编成3个集团军40个团投入战场,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兵力,蒋介石不能不有所表示。他除了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外,还把安徽地盘给桂系,这是因为:湖南与广西毗连,湖北据长江上中游,与广西距离也不远。如果把两湖之一送给桂系,则桂系地盘连接起来,将成尾大不掉之势。只有安徽邻接南京,易于控制,而且自从国民政府建立以来安徽早已成为应酬各派军阀的礼物,送给桂系再也合适不过。这样,安徽为桂系所控制。第五战区所辖战略地域,在抗战初期为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的安徽、江苏,相持阶段到来后为皖西、鄂北和豫南。它“在当时辖地最广”,不仅大别山区仍归李宗仁直接指挥,“即鲁南、苏北名义上亦属五战区战斗序列之内。”在兵力上,前期所辖兵力为35个师,后期为36个师又81个游击纵(支)队,李宗仁“前后直接指挥过的部队不下百余万人”[1](p.546,559)。因此,第五战区成为西南大后方的东部屏障。
李宗仁在第五战区的几年,实际上“在费尽心机地同蒋介石各演各的戏”,暗中较量,以“保住五战区的地位为首要任务”[2](p.59),其企图显然是在战后以此为基础与蒋介石角逐全局。为此,他采取两项主要的措施:其一,同第五战区杂牌部队“泪眼对泪眼,休戚与共”[3](p.114),竭力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一方面增强自己的实力,一方面树立自己不仅是桂系军队而且是杂牌军队的领袖的形象。其二,利用第五战区战略地域的演变,竭力扩大桂系地盘。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兼任安徽省主席之初,虽然战场指挥很忙,但是也亲自到六安就职安排一切,固定这块地盘。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到襄樊后,他将省主席一职先后以桂系大将廖磊、李品仙等担任。按照司令长官得兼任辖区省政府主席以利军政配合的规定,其意显然是想兼湖北省主席。
针对李宗仁的企图,蒋介石相应地采取了系列措施:其一,竭力缩小第五战区的战略地域。他“将宜昌以下的江防,由五战区划出”[1](p.546)归入陈诚的第六战区,同时以湖南为中心成立第九战区。这样不但分割了第五战区,而且将第五战区、安徽和广西横刀切断,李宗仁不得不将第五战区重心从襄樊移至西北面的老河口。其二,在人事上,拒绝李宗仁兼任湖北省主席,而让陈诚兼任,并以薛岳兼任湖南省主席。这样,三个战区司令长官中只有李不能兼省职,更使他气愤的是,汤恩伯在指挥系统上属于第五战区,蒋介石却让他兼任河南省主席。如此,鄂西、鄂南、豫南分别在蒋介石的亲信控制下,李宗仁被架空,只有对皖西的李品仙能指挥如意。程思远指出:“蒋介石不愿广西军人的势力过于庞大,以免一九二七年八月迫蒋下野的故事重演。”[4](p.3)
中共在努力全力抗日、积极渗入敌后以后,建立了一系列抗日根据地,分布在华北和长江南北,这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带来了更大的担心。他认为:“如果黄河以北的八路军和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深入中原,就有中共南北武装力量连成一片的可能,如果进入作为江河之间脊梁地带的大别山区,则江淮河汉均在俯瞰之下。”[5](p.1114)蒋介石长子蒋经国视1944年“为抗日战争最险恶的一年”[6](p.44),且不论他如何作此论断,但是随着该年过去,蒋介石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本消灭中共。针对中共所提联合政府的主张,他在1945年1月24日的日记中写到:“对此破坏我国家法规与革命制度者,决不能再有迁就也。”[7](p.713)在这背景下,第五战区及其所属大别山区的反共地位上升,他打算夺回安徽,牢固控制大别山。他提出设立第十战区于大别山,以亲信刘峙出任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宣称刘峙“在进剿大别山红军时期,战功卓著,地形熟悉,指挥这一地区的军事非常合适”[5](p.1114)。
李宗仁“一向把安徽视为禁脔,不许他人染指”。他强调:李品仙“在安徽,历有年所,人地相宜”,如果要把大别山划为新战区,最好由他担任司令长官并兼省主席,“军政统一,便于指挥。”[8](pp.186-187)他还强调:“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中途更换指挥官,只会予以敌人可乘之机。如果委员长为了安置刘经扶(刘峙字),那么就把我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让给他。”[5](p.1115)
蒋介石认为,如果强行夺去安徽,不利于反共;如果让步同意桂系人物出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不但可以团结桂系共同反共,还可乘机撤去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这一重要职务,因为尽管蒋介石竭力掣肘第五战区,但是其地位仍很重要;特别是李宗仁对杂牌部队的拉拢,使蒋介石如坐针毡,他发出了李“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1](p.518)的感叹!再说,“如果以第五战区的豫、鄂边区为轴,以刘峙为中心来进行防共反共的措施,同样可以达到他的战略目的”。因此他将计就计,1945年2月10日下令“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9];接着下令刘峙、李品仙分别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同年12月刘峙指挥第五战区兵力将八路军李先念及王震部由鄂北压迫到鄂豫皖边一带时,蒋之侍从秘书曹圣芬得意地说:“委员长当时的眼光看得非常远大,那时候他就开始布置战后‘接收’的准备工作。李德公调汉中是为使他负几个战区党、政、军的全面责任。刘经扶(即刘峙)对付共产党很有经验。”[8](p.187)
这一角逐,蒋介石达到了布置战后“剿共”和“割断李宗仁与杂牌部队的关系”[2](p.61)之目的。汉中行营的性质与前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名义上辖第一(胡宗南)、第五(刘峙)、第十(李品仙)3个战区和大别山游击区,实际上是蒋“为了架空李宗仁而设置的”③[10](p.154)。在3个战区中,第十战区算是桂系的地盘,无论建制上归谁,他人不能染指。另两个战区“从人事关系上说,胡宗南和刘峙都是蒋家的嫡系人物;从职权来说,小事自己决定,大事直接于中央”[8](p.190),只是给蒋之报告“亦送一副本给汉中行营罢了”;至于行政和党务,李亦无权指挥,汉中行营不过是例行“备查”、“照转”而已。因此,他气愤地指责:“抗战六年,我第五战区可说是战绩辉煌,蒋先生实无适当藉口把我调职。所以他唯一的抉择便是成立一个位尊而无实权的新机构,把我明升暗降,与部队脱离实际关系。”[1](p.566)
对李宗仁来说,并非如其所说是“忽然”被调离的,也非“六年来戎马倥偬,案牍鞅掌,个人也很想得机会休息;加以功高震主,无端招忌,倒不如暂时减轻一些责任为愈”[1](pp.566-567)。他以离开第五战区为条件,换取了第十战区的战略地域扩大“北至陇海铁路,南至长江,西至汉口,东至海州”[11](p.272)。更主要的是,尽管汉中行营主任无实权,但毕竟“位尊”,把李之地位凸现出来,他可以借此舞台发展自己,因而自称此职“亦深合我意”。他“对今后中外大局的演变,作一番冷静的思考”,得出“战争在华南,问题在华北”[1](p.566,569,601)的结论。据此结论,李宗仁以第五战区长官部组织和人事为基础④,对汉中行营作如下调整:
其一,起用北方籍人士。原参谋处长高松元改任高参,由在晋系军队工作过的河北籍梁述哉任参谋处长;以曾任西北军系统刘郁芬的参谋长的河北籍张寿龄任总务处长;以东北籍李宇清任高参兼副官主任。秘书长聘请梁寒操担任,由于梁既未到任也未表示拒绝,此职“一直虚悬未决”,秘书处乃由山西籍、曾在晋军任过参谋处长的尹冰彦“支应门面”。
其二,注意协调桂系内部关系。原军务处长梁家齐改任高参,遗缺由白崇禧的保定军校同学、安徽籍方克猷继任(方也曾在晋军徐永昌部任过职);副官处长农之政也改任高参。梁家齐是桂系里“少壮派的中间人物”,农之政是“元老派巨子”,两派“明争暗斗,势同水火”,李宗仁给他们闲散高参的名义,以缓和矛盾。至于行营其他官员,“一仍原第五战区长官部的原班人马。”
可见,李宗仁不但注意协调桂系内部关系,还注意“突破桂系封建集团这个小圈圈”,这意味他“未来个人发展的企图,目标在北方”[8](p.188)。此外,李还特别安排曾在张学良手下军长、辽宁籍董英斌担任第十战区的参谋长,“其用意对战后的东北不是没有想法的。”[5](p.1114)蒋介石对这一切心知肚明,1945年6月巡视汉中,对同李宗仁一起到机场迎接的次子蒋纬国指桑骂槐:“为什么不好好地在部队里,跑到汉中来胡闹!”[8](p.191)
二、北平行营的设置:中共问题下的蒋李角逐的继续
日本投降之后,李宗仁马上想到自己的出路。他认为,蒋李停止对抗就是因为抗战,而抗战胜利,蒋介石很可能又要对桂系下手,桂系“就是顺他,他也不会放心的”[12](p.1)。1945年8月14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大意是“致以领导抗战赢得胜利的祝贺;表示追随蒋介石完成国民革命的北伐大业后,现又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抗战胜利,自己在前方担任方面军事统帅8年之久,心力交瘁,请求予以名义出国考察,藉资休养”。他还以中共问题相威胁,宣称“至于战后对共产党问题以及加何实现国家军事与政治之统一问题,中央自能妥善处理,庶不至战乱再作,重陷斯民于水火之中”。8月17日,蒋介石亲自电话李宗仁:“战后建国的任务重大,国家遭遇严重破坏之后的重建工作,还需要出任艰巨。将来到可以放手的时候,‘我们弟兄一道下来休息。’并表示汉中行营是要撤销的,至于将来李的出处问题,中央方面正在研究。”[5](p.1117)
蒋之所以犹豫,主要是相互间对华北、东北的角逐。早在1944年5月,李宗仁就提出:其一,采取“后浪推前浪”的方式接收华北:“原驻河南、安徽和苏北的国军,即向山东、河北前进,原驻山西、宁夏、绥远的,则向察哈尔前进。各该军所遗防地,则由后方部队递补。”如此,驻扎在安徽、河南一带的桂系部队“将先入华北,甚或东北”。其二,东北地区最为重要,“最为棘手”,主事者“尤应慎重遴选”。此人“必须有眼光,有魄力,勇于负责,必要时敢于便宜行事”[1](p.596,597,596),黄绍竑最为合适。李宗仁推荐黄绍竑的原因,“一是李早有到东北掌权之意,他知道蒋介石是不会同意黄绍竑去东北的,李这样做是企图达到毛遂自荐之目的。二是李、黄本来是定桂讨蒋的伙伴,但因蒋桂战争桂军失败后,1930年夏黄不愿再战,通电求和并弃桂投蒋,李这样做,藉以达到离间黄和蒋的关系,迫使黄再回到李的方面来。”[13](pp.174-175)总之,李宗仁企图囊括华北与东北。
1945年8月24日,李宗仁通过白崇禧致电蒋介石,宣称在“近查华北各省,自敌军投降后,中共军队乘机积极进展,压迫伪军,侵夺要点,并思利用敌伪武器扩军抗命”的情况下,“请迅即发表北平行营命令”:(1)“以便先遣要员,率一小部空运部队早达平津,指挥先遣军及伪军,巩固要点,控制机场及海口,以保持交通连络,并安定民心及归顺军之军心。”(2)“令由行营指挥河北滦东一带之归顺之伪军,布防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之线,以防奸军东窜,渗入东北境内,夺取伪械,发展组织。因苏军进入伪满境内,其撤退完毕有三个月以内之时间,倘此时,如任奸军渗入,苏军以不干涉内政为口实,恐不至拒止,我对奸军投鼠忌器,东北环境恐日趋困难矣。”(3)“黄河以北,党政军各机关渐次向北推进,连(联)络通信既已困难,协同一致亦属不易,请划定行营管辖区域及所属战区,俾便督导指挥。”电文最后强调:“长江、珠江流域,由陆军总司令、各战区司令长官,就近督导国军,实力雄厚,党政力量亦能配合,尚不十分严重。惟黄河以北,我党政军力量均属薄弱”,必须尽快设置行营[14](pp.38-39)。
桂系抓住了当时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中的一大焦点,即北平行营如何设置的问题。8月30日,中共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中提出:“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委任中共人员为主任。”“确立省制,信任地方,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请委任中共推选之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组织省政府,其他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各省与平、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请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副主席、副市长及委员。”[15](p.21)9月2日,毛泽东指出:“宜以北平行营给予中共将领,俾秉承蒋委员长之命,指挥中共在山东、江苏、河北、热、察、绥等地方之军队。”王世杰宣称“此不可行。中央军事委员会中或可有中共将领参加”[14](p.39)。9月3日,周恩来、王若飞提出谈判要点九项,之一即为“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16](p.14)。国民党拒绝指出:“北平行营主任,不宜规定由中共推荐,北平政治委员会之设置,更不相宜。”[17](p.43)9月4日,邵力子又称:“北平政治委员会一事,政府现时根本无此制度。政府于东北行营内设置政治、经济两个委员会,系应东北收复后特殊情况之需要,以收复沦陷已久之东北政治、经济为目的,而兄等所提之政治委员会之性质,实与‘九一八’以前华北、西南政治委员会相同。其于国家之统一,实相违背。”[18](p.48)对此,周恩来指出:“北平政治委员会之设置,乃为改组过程中增强两党团结之办法。其隶属或在北平行营之下,或置于行营之上,均可商量,盖我党所着重者,并非在此,而惟在谋北方几省政治问题之解决也。”王若飞指出:“我党既有百余万党员与百数十万军队,又有许多由人民产生之解放区政权,这一般党员官兵等皆须顾到,期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过渡到团结统一。故我党建议中之北平行营,与北方政治委员会,即系应此目前实际之需要而设置,如无此安置之办法,则我党即无以对全体之官兵与党员民众。”[18](p.51,52)9月8日,他进一步指出:“解放区乃既成之事实,只求中央同意,并非要求中央另划地区。如华北五省,过去系由中共军队坚持抗战,始有今日,故要求此五省由我党负责。”[19](p.366)
由此看来,国共双方在华北机构的设置问题上分歧很大。蒋介石指责中共“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踞热察,扩大叛乱”[20],需要团结桂系共同对付中共。因此,他一方面回电要求李宗仁助他一臂之力,一方面赶紧宣布成立北平行营,于9月1日“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周恩来对此反对,9月19日再次强调指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北平行营应“由中共主持,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张群声称“此新方案,甚难考虑”[21](p.87)。9月21日,张治中强调:“关于军事指挥机构,北平行营之人事任命甫经中央明令发表,不宜更改。我们且不说中共军队遵令整编确定以后,驻在一地,即可受当地军事最高司令部之指挥调度,不必另设指挥机构,即令为顾及事实,亦不必设置行营一类之机构,而只可由中央按照军事指挥系统,予以适当之名义,以便统率指挥。”周恩来提出:既然“北平行营已经设置,另设北方行营亦可”。邵力子回称“政府无此体制”[22](pp.90-91,93)。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东北接收作出处理,决不让桂系染指东北。8月31日,特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李宗仁甚为不满,认为熊式辉总揽东北九省大权,地位在其之上[23](p.252),批评熊式辉“是个只会敷衍做官,不敢负责做事的官僚”[1](p.606)。北平行辕总务处长张寿龄指责说:“中央用人,主要还是派系问题,东北九省的主席中,政学系的占几个,CC团占几个,原来他们早就分配好了的。”[24](p.88)
三、北平行营的组织与职权:李宗仁的雄心与蒋介石的掣肘
法律上,北平行营的地位比汉中行营“确实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因为:其一,地理上,“由一个偏处在陕西的汉中小城市,一跃而进到当时所谓‘故都’的北平,与汉中相比,不知优越多少倍。”[23](p.252)其二,职权上,北平行营直辖第十一、第十二两个战区,辖境包括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5省和北平、天津、青岛3市,“辖区内一切军、政、党的设施俱得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李宗仁的权力“不可谓不大”[1](p.601)。蒋介石还对上任做了特意的安排,使其风光无限:1945年10月26日,李宗仁乘坐蒋的“美龄”号专机,在6架战斗机护航下抵平。
李宗仁对此“感到鼓舞”,认为正符合自己“施展抱负的愿望”[23](p.252)。他抵达北平时发表谈话:“当遵照委员长之指示,代表委员长执行一切命令,今后不但要求中央政令在华北的彻底,尤须作到中央政令在华北的彻底执行。目前旨在处理受降善后等问题,并督导省市政府和军队协力,以谋地方秩序之安定,并作长治久安之计”,“使华北成为民族复兴之重镇。”[25]为此,他按照北平行营的组织,对人事作了精心遴选。
关于北平行营的组织,张寿龄指出:“北平行营的编制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编制表有甲、乙两种,甲种编制的人员比乙种少。北平行营是按甲种编制组成的。可是第二处却按乙种编制,因为这个处是特务机关,所以也就特殊了。当时北平行营共有10个处:参谋、军务、总务、政务(后来改称秘书处)、经理、军法、新闻、外事(后来并入总务处改为外事科)、交通、第二处等。经理处在编制表上是属于总务处的一个科。但是从汉中行营到北平行营都是另成立与各处并立的经理处。”[10](p.154)第四处科长唐真如说:北平行营内设“总务处、第一、二、三、四等处以及政务处、政工处、经理处、军法处”,政工处、第二处(特务处)虽设在行营里,但属于“另一个系统”[23](p.253)。
关于人选,除政工处、第二处外,参谋长王鸿韶,副参谋长甘沛泽,秘书长萧一山,政务处长王捷三,秘书处长尹冰彦,总务处长张寿龄,副处长李宇清,军务处长方克猷,参谋处长梁述哉,交通处长赖和平,经理处长何福荣,军法处长黄敬修,新闻处长先后为赵可夫、赵仲容,外事处长黎度公(黎被顾问石颖排挤去职后由石颖取代)。机要室主任李扬,秘书主任黄雪村并兼任政工处副处长,刘仲华为总参议。北平行营改称北平行辕后,“其组织与人事除增加一调查处之外,余均照旧。”[1](p.601)
这张清单把李宗仁的企图表露无遗:其一,萧一山和王捷三分别为西北大学、北洋大学教授,王捷三为陕西城固人,曾任陕西教育厅长。两人不但“与全国教育界人士极为熟悉”,而且与蒋介石“政治主张格格不入”,因而与李宗仁“颇为投契”[1](p.602),李便对他们“诚心”相邀[26](p.161),欲借重两人“与学术界的深厚关系,谋求与北方上层文化人士的联系,从而取得同情与支持”[27](p.133)。其二,以原有桂系班底为基础,在汉中行营的基础上继续延揽原属晋系、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有关军政人士,以立足华北,面向全国。除了军法处长由李宗仁表弟黄敬修、经理处(一度由山东人、原东北军军需官张寰超担任)改由何福荣担任外,其他各处的“人员多数还是老的班底,变动不大”[23](p.253)。其三,刘仲华为中共地下党员,出任总参议是李宗仁安排用来与中共打交道的,他后来在北平和谈中起了传递作用。
当然,这一安排的前提是不能有害于李宗仁及其心腹对关键机构的掌握,广西籍以外人员的延揽不能违背这一前提。经理处“管现款物资,掌经济大权”,经理处长何福荣广西人,曾任第五战区兵站总监部经理处长;副处长关仲方也为李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交通处不只管交通,还管补给、通讯、卫生,“也属于经济物资的范围,不能随便放手”,因此“由广西调来赖和平当处长”。总务处“也掌握一部分物资、款项,但由于张寿龄、李宇清二人还听话,同时从老河口起,他们就跟随李宗仁,也深知李宗仁的性格和作风,况且总务处下面的科长如潘展云及廖某等,也是新桂系老人”[23](p.253,254)。对于机要室,李宗仁以心腹李扬负责。此外,李宗仁对“另一个系统”也设法介入,竭力以黄雪村任政工处副处长,黄明钧为专员,陈大文为科员;以郭琅光任第二处副处长,廖小文为参谋。
蒋介石颇知李意,把他“捧得高高在上,负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使行营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1](p.601)的机构:
其一,任命孙连仲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统率3个军坐镇保定,省政府设在保定,长官部却设北平;以傅作义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辖察哈尔、绥远两省。蒋介石把军事实权交给这两个人的原因是:孙连仲自中原大战后投靠陈诚,傅作义在抗战爆发后为蒋成功地从阎锡山系分化出来,他们在军事上不会让李宗仁染指;特别是孙连仲,其出任完全得力于陈诚和CC系骨干张厉生的“推荐”[28](p.136)。两人的出任,是蒋介石与陈诚“精心策划的架空北平行营、削弱其职能的一种措施”[5](p.1118)。由于孙连仲还兼任北平行营副主任,“实际上掌握了北平行营的军政指挥实权”。这样,李宗仁对冀察绥三省的权力就被剥夺,“连发给属下20支步枪也做不了主。”[13](p.175,176)此外,蒋介石以王耀武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直接对蒋介石负责。阎锡山的山西,就是蒋介石也不能指挥。刘多荃的热河,在军事指挥上却划入东北行营。北平行营辖5省3市,哪个省市也辖不了。
其二,在机构层级关系上,北平行营名义上是“华北军政最高官署”,蒋介石“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从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1](p.603),但这些只是敷衍李宗仁面子的虚文,实际上“战区司令长官受军事委员会的直接统辖,而各省市政府又必须听从行政院的命令”[24](p.89)。蒋介石在华北地区重要人选任免上概不征求李宗仁的意见,事先既不打招呼,命令发表后也不通知。因此,北平市长熊斌、何思源,天津市长张廷锷上任时来拜见,李宗仁才知道。北平行辕“所辖各省市的负责人,都是来头很大、各事其主的。如果对李听命过多或过从较密,反而于自己不利,甚至会遭到横祸”,他们“都了解政治市场上的行情,所以对主管机关北平行辕的态度,不过是呈送公文备查、虚与委蛇而已”[5](p.1120)。
其三,在北平行营打入两个棋子政工处和第二处。政工处人员“主要由上面任命”,处长张某“是国民党中央派来的”[23](p.253)。第二处由军统特务马汉三任处长,“该处在行辕中是个独立王国,人事经费,都单独起炉灶,业务上更非李所能过问。事实上李本人也是他们的工作对象,副官主任李宇清就是他们放在李身边的一颗钉子、一个窃听器。”戴笠还当着李宗仁的面对马汉三指桑骂槐:“你要好好听话,不许你自由行动,不然,我就枪毙你。”[5](p.1119,1120)
四、北平行辕的撤销:李宗仁“澄清”华北与树立“民主”形象
在国共内战下,北平行营负责指挥华北“戡乱”军事,并负责支援东北军事[29](p.344)。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认为,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以该机构统一指挥3个战区43万的兵力,“以张家口为主要目标,对我晋察冀解放区从东西两面进行夹击,占领热河、察哈尔两省,从而打开由陆路进入东北的通道,并切断我华北、东北、西北战略区的联系。”[30](p.471)这一目标,按照李宗仁所说,只有傅作义“攻占”张家口“为内战初期政府军唯一的胜利”[1](p.608),其他皆败,而其原因即在于蒋之掣肘。李宗仁到达北平次日即1945年10月27日,就公开指出:“此间妯娌众多,本人忝居长嫂,但以职权仍欠明确规定,做事不无困难。”[12](p.10)他后来回忆强调:“如果中央能按照规章,授我实权,以我数十年统兵和从政的经验,以及鞠躬尽瘁的决心,自信可以澄清华北,辅翼中央而复兴中国。”[1](p.601)
北平行营设置之初,蒋桂双方爆发了两场争论。一是桂系军队是否调入华北。李宗仁在不能染指东北后企图竭力“澄清”华北。根据事先“后浪推前浪”的计划,他要求将第十战区桂系军队李品仙部调入,并要求白崇禧“相机向蒋先生建议”。蒋则命令该部开到徐州受降接收,尔后“不得再向北方推进”;至于华北与东北,则派远在滇西、缅北的嫡系军队前来。李气愤万分,华北局势的“不可收拾可能是由于我权力受无理限制,人不能尽其才之所致”,宣称如能将桂系军队调入,“华北局面或可改观。”[1](p.608,597,615,608)
另一场为东北、华北何者为重之争。1946年5月,白崇禧根据李宗仁之意,建议蒋介石要想“彻底肃清东北”,须“抽调五个美械装备师到华北,归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指挥,绥靖华北地区,事毕再行调回”[31](p.234)。蒋拒绝。于是,李宗仁也不准将华北军队调入东北。8月20日,熊式辉致电蒋介石,指责李宗仁以“加强关内兵力”为由,不准经蒋批准的林伟俦62军支援东北。蒋介石也无可奈何,8月25日回电称:“惟闻六十二军已到冀东开始扫荡,如此则一时恐不易转移,好在扫荡时间最多半月或待告一段落,再令归还东北也。”[32](p.416,417)1947年6月19日,熊式辉又电话李宗仁,要求调拨驻守天津的一个师,无论是李宗仁还是孙连仲,均称“天津保定势将与匪决战,天津周围有匪六七万,不能令即开沈”[32](p.454)。比较起来,晋察冀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密切配合,在兵力上,晋察冀解放区自1945年8月至1947年划归东北解放区的有10多万人,14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尚不包括在内;在战略地域配合上,晋察冀将冀热察与冀热辽军区、冀东地区划归东北解放区[30](pp.480-481)。国民党军焉能不败!
1947年7月,蒋介石对李宗仁表示拟调其为东北行辕主任,李以“患胃溃疡甚重”而“拟要求赴美就医”。蒋表示:“如果李答应去东北任职,可准假两月赴美治病,先由白崇禧前往代理。”李宗仁因东北“少有挽救希望”而拒绝[31](p.236),指责蒋此时才想到由他出任,简直是“异想天开”[1](p.615)。蒋乃采取两项措施:其一,于8月以陈诚接任东北行辕主任,给予他“坚守东北,确保华北,力争华中,巩固华南”的任务;这样,李宗仁不但对东北而且对全局再无军事指挥权的希望。其二,于12月2日电令撤去保定、张家口两个绥靖区,调孙连仲、傅作义为北平行辕副主任,设置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傅任总司令。电令“叙明冀、鲁、热、察、绥五省为其辖区”,并催傅“于本星期内成立总部,并立即宣布就职,勿予匪以乘机之间隙”[32](p.499);这是以“统一”华北军事指挥系统为名,在法律上剥夺了北平行辕的军事指挥权,李宗仁立刻意识到华北军事既由傅统一指挥,“行辕更可不必多管。”[1](p.616)
在上述争论的过程中尤其是之后,李宗仁利用北平行营这个舞台树立自己的“民主”形象,等待时机取蒋而代之。这方面的活动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首先,经常与大学教授、文化界人士以及在野的军政耆宿与社会名流来往、座谈,目的在于从蒋介石的独裁中塑造自己“作为一位众望所归的民主改革政治家的形象,树立在华北的大地上,铭刻在各阶层人士的心目中”[33](p.33)。
其一,努力争取各界的人心,设法解决他们的困难。如将协和医学院几位知名教授安排到广西医学院任教,解决他们的政治困境和饥寒问题;又如充当“替各方搜罗柴、米、油、盐的总管”,设法解决了北平各校员生及日本战俘的粮荒、煤荒,送米、送煤给著名画家齐白石;再如坚决制止军统特务马汉三对大学生的暴行。
其二,摆出开明姿态,邀请各大学名教授举行“双周座谈会”,要他们“对政府设施尽量批评与建议,不必隐讳”[1](p.605),不失时机地强调蒋介石是华北局势乃至全国局势恶化的根源,而他这个身负华北最高军政责任的北平行辕主任却在蒋之架空毫无所为。他宣称自己并不失望,强调:“我身为封疆大吏,既不能守土,又不能卫民,已经很对不住华北的父老兄弟姐妹啦!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决心和诸位一道为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而奋斗到底!”[33](p.30)同时,尹冰彦等人拿出他的名片,频繁拜访各方人士。他本人“不但对所接触的原东北军高级将领如于学忠、何柱国、刘多荃等礼遇优渥,就是对一般东北人士也总是表示关怀”[5](p.1115)。一时间,他在北长街的李公馆,“居然竟‘谈话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24](p.95)
其次,设法与美国政府直接往来,将自己作为国民党内一个“民主”而又能挽救国民党政府崩溃的柱石形象树立在美国政府眼中,企图在它的支持下出掌国民党政权。
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利益考虑,在日本投降之后即定下了对华政策基调,即“通过使交战的各派和解的办法,恢复一个‘强大、统一和民主的中国’”[34](p.14)。但是蒋介石的独裁和对中共的军事失败,使美国政府很失望,而李宗仁的“民主”形象引起了它的注意。他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北平调处国共冲突期间就提出许多建议,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马歇尔回国任国务卿后指令司徒雷登到北平专访李宗仁。司徒雷登不但同他深谈,还通过燕京大学进一步认识了其“民主”形象。1947年9月8日,司徒雷登报告美国政府说,“在学生中间,作为国民党统治的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而李“日益获得了公众的信赖。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他不忠于国民政府的谣言”[35](p.299,300)。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到北平与李长谈后,也指责国民党政府“麻木不仁”,吹捧他为“擎天一柱”。
上述活动收效明显,北平大学校长胡适称李宗仁是“民主”的象征,美国政府决定支持他成为国民党政府内团结“改革派”的核心。李宗仁便等待时机的来临。
自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发表“双十宣言”、首次公开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之后,李宗仁意识到不能继续留在华北。1948年春,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李宗仁决心竞选副总统,“挺身而出,加入中央政府,对彻底腐化了的国民党政权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以挽狂澜于既倒”[1](pp.615-616)。蒋介石要白崇禧赶快复电:“北平很重要,共产党正猖獗,北平是北方最高指挥机关,关外虽然不属北平指挥,但接近北平,关系重大,不可离开,这是一理由;再一理由,我是军人,副总统又是一个军人,不好,要他安心剿共。”[36](p.545)李宗仁断然拒绝,指责“北平有许多事情办不通”,宣称“若竞选成功,即不回北平,若竞选失败,亦不返北平”[29](p.344)。经过一番苦战,4月29日如愿当选。
竞选成功,是李宗仁在北平与蒋角逐的结果,他“要摆脱北平行营主任的想法,终于成为现实”[37](p.1105)。无论是在北平的“民主”活动中还是在南京的竞选活动中,他对北平行营人事的有意安排起到了效果,王捷三即指出:“行辕高干中,广西人并不多,北方各省市人都有,分头拉拢,都很顺利。”[26](p.163)李宗仁对他们的“苦心孤诣,自是铭刻难忘”[27](p.133)。虽然他从北平行辕主任改任副总统“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1](p.630),但是形成了新的权力格局,使以后桂系逼蒋介石下野成为可能。出任副总统后,李宗仁即提出辞去北平行辕主任之职。这个机关既是安插李宗仁的,蒋介石即随着李的辞职而裁撤。
总之,汉中行营和北平行营的设置与演变,深刻体现了1945年至1948年间蒋介石、李宗仁对全局的角逐。从军事指挥系统来说,汉中行营设置的必要性不大。因此,尽管早在1938年就颁布了行营组织大纲,但是该行营实际上未成立。它的成立,是两人较量的结果。北平行营的设置虽然在对中共军事进攻下有一定的必要,但是设置起来之后变成两人角逐全局相互较量的工具,丧失了本来的职能。两人的矛盾和对全局的角逐,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崩溃。
注释:
①早在1938年12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军委会委员长行营组织大纲》,规定设置桂林行营和汉中行营。关于李宗仁何时上任汉中行营主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李宗仁自己所说的1943年9月,二是其心腹程思远和张寿龄所说的1945年1月或2月(参见程思远的《李宗仁五战区来去——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张寿龄的《抗战期间我在老河口的五年》,载《老河口文史资料》第22辑,老河口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4月编辑出版,第3、35页)。根据《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753号中所载任命,应为1945年2月。
②行营旧指统帅出征时办公的营帐或房屋,也指专设的机构;行辕同行营。但是蒋介石统治史上的行营指机构,其典型代表是1932年1月至1935年2月的南昌行营。行辕并不完全同行营,一般指蒋介石的临时办公地点,但也指机构。行辕称机构始于1935年1月设立的宜昌行辕,其原因在于以参谋长代行职权的陈诚,为有别于同他有矛盾的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而改称行辕。因此,行辕的改称本来是矛盾的反映,在字面上无丝毫意义。抗战中后期,行营是军事委员会之下、战区之上的区域性军政机构,一般下辖几个战区。行营全称,随着蒋介石的职务变化而变化,1932年前全称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1932年至1946年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1946年9月为国民政府主席××行辕。
③最初,汉中行营与桂林行营一样,是“军事委员会为顾虑尔后作战训练及交通通讯、补充经理之便利”而设置的。汉中行营“主管第一、第二战区业务”,具体为:作战部分,“本军事委员会既定方针与指示,主持各管辖战区之作战,并与本会各部联系”;军政部分,“办理各该管辖战区部队之整理、补充、经理、卫生诸事项”;军训部分,“办理各该管辖战区内部队之教育、检阅、点验诸事项”;政训部分,“办理各该管辖战区内军队、民众之政治训练及宣传诸事项”;后方勤务部分,“办理各该管辖战区内之交通、通信、补给诸事项”;军法部分,“办理各该管辖战区内与军法有关诸事项。”在组织上,设行营主任、参谋长、副参谋长各1人,“行营主任、参谋长以下设总务处、参谋处、军务处、军训处、政训处、军法处,并指挥后方勤务部办事处分担业务。以上各处除总务处外,概由军委会各主管部派必要人员组织之。各部设有办事处者,即以该处人员兼任之。”(参见《军委会委员长行营组织大纲》(1938年12月4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3页)。
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组织的基本情况为:除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参谋长外,设秘书室、侍从室、顾问室、机要室、调查室5室;参谋处、交通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务处、卫生处、军法处、军械处8处;另外还有一些下属机构,如兵站总监部、战区政治部等。参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编制及人事简表(1938年1月-1945年2月)》,载《老河口文史资料》第22辑,第36-39页。
标签:李宗仁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抗日战争第三战区论文; 蒋介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战区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