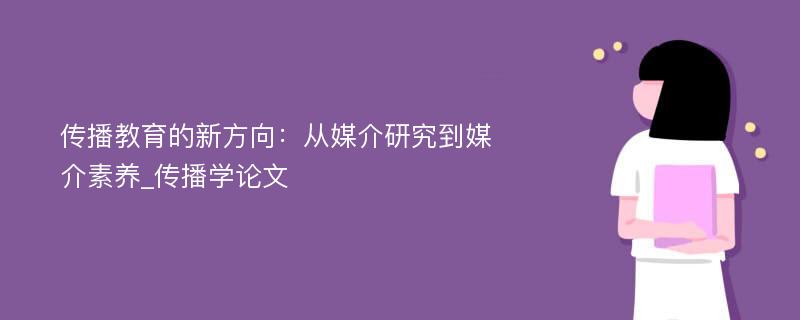
传播学教育新方向:从媒介研究到媒介素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传播学论文,素养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大众传播在世界范围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信息社会迎面而来:WTO、跨国传媒集团、IT、新媒体、媒介全球化等等,带来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大众传播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不仅承担着监测环境、传递信息、反映社会、提供娱乐等社会功能,也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塑造着公共生活的共同体。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的稳定、前进,对于民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和谐与进步,都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大众传播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关于大众传播社会效果的研究始于美国。早在1929-1932年间,美国学者就在佩恩基金会的资助下,展开了一系列关于电影对儿童影响的研究。参与研究的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使用了大量的问卷调查、内容分析等实证方法,得出了大众传播的“效果不一”的结论。早期的方法对后来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到底媒介对人们(包括青少年)的生活、对社会发生了哪些影响,产生了什么效果,对这方面问题的不断追问和研究、积累和验证,终于使得这个研究领域发展成了一门学科——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在美国的新闻教育体制中不仅博得了一席之地,并且成为“在过去90年来,美国大学里最广泛受欢迎的新领域”。(注: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70页.)从而走上了职业化和专业化教育发展的道路。
在2000年新出版的《大众传播学理论》第二版中,作者巴伦(Stanley J·Baran)和戴维斯(Dennis K·Davis)指出,媒介素养运动及相关讨论已经成为大众传播理论的最新动向。(注:Stanley J·Baran,Dennis K·Davis,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oundations,ferment and future2000 Wadsworth.p358.)在最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中,一些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动向,但与媒介素养运动在信息社会的重要性相比,关心的人还是太少了。本文将在这些学者讨论的基础之上,从传播学学科建设的角度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和思考。
媒介素养:概念的提出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电影为首的大众传媒所导致的流行文化给传统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冲击。英国学者FR·利维斯(FR·Leavis)和D·汤普森(Denys Thompson)以文学批评家的敏锐,观察到了这个深刻的社会现象,在1933年发表了《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作者首次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并提出了系统的教学建议。(注:宋小卫:《学会解读大众传播——国外媒介素养教育概述》,《当代传播》,2000年第2期、第3期.)当时他们提出的“文化素养”的概念,目的是为了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反对大众传媒中的流行文化。
“素养”一词在我国古已有之,“媒介素养”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也有学者译为媒介认知能力),“Literacy”的英文本义为“识字”、“有文化”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而media literacy,被引申为具有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一种能力,即素养,如具备识字、阅读和写作能力一样,也属于一种认知、认识和批判能力的启蒙。这个概念的发展也经历了历史的与逻辑的相一致的过程。
伴随着媒介技术的突破和人们认识的拓展,媒介素养的名称也不断变化,比如屏幕教育、图像素养、电视素养、视觉传播、媒介批评等。进入信息时代以后,随着计算机及其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计算机素养、信息素养和网络素养等相继提出。媒介素养的概念经过演变,发展成一种多含义、多角度和多层面的概念。据学者鲁宾的分析,主要有三个层面(注:Stanley J·Baran,Dennis K·Davis,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oundations,ferment and future2000 Wadsworth,p358.),我们也可以认为是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即“能力模式”、“知识模式”和“理解模式”。1992年12月,有志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美国学者召开了一次媒介素养的全国领导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经过激烈的辩论,学者们对媒介素养的概念达成了共识,认为,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公民所应该具有的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形式信息的能力”。(注:Art Siverblatt Media Literacy1995 Praeger,p2.)这个定义侧重对信息的认知过程,这就是媒介素养“能力模式”。来自媒介学者P·马萨瑞斯的定义,也就是“知识模式”的观点,认为媒介素养就是“关于媒介如何对社会产生功能的知识体系”(注:Stanley J·Baran,Dennis K·Davis,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oundations,ferment and future2000 Wadsworth,p35.),这个定义侧重信息是如何传播的。而来自大众传播研究者J·刘易斯“理解模式”的观点,则认为媒介素养就是“理解媒介信息在制造、生产和传递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技术的诸力量的强制作用”(注:ibid,p358.),在这个模式中侧重对信息的判断力和理解力的强调。
在纷纷争论中,学者W·克瑞斯特和W·J·波特进行了总结,认为,几乎所有关于“媒介素养”的概念都包含有以下的元素:媒介是被建构的,它也在建构真实;媒介有商业的利益和追求;媒介有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诉求;由于内容和形式各异,不同的媒介有各自不同的审美特质、符码和传统;受众获得媒介的意识是通过协商而来。(注:W ·James Potter,Media literacy 1998 Sage,p7-8.)
媒介素养:运动的发展
随着大众媒介不断地深入人们的生活世界,也随着人们对媒介素养意识的不断加强,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大众传媒就象社会的神经一样延伸到越来越多的地方,从英国到欧洲、大洋洲、美洲以及亚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感觉到了发展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注:宋小卫:《学会解读大众传播——国外媒介素养教育概述》,《当代传播》,2000年第2期、第3期.)这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方兴未艾,大体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普及化和规模化
20世纪70至80年代,许多国家和地区在青少年中普及了媒介素养教育。在一些大众传媒发达国家,学术的媒介教育开始形成规模。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芬兰、挪威、瑞典、瑞士等国已将媒介教育正式纳入正规的教育课程,对中小学生进行普及教育。进入90年代,日本、印度、韩国等亚洲国家也开始结合自己的国情普及媒介素养教育。韩国的信息教育就颇具特色,在韩国《中小学信息通讯技术教育课程开发指南》(注:刘微:《韩国:信息素养创造性地应用在生活中》,《中国教育报》,2002年12月12日第3版.)中写到:应用信息技术处理资料和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创造新知识和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已经成为与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也是基本的条件。这种能力必须通过学校教育去培育。重要的不是单纯地培养学生操作信息技术的能力,而是培养能够在各种情况下利用信息技术去解决相应问题的能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2003年1月,我国台湾地区颁布了公民媒介素养白皮书。(注:http://www.mediaresearch.cn/2003/1/6.)
第二、无统一建制,模式多样化
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对学校实施媒介素养教育作了规定,要求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或在有关学科中增加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据介绍,媒介素养的教育形式并不统一,比较多样化。主要有四种模式:1.媒介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科目;2.媒介研究作为某一科目中的一种组成部分;3.把媒介教育融于所有的科目中;4.媒介研究作为一门整合的、跨学科的课程。这种设置一般都与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有关。(注:蔡骐:《论媒介认知能力的建构与发展》,《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5期.)比如德国,由于历史上有被独裁者控制了媒体的教训,有关媒介素养的知识是在政治、社会常识和社会研究等课程中讲授,并且是师范院校、成人教育机构、宗教团体和社区工作者的经常性的讲演和宣传内容。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帮助学生树立公民意识,引导学生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社会的决策过程。
第三、社会化、全球化、网络化的趋势
非政府组织和非赢利组织的加盟,是媒介素养运动的又一个显著的特点。近年来经常开展的媒介素养活动,不仅包括不同的学科和机构,还包括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者、教育者、家长以及媒介专业人员。比如,“国际教育媒介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Media)就是积极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主要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其代表来自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丹麦、芬兰、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日本、科威特、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30多个国家。诸多国家一起合作从事媒体教育的研究与推广,并发展媒体教育资源,培养具有思辨力的公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大力倡导者和积极支持者。在它的推动下,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纷纷投入了媒介素养教育运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贯认为,在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的消极影响不可避免。大众传播,有可能发展成为操纵公众舆论的重要工具。因此,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不仅是教会青年人如何应对各种大众媒介,而且要鼓励学生为建立具有真正民主精神的高质量的大众传播体制而努力。1980年、1982年、1984年和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依次出版了《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将大众媒介用于公共教育国际研讨会的最后报告》、《媒介教育》、《了解媒介:媒介教育与传播研究》等多种决议、宣言和读物。为媒介素养运动在全球范围的展开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国际互联网上,只要搜索media literacy,就可以搜到1,040,000项查询结果(相信会越来越多),有许多公益性的网站和非常精彩的网页为全世界的人们提供媒介素养的共享资源。如《媒介素养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 CML)、《儿童与媒介节目》(Children and the Media Program)、《电子雪:我们时间里的电视》(Electric Snow:TV in Our Time)、《耶稣传播工程》(Jesuit Communication Project)、《媒介知晓网络》(Media Awareness Network)、《媒介和传播研究》(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Studies Site)、《网上的媒介教育资源》(Media Education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媒介的历史工程》(Media History Project)、《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媒介素养网上工程》(Media Literacy On-line Project)、《媒介看门狗》(Media Watchdog)等等。
媒介素养:我们的回应?
传播学从20世纪80年代引进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期间坎坷起伏,与大陆社会改革的命运休戚相关。1997年教育部把新闻传播学设立为一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一起并列为二级学科,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地位的正式确定。2000年教育部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成立,2002年中国新闻教育分会的中国传播学会的成立,都表明传播学在中国已经进入了相对的学术自立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的传播研究伴随着新时期新闻事业的改革步伐,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以青少年与媒介的研究为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80至90年代,主要受美国传播学的影响,以效果研究为主。有一些零散的关于电视对儿童影响的研究;第二阶段是90年代以后,得到了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其他项目的支持,在传播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成果:卜卫的《媒介与儿童的现代化》,陈崇山和孙五三的《媒介、人、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公民研究中心合作的关于媒介使用对儿童道德和人格的影响的课题等;第三个阶段,就是进入新千年,以卜卫的《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新华出版社,2002年)为标志,终于突破了传播学效果研究中“以媒介为中心”的限制,在研究的结论中提出了媒介教育的概念。
传播学的本土研究取得了丰盛的成果,与此同时,传播研究从外在形式的模式,深入到对概念和体系的讨论,既反映了本土化的宝贵探索,也体现了传播学从学术自立逐步走向学术自觉的过程。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名称的歧义:是传播学还是“传通学”、“交流学”,不同的译名反映了不同的语境和理解。
2.教育体例上的混淆:传播教育与新闻教育、媒介教育的混淆,体现了传播学定位的尴尬。
3.中心问题的游移:是“以媒介为中心”还是“以阅听人为中心”、“以社会为中心”,这反映了传播学研究立场的多样化。
4.教育定位的争执:是专业教育,还是素质教育?
这些问题,既反映了我们对于传播学认识的深入,也反映了传播学从专业的媒介研究到通识的媒介素养的一个必然的延伸趋势。目前中国的媒介教育基本上沿袭了美国的教育体制,注重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教育,媒介素养教育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在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除了新闻和传播学院里设置的专业教育课程之外,其他的院系几乎是一个空白。少量的选修课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素质教育和公民通识教育的需求。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大力建设信息化教育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意识到:
首先,传播学教育本身需要有从职业教育到素质教育立场的转向,从媒介研究到媒介素养,不仅是传播学教育的新方向,也是传播学学科发展从学术相对自立走向学术自觉的反映。如前所述,中国传播学的设立,与美国传播学当初的建立一样,与其说是为阅听人提供了更多的关于媒介的知识和认识方法,倒不如说为新闻学争取了更大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地位更加贴切。当然,这也并不是截然相对的,媒介研究也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题中之义。因此,为了避免“为知识而知识”的嫌疑,媒介教育急需媒介素养意识的建构,要从专业教育的局限中挣脱出来,或者确切一些说,要从新闻专业主义教育的起点走向素质教育的公共平台,成为青少年的通识教育。媒介素养教育本质上是信息素养的教育,对于信息化教育相应的硬件建设而言,媒介素养则是不可或缺的软件配置。
其次,媒介素养教育要突破新闻专业教育的局限进入通识教育和公共教育,这也是信息化社会对传播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可以说,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培养民主社会的公民。媒介素养不仅是传媒人的需要,也是阅听人的需要、社会公民的需要。通过口头的、印刷的和其他媒介文本的形式来传情达意,对于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的人来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素养。在一个高科技的社会,人们需要学会通过不断增加的、日益多样化的资源渠道来选择、理解和整理思想与信息。通过口头的、印刷的和其他媒介的文本学习,阅听人可以体验、了解和感知各种情境、人群与文化所透露的讯息,并从中认识自我、认识社会。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他的名著《理解媒介》中认为,媒介文化已经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的过程,将每一个人都裹挟其中。生活在媒介文化所制造的仪式和景观之中,我们必须要“学会生存”。在麦克卢汉看来,自动化使文理综合教育成为必须:“在教育中,课程分科的传统划分法,和文艺复兴之后各级学校中的学科分化一样,已经过时了……如果我们的课程设置继续沿袭目前肢解分割,互不关心的模式,他们培养出来的公民,必然无法理解自己生活其间的自动控制社会”。
最后,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注: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26页.)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形成了不同的媒介教育的范式。比如英国从文化素养的传统出发,形成了“超越保护主义”的模式;而美国大众传播的研究传统,基本上因袭了“使用与满足”的立场;而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则是从“抵抗文化帝国主义”的角度出发,是一种文化自觉模式,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需要营建相应的公共空间以及相应的公民基本素质。作为“后发”的国家,我们有着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因此,在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建构肯定有着与西方社会的不同。但相同的是,对每一位生活在当代的公民而言,尤其是青少年,接受“媒介启蒙”已经成为成长过程中的必要和必须。大众媒介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建构现实。身处“拟态”环境,我们的认知环境取决于媒介体制、传播者的意识形态、媒介对受众文化认同和需求的理解以及市场的需要等等。因此,对受众、阅听人而言,大众媒介意味着知识、信息、主流文化甚至是权力。在这种情形下,通过媒介教育来培养受众认识和利用大众媒介的能力和自觉理性,提升公民的判断力和思考力就尤其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在1994年1月1日的《新闻出版报》上,署名夏商周的作者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国的“媒介扫盲”尚未起步》。十年过去了,我们应该更加认真地反思这个问题,追问目前的状况,媒介扫盲已经起步了吗?媒介教育已经走到了哪个阶段,将有哪些发展和作为呢?从目前我国传播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扬帆既起,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