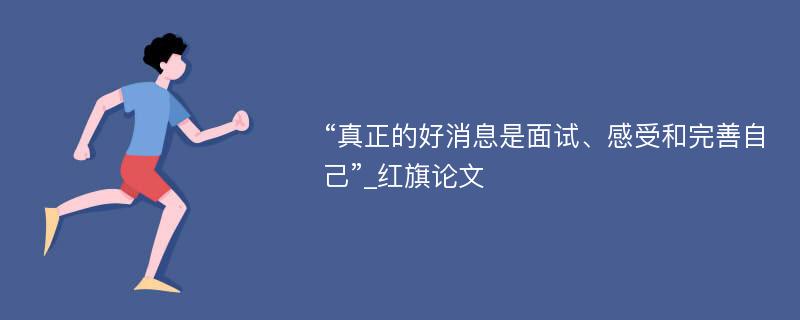
“真正好新闻是自己采访、感受、提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采访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段存章,男,山西左权人,1938年12月出生,《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他自学成才,从农民通讯员做起,从事新闻事业40余年,最后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20世纪60—70年代,曾在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大寨任常驻记者10余年,发表了很多著名的大寨作品。对这段历史,段老有深刻的体会。 本栏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新闻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成果,项目批准号:15ZDB140。采访小组成员:白博、黄欢、马梅若。指导教师:王润泽。 我为何去了大寨呢? 因为一搞“文化大革命”,我当时在(山西)电台,还是想去基层。想去看看我这两年努力后写作水平到底怎么样了,没有去试过——其实当时两派造反,我还是一派的头头,有了一定的审稿权,我可以签字,可以组织他们采访。我有权了,领导对我也不错,但是我不满足于这个。我总想去记者站当记者。当时大寨轰轰烈烈,记者去了很多,我们《山西日报》、山西电台都派了记者轮流去,有的人都去了好几回。我刚去大寨当记者的时候还很危险,很多人不愿意去,我就说我去,我想去基层锻炼锻炼。 1964年是我第一次去大寨,给河北广播电台写了一篇稿,当时在那儿住了7天。真正去(长时间待在那儿)是1967年冬天,我在大寨成了《人民日报》的一个写稿人了,虽然当时编制不属于报社。 一、真正好新闻是自己采访、感受、提炼 几件事。一个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这是必须得有大寨的。当时我驻扎在那儿的时候,只要一有毛主席最新指示,《人民日报》的编辑——我也不认识,就给我打电话,要我给他写反映,我就赶紧给他写。写了之后给陈永贵念念,给郭凤英念念,他们同意了就发。 现在我感觉写给《人民日报》的文章里,1968年有一篇东西对我影响深远。这个东西不是指令性的,不是谁让你写的,是因为我在那里、住到大寨里来,通过劳动和大寨人民熟了,我看到陈永贵当了省“革委”副主任以后,他还是回去劳动,跟群众在一块儿,端上大碗在山上吃饭。而且给他派的警卫员他也不要、退了。根据这些事儿,我感觉我想写一篇东西。谁也没让写,县里、省电台、《人民日报》都没让我写。我就写了《不是要当官 就是要革命》,记陈永贵当了省“革委”副主任以后的生活作风变化。这篇东西写了他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不脱离艰苦奋斗生活的几不“脱离”。有这个主题和这些内容以后就开始写稿子。这时候大寨接待站只有那个小平房,记者都是七八个人挤在一个通铺上,晚上根本不能写稿。我就借了邮电局一个办公室写这篇稿。我从吃过晚饭写,写着写着听到外面摇铃响了,一抬头,天亮了。一黑夜写了1万多字。这篇通讯写了以后就找人打印,投给了《人民日报》,还投给《山西日报》。 过了有半个月,《人民日报》打电话说你这个稿子收到了,内容还是不错的,就要我过来修改。那时候我还没有去过《人民日报》,就坐上火车到了王府井,和几个编辑看稿子,老师们就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改了以后排出来大样看了看,人家说你回吧,赶我们看情况、啥时候用再通知你。结果一等几个月没有用,可能“气候”不到。咱们不知道上面什么“气候”。又过了几个月,快开“九大”了,又给我打电话说你还得来修改。我就又来了,人家又提了些建议,改动不大。改了以后很快在《人民日报》二版以很大的篇幅刊登了。发了以后上海《文汇报》发了两篇社论《陈永贵当官不像官》,第二篇叫《不要警卫员》。这就轰动了。 咱们不知道文章是要配合“九大”的,陈永贵当了“九大”代表了,甚至于地位起了变化。“九大”毛主席接见了几个人,说王维湘很年轻嘛,说纪登奎你是我的朋友(“文革”时期他在河南),接见陈永贵说你还是老样子。 真正的好报道还是要自己采访、提炼,才能发现好新闻,不能靠指令,真正好新闻是自己采访、感受、提炼。 80年代初,安岗带着我去上海采访,他到了上海以后,我们就深入广场、车间去采访,《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老总去看他,提出来到上海之后是不是见见市长和市委书记,安岗说不要,这次的采访任务跟两位没有关系,因此可以不见。如果现在的话,安岗要去采访起码会有宣传部部长去陪同,安岗那个时候就认为我是记者就是记者,我是总编辑但是我去采访也是记者,我认为这种风气现在很少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的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我们到上海当时就是一个一个去调查怎样扩大生产,调查完之后就赶快写,赶回北京发表,这种作风值得我们去学习。作为记者还是要去实际采访,你用电脑再多,把所有的资料都放上也没有效果,跟采访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就像现在去采访新闻发布会一样,你去之后别人把材料编得很好,打印得很好,根本都不需要采访,我不喜欢这样。我亲自看了、了解了,这样我写着也心安理得,至少是我自己调查了的。 二、“你调查研究了,事实上没有问题” 大寨的报道很多,刚才也说了一篇。那么多报道,现在回头看——我曾写了一本叫《我在大寨十三年》,基本上把我在大寨十三年总结、思考的东西都写了——从报道上来讲,我不是一贯正确的,有不对的,也有半对半错的,也有现在回头看还能站住脚的。回头想,那个时候讲“阶级斗争为纲”,你不能离开这个,如果离开这个,你就上不了稿。那个时候还有《红旗》、两报一刊。那个时候我写了一些报道,给《红旗》看了说行不行,他就说你还得修改,你别着急,你坐车回来,肯定是《红旗》杂志新一期出来了,你这里面没有《红旗》杂志的新提法。你必须找一本《红旗》杂志,看看有什么新提法,你就加上去。加在前面或者后面,总结一下,这就行了。它不需要有多少事实,它需要你最新的观点。这就是“阶级斗争为纲”。 比如说我现在再回头看,大寨上写的东西,因为你调查研究了,事实上没有问题。但是也有一些,比如“批林批孔”,让你写你就写。将来我要把我所有的文章印成一个小册子,你就看出来了,那个年代,阶级斗争我也搞,处处不离“大批判”,现在回头看,基本上就是(错误的)……但如果没有阶级斗争为纲,这些文章就出不来。这些文章有的是指定的。比如说“批右倾翻案风”,这是编辑部让你这样写的,找一个典型来写“文化大革命”的好、“文化大革命”学大寨变化大的。我就写了两个,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很醒目的位置。现在回头看,这样就错了。那时候是指令,你必须完成。毛主席各项指示,指定你上山下乡你就得写,毛主席说反潮流那你就得写反潮流。比如说路线斗争,现在你回头看,到底路线斗争有没有用。这种东西,就是你不应该写的。但是不写,像张志新,当时就不写,但是这种人极少。老百姓很少有这样的觉悟。那天我突然想起来一句话,国际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现在不要做奴隶,起来不要做奴性的人们。这种奴性少一点,可能即使上面有问题,老百姓有了觉悟以后,民主、科学可以自然避免一些东西。 从我自己的思想来说——其他记者我不知道——上面说要批刘少奇我没有怀疑过,没有怀疑过批的不对。批邓那时候也是紧跟,并没有感觉到批人家是不对的。如果我意识到我可能不写,但是不写就不能吃这碗饭了,就不能当《人民日报》记者了。让你批,当时我觉得并不是完全违心。咱们不能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盲从,当时就是盲目。 比如说当时“文化革命”,在电台我也批过我的老领导。我写过文章反思,当时开会也批斗过。那时候闹浮夸风的时候,《人民日报》编辑记者有没有有看法的咱不能排除,但多数人都还是跟。包括李克林①老太太最敢说真话,学大寨报道是她一手搞的。全国学大寨运动,《人民日报》报道她是负责人。包括我在大寨写的题目都是她给出的。我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都是她给策划的,包括《大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全国农业学大寨》等很多报道。 农村基本建设会、全国农业饥荒会等也都参加了,我感觉在会上也是体现中央精神的。比如说,李克林就让我写了一篇杂文,短评《窝头加镢头,高山能低头》,讲大寨治理河山的,就是说只要有窝窝头和镢头,就能治理河山,也用了抗战我们能打败日本人时候运用的“小米加步枪”这种精神。那个时候中央还提倡搞农村基本建设,我也写过两篇社论,现在回头看农村基本建设没有错,但是后来搞的形式多了,也伤害了一些老百姓,这才有问题。但是农业基本建设方向没有问题。现在也搞抵御洪灾、抵御旱灾,这是没有问题的。我在大寨写了一篇文章叫《泼脏水,不要把孩子倒掉》。我们往往是这样,给孩子洗澡是对的,但往往连孩子也给扔了。应该是给孩子洗澡,把孩子洗干净,把脏水倒掉,把孩子保护起来,但是现在很多时候都把孩子给扔了。 (问:那大寨这个典型您如何看?) 我认为,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眼光去看待当时的农业学大寨专题新闻报道。当时,全国的形势可谓是工业缺油、农业缺粮的局面。在这样的大背景环境下,毛主席喜欢用树立典型的方法来做宣传,昔阳县的大寨村是当时全国各地抓典型中比较平凡的一例,《人民日报》都有报道过。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也已经向毛主席汇报过山西省的农业典型生产方式,就是昔阳县的大寨村,毛主席特意了解了陈水贵的情况后,说要找来一些近期的报纸,看看报纸上是怎么报道大寨村的。随后,毛主席在几次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讲到农业靠大寨的说法,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上首次讲到农业要学大寨。客观上讲,大寨村的农民确实是靠自身勤奋努力和艰苦奋斗而解决温饱问题,50年代土地改革以来,昔阳县大寨村农田可用地很少,大多数的土地是山地,土壤条件也不佳。陈永贵带领全村上下搞农村合作社,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群众实现基本的温饱。陈永贵真正开始出名是源于1963年的一次大洪灾,洪灾过后,大寨村修筑的水利工事起到了较好的防护作用,粮食减产量较少。经过前期动员,1964年,大寨经验开始辉煌起来。其间,陈永贵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毛主席也专门接见了陈永贵。1952年至1962年,是大寨群众艰苦奋斗、建设大寨的十年;1963年,大寨村提出农业发展“三要三不要”,陈永贵本人也提出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这些都展示出大寨群众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寨成为农业生产的典型被树立和推崇。1964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一共有7篇,都将大寨的农业生产典型升华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政治意味很浓重。当时的新闻报道也被这样的大环境引导,于是大寨本身的农业生产典型就被广泛地宣传引导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本来单纯的大寨农业生产问题,被加入农民公社运动、取消自留地等因素,后来,我才发现农业学大寨运动确实有负面的因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粮食奇缺的情形下,农民群众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开垦出很多地,解决了自身吃饭问题,这在当时来说,是不可磨灭的功劳,老百姓不会忘记的。但是,大寨模式在中国并不是可以完全复制,内蒙古、新疆、广西等偏远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绝不可能像大寨模式一样去复制。 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大规模的拨乱反正运动开展起来了,关于大寨新闻报道的政治意味也渐渐地消失了,新闻报道重新回到了农业生产的典型。现在关于农村新闻报道就比较客观,针对全国各地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各有不同的新闻报道方向,例如华西村和吴仁宝、南街村和史来贺等。在多元化的社会形态下,就是要有多元化的新闻报道“样板戏”,要造就多种不同的样板。我们一定要用平常心来看待大寨现象。 70年代树立典型的方法是把这个典型写得很完,很英雄,老百姓没办法学习。比如写献血,我就不同意无限制的献血,这也是一个生命,你无限制献血能行吗?再写家里电视机,几台都捐走了,最后一台电视机小孩想看也捐走了,我觉得这么写不好。人是有人性人情的,你不能树立一个典型出来一看还是我们五六十年代树立的典型。过去我们就是一讲党性,就不说人性了,不讲人情了。所以我们报道里面还是要以情动人,以事实这种感人的东西。 三、“要站在人民立场上,和人民同呼吸” 这个事儿(指成功树立陈永贵“不要当官、要革命”典型)现在回头看,有我个人的特殊性,也不代表别人。但是我觉得有个很动人的东西就是,1964年提出农业学大寨以后,参观的人就多了,一天几万人,记者成群结队去,出版社都去了,它客观上也有困难。它要不限制就搞乱了,都叫去就不可能了。记者大部分住在接待站,不允许你进村的,更不允许你参与劳动的。我一个年轻人去了更不行,住在那里过了40天,每天就是看看材料,跟这些人聊聊天,进不去的。每天中午,只能是中午,成群结队的人,包括西藏来的人、参观的,拿着毛主席语录,喊着陈永贵口号,两边站得满满都是人,都是按照布置走过去看一下,只能让你见一下面。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继续住下去吧进不让进,走了吧又觉得心不甘。动脑筋,我就想怎么办。 有一天我想到:大寨后面挨着山,可以有进村的路。我就摸着石头找了一条小路,看见贾敬才在前头,跟他慢慢进了工地。我也没跟他说话,就帮助那儿的人搬个石头啊,铲铲土啊,做了一阵也没有人赶我,嫌我烦。后来贾敬才休息的时候就坐在一块石头边抽烟。我就跟过去坐下,老贾这个人是很随和的,他说,哎,你是哪儿的人?我说左权的。那个村子的?多大?我说了一下。你来了多久?一个多月了。那我怎么没有见你?想劳动不能劳动。 这后来他们就不赶我了,可能感觉我劳动还可以。后来我就每天抽半天时间在里面劳动。这样一劳动就认识人了,不光贾敬才,和其他人也熟了。以后我就慢慢扩大劳动场地,修堤什么的都有了。实际上我就用我的努力进去了。后来慢慢熟悉到我能去散场会,谁家里也能去了。陈永贵叫我小段,其他人叫我老段了。我发现其实大寨人都是很亲热的,你劳动,有时候在地头给他多帮忙就行了。 这样,其实我不用采访,在劳动过程中就了解了,比如《陈永贵当官不像官》,这就是在劳动中体会出来的,不用专门和人们交谈。别的记者没有我这种特殊情况,在那里还有记者来采访我呢。有些人想写陈永贵,就千方百计找我讲陈永贵怎么样怎么样,我成了被采访者。 那时候我没有名,也没有利。我是广播电台记者,人家《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都在),(省)广播电台记者不算什么;再一个,你年轻,你还不到30岁,没有什么自己的包袱,那时候也不署名,都是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吃饭买上饭票自己去买饭,没有什么特殊待遇。因为你对写作有兴趣,那么你写给《人民日报》见了报,你当然高兴。(1968年)不算给电台、《山西日报》的东西,光给《人民日报》我就写了11篇东西,都在一版、二版占比较大的篇幅,我就比较高兴。《人民日报》有很多资历老的大记者、大编辑,没想到得到人家的认可。 感觉到《人民日报》的稿子还是和省里面的不一样。在省报很厉害的记者,没有一两年,适应不了《人民日报》。没有一两年,还是省里面的眼光。按照《人民日报》的老编辑说,你处理稿子、判断事物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从这时开始,虽然不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也慢慢开始给《人民日报》写东西了。 到了《人民日报》之后,我一采访就感觉到,逐步地,你的思想、发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我写过一本书叫《一路师》,我们常说一字师,我写的是一路师,就是人生的路上都会遇到老师。当记者的好处就是一路走一边采访各行各业的人,在全国范围内跟在全省范围内又不一样。像现在国际新闻记者全世界跑,那眼光又不一样。这个东西就有个适应过程。我就感觉人除了读书以外还有个无字书,就是和社会适应的过程。跟大量的社会人接触,在某种程度上比书上的东西还要可贵。因为书是人写的,写书的人还有假有真的,有时候你还会上当,但是生活不会这样,很真。所以说,当记者,我想你们都看过凤凰台,凤凰台有些记者是很厉害的,闾丘露薇在打仗时就在战场上;杨锦麟,采访各个类的专家;曾子墨也是,做各种群体采访。记者要有这种强烈的东西。 我觉得新闻记者有担当、有责任。要不你说《人民日报》记者有什么?起码你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和人民同呼吸。即使不说同呼吸,起码你得挨近人民。现在提倡走基层,我觉得这种提法应该是“记者在基层”。 四、“新闻记者就更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保持独立思考” 当然,我这人有个特点,你赞扬我的时候,我看的不是很重,但是如果有人看不起或者另眼看待我,我就很在乎,不过我能忍。记得最难的时候,有一年我表现得很好,别的人生怕我的工作水平和能力追上他们,就产生了嫉妒心态,甚至有些人还向组织打我的小报告。(开会的时候)所有的出版单位和媒体单位(都到了,却)没有通知来自《人民日报》的我,很多人都疑问,怎么没有《人民日报》的段存章。于是,我的压力就很大了,思前想后,反复斟酌,最后决定不能走,我是《人民日报》派来当记者的,所以我要继续留下来。后来,事情平息以后,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在逆境中要学会忍,学会低头、学会弯腰,等风平浪静以后,我们照样可以昂首挺胸地走下去。生活并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生活本就包含着顺境和逆境两种状态。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普通人,在顺境中成长的人容易取得成就,这不算什么;而在逆境中,只有会低头、会忍让的人方能摆正心态,走出逆境。作为新闻记者,更要学会在逆境中保持冷静的独立思考,否则,很容易陷入逆境、走弯路。 如果大的政策环境“风向”不对,新闻记者就更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保持独立思考,在大“风向”中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毛主席曾经说过,当一个情形来的时候,要时刻注意另一种情形。这就告诉我们,要用全面的观点(看)事物。当全国上下都说中国富裕的情况下,请一定要保持冷静,要注意到我们还有很多地方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新闻记者更是这样,当其他从业者都提出来一种观点,都看到这个层面的时候,你再去重复提出,那你的文章不仅毫无新意,也不会引人注意。在大环境下,新闻记者有独立思考的内容,并能够用文字反映出来,那才是真正的本事。在当时的新闻体制环境下,我力所能及地坚持用自己独立思考的内容写文章。 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新闻标题拟定,我自己写的关于大寨的文章题目,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绞尽脑汁独立思考得出来的,能够做到相对不随波逐流。在按照要求完成写作任务后,更多的时候,我会将自己思考的内容和思想表达出来。比如,我参加过十多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道活动,其中,会有中央领导人到各代表团参加审议、讨论的环节,我是不太喜欢这些环节的。但是,作为新闻记者,我必须得去参加这些环节的新闻报道活动。记得有一次,江泽民同志到黑龙江代表团参加审议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他谈到国有企业工人下岗的问题,很多人大代表都将“苦水”和盘托出,讲了很多下岗工人的难处。我作为参会的新闻记者,一方面,要完成新闻报道任务,将领导人的讲话报道出来;另一方面,我也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人大代表在分组讨论环节是为民代言、为民请命的,我应该适当地将人大代表的话语表达出来,让读者看得到。于是,在会议结束后,我马不停蹄地将当时会议的新闻报道写了出来,还特地用了1000字专门写了人大代表讲到的关于国有企业改制下岗工人的苦声。我将写好的新闻稿件转给省委书记阅示,他没有意见,说写得好,晚上9点钟,我将稿件拿到《人民日报》编辑部。但是,第二天,报纸刊印以后,我才发现,报纸刊登的是黑龙江省委早就准备好的,预先起草过的讲话稿。经历了那件事情以后,我对这种不能反映新闻事实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人大代表会议的新闻报道不应该是全篇累牍的空话、大话,而没有人大代表的声音。 当然了,现在的国内新闻报道比较进步了,历史总是向着好的一面发展,变化的过程是渐进的,但终究是往正确的方向去的。当今社会媒体十分发达,现在的新闻比我们当时做的新闻好。比如凤凰卫视,我每天早上7点钟都会关注凤凰台,电视台播出的台湾局势,节目中关于马英九、王金平、陈水扁等政治人物分析的都比较客观,为观众提供了大量的新闻事实,开阔了观众的视野,新闻评论员的解剖思维也很广泛。这些是我对新闻真实性的观点与看法。 关于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报道问题。在80年代的时候,《人民日报》农村报道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各地驻站记者要与所在省委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走得太近,要尽量保持人民日报社独立的观察视角,对人民日报社负责任。现在来看,很多驻站记者与当地省委关系太过于亲密,贴得太近,容易导致缺乏独立视角,这样的新闻报道多数是为省委唱台,歌功颂德,毫无任何批判精神,这也是不正常的新闻报道。驻站新闻媒体一定不能沦为当地省委、省政府的机构,完全跟着步调走,那就架空了驻站记者,失去了新闻监督的意义,我认为这是很不合理的。人民群众现在很少看《人民日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驻站记者关注基层、关注百姓、关注生活太少,报纸上充斥着一些也算真实的硬新闻、空新闻,百姓最想了解的基层信息太少。驻站记者不能只会当“喜鹊”,每天喳喳地叫,全是喜事也会令人反感,给人一种粉饰太平的感觉。我认为,驻站记者既要当“喜鹊”,又要当“啄木鸟”,也要适当地去“抓虫”,敢于揭露黑暗。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广东去采访,因为坐船太久,身体不适,我改乘汽车到广东,没有写出长篇通讯式的文章,只是捡要害写一封记者来信给报社,结果反映很好。当时,我和广东省委的一名宣传干事一起由湖南下广东,经过韶关地区,在行进的过程中,我发现韶关地区的路竟然这么难走,山路崎岖,没有一条像样的平整大路。我当时就决定写一篇文章来反映韶关行路难的问题,身边的宣传干事还劝我不要关注这些小事情,要与省委宣传步调保持一致。我告诉他说,我采写我眼见的新闻事实,出任何事情,我担责任。于是,我就撰写了一封记者来信给人民日报社,标题是《广东北大门行路难》,详细描述了道路基础设施的落后。后来,广东韶关市的一位宣传部长来北京开会期间见到我,他高兴地说到,那篇文章刊登以后,省领导很重视,专门拨款几百万元用于广东省“北大门”道路的疏通。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改革开放之前都归中央书记处直接管辖,中央领导人很重视。现在人民日报社做出很多改革,直接归中宣部管辖。人民日报社以往还有一个特殊部门,那就是群工部,专门用于接收人民群众和基层记者的来信,这些都是反映群众呼声的渠道,现在被撤销了,这一点很不好。我个人觉得,现在《人民日报》上很多新闻评论的量虽然很多,大多数是抄过来抄过去的“炒剩饭”,缺乏独立的新意,缺乏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评论内容。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空谈误国,我认为,新闻媒体也要少一些空谈,多一些贴近群众的报道。其实,真正评判稿件质量的标准是且只有读者。以往人民日报社有很多的读者反馈,从这些反馈的内容中,就可以轻松地找出什么是好稿件。所以,我认为一切新闻改革都要以尊重新闻报道规律为原则,这样才能做好新闻。 ①李克林(1916-2003),曾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是参加了《人民日报》创建的为数不多的女编辑(记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