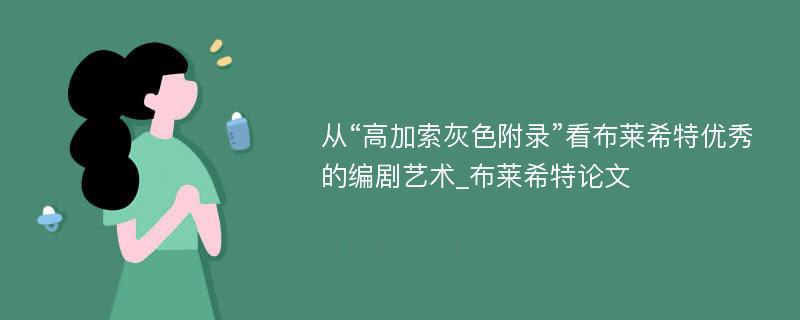
翻空出奇,混纺出新——从《高加索灰阑记》看布莱希特卓越的编剧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加索论文,编剧论文,布莱论文,艺术论文,翻空出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布莱希特一度被人指责为抄袭者①。的确,他的戏剧作品,有不少是根据他人作品创作出来的。比如,他的《高加索灰阑记》就是根据我国元代杂剧家李行道的《灰阑记》创作的;《三分钱的歌剧》就是根据英国剧作家约翰·盖伊的《乞丐歌剧》改编的;《潘第拉和他的仆人马狄》就是根据芬兰女作家赫拉·沃里约基的小说和剧本改编的;《唐·璜》就是根据莫里哀的同名剧本改编的……。然而,改编是否一定就是抄袭或剽窃呢?如果说布莱希特这类创作是剽窃、抄袭,那么,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算不算剽窃?歌德的《浮士德》算不算剽窃?我不想为布莱希特辩护。我所要说的是,布莱希特利用现成的材料(作品)进行创作的这种艺术独创性——这种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吸收和消化繁复多样、表面看来毫不协调的各种成份的不可思议的才能”②,恰恰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本文拟将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和李行道《灰阑记》作一番比较,从而阐述布莱希特的翻空出奇、推陈出新的编剧技巧。
众所周知,布莱希特所创立的以“间离效果”为核心的表演体系,曾经受到中国传统戏曲的启发——其实布莱希特不仅仅对中国的戏剧,对中国的整个精神文化,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中国文化使他感到亲切。他甚至有点崇拜。可以说,哲学家老子、庄子,诗人杜甫、白居易对他的创作产生的影响一点也不弱于但丁、莎士比亚、斯威夫特、伏尔泰等西方作家对他的影响。“中国人的那种温柔敦厚,中国古代先贤的那种不拘泥教条的大家风范(undogmitic authority),对布莱希特来说,代表着一种作为人类关系基础的、根本的社会主义友爱理想。”③所以,埃瑞克·本特雷说:“从政治观念上看,布莱希特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透过这种社会主义者的表层,我们却可以称他为一个儒家(confucian)。”④布莱希特对中国几百年前的一部杂剧产生兴趣,并使之以新的面目重现于欧洲戏剧舞台,除了布氏本人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感情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古代戏剧在柏林戏剧舞台上的成功表演。中国戏剧进入欧洲的时间,可上溯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巴黎耶苏会教士杜赫德(Du Halde)在《中国通志》上发表法文版《赵氏孤儿》为标志。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元代戏曲中,已有三十多种被译为欧洲各种文字了。⑤李行道的《灰阑记》,一八三四年由英国裘利安(Julian)译为英文;一八七六年由德国人Wollheimda Fonseca译为德文;一九二四年德国作家Johannesvon Guenther和克拉帮(Klabund)分别出版了《灰阑记》的改写本。克拉帮是布莱希特的好友。布莱希特曾于一九二五年在柏林观看过克拉帮《灰阑记》的演出。克拉帮的《灰阑记》虽然对李行道的原作作了一些改动,如对故事发生的地点、时代、人物关系、灰阑的象征意义等都作了一些修改,但从总体上说,原有的故事格局基本上没变。然而,克氏的《灰阑记》的演出获得了成功。克拉帮的成功大大鼓舞并且启发了活跃在柏林戏剧舞台上的布莱希特。他想根据这部中国戏剧写一部新的作品。一九四○年,布莱希特根据《灰阑记》的故事创作了短篇《奥古斯堡灰阑记》。五年后,他完成了构思多年的《高加索灰阑记》。
布莱希特在《高加索灰阑记》的楔子中,通过歌手阿尔卡第之口告诉我们他们将要表演“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它叫《灰阑记》,从中国来的。”可是,过了一会,他又说“这本来是两个故事。”显然,布莱希特想要告诉我们,在他的这部戏中,除了《灰阑记》故事外,还包含着另外一个故事。布莱希特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名字,但从这个故事的前半部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出,这里头的确含有一部中国古典悲剧的影子——《赵氏孤儿》故事的影子。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小米歇尔逃难的格鲁雪,在精神上类似于程婴和公孙杵臼;阴险狠毒的胖侯爵卡兹贝基,类似于奸臣屠岸贾;格鲁吉亚总督焦尔吉的悲剧命运类似于赵朔……不过,从整体看,《赵氏孤儿》与《高加索灰阑记》的关系,远不如李行道《灰阑记》的直接与重要,姑且存而不论。
我们先来看看李行道的《灰阑记》。
李行道的这部杂剧是一部道德教化剧。淫邪贪婪的马大嫂与赵令史私通,为了霸占马家产业,她勾结赵令史,毒死丈夫马均卿,夺走了张海棠的儿子,却反诬马均卿的小妾张海棠谋夫夺子。马大嫂买通街坊作伪证,与赵令史内外勾结,将海棠屈打成招。包待制用灰阑计重审批案,终于使真相大白。海棠申冤;马大嫂赵令史受罚。剧中重点刻画了六个人物:淫荡愚蠢的马大嫂,狡诈势利的赵令史,善良柔弱的张海棠,直爽粗豪的张林,糊涂懒散的苏模棱,正直睿智的包待制。象中国杂剧中大多数角色一样,这六个人物的性格,都带有类型化特点。作者正是通过这些类型化人物,巧妙地表达他对丑恶的愤慨和嘲弄,对善良的呵护和赞美的。
《灰阑记》具有浓厚的讽刺色彩。这首先表现在对马大嫂形象的塑造上。我们先来看看马大嫂的自报家门:
我这嘴脸实是欠,人人赞我能娇艳,只用一盆净水洗下来,倒也开得花粉胭脂店。妾身是马员外的大浑家。俺员外娶得一个妇人,叫什么张海棠。他跟前添了一个小厮儿,长成五岁了也。我瞒着员外,这里有个赵令史,他是风流人,又生得驴子般一头大行货。我与他有些不伶俐的勾当。我一心只要所算了我这员外,好与赵令史久远做夫妻。
马大嫂的丑陋、浅薄、淫邪、恶毒、无耻,在她自己这一段颂歌式的自报家门中,得到了喜剧性的展现。但是,马大嫂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小丑。不,她还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可怕的毒蛇。她为了长期与赵令史苟合,为了霸占马家产业,挖下了陷阱,设下了毒计,害死了马均卿,并把杀人之罪栽赃到海棠身上。她与赵令史、刘四嫂、张大嫂等人内外勾结、机关算尽,险些将善良无辜的张海棠置于死地。然而,尽管马大嫂是那么险恶、那么阴毒,她最后还是失算了,在包待制的灰阑计面前失败了。于是,在她的手段与目的,在她的过早庆幸与可耻的失败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从而也就产生讽刺效果。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赵令史在马大嫂官司败落之后态度的反转。马大嫂谋害亲夫,嫁祸张海棠,赵令史是帮凶,甚至可说是主谋。可是,马大嫂在灰阑计之后,赵令史眼见情妇落败,竟将官司全然推到马大嫂身上,他向包公申辩道:“难道老爷不看见的,那个妇人满面都是抹粉的,若洗了这粉,成了什么嘴脸,丢在路上,也没人要,小的怎敢和她通奸,做这等勾当?”赵令史的态度陡转具有双重的讽刺效果:赵令史对马大嫂形象的贬损(也是事实),既是对马大嫂忸怩作态、东施效颦的恶俗形象的嘲讽,也是对赵令史自身的嘲讽:嘲讽他的虚伪不实和低级趣味。赵令史曾自供:“我做令史只图醉,又要他人老婆睡,毕竟心中爱者谁,则除脸上花花做一对。”这真是赵令史的生活准则的宣言。赵令史明知马大嫂丑,却与她勾搭成奸,甚而不惜弄出人命,把一个登徒子式的风流韵事渲染得如此惊天动地,最后却又将马大嫂贬得一文不值,赵令史的品味与人格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比起赵令史这种见风使舵、知难而退的行径来,马大嫂似乎显得有情有义得多。在戏剧结尾,作者写马大嫂尽管是死到临头了,尽管遭到情夫负情的诋毁,却仍对赵一往情深,表示要与赵“在黄泉下,做永远夫妻”,然而,由于赵显然是位贪生怕死、没有担待的家伙,马大嫂这种款款深情也就具有讽刺意味了。
苏顺是《灰阑记》另一个喜剧人物。他是一个贪官,他爱钱,可是他懒散、愚蠢、糊涂,既没有为官的原则,也没有生活的目标。他绝非那种凶神恶煞的大坏蛋和恶棍,他也不太能够主动地、积极地去害人,因为他没有这种能力与热情。他是一个玩忽职守者。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钱和闲(不理事)之外,似乎没有别的东西能叫他动心。请听他的自报家门:
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司便了。可恶这郑州百姓,欺负我罢软,与我起了个浑号,都叫我模棱手,因此我这苏模棱的名,名播远近。我想近来官府尽有精明的,作威作福,却也坏了多少人家,而我这苏模棱,暗暗的不知保全了无数世人……
一个只要白银、律令不晓的“父母官”,竟会“暗暗地不知保全了无数世人”,苏顺竟有这么好的自我感觉,可见他是多么厚颜无耻。
苏顺虽然糊涂愚蠢,但他也自有他一套处世哲学,欺软怕硬,见风使舵。李行道写马大嫂来郑州府衙诬告海棠时,对苏顺的势利和愚蠢作了辛辣的嘲讽:
〔搽旦云〕小妇人是马均卿员外的大浑家。〔孤作惊起云〕这等,夫人请起。〔祗从云〕她是告状的,相公怎么请她起来?〔孤云〕她说是马员外的大夫人。〔祗从云〕不是什么马员外,俺们这里有几贯钱的人,都称他作员外。无过是个土财主,没品职的。〔孤云〕这等着她跪了……〔孤云〕这妇人会说话,想是个久惯打官司的,口里必力不剌说上许多。我一些也不懂的。快去请外郎(即他的办案助手赵令史——引者注)来。
别看苏顺平时尽装糊涂,骨子里却精明得很,单说这里的“一起”“一跪”,就大有讲究。苏顺是白银爱好者(而非真理爱好者),因此,对白银有极敏锐感觉,一般地说,凭职业的直觉,有人告状,就意味着又有白银入腰包。这回来的既是员外的“大浑家”,自然是位大财神,所以必须以礼相待,“请起”。然而,一当侍从指出,员外并非等于财神爷时,苏顺自然就要前恭后倨,“着她跪下了,”并且也不乐意问她的官司了。这种行为的前后不一致,本身具有浓厚的讽刺性,然而,李行道在刻画苏顺这个形象时,还不仅仅从他行为上的这种前后不一入手,还着力刻画了他坦然的“财胆包天”。请听苏顺的为官哲学:“今后断事我不嗔,也不管他原告事虚真,笞杖徒流凭你问,只要得的钱财够两份分。”可真是“有奶便是娘”了。苏顺不以其贪得无厌为耻,竟敢大肆兜售其金钱哲学,这说明整个封建社会的官场之黑暗到了何种程度,这就赋予作者的讽刺以普遍的社会意义了。苏顺的性格尽管带有类型化特征,然而却也有着丰富而复杂的性格内容。他的装疯卖傻与精明狡诈,他的糊涂懒散与贪赃枉法是如此和谐地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富有装疯和滑稽意义的性格特征,为布莱希特塑造阿兹达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灰阑记》最有光彩的地方,是包待制的灰阑判案。用石灰画成圆圈,让孩子站在圈中,让争夺孩子的两位母亲扯孩子出圈。包待制告诉两位母亲,谁能将孩子扯出圈,就判谁为孩子的母亲。实际上,包待制采用的是哄骗法。灰阑实际是一个圈套,一个陷阱,一个骗局。他要从母性直觉的角度测试谁是真正的母亲。他一连测试了两次,第一次,海棠“输了”,孩子被马大嫂扯出圈了;第二次,海棠又“输了”。海棠每输一次,都给包待制带来一种辨出真伪的惊喜。可是包待制始终不露声色。不仅如此,每当海棠“输”掉时,包待制总会大喝:“张千,与我采那张海棠下去,打着者。”这不仅表现了包待制的精细与稳重,同时也使戏剧本身增添了起伏,获得了张力。包待制对真假两位母亲的情感是以逆反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对假母亲马大嫂,是欲擒故纵,而对真母亲海棠,则是欲纵故擒。两次测试,使善良者更显其善良,使恶毒者更显其恶毒。戏剧的结局,既充满了紧张感,又具有喜剧性。李行道将轻松以紧张出之,将喜剧以眼泪出之,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
灰阑计带有强烈的民间文化色彩。我国民间故事和公案戏(小说)中,有许多这类智慧故事,如杂剧《合同文字》、《鲁斋郎》都是以狡智使坏人上当。不过,灰阑计的智谋设置更精巧完备,更具有戏剧效果,而遥远的时代背景使作品本身更带上了浓厚的传奇和神秘色彩。
布莱希特非常喜欢在他的戏剧中渲染一种异国情调,他经常将他的戏剧的背景安排在中国(《四川好人》)、日本(《Measure′s Taken》)、蒙古、罗马、印度、大罗马等地。《灰阑记》中的异国情调显然对布氏产生了吸引力。因此,布氏在创作他自己的《高加索灰阑记》时,他只把灰阑计依样画葫芦地照搬了,在其他方面,我们很难直观地发现李行道《灰阑记》的影子。
与伏尔泰改编纪君祥《赵氏孤儿》和克拉帮改编《灰阑记》不同,布莱希特将《灰阑记》中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彻底打乱,再作重新组合。故事人物关系和结局都采取与李行道的《灰阑记》相逆反的方式进行安排。在李行道的剧中,寿郎的生母张海棠是位善良、本分、性情柔顺的母亲;在布莱希特的剧中,小米歇尔的生母却是一位自私、庸俗、性情歹毒的母亲;在李行道的剧中,寿郎的大娘马大嫂是位淫邪残忍的奸妇;在布氏剧中,小米歇尔的养母却是一位勇敢善良的女性。两个剧本中,生母与生母、养母与养母,在身份和人格上,都作了对称性置换。与人物关系的置换相适应,布氏的灰阑判案,自然也出现了与李行道相逆反的结局:获得法定的对儿子的抚养权的,不是生母,而是养母。天才的标志之一,就是非凡的综合才能。布莱希特就是这样的天才。他善于点石成金,混纺出新。《高加索灰阑记》由于采用了纪君祥《赵氏孤儿》的某些情节因素,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富于现代色彩的故事情节,戏剧的场景更为壮阔、戏剧结构更加紧凑,具有史诗的宏伟。
著名戏剧理论家马丁·爱斯林在评论布莱希特的诗歌语言时,曾称赞说:
“他(布莱希特)的诗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他的诗自身的率直与朴素中,存在于他在非俗套的上下文中对俗套语言的大胆运用。”⑥
马氏的评论同样适用于布氏的戏剧:因为布氏更擅长用绝非俗套的方法处理非常俗套的故事,这在《高加索灰阑记》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首先是剧中剧结构的运用,布氏在《高加索灰阑记》中运用蒂克、肖伯纳等作家用滥了的剧中剧套式,但丝毫不给人以俗套之感。因为布氏在这个俗套的结构中寄寓了他独特的哲学思考:关于个人与集体的权力与义务的思考。在一般人看来,土地归土地所有者耕种,孩子归亲生父母所有,这是亘古不变的朴素真理,谁也不会反对。然而,布莱希特却以他的睿智洞见到这个看似合理的道理中所包含的不合理成分。在布莱希特看来,如果土地所有者具备耕种自己土地的能力,如果孩子的父母具备一个父母对孩子应有的爱心,那么,土地归属于土地所有者,孩子归属于父母,自然是没有问题。然而,造物主并没有为每位土地的所有者赋予相应的耕种能力,并没有为每位父母赋予相应的爱心。常有的情形是,富有的土地主有大片的田地,却没有能力使地上长出庄稼;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却没有半片土地;生性残忍的人生育出一个个孩子,温柔善良的人却偏偏没有生育能力。这是造物主对我们人类的嘲弄。为了公平,为了使我们人类先天的权力与后天的义务相符,布莱希特在戏剧结束时,通过歌手告诉我们:
但是《灰阑记》的听众,
请记住古人的教训,
一切善于对待的,比如说
孩子归
慈爱的母亲,为了成材成器
车辆归好车夫,开起来顺利,
山谷归灌溉人,好让它开花结果。
灰阑判案的结果,使剧中剧的故事获得如下结局:作为养母的格鲁雪获得了对小米歇尔的抚养权,而生母(原告)总督夫人却败了诉。同时,第一幕戏——楔子——中的矛盾获得解决:山谷应归灌溉人,而不是土地所有者。于是我们的习惯思维被打破了,我们只问权利不讲义务的陋习遭到挑战了。布莱希特用启发与反思的哲学思考使《灰阑记》原有的道德批判主题得到了升华,获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其次是结婚故事的巧妙安排。比之于剧中剧模式,舞台上的结婚场面更属戏剧俗套。然而,布莱希特对结婚故事的处理却非常别致。少女格鲁雪带着小米歇尔四处躲藏,卡兹贝基的铁甲兵却如影随形地追踪着她。格鲁雪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甩开追兵,逃到哥嫂家,哥哥以为格鲁雪有了私生子,为了遮丑,逼着妹妹嫁人。这位哥哥对妹妹的生活考虑得无微不至,他知道妹妹还在等外出打仗的心上人西蒙,就为她物色了一位行将就木的丈夫。格鲁雪觉得嫁给这样一个只剩一口气的人,既可保持自己的纯洁,又可保护小米歇尔,还可不再看嫂嫂的冷面孔,因此一口应允。格鲁雪的哥哥为了妹妹这个形式上的婚姻,已花了四百元代价。结婚那天,“新娘走进门,新郎要咽气”。这可急坏了新郎的母亲,她害怕媳妇没进门,儿子已咽气,四百元泡汤,所以急得团团转,请来一个和尚,把婚礼与葬礼同时操办。于是,舞台上出现了两种绝不相容的仪式场景:结婚仪式与送葬仪式。正当低沉的结婚进行曲和热情的送丧圆舞曲交错奏起时,格鲁雪的那位只剩一口气的丈夫尤普索突然从病榻上坐起来了。尤普索为了逃避兵役,已整整在病榻上躺了一年,他的装病装死不仅瞒住了格鲁雪的哥哥和亲邻,而且也瞒住了自己的母亲。因此,尤普索的“死而得活”不仅震惊他的母亲,他的新娘,而且也震惊了观众。布莱希特将这个结婚场面写得兔起鹘落,奇峰突起,显示出他驾驭舞台的高超技能与非凡的艺术功力。
第三是法官阿兹达克形象的塑造。柏林剧团当初演出《高加索灰阑记》时,在节目单上写道:“故事现在讲的是一种崭新的智慧,一种建立在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处世态度。”⑦这种“崭新的智慧”和“新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处世态度”正是通过法官阿兹达克表现出来的。阿兹达克绝非传统上的那种清官,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虚拟化的包青天而已。无论是在李行道的《灰阑记》中,还是在元代包公戏中,包公一直是一个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不苟言笑、气概威严的形象,是一个被中国老百姓充分理想化和偶象化了的十全十美的文化英雄。阿兹达克和包公完全不同,他既贪杯又贪财,相貌猥琐,出言粗俗,类似酒鬼、草包、乞丐、囚犯和流氓。然而,在骨子里,他却是一个浑身充满智慧的饱学之士,是平民的保护神。他是精神上的“义盗”,不断地把正义、真理“盗”来还给受苦的平民。他毫不掩饰地从富人手上索取钱财,又把这些钱财分给缺食少衣的人民,自己却永远穿着一身乞丐式的破烂不堪的衣服,布莱希特通过歌手之口,赞颂他——
他放手把法律破坏,
象面包给大家掰开;
他用法权的破木船救大家上岸。
穷光蛋和下贱货,
偏偏享受到袒护,
阿兹达克是公然受空囊贿赂的法官。
七百天一管无星秤,
量过多少批案情,
他讲粗人的粗话和粗人通气,
绞刑架
就横在法官楼顶上,
阿兹达克在那里推行着带刺的公理。
显然,布莱希特是把他当成一个“正直的歪官”来塑造的。他在阿兹达克的表与里、形式与内容之间,展开了逆反性对比:滑稽的、庸俗的、醉醺醺的、色迷迷的、贪财的、昏沉沉的……外表和严肃的、文雅的、清醒的、仁厚的、慷慨的、美丽的内心构成了强烈的反差。由此使观众在认清这一形象的真面目时产生困难,从而增加了审美的难度和长度,使这一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感。布莱希特在塑造戏剧形象时,最擅长的是塑造具有内在个性矛盾的人物形象,如沈黛与潘第拉,一人两面,性格分裂;伽利略言行相悖;麦基善恶兼备……布莱希特曾经在《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中说过:“人啊,有两个灵魂盘踞在/你的胸中!/可别想二者择一,/因为你必须两个都有。/你就永远和自己吵个不停吧!/只要有一个在就总会一分为二!/保住高尚的,保住低劣的,/保住粗野的,保住文明的,/把他们两个都保住!”阿兹达克的形象正是高尚与低劣、粗野与文明的辩证的统一。也许布莱希特从李行道的包公形象上获得了平民传统的源泉,从苏顺身上获得了某种富有反讽意义的滑稽,然而,阿兹达克却绝非包公与苏顺的生硬拼凑,他是布氏的独特的创造。布氏还通过阿兹达克展示了“一种建立在崭新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处世态度。”这是怎样一种处世态度呢?我认为,是一种在装疯卖傻、玩世不恭的装扮下的严肃的生活态度。换句话说,是一种幽默的人生态度。任何故作镇静的严肃,任何故弄玄虚的高深,任何故作深沉的悲伤,在阿兹达克看来,都是一钱不值的。正因为此,他敢于伸手向富人们要钱,敢于对格鲁雪言挑语逗,能够安然地乐意地倾听格鲁雪对他的呵斥与怒骂……他从不讲豪言壮语,从“不在任何人面前装英雄”,相反,他总是将自己装扮成一幅贪婪、愚蠢样子,使自己远离庄严、理智,而靠近滑稽、荒谬。布氏赋予了阿兹达克平民色彩,他似乎要通过阿兹达克为虚伪的道德、伪装的正义唱出一曲讽刺挽歌,为高高在上的英雄们提供一个反嘲性的复本。因为,在布莱希特看来,现代社会显然不是一个英雄主义时代。浪漫主义在当代世界已经无法奏响它优美的旋律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非英雄化时代——这是一个“时代已经越出轨道的非理性的时代”,战争把人类推进苦海,而和平又将人类置于愚蠢与平庸。我们的社会是由某种非理性的偶然的东西控制着的可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已很难找到公理与正义,更无法发现人性的伟大。因为社会的激变已不断地将人类的野性酿成凶残。那些表面上看来文雅、庄严的东西,其实是最丑陋、最滑稽的东西。相反,那些自认为贱、自认为非的人,却是我们社会最高贵、最正确的人。布莱希特正是通过将地位显赫的胖侯爵和总督夫人与出身卑贱的女仆格鲁雪置于人性的两极,来展现人类两类相抵触的本质的。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布莱希特着力要展现的,恰恰是这两类人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在阿兹达克,他几乎是采取着一种作贱自己的方式,然而,结果恰恰相反:他的人格并没因此而被贬低,却获得了升华;在胖侯爵和总督夫人,他们是采取着一种雅化自己的方式,然而,结果也恰恰相反:他们的人格并没因此而被抬高,却遭到了贬低——换句话说,不是遭到贬低,而是丑恶本性被彻底暴露。布莱希特象一个技艺精湛的魔术师,使他的剧作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幻术效果。
布莱希特亲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对战争的残酷,战争对国家、社会、人性的摧残,有着深切的体验。因此,在这个剧本中(当然还有其它好些剧本),布莱希特对使国家遭倾覆、社会遭动乱、人类受煎熬的战争,表现了深深的厌恶,对那些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则倾注了深深的同情。布莱希特通过阿兹达克之口唱道:
老妈妈,我几乎要叫你“格鲁吉亚母亲”,
你孤单,你悲苦,儿子却投入了战争,
你挨拳头,却充满希望!
要是得到一头牛,就眼泪直淌。
你要是没有挨揍,反而惊慌。
老妈妈请宽恕我们这些罪人!
然而,布莱希特在更多时候,是对他所憎恨的政客和战争贩子,所蔑视的社会庸众进行嘲讽。为了这一目的,布莱希特赋予了阿兹达克一种愤世嫉俗的社会讽刺家的资禀。阿兹达克唱的第一首歌,都可说是富于酷评性的讽刺佳篇:
国王必须添一块新疆土,
农民必须把卖奶的钱都交出。
世界屋脊呀必须索取,
茅舍屋脊就必须揭去。
我的子弟给拉到天涯海角,
好让大老爷在家里吃喝玩乐,
当兵的你杀我来我杀你,
当官的见了面互相敬礼。
在这里,阿兹达克对让人们作无谓牺牲的战争及战争贩子们作了无情的嘲讽。
衙门拥挤不堪,满街都是官员,
河水涨过河岸,田亩一片泛滥。
连裤子都不会脱的草包,执政当朝,
数数目数不到百的蠢才,吃饭八道菜,
种粮食的等顾客上门,却只见跳蚤成群,
织布人离开织布机,回家来衣不遮体。
这是阿兹达克对暴君统治下的“太平盛世”的嘲讽。
乡村文书阿兹达克在短短的时间内,一会被推举为法官,一会被送上绞刑架,一会又被拥戴成法官,这本身虽然包含了某种命运的无常感,但更主要的是表现布莱希特对无法无天的混乱世道的责难,对无头无脑的社会庸众的失望情绪。几分钟前,他们可以不须任何理由地、恭而敬之地把某人推上政治舞台,几分钟后,他们又可以随着政治的变幻将同一个人推进地狱,所以,阿兹达克对差点要了他的命的铁甲兵们大骂:“你们好,狗子?怎么样,狗子世界怎么样?臭得好闻吗?又有耗子好舔了吗?你们又你咬我、我咬你了吗?……”“我的狗弟兄们,随时找一只耗子舔舔。”这不是一般的所谓世态炎凉之感,而是对无知的庸众的盲信盲从劣根性的讽刺与鞭笞。
总之,《高加索灰阑记》在多个方面,为剧作家的利用现成材料进行创造性转化提供了范例,认真研究布氏这类作品,对繁荣我们当代戏剧创作,必将产生有益的影响。
注释:
①参见Petetr Demetz编《布莱希特评论集》P.181 Prentice-Hall,Inc.
②参见Petetr Demetz编《布莱希特评论集》P.181 Prentice-Hall,Inc.
③Martin Esslin:Brecht's Language and It's Sources参见Petetr Demetz编《布莱希特评论集》P.179 Prentice-Hall,Inc.
④Eric Beutley:The Brecht Commentaries P.52。
⑤《王国维戏曲论文集》P.112-113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⑥Martin Esslin:Brecht's Language and It's Sourceso Peter Demetz编Brech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⑦《布莱希特研究》P.13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