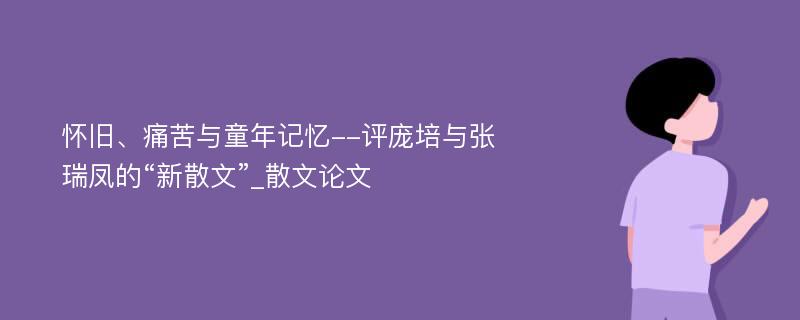
怀旧、伤痛与童年记忆——评庞培、张锐锋的新散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伤痛论文,童年论文,记忆论文,庞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心的读者或许已注意到了庞培、张锐锋二位与众不同的散文。近年来,关于散文的说法已经不少,比如美文、文化随笔、学者散文、手记之类,所以任何标榜都难免会有多事之虞。但我又想到,这是否意味着散文写作已到了山穷水尽、不可再写的地步了呢?这大概是我在杞人忧天。早在五四时期,鲁迅曾对散文有个基本估价,认为其成绩在小说、诗歌之上。1936年夏,他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是谁”的问题时,毫不犹豫地一口气说出了周作人、林语堂、陈独秀和梁启超等一连串名字。为什么在诸多文学样式中他对散文情有独钟呢?尘埃落定,我们不便妄猜其中深意。以他深邃的眼光,可能已注意到,在西学东渐、西洋诗歌小说的影响滚滚东来之际,散文这一古老的民族文学形式不仅未被摧毁,而且愈益显示出它的最适于表现中国人气质、情感、心理的种种长处。它是一个贯通古今和极富想象力的审美空间。负芨美国多年的学人林毓生,回过头重温散文文字的妙处,更是生出痛切之感:“它特别能够表达具体的感情与丰富的想象,所以它特别适合抒情”,“无论动之以怜悯,或动之以仇恨”,它“都是很有效的。”〔1〕有效性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是指时效、时尚,它以在某种特殊背景下引起轰动为目的,另一指文字本身原有的文化魅力,它是时尚的反面,甚至有一种陈旧之感,然而又确确实实透露出今人的伤痛,叫人回味、惦量、摩挲,反复不已。
一
稍稍搜索一下本世纪中国文人的心灵史,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时代转折之际,总会有敏感之人慷慨陈言,留下凌厉浮躁的议论,而后出现退隐,成为一个古人。在20年代,周作人是一个典型,陈寅恪是五、六十年代的代表,然后是钱钟书、季羡林、金克木等人。或许还会有人步其后尘,以致连绵不绝,也未可知。
我想这是我对庞培、张锐锋作品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两人先为语言很新、骨子里很旧的先锋诗人,后为态度古旧的散文作家,身份虽变,却无出人们意外。因为,从刚开始写作直到今天,在他们笔下始终滚动着故乡湍急或者平缓的河流。在河的两岸,既有他们早年黯淡的生活,亦有至今人生仍旧黯淡的亲人、友朋、邻里、故旧,更有刻骨铭心的伤心的记忆。5年前, 庞培就在一首题名《在浮桥上》的诗里表白:“人们纷纷涌过浮桥,/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的命运跟他们一样。/从一开始,我就注定会回来,/回到这里,梦想并眺望,/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的晚上。”在散文《大河》里,张锐锋也曾感慨道:“一个人太孤单了,太渺小了,容易被大河所淹没。一个人可以是一个世界,同样可以是一个零。”人们会问:为什么中国社会如此激烈、残酷的变动不能彻底改变一个人,他最终却要“回来”,结局“是一个零”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传统对故乡的命名远远要比时代生活对人的命名表现得固执、持久和不容怀疑呢?海德格尔把这种现象归之于写作的“前理解”。布尔特曼说:“没有前理解,任何人都不能领会文学中的爱和友谊、生与死……一句话,根本无法理解一般的人。”〔2〕在这个意义上, 庞培的散文《乡村肖像》事实上是“一般人”生命的写照。在故乡“运河”的文化阴影里,这些人的生生死死,快乐哀痛,无一不与它发生某种深刻的关联。在《乡村教堂》里,我们看到的是修女们不知不觉的“本地化”,她们的日常举止、穿着不单被“小镇生活”同化了,而且口音与本地人也已经没有差别:“重浊、苦闷,满含着对生死、天命的迷惑不解。”摇面店的顾老板则是作者心目中的另一种典型:他善良、知天命,从做伙计而到老板,再到老板兼伙计,平淡而窝囊地过了一生,对时事的剧变、时间的流逝竟习焉不察,不为所动。《摇面店》显然在顾老板这个人物身上暗示了一个道理,在中国广大的乡村,尤其在乡村生活的深处,个人的时间观与历史(运河)的时间观是截然不同的,但更多时候又常常浑然难分。在这里,运河恰好成了一面活生生的镜子,它决定着两岸人物的命运,同时又是这一切的观察者。在我看来,关于运河的宿命感深入到了庞培的生命结构之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观察方法,一种写作风格,也成了他本人命运中的重要部分。在这种情形之下,无怪乎他笔调阴郁,口气沉缓,也无怪乎他为何放弃了对命运的反抗(与本世纪中国多数作家的做法正好相反),甘心情愿地与他钟爱的这些“一般的人”默默去承受“运河”那毫无道理、亦没有穷期的狠狠的惩罚。在处理大河与个人的关系时,张锐锋的散文涌出的是一声你不禁打一个寒颤的“天地皆宽我渺小”的慨叹。如果说庞培的情绪表现是克制的、节省的,毋宁说他在气质上更像一个诗人。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与江南运河细锐的感伤相比,北方的大河更显出历史的疼痛和厚重来。它所构成的是中国人生命哲学的另一方面:对命运的宽恕。在《小河》的背景之下,是我、小毛、老虎三个人童年生活的悲喜剧。“小河”决定了我与小毛打从小就得劳作的命运,自然也决定了与世界基本的悖论关系:在深夜里浇水,而不能像城里孩子那样疯玩,“那年的夏天,生产队长让我去浇地。入夜时分,我穿着水靴走出村庄。手电筒的光芒射穿了黑暗,形成了一个长长的锥体。顶点握在我手里,……我晃动着手电,才能证实我的存在。”从我和小毛的成长历程看,劳作是一种宿命,但它于孩子而言,在本质上是缺乏诗意的,因为它反对孩子天性中的“玩”。劳动是在取消孩子的权力。从另一角度来观察,老虎是与我、小毛那场打架中的“胜利者”,然而,他浑身的野性在强大的“劳动宿命”面前却无计可施。他毕业之后的车把式身份,与浇水者的社会地位毫无二致。命运把胜利与失败一下子扯平了,他发现:“欺侮与被欺侮已成往事,往事被埋葬在劳动的苦痛里。”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人都是值得怜悯的。在张锐锋另一篇值得重视的散文《大河》里,“大河”成了每个人的“镜像”。它照耀出人成长中微妙的历史,也反观到,“它经历过无数的故事,这故事总又包含着人的末日。”于是,我们看到,在大河巨大的皱折里,哑巴眼看着母羊母子冻死在荒野却无动于衷;生产队长手里的马蹄表成了这个村庄的“二十二条军规”,它的快或慢都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裁决人们命运的不是人自己,而是这块表的“某一刻度”。我们还发现“哑巴”在作品中是一个非人化的象征,对大河而言,他是唯一的见证,而对于人来说,他却是无从证明的,在这个意义,他成了人与大河之间的一个认识的误区,由于他的遮蔽,大河这个镜像是残缺不全的——因为,谁能真正解释中国人对“二十二条军规”既恐惧又亲昵的矛盾态度呢?这就是大河、运河对我们的命运?
中国现代文学中始终有一个“怀旧”的主题。以鲁迅为例,实际也有某种阅读上的复调性。在《在酒楼上》中,他借吕纬甫之口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据说《孤独者》里有鲁迅好友范爱农的某些影子。作者一开始就写道:“我……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只有亲人、友好才会为之送终,语气也才会如此沉痛。因为就每一个当事人而言,他们都意味着“过去”的日子,是一个陈旧的往事。然而,人又不能割断与过去的情感联系,写作就是一次次经验上的“还乡”,他只能在记忆中寻觅今天的自己。所以,有研究者认为,鲁迅是一个反传统的思想战士,然而至少在1926年之前,他与传统(某些称之为“旧”的东西)之间,确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的精神联系的。〔3〕在30年代, 另一位作家李广田不止一次地在其作品里发出过“我是乡下人”的痛苦呻吟。1922年,沈从文自湘西来到古都北京,留下的多半是关于乡下的文字。最后封笔时,写的仍然是与故乡沅水有关的长篇小说《长河》。他告白说:虽身居都市,“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给我的印象里。”〔4〕40年代初,周作人写下了诸多怀旧的文章, 如《关于范爱农》、《玄同纪念》、《记蔡孑民先生的事》、《关于朱舜水》、《关于杨大瓢》、《上坟船》等等。怀念故人,忆及乡里,甚至不能自抑。对这种非常的情感变化,他解释说:“中年以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5〕可见, 在文学史看似明白的线索里,除革命、抗战、光明与黑暗决战等社会学意义堪称主流的文学主题之外,分明有着另一个并非显学的潜在话语谱系。由于前者的“遮蔽”,或说因它的拒斥,后者仿佛一堆历史的瓦砾,被长期封存在它沉默的文本当中。在林毓生看来,中国社会乃至文学的发展之所以缺乏稳定的底色和价值上的方向性,原因就在,思想的冒险不仅未得到稳定的社会和文化的滋养,而且还促成了导向的混乱,“20世纪的中国思潮的主流却偏偏是:一方面企盼与要求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兴起与泛滥。”这恰好是“中国近代与现代思想发展的最大矛盾之一。”〔6〕所以,怀旧也 罢,还乡也罢,成为古人也罢,无非是要回到传统的思想脉络之中,以图建立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而已。
在八、九十年代,庞培和张锐锋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是意味深长的。在《茶馆》一文中,庞培所描绘的是一个正在人们生活里消失着的“传统”:“从本世纪60年代,这类公共的茶馆样式已在中国各地尤其是江南一带渐渐式微了。我小时候所见的市井中的茶市,应该是它漫长历史的最后一次投影吧——……30岁以后的周围街市,以每年一两处的速度在拆迁、凿毁它们,包括民居中的其它老房子,而且根本不屑重建了——记忆中的一根神经随着人们对新的阆修材料的兴趣而停止了跳动。”而张锐锋所得出的是一个“必死”的结论,在《武州川》中,他戏言道:“人们出生,直到长大,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唯一的目的是让自己的历程越来越深入到自设的陷阱之中。直到那陷阱上面的土掉下来,埋住人的一生,这就是坟墓的意义。”有趣的是,就在61年前,鲁迅对已然陷落的传统也曾有过“坟”的比喻,他声称这是要“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7 〕假如鲁迅对传统表现的是一种爱恨交集的心情,张锐锋这里则是一个沉痛的凭吊——历史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呈螺旋式地上升,好像是在经历一次折回,从传统的断裂处开始,重新去检讨那个人们“自设的陷阱”。
二
据庞培说,在80年代后期,他曾有过一段在江南的大地上“闲逛”的时光。目睹一个个小镇上遗留着的“古老中国的陈迹”,他仿佛经历了一场浩劫,或是一场噩梦。〔8〕
很难说,这不是他留在90年代文学阅读中“文化遗民”的悲凉身影。在陈祖武看来,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是明末清初文化遗民的典型,他们痛悼一个时代的逝去,在新、旧之间辗转不安,先是激烈抗争,后来著述终老。黄宗羲的《避地赋》正可看作他于“转徙不宁,扶今追昔”中的寄怀之作,是颇引人深思的。〔9 〕可以说,在一个时代分崩离析之际,尤其当它的文化积累眼看要荡然无存之时,文人墨客或如王国维沉湖自尽,或如海子卧轨自裁,已不止是一个坚守人格的伦理学问题,它所促发的还有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命题。南宋以来,江浙一带历来为中国的人杰地灵之地,庞培的故乡江阴自然也不例外。既然文化的积存不是一朝一夕获得的,它是千百年来思想风气熏染、沉浸的结果,文化的摧毁,往往又发生在一夜之间,因此它必然会引起庞培撕心裂肺般的心灵伤痛。然而,他的气质、教养又决定了,他会将传统文化的思考,转化为对细小、具体事物的关切。比如,在《摇面店》里,他关心的是顾老板那爿老字号小店是如何在急风骤雨似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悄无声息地衰微的,而顾老板态度的麻木又意味着什么。在《小学堂》中,一对做乡下教员的年轻夫妇对外面变化之中的世道人心置若惘闻,怡然自得地生活在个人自足的世界里。《白铁匠店》那些“厚道、老实、安分守己”的传统铁匠,仍然对落伍于时代的手艺坚贞不渝,“干这种营生的人穿着和平时脸上的表情都像是传代的,师傅徒弟都一个样,都有拘谨、向里抠的小眼睛——即使大眼睛也不觉得大——不时抬头看你,又很快低下去——有一种不停低头的习惯。”庞培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上层经常性的变革中,文化的封闭向来被视为变革的阻力,然而,在今天值得检讨的恰恰是它的反题:变化不断的变动究竟给文化传统带来了怎样的思想结果,在此背景下,他对江南各地比比皆是的乌篷船发出的赞美就值得我们深究了:
乌篷船是典型的中国式梦境的产物。它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于河
流、水乡、日夜的精妙看法。……它继而溶合在宋元两朝以来中国
人的日常戏曲里,尤见于长江流域几个奇异的剧种:目莲戏、越剧
、皮黄和安徽黄梅戏里。作为物的乌篷船的性格和气质里冬天的成
份,比之夏日的雷雨、暮春的光景,秋冬两季的霜冻和薄雪,似乎
更能映衬她的娉婷娇娆、以及清秀明丽——她的平民品质的简朴节
俭——她的妖弱翘起的船头那近乎无助的美。她是中国式河道的青
春写照。她在水上的形状酷似江南地区一些乡村女人在身段、容貌
、气质上的反映——她们之间的如此融洽——简直令我要下出武断
的结论:最先发明它的一定是女人!
在我看来,这段文字已经不单是欣赏,简直就是作者偏执的酷爱了。15年前,我曾有过一次在苏杭之间乘坐乌篷船的游历。我记得,那好像不是在坐船,而像是在做梦:吴地软歌,春光浅影,蕴藏着多少当地文化的魅力。文化意义上的“遗民”,其实不止是对反文化行为的激烈对抗,它还是另一层含义:通过文字的记载、描述,使文化在一代代中人赓续,以达文化保存和发扬光大的深刻用意。而周氏两兄弟正是这方面特别突出的显例。拿周作人的话说,鲁迅与他从故乡绍兴去南京求学,走的正是一段水路,先坐乌篷船再换大船,乌篷船与他们的人生有着难解难分的缘分。〔10〕就此思路观察,民国初年两人热心搜寻、辑录故乡山阴、会稽籍同乡著作,积数十年之功,据说后来成集的就是:《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等。之后,两人先后北迁古都北京,仍沉迷于对古墓砖、拓片的收藏与拓印,终不能已。1932年,母亲生病,鲁迅从上海返京探视,又留下诸多与郑振铎切磋墓砖、字画体会的文字。对这一嗜好,两人乐此不倦直到终生。从乌篷船到古文物,它象征性表明,从旧文化中来的人物即使一时是它的反叛者,也是对文化传统的价值深以为然的。不错,鲁迅、周作人等反传统文化先驱者的形象早已深深镌刻在文学史、尤其是思想史中,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得以成立的一个强大的逻辑。然而,他们数百万字的著作又显然向世人证明,在深邃的思想之外,它长久吸引人心的恐怕还有通过文字所透露出的文化的魅力。在新旧交替的两个时代之间,说他们是另一意义的文化的遗民,也是未始不可的。
张锐锋所依赖的是对苏轼、王安石、李白、杜甫等古典文学文本的“重读”。按照加达默尔的说法,人与历史(时间状态中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两个层次:一是历史向人敞开,使人生活在一个历史开放的时空中;二是人向历史敞开,使历史变成开放的,非封闭的。这种“对话式”的逻辑构成阐释者与文本之间有趣的交流。〔11〕就是说,张锐锋不是把苏轼们当作“死人”来读的,而把他们当作“活人充满了复调性”。在《飞箭》中,苏轼“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的诗句不再充斥着通常文学史教科书所叙述的刀光剑影,或黎民百姓的痛苦呻唤,而呈现了诗人写这首诗时各种可能的情景:苏轼是“寂寞的、孤单的”,但他好像原来是“在欢乐之外”,诗中的美女歌弦与他并无关系。进而发现,诗人总是在生活之外写诗的,正如文化在人们的强词夺理之外才获得正含义正是对今天、当下生活的否定。在张锐锋看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对时间的喟叹,其实是不能仅仅做新旧年交替解的。他说:
实际上诗人王安石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要写的是真实生活之外
的东西,他所吟诵的诗篇是要深入到更深的谜底里去的。此时,王
安石在新春之初步出家门,家家门前换上了桃符,旭日初起,春风
送暖,人们在家中已备好屠苏美酒,诗人忽然感到了这其中含有更
加深沉的内容。是什么呢?他摇摇头。那些更深的东西单凭理智的
力量是不可追寻的,他只有将它隐藏在诗中,这是唯一的办法。…
…这是一些美好的事物总是让人悲痛的理由。
与庞培人情风物上的文化理解不同,张锐锋对文化的解读是时间和诗性的。所以,目睹细小事物中文化的崩溃,庞培在惊呼世道人心不古之余,宁愿去做一个遗世独立的高古之人。而张锐锋的观察中则不免充满存在主义怀疑的色彩。是故,他发现皇帝尽管如史书所言是秩序和人间的起点,却原来“是一个可悲的无意义的历史的替身,他所做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通过古人郑谷的一首羁旅诗,进而察觉“想象中”的妻子与“真实”的妻子原来也是有“差异”的。由此,他得出了“文化”在拒绝“生活”的大胆结论:“历史沿着物质的方向从根本上取缔人的梦幻,你只能在现实中生存。我们看看那些腰缠万贯、大腹便便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可以过奢侈的皇帝的生活,但不可能有人的生活。他们可以用钱来收买爱情,但爱情一经收买便变成了钱的僵死外形。爱情是在孤独的内心形成的,它实质上是梦幻的复制品,在一个没有梦境的晚上,还有什么存在呢?”在张锐锋眼里,今天这个时代,就像是“一个没有梦境的晚上”。文化可能还在小镇生活某一个建筑物、某一个细节里存在,但它已经不再是文化本身,因为从根本看,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诗性的、抒情的。〔12〕那是已远离今天和永不复还了的一种“存在”。张锐锋与其是心怀不满的文化遗民,莫如说他更像是一个耽于幻想的诗人。
三
说到底,文学作品中纯粹的童年眼光是不存在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成人的事业。有研究者认为,鲁迅的小说《孔已己》借助一个儿童的观察写出了晚清社会的衰落,作为晚清文化负载者的孔已己的人生惨剧,正是这一衰落过程中的一个投影。由此可以说,这其中渗透的是中年鲁迅的人生体验,“孔已己”命运的沉痛恰恰是中年鲁迅的沉痛。
我注意到,庞培和张锐锋的写作风格虽存有差异,但不约而同都是通过童年的记忆来表现在年的心灵的疼痛。在《乡村肖像》中,庞培讲的最多的是他幼时的故事。《钟表店》写的是他早年感觉到的“一种陈旧、与世隔绝的气氛”,《糖果厂(二)》记述的是那位拖拉着六个孩子、生活毫无着落的女邻居,《一个拉二胡的》中是受孩子欺负、却认真地拉着每支曲子的盲艺人,而《摇面店》里孤寂善良的顾老板,无疑是作者灰色童年的全部缩影。庞培做过工人、酒吧里的吉它手和私营书店的老板,过早地品尝了中国下层社会生活的艰涩与苦痛。这使他异常的敏感,也最容易受到外界的伤害,所以,当他以童年的视角进入各种人物的生活,你会感觉到,那生活深处是无童年的天真乐趣可言的,有的却是成年的世故和沉重的无奈。这段话,正好可以用来做他内心的表白:“她说‘你要保重’(声音如此绝望)——保重。我也说出这个词,但它却像人世间最深的侮辱、最重的一记巴掌。”是的,在庞培迄今为止的人生中,究竟挨过多少次这意外飞来的“最重的一记巴掌”?
张锐锋也说过:“惩罚是比生活更有耐心,却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正是对他诸多作品的最好的注脚。在《倒影》中,乡下的孩子过早地被推向了生活:深夜浇水。“一个人置身于夜晚,尤其是没有月亮的夜晚,世界与人的联系被一把刀轻轻地割断了,你突然会想,你与世界的联接之绳原来是那么细小,那么脆弱,仿佛一用力气就能崩断。”或者说,一个孩子被仓促地推向了危险、痛苦的中年阶段,因为生活要他承担过于沉重的责任。显然,张锐锋是以中年的眼光打量与重新检点他的童年生活的,通过这种观察,他发现了这种生活的虚拟性,就是说,所谓童年的天真无邪是根本不存在的:“那时,我们都很小,提着篮筐挖野菜,我踩着弟弟的肩膀,想攀住屋橼,结果扒下一块砖头砸在我的头上。我想攀住的原来是一种惩罚。那惩罚静静地一直等待着。而我却是那么急不可耐地想要得到它。”从中年的角度讲,这何尝不又是生活本身!因为,它一直延伸到了中年经验的深处。所以,才会有《大河》里生产队长那只“马蹄表”的荒诞的权威,也才会有《武州川》里两个孩子恐惧的对话。值得一说的是,张锐锋的叙述中显然有两个相互作证的层面:表面上看,这是一段乡下孩子的童年生活,但它的每一步都存在叙述的悬念。比如,手电筒的恐惧,意外砸下的砖头。就是说,中年的眼光不仅窥视着、实际也戳穿了童年的虚幻。反过来,中年又证明人的童年是弥可珍贵、不可替代的,童年的空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人生的空白。
细究起来,中国现代文学中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书写童话的阶段。鲁迅的小说《故乡》可以说是一个童年的故事了,然而他自己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3〕这实际也意味着,近百年前的现代文学是直接跨过童年期进入中年阶段的。一方面,它说明现代文学生存条件的残酷性和复杂性,文学一开始就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必须被纳入到中国社会惊心动魄的变革之中;另一方面,文学的发展也要求自己处于多维的视域当中,向复杂的经验和历史敞开,更向一切写作的可能敞开。这决定了庞培、张锐锋写作的底色:他们都是在文化价值分崩离析之际开始散文创作的,文化的崩溃不仅没有使他们像某些人那样人格萎缩,相反,使他们进一步意识到来自写作者本身的危机。文学从来就不是行为的艺术,而是发自作家生命深处的切身之痛。它更应该是对新的、先锋性的标榜,而是对文化传统血缘的积极回应。正如鲁迅之于浙东小镇,沈从文之于浑沌未开的湘西,老舍之于北京传统市民社会,庞培、张锐锋于今天散文的意义,也许正在这里。他们是从故乡出发的,世事纷乱之中,“故乡”像征的是一个正在逝去的文化传统,它是秩序、价值的所在,诗的所在,是作家灵感、生命的源泉,更是其安身立命之本。这无疑成为庞培、张锐锋散文的双重特色:它在阅读的层面上是焦虑的、中年的,隐隐透出世纪之交的“乱世之音”,在其文字内部,它又含蕴着令人心动的童年的诗意。这种并不协调的双重色调,在我们内心唤起的是亦悲亦喜与深广忧愤的复杂感情。相对于目前文学诗意普遍的匮乏,庞培、张锐锋严格地说是那种诗性的写作。它使我们想到,在人心溃散的今日,文学有责任找回自己语言的“栖居之所”。
注释:
〔1〕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3页,三联书店1996年第3版。
〔2〕默里:《现代批评理论》第4章。
〔3〕同〔1〕,第202页。
〔4〕沈从文:《从文自传》
〔5〕周作人:《苦茶》第397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6〕同〔1〕,第5页。
〔7〕鲁迅:《坟·题记》。
〔8〕庞培:《茶馆》,《大家》1997年4期。
〔9〕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辩录》第106—111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周作人:《苦茶》。
〔11〕胡经之 张首映:《西方20世纪文论史》第255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2〕同〔1〕。
〔13〕鲁迅:《呐喊·自序》。
标签:散文论文; 文化论文; 庞培论文; 张锐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周作人论文; 乌篷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