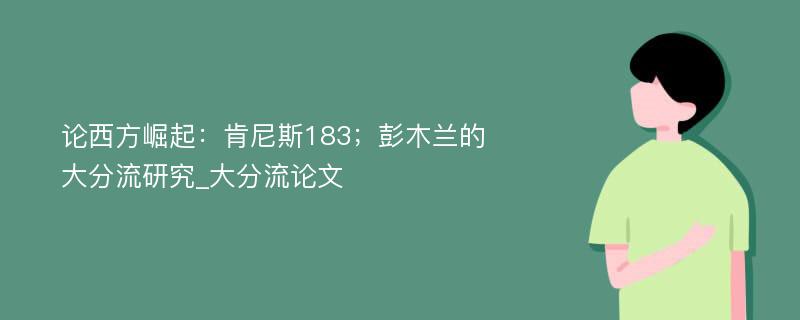
论西方的崛起:肯尼斯#183;彭慕兰的大分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肯尼斯论文,慕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欧洲与中国的大分流
欧洲何以能于19世纪从世界文明大国中崛起,避免了“马尔萨斯陷阱”?这是一个难以琢磨的基本命题,曾激起了无数学者的兴趣。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获奖无数,是这场争论中的一本力作,赢得了广泛好评,在最近一波寻求解释1800年左右西欧与亚洲经济差异著作中最具挑战性。尽管文献数量以及来源众多,《大分流》并非没有经验主义缺陷。我们需要对该书论据的结构做出清晰的评价。它主要包括以下五个相关命题。
1.至迟到1750至180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欧洲相当。
2.中国的土地、劳动力(可能还有资本)市场,与欧洲同样有效率,抑或更高。
3.虽然欧洲人均拥有更多的牲畜,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农业收益,在土地节约方面直到19世纪仍位居前列。
4.18世纪,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必然会向工业突破方向发展。
5.英格兰之所以脱离短缺与限制,率先于19世纪实现工业化,主要基于两个生态或地理因素,即廉价和充足的煤炭和新大陆未开垦资源的供应。
我认为,如果第3、4条观点正确的话,则对欧洲中心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观点1如果被证实,则是对18世纪中国马尔萨斯印象的一种否定。观点2尽管挑战了认为欧洲因为有比较规范的市场而更发达的新古典主义观点,但它仅表示中国和欧洲有相当的商业化水平和经商技巧,不能告诉我们未来经济的增长方式和创新水平。
传统观点认为,在18世纪欧洲已经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增长道路,如果该书不能反驳这一点的话,观点3、4、5同样不具有说服力。彭慕兰认为英格兰在1800年前和中国相比并没有很大的技术优势,特别是在能源技术方面,欧洲在1800年前面临着严重的限制。在1850年前欧洲农业生产力没有实质性的转变。这是该书论题的关键所在。
通过对第3、4观点的文本分析,并在参考二级文献的基础上,我认为这些观点缺乏实质性的经验主义支持。18世纪欧洲并没有面临任何主要的生态限制,或资源紧张和回报降低迫使农民更加辛勤地劳作。相反,在1700至1850年间,西欧大部分地区(始于英格兰)由于土地和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改善,正逐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二、马尔萨斯生也晚
彭慕兰的第4个观点,即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在1800年前面临严重的生态局限,可能与他阐述的第1个观点相矛盾,即18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经典的马尔萨斯式社会。他在第3个论点中关于欧洲农业的低亩产量和未充分利用资源方面比中国效率更低的论述也存在矛盾。既然欧洲有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为什么不用它来降低人口压力。
1.法国与德国没有受到土地限制
彭慕兰非常希望(和需要)得出结论认为,欧洲,至少是西欧(而不仅仅是英格兰)与中国一样,经历着农业回报逐渐减少,资源成本逐渐增加的发展路径,西欧和中国在18世纪晚期进一步增长的空间都很小。他知道,西欧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能满足他论证的要求,因此很快从这个判断后退。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他认为法国比中国更远离于新古典主义理想当中的开放市场。
西欧不能通过增加劳动力强度和使用土地开发那些未充分使用的资源么?彭慕兰想让我们相信,欧洲农业的性质使它不可能充分开发这些可能性。那么刚才所引用的格兰瑟姆的话又是什么意思?或者像彭慕兰对德国做出的相似判断,即1800年后,由于旧制度对土地利用限制的结束引起休耕地剧减,出现了一个向新作物和市场导向的农业的明显转变。彭慕兰的回答是,劳动集约型改变不可能为满足19世纪新增长的人口与其他压力而迅速方便地动员起来。我们相信法国和德国的农业实践在1800年后仍没有任何改变么?在这个最要紧的问题上,彭慕兰似乎对格兰瑟姆在其他地方的论述和托马斯(Thomas Nipperdey,1996:217)对德国的认识很满意。这就是彭慕兰想说的,西欧在1800年遭受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1750年前,法国经济的确容易受到全国性生存危机的影响。战争,与气候有关的食物短缺,以及流通困难,很容易转变为死亡危机。随着1720年后生产力迅速增长,危机逐渐减弱,直到一个世纪后消失。图泰(J·C·Toutain)所作的关于农业发展趋势的统计认为从17世纪初到 1780年代,农产品总额增长了约60%,而人口增长了28%,这或许太乐观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彭慕兰用来支持自己悲观论点的拉杜里(Le Roy Ladurie 1975:13; 1982:174)认为,18世纪,法国人口第一次打破了1700万到2000万的最高限度,这在1320年到1720年很少达到。一个更为现实的估计是法国农产品的增幅在1710到1789年是30-40%。他认为这种产量的增长不仅是一种普通的正常提升或恢复,而是一种预示新时代的增长。
如果我们将焦点局限于法国的发达地区如巴黎盆地或者诺曼底临近布雷特维尔的地区,情况似乎更好。比较一下盆地的粮食供应和城市人口,霍夫曼估计18世纪晚期粮食供应以每年0.46-0.53%的速度稳步增长,而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仅为每年0.39%。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 2002:16-17)观察到,即使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喧嚣年代,法国一些地区,如莱曼、鲁昂等,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增长。格兰瑟姆观察到,法国北部许多地区,包括比较贫困地区,小麦产量在1750年到1850年持续增长,而日均消费量在逐渐减少。
法国农业机械化和合成肥料的使用是1840年之后的事情。那些过去是牧场地、沼泽地、高沼、休耕地的减少,新的谷物混种的引进,使产量从1750年到1840年的增长成为可能。草料种植的大量应用,使牲畜从1815年到1835年增加了50%。这怎么可能是一个资源被耗尽,所剩余的内部资源无法动员的社会呢?
19世纪的德国,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可能没有超过人口惊人的增长速度,但它的确成功地满足了人口增长的需要。像法国一样,德国在这一时期有足够的增长空间。彭慕兰关于欧洲土地利用模式是它不能充分利用所开发资源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1816年到1852年,通过耕种以前废弃的土地、减少休耕地,以及牺牲草地牧场为代价,普鲁士的耕种土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1807年至1721年的施泰因和哈登堡改革后,一种全新的农业资本关系系统建立起来。根据理查德·梯利(Richard Tilly)的观点,结果是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增加。彭慕兰坚持认为这种增加是以加大劳动强度为代价的,在个人平均所得上没有任何明确的增长。他错误地把德夫里斯“勤劳革命”的观点与黄宗智(Philip Huang)清代中国经济产量和交易的扩大是“内卷”的观点等同起来,所谓“内卷”是指它依靠的是不断投入更多不计报酬的家庭劳动,每单位的劳动收益很小(并且不断萎缩)。他显然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当德夫里斯阐述现代英格兰的“勤劳革命”时,他是指家庭愿意更加努力工作、牺牲休闲时间来增加他们对新消费产品的供给与需求。这与黄宗智阐述的观点完全不同,黄说,由于每单位劳动所能获得商品量在减少,中国的农民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
彭慕兰引用了一些有意思的数据来说明尽管总劳动时间在1500年到1800年增长了,但是欧洲的生活水平只有很小的增长。1850年之前德国工资没有改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这个弱工会时代,绝大部分人的收入和消费都被资本家的积累压榨了。由于这一时期生产力的显著增长,我们很难接受人口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经济增长,甚至使它难以维持的观点。梯利补充道,工资的压力与收入转向资本投入份额的增加相伴而生,高收入所占份额显著增加,更确切地说,收入高低主要受资本收入的影响,收入的重新分配对投资和增长率有直接的影响。
2.农业革命和英格兰旧马尔萨斯制度的终结
彭慕兰认为英格兰早在1750年,未充分使用的资源已很少,或者说有待开发的闲置资源已非常少。他坚持认为,英格兰在18世纪木材始终短缺,钢铁工业处于下降状态,尽管有关税收保护,以煤为基础的生产也开始出现实质性紧张,从瑞典和俄罗斯的进口大幅上升。好像是为了说明燃料更加短缺一样,英国经济在1815年蒸汽机的全盛期之前,人均使用的以煤为基础的能源已经超过了800万大卡。
更令人苦恼的是英国农业,到18世纪晚期,它似乎到达了顶峰,如果没有一个主要的技术突破,产量进一步增长已不可能。从1750年到1850年亩均产量和总产量处于停滞状态。彭慕兰得出结论,如果没有煤和殖民地的双重利益,英国会面对一种没有明显内部解决方案的生态绝境。
彭慕兰想说的是到1750年,英格兰遭遇了严重的生态局限。关于生产力在1750年到1850年没有很大改善的观点,他主要依靠乔治·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文章《1250年至 1860年英国农业的亩产量:来自劳动力输入方面的证据》。1850年后的数据,他主要依靠毛罗·安波索里(Mauro Ambrosoli)1997年的著作。在安波索里关于英国农业产出的一般评论中,没有人反对1750到1850年农业革命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次农业革命结束于约1850年,紧跟而来的第二次革命主要基于技术发现。克拉克的估计也不像彭慕兰一样悲观。他认为,在1600年前长期维持中世纪水平后,英格兰的小麦产量从1600到1800年间似乎稳步增长,从1770年 (而非1750年)到1860年的产量增加没有前两个世纪多。18世纪产量收益约为30%,而 1800到1860年仅为15%。
这一发现似乎暗示,到1770年,英国面临着亩产量的进一步增加更难取得的境地。但是,我们在绝大部分文献中发现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尽管农业革命的时间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并且基于不同计算方法的调查结果所做的估计也各不相同,但是各原始资料所透出的信息却很清晰:在1550到1750或1900年,英国农业生产力经历了实质性的、加速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
罗伯特·阿伦(Robert Allen)认为早在1520年开始,在产出和生产力方面就有前所未有的改变,但是,扩张的速度在18世纪下半叶大幅缓慢下来。他认为奥佛顿(Mark Overton)地区总量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阿伦估计,从1700年到1850年,小麦和燕麦产量分别提高了 78.1%和66.7%。霍德尼斯(B·A·Holderness)认为,在1750年到1850年间,小麦亩产量增加了56%。哈德森(Hudson 1966:66)估计,从1800年到1914年,小麦产量从每英亩20蒲式耳增加到36蒲式耳。为什么彭慕兰仅仅依靠一篇论文的估计,就认为产量在1750年后保持不变呢?
对于1700年到1850年的工人平均劳动产出增长也有不同的看法。布伦特(Liam Brunt)认为,在1705年到1750年,劳动力产出几乎翻番,但是此后劳动力产出长期维持不变。这或许是因为某些土地生产力的增长趋向于劳动力使用而非劳动力节约。到16世纪,可用的新土地数量已非常小。因此,增加产出需要更多的劳动密集型活动。奥佛顿观察到,这种劳动密集型活动主要发生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
尽管某些因素增加了对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劳动力投入要求,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因素抵消了这一趋势并把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首先是耕作牲畜的更广泛应用,以及中世纪以来马逐步取代了牛,理论上马比牛的工作速度要快1.5倍,能够替代劳动力要求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原来分散的土地被合并成大块的土地。从17世纪中期开始,普通工人逐渐被农田专家所取代。第三是对现有工具的革新,包括1600年东部英格兰出现的更轻的“荷兰犁”,轻便可翻转的罗瑟勒姆犁,以及高产、抗疾病的种子和播种机的逐渐推广。根据布伦特的观点,这些是1750到1850年推动生产力的基本因素。
彭慕兰认为,英格兰人口的扩张与食品价格的上涨相伴而生,因为农业部门无力维持足够高的产量来满足需求。奥佛顿对此表示了强烈置疑。他认为,英国在18世纪经历的农业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增长导致了一个新历史局面的产生。旧的人口增长和食品价格增长之间的马尔萨斯式联系不可避免被打破了。
3.关于生活水平的争论
彭慕兰仍然可以反驳,所有可用的估计都显示出19世纪英国的人均粮食供给是停滞或下降的,直到19世纪,英格兰普通百姓的粮食购买力并没有得到改善。但是,这是他没有对证据权衡就草率做出的另一个结论。有证据表明,19世纪上半叶,人均食品消费并没有很大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些方面如城市居住环境(由于拥挤的和不卫生的住宿条件)和工厂工作环境(由于更加艰苦和快速的劳作)在工业革命时期甚至恶化了。但同样有大量证据表明,虽然成年男性工人的平均工资在1790年到1820年基本保持不变,但是之后却稳步上升。彼得·林德特 (Peter Lindert)和杰弗利·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甚至认为,在1820到1850年间,实际工资几乎翻了一番,尽管这一改善随后又下跌了62%。即使最悲观的克拉克也认为,1820年后,男性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保持了适度而是持续的上升趋势。
当然,这一估计主要依赖于成年男性工资指数,忽视了女性工人和传统工匠的真实收入,而这些人处于受损失的地位(Mokyr,1992:128; Hudson,1996:31)。查尔斯·菲尔斯汀(Charles Feinstein)使用平均年收入指数(包括男性和女性工人),发现工资从1778-1782年到1853- 1857年实现了低于30%的缓慢增长,这不能视为英国是马尔萨斯社会的证据。对这一缓慢增长更合理的解释是经济发展收益的不平等分配的结果。尽管在工业革命头50年收入分配的争论仍未定论,但是彭慕兰努力使我们相信,欧洲比亚洲的收入分配更不均匀。
是什么导致了不平等?1750年后由于人口的超高速增长导致廉价劳动力膨胀、食品原材料需求及价格的上涨,从而恶化了生活条件。人口的运动事实上是资本逐步聚集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这一过程的一个部分。在阿伦关于南部内陆地区农业革命的研究中,他相当肯定地指出,“农业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利益由于地租的提高到了地主的手里”。
威廉姆森后来也注意到了他所谓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共领域失败”以及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由于倾向于私有化投资和上层阶级的消费,一些公共事业比如排污、供水、消防和公共卫生等严重供应不足。自1834年的“穷人法律改革法案”以后,用于穷人救济上的花费从占国民收入的2%降到了1%。这种降低,“事实上使最穷那部分人的收入降低了7%到10%”。
三、欧洲真的享受了新大陆资源的“生态暴利”么?
彭慕兰认为西欧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对新大陆的开发逃出了原始工业的死胡同,这使它不必动员数量巨大的追加劳动力,这些追加劳动力是以更为集约且在生态上可以维持的方法利用欧洲自己的土地所必需的。我们不能说,彭慕兰对美洲的“土地节约型进口”如何帮助解除西欧的局限没有提供任何解释,但他的考虑只适用于英国。
1.蔗糖进口和甜菜糖替代
即使在英国的案例中,我不认为彭慕兰对新大陆的进口是英国克服土地短缺很有必要的观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他认为英国从美洲进口的最重要的土地节约型产品是糖、棉花和木材。他计算了1830年进口这些产品获得的总“鬼田”,约在2500到3000万英亩,这个数字超过了英国农田和牧场的总和。但问题是假定英国有土地的限制,即使它不能从美洲获得这些产品,它是否需要用自己的土地来生产。彭慕兰忘记了欧洲最终通过进口替代的相似过程最终减弱并打破了对蔗糖的依赖。在18世纪末,德国、匈牙利、法国的化学家和农学家发现了从甜菜中提取糖的可行办法和种植栽培甜菜的方法。此后,欧洲的甜菜糖产量与加勒比海的蔗糖产量在世界糖总产量中的比重发生了颠倒变化。我们很难说有多少甜菜糖被英国人所消费,但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对彭慕兰的估计提出怀疑,普通英国人饮食中糖在卡路里摄入量中的比例从 1800年的4%增加到1901年的超过18-22%。正是同一时期,英国食糖进口的来源地区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英属西印度群岛转向了欧洲。
2.木材进口:波罗的海和美洲
表面上,相对蔗糖进口,北美木材进口对英国来说重要性更大一些。之所以说“表面上”,是因为这一论断隐藏了一个假设,即为了获得所需木材供应,英格兰和西欧“需要”一个像新大陆一样的贸易伙伴。彭慕兰知道,东欧包括波罗的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俄罗斯,在生态上也有能力出口大量谷物、木材和其他土地集中型产品。但仍然坚持这些地区增加出口的能力受到了以下限制:当地农民绝大部分不是自由的,并没有处于向西欧出口的市场当中。换句话说,他们的经济是生存导向型的,这限制了西欧对它的初级产品的支付能力。斯堪的纳维亚大部分地区农民是自由的,但他们的数目不足以购买很多东西。听起来似乎很奇怪,新大陆的奴隶解决了消费不足问题,克服了欧洲的马尔萨斯幽灵。奴隶不仅便宜,他们的产品也不贵,而且他们不生产自己所需的食品和衣服,因此是非常重要的进口市场,特别是廉价的棉线,这代表了英国向西印度出售的大部分产品。
彭慕兰关于木材重要性的案例很快遭遇到了困难。如他所说,英国在1800年前从北美大陆进口的木材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又迅速补充道,到1825年,从这一地区进口的木材相当于 100万公顷欧洲森林。我们疑惑英国经济怎么能够在18世纪用如此“微不足道”的进口木材资源取得我们上边所看到的生产力增长。彭慕兰当然可以回应,后来木材进口的增长是19世纪可以减少土地限制的关键因素。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断,但是我们首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观点,即东欧、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在它可以出口到英国的木材和其他土地节约型商品上受到了内在的局限。彭慕兰在其他地方写道,在1750年代从瑞典和俄罗斯进入英国港口的船运总量超过一半都是木材,杉木进口从1752年到1792年增长了700%。当他写到这些的时候,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会在接下来的某些地方说明东西欧贸易的“关键性的内在局限”,而欣然写道,尽管有关税保护,从俄罗斯和瑞典进口剧增。
所有西欧国家潜在或实际上都是波罗的海初级产品的顾客。彭慕兰关于这一贸易在1650年后达到了顶点或者稳定下来的观点仅适用于运往荷兰港口的谷物。波罗的海国家完全有能力供应西欧和英国的初级产品,北欧国家和俄罗斯一样迫切地希望出口大量的木材。当英国明确自由市场将最好的服务于其国家目标,降低了波罗的海木材的关税,到1849年终止了航海法案,瑞典木材出口在1850年代的头5年就增加了50-60%,此后还有更高的增长。尽管远洋运输技术有所革新,但自由贸易的转变导致了英国从北美大陆(包括美国)进口木材比例的持续下滑,而欧洲的份额则大幅上升。
3.棉花进口和贸易条件
我们很容易被彭慕兰的以下估计所影响:养足够多的羊代替英国从新大陆输入的棉花制成的棉线,需要的土地数量令人无法相信。但我们知道,尽管为了棉线饲养绵羊需要广阔的土地,但是在棉花生产地区,如美国,棉花并不是土地集约型产品。即使英国被迫为其他地区的棉花付出了很高的成本(这些可能并不是必需的,因为与世界供给相比,棉花的需求已缓和了),由于英国纺织工业这些年的显著革新和组织转变,它很有可能支配了世界市场。新世界的国内市场对英国出口是重要的,但并不像彭慕兰所说的那样大。在1820年,欧洲仍是英国棉线的主要进口商。美洲作为整体在1820年到1896年从来没有占到过英国棉线出口的30-35%。不仅因为西印度群岛的人口很少,而且在美国南部的许多奴隶也自己生产他们的食品和衣服。欧洲对殖民地原材料需求和美洲对欧洲制成品需求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改进造船技术和降低运输费用的结果。
四、廉价的煤炭是充足的还是必需的?
如果新世界对英国不是“生态暴利”,那么煤炭呢?当煤炭每年产出超过1000万吨时,它的使用不是18世纪末英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么?假如英国与中国处于同样的境地,没有廉价和方便的途径获得这种资源,需要增加多少英亩的森林来满足煤炭工业每年的能源产出?彭慕兰提供的数字是以百万计算的。在英格兰,以木材为基础的能源形势十分严峻。在17世纪的后三分之二年代,有明显迹象表明英国的钢铁工业由于木材短缺的加剧而放慢了速度,从瑞典进口的条形铁数量逐渐增长。在钢铁工业能够再次稳步增长之前,英国需要学习如何从煤炭中获取焦炭。如果没有亚伯兰哈·达比(Abraham Darby)1709年使用焦炭生产铸铁的想法和亨利·科特(Henry Cort)1784年生铁转换为熟铁的想法,英国钢铁工业的未来就很不确定了。但是,煤炭使用的增加带来了问题,即矿井的逐步加深以及把水排出矿井所需动力的增加。这一困难导致了1712年纽克曼蒸汽机的发明,它是一种活塞式蒸汽机,效率极差,燃料耗费极高,应用受到了限制。在它的设计和建造方面接下来的改进几乎不能带来“煤炭突破”。直到1765年瓦特发明了单独的冷凝器,蒸汽动力才成为了工业革命。
彭慕兰的观点是导致纽克曼蒸汽机转变为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的条件是非常意外的。英国集中建造蒸汽机是因为大自然已给它带来足够的煤炭资源,使开发在财政上完全可行。他坚持认为,我们不应当认为蒸汽机的潜力在当时是明显的。早期的瓦特蒸汽机修起来非常昂贵,而不能与廉价的水力技术相媲美。
彭慕兰是对的,但还需要解释,矿产替代有机和水力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尽管如此缓慢,但为什么仍能增加工业产出。换句话说,假如英国的传统经济扩张空间很小,我们怎么来解释以下事实:直到1860年,50%的生产力增长来自于经济当中的非机械化部门。这表明,廉价的煤炭不是英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主要突破的惟一因素。还有其他工业化发展的“少煤路线”,假如英国在矿产资源方面没有那么幸运,它将更多依赖水力,就像法国那样。
缺乏可以转换为焦炭的煤以及面临着交通成本是煤炭价格两三倍的地理位置,法国比他的富煤邻居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水力。尽管英国人,如约翰·史密顿(John Smeaton)对水车做出了大量改进,但是法国人在把这种能源从传统工艺转变为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19世纪上半叶,法国人对水力技术做了一系列改进。到1845年水力装置提供的马力是蒸汽动力的三倍。尽管1850年前蒸汽动力的缺失,法国经济表现仍相当好。在丢失了北美殖民地,加勒比海地区糖产量从1787年的12.5万吨下降到1815年的3.6万吨的背景下,法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取得了增长。
法国的案例清楚地表明,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煤炭的替代品并把它作为工业所需能源的补充。毕竟,像荷兰一样的“贫煤国家”在17世纪许多工业当中,通过完全依靠泥炭作为热力也能取得了例外的成功。这不是低估英国煤炭相关技术的革命性意义。就像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强调的,英国蒸汽机的发明开创了一种新的、更高产的生产模式。这种发动机使热能转换为动能成为可能,完全是一种新型动力,比法国在丝绸和碱金属生产方面的改进具有在更广阔的经济中有更广泛的应用和更大的潜力。
五、结论:中国的“生态暴利”怎样?
与西欧不同或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在1750年到1850年人口翻了一番,谷物产量与此保持了同步,人均收入停滞下来,对传统经济的变革没有打下一个基础。彭慕兰承认这一点,他写道:1800年到1850年间,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可能并没有很大改善(即使不是全无改善)。但是他错误地认为欧洲也是同样的走势。他的整体观点是,1850年后中国而不是欧洲出现了生态和经济问题的恶化,仅是因为中国没有欧洲人从新大陆获得的特别生态施予和廉价煤炭供应的好运。
汉学家彼得·珀杜(Peter Perdue)在他对《大分流》的评论中说,幸运的欧洲,正常的中国。但是一旦我们仔细审阅本书,而不是夸大其内容,那么彭慕兰的地理和生态视角是多么的有偏见就变得很清楚了。地理在他的论述中只有在它表明欧洲是内部和外部生态资源的受益者时,或者中国没有享受到任何地理上的好处时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假如英格兰在利用煤炭能源方面取得了突破,它是“地理环境的幸运”的作用;假如中国不能发展蒸汽机,即使他理解大气压力的基本原理,那是因为它的煤炭供应与它的经济中心相距太远;假如欧洲有更多的闲置资源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由于它早期未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讽刺性的收益”;假如中国有更少的未使用资源和更小的发展空间,那是因为它对资源更高效的利用;假如欧洲有更多的草原和牧地可转为可耕土地,这是因为这些土地水源充足,是原始的恩惠;假如中国不能将它的残留草原转为可耕土地,这是因为它不幸处于半干旱气候。
事实上,中华帝国并不是不正常的。在广泛的生态因素范围内,它是例外的,远比欧洲幸运,不仅在于它继承的内部资源是一种原始的恩惠:湿米作为一种植物,与其他谷物相比,能每年在同一土地上种植,并可以一年两到三收。而且它在从1500年后的领土扩张中享受了真正大量的“生态暴利”。彭慕兰认为,中国不可能像欧洲从与新大陆的强制贸易中那样从长距离贸易中获益,这使我们认为现代中国是一个没有任何帝国野心的社会。
为什么彭慕兰如此热心计算欧洲从跨大西洋的殖民地当中享受的生态好处,而对现代中国的帝国扩张却保持沉默?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资源中的绝大部分来自其向西南和中亚的扩张,我们应如何评判他的以下观点:中国在寻找缓解土地集约型资源短缺的地方性方法时比欧洲做的更好?
假如英格兰幸运地可以方便地获得煤炭供应,那么从广泛的甘蔗种植中获益的中国南部热带地区又当何论呢?亦或由于湿润的气候能够大量种植棉花的中国许多省份呢?“幸运的英格兰”不得不跨越大西洋去获得大量的棉花和蔗糖供应,究竟是欧亚大陆哪一地区在资源上享受到了最大的“生态暴利”?
因篇幅所限,译者做了压缩,参考文献略。——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