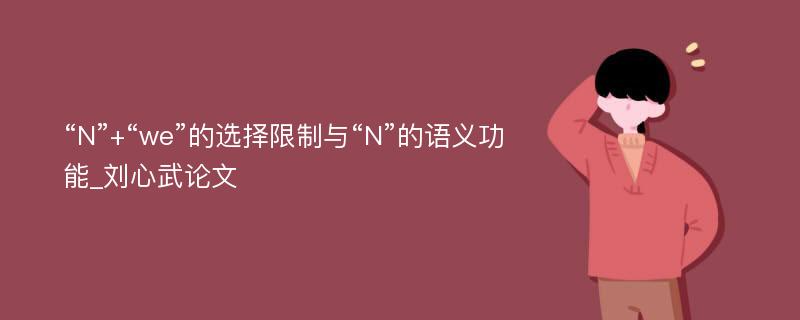
quot;Nquot;+“们”的选择限制与“N们”的表义功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用论文,quot论文,Nquo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 引言
迄今为止,语言学界对"N"+“们”(注:现代汉语中存在着同形同音的两个“们”:“们[1]”主要表示各种群体义,“们[2]”主要表示各种词汇义;“们[1]”的附着对象是任意的、开放的,“们[2]”的附着对象是固定的、封闭的;尽管都具有黏着、定位、后附的特点,但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本文主要讨论“们[1]”,有关“们[2]”的情况,请参看张谊生、张爱民(1991)。)的认识,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a.附在指人名词后面表示“复数”或“多数”;b.附在专有名词后面相当于“等人”;c.附在指物名词后面构成修辞格;d.可以附在名词性联合短语后面;e.不能与表示确数的数量词语共现。(注:可以以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0年)为代表。)上述观点自然有其符合汉语语言事实的一面,然而,这些认识都是在比附了印欧语复数形式的前提下得出的,似乎不很确切,也不够全面;尤其是没能切中“们”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就其主要表达功用看,作为一种非形态的分析性语言,汉语的“们”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表示“复数”范畴的语法形式,而是一种相对灵活的强调“群体”特征的表义手段。我们感兴趣的是:“们”对"N"的附着究竟具有哪些选择限制?“们”与不同的"N"黏合之后到底又有哪些表达功用?
本文所说的"N",主要指各种类别的名词,偶尔也指名词性偏正短语。
一 “们”对"N"的选择
1.1 音节选择
在音节方面,由于“们”是一个黏着的后附成分,缺乏独立性,在语流中常常以轻声短音的弱化形式出现,这就对"N"的音节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其选择性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们”一般不宜附着在2+1的三音节"N",譬如“两面派、乡巴佬、目击者、教唆犯、不倒翁、暴发户、布衣交、工薪族”等词语的后面,尤其是一些以“人”为中心的三音节词或短语,譬如表国籍的“中国人、美国人”,表地域的“北京人、乡下人”,表年龄的“老年人、青年人”,表职务的“庄稼人、主持人”,表品行的“老实人、老好人”,表特征的“明眼人、意中人、有心人”,表关系的“局外人、代言人、候选人、继承人”等,都不宜构成“2+1+们”这样的语音结构。例如:
(1)还要引导他们注目于更广阔的世界,使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产生兴趣,具有更高的分析能力,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们),……(刘心武:《班主任》)
(2)的确,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迎送往来以及别的什么屁大的事,都可以成为中国人([*]们)大吃大喝的理由。(刘心武:《高雅的话题》)
我们曾经统计过50多万字的刘心武作品,其中出现“年轻人”30多次,无论是否表示“群体义”,没有一例使用“们”的。例如:
(3)有让一群带红袖章的年轻人([*]们)推搡着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去游街的;有让亮得能照出人影的小轿车接出去又送回来的。(刘心武:《小墩子》)
再比如,《余秋雨散文集》中的《上海人》一文,“上海人”这一词语出现达80余次之多,其中表示群体概念的“上海人”就有70余例,没有一例是附加“们”的。(注:这也同该文的“上海人”多是通指的有关,具体分析请看本文1.3节。)例如:
(4)近代以来,上海人([*]们)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余秋雨:《上海人》)当然,这种限制也不是绝对的,我们偶尔也发现这样的用例:
(5)园主是财主,而喜艺术。他死后,继承人们组织了委员会,把园子作为招待艺术家来创作的地方。(老舍:《大地的女儿》)
其次,除了“人们”一词十分常见之外,“们”一般也较少出现在单音节"N"之后。(注:参看胡裕树(1985)。)例如:
(6)停战了。困在浅水湾饭店的男女们([*]男们和女们)缓缓向城中走去。(张爱玲:《倾城之恋》)
(7)着热的虱子们兴奋起来,沿着将士们([*]将们/[*]士们)的脊背蠕蠕往上爬。(张廷竹:《支那河》)
不过,“单音节N+们”较少见到,并不都是因为“们”不宜附在单音节之后,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现代汉语中指人的单音节"N"大多已经语素化了。譬如上面的“男”、“女”现在已成了名词性语素或者区别词了,都不能单说了;“将”、“士”作为名词,也已经很少单用了。事实上,一些未语素化的单音节"N",譬如“兵、贼、迷、鬼”等,在一些作者的笔下,偶尔也有附加“们”的:
(8)他准知道,兵们又得退却,而且一定往山中去。(老舍:《骆驼祥子》)
(9)无奈面孔太熟,常常被人认出,于是乎书架前一心看书选书的“迷”们,转而为他所“迷”,悄悄地,看他买什么书。(钱雯:《读书就是生活》)
“官、头”等儿化之后也可以加上“们”。例如:
(10)大哥一天到晚跟文学家们,官儿们在一起,……我们不敢求巴结。(老舍:《方珍珠》)
(11)连头儿们也停止了说话,人们一齐望着我们。(王朔:《永失我受》)
总之,在语音方面,“们”对"N"的音节构成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但其限制并不是十分严格的。
1.2 语义选择
在语义方面,由于“们”主要是表示“群体”概念的,所以对"N"的语义具有较严格的限制。
首先,“们”通常不与具有下列语义特征的"N"搭配:
a.部分非量名词。如“个人、旁人、世人、皇家、官方、女方、双方,浪子、笔者、当局”等。非量名词都不受数量概念修饰、限定,其内在的非量属性同“们”的“群体义”是矛盾的。如:
(12)……所以当今皇上对他(北静王)最放心,也打算在将其他近支皇族剿灭后,留下他并当众演示情深谊重的场面,以掩世人([*]们)攻击诟骂之口。(刘心武:《贾元春之死》)
b.部分集体名词。如“人类、人群、人物、人马,家人、门人、众人、国人,大众、公众、民众、群众,帮派、党派、反派,家族、部族、种族、民族、异族、外族,军队、部队、团队、连队”等等。此类集体名词的“群体义”是固化的、凸显的,所以不能再附加“们”。
(13)新上任的改革家,铁腕人物,第一招就是对那些调皮捣蛋的人物([*]们)实行“炒鱿鱼”。(刘心武:《公共汽车咏叹调》)
c.部分关系名词。如“亲家、本家、冤家,情敌、政敌,敌人、爱人,知音、知交,对头、对手,近亲、远亲、至亲,世交、至交,相知、相识,伴侣、情侣,连襟、妯娌、搭档”等等。关系名词重在显现相互之间的对等关系,而这种对称性语义特征同“们”的“群体义”自然是不相容的。(注:逆向关系名词可以带上“们”表示交互义,参看本文2.1节。部分关系名词用于指称时,也可以加“们”,譬如“同学们”、“朋友们”。关于关系名词,请参看张谊生《交互类短语与连介兼类词的分化》,《中国语文》1996年5期。)例如:
(14)当然,在自己家中或几个知己([*]们)在KTV包房中唱卡拉OK,也许会把所宣泄的感情表达得更从容、更精致、更舒畅。(刘心武:《你哼的什么歌》)
其次,“们”不能附在表示确数义的"N"之后。(注:在早期现代汉语,尤其是译文中,曾经出现过确数词语加“们”的现象。比如鲁迅《爱罗先珂童话集》和《小约翰》等翻译作品中,就有“两个孩子们”、“二百零一个女人们”、“一千二百匹飞蝇们”的说法。)例如:
(15)原来,有三千名太学生([*]们)正拥挤在刑场边上请愿,要求朝廷赦免嵇康,让嵇康担任太学的导师。显然,太学生们想以这样一个请愿向朝廷提示嵇康的社会声誉和学术地位。(余秋雨:《遥远的绝响》)
再比如,下面两个“弟弟”所指完全相同,后用“们”而前不用,就因为该"N"含有确数义:
(16)他还有三个弟弟,他母亲给人家帮工当佣人,弟弟们就得由他照顾。(新凤霞:《傻二哥》)
需要指出的是,“N们”虽然不能同表确数义的数量词语共现,但却可以同表示概数义的词语共现。“N们”与表概数的词语共现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A.一+集体量词+“N们”。例如:
(17)他笼络着一群他所认为可以做喽罗的大夫们。(曹禺:《明朗的天》)
(18)“……都是一些个庄稼汉们,谁又懂得什么?”(梁斌:《播火记》)
B.这/那+集体量词+“N们”。例如:
(19)朱老忠……看着这群满腔心事的孩子们。(梁斌:《播火记》)
(20)……那些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们容许你们再抗日么?(毛泽东:《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C.概约性数量词+“N们”。例如:
(21)统舱里全是空铺,只有三五个人们。(鲁迅:《准风月谈·“推”的余谈》)
(22)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挂过来,叫做“发扬国光”。(鲁迅:《拿来主义》)
这些概数表达式同“们”共现其实是一种词语搭配的羡馀(redundancy)现象;纯粹从逻辑的数量概念看,这些“们”都是多余的“重复”,因为前面的词语都已显示了“群体”概数义;然而,如果从交际的表达效果看,这些“们”又是必要的“呈现”,因为它们进一步强调和突出"N"的群体性,可以起到配合的作用;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们”是一种强调群体的表义手段。
1.3 语用选择
“们”的基本功用是表示“群体义”,然而,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使用“们”往往要受到语言环境和语用表达的各种因素的制约。据考察,主要有互有联系的以下三个方面。
A.陈述与指称。陈述和指称是语言单位作为信息传递载体所表现的两种基本的交际功能。一般情况下,谓词多用于陈述,体词多用于指称;然而,作为一种非形态语言,有相当一些汉语的体词也可以用于陈述,谓词也可以用于指称。既然陈述是用于表示行为、性状的,那么陈述义同群体义自然不能兼容;所以,凡是用于陈述的"N",一律排斥使用“们”。
(23)论年龄,她们几个都快老太婆([*]们)了,可学电脑上网的热情一点也不亚于青年人。(《新民晚报》1999.12.3)
(24)我校七七级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现在全都讲师([*]们)了。(《青年文摘》1988年4期)
至于用于指称的"N",那还要看究竟是用于背称的还是面称的。凡是用于背称的,既可以使用附加式也可以使用零形式,只是表达的语用效果略有不同而已。试比较:
(25)学生们差不多已把脚站木了,台上还没有动静。(老舍:《四世同堂》)
(26)学生[ ]差不多已到齐,但天安门前依旧显得空虚冷落。(同上)
上面两句说的是同一批学生,一句用“们”,一句不用,基本语义要同;差异在于“N们”更强调和凸显"N"的群体性。如果仔细辨析它们之间细微的区别,还可以发现:前句着眼于学生的整体,“差不多”指学生“脚”“木”的程度,后句着眼于学生的个体,“差不多”指学生“已到”的范围。
用于面称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一般都必须使用附加式。比如下面两句中的“同志们”和“先生们”,如果使用零形式就会被误认为现场只要一个“同志”、一个“先生”:
(27)于是我打算结束整个评选工作,环顾了一下全室,例行公事似地问:“同志们(试比较:[?]同志)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刘心武:《我爱每一片绿叶》)
(28)别怪我脾气不好,先生们。(试比较:[?]先生)(邓贤:《大国之魂》)
此外,背称和面称还有一个区别,如果指称的是多项并列的两个或多个"N",那么,背称一般多用联合式;而面称大都只能使用分述式。试比较:
(29)除了华夷之分的敏感点外,其他地方他倒是比较宽容,有度量,听得进忠臣贤士们(试比较:[?]忠臣们、贤士们)的尖锐意见和建议,……(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
(30)领袖(委员长)今天特意身着戎装,……他缓缓环视来宾,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沉重口吻说道:“尊敬的先生们,朋友们(试比较:[?]先生和朋友们):……”(邓贤:《大国之魂》)
B.内涵和外延。内涵是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指的对象的范围。任何一个名词性成分,都具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然而,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说话人对某个"N"的使用,则既可以显现内涵,也可以凸显外延。试比较:
S[,1]你是父亲么?父亲有跟女儿这样说话的么?(曹禺:《雷雨》)
S[,2]这时候,她父亲的财产全丢了。她非嫁人不可。她把自己卖给一个阔家公子,为的是供给她的父亲。(老舍:《微神》)
上面前两个“父亲”主要显现内涵,意谓“威严、正统,对子女尽抚养教育之职,具有男子汉气概”等,后两个“父亲”主要显现外延,意谓“某一个有子女的成年男子”。很显然,“们”的“群体义”同名词的外延义是相容的,同内涵义则是抵触的。所以,凡是显现外延义的"N",一般都可以附加“们”,反之,凡是显现内涵义的"N",一般都不能附加“们”。试比较下面四个“朋友”:
(31)朋友们看出我的悲苦来,眉头是最会出卖人的。(老舍:《微神》)
(32)真羡慕广州的朋友们,院里院外,四季有花,而且是多么出色的花呀!(老舍:《内蒙风光》)
(33)据我看,一个人即使承认英国人民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和他们交朋友([?]们)。(老舍:《英国人》)
(34)我真想不出,彼此不能交谈,怎能成为朋友([?]们)。(同上)
据观察,现代汉语名词表示内涵义主要出现在以下这些句位中:偏正结构中的属性成分;判断结构中的类属成分;述宾结构中的从属成分。我们发现,"N"的分布选择正好在上述三种句位上都受到了较强的限制,基本上都不宜附带“们”。例如:
(35)我利用到竹叶胡同访问学生([?]们)家长的机会,搜集着有关的消息。(刘心武:《班主任》)
(36)因为是学生([?]们),因为他们的目光曾与一个个汉字相遇,因为他们的手指曾翻动过不多的纸页,他们就要远离家乡,……(余秋雨:《千年庭院》)
(37)“四人帮”给咱们造成了些什么样的学生([?]们)啊!(刘心武:《班主任》)
C.有指和无指。从篇章分析的角度看,所谓有指(referential),是指实体(entity);所谓无指(nonreferential),是指属性(property)。一般情况下,凡是有指的"N"大都可以自如地附加“们”,而无指的"N",作为一种属性,无所谓群体不群体;所以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N们”中的"N"几乎都是有指的。试比较:
(38)还给学生们安排什么活动呀?忆苦饭都吃过两回了!(刘心武:《班主任》)
(39)总之,不管是什么派,只要是学生([?]们),也包括一时没有被打倒的青年教师,大学的,中学的,乃至小学高年级的,……悉听尊便。(余秋雨:《千年庭院》)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当一个"N"的所指具有下列两方面因素时,才是典型的有指:说话人所指的事物是一个单个实体——单指(individual),而不是指称整个的一类——通指(generic);说话人发话时心中已确知该实体的存在,听话人能够在具体的语境中辨识出该实体——定指(identifiable),而不是一种难以辨识的不确定客体——不定指(nonidentifiable)。所以,即使同样在有指的情况下,只有那些典型的有指——单指和定指的"N"才更适宜后加“们”。而那些非典型的有指——通指和不定指的"N"则一般不宜后加“们”。试比较下面四句,分别是单指与通指、定指与不定指:
(40)科学家们正密切注视着实验的进展。/儿童们围着花坛在做丢手帕的游戏。
(41)科学家([?]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儿童([?]们)是我们祖国的花朵。
(42)一堵壁画,加上壁画前的唏嘘和叹息,才是这堵壁画的立体生命。游客们在观看壁画,也在观看自己。(余秋雨:《莫高窟》)
(43)卫生间还是没有水,我把所有的水龙头拧开,出门去寺前闲逛,旅行车又拉来一批批新到的游客([?]们)。(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据我们调查,现代汉语中典型的有指"N"在实际言语中的分布概率依次是,主语>宾语>定语,同样“N们”的出现概率也是主语>宾语>定语,尤其是主语,占有绝对的优势。我们统计了钱钟书、刘心武、余秋雨三位先生近一百万字的语料,(注:钱钟书《围城》、《猫》、《写在人生边上》,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刘心武《刘心武选集》以及《白牙》、《曹叔》、《多桅的帆船》等。)发现:“N们”总共出现355次,其中主语276次,宾语(包括介词宾语)38次,定语22次(此外,还有兼语19次),比率大致为23.8∶1.9∶1.1。由此可见,“N们”的有指倾向是相当强烈的。其实,有时即使所指完全相同——都是定指,说话人也倾向于主语用“N们”,宾语用"N"。例如:
(44)大人们忙忙碌碌。顾不上孩子了,孩子们自由了。(航鹰:《老喜丧》)
(45)可是他回头看看战士,战士们低着头,满身是汗,……(刘白羽:《火光在前》)
有些"N"尽管说话人是清楚的,但从受话人的辨识角度出发,还是初现用"N",回指用“N们”:
(46)十来点钟的时候,门外鞭炮大作,客人都拥向栏杆往下看热闹,只见鼓乐吹吹打打,一顶篷轿随着出发了,这是去接四叔那个孩子的。于是客人们的兴致更加高涨,都称赞今天的喜事办得气派。(司马言:《没有儿子的母亲》)
对于“N+们”的选择性限制,尚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这几方面的限制并非互不关联、互不相涉的,而是常常互相牵连,互相影响的;其次,由于表义需求极为复杂,“们”的使用与否又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这些限制只是一些明显的倾向,而不是绝对的规律。
二 “N们”的表义功用
在现代汉语中,“们”的表义功用同它的分布具有密切的联系:同一个“们”,附在不同性质、特征、类别的"N"后面,可以具有不同的语义关系、结构关系和表达功用。
2.1通名与专名
从"N"的指称对象看,“们”既可以附在普通名词上,也可以附在专有名词上。无论是“通名+们”还是“专名+们”,都可以分别表示一系列各有特色的功用。
“通名+们”可以表示三种语义关系:群体义、连类义和交互义。
a.群体义是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不计确数的同类聚合关系,这是现代汉语“们”所表示的最普遍、最常用的语用义。例如:
(47)不过,更让学生们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刘心武:《班主任》)
我们认为“通名+们”是强调“群体”的表义手段,而不是表示“复数”的语法形式,是因为汉语的“通名+们”同该通名的具体数量之间并没有内在的、确定的关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非强调群体的"N",即使是复数,也可以而且经常不用“通名+们”形式。例如:
(48)学生[ ]也反映他讲课清晰易懂,“没有一句废话”。(同上)
两例所指对象完全相同;由于这例不强调“学生”的群体性,就没有必要用“们”。
其次,"N"逻辑上的单数或复数同言语中“们”的使用与否并没有必然联系。例如:
(49)人民大会堂前的欢迎仪式已经结束,官员们和外宾[ ]乘着黑色的豪华轿车,在摩托车的开道下,鱼贯驶出。(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官员”和“外宾”都不止一个,之所以前用后不用,是因为:如果只用一个“们”附在“外宾”后面,就会把“官员和外宾”这两个群体归入同一个群体之内,而用两个“们”又显得啰嗦、拗口。
b.连类义是以某人为代表的相关人物的同类聚合关系,通名一般较少表示连类关系。如:
(50)族长们便立刻照预定计划进行,将他叫到大厅上,先说过一大篇冒头,然后引入本题,而且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鲁迅:《孤独者》)
这里的“族长们”并非指由多位族长构成的一个同类的聚合,而是指以族长为代表的本族的一些亲戚。连类关系的使用对语言环境的依赖特别强,这“相关的其他人”必须在上下文中有一个明确的交代,读者或听话人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信息下面,才能顺利地理解。试比较:
(51)校长们都没在这里。(老舍:《微神集·大悲寺外》)
(52)所有这些,都凝聚着高亭镇名誉校长们的心血和汗水,显示了渔村尊师重教的崭新风貌。(郑忠德:《高亭镇名誉校长们》)
同样都是“通名+们”,前句是连类关系,指校长及其诸位同僚;后句是群体关系,指镇上的多位校长。而这种区别仅仅依靠“通名+们”本身是难以分辨的,关键还是要依赖于特定的语境。
c.交互义是指一种相互之间彼此对等的同类聚合关系,其"N"多为逆向关系名词或短语。
(53)夫妻们在自己卧房里有时免不了说玩话:小二黑好学三仙姑下神时候唱“前世姻缘由天定”,小芹好学二诸葛说“区长恩典,命相不对”。(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54)父女们在平日自然也常拌嘴,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了,不能那么三说两说就一天云雾散,因为她已经不算刘家的人了。(老舍:《骆驼祥子》)
表交互义的“们”都可用“俩”替换,也可以改用“之间”,不过表义方式和语用重点有所不同。
“专名+们”可以表示两种语义关系:连类义和比况义。
a.专名连类是以某个或某些特定人物为代表的同类聚合,用专名+“们”表示连类关系在早期现代汉语中是比较常见的。例如:
(55)祥子们擦擦汗,就照旧说笑了。(老舍:《骆驼祥子》)
(56)辛楣们忙着领行李,大家一点,还有两件没运来,同声说:“晦气!”(钱钟书:《围城》)
严格地讲,用专名表连类实际上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隐含式的,专名只是其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或代表人物,其余的、次要的人物都隐含了,譬如上面两例中的“祥子们”、“辛楣们”均是。另一种是概括式的,用两个或几个专名尽可能概括同类的所有人物。例如:
(57)李将军,向三元,丁副官们的气,我受够了!(老舍:《方珍珠》)
(58)他不明白以汪逆的名望与地位,会和冠晓荷李空山蓝东阳们一样的去想在敌人手下取得金钱和权势。(老舍:《四世同堂》)
隐含式和概括式的“们”都可以换成“等”、“等人”、“之流”、“之类”,概括式的“们”还可以换成“他们”、“她们”,但换用之后不但结构关系不同,而且所表示的同类聚合义也会淡化甚至消失。
b.比况义是一种与"N"具有相似性的类比或类推的同类聚合关系。例如:
(59)于是,临江市的诸葛亮们,小道消息分析家们,幸灾乐祸的预言家们,业余星象占卜家们,街谈巷议,莫衷一是。(李国文:《花园街五号》)
(60)走在前面的,是我的伯父、父亲,和他们崇拜的“专心于事业”的摩根们,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大群他们所雇佣的工人。(张贤亮:《绿化树》)
上面的“N们”就是指像"N"那样的人们,“诸葛亮们”和“摩根们”就是“诸葛亮那样的聪明人”和“像摩根那样的大资本家”。细究起来,用专名表比况也有两种:一种是类比关系,“N们”的"N"在具体的语境中并不存在,其构成基础是“比喻”,上面两例均是。另一种是类推关系,“N们”不但指类似的同类聚合,还包括"N"本身,其构成基础是词汇学中的“泛化”。例如:
(61)清晨,刚刚送走了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还得迎来刘备们的马蹄。(余秋雨:《三峡》)
(62)老摩根会利用人的视觉误差把鸡蛋变大,我会利用人的视觉误差把打的饭变少;摩根们会盘算,我的算盘也很精。(张贤亮:《绿化树》)
这两例“N们”就是指"N"及其相似的人们。从联系和发展的角度看,类推关系既是连类和比况相连接的交叉形式,也是连类向比况发展的过渡环节。
上面“N们”的五种表义功用,表群体义是最基本的用法,而其他四种都是扩展的或引申的用法;表群体义所受的制约相对较少一些,而其他四种都要受到语境或语体的一定的制约。
2.2转指与本指
目前通行的参考书、教科书和语法书几乎都认为,“们”只能附在指人名词上,附在指物名词上是修辞用法。其实,现代汉语中存在着两种指物“N们”:一种是出于某种语用和修辞需要的转指用法,一种由于语言类推作用而形成的本指用法。
转指法就是指字面上是“物类+们”,实际上还是表示“人类+们”。又可以分为三种:拟人、借喻和借代。拟人是把物当作人来描写,句中总有一些与人类行为或性状有关的词语。
(63)昏雾中间,只有风哭,雪笑,植物们叹气,蛰虫们合噤。(林如稷:《将过去》)
(64)星星们——在他眼中——好似比他还着急,你碰我,我碰你的在黑暗中乱动。(老舍:《骆驼祥子》)
上面的动词“叹气”、“合噤”、“着急”,代词“你”、“我”都是被临时用在“物”之上的。借喻是把人当作物来描写,句中虽然只出现喻体,但本体在上下文中是清楚的。例如:
(65)他像一匹被人弃舍了的老马。任凭苍蝇蚊子们欺侮,而毫无办法。(老舍:《四世同堂》)
(66)再加上在低成长时代中,公司业绩不振,那群创造高度成长的工蜂们不论多么努力冲刺也属枉然。(《海外文摘·日本男人的三大杀手》)
恶霸地痞被比作“苍蝇蚊子们”,勤奋的工人被比作“工蜂们”,这在文中都有交代。借代是换一种说法,与借喻的区别是,借喻的"N"同本体具有相似性,借代的"N"同本体只有相关性。如:
(67)她们的死,不过像在天边的人海里添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一些味道,但不久还是淡、淡、淡。(鲁迅:《论“人言可畏”》)
(68)在报社培训那阵子,我一天干16小时,想感动“上帝”,夺取“护照”,周围一帮眼镜们也火上浇油,……还联名向惜才如命的总编大人写推荐信。(《青年一代·啊!护照》)
“嘴巴们”用来替代那些爱说闲话的人们,“眼镜们”则用来替代那些戴眼镜的同事们。其实,拟人也好,借喻也好,借代也好,从认知的角度看,都是通过“物+们”的转喻(metonymy)方式来转指具有相似或相关特征的人们。需要指出的是,指物名词的转指并不完全依赖于“们”的使用,相反,正是因为运用了转指手法,才使得“物+们”的组合显得既贴切自然,又生动形象。
本指法就是字面上是“物类+们”,实际上表示的也是“物类+们”。也可以分为三种:动物、植物、事物。动物加“们”的用法,细分起来包括走兽、飞禽、鱼虾、昆虫等等。例如:
(69)她的一声尖锐而细长的呼叱,把狗们的狂吠阻止住了。(老舍:《四世同堂》)
(70)鸟雀们费力地扇动着淋湿的翅膀,急急忙忙投进落光了叶子的小树林里。(张贤亮:《绿化树》)
(71)冰块软化,……对虾们裸露出来,透着肉色。(江灏:《纸船》)
(72)小蚂蚱们蹦起来,“噌噌”地飞到架子的最顶端,又向着一边逃去了。(张炜:《秋天的思索》)
相对说来,植物加“们”的用例还不算多。例如:
(73)所谓“半空儿”,是那种入不了干果店、一头瘪一头有一粒小小果仁的花生。……卖半空儿的老爷子们,眯缝着笑眼,伸出大手,抓一大把半空儿,一边往上提,一边缩小着手指头聚拢的空间,令人馋涎欲滴的半空儿们,一个接一个航天飞机似的“由空中返回地面”。(苏叔阳:《傻二舅》)
(74)那岁数比我爷爷都大的柏树、杨树们,死尸似的一根根倒在草窝里。(苏叔阳:《我的一天》)
事物名词加“们”则又可以分为物品和现象两类。例如:
(75)小茶馆们已都上了门,十点多了。(老舍:《骆驼祥子》)
(76)现在流传的古镜们,出之家冢中者居多,原是殉葬品。(鲁迅:《看镜有感》)
(77)课文对于闺女们虽然深不可测,但老有爹讲得明白,学生对字们也认得死。(铁凝:《棉花垛》)
从音节的角度看,单音节的指物名词比指人名词要多得多,在一些作者的笔下,不但“狼、猴、猪、羊、狗、牛、鸡、鸟、猫、鱼”等可以附上“们”,甚至连“船、蜜、霜、露”也可以加上“们”:
(78)他照例把七八只绵羊往河滩的草丛里一撒,……羊们就啃起草来。(赵金九:《乡村酒肆》)
(79)不远的一排猪圈,猪们在吃饭,吱吱呀呀拱叫不已。(王朔:《过把瘾就死》)
(80)为了山的陪衬,船们显得庞大一些……(肖军:《羊》)
(81)就说那些粉红的、浅黄的、奶白的“蜜”们、“霜”们、“露”们,看一眼也如见了妇女用品商店橱窗里那些越做越招人胡思乱想的乳罩们、连裤袜们。(陈建功:《卷毛》)
如前所述,语言学界迄今大都不承认指物名词的本指用法是符合汉语习惯的规范用法。我们认为,此类用法虽然还不很普遍,但却不容忽视。“物类+们”本指用法的产生和发展既是语言接触的必然结果,也是语言表达的现实需要——其产生无疑是受到了印欧语复数表达方式类推作用的影响,其发展又与现代汉语表达方式日趋精密化、多样化的自身需要密切相关。
2.3联合与聚合
在现代汉语中,“们”除了经常附在单词"N"后面以外,有时也可以附着在短语"NP"之后。“NP们”在结构上比“N们”要复杂,可以组成结构层次和语义关系都不相同的两种形式:并归联合式与类同聚合式。并归联合的基本模式就是“N[1]们+N[2]们”→“NP们”。例如:
(82)一座繁华的都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事情不仅会引起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浓厚兴趣,而且对不管相隔多少年之后的普通老百姓也永远是一个巨大的悬念。(余秋雨:《脆弱的都城》)
上面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就是“历史学家们+考古学家们”的并归和省略。同样,如果前面"NP"有一部分相同或相近,也可以同时并归"NP"。例如:
(83)总公司的干部们在这种情况下调薪无望,司、售员们当然不可能再提高收入,整个系统的福利待遇只能维持在低水平上。(刘心武:《公共汽车咏叹调》)
“司、售员们”就是“司机们+售票员们”的并归和省略。其他如“指战员们”、“演、职员们”等等也都属此类,这是最常见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中也存在着少数非归并的联合式。例如:
(84)也不知是假不热还是真不冷,不过时髦男女们有一点是肯定的——派——挡不住的感觉。(阿留:《派的错乱》)
(85)在善男信女们的眼里,这巨石是上苍神力使然。(王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此类“NP们”的"N[1]"和"N[2]"都不宜拆开单用,“们”必须附在整个"NP"上面,所以“NP们”不是由“N[1]们+N[2]们”归并而来的,而是先组合、后附加的联合式。
类同聚合的基本模式是“N[1]+N[2]们”→“NP们”,也可以是“N[1]们+N[2]”→“NP们”:
(86)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掐死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
(87)据我伯父、父亲们的说法,……(金庸:《连城诀·后记》)
“夫儿们”指大堰河的丈夫和四个儿子,是“夫+儿们”,“伯父、父亲们”则是“伯父们+父亲”,所以都可以构成一个类同聚合。比较而言,“N[1]+N[2]们”式类同聚合更多一些。
联合式和聚合式也可以交替配合使用。例如:
(88)解放P城的野战部队的司令员、政委们,在地下市委的基础上刚刚充实起来的新市委的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们,原地下的学委、工委、农委的负责人们,早在战斗打响以前便组建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P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们……坐满了主席台。(王蒙:《布礼》)
“司令员、政委们”、“学委、工委、农委的负责人们”是归并联合式,而“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们”、“主任、副主任们”则都是类同聚合式,因为P城的“第一书记”和军管会“主任”都只有一个。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N们”表义功用的描写和分析,可以统一列表归纳如下:
类别小类关系
例子
群体义 N们=一群N或N[n] 学生们;同学们
通名+们 连类义 N们=N[1]N[2]N[3](N[4]) 族长们;校长们
交互义 N们=N[1]←→N[2]夫妻们;父女们
连类义 N[1]们=N[1]N[2]N(N[4]) 祥子们;辛楣们
专名+们 比况义 N们=(类似N)[n]诸葛亮们;雷锋们
融合义 N们=N+(类似N)[n]
摩根们;李白们
表拟人 N们与N具有比拟性 蛰虫们;星星们
转指用法 表借喻 N们与N具有相似性 苍蝇们;工蜂们
表借代 N们与N具有相关性 嘴巴们;眼镜们
指动物 N们指兽禽鱼虫等 鸟雀们;对虾们
本指用法 指植物 N们指树木花草等 半空儿们;杨树们
指事物 N们指物品现象等 茶馆们;古镜们
归并式 N[1]们+N[2]们→NP们
司、售员们
联合短语 组合式 (N[1]+N[2])们→N们
善男信女们
聚合式 N[1]+N[2]们→NP们主任、副主任们
三 结语和余论
3.1“们”的表义功用既复杂又灵活,不但可以显示或强调多种不同语义关系,而且还可以显示多种语用效果;其次,“们”的使用既自由又必然,从句法结构和语义关系的角度看,“们”的运用与否往往具有相当的任意性,然而从和特定的语境和语用需要看,又常常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再次,“们”的表达功用主要取决于其附着的对象和所处的语境,其表达方式和表义功用不但要受到其所附"N"的性质和义类的制约,还要受到特定的语用因素的限制;所以,严格讲,汉语的“们”,与其说是一种语法形式,不如说是一种表义手段。
3.2需要指出的是:限于篇幅,本文没能从发展的角度对现代汉语“们”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纵向的考察和分析。其实,据我们调查,半个多世纪以来,“们”的表义功用和搭配范围已经并正在发生一系列微妙的变化。大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从所表达的语义来看,呈现出越来越简的趋势:普通名词的“群体义”更趋普及,已占有绝对优势,“连类义”和“交互义”则日见稀少,接近于消亡;专有名词的“比况义”略有发展,日益增多,“连类义”则相对减少,逐渐萎缩。(注:《王朔文集》一至四卷(华艺出版社1994年)中没有发现严格意义上的表示连类义和交互义的“N们”。)其次,从所受到的限制来看,呈现出越来越少的趋势:指物名词后附“们”的本指用法近年来有进一步扩张和流行的趋势,不但在文艺作品、报章杂志中时有所见,而且在各种广播、电视、电影中时有所闻;“们”对"N"的音节限制也不如以前严格,单音节词、甚至三音节词后附“们”的现象有所增加。总之,现代汉语“N们”的表达功用正趋向简洁、实用,灵活、明确。
3.3长期以来,汉语语言学界在论及“们”的意义和作用时,总是以印欧语的复数形式作为讨论的依据。我们的体会是:同印欧语系诸语言的复数形式(譬如英语的"NS")相比,汉语的“N们”具有自己独特而又鲜明的个性特点。"NS"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基础的语法形式,其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一般不受"N"自身的语义性质和语用条件的影响;而“N们”的表义功用不但要受到其所附"N"音节、语义、语用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其所处语言环境的限制。无论是屈折变化还是分析形式,印欧语的复数表达式全都十分严格,而且所表语义明确而稳定;而“们”作为一种词汇化的分析形式,其使用与否具有相当的自由度,而且所表语义多样而灵活。总之,汉语的“们”同印欧语的复数形式之间虽然表面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其实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形式和表达手段:前者是一种表示语法范畴的严格的构形程式,后者是强调各种语用效果的自由的表达方式。
3.4近年来,随着西方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配价语法、系统功能语法、认知语法等流派和学说不断地被介绍和引入,汉语语法的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语言现象的解释,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理论意义。然而,我们觉得,比起西方语言学界对其本族语言事实的描写和研究,我们对汉语事实的发掘和归纳还是十分肤浅和粗疏的。解释固然非常重要,但当前首要的任务还是应该立足于汉语自身的特点,在真正融会贯通西方现代语言理论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对现代汉语中的各种语法现象进行更加细致、更为科学的描写和分析。我们深信,任何合理的解释,不仅需要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而且更需要准确而清晰的事实描写作为基础。
标签:刘心武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复数名词论文; 现代汉语论文; 文学论文; 班主任论文; 骆驼祥子论文; 父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