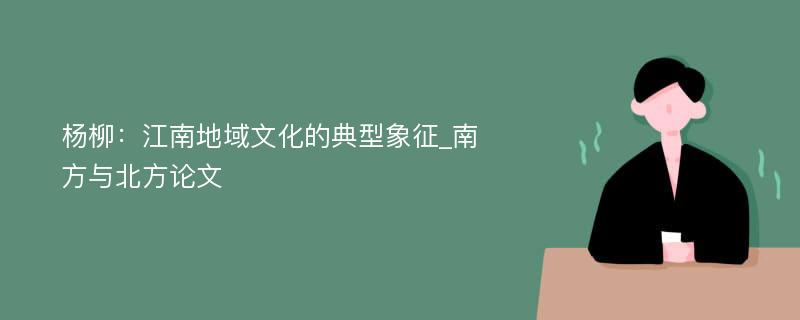
杨柳:江南区域文化的典型象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杨柳论文,象征论文,典型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7)02-0122-06
杨柳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意象,文学上经常吟咏的杨柳通常指的是现在的垂柳。提及杨柳,人们总会把它与烟雨楼台、小桥流水等秀丽的江南水乡风光联系在一起。但杨柳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江南风物的代表。先秦到汉唐,对杨柳的吟咏更多体现出北方地域文化色彩;中晚唐以来,杨柳意象才逐渐体现出江南地域文化色彩;到了宋代,杨柳意象基本定型,成为江南风景和文化的象征。这里的南北区域主要是以江淮为分界线的。杨柳作为江南意象,典型地体现了江南物华繁茂的富庶景象、水乡清柔的秀丽风光和歌儿舞女之乐的欢乐场景。
一、杨柳由北方意象向江南意象的转变
杨柳作为江南意象的重要代表,经历了一个由北方意象向江南意象的转变过程。早期作品中最常见的“杨柳”,如“杨柳依依”的描述,或“细柳营”的典故,多与北方风光和边塞战争相关联,杨柳意象具有浓厚的北方地域文化色彩。中晚唐以来,有关杨柳的经典描述,如“烟柳画桥”,“杨柳岸、晓风残月”,“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等,多与江南风光相联系。这种转变在杨柳题材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杨柳是我国较早开发利用的一个物种,在我国分布极为广泛,遍布大江南北。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周易·大过》就以“枯杨生稊”喻老夫得少妻,《孟子》亦有“性犹杞柳”之喻,《战国策》曰:“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1] 838《诗经》是我国北方文学的代表,《诗经》中大部分诗歌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诗经》中记载的植物种类繁多,有一百多种,杨柳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如《齐风》中的“折柳樊圃”,齐风是齐国的民歌,齐国在今山东境内。又如《小弁》中的“菀彼柳斯”,《菀柳》中的“有菀者柳”。《小雅》产生于周京畿地区,其中最有名的是《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对后世咏柳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采薇》是一首战争诗,诗中关于杨柳的描写是与具有北地色彩的风雪相联系,表达了士兵久戍思归之情。《楚辞》是我国南方文学的代表,多产生于湖北地区。楚地幅员辽阔,土壤肥沃,草木繁茂。《楚辞》中就出现了大量植物,如兰草、芰荷、白蘋等,却很少提及杨柳。我们知道,南方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杨柳的生长,《山海经》中多处出现柳。《中山经》曰:“又东南二百里,曰即公之山,……又东南一百五十九里,曰尧山,……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又东二百三十里,曰荣余之山,……其木多柳。”[2] 其中柴桑之山在今浔阳柴桑县南,与庐山相连。即公山、尧山、荣余山虽不能确定其具体位置,但肯定在南方,可见,柳在南方分布比较广泛。然而,在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中却没有发现柳的踪影。这就说明,先秦时期,在南方人们对柳的审美关注要晚于北方,杨柳从一开始就多出现在北方文学中,带有浓厚的北方地域文化色彩。
汉唐时期,杨柳意象也多体现北方地域文化色彩,这在汉魏时期的杨柳赋和乐府《折杨柳》中可以体现出来。
汉代,杨柳开始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专门吟咏杨柳的作品,这最早体现在杨柳赋中。自西汉枚乘的第一篇《柳赋》后,杨柳赋创作蓬勃兴起,在魏晋时期达到高潮。从作者来看,这些杨柳赋大部分出自北人之手。汉晋时期一共有九篇杨柳赋,分别是枚乘、孔臧、应玚、繁钦、王粲、陈琳、魏文帝、晋傅玄、成公绥之作。他们中除了枚乘、陈琳外,都是北方人。其中孔臧是西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繁钦是东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应玚是汉末汝南(今河南)人,傅玄是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成公绥是西晋东郡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人。从杨柳形象来看,这些作品或者突出了杨柳根粗干壮、枝繁叶茂的伟岸形象,如“巨本洪枝,条修远扬,夭绕连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或擢迹而接穹苍”(孔臧《杨柳赋》);或者彰显了杨柳旺盛的生命力,如“枝扶疏而覃布,茎森梢以奋扬”(王粲《柳赋》)。在汉赋作家笔下,杨柳更像是北方“伟丈夫”,充满阳刚之气。
除了柳赋之外,汉晋时期还出现了乐府《折杨柳》。《折杨柳》属于横吹曲,是“军中之乐”。《乐府诗集》载:“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3] 309《宋书》载:“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辞。”[3] 328《折杨柳》民谣传入北方少数民族后,产生了民歌《折杨柳歌辞》和《折杨柳枝歌》,这些民歌后被梁代乐府机关保存,收录在“梁鼓角横吹曲”中。北方《折杨柳》常与杨柳自身的形象相结合,如《折杨柳歌辞》:“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兒。”从中可以看出,杨柳在北方分布很广,其枝条可以用来当作马鞭,还可以用来制作柳笛,就是抽掉嫩柳枝茎中的木质干,留下茎皮,在茎皮一端略加修整即可吹响,犹如笛声,故叫柳笛或柳哨。北朝《折杨柳》表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自然风光、风俗习惯和北人刚劲勇猛的性格,自然具有北方地域色彩。
北朝乐府民歌《折杨柳》传入南朝之后,梁、陈君臣开始拟作,出现了文人拟作《折杨柳》的高潮。梁、陈文人拟作《折杨柳》虽然受齐梁绮艳诗风的影响,闺怨色彩浓厚,但闺中所思之人主要是征人,诗中常用意象、典故多同边塞、军营、战争密切相关,浸染了浓厚的北方边塞气息。如陈后主《折杨柳》:“武昌识新种,官渡有残生。还将出塞曲,仍共胡笳鸣。”其中“官渡”指的是官渡之战,据曹丕《柳赋》序曰:“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4] 1075此外,周亚夫细柳营也是乐府《折杨柳》常用的一个典故,如岑之敬《折杨柳》:“将军始见知,细柳绕营垂。”细柳营是汉代名将周亚夫屯军之所,据《元和郡县志》载,细柳营在今咸阳县西南二十里。因周亚夫治军严明,后常用细柳营或柳营作为军队的代称。
隋唐时期,两京尤其是长安种柳繁盛,宫廷、官署、庭院、行道、河堤等地多种杨柳以美化环境。这在文学中也多有反映。唐代边塞诗中多出现柳,如李益《临滹沱见蕃使列名》:“漠南春色到滹沱,碧柳青青塞马多。”乐府《江南曲》主要是歌咏江南秀丽的自然风光,在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江南》中,莲、白蘋等南方植物反复出现,其中“莲”22次(包括“芙蓉”5次),“蘋”7次,杨柳意象却一次也没有出现。这说明在时人心目中,杨柳并不像莲花、白蘋一样是江南风物的代表,杨柳更具北地色彩。
中晚唐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在描写江南风景的诗歌中开始出现杨柳,如刘禹锡《忆江南》:“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晚唐更是如此,如黄甫松《忆江南》:“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晚唐五代无名氏的《望江南》:“湖上柳,烟柳不胜垂。宿露洗开明媚眼,东风摇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环曲岸,阴覆画桥低。线拂行人春晚后,絮飞晴雪暖风时。幽意更依依。”这表明,在时人心中,杨柳成为江南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以来,文学创作的重心转移到南方,杨柳也随之成为江南意象的典型。有宋一代,词为之大盛。宋词可以说是南方文学的代表。据南京师范大学《全宋词字频表》统计,“杨”出现了1042次,“柳”出现了2864次,总数超过排名第二的梅花,“梅”出现的频率是2956次。另外,根据对《全宋词》《望江南》词牌的统计,词中“梅”出现的频率是15次,“莲”7次(包括“芙蓉”2次),而“柳”是22次,高于“梅”和“莲”。这说明,入宋以后,杨柳已经完全成为江南风物的代表。并且,在宋代之后的《江南曲》中,杨柳意象也频频出现,如明谢榛《江南曲》:“夹岸多垂杨,妾家临野塘。”又如清吴绮《江南曲》:“江南三月杂花生,江上游人春眼明。琪树家家栖海鹤,垂杨处处带啼莺。”可见,杨柳作为江南风景的标志已深入人心。
颇有意味的是,从此即使在北方看到杨柳,人们也会想起江南的秀丽风光。《帝京景物略》曰:“元廉右丞之万柳堂、赵参议之瓠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弥望间,高林疏柳,沿溪夹岸依依,有江南之色。”(《御定渊鉴类函》卷352)北京名胜万柳堂、瓠瓜亭、玩芳亭等,因河畔栽种杨柳,故使人想起江南风光。其中最有名的是万柳堂。万柳堂原是元代廉希宪的别墅,位于右安门外,清代大学士冯溥非常仰慕廉希宪,就效仿他在崇文区广渠门内另建别墅,亦名“万柳堂”。清毛奇龄《西河集》有记载:“万柳堂者,益都相公冯公之别业也,其地在京师崇文门外。……其外长林,弥望皆种杨柳,重行叠列,不止万树,因名之曰‘万柳堂’。”(卷127)万柳堂是京师文人宴游之地,风景秀美,时人多有吟咏。如清彭孙遹《奉和冯益都夫子秋日燕集万柳堂即席留别之作》:“清渠一曲荫修杨,秋气高寒晓欲霜。尘外心期在丘壑,樽前风物似江乡。”又如施闰章《冯相国万柳堂二十四韵》:“不向城东去,名园我未谙。争传雄蓟北,大好压江南。”万柳堂虽不在江南,但貌似江南,万柳如云、夹岸拂水的美景绝胜江乡风光,让人流连忘返。又《河南通志》载:“王九畴,字叙吾,邓州人,万历己酉举人。任华阴县,自潼关以西,植杨柳数万株,行人终日在柳阴中,时比之江东。”(卷59)江东即江南。潼关在今陕西境内,王九畴任华阴县令时,在潼关以西的道路两旁植柳万株,行人终日庇于柳荫之下,仿佛置身江南山水间,好不惬意。这些都表明,杨柳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为江南风景的标志。
二、杨柳转变为江南意象的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杨柳成为江南风物的标志之后,并不意味着北方没有杨柳。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温带和亚热带,杨柳又是温带亚热带植物,故其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均有广泛分布,甚至柳在北方分布更广。清汪灏《广群芳谱》引《木谱》曰:“(柳)北土最多,枝条长软,叶青而狭长。其长条数尺或丈余,袅袅下垂者名‘垂柳’。”[5] 1807又载:“北方材木全用杨、槐、榆、柳四木,是以人多种之。”[5] 1874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柳不是江南所独有的,可为什么却成了江南水乡的代表?
(一)跟北方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关。周秦气候比较温暖,北方植被茂密,许多亚热带植物如竹子、梅花等在北方都能生长,这在《诗经》中也有反映。相应地,杨柳在北方也比较普遍,《山海经》中也多有记载。《中山经》曰:“又西十里,曰廆山,……其木多柳。……又东一百五十里,曰熊山,……其木多樗柳。”[2] 其中廆山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南,熊山在今河南宜阳西,说明汉晋时期杨柳在北方分布很广。隋唐时期,两京生态环境良好,植柳繁茂,诗人多有赋咏,如宋之问的“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龙门应制》),崔灏的“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渭城少年行》)。中晚唐以来,气温降低,北方转冷,再加上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使得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整体衰退,杨柳长势渐渐不如江南。白居易《苏州柳》曰:“金谷园中黄袅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来处处游行遍,不似苏州柳最多。”金谷园在洛阳,是石崇的私家园林,曲江在长安,江畔栽柳,号称“柳衙”,二者都是北方著名的风景区。白居易有过南北不同的生活经历,他认为不管是金谷园中还是曲江亭畔的杨柳,都没有苏州杨柳茂盛。
相对于北地而言,江南气候温暖湿润,湖泊众多,更适合杨柳的生长,杨柳的分布也更为普遍,房前屋后、溪边桥头随处可见,如余延寿《南州行》曰:“摇艇至南国,国门连大江。中洲两边岸,数歩一垂杨。”又如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曰:“吾三吴人家,凡有隙地即种杨柳。余逢人即劝,令之拔杨种臼,则有难色。凡所利于杨者,岁取枝条作薪耳;取臼子者,须连枝条剥之,亦何尝不得薪也。”[6] 1066三吴指今苏州、上海一带,江浙人家凡有空隙之地都栽种杨柳。徐光启劝其拔掉杨柳,改种乌桕,因为乌桕的经济价值比杨柳大的多,不仅可以用作薪材,还可以用来做蜡烛和肥皂。但人们还是不肯拔柳种桕,可见杨柳深得江南人家之喜爱,被广泛种植。
(二)跟社会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有关。先秦到初盛唐,经济、文化的重心在北方,作家笔下的杨柳也多生长在北方,所以对杨柳的描写更多沾染北地色彩。自安史之乱后,北方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实力下降,而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则相对安定,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大量南迁的劳动力,江南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中晚唐开始,经济、文化的重心逐渐向江南地区转移,如明刘基《江南曲》:“江北风沙人住少,江南秔稻雁来多。”长期远离北方战火的江南,以其秀丽的自然风光、富庶的鱼米之乡,成为文人向往的人间天堂。北方文人由于漫游、隐居、避乱、赴任或贬谪等原因频繁出入江南,使得江南的文化优势得以加强,文学创作的重心也逐渐由北方向江南地区转移。江南自然湖泊众多,同时,江南经济发达,园林兴盛,园林中亦多湖景,而湖边多种植杨柳,著名的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都以植柳闻名。所以,诗人笔下的杨柳常常与水乡风光相联系,如明于慎行《江南曲》“萧萧烟雨秋江口,两岸青旗拂细柳”,又如张英《忆江南曲》“海棠树树堪铺席,杨柳家家好系船”,杨柳也自然成为江南地域风景的重要代表。
(三)跟杨柳品种结构的变化有关。人们对杨柳品种的关注经历了一个从实用到审美的过程。《诗经》中多次出现柳,历来关于《诗经》中杨柳种类的解释众说纷纭。其实,《诗经》中杨柳品种是很泛化的,属于广义的柳属。清姚炳《诗识名解》曰:“愚谓《释木》文柳类甚多,有河柳、泽柳、蒲柳诸名,而杨仅列柳之一,则杨为柳属,柳不可言杨属,明矣。说家多谓柳有小杨、水杨、垂杨之称,并未足据。”[7] 522《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传》曰:“杨柳,蒲柳也。”认为杨柳就是蒲柳。《尔雅》也有类似解释,《尔雅·释木》曰:“杨,蒲柳也。”清姚炳也认同这一点,曰:“《传》专释此为蒲柳,甚当,以其为柳属,故亦得称为杨柳,非兼言杨与柳也。今人不问蒲、泽之类,统呼杨柳,可哂。”[7] 524可见《采薇》之杨柳为蒲柳,并非后世文学中之垂柳。“依依”也并非“不舍”之意,《传》曰:“依,木茂貌。”那么,“杨柳依依”即为蒲柳茂盛之意,主要基于蒲柳的实用价值。蒲柳没有垂柳婀娜的身姿,观赏价值不高。蒲柳常生长在河滩上,北方较多。垂柳枝条细长,婀娜多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诗文中之杨柳通常指垂柳。垂柳喜水湿,《广群芳谱》曰:“百木惟柳易栽、易插,但宜水湿之地尤盛。”[5] 1859江南水乡水域众多,更适宜杨柳的生长,尤其是江湖之地。如杨万里《舟过桐庐》:“潇洒桐庐县,寒江缭一湾。朱楼隔绿柳,白塔映青山。”又如玄烨《宿迁》:“行过江南水与山,柳舒花放鸟缗蛮。”可见,沿途经过江南,无处不见杨柳。
三、杨柳作为江南意象的审美文化意义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江南不仅是一个区域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和美学概念。《乐府解题》曰:“江南古辞,盖美芳晨丽景,嬉游得时。若梁简文‘桂楫晚应旋’,(唯)歌游戏也。”[3] 384也就是说,江南在人们心目中,不仅具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更具有欢乐的人文风情。杨柳作为江南风景的重要组成要素,蕴含了丰富的审美内容,典型地体现了江南区域文化的美学意义。
(一)杨柳体现了江南物华繁茂之美。梁朝丘迟《与陈伯之书》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白居易《忆江南》曰:“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说明江南在时人心中是一派姹紫嫣红、生机盎然的繁荣景象,而红花绿柳是体现江南春天物色繁茂的重要元素。如吴潜《望江南》:“家乡好,好处是三春。白白红红花面貌,丝丝袅袅柳腰身。”花、柳在江南随处可见,遍布乡村,如“园庐渐以完,村村偏花柳”(陆世楷《白沃史君庙》)。陆游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经典描写,把花柳作为村庄的标志。不仅乡村,城市也都触目可见。《西溪梵隠志》载:“西溪有三桥,多植柳,浓阴夹道,东西两涯,民居临水,花木周庐,亦称花市。”(《浙江通志》卷280)本来花柳指的是美丽的春光春景,没有南北地域之分,北方也经常使用,如“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崔灏《渭城少年行》),“洛阳宫中花柳春”(冯著《洛阳道》)。但随着北方生态环境的恶化,植被的大量减少,春天柳树发芽比较迟,花开也比较晚,北方同南方相比,就显得萧瑟不堪,好像没有春天一样。难怪唐人有这样的体会:“怪得春光不来久,胡中风土无花柳。”(刘商《胡笳十八拍》)红花绿柳把江南水乡装点得绚丽多姿、如诗如画,花柳就成了江南美景的标志。杜甫曾把南方花柳同塞北雨雪对举,来比较南北两地自然风光的迥然不同:“北走关山开雨雪,南游花柳塞云烟。”(《赠韦七赞善》)中唐以来,这样的例子增多,甚至直接称杨柳为“江南柳”,如“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独知”(王智兴《徐州使院赋》),“春入江南柳,寒归塞北天”(周弘亮《除夜书情》)。可见,中唐以后,杨柳常与江南相联系,来描写清丽烂漫的江南春景,与寒冷萧瑟的塞北风光形成鲜明的对比。司马光就认为,陶渊明门前如果不种柳,就会使人觉得萧瑟,不堪居住:“天意清和二月初,春风不动整如梳。陶潜宅外如无此,想更萧条不易居。”(《垂柳》)陶渊明是晋浔阳郡柴桑县(今九江市西南)人,属于南方人,可即便是南方,没有花柳的装点也会显得枯寂。明张以宁鲜明地对比了江南和江北风光的极大不同,其《江南曲》曰:“中原万里莽空阔,山过长江翠如泼。楼台高下垂柳阴,丝管啁啾乱花发。北人却爱江南春,穹碑城外如鱼鳞。”可见,在江南物华饶美和江北空阔萧条的景物对比中,杨柳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二)杨柳体现了江南水乡清柔之美。江南水域众多,家家面水,户户枕河。“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杜荀鹤《送人游吴》)。而杨柳是湿生阳性树种,喜温暖潮湿的土壤,素有“水乡泽国”之称的江南十分适合杨柳的生长。故水滨池畔、桥头河岸多有种植,正如古人所言“芳草连山碧,垂杨近水多”。水和杨柳就构成了江南春天最普遍、最美丽的风景,寇准《江南春》曰:“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远,苹满汀洲人未归。”《小辋川记》载:“蓝田别墅前有池,渟泓一碧,左右垂柳交荫,颜曰:‘水木清华。’”[6] 1811杨柳枝条细长,微风吹来,摇曳多姿,同水中倒影交相辉映,美不胜收。宋钱易《南部新书》曰:“池四岸植嘉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8] 101故在园林景观配置中,水边植柳是花木和水的最佳搭配。而最能体现江南水木清华美景的,莫过于被誉为西湖十景之首的“苏堤春晓”:“起南迄北,横截湖面,绵亘数里,夹道杂植花柳,中为六桥,行者便之。”(《咸淳临安志》卷32)水边杨柳不仅在描写江南风景的诗文中多有出现,如“洛渚问吴潮,吴门想洛桥。夕烟杨柳岸,春水木兰桡”(崔融《吴中好风景》),而且在羁旅行役的诗歌中也经常出现,如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因为江南多水,出行多取舟楫,而江边堤岸又多是送别之地的缘故。
与北方风景的苍劲气貌相比,江南风景是一种清柔的美。就植物而言,描写江南美景多以梅柳、青枫、翠竹、荷花、白蘋、芦苇、蓼、菰等为主,描写北方则多以松柏、梧桐、槐、榆等为主。江南多水,水是至柔至弱之物,杨柳又适合在水边生长,且枝条细长,柔软下垂,典型体现了江南物色清柔之美,如欧阳修的“江南柳,花柳两相柔”(《望江南》)。江南乡村尤其如此,杨万里《舟过德清》曰:“人家两岸柳阴边,出得门来便入船。不是全无最佳处,何窗何户不清妍。”碧波荡漾,绿杨堆烟,小窗珠户,门前小船,以碧绿为主色调的景物给人一种清丽的感受,展现出一幅清丽柔美的江南美景图。南方多水,多桥,多柳,小桥流水与依依杨柳更像是江南水乡的风景。《明水轩日记》载:“净业寺门临水,岸去水止尺许,其东有轩,坐荫高柳,荷香袭人,江南云水之胜无以过此。”(《钦定日下旧闻考》卷53)净业寺在北京城内德胜门西,寺内风景明媚,有水有亭,高柳蔽日,荷香袭人,可谓北方之江南。
(三)杨柳体现了江南歌儿舞女之乐。杨柳常用来比喻美丽女子,柳枝柔软,女子的腰便称为“柳腰”;柳叶细长,女子的眉便称为“柳眉”。清王士禛引《徐氏笔精》云:“古人咏柳必比美人,咏美人必比柳,不独以其态相似,亦柔曼两相宜也。若松桧竹柏,用之于美人,则乏婉媚耳。”[9] 200以柳喻女子情态的词语也很多,诸如柳态、柳质、柳眠等。中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柳又与青楼女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咏柳作品中常以历史上有名的歌妓,如苏小小、柳氏等来比拟柳,如白居易《杨柳枝》:“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晚唐到北宋,“柳越发同青楼女子——这种具特定身分职业的风尘女性的居处相联:柳市花街、柳陌花衢、柳际花边……”[10] 66
值得注意的是,歌妓不为江南独有,北方也有。只是宋代以来,江南经济发达,生活富庶,都市繁荣,促进了歌妓的兴盛,歌儿舞女享乐生活就成了江南文化的重要特征。如张籍《江南曲》曰:“倡楼两岸悬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又如明皇甫汸《江南曲》曰:“锦帆西去绕横塘,画舸携来悉粉妆。旭日笼光流彩艳,晚云停雨凈兰芳。飞丝带蝶粘罗幌,吹浪游鱼戏羽觞。自是江南好行乐,采莲到处棹歌长。”凡歌妓活动之场所多莳花栽柳,花柳就不仅仅是美景的代称,更同青楼女子娱乐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柳永《笛家弄》:“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岂知秦楼,玉箫声断,前事难重偶。”故常用杨柳比喻江南歌儿舞女之享乐生活。柳永《望海潮》就真实再现了钱塘江畔杭州的繁华富庶,其中“烟柳画桥”不仅是对杭州街道风光的描写,更是杭州歌舞娱乐生活发达的写照。因为晚唐以来,垂柳、画桥经常同青楼女子住处联系在一起,如徐铉《柳枝辞十二首》:“此去仙源不是遥,垂杨深处有朱桥。共君同过朱桥去,索映垂杨听洞箫。”仙源指青楼,并非仙境,所以没那么遥远,它就在烟柳画桥之处,可见烟柳画桥往往成为青楼楚馆的标志。
综上所述,杨柳作为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意象,从先秦到汉唐时期,对杨柳的吟咏多体现北方地域色彩,晚唐以来却越来越具有江南水乡的气息。这不仅同北方生态环境的整体衰退有关,而且也是建立在社会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基础之上,同时和杨柳品种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杨柳作为江南意象,包含了物华繁茂、水乡清柔和风俗奢乐的象征意蕴,典型地体现了江南区域文化的美学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