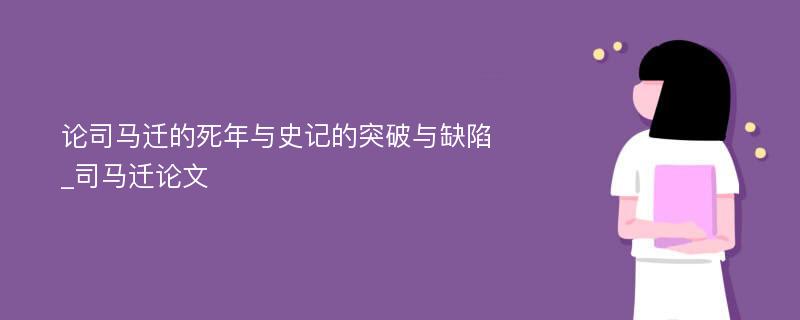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和《史记》的断限、残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司马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司马迁的卒年史书无明文记载,后人有各种各样的推断。我认为最重要的应根据《报任安书》来推断。通过《报任安书》,司马迁将自己长期隐藏在内心的冤屈和痛苦喷发出来,触怒了汉武帝。所以,汉武帝将“有怨言”的司马迁“下狱”处死。这是东汉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的记载。
现将有关司马迁卒年的一些旁证选择罗列于下: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全文引用《报任安书》之后,立即说:“迁即死”。又在传后的赞语中说:“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这就说明“报”书与“死”有密切关系。
裴骃《史记集解》在“七十”一句下,注引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进一步说明因“报”书中有怨言而死。
陈寿《三国志·魏志·王肃传》:“帝(曹丕)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这说明至晋代才有人敢于为迁抱不平,以前是皇家之大忌。葛洪《两京杂记》、桓宽《盐铁论·周秦篇》也记叙了相同的事实。
褚少孙在《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孝武封国”一语下说:“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故复修记孝昭以来”。这样,褚先生就将孝武封国的最后四侯,列在本表之后。说明四侯不是司马迁所记。如:田迁秋封富民侯是在征和三年六月后,中山王昆侈卒于征和二年,而《史记》没载。
王国维说:“《史记》中最晚之纪事,得信为出自公(司马迁)手者,惟匈奴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之事,余皆后人续补。”他认为《汉书》中《宣帝纪》和《丙吉传》之内谒者令郭穰,即《刘屈氂传》之内谒者令郭穰。亦即司马迁之继任者,“其时史公必已云官或前卒。”
综上所录,足以说明司马迁的死因死时了。
但是,关于《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王国维的考定影响很大,不弄清这个问题,司马迁的卒年是无法坐实的。
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考定在汉武帝太始四年。王国维说:“案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按指太始四年)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所云‘会东从上来’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时。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者也。是报任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或以任安下狱坐受卫太子节,当在征和二年,然是年无东巡事。《田书列传》后载褚先生所述武帝语曰: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报安书自在太始末审矣。”
其实,王国维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怎么解释“会东从上来”?“会”,正遇上。“东”,往东,等于说由西边。“从上”,跟随皇上。这句是指征和二年七月戾太子举兵后,司马迁跟随汉武帝自甘泉宫还长安的事。《汉书·武帝纪》载,征和二年“夏,行幸甘泉。秋,七月,按道侯韩说、使者江充等,掘蛊太子宫,壬午,太子与皇后谋斩充,以节发兵,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因此汉武帝闻讯,急忙从甘泉宫还长安。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武帝从甘泉宫还长安,是由西向东走。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是皇帝当然的随行人员,所以说是“会东从上来”。
关于这个历史事件,根据《汉书》有关传记的记载,大致是这样的:武帝末年,戾太子的生母卫后宠衰,江充用事。江充与戾太子及卫后家都有矛盾,恐怕武帝死太子即位后自己遭祸。恰在这时巫蛊的事情发生了,江充便利用这个机会陷害戾太子。武帝使按道侯韩说、御使章赣、黄门苏文,共同协助江充,到戾太子宫里掘出几个桐木人。武帝本来有病,在甘泉宫避暑疗养,请示也得不到回报。所以戾太子觉得情况可疑,就命他的客人搜捕江充等,并以“谋反”的罪名杀了江充。但章赣和苏文逃到甘泉宫,却在武帝面前诬告太子谋反。武帝马上命丞相刘屈牦发兵和太子交战,同时回到长安城西建章宫。当时戾太子召兆军使者护军任安,给以符节,叫他发兵助战。任安接受了命令,但闭门不出。戾太子和丞相大战的结果,死了几万人,战败逃走,在长安东面新安县附近的湖地自经而死。后经壶关三老和车千秋上书,说明了事实的真相,武帝感到后悔,于是“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并“怜太子无罪,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①。恰在这时,有一钱官小吏诬告任安当时对太子有所要求,所以闭门不出。这就触发了武帝的思子之情。他认为任安是戾太子舅父卫青荐举的,汉王朝曾多次提拔重用,他却“坐观成败”,未支持太子,罪不容赦,应该处以死刑。
而王国维认定“会东从上来”是指东封泰山,因而在《汉书·武帝纪》里找到了“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于是得出结论说“书所云‘会东从上来’者也”,显然是不符合作者愿意和历史事实的。
第二,如何解释“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旬月”,满一个月。“季冬”,十二月。汉律,十二月处决囚犯②。“薄”,同“迫”。“从上”,跟随皇上。“上雍”,上雍地去。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其地有五畤,汉武帝常到那里祠神。这句话是说,再过一个月,就进入处决囚犯的十二月了,那时我又迫于要跟随皇上去雍地。
王国维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他认为征和二年“无东巡事,又行幸雍在次年正月,均与报书不合”,所以把《汉书·武帝纪》太始四年“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硬扯到这里来。沈钦韩《汉书疏证》说:“任安怀二心腰斩,而犹须系至冬尽,则汉法之异于后也”。司马迁见武帝心情已变,任安非死不可了,但又不忍心说出任安将要在十二月腰斩,所以只在此暗示了一下,这种低徊哽咽的辛酸情绪,对任安不幸遭遇的痛惜心情,王国维竟弃置不顾,是很不应该的。是的,《汉书·武帝纪》是说“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但这并不是“与报书不合”。《汉书·武帝纪》说的是具体到达雍地的时间,而《报任安书》说的是迫于要跟随武帝去雍的出发时间,所以二者是完全相合的。
第三,王国维既肯定《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为太始四年,但又找不到太始四年任安犯罪的事实,只好将褚少孙补的任安事迹中,汉武帝说的“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③加以强相牵合,算是任安的罪状。但对“任安有当死之罪”是什么内容却答不出来。其实这话是征和二年,武帝诛任安时,“欲成其死,而加之罪”的愤恨之言,并无任何事实根据。任安是司马迁的老朋友,如果真有“当死之罪甚众”,以“信史”和“实录”著称的《史记》,为什么于任安受太子节一事外,毫无记载呢?任安并非武帝“幸臣”,为什么屡次犯死罪,而残忍寡恩、喜怒无常的武帝却要赦免他呢?因此《报任安书》说的“今少卿抱不测之罪”,的确是指征和二年七月任安受戾太子节一事而言的。因为这件事是在不久前发生的,所以作者才用了一个“今”字。而事件又直接牵涉到汉武帝,所以作者说任安受到“不测之罪”。王国维把这一确凿的事实当作不可信的,而自己的考定却没有确凿的史实依据,无法自圆其说。
第四,《报任安书》说“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又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这些话也可证明此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
任安被钱官小吏诬告的时间,史无明文记载;但从他触发武帝的思子之情来看,应当在壶关三老和车千秋上书之后。车千秋在什么时候上书,也是史无明文记载的;但车千秋从高寝郎晋升为大鸿胪,是由于“上急变,讼太子冤”④。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载,征和二年“九月,大鸿胪商丘成为御史大夫”。可见车千秋继商丘成为大鸿胪,其时当在征和二年九、十月内,而车千秋上书自然应在这之前了。由此可以证明,任安被钱官小吏诬告,一定是在九月到十月这段时间内。司马迁在戾太子举兵(征和二年七月)后,跟随武帝还长安,当在征和二年八月左右。不久任安就被投入狱中。这与“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的话完全相应。这句话是说,我们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始终勿忙急促,没有一点空闲。如果照王国维的说法,司马迁是在太始四年五月跟随武帝由山东回长安的,那么《报任安书》写于这年十一月,中间相隔七个月。七个月时间,两人同在长安,其时司马迁又没有什么事情,怎么能说是“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呢?
“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这句话,涉及到司马迁始仕为郎中究竟在什么时候的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此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又据《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西、沈黎、文山郡。”既然汉王朝在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那么司马迁以“郎中”身份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就决不会在元鼎六年之前,因为那时汉王朝还未“平西南夷以为五郡”。司马迁出使西南地区回来复命时,正是武帝“始建汉家之封”,也就是元封元年武帝封泰山的时候。而武帝封泰山是在当年四月,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司马迁是不可能在元封元年初的三个月内完成出使任务的,所以司马迁以“郎中”身份出使西南地区应该在元鼎六年,回来复命是元封元年以后的事了。由此可见,《集解》引徐广的话“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是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的时间,而“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司马迁“还报命”的时间。司马迁在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仕为郎中”,到写《报任安书》的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恰好渡过了二十一年的仕宦生活,所以这和《报任安书》中说的“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完全符合。如果照王国维的说法,《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即公元前93年,那就只能说“待罪辇毂下,十九年矣”,因为十九年是万万不能说成“二十余年”的。自然,王国维把司马迁“仕为郎中”的时间含糊其辞地说成“大抵在元朔、元鼎间”,但按他的意见,无论怎样推算,都与“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相矛盾。
第五,司马迁这封《报任安书》,是和自己的生死有关系的。卫宏《汉书旧仪注》和葛洪《西京杂记》都说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这“怨言”便表现在《报任安书》里。这封书,满腔愤怒,大发牢骚,说他为李陵“陈情”,是“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睢眦之辞”,结果“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言外是说,武帝贤愚莫辨,是非不分,袒护裙带关系,是一个专制残暴的君主。对于遭受“宫刑”,司马迁更是悲愤欲绝,痛不欲生。说什么“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对于汉王朝屠杀功臣,虐待大臣的行为,司马迁更予以大胆地揭露:“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子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这些无情的揭露,活画出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帝王的专制残暴,使人感到触目惊心。这些所谓“怨言”,可能后来被人抓住告发了,致下狱而死。司马迁还在《报任安书》里,告诉任安一个重要的消息:“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他的著作已基本完成了。但下文又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则证明《史记》又还未最后完成。那么,《史记》的最后完成当然是征和以后的事了。所以司马迁的卒年,自然是在写《报任安书》的征和二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如果照王国维的说法,《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则李长之、王达津等更据以断定司马迁就死在太始四年,那就更是错误的了。
总之,《报任安书》究竟作于何时,不仅关系到司马迁的卒年,还关系到《史记》一书写作所经历的时间与部分材料的真伪问题,因此这是一件值得考辨清楚的事情。
(二)
司马迁的卒年既然在汉武帝征和二年,死因是“有怨言,下狱死”。那么关于《史记》的下限问题自然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书》“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说:“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看来司马迁本人的说法就不完全一样。而《集解》、《素隐》、《正义》的《序》又都说“下讫天汉”。“麟止”就是汉武帝曾在雍(今陕西凤翔)狩猎一只白麟,所以改年号为“元狩”,又做钱币成麟的脚形。这里即指元狩元年。从元狩至太初,中间经历了好几个年号。为什么同一篇里出现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我们认为,这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可能是两个计划。起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计划,司马谈把写《史记》当成是续《春秋》,《春秋》的下限至于获麟而止,这可能是司马谈最初的计划。起于黄帝,至于太初,是其子司马迁修改后的计划。
至“太初而讫”是史迁记事的实际下限。太初之前,为元封六年(前105);太初之后,为天汉元年(前100)。由于“太初而讫”四字不够精密,因而又有人认为讫于元封六年,如朱东润《史记考索》,有人认为讫于天汉,如《汉书》及三家注。对此,我们既不能责怪史迁记事之疏漏,也不能苛求前人对问题的争辨。我们只能就《史记》的实际来考察。《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均讫于太初四年,便是明证。所以范晔《后汉书·班彪传》及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均说:“太初已后,缺而不录。”范文澜《正史考略》说:“太初以后事,则犹《左氏》之有续传也。”
《史记》记事为何要讫于太初?因为司马迁认为从元狩到太初是西汉鼎盛的一整个时期,所以把下限从元狩元年一直扩展到太初四年。据《汉书》,任安坐受卫太子节而下狱在征和二年,著名的《报任安书》即写于这年秋天。所以这之后的史事,很难确证为司马迁手笔。
回头我们再来谈关于《史记》的上限问题。司马谈计划起自陶唐,理由是:1.儒家的权威著作《尚书》的记事即起于尧,司马谈的计划是以《尚书》为典范,所以也要从尧开始。2.百家言黄帝,文字不够雅驯。“黄帝以来皆有年数”,这跟古文经典不相吻合,所以司马谈不相信那些百家言黄帝,更不相信年代说得那么清楚。因此要从尧开始。司马迁修改这个计划,提前到黄帝,也有自己的理由:1.司马迁“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走遍全国各地。他在游历考察当中发现,尽管各地的风俗教化不一样,但各地长老皆谈传说中的黄帝。这个传说尽管是口头的,但长老们谈得都比较生动,绝非凭空捏造。所以司马迁相信这些传说事出有因,认为黄帝这个历史人物确实存在。2.《五帝德》、《帝系姓》这些著作,司马迁相信是孔子所传的典籍,拿它来和《春秋》、《国语》互相参证,认为是可靠的资料。3.各种谱谍资料,百家言黄帝虽然“其文不雅驯”,但绝非无因。4.《五帝本纪·赞》说:“《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儒家的典籍中虽然有些东西没有记载,但黄帝的轶闻轶事时时见于其他著作。司马迁对古文资料,百家之言,长老的口头传说选择比较雅驯、符合实际的东西加以记载,对于那些不可信的资料,则弃而不录。所以司马迁修改了他父亲原来的计划,把历史记载从尧上推到黄帝。为什么只上推到黄帝而不再往前推呢?司马迁认为黄帝轩辕氏“修德振兵”──既注意自己品德的修养,又使用武力征伐来统一天下。《史记》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天子以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追祖溯源,他们都来源于黄帝这个系统。中华民族皆是黄帝子孙,这一民族观念就奠基于《史记》。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是司马迁修改《史记》上限的一个重要思想。
司马迁修改《史记》上限的证明是:
第一,司马迁本人有着明确的交代。《五帝本纪·赞》说:“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三代世表·序》又说:“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不论是《五帝本纪·赞》,还是《三代世表·序》都说从黄帝始,而不是从尧开始。
第二,《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最初由司马谈规划,最后由司马迁修改完成。《自序》里所说的和《五帝本纪·赞》、《三代世表·序》交代的完全相符,证明“自黄帝始”“至太初而讫”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符合事实的。司马迁对《史记》上限的修改既然有这样明确的交代,从中还可以看出他的修改有两条标准:1.相信文献典籍的记载。在《伯夷列传》中说:“考信于六艺”。《孔子世家·赞》说:“折中于夫子”。所以对《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尚书》等古文很推崇。2.他通过实地调查来补充、验证文献资料的记载。
(三)
现存《史记》不仅有断限问题,而且还存在着一个残缺问题。《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现存《史记》的字数却比原书要多将近三万字。由此看来,现存的《史记》绝非司马迁《史记》的原貌。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东汉的卫宏。因为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过:“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其后班彪、班固父子提出:“十篇缺,有录无书”⑤。班氏汉人,去迁未远,人们因而常以班说为据。但到底缺哪十篇班氏没讲清楚,后代也就产生了各样的说法。三国时魏人张晏第一次提出十篇的名称,说:“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又说:“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张守节则说:“褚少孙补《景、武纪》、《将相表》、《礼》、《乐》、《律书》、《三王世家》、《傅、靳》、《日者》、《龟策传》。”司马贞却说:“《景纪》,取班书补之;《武纪》,专取《封禅书》;《礼书》,取荀卿《礼论》;《乐书》取《礼·乐记》;《兵书》亡不补,略述律而言兵,虽分历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续此篇;《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同异,而论司马季主;《龟策》,直太卜所得占龟兆杂说,而无笔削之功,何芜鄙也。”
吕祖谦说:“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俱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无书也。”⑥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赵翼《廿二史札记》均有详细论证,以为班张之说未可全信。从《史记》各篇的实际情况考察,吕说诚可谓至当难移。班氏父子和张晏提出的十篇,可分为四类不同的情况。
第一类为《孝景本纪》、《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和《傅靳蒯成列传》三篇,均未缺佚。
司马贞在《太史公自序》篇的《索隐》中说:“《景纪》取班书补之。”此不知何以为据。究竟是《史记》取《汉书》补缺,还是《汉书》录《史记》成篇?显然只能是后者。现取《史记》和《汉书》加以对照,《史记》和《汉书》的《景帝本纪》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并不能说明《景帝本纪》就亡佚了。崔适是个过头的疑古派,他在《史记探源》中也说:“盖此纪实未亡尔。”这个“纪”就是《景帝本纪》。
据《太史公自序》,“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查今本《年表》,与这一意旨完全吻合,无法证明原著已佚。陈直《史记新证》认为《将相表》是司马迁《史记》里很出色的篇目,这种构思为别人所不能。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而且《史记》首创纪传体,此表却为西汉前期的编年体大事记,纲目了然,线索明晰。以纪传为主,而以编年为辅,此亦史迁记事之匠心独具。王应麟说:“复从汉兴以来大事为之记,盖以存《春秋》之法也。”⑦汪越说:“《汉书·百官公卿表》详一代之官制,《史记》但表相与将、御史大夫,意在论世知人,以备劝惩。”⑧如此,则史迁作《将相名臣表》,还不止是一种记史手法,而且寓有劝善惩恶的深意。这哪是后人所可随便补缺的呢?至于表中太初以后事,当为后人补续。
至于《傅靳蒯成列传》,《太史公自序》说,它的写作意旨是:“欲详知秦楚之事,维周緤常从高祖,平定诸侯。”可是今本《史记》中记周緤事甚简略,难以据此详知秦楚之事,但也没有根据可断定今本《傅靳传》非迁原著。梁玉绳认为这个列传“非史公不能作。”甚至崔适也说张晏“此言转不足信”。他还举了三证:第一,《傅靳蒯成列传》里的赞语是班固《汉书·傅靳蒯成列传》里没有的;第二,“文亦是太史公作”;第三,“三候立国之年,皆与功臣侯表合”。也就是《傅靳蒯成列传》根本没有亡。
第二类为《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此三篇均被指为褚补。其实,三篇中凡褚补者均冠有“褚先生曰”,甚为明显;三篇又均有“太史公曰”的论赞,亦甚明显。
《三王世家》仅载群臣奏请及封策书,借以说明三王受封的起缘和经过。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取材?我们推测司马迁本来就没有作传,这一点司马迁在赞语中交代得非常明白。他说:“燕齐之事,无足采者”。可见“三王”并无事迹可传,但封他们的策文,司马迁认为“文辞灿然,甚可观也”,故“附之世家”。就是说取三王的“封策文”,姑且当作三王的世家,并不是说将“封策文”附入世家。我们考察三王受封,同在元狩六年四月乙已这一天,齐王刘闳死于元封元年,没有后代,封国也取掉了。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都死于汉昭帝时代,都因谋反被诛。司马迁作《三王世家》时,三王既没有传代,又没有可以记载的事情,所以说:“燕齐之事,无足采者。”但按司马迁作史的体例,应当给已经封王的武帝的三个儿子作世家,于是就取了“封策文”来敷衍成篇。
我们再看一下褚少孙的续补,也只是搜求了一些遗文来说明“封策文”的意义,是补充司马迁所说“文辞可观”之旨的。仔细琢磨褚少孙的话,他的意思很明白,他是对司马迁用“封策文”代替世家这一作法进行评述,并没有说《三王世家》亡佚了。
至于《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的道理也和上面相同,都是司马迁所作,没有亡佚,也不是草创未就。后代学者嫌《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太简略,殊不知司马迁这两个传本身就这么简略,并不是什么未成之作。《太史公自序》说:“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但今本《日者列传》并未阐述诸国之俗,仅记司马季主之事,可能是一篇未最后定稿之作。司马迁作《龟策列传》,主题在这两句话:“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联系《封禅书》来读,司马迁讥讽时政,微言大义,何鄙陋之有?
总之,今本《三王世家》等三篇均言辞简洁,篇幅不长,也许史迁就只准备写这么一点点,也许是草创未具,而绝不可说它们已经亡佚,否认今本为史迁之作。
第三类为《礼书》、《乐书》、《兵书》。今本《礼书》、《乐书》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礼书》取荀子的《礼论》及《议兵》来代替它的正文。《乐书》取《礼记乐记》来代替。这些撮取的部分,吕祖谦认为属于“草具而未成者也”,王鸣盛则认为,“其实亦是子长笔,非后人所补”⑨这点,不可妄测,亦可置而不论,因为它确属撮取,谁也不会去否认。
至于《兵书》,今本《史记》无此篇目。梁玉绳《史记志疑》,王元启《三书证伪》,赵翼《廿二史札记》,均认为《律书》就是《兵书》。因为《太史公自充·集解》里引张晏的话作“亡……律书”,与“律书序目”里所说“作《律书》第三”相符合,但其意旨与现在流传下来的《律书》的内容并不吻合。所以“《律书》即《兵书》”的论断,实在很牵强。今本《史记·律书》实际上是《律历书》的一部分。《兵书》实际上亡佚了,没人补。今本《史记》的《律书》,其序文也应该是补亡者搜求到的逸文。总之,《礼书》等三篇,今仅存序论而残本论。
第四类为《孝武本纪》。赵翼的《廿二史札书》认为《武帝本纪》“非仅侈陈封禅一事。”我们也认为《今上本纪》不可能完全抄自《封禅书》,司马迁怎能自己抄自己的书?现存《史记》中叫《武帝本纪》,而《太史公自序》里叫《今上本纪》,篇名都不符,说明《今上本纪》亡佚了。后人抄《封禅书》以代替《今上本纪》。补者为示区别,改名为《武帝本纪》,曲折地显示出这不是司马迁的原作。这就是说《武帝本纪》真正亡佚了。
综上所述,班、张所说的“十篇有录无书”虽情况各异,但真正“无书”的,只《今上本纪》一篇而已。如果再加上只有序论的《礼书》、《乐书》、《兵书》,也只四篇亡佚。《汉书·艺文志》说:“省太史公四篇。”这是符合《史记》的实际的。所以,班、张之说实在未可全信。
注释:
①见《汉书·刘据传》。
②见《汉书注校补》。
③见《史记·田步列传》。
④见《汉书·车千秋传》。
⑤见《汉书·司马迁传》及《后汉书·班彪传》。
⑥见《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一四《辨〈史记〉十篇有录无书》。
⑦见《玉海》卷四九《汉大事记》。
⑧见《读〈史记〉十表》。
⑨见《十七史商榷》卷一《十篇有录无书》。
标签:司马迁论文; 史记论文; 汉书论文; 傅靳蒯成列传论文; 太史公自序论文; 汉朝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报任安书论文; 汉武帝论文; 春秋论文; 太史公论文; 西汉论文; 刘据论文; 黄帝论文; 离骚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后汉书论文; 东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