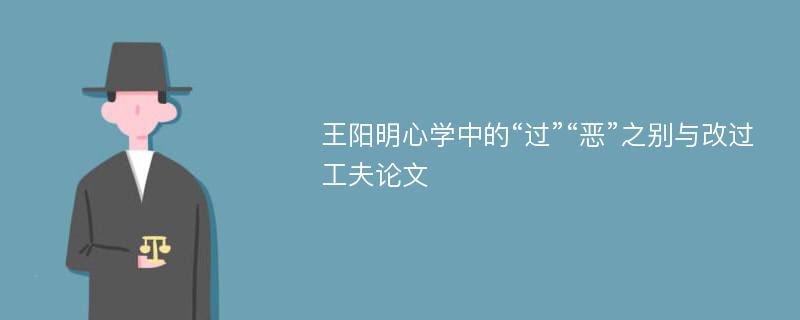
王阳明心学中的“过”“恶”之别与改过工夫
王凯立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在王阳明心学中,“过”“恶”之别与改过工夫是致良知落实到市民社会的重要环节,而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王阳明看来,“过”可以与圣贤人格相容,因而“过”与“恶”在根本上就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虽然如此,改过工夫要求调动良知心体来照见、改正过误,因而改过实际上就是致良知。就内容而言,改过工夫可以概括为自思内省、痛自悔咎、洗涤旧染、相责以善四个方面,它不仅是个人的修身之事,而且还是集体的儒学实践。总体而言,“过”“恶”之别及改过工夫撬动了王阳明心学融通于哲学与世俗之间的多维面向,王阳明心学并非只是抽象的哲学观念;哲学观念向世俗教化的适应性转变,即建构起一个创生意义的功夫世界才是王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儒学的核心关切。
关键词: 王阳明;心学;世俗教化;改过工夫
在阳明学研究中,“过”与改过工夫的研究相对较少。胡永中博士曾在《致良知论——王阳明去恶思想研究》一书中简要地论述了王阳明关于“过”“恶”之别的看法,并从反省、悔咎、去傲、责善四个方面概括了阳明心学中的改过工夫[1]215-228。与之相似,拙作《心学功夫》也结合王阳明的生平事迹,从自思内省、痛自悔咎、洗涤旧染、相责以善四个方面介绍了阳明心学的改过工夫[2]112-123。诚然,王阳明本人并未明确地对改过工夫做出系统的哲学的论述,但当我们将关注点从哲学文本转向那些具有日常语言性质的文本时,会发现王阳明时常以改过工夫教导他人。也正是如此,笔者认为“改过”这一话语在阳明心学中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改过”话语代表了王阳明致良知工夫的一种社会实践,透过“改过”话语,我们可以看到阳明心学协调于哲学性与世俗普及性之间的多维面向。
城市旅游产品是城市旅游发展的核心部分,开发城市旅游产品能推动区域经济社会良性发展。比如将湖湘文化融入到浏阳河两岸,打造文化融合区,依托浏阳河畔的黄兴故居,将湘籍名人集中展示在浏阳河两岸,融入历史文化元素。也可在浏阳河两岸建设体育广场、国际自行车道,助力国际化城市建设。比如依托长沙经开区世界500强企业以及智能制造的优势,实施“工业旅游”工程,策划亲子题材的一日游、夏令营等主题工业游;开发“工业旅游+农业旅游”、“工业旅游+空港”、磁悬浮、会展休闲以及针对大众受用的“工业旅游+生态休闲游”、“工业旅游+红色旅游”等旅游产品。
一、 “过”“恶”之别
王阳明曾多次指出,“过”不同于“恶”。在龙场教导诸生时,王阳明有言:
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3]1123
从这句话中,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两方面内容:其一,“过”与“恶”的确是有区别的;其二,“恶”在道德层面上似乎是比“过”更严重的东西。那么,“过”与“恶”间的区别到底只是程度上的区别,还是说二者在性质上根本就是两回事?在王阳明看来,“过”具有一个最根本的特征:“过”与圣贤人格相容。他说:
另一方面,代理机器人分析,即在DepthMap软件的数据分析中,根据空间的系统特征让代理机器人模拟人在其中的行为,同时记录其行动路线的分析方式.该分析反映整体空间中人流活动的分布规律[6],其中分析图中的颜色越趋于深色表明人流活动越密集.如图6所示,人群活动区域集中于曲阜路及中山路与肥城路的交汇点两处,教堂广场空间明显处于人群活动较少区域,结合视域整合度的分析,可知由于广场空间中不合理的空间形态设计,阻碍了游客对教堂广场区域的探索,在整体区域视线聚集性受限的情况下,即使广场西北角具有较高的整合度数值也无法带动游客的积极性.
随访从手术之日起截至 2017-12-31,随 访 时 间6~96个月,中位随访时间51个月。通过门诊定期复诊或电话随访等方式确定生存期。总生存时间自确诊时间至患者死亡时间或随访截止时间,随访率为100%。
蘧伯玉,大贤也,惟曰“欲寡其过而未能”。成汤、孔子,大圣也,亦惟曰“改过不吝,可以无大过”而已。人皆曰人非尧舜,安能无过?此亦相沿之说,未足以知尧舜之心。若尧舜之心而自以为无过,即非所以为圣人矣。[3]210
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是以能无过,非其心与果与人异也。[3]210
就改过工夫而言,“如果说反省相当于自我批评,责善就相当于互相批评。阳明认为,反省与责善都能使人长进”[1]224。责善使改过工夫不再囿限于单个主体,从而走向了主体之间,成为一种具有集体性质的行为。正是这种性质的转变,使得改过工夫不得不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在王阳明看来,师友有过,自当忠实地相责以善,但也要“致其婉曲”[2]122-123。“直接地揭露师友的过错,不仅容易让师友产生羞耻愤恨的情绪,同时这种负面的情绪还会阻碍师友改过,甚至还会相反地刺激他去主动做恶。因此王阳明认为,这样的批评方式并不能称之为‘责善’。当然,王阳明也强调,如果师友直接地指出了自己的过错,那也不应该对师友产生愤恨的情绪,而应该主动接受,痛加悔改。”[2]123
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过处。[3]140
昔孔子,大圣也,而犹曰“假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仲虺之赞成汤,亦惟曰“改过不吝”而已。所养之未至,亦何伤于二先生之为贤乎?[3]961
惟吾兄去世俗之见,宏虚受之诚,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异;勿以无过为圣贤之高,而以改过为圣贤之学;勿以其有所未至者为圣贤之讳,而以其常怀不满者为圣贤之心,则兄与舆庵之论,将有不待辩说而释然以自解者。[3]962
这些论说表明,王阳明认为圣贤之为圣贤,不是因为他们不会有过,而是因为他们有过能改。由此可见,“过”本身是一种不会贬损圣贤人格的存在。那么,“恶”又如何呢?在王阳明看来,“君子之过,悔而弗改焉,又从而文焉,过将日入于恶”[3]1043,换句话说,如果有过不改,那么“过”就会转变为“恶”。在王阳明这里,与“过”相区别的“恶”可以视作是有过不改的后果。既然圣贤之为圣贤乃是因为他们有过能改,那么“恶”显然与圣贤的人格形象不能相容。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在王阳明哲学中作为理想人格的圣贤与普通人之间有本质的不同,那么我们就必然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在阳明看来,恶与过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它们根本就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1]217
关于“过”与“恶”的不同,我们还可以借用王阳明自己的一个比喻来理解。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在教导南大吉改过时曾说:
2)“一张图”大数据服务。基于统一的矿图标准规范体系及“一张图”数据库,采用面向服务架构(SOA)实现符合OGC国际标准的地理空间数据和业务数据共享接口,可以为煤矿安全生产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和与现有业务系统的集成提供坚实基础。
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3]1469
在这里,“镜”是比喻人本有的良知心体,它本来就是光亮澄明的。“镜未开”是比喻普通人的存在状态,他们本有的良知心体受到了私欲私意的遮蔽,正如镜子因表面的污垢而遮蔽了原本的光亮。需特别留意的是,王阳明是用“垢”来比喻这种状态。另外,“镜明”乃是比喻圣贤的存在状态,圣贤之为圣贤正是由于他们能将良知心体澄明无碍地实现出来,正如没有污垢附着的镜子能呈现其本来的光亮一样。王阳明注意到,已经光亮澄明的镜子并不意味着它就永远纤尘不染,明镜上仍然会有“尘”落下。然而,正因为明镜上没有了“垢”的附着,所以“一尘之落,自难住脚”。由此可见:“垢”与“尘”是相区别的;圣贤的良知心体虽然光亮无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永远纤尘不染,圣贤之为圣贤不是因为他们的心体明镜上不会有“尘”,而是因为没有“垢”而“尘”自难住脚。
这可能是王阳明对改过工夫最为详细的论述,自思内省、痛自悔咎、洗涤旧染、相责以善这四层意思均能在这段文本中找到。而胡永中博士从反省、悔咎、去傲、责善四个方面概括王阳明心学中的改过工夫[1]215-228,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似乎并没有直接的文本证据表明“傲”就是“过”,“去傲”就是“改过”。以下我将以拙作的概括为依据,对王阳明心学中的改过工夫做进一步的补充论述。
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如何?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有哪些?如何进一步提高公众科学素养?近日,在首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上,中国科协发布的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具备科学素质的公众比例达到了8.47%。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借助“垢”与“尘”的比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明晰改过工夫与打磨心体的关系。就圣贤而言,改过似乎是一个十分自然的事情①,因为光亮澄明的良知心体很容易照见过误,从而去除过误,正如在一块光亮的镜子上,一丝一毫的灰尘都难以掩藏。就普通人而言,改过工夫意味着通过某种人为的努力去调动良知心体来照见过误,这个过程就好像一缕灰尘落到布满污垢的镜子上,而为了照见这一缕灰尘并去除它,我们须要对这面布满污垢的镜子进行一番打磨。在这个意义上,拂去一缕灰尘如同要求去除镜子上的污垢,即改过工夫其实就是要去恶,就是要打磨心体,就是要致良知,所以王阳明说:“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3]210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改过工夫与致良知之间的关联,即改过工夫成为了致良知的一种现实化方案。如果说改过工夫体现了王阳明心学教化的世俗面向,那么改过工夫与致良知之间的关系则在理论上打通了王阳明心学世俗性与哲学性之间的隔阂。
二、改过工夫
既然改过可以收摄入致良知的工夫范畴,那么我们也就不难明白王阳明为何在日常的工夫劝诫中屡次提及改过。拙作《心学功夫》之所以将王阳明的改过工夫概括为自思内省、痛自悔咎、洗涤旧染、相责以善四个方面[2]112-123,是基于王阳明龙场悟道后所作《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的“改过”一节:
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所容,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为恶矣。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虽然,我以是而施于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3]1122—1123
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谑,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过矣。”自后四子亦渐敛容。[3]1389
在上述比喻中,我们只要稍作对比就可以发现,“垢”与“恶”、“尘”与“过”之间具有相同的结构。而王阳明在教导南大吉改过时引入这一比喻,似乎也暗示了他解释“过”“恶”之别的合理性。我们可以发现,“垢”与“恶”一样,是普通人良知心体被遮蔽的状态;“尘”与“过”一样,是一种与圣贤人格相容的存在。圣贤不会有“恶”,正如圣贤的心体明镜上不会有“垢”;但圣贤良知心体的光亮澄明并不意味着这块明镜上不会有“尘”落下。圣贤之为圣贤在于“一尘之落,自难住脚”,这正如圣贤之为圣贤不在于不会有“过”,而在于有过必能改。更为重要的是,“尘”与“垢”显然是两种在存在方式上根本不同的东西,这就如同“过”“恶”之别乃是性质的根本不同,而非程度的不同。当然,我们还可以将这个比喻推进一步来解释有过不改、积过成恶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如同“尘”落在镜子上,如果不及时拂去,用不了多久就会积“尘”为“垢”而附着其上。须要强调的是,这个过程并不意味着“垢”是“尘”在数量上的简单累加,好像说“过”与“恶”只是程度上的区别一样,对于一块镜子而言,由“尘”变“垢”显然有着质的不同。
少先队员们在志愿活动中自主策划方案、自主践行活动、自主评价成果,不断促进自身主动地成长。自主,是少先队员当家做主的权利,是雏鹰日渐丰满羽翼的催化剂,是少先队员翱翔蓝天的力量源泉!
(一)自思内省
改过首先需要知过,知过就需要时常自思内省。在这一点上,少年王阳明就是这样做的。《年谱》记载:
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于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之习者乎?诸生殆不至于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诸生试内省,万一有近于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当以此自歉,遂馁于改过从善之心。但能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虽改过而从善,将人不信我,且无赎于前过,反怀羞涩凝沮,而甘心于污浊终焉,则吾亦绝望尔矣。[3]1122
知过、改过并非一句空言,它需要真切的自思内省。就内容而言,自思内省乃是既要省察自己平日在廉耻忠信方面的行为是否有所欠缺,也要省察自己是否“薄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之习”。在方法上,王阳明提供了一种“端坐”的省察方式。如果说“端坐”与“静坐”具有某种相通之处,那么王阳明所践行的改过工夫显然相契于刘宗周在改过方式上所主张的“静坐悟心”[4]。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来反观改过工夫,自思内省就可理解为通过某种工夫方法(如“端坐”)来调动良知心体本有的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从而洞见自己的过错并切实地走向改过的工夫实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自思内省就是打磨心体,就是致良知。
(二)痛自悔咎
在自思内省之后,痛自悔咎乃是落实改过工夫的关键环节。在教导学生南大吉改过时,王阳明曾说:“人言不如自悔之真。”[3]1469也就是说,唯有自己悔悟过错,改过工夫方能真切,这就是《教条示龙场诸生·改过》中所强调的“痛自悔咎”[2]115-116。王阳明曾说:
悔者,善之端也,诚之复也。君子悔以迁于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惟圣人而后能无悔,无不善也,无不诚也。然君子之过,悔而弗改焉,又从而文焉,过将日入于恶;小人之恶,悔而益深巧焉,益愤谲焉,则恶极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恶之分也,诚伪之关也,吉凶之机也。君子不可以频悔,小人则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3]1043
由此可见,悔过构成了道德修为的关键,是“善之端”与“诚之复”,是善与恶、诚与伪、吉与凶分别的关隘和枢纽[2]117。在劝导浰头贼寇的告谕中,王阳明特别强调了悔悟:“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然亦皆由尔等悔悟不切。”[3]681-682在王阳明看来,只要贼寇能真切悔悟、改过从善,亦不妨碍他们成为好人。“因此,有过必须痛自悔咎,如此才可能去恶为善、去伪存诚、化凶为吉。此外,王阳明还强调了悔过之后必须改过,君子之过,悔而不改,将积过成恶;小人之过,悔而不改,将深谋讨巧,欺诈怨愤,终将恶极而不可解。”[2]117在这里,王阳明还告诫“君子不可以频悔”,《传习录》(上)记载:
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3]1122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3]38
四百五十年间,风云激荡,范氏家族既非冠冕不替的簪缨世家,亦非富可敌国的江南豪族,在如此环境条件下,该家族依旧能够温和而不失气度地屹立在华夏国土,其诗文传承岿然独存,非有良好、醇厚的家族风尚何能如斯?可见,南通范氏一以贯之的“家风”是其家族踽踽独行而未被湮灭于浩瀚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因素。
作为改过工夫的必要环节,悔过本是使心体澄澈无碍的工夫法门。但如果悔过过多,却不加以切实改正,那么就会“留滞于中”,悔过反成心体的滞碍。此外,“懊悔过多还可能丧失自信心,导致自暴自弃,不肯改过自新”[1]127-130,因此王阳明劝诫龙场诸生对自身过错的痛自悔咎“不当以此自歉,遂馁于改过从善之心”。由此可见,悔过虽是改过的必由之途,但若不真正落实为改过,悔过不仅无益于心体的打磨,反而容易带来流于恶的危害。
(三)洗涤旧染
在痛自悔咎的基础上,洗涤旧染乃是改过工夫的真正落实。人若能切实通过洗涤旧染而改过迁善,那么“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矣”。在《寄诸弟》中,王阳明曾教导自己的弟辈说:
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是以能无过,非其心果与人异也。“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者,时时自见己过之功。吾近来实见此学有用力处,但为平日习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预为弟辈言之,毋使亦如吾之习染既深,而后克治之难也。[3]210
显然,王阳明注意到了习染深痼之难以克治。在王阳明看来,为了不让过错积累成难以克治的“习染”,弟辈们须时时下戒慎恐惧的工夫,一旦见己之过,就即时改之,不要积过成习、积过成恶。在这里,戒慎恐惧的工夫与改过的自思内省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对于已有的习染而言,它之所以难以克治,乃是因为“欠勇”。此处的“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改过须有直面己过之勇。在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向皇帝朱厚照上疏救戴铣、薄彦徽等人时,就劝谏皇帝“明改过不吝之勇”[3]354,意在使皇帝勇于直面己过,并痛加悔改。其二,改过之勇还包含了洗涤旧染的果敢决断与恒久毅力。在《教条示龙场诸生·改过》中,王阳明特别提醒诸生不能因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反怀羞涩凝沮”,这不仅会使人对改过工夫产生懈怠情绪,还会使人“甘心于污浊终焉”。因此,面对“习染深痼”的情况,切实的改过工夫更需要不畏惧外界评价的果敢决断,更需要时时警惕、持久不懈的毅力,这些都构成了“勇”的品格特征[2]119。
(四)相责以善
在《教条示龙场诸生·改过》中,王阳明将诸生过误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不知而误蹈”,且“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这意味着改过工夫并非只是一人之事,它需要师友之间时时提醒、相互勉励,这就是王阳明在教导龙场诸生时所提到的“责善”:
(31)从探索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模式到开展绿色GDP核算试点,江西绿色崛起落子声不绝于耳。 (2012·《人民日报》)
王阳明的“责善”观基本继承了孟子的看法。《孟子·离娄下》有载:“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朱子注曰:“朋友当相责以善。父子行之,则害天性之恩也。”[5]“所谓责善,就是相责以善,即以善作为行为标的,相互要求、相互勉励。这实质上就是师友之间相互劝善改过的工夫。”[2]120从伦理层面看,“责善”是一种朋友之道,“其任乃在师友之间”[3]272,而非父子相处之法,“因为责善会使父子之间的关系淡漠疏离,从而破坏了整个儒家意义上的人伦基础”[2]120。正如孟子所指出的:“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娄离上》)
“2003年时,湖区的养殖面积一度达到36万亩。2010年国家加强养殖权制度建设以来,高宝邵伯湖按照省政府批准的养殖规划实行严格的限制措施,尽管如此,2016年初湖区仍有养殖面积30.5万亩,占湖泊总面积的21.2%。其中,养殖发证面积23.4万亩,持证养殖渔民2244户;无证养殖面积7.1万亩,无证养殖渔民约600户。”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管办副主任索维国介绍道。
三、功夫世界:融通哲学与世俗
在王阳明心学的发展过程中,与王阳明进行对话、交往的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修行共同体”成员,如王阳明的大多数弟子,这类人往往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准与文化修养,是所谓精英阶层;另一类是“草根阶层”,如乡民、匪寇等,这类人往往不具备多少知识水准与文化修养[6]。这提示我们,王阳明心学绝不仅是具有精英性质的哲学探讨,而是互动于哲学理论与世俗教化间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意义上,一种仅仅局限于哲学层面的研究,很可能从一开始就背离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精神。
王阳明关于“过”“恶”之别的叙述,实际上是一种话语实践,这种话语实践旨在激励“草根阶层”改过向善的工夫践履。从哲学上讲,王阳明在道德价值上是主张善恶矛盾且排中的,《传习录》(下)记载:
问:“先生尝谓‘善恶只是一物’。善恶两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谓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直因闻先生之说,则知程子所谓 “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又曰:“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其说皆无可疑。[3]120
在这段文本中,王阳明将“恶”视为“善”的过与不及。由此可见,“善”与“恶”之间并不存在第三种道德价值,这实质上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道德严格主义。在这一哲学讨论框架下,“过”“恶”之别其实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过”显然不能是“善”,而如果“过”也同时不是“恶”的话,那么“过”就成为了介于“善”“恶”之间的第三种道德价值,这对于主张善恶矛盾且排中的王阳明而言是难以接受的。这就告诉我们,王阳明关于“过”“恶”之别的论述不能从哲学讨论的意义上进行理解,而要把它看成是一种面向“草根阶层”并对其进行具有道德规劝意义的话语实践。从理论上说,当王阳明提出“过”“恶”之别时,实际上意味着松动了“恶”精确的哲学含义,同时也放弃了道德严格主义的立场。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王阳明在面向“草根阶层”的道德规劝中要使语言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并顾及规劝中的话语效力。我们仔细体会一下就能发现,在日常用语中说“恶人”其实意味着一种比哲学上说“恶”更为严重的东西,“恶”在日常语言中有着更为严厉的话语效力。王阳明提出“过”“恶”之别,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日常语言中对“草根阶层”所犯过误加以类似“恶人”这样的严厉评判,这显示了王阳明在道德规劝时对“草根阶层”的更多理解与同情,从而使“草根阶层”保留向善的信心;另一方面,“过”“恶”之别的区隔使得“过”可以与圣贤相容,并使圣贤这一道德理想人格具有更加贴近“草根阶层”的性质,也就是说,圣贤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道德理想,圣贤与凡人一样都会有“过”,只要改过向善,就能成圣成贤,这就更加彰显了圣贤这一理想人格在市民社会的现实示范性力量。由此可见,如果说致良知、打磨心体等话语更多的是面向“修行共同体”的工夫话语,那么改过则是这些话语面向“草根阶层”的现实转化,而最为关键的是,这两套话语是相互融通的,一起构成了王阳明心学的立体样貌。
经历此次创伤事件后,9例病人均获得一定程度的创伤后成长。病人C:“(以前常常因为)上班来不及了,横穿马路,以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对别人负责的同时也对自己负责。”病人D:“我在搬货时不小心从车上摔下来,以后一定要克服毛毛糙糙的毛病,家里收入都靠我做点生意来维持,自己要是垮了,家人咋办(声音突然哽咽)?”病人H:“经过此次事件后,以后上班不开电动车,骑自行车上班,既环保又利于身体健康(边说边斜视她老公一下)”。
就改过工夫而言,从自思内省到相责以善,改过工夫从个人的修身之事发展为集体的儒学实践,这背后实际上是哲学观念向世俗教化的适应性转变。正如吴震先生指出的:“可以发现明清之际不少知识精英在日常生活领域,开始把儒家传统的‘改过’实践发展成为互相‘纠过’的集体行为。”[7]事实上,这一社会图景在王阳明的改过工夫中已见端倪。从这个意义上看,王阳明将具有哲学意味的致良知世俗化为一种面向市民社会各个阶层的教化实践是相当成功的,而如何将哲学观念转变为切适的世俗教化才是儒学念兹在兹的问题意识。
在拙作《心学功夫》中,笔者试图用“功夫世界”这一观念来把握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特质[2]154-170。所谓“功夫世界”,其实就是一个成己成物的世界,它意味着主体通过功夫修为创造意义,并将其建构为不断创生意义的时空秩序,而这个时空秩序将在建构过程中教化更多的人进行功夫践履,实现生命转化,进而对意义进行再创造。“功夫世界”不仅关乎哲学观念,更关乎哲学观念向世俗教化的适应性转变,它是哲学观念在功夫实践中的现实化与客观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功夫世界融通了哲学与世俗、精英与平民,旨在全人类生命的转化与对存在意义的追寻。在笔者看来,建构一个功夫世界才是王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儒学的核心关切,因此,王阳明心学绝不仅是“良知”“诚意”“格物”等这些抽象的哲学观念,更是这些哲学观念向世俗教化的适应性转变。在这一视域下,王阳明关于“过”“恶”之别的叙述以及对改过工夫的强调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过”“恶”之别及改过工夫是王阳明将致良知落实到市民社会(特别是“草根阶层”)的重要环节,它撬动了王阳明心学融通于哲学与世俗之间的多维面向,暗示了建构一个创生意义的功夫世界才是其心学乃至整个儒学的核心关切。
当今世界是一个意义迷失的世界,劳动异化、人格物化、生活碎片化使得人总处在彷徨、焦虑、不安的意义空洞中,因此,生存、生活的无意义便转变为对某种功利的追求或当下的及时行乐。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阳明心学所构建的功夫世界显示出了对当今世界的批判向度,即人须要通过现实的功夫实践来创生意义,这才是构建人美好生活的正途。在王阳明心学看来,美好生活的构建最终落脚于人本身的功夫修为,正是在功夫修为中,外界的一切才成为了人的意义的承载,成为了人的栖居之所。在笔者看来,当人的生活如当今世界的境况一样,即注重于直接的情感体验与可见的利益获取时,重拾王阳明这种通过功夫修为来创生意义的身心之学,或许将是提升生命厚度、丰富存在价值、构建美好生活的有益探索。
注 释:
①在这个意义上,改过对圣贤而言似乎不能说是一种“工夫”,因为“工夫”多少具有人为努力的意味,并非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表达式中,考虑电流环的动态性能将增益Kp1设计为2500rad/s。对电流环进行控制,需确定电压环的控制策略,其为公式(5)提供参考电流。图5为用于决定参考电流的逆键合图模型。
参考文献:
[1]胡永中.致良知论——王阳明去恶思想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7.
[2]王凯立.心学功夫[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
[3]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M].王晓昕,赵平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
[4]张瑞涛,肖红春.论刘宗周《人谱》的“改过”六法[J].理论月刊,2013(8):45-46.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305.
[6]陈立胜.王阳明思想中“恶”之问题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5(1):18-23.
[7]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5.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ault and Evil and Self-Cultivation of Correcting Faults in Wang Yangming's Theory of Heart-Mind
WANG Kaili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Xiamen University,Xiamen,361005,China)
Abstract: In Wang Yangming's theory of heart-mind,the difference between"fault"and"evil"as well as the self-cultivation of correcting faults are the important link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science to the civil society,but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in this field.In Wang Yangming's view,"fault"can be compatible with sages'personality,so"fault"and"evil"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in nature.However,the self-cultivation requires the mobilization of conscience to seeing and correcting faults,so it is actually to realize conscience.As far as the content is concerned,the self-cultivation of correcting faults can be summed up in four aspects:introspection,bitter self-regret,washing up the old dye,and mutual requirement of kindness.It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personal cultivation,but also a collective practice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Wang Yangming;the theory of heart-mind;secularization;the self-cultivation of correcting faults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014(2019)06-0013-07
DOI: 10.16514/j.cnki.cn43-1506/c.2019.06.002
收稿日期: 2019-08-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13&ZD062)。
作者简介: 王凯立,男,浙江义乌人,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道德哲学。
(责任编辑:张群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