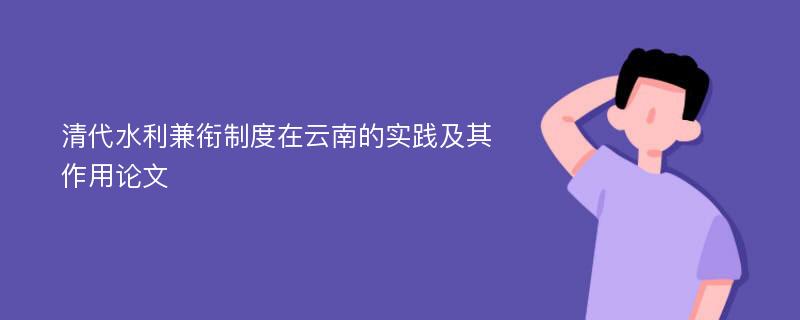
清代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的实践及其作用
吴连才
(玉溪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云南 玉溪 653100)
[关键词] 清代;云南;水利兼衔制度;水长制
[摘 要] 清代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的实践,开始于雍正十年(1727),在乾隆年间发展到高潮。通过让道员以及同知、通判等佐贰官员兼署水利职衔,并不断结合地方实际进行改革,清政府在云南建成了较为完整的水利管理官僚体系。水长制度作为水利兼衔制度在乡村社会的延伸和补充,为云南基层水利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有效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水利兼衔制度的实施提高了云南官员对地方水利发展的参与度,推动了云南水利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在客观上促进了清代云南人口增长,对稳固清朝在云南的统治起到积极作用。
所谓水利兼衔,就是清政府为解决地方水利发展问题,让一些已有职守的地方官员兼署水利职衔,担负起发展所在区域水利的任务。清代水利兼衔制度实施始于雍正五年(1727),两广总督孔毓珣在奏疏中提出让管理水利的同知、通判、县丞、主簿等官员兼署水利营田衔,该提议得到雍正皇帝和工部支持而得以施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河南布政使刘慥提出将各省守、巡各道及同知、通判等官“概兼水利”,获批后水利兼衔制度的施行达到顶峰(1) 吴连才,秦树才.清代水利兼衔制度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18-125. 。嘉道(1796~1850)以后水利兼衔有所衰退,但一直到清末都还在部分地方施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光绪帝在对内阁的谕令中提到有些地方的基层官员虽然兼衔水利,但其实并无水利职责(2) 《清德宗实录》卷425,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乙丑条。 ,考虑将其废除。清末仍有道员在水利兼衔中扮演重要角色,四川成绵隆茂道兼衔水利的制度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才取消(3) (清)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16:职官三[M].北京: 中华书局,1976:3354. 。宣统元年(1909),浙江设南田抚民厅,以宁波府水利通判移驻(4) 《宣统政纪》卷16,宣统元年六月癸卯条。 ,由此可见,水利兼衔制度基本上是到清朝灭亡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水利兼衔制度是清代国家管理制度的新发明,是清代水利职官制度的重要变革,为促进云南水利事业发展、推动农业生产进步和保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现有清代云南水利史的研究成果较少从水利职官制度的视角进行考察,也很少涉及水利兼衔制度(5) 清代云南水利史研究主要关注水利发展及其影响,聚焦滇池水利发展及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代表性成果有:方国瑜.滇池水域的变迁[J].思想战线,1979(1):33-38;陆韧,马琦.历史时期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及生态环境演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研究清前期云南水利促进农业发展的代表性成果有:方慧.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2):26-32。研究水利在推动云南内地化发展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代表性成果有:周琼.清代云南内地化后果初探——以水利工程为中心的考察[J].江汉论坛,2008(2):75-82。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张海超.明清时期大理洱海沿岸的水利建设与水资源配置[J].鄱阳湖学刊,2012(2):5-10;董雁伟.清代云南水权的分配与管理探析[J].思想战线,2014(5):116-122;马琦.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水利纠纷与社会治理[J].思想战线,2016(3):133-140. ,本文对清代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的实践及其作用进行初步探讨。
一、清代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职官体系中的施行情况
清代水利兼衔制度在各省施行有前后之别,具体情形也有所差异。云南是较早响应清代中央政策施行水利兼衔制度的省份之一。清代在山东、河南等重点水利发展区域设有专门管理重大水利工程的机构和官员,与这些地方不同,云南则是采取由地方官员兼署水利职衔的方式完成对全省水利的管理。施行水利兼衔制度以前,云南水利工作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主官负责。水利兼衔制度施行以后,地方各级主官依然有发展水利的责任,但具体工作的落实主要分配给道员、同知、通判等官员,使清代云南水利管理更加细化和高效,水利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更强。
(一)清代云南道员兼衔水利的情况
道是介于省、府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清代云南的道虽有调整,但始终是一级常设行政机构。道员是职兼文武的地方大员,是云南贯彻水利兼衔制度的重要责任群体。守巡道官员兼署水利职衔,其辖地范围内分管水利和兼水利衔的官员都在其领导下开展水利活动。兼署水利职衔的云南守巡道官员,经地方督抚奏请朝廷批准、国家颁给关防印信,使其合法性、权威性得到进一步增强。
鄂尔泰于雍正三年(1725)至十年(1732)担任云贵总督(雍正六年后任云贵广西总督),任内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为云南水利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雍正十年(1732),鄂尔泰奏请将云南兼水利职衔的地方官全部划归粮储、迤东、迤西三个守巡道管理,获雍正皇帝支持并付诸实施。其中,云南府水利归粮储道管理,迤东地区水利统归迤东道管理,迤西地区水利统归迤西道管理(6)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水利》卷134,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到乾隆时期,国家铸给兼署水利职衔的云南守巡道官员关防,其水利职责更加明确,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乾隆二十四年(1759),云南巡抚刘藻上奏朝廷提出在粮储道已经兼水利衔管理云南府水利的基础上,应该将这一制度推广到云南府以外地区,让迤东道、迤西道一起兼署水利职衔(7) 《清高宗实录》卷591,乾隆二十四年己卯闰六月甲辰条。 。雍正十年(1732)鄂尔泰奏准云南粮储道可以兼署水利职衔,但迤西道、迤东道并未能兼衔水利,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方才获准兼署水利职衔,这次调整使云南道员兼衔水利的制度日趋完备。
水长制度作为清代官方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乡村社会中的延伸,曾得到广泛施行,且成就显著。罗次县地理位置特殊,处于山间平坝之中,水患少而干旱多,各村设置水长的主要目的是负责组织百姓修缮水利工程。罗次“无河防之患,惟干旱是犹,各村间设水长三,月初祭龙之辰,水长鸣锣聚众,修浚沟道,知县、典史不日亲往查核。”(20) 光绪《罗次县志》。 嵩明州知州吴宝林在大力整饬金马里上枝地方水利之后,也建立水长制度,其职责是在组织人修浚河道的同时,监督滨河百姓,不允许冲沙阻河增加耕地,也不能够在河道上修筑土坝,以免造成河道淤塞。“次期与此邦绅士、里民图善后之计,其要在开河尾以泄水之势,设闸枋以定水之数,而其补救之目则又有三。一曰禁冲沙,滨河之民,冲沙广地则河阻。二曰禁土坝,以木易之则不淤。三曰,去截泥,河尾交修处必多横截之泥,责令滨河之民去之。嗣后设水利二人,复其差,比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率以为常,而河自是无患矣……水利陈运泰、杨德君,其余姓名不及备载。”(21) 引自吴宝林《重修金马里上枝诸河碑记》,载于光绪《续修嵩明州志》卷7《艺文志下》。 康熙二十年(1681)知州张国卿修治剑川州海堰,筑堤建闸保护,使周围田地免于淹没,竣工后也设置水长负责巡查水患,一旦有警及时修补。“在城南,滨湖豬圈场、西荘、汉登等村田亩每被淹没。康熙二十年,知州张国卿沿湖筑堤建闸,始不为患,每村派徭役一人巡守,海防始固。”(22) 道光《云南通志稿》卷53《水利二》。
(二)清代云南佐贰官员兼署水利职衔的情况
雍正十年(1723),鄂尔泰上书朝廷请求对云南水利职官制度进行改革,获得批准。他在奏疏中提出在昆阳州增设水利州同一人,长期驻扎滇池海口,主要任务是对滇池海口水位、隐患等进行巡察,如果遇到海口大河两岸沙石冲入河道、壅塞河水,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疏通,一旦堤坝冲塌则要立即堵筑,有不能解决的严重水患时要及时上报督抚等地方主官。另外,对于其余各州县凡是有水利设施的地方,当地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历、吏目、县丞、典史等官员都准予加水利职衔,责令其专理辖地内的河道、沟渠疏通及水利设施的修缮、维护工作(12)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水利》卷134,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令云南府水利同知巡查,并请于昆阳州添设水利州同一员,驻劄海口,以专责成。再通省有水利之处,凡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历、吏目、县丞、典史等官,请加水利职衔,以资分办。均应如所请。”(13) 《清世宗实录》卷117,雍正十年壬子夏四月辛丑条。 由此开启云南水利发展新局面:一方面,在昆阳州设置水利州同密切关注海口水利形势,有利于防止因海口河道淤塞造成滇池水位上涨、危及滇池周边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充分反映出清代云南地方政府对滇池海口水利的重视;另一方面,让同知等佐贰官员兼署水利职衔,意味着清代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的全面实施。
实践性强是医学学科的一大特点。模拟医学教学的主要特点是教学场景高仿真、可重复。在医学诊断学,医学解剖学等领域已取得了显著效果[18]。由于患者隐私权保护,维权意识提高,寻求医疗服务质量的心理需求等因素下,全科医生仍然缺乏直接对患者行有创操作的机会。模拟医学教学环境创造了安全可靠的教学平台,且有利于激励全科医生全面提高技能。
水利兼衔制度在一省之内广泛推行,从实际情况来看,云南的改革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就全国来说,乾隆二十二年(1757),河南布政使刘慥上奏朝廷,提出让“各省守、巡各道及同知通判等官,原有兼司水利之责,即或向无兼衔者,亦请概兼水利……令各省督抚查明守、巡各道及同知通判等官原兼水利者,毋庸再行兼衔外,如该地方有水利而尚未兼衔者,分别具题,到日再行办理”(14) 《清高宗实录》卷549,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丙戌条。 。这一提议经吏部等多部合议以后得到批准。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皇帝谕令:“凡水利,直省河、湖、淀、泊、川、泽、沟渠,有益于民生者,以时修治,务令蓄泄随宜,旱潦有备。以府州县丞、倅(佐)贰董其役,各给以管理水利职衔。”(15)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河工》卷74,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此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佐贰官员才广泛兼署水利职衔,专门负责当地水利发展。
(6)在数组W=[we,r]w×r中,改变调度过程中工序在机床上的加工顺序,以生成工序在机床上的加工顺序相邻解。
乾隆二十四年(1759),云南巡抚刘藻在奏疏中提出因部分佐贰官员管辖地方较大、距离较远,不能兼顾水利发展事务,尤其水患突发时难以快速救援,故而将大关同知、弥渡通判等 12名佐贰官员所兼署的水利职责移交给地方官员,以方便水利管理;其他运行较好的地方则仍然由佐贰官员兼署水利职衔。昭通府分防大关同知、鲁甸通判,镇沅府分防威远同知,普洱府分防思茅同知,广西府分防五嶆通判,元江府分防他郎通判,顺宁府分防缅宁通判,丽江府分防中甸同知、维西通判,大理府分防弥渡通判等官员,因相距较远,各有各的地方职责,难以兼顾别处水利。因此将自身肩负的水利职责转交给各知府并所属州县的一把手,由他们随时督率勘办地方水利事务。此外,景东、蒙化二府的掌印同知,职责在专司地方事务,也不需要再兼水利衔。但曲靖、临安、开化、永昌、永北、大理等府同知及澄江通判,对地方水利发展作用巨大,有必要继续兼水利职衔(16) 《清高宗实录》卷591,乾隆二十四年己卯闰六月甲辰条。 。
由此可见,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云南地方官员对同知、通判等官员兼水利职衔负责地方水利发展事务的认识更加务实,不再“一刀切”地强制推行水利兼衔制度,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一些地域辽阔的边远地区,因分防的同知、通判等佐贰官员其他职责任务繁重,无法兼顾当地水利事务,也不再勉强推行水利兼衔制度,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取消其水利兼衔;对水利兼衔制度运行效果良好的如临安等地,也根据实际需要继续推行水利兼衔制度,这可以看作是云南水利兼衔制度发展日趋成熟的表现。
铁路系统中的各设计单位正在大力推广基于BIM的设计技术,咨询单位对BIM的研究、应用成熟度,需与设计单位基本同步。
主要是掌握语法规则,理解语言逻辑,遵守交际规则,从而形成准确而规范的表达能力。建议普通高中每周开设一节语法或逻辑课,授课内容主要包括古代汉语语法规则,如通假字、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等;现代汉语语法规则,重点是句法、修辞和应用文写作,等等。
KANG Zi-jian, LIU Ya-qun, ZHANG Zhi-guo, LIU Yao-yang, XU Hu-ji
二、清代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基层社会的延续——水长制度
清代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乡村社会中的施行以水长制度最为典型。水长制度是清代云南基层社会为了调节水资源分配而普遍施行的一种水利管理制度。水长又有坝长、沟头、水利、水头等称呼,一般都由乡间较有才干之人充任,主要负责当地水资源的分配、管理,水利纠纷的调解以及组织百姓兴修和维护水利设施,多为民间共同推举产生,代表乡民行使水利管理职能,其管理范围或为一河、一沟,或为一塘、一坝,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差别。水长在当地都有自己的营生,在经营自身农业生产的同时,出面兼任水长一职,因其产业多与农业密切相关,受地方水利发展影响较大。因此,在担任水长期间大部分都能够秉公履职、兢兢业业地从事地方水利的兴修和水利工程的修缮维护工作。水长依据乡村社会共同定立的水规、分水制度等乡规民约,对本村水利进行管理,担任水长的人能够通过管理水利的劳动获得一定补偿。水长虽未进入国家职官管理体制,也没有官方任命和公职身份,但其权力却会得到官方认可,是清代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基层社会中的延伸,是清代国家力量在云南基层的一种延续。尽管水长执法所依据的乡规民约带有乡村自行订立的特点,但在实际的纠纷调解中却能得到官方的肯定和支持。当出现水利纠纷时,水长也有代表村民参与官方主导的交涉活动的资格。
水长制度明代就已在云南施行,清代得到沿用而发扬光大,是云南基层水利顺利发展的基本制度保障,对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明代万历六年(1578),石屏州知州曹所能修筑鉴塘,完工以后设有坝长负责之后的维护管理。“西塘之西有鉴塘焉。明万历六年,知州曾所能就岗陵之隘筑长堤一道,潴西湖下游之水汇成巨津,中央有屿,九天观在其上,建石闸设坝长二人,以时启闭,民赖其利。”(18) 嘉庆《临安府志》卷5《山川》。 120年后的康熙三十七年(1698),知州张毓瑞再次增修鉴塘。增修之后,同样设置水长管理,当年附近区域农业就获得丰收,起到良好的水利效果。“就其岗陵之隘,而阨塞之中,为石门以通启闭,立碑一所,佥水利官一员,坝夫二名掌之,工成盖戊寅八月也。湖水渐盈,汪洋千顷,农夫欣然,喜如君者之有积仓也,是岁果大稔。”(19) 引自曹所能《九天观塘水利碑记》,载于康熙《石屏州志》卷8《艺文》。
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政府对云南道制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迤东道辖曲靖、澄江等7府;迤西道辖楚雄、景东等10府和维西、中甸、阿墩子等处地方;迤南道辖普洱、临安等4府;盐道辖云南、武定2府(8) 邹建达.清时期云南督抚、道制与边疆治理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01:67. 。乾隆三十三年(1768),云南、武定两府不再归盐道管辖,而是调整归粮道管理,后改称为云武分巡粮储道(9) 邹建达.清时期云南督抚、道制与边疆治理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01:67. 。同年,云南巡抚明德针对云南粮储道、迤西道、迤南道虽然已经兼署水利职衔,但还没有关防的情况,向朝廷奏请给三个守巡道颁发关防。“给云南分巡迤西兵备兼管水利道,清军驿传、盐法分巡云、武二府兼管水利道,分巡迤南兵备兼管水利道各关防”(10) 《清高宗实录》卷816,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八月丁巳条。 。三十四年(1769),新调任的云南巡抚喀宁阿再次奏请“铸给督理云南屯田粮储分巡云、武二府兼管水利道关防”(11) 《清高宗实录》卷838,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秋七月。 ,获得批准。至此,在全国普遍施行水利兼衔制度的背景下,云南基本形成四个兼水利衔、配关防的守巡道分掌全省水利的格局。兼署水利职衔的守巡道官员统领辖下兼水利衔的同知、通判等官员,以垂直领导方式完成对区域内水利事务的管理,从而使云南道员兼衔水利的制度最终建设完成。
保山县的诸葛堰,又称为大海子。乾隆三十四年(1769),地方官在治理大海子后,定立水规,规范分水、放水的秩序,水规的执行就是由水长最终负责落实。其主要职责是负责轮值看守放水,监督民众用水,如果出现违误还得交罚款充公作为修坝费用。“重九塞篡后,岔纂沟水头守满水过减口。厥后,四大沟水头轮守至河水干后。如有违误者,罚银五两,修海公用。一开纂水干之后,河水复出,仍系各沟水头守入海内,照班分放。如有沟众紊乱班次,罚银五两;如有水头违误,罚银五两,俱入修海公用。水头闵士俊、苏清、朱必达、苏廷秀暨众姓老幼人等同(立)。”(23) 轮放大海水规碑记[G]//保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保山碑刻.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41. 保山县南门外上、下哨因分水需要,共同定立水规,而各村参与水规制定的人就是水长。“计各村水头芳名录列:汉庄水头董连贵、董连成;唐官屯水头许全福;薛家屯水头李发新;姜家屯水头姜有荣。下哨管事常忠、张连佐;湾子水头王春玉、李连荣;中沙河水头陈文高、常应春;下沙河水头乔松有、乔永春;大石庄村水头赵士达、杨发傅;小石庄村水头杨成满、杨成新;辛家庄水头张相;杨官屯水头崔兆全、陈华;武家屯水头李忠、梅本、顾培;朱官屯水头朱发澄、徐有材;唐官屯水头李湘、白凤林;方官屯水头董成富、黄堂;北哨屯水头王福、王有伦;南哨屯水头邵连武、朱向荣。同治十一年岁次闰二月二十日,南门外绅士苏学仁、段崇玉等,下哨管事常忠及各村水头人等同立石。”(24) 公立水案碑志[G]//政协保山市隆阳区委员会.保山市隆阳区政协文史资料:第十四辑:隆阳碑铭石刻.政协保山市隆阳区委员会.[出版时间不详].
第一,清代水利兼衔制度提高了云南官员对地方水利发展的参与度。在施行水利兼衔制度的地方,自道员开始,下至同知、通判、州同、州判、县丞、典史、主簿等官皆准加水利职衔,意味着清代云南各级政府机构当中的佐贰官员都肩负有发展地方水利的使命,从而形成兼衔水利的道员统领辖下兼衔水利的同知、通判,兼衔水利的同知、通判等官员直管治下兼衔水利的县丞、主簿等官吏的格局。而兼衔水利的县丞、主簿等官吏则与乡村水长制度连接。总体上看,云南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水利管理系统,使云南全省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都能有专人负责管理,责任落实到人,极大地改善了云南水利发展格局。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云南的巡抚虽没有明确兼水利职衔,但自督抚而下各级府、州、县主官都有管理一方水利的职责,兼衔水利的官员也都是在其领导下开展地方水利发展工作。
宜良县的响水沟流经宜良、陆凉、路南三州县,三地田亩均沾其利,也共同修浚维护。乾隆四十七年(1782),为保持响水沟水利功能的可持续发展,三州县共同订立水规,将响水沟分为七段,按要求疏浚、修挖,违者禀官究治,同时设立水长,负责水利工程的日常管理工作。“嗣后凡有沟道坍塌,都需按照济田亩多寡,共同出夫修筑,勿得观望延挨,彼此推诿。倘有恃强不行出夫修筑者,许该管沟首水利查勘具禀,以凭提究,各宜凛遵毋违。特示给响水沟沟首、水利人等永远遵守。”并且沿河各村都有相应的水长负责河道管理事宜,“至于七村水利,务需上下不时巡查,恐有坍塌淤阻,即按田亩派夫修筑。如有推诿不前,因循怠玩者,沟首禀官究治;如有人夫抗拗者,水利亦指名赴官。车田水利:王尧侯、王希尧、龚、淳、王谈;大村水利:李茂、蔡琼、蔡全、何显堂;蔡家营水利:罗士珍、蔡胜朝、蔡允中、蔡荣祖;中村水利:白天贵、方发科、周起;摆夷村水利:周阳甫、李有先、舒发甲、蔡显祖;新村水利:李沛、张焕、李槐;前所水利:李伯才、杨槐、赵莲升。公议监管大坝、龙口水利李希颜、仕家骐,公议上下巡查沟道,催收上前所军田水租水利龙云淳、李伯才、王琰、蔡全、何显堂、蔡允中、蔡荣祖、署发甲。以上十人务宜尽心协办,勿得怠情偷安,如违,赴官惩处……八村沟首、水利、田户人等暨石工阮仝立 ”(25) 响水沟碑一[M]//郑祖荣,周福恩.宜良县碑刻.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32.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据民乡士民李恒……任家骐等禀称,响水坝水沟一道,有济田亩,现有沟首、水利不时疏通,得以田亩及时灌溉。”(26) 响水沟碑二[M]//郑祖荣,周福恩.宜良县碑刻.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37. 将水长的职责具体到人,对维护响水沟的水利功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水利兼衔制度实施高峰期的地理范围几乎覆盖云南有行政建制的绝大部分地方。守巡道员、同知、通判等官兼署水利职衔后,清代云南官吏当中与水利有关的官员人数占到很高比例。按《清朝文献通考·职官》部分的记载,乾隆年间一段时间内云南的文职官员大致为429人。其中,绝大部分佐贰官员都加水利职衔,再加上督抚等本身就肩负水利职责的各级正职官员,云南全省范围内与水利发展有关的官员人数将达214人,近50%的云南文职官员有发展地方水利工作的任务,其规模和作用不可小觑。
三、清代水利兼衔制度对云南的作用
清代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的施行,对云南水利职官制度、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社会治理等产生多方面影响。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清代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普遍施行以后,佐贰官员成为云南水利发展的重要负责人群,但并不意味着督抚等各级“一把手”就与水利发展事务无关。事实上,各级主官仍然是云南水利发展的主要领导力量,这在全国也是通行的制度。吏部等多部合议河南布政使刘慥奏疏的时候,除了同意其提出的让各地佐贰官员兼衔水利的意见外,还特别强调地方主官在发展当地水利事务上责无旁贷,如果不尽心水利事务就会被“议处”。“但各省事件,责成全在大吏。凡一切勘修工程,该督抚应揆度地方情形,随宜办理。不得徒委厅道等官,乃至有名无实,将该督抚一并交部议处。”(17) 《清高宗实录》卷549,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丙戌条。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是长征精神的集中反映,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4]
水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乡村的延伸形式,适应云南地方水利发展需要,为清代云南水利事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水长制度完善了云南乡村社会的水利管理体系,规范了基层水利设施的修建维护,使得乡村水利设施从兴修到维护都有专人负责,为云南基层水利事业的健康发展打牢了基础,对保证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二是水长除有管理地方水利工程、分配水资源、调解乡村纠纷等职责外,也具有代表百姓与官方接触、和邻村交涉的功能。水长作为国家水利制度和政策在云南乡村社会中的具体执行者,除宣传国家水利政策和推动政策落实外,也代表政府对地方水资源进行管理,是国家统治力量在云南乡村社会的延续,是国家治理制度在基层社会的代表。三是在传统农业社会,水利兴衰影响着一方社会财富的收益情况,关系着国家统治的稳定和治理好坏,对云南来说更是影响边疆稳定的大事,从这个角度看,水长制度对维护清朝在云南的统治同样具有积极作用。
清代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开始施行及其结束的时间,难以准确界定。一般认为,有确切记录的起始时间是雍正十年(1732),鄂尔泰在奏疏中请求将云南同知、通判等官皆加水利职衔,得到雍正皇帝批准后开始施行。道光二十一年(1841),永北厅知县熊守谦兼同知衔主要负责发展水利,“以兴修云南永北厅水利,予知县熊守谦同知衔”(27) 《清宣宗实录》卷344,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己丑条。 。亦可看做水利兼衔制度的一种形式,可知其时这一制度仍在云南施行。就全国来看,水利兼衔制度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部分地区仍在施行,云南的情况应该也不例外。可见,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施行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曾在云南为官的人大半参与过云南水利发展事宜,对云南水利发展起到过推动作用。
其次,阅读作为作文素材的来源,需要学生在平时课外阅读或是看到课文中的好的词语和句子时,摘抄到一个本子上,收集起来,便于使用时查找,例如“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名诗。又如朱自清在《春》中是这么描写南方春雨的,“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胸中有墨水,下笔之时才能够信手拈来、旁征博引。
从水利职官制度改革的角度看,清代为实现对地方水利管理全覆盖,在云南范围内广泛推行水利兼衔制度。大量的同知、通判、典史等官兼署水利职衔,甚至兼衔水利的文职官员一度接近云南文官总数的50%。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的施行,实现了国家对基层水利的直接管控,有利于政府主导地方水利发展。同时,水利兼衔制度打通官方和民间的治理隔阂,实现国家统治和乡村治理的有效结合,在政府行政权力难于触及的乡村社会,同样建立完善的基层水利管理制度,使国家和农民、政府和百姓、中央和地方、内地和边疆通过水利兼衔制度整合到一个系统里面。国家、地方和乡村因水利兼衔制度而结成一个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完成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性建构。
第二,清代水利兼衔制度施行推进了云南水利事业发展。康熙《云南通志》载云南水利工程233处,雍正《云南通志》载1 045处,道光《云南通志稿》载1 067处;光绪《云南通志》载1 296处,光绪《续云南通志稿》载1 238处,《新纂云南通志》载1 274处。单就数量看,清代云南水利工程由康熙年间的较低发展水平,经过康、雍两个时期休养生息和励精图治,到乾隆初期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并保持了一个相对较长的平稳发展时期,一直延续到道光年间。由此可见,水利工程数量增幅与水利兼衔制度施行基本呈正比关系。这与清代云南水利兼衔制度施行由点到面、由局部到全省的发展历程相吻合。
水利兼衔制度在云南推行以后,各地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得到新修或维护,水利工程数量一度呈现出急剧增长的势头。可以说,水利兼衔制度使清代云南水利发展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清代云南水利发展还有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值得一提:一是清代云南水利工程不但数量上增加,质量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从史籍中有关水利建筑材料的大量记载可窥一斑。清代水利设施采用包括石材、椿木、铁器等耐用建筑材料修建,堤、坝、闸、塘等设施的寿命明显比土坝要长,抵御水患的能力也更强。二是重点水利工程的维护修缮能力明显提高。云南地处高原,群山环峙,溪流蜿蜒于河谷、坝子之间,农业经济植根于大大小小的盆地之中。有学者统计,云南面积大于1平方千米的坝子数量为 1 868个,总面积为25 687.65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面积的6.25%(28) 童绍玉,陈永森.云南坝子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22-23.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水利工程以中小型居多,大部分的水利设施都处于坝子中间,其水利功能的发挥具有局部性、小规模的特点。个别地区如滇池、洱海流域的水利任务也颇为繁重。因这样的现实情况,清代云南建立了水利工程修缮维护的基本制度,规定各级官吏对辖地内水利设施要做到每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如果出现突发的严重水灾,要不遵此例、及时进行抢救性维护,这极大地提高了清代云南水利抵御风险的能力。三是清代云南水利兼衔制度施行以后,推动云南水利由传统水平较高的昆明、澄江等汉族集中地向边疆的保山、思茅、西双版纳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展。另外,在全省各地坝子水利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山区、半山区的水利能力也不断提高,并产生了枧槽灌溉、地龙灌溉等极具特色的水利发展形式。总之,清代水利兼衔制度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云南水利发展水平。
天空细雨如乱丝,河上春潮初泛,间或有焦黑的断木和星散的水莲花自上游漂来。一叶敞蓬小舟,拴在一棵才冒黄芽的桑树腰间。春草丛中的桑树瑟瑟抖动,缆绳绷得梆紧,发出努力挣扎的“嘎吱”声,仿佛立刻就要断掉。一个人坐在船头,簔衣竹笠,两眼空茫,仿佛置身尘世之外,生死荣辱,都可以无动于衷。有人在对岸把手拢在嘴前喊:“过河!”摆渡人立即站了起来,手忙脚乱地解下缆绳,惊走野鸟一片。
第三,水利兼衔制度的实施促进了清代云南农业的发展。水利兼衔制度施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更好地发展地方水利,推动农业进步,增加社会财富。从云南水利兼衔制度施行的效果来看,确实达到了预期目的。首先,水利兼衔制度施行以后,云南水利发展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从而使大量抛荒土地得以复垦,许多荒地、无法耕种的土地得到开发耕种,为云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顺治十八年(1661)云南耕地面积为52 115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增至64 817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更是高达83 363顷(29) 秦树才.清代前期云南农业发展原因初探[J].昆明师专学报,1990(1):80-86. 。到1725年,云南的新垦耕地面积达125万亩,到1800年,云南新垦耕地面积在200万亩以上(30) [美]李中清.清代中国西南的粮食生产[J].秦树才,林文勋,译.史学集刊,2010(4):72-79. ,水利兼衔制度的施行对云南耕地面积增加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次,水利兼衔制度促进了云南水利的发展,随即带来耕地面积的增加,进而使云南粮食产量有了大幅提升,解决了云南地方百姓和驻军的粮食供给问题。明末清初云南饱受兵燹,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清初的很长一段时间,保证粮食供给一直是地方督抚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缓解粮食紧张的状况,除了采取采买、转运等急救措施以外,发展水利、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是一项标本兼治的措施。通过持续努力,到乾隆时期,云南的粮食供给问题已基本解决,文献中关于兵食的记载开始减少,雍正年间和乾隆前期营建的兵食体系已经稳定地运转起来(31) 彭建.康雍乾时期云南兵食问题研究[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6(9):27-32. 。
第四,水利兼衔制度的实施对促进清代云南人口增长产生积极作用。水利兼衔制度的施行,在推动农业进步、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人口增长。《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一》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云南人丁为117 582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为158 557人,雍正二年(1724)为145 240人。依照倪江林先生的回测法,这三年云南人口分别应为1 270 174人、1 712 804人和1 124 180人。道光《云南通志》据《案册》载:乾隆十三年(1748),云南有民屯男妇1 946 173人,乾隆二十三年(1758)为2 022 252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为2 224 234人,嘉庆元年(1795)为 4 088 252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增至 6 067 171人。道光十年(1830)云南全省有“民男妇”4 809 391人,“屯男妇”1 743 717人,合计6 553 108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6%。另据道光户部清册统计,道光二十年(1840)云南人口约为7 019 000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全省人口约为706.6万人,此后缓慢增长,道光三十年(1850)约有737.6万人,平均每年净增3.5万余人。
咸丰元年(1851)云南人口为740.3万人,咸丰五年(1856)达到752.2万人。光绪十年(1884)锐减到2 982 664人(广南、镇沅两县未编审在内)。主要原因是咸同年间云南和全国一样,处于农民反抗斗争高潮中,农民起义战争中大量人口死丧流亡,致使人口数大幅度下降。《续云南通志稿》说,云南自咸同军兴后,30余年间无人口数字记录。光绪十八年(1892),全省人口恢复到1 202万(32) 李寿,苏培民.云南历史人口述略[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3):23-29. 。显而易见,清代云南人口变化的情况,基本上与云南水利工程的数量变化态势相一致。水利兼衔制度的施行促进云南水利发展,水利发展推动农业经济进步、粮食产量增加,从而使得云南人口能够得到稳定增长。
最后,水利兼衔制度的施行,对清朝巩固在云南的统治起到重要作用。政治和水利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政治稳定有利于地方水利发展,地方政府才会有力量投资水利事业,兴建水利工程和提供资金修缮水利设施。同时,随着水利发展,大量土地得到开垦,粮食供给充足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对政府统治的长治久安作用巨大,当双方处于良性互动之时,必然会造就社会繁荣。相反,一旦出现政治动乱、社会不稳定,政府和民间都无力投资水利,大量田土抛荒,人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之时必有水利急剧衰落的局面;而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必然带来农业经济凋敝,最后将加剧政治不稳定。
从整个清代云南水利发展与地方政治的关系来看,水利兼衔制度的施行,使国家力量深入到云南基层社会当中,政府通过水长制度直接参与农村水资源的分配,实现国家对云南基层社会的管理,进而达到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的目的。大量水规、分水制度的建立是乡村统治秩序稳定的重要保障之一,也是清代云南乡村治理规范化的表现。
The Practice and Function of the Qing Dynasty’s Dual-post Water-affairs Officials System in Yunnan
WU Liancai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Yunnan 653100)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Yunnan; the dual-post water-affairs officials system; system of water chiefs
Abstract :The system of dual-post water-affairs officials of the Qing Dynasty began to practice in Yunnan in the tenth year of Yongzheng (1727), and developed to the highest point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Qianlong. The government formed a more complete the dual-post water-affairs officials administration in Yunnan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assistant officials and other auxiliary officials, such as the tittles of Tongzhi and Tongpan, and continued to carry out the reform in combination with local reality. The system of water chiefs, as the extension and supplement of the rural society, provided a basic system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ss-roots water conservancy in Yunnan, thus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 Besid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ual-post water-affairs officials system raised the participation of Yunnan officia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Yunnan. Accordingly, the water system, which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stability and the ruling of the Qing Dynasty, promoted the population growth of Yunnan.
[作者简介] 吴连才,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云南水利史。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南盘江流域云南水利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QN2017035)阶段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506(2019)02-0078-09
标签:清代论文; 云南论文; 水利兼衔制度论文; 水长制论文;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