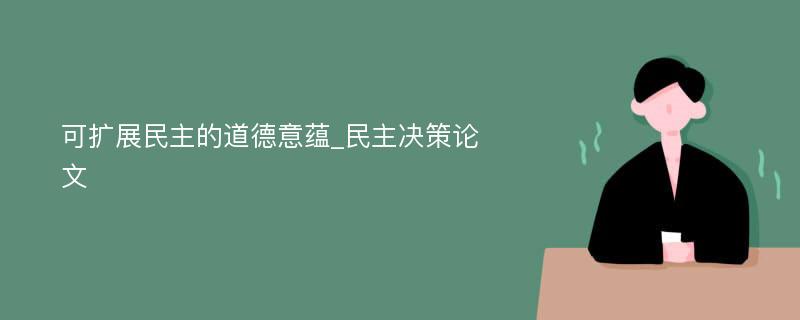
扩展性民主的道德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扩展性论文,民主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既含有“民主理念”之义,也含有“民主程序”之义,这种复杂性决定了民主本身并不是一个具有绝对正面意义的道德范畴,例如,经过民主程序作出的决断对于一些人来说不能必然和充分地保证公正。正因为此,一方面出现了对民主的抨击,如责任伦理学家忧那思(Hans Jonas)有关在生态危机独特的历史境遇下必须放弃民主决策程序、实施“生态专制”的呼吁,另一方面产生了共同体主义(也称“社群主义”)者试图从外部将道德内容嵌进民主形式的努力,以及另外一些学者所倡导的用扩展性民主机制来激发、提升民主决策之伦理内涵的方案,这就引发了西方政治伦理学界有关民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民主程序能否维护和保障道德要求等问题的论争。本文现对这些论争作一批判性考察。
一
民主意味着一种组织形式,即人民的自我决定与自我统治的形式。从理论上讲,按照民主本身的规范性要求,每一位公民自我决定的权利都应在民主中平等、公正地得到实现。然而从实践上看,民主却无法解决自身“理念”与“程序”的统一问题,无法完全通过程序来实现理念的规范性要求。恰恰相反,民主程序的两个基本缺陷业已暴露无遗:
其一,由于公民与公民之间观念与利益的差异,民主程序不可能使每一位当事人的自主意志都得到尊重,它只能尊重大多数人的意志。正如贝克尔(Werner Becker)所言:“实际上民主共识决不是真正的共识,因为它无论如何都总是靠绝对多数达成的”(Becker,S.52)。总之,民主程序的一项根本原则是多数人决定原则。但是由这一原则支配的民主程序只能体现对多数人自我决定权利的尊重,而对于下述两类人却意味着永久的威胁:一类是身处民主决策程序之内但并不认同多数人意志的所谓少数派群体,另一类是本身无法作为在场的当事人参与民主程序但其命运又为民主决策之结果所左右的那部分人群(如尚不具备或已经丧失自我意识的人及未来人)。换言之,从由多数人(或在场人)决定原则支配的民主程序中,逻辑上只能推出多数人(或在场人)自主权利的实现及其公正需求的满足,却推不出少数派群体及无法参与决策的人的自主权利的实现及其公正需求的满足;相反,对于这两类人来讲,民主程序及决策结果可能意味着他们权益的牺牲,意味着强制与不公正。因此,“民主合法的决策并非必然而然是公正的”,“一种合法的程序也可以导致错误的决断”(Wellmer,S.278、274);对于这两类人而言,“这样一种现实的民主程序不会为人权与基本权利提供足够的保障”(Alexy,S.263)。这就呈示出了民主程序与民主理念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是民主理念所规定的对每个人的自主权都应尊重并使之得以公正、平等实现的规范性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制约着民主程序的多数人决定原则。公正、平等的规范性要求与多数人决定原则这两个要素从内容上无法相互还原,从逻辑上无法相互推演。
其二,民主是通过一套复杂的运行程序体现出来的:公民投票直选出自己的代言人,民选代表组成的议事机构依照多数人决定原则作出决策并委托政府予以贯彻执行。这样一来,在代议制民主中普通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就受到巨大限制;与此同时,国家机器、政府的行政权力则日益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这种日趋独立化的国家机器有可能作出与广大公民意志相悖的决策,从而损害大多数民众的权益。
既然合法的民主程序无法必然和充分地保障决策的内涵符合尊重人权、人的自决权、平等权等道德要求,即程序公正无法必然和充分地保证实质公正,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设想与尝试,试图化解道德要求在民主制度中所面临的危机,增进民主决策的道德质量。在这里,第一个需要提及的便是忧那思所提出的摈弃民主程序、实施“生态专制”的极端方案。
忧那思的方案是针对合法的民主程序不能充分保障无法参与决策程序的未来人的基本权益这一重大缺陷的。在他看来,在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今天,西方世界所创立的那种自由已经难以为继,以常规的方式根本就无法推动民众对习惯化了的现实利益的主动放弃。因为民主程序中所谓集体的意志就是选民的意志,而选民又总是理所当然地把自保和自身需求的直接满足摆在第一位。对于选民而言,他们自己未来几年的工作与生活状态远比星球的前途更为重要。因而在经济与环保之间,选民会选择经济;在眼前利益与长远的义务之间,他们会选择眼前利益。于是忧那思提出,在极端情况下,为了人类生存基础的维护及未来人类的利益,人们必须放弃民主决策之程序,实施一种启蒙化的生态专制,一种“人类之拯救者的专政”。(Jonas,S.15)忧那思的方案引起了两种针锋相对的反响。魏茨泽克(Ernst Ulrich Von Weizsaecker)认为,在自由民主无法解决生态问题的今天,只有依靠国家来加强经济现象细节上的控制并自上而下地规定公民为了环保和后代的利益所必需的举措。德国社会民主党环境问题发言人米勒(Michael Mueller)更是宣告:我们已完全进入了一个强制政治的时代。而波普尔(Karl Popper)则控告忧那思是民主理念的叛徒和独裁者的朋友。 著名的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更是指出,如果是为了人类的持续生存而赋予一小撮专家、哲学王以对公民的决断、选举权利进行限制的特权,“那么我就要怀疑,这样一种持续生存是否值得”。(Dahrendorf,S.11)当忧那思强调生命延续是自主意志存在的前提条件的时候,达伦多夫则指出受奴役的生存没有丝毫的价值,自由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在达伦多夫的论述中,蕴涵着这样一种理念:我们并没有穷尽民主程序的效能,对公民的明智的判断力也还没有理由丧失信心,民主程序的缺陷应当能够通过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而得到弥补。
第二个需要提及的是共同体主义的方案。它的特点在于:不指望单子式的相互独立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自然形成合乎道德要求的表决结果,而是认为要保障最终决策的道德性,必须在进入民主程序之前便将零散的社会成员结成一个统一的道德共同体,就像将原本散布在城区四处的街头乐师组织成一个和谐有序的大乐队那样,于是,分享着共同的善的理念的人们自然就能够将共同的道德意志传递到经合法的民主程序所作出的表决结果之中去,如此这般民主程序与道德要求之间的矛盾也就从根本上得到了化解。可见,共同体主义方案的特点是:坚信不论从内容上还是逻辑上讲善的理念都优先于程序公正,主张从外部将道德理念嵌入民主程序之中,从而先定地保障决策的道德含量。
然而,共同体主义方案的最大难点,在于如何将一个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代公民社会,整合成一个所有社会成员均拥有高度的自觉认同意识的道德共同体。共同体主义者十分向往能够将社会与国家塑造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家庭式的集体,所有的成员都分享着共同的善的理念并借此相互维系在一起,一种崇高的团结意识构成了这一使每位社会成员都能产生归属感的命运共同体的灵魂。问题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共同体意识很难超出家庭、公司、微型的村落与社区、志愿者的社团与组织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外不可能形成如同家庭、社团里那样密切的交互关系与关爱情感。原因并不复杂:一个人与其家庭成员或工作岗位上的同事之间的联系,同他与在街上随便碰到的行人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就连共同体主义者泰勒(Charles Taylor)也不否认;他说过,在大城市中公民难以产生整体认同的意识。(参见Nusser,S.253-254)所以努瑟(Karl-Heinz Nusser)指出:“在许多共同体和有约束的组织中的那种‘我们’之感受,到了国家政治层面就不可能是同一回事”(Nusser,S.262)。共同体主义方案的失误,在于混淆了传统社会意义上的道德共同体与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区别。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最明显之处,便是其人际关系超越了血缘、地域的局限,广博而又复杂。文化背景、宗教渊源、政治理念、社会归属、价值诉求、利益取向等的差异,使人们难以在宏大的社会层面形成传统社会意义上的单质的道德情感和像家庭中那样强烈的关爱、奉献的意识。正如拜耶慈(Kurt Bayertz)所言,这种意识与精神的流失就像传统手工艺由于机械化的出现而消亡一样令人无可奈何(Bayertz,S.327)。于是,在现代社会,传统的道德共同体已经无可挽回地被一种政治共同体所取代,而政治共同体由流动性的“我们”所构成。由于“政治并非,而且首先并非是由对伦理的自我理解的追问构成的”(Habermas,S.283),因而对利益关系的调节而非对共同价值理念的追求构成了共同体的原始动力。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共同体本身没有任何道德涵义,而只是说与“过去的强烈的博爱”及其“强制”的特性(Bayertz,S.327)不同,政治共同体所包含的道德只是一种消极的、稀薄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即“消除歧视与痛苦以及对处于边缘状态的人群的相互顾及”(Habermas,S.7)。由此可见,共同体主义试图回归传统、从而塑造“道德公民”的方案,在一个道德共同体赖以生成的基础不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历史境遇下,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二
如上所述,欲克服民主程序的两个基本缺陷,解决民主制度中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既不能像忧那思主张的那样全然否定民主程序本身(因为那样就会违背大多数人的自主意志,退到专制体制的死胡同),也不能指望共同体主义那种“过于理想化”(哈贝马斯语)的方案。真正值得考虑的方案乃是实施扩展性民主,这就是在尊重由多数人决定原则所支配的民主程序及作出的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在尊重和维护民选政府的法律权威的前提下,采取某些补救措施,从而一方面尽最大可能满足少数人群体及未来人等的需求,提高民主法规的道德含量,另一方面缓解有着独立化趋向的国家机器与民众意志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些补救措施主要是建构“宪法法院”和“公共领域”机制。
主张依靠独立的宪法法院来解决民主制度中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主要代表,是德国法哲学家阿雷克西(Robert Alexy)。在他看来,宪法法院的作用,一是对政治程序进行反思,二是根据人的基本权利的论据来反驳经民主程序作出的某些决定,包括违宪的法律规定本身。这样可以使多数人的或政府的决定获得一个对其正确性、合宜性进行重新审视和纠错的机会,就像人们在法庭上不服判决,可以上诉到更高一级的法院那样。阿雷克西认为,只有宪法法院提出的论据能够在社会公众与政治机构中得到严肃的思索与广泛的讨论,“只有这种在公众、立法者和宪法法院之间的反思过程持续下去,才谈得上成功地将人权机制化于民主的宪政国家之中”。(Alexy,S.264)目前采用宪法法院模式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且以德国为典型。但也有些法制国家或是因为没有成文的宪法而无法设立宪法法院,或是认为宪法上的争执由于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并不适于诉诸法院裁决而拒绝了宪法法院的模式。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宪法法院存在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个体权益受到多数人意志或国家机器的侵犯,因而宪法法院的存在本身对于民主程序以及国家权力无疑是一种打击。但如果我们将民主程序及民选政府只是视为一种不仅以实现多数人的意志、而且更是以维护人权的神圣性为目的的手段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有限的打击就是可以而且应当承受的。
主张诉诸公共领域中的公开商议来解决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主要代表是哈贝马斯、泰勒及沃尔策(Michael Walzer)。尽管在如何评价所谓道德共同体的问题上,哈贝马斯与泰勒及沃尔策等共同体主义者的立场完全不同,但在倡导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的政治参与的问题上,他们却拥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哈贝马斯等人倡导公民社会、强调公共领域的作用,目的也在于克服民主程序的两个基本缺陷,即一方面解决就少数派群体及未能参与决策程序的未来人而言,民主程序与道德要求之间的矛盾问题,另一方面与日趋独立化的、可能与广大民众的意志严重相悖的国家权力相抗衡。在沃尔策看来,公民社会是超越国家的理想场所;在哈贝马斯看来,公民社会是民众进行社会交往、参与政治决策的广阔平台。需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等强调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并非旨在削弱或取消体现为国家行政权力的民主程序,而是认为仅靠民主程序本身无法化解其与道德要求之间的矛盾,所以才需要另寻一个平台,从而形成一股能够对单纯的民主程序及其决策进行修正的力量。因而不论是哈贝马斯还是泰勒,都强调两个要素的协调一致,用后者来补充前者:一方面是法制国家中“体现在议会党团之商议上的机制化了的”意志塑造(Habermas,S.288、291),即机制化了的意见与意志的建构的形式化程序(同上,S.292),用泰勒的话讲是作为对选民意志进行调节的政党系统(参见Nusser,S.257);另一方面则是公民社会的非形式化的政治公共性交往网络(Habermas,S.288、292),用泰勒的话讲是公民运动与公民参与活动(参见Nusser,S.257)。哈贝马斯与泰勒共同强调的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公民的意愿与理念得以直接表达的一种合宜的空间——由社会媒体、因特网、公众会议、全民公决、示威游行及民意调查等活动构成。在18世纪的欧洲,这一空间仅属于有教养者、启蒙了的阶层的天下,而今天,它却向所有社会公民开放。在公共领域中,行为主体是普通社会公民,作用对象是国家行政权力,商议、论争的主题是公众话题、急需集体负责与决策的事务。这样,公共领域就如同一个连接圈,把这一端的国家行政机构与另一端的广大普通公民及其组织直接联系在一起。根据启蒙运动的观念,人们通过公共领域这一平台可以在无外在压力的前提下对政府的民主决策进行商谈性的审察与批判性的检验,对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结果是公开言论的交流力量也能迫使决策作出修正”(Wellmer,S.279),从而达到对政府行为进行制约乃至纠错的效果。就此而言,在泰勒的作为一种“集体性自我统治的系统”的民主概念中,公共领域拥有着一种“本质性的功能”(参见Nusser,S.256)。联邦德国自1968年学潮以来的政治与社会观念的演变为此提供了明证:“68运动”促使了所谓“基础民主”理念的深入人心,即人们感到代议制民主并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自己的参政权也不能完全托付给某个政党,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基础民主的建构过程,即取决于每位公民随时参与各级政府的决策。基于这一理念,民众们自发地组织起来,积极投身到国家与社区的事务之中:无论是建造核电站、修建高速公路、改造城区,还是保护森林、修建儿童游艺场,他们都要表达自己的主张,影响各党派和政府的决策。这场深刻的公民运动在环境保护领域结出了硕果:一方面是70年代末先是以反对派身份出现、而至90年代中叶就已顺利挺进联邦议院的绿党的建立,另一方面则是在生态组织、大众传媒的推动下国家反环境污染法的相继出台。公民运动的开展和基础民主的普及,不仅使政治而且使整个社会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自由、宽容与开放。总之,只有依靠民主程序与公共领域两种要素的内在关联,依靠“法制国家中机制化了的意志塑造与由文化所激发的公共领域之间的交互作用”(Habermas,S.291),依靠公开商谈对民主决策施加的连贯性影响,才能实现政府的行政力量、企业的经济力量和公众的团结意识三种社会资源的平衡状态,最终“达成理性和公正的结果”(同上,S.286);才能导致“民主的道德化,也就是说,民主能够从过去的不公正的泥沼中得到拯救”(Wellmer,S.280)。就此而言,公共领域已成为公民社会时代最重要的民主调控机制:它的存在及作用的增强一方面为增进国家对矛盾与冲突的承受力从而实现社会的和平稳定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则为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勃勃生机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三
设置并充分依靠独立的宪法法院的作用以及诉诸公共领域中公民公开的商谈讨论,均是对民主程序的补救措施。这些补救措施被称为扩展性民主;践行扩展性民主的结果,便是民主决策道德含量的提升。所谓使“民主更加道德”,就是扩展性民主所体现的道德意蕴。扩展性民主展示的精神实质,在于公民不仅要为民主程序的产生及运作负责,而且还要为民主决策的性质及后果负责。公民不再像在传统的自由政治体制中所通行的那样,仅仅满足于将自己的“主权”部分地托付给社会精英,而是要更加积极、广泛、深入地参与社会政治进程,对政策的形成与变迁自始至终(也就是说即便在法定的选举期之外也能)施加自己的影响。然而,扩展性民主或许能够提升民主程序及决策的道德含量,但永远也不可能绝对担保民主决策的道德性。恰恰相反,不论是诉诸宪法法院,还是借助于公民公开商谈的方式,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都不排除将正确的决策予以否定的潜在危险。特别是就公共领域而言,泰勒将公共领域与理性等同起来,界定公共领域拥有在政府权力之外建立一种达到共同理念的理性对话之功能,这种看法其实高估了公共领域的作用。黑格尔早就指出,公共意见值得尊重,但当其所呈现的只是未加深思熟虑的任意的谬论时,也就不值得尊重。更何况公共领域本身也在经历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因此“公共领域并不是理性之自我驾驭的过程”(Nusser,S.257);它所蕴含着的道德潜能,也并非绝对具有规范性的意义。总而言之,扩展性民主理念的初衷是可圈可点的:在一个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的时代,在找不到一个人人认可的最高的道德裁判官的今天,除了法定的民主程序之外,多一项制约机制,多倾听一些“噪音”,多关注一些反应,多一分思考,多一场论辩,少一点专断,对于人权的维护应当是有益的。然而,民主程序本身也好,经过扩展性民主机制对民主决策进行校正也好,均不足以对民主程序之成果的道德性提供百分之百的担保。当然,这绝不构成对民主程序及扩展性民主予以否定的理由,相反地,这只能使人们纠正以前对民主的不切实际的过高期许,从而在对民主的本性获得一种更为深刻的认知的基础上,对民主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信念。
首先,民主没有替代物 如前所述,民主本身并非无条件地意味着道德,但民主中拥有丰富的道德内涵。特别是从对扩展性民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坚持民主的原则,需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但民主原则同时也主张关注少数人的心声,尽可能倾听所有公民的观点。民主维护大多数人的权威,但同时也尊重少数人对民主决策的保留意见,尊重少数人对这一决策形成自己的道德评价,尊重所有的人对道德拥有自己的看法。 正如德国政治学家古根伯格(Gernd Guggenberger)所言:“恰恰是当我赞同宪法的精神时,我才认为,当政府或者大多数人在一个根本性、决定性的问题上犯了错误的时候,我就可以……采取公民的不顺服的手段。而民主最终至少是不会禁止这一点”;民主不会扬弃“对国家的顺服与良心义务之间的冲突。我们必须伴随这种紧张关系生存”。(转引自Wehowsky,S.57)由此可见,民主蕴含着对人的自主性的尊重这一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单就这一点来看,民主就呈现出任何专制政体都难以企及的竞争力。民主能够使人们产生出一种基本性的政治道德直觉,“这是一种根据民主与专制间的对立之标准来判断善与恶的道德直觉”(Becker,S.42)。民主没有替代物;如果有,那就是专制以及历史教训反复验证了的专制统治的恶果。民主或许不是最好的政治生活形式,但正如丘吉尔所言,自由民主是所有坏的国家形式中最好的形式。
其次,公正在民主的前提下意味着一项未竞的事业 民主的根本原则在于多数人决定,而多数人的决定未必合乎道德的要求,所以就需要有扩展性机制的匡正。扩展性民主的存在意味着在民主的体制下,道德要求的满足是在一种动态的作用与反馈机制中逐渐实现的。就像宪法和法律总是在经历着修正那样,公正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要求,在民主制度中也总是处于一种正在来临的状态。也就是说,公正既不意味着完美的理想王国,也不是指决策与合理性之间天衣无缝般的吻合一致,而总是呈现出一幅暂时的、相对的、未竞的图景:“对于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任何民主形式而言,情况都是一样,即公正只是正在来临”(Wellmer,S.280)。总之在民主的环境中,公正并非体现为一种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目标,而是像一块遥远而又颤动着的靶子,吸引着我们的共同行为组成的射击器上的准星;我们对准着这块靶子,持续地调正着角度;我们坚信越对越准,但总是不知哪一天可以扣动扳机,击中目标。这就决定了在一个民主的制度中,政治哲学似乎难以体现为一部以自由、平等和公正为内涵的清晰详尽的教条式的理论全书,而仅仅是表现为一种由基本的自由、平等和公正之原则主导的理论与实践框架,更准确地讲,表现为一种以公正、平等为目标的自由的永无止境的批判性的活动。认可民主的这种有限性、不完满性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贬低,恰恰相反,这种认知提示着我们应“以正确的方式来礼赞它”(Wellmer,S.290)。
最后,民主的根本任务不是整合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而是使公民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得到调解公民社会的基本特点在于每一位公民都有权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益,追求自己的理想目标。人际间价值信念与切身利益上的差异使人们产生了对民主程序的需求。基本的民主程序以及扩展性民主机制就是对公民在信念与利益上的矛盾进行调解的工具。这一调解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公民各种道德理念的充分表达与互动作用,而且更取决于利益间的平衡,取决于必要的让步、牺牲以及妥协。正如贝克尔所言,“在民主中社会公正之存在并非取决于学术上推导出来的基本原则,而仅仅是作为在社会政治利益方面的均衡中产生的历史上相对的结果”(Becker,S.53)。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的取向“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政治意志形成的输入,而是国家活动之富有成效的结果的输出”(Habermas,S.287);民主或许并不能对民众意志作出一种准确的表达,“不如说民主是一种对政治问题及其不确定性与危险予以回答的可行的途径”(Nusser,S.258),“是对共同生活的最重要、最紧迫问题的解决”(同上,S.266)。民主的这种本质性的利益均衡、利益调节的功能也就为公民的不顺服行为设置了底线:当某些公民对民主决策不予认同且经扩展性民主机制也未能使该决策的性质发生改变的时候,对于这些公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在行动上遵守游戏规则,就是必须履行一个法律共同体中作为公民应尽的维护公共法律秩序的义务。我们或许可以放弃通过民主来实现自己道德理想目标的期许,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实践表明,民主最根本的价值在于解决冲突,维护社会整体稳定的效能:“民主的现实理想模式……在于以避免公民战争为目的的达成妥协的能力”(Becker,S.53)。
1 Alexy,Robert,1998,"Die lnstitutionalisierung der Men-schenrechte im demokratischen Verfassungsstaat", in Stefan Gosepath und Georg Lohmann (hrsg.), Philosophie der Men-schenrechte,Frankfurt am Main.
2 Bayertz, Kurt,1996,"Staat und Solidaritaet",in KurtBayertz(hrsg.),Politik und Ethik,Stuttgart.
3 Becker, Werner, 1996, "Die Ueberlegenheit der Demokratie", in Kurt Bayertz(hrsg.), Politik und Ethik,Stuttgart.
4 Dahrendorf,Ralf,1993,"Eine grosse,universelle Sicht",in Spiegel Spezial - Die Erde 2000,Hamburg.
5 Habermas,Juergen,1999,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Frankfurt am Main.
6 Jonas,Hans,1993,Dem boesen Ende naeher,Frankfurt am Main.
7 Nusser,Karl - Heinz,2002,"Expansive Demokratietheo-rien bei Charles Taylor,Michae Walzer und Juergen Habermas",in Zeitschrift fuer Politik,49,Jg.3.
8 Wehowsky, Stephan, 1995, Gespraeche ueber Ethik,Muenchen.
9 Wellmer, Albrecht, 1998, "Menschenrecht und Demokratie", in Stefan Gosepath und Georg Lohmann(hrsg.),Philosophie der Menschenrechte,Frankfurt am Main.
标签:民主决策论文; 公共领域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政治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