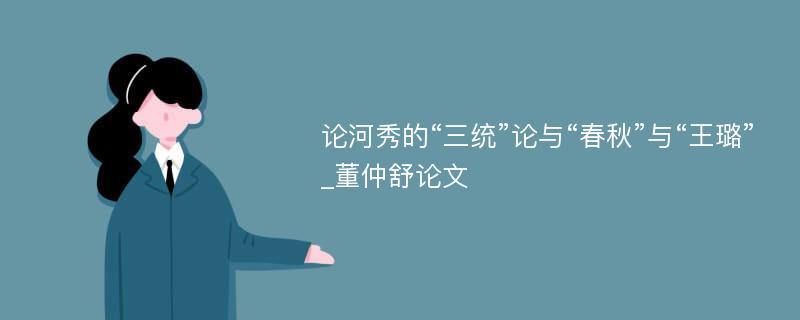
公羊“三统”说与何休“《春秋》王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羊论文,春秋论文,说与论文,王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统说”与“三世说”一样,都是《公羊》学派观察与解释历史演变以及动因的基本理论内容,属于《公羊》学派历史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公羊》家通过它来说明历史上各个朝代兴衰更替的内在关系,描述社会嬗递的逻辑脉络以及具体表现,为人们理解纷繁复杂的历史变易现象提供简明扼要的思想方法。这一理论的主要特征有两点,一是承认历史的变易进化性质;二是强调这种变易进化是循环复始的过程。由此可见,和著名的“五德终始”学说相同,“三统说”也是典型的历史循环进化论,它与“三世说”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构筑起儒家《公羊》学派历史哲学的理论大厦。
作为东汉时期最著名的《公羊》学大师,何休的历史哲学体系中,“三统说”同样占有非常显著的位置。何休一方面全盘继承了《公羊》先师有关“三统说”的主要内容,另方面又对“三统说”加以充分的丰富和发展。这表现为他通过自己的理论阐述,使“三统说”与“三世说”更加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春秋》王鲁”的理论命题,为《公羊》“三统说”作了圆满的总结。
一、《公羊》“三统说”的内涵与实质
“三统说”也即“三正说”,是儒家今文经学的重要原理之一,尤以《公羊》家阐述和发挥为力。它早在《尚书大传》中即有记载:
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寻根溯源,可以看到“三统说”的源头在儒学创始人孔子那里。孔子曾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虽然不是明确地谈论“三统”问题,但其所包含的因革损益、历史循环进化思想,则给后儒以极大的启发。他们正是以此为思想资料,逐渐建立起系统完整的“三统”说理论,用以指导“更化”,从事“改制”的:“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汉书·董仲舒传》)
大体而言,“三统说”的基本涵义是: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专属于自己的一“统”,“统”是受之于天的,旧王朝如果违背天命,暴虐无道,那么其“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将由另一个新王朝“承天应命”来替代。新王朝就必须“改正朔,易服色”,以表明新受天命的开始:“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春秋繁露·楚庄王》)
根据这一原则,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勾勒了“三统”的基本模式。他们把朝代的交替,归之于“黑统”、“白统”、“赤统”三个“统”的循环变化。认为得到哪一个“统”而为天子的,则其“礼乐征伐”就必须按照哪一个“统”的定制去处置,不可违背。以夏、商、周三代而言,它们分别属于“黑统”(天统)、“白统”(地统)和“赤统”(人统)。因此它们的制度便各有因革损益,并非凝固不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羊》家的“三统说”的确包含有历史变易进化的特色。可是,这种变易在《公羊》学家们看来,又是循环往复的过程,所谓“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正是“三统”的本质属性。新王继起,只能在“损文用忠”、“损忠用敬”、“损敬用文”之中盘旋,“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春秋繁露·楚庄王》)。这表明《公羊》家所宣扬的“三统说”变易性质是存在着明显的局限的,带有历史循环论的色彩。
《公羊》家以“三统”梳理历史发展脉络,理解社会嬗递动因,从而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历史哲学。为了更好地说明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以及新、旧王朝之间关系等问题,他们提出了“通三统”的命题。所谓“通三统”,又称存三统、存三正、通三正、通三微等等。它是指王者在改制与治理天下时,除了以自己独有的一统为本位外,还必须参照其他王者之统,“大一统者,通三统为一统。周监夏商而建天统,《春秋》监商周而建人统”(注:《公羊何氏解诂笺》,载《清经解》第七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419页。)。为此, 汉代《公羊》家系统地为汉以前的各代描绘规划了一幅“正某统”、“亲某”、“故某”、“绌某”的图画。这实际上是体现了历史演进中的延续性、继承性关系问题,至于其指导思想,仍是详近而略远、绌古而尚今。如在董仲舒看来,虞舜在殷代还是“故”的对象,可是到了周代,其位置则由夏所替代,而成为“绌”的对象了。由此可见,《公羊》家的“通三统”观点充满着历史进化变易的理性精神。
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对“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的关系问题略作考析,因为这对于我们深入探讨何休的“三统说”思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在这一问题上,一般的意见是将两者视为同一种类型的学说,都是“对于帝王兴废的解释”(注: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128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然而亦有一些学者认为“三统说”的性质与“五德终始说”有别,绝非同一类型的学说。崔适指出,古代无终始五德之说,其出现并与三统说窜乱混糅,是刘歆为王莽篡汉制造舆论的产物:“古无终始五德之说,则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其义何居?曰:此因三正,不缘五德也……是则易服色之义,自改正朔而出,岂由终始五德耶?《王莽传》曰:‘定有天下之号曰新,服色配德尚黄,牺牲应正用白。’是则别服色于正朔之外,而属之终始五德,亦自(刘)歆为(王)莽典文章始。”(注:《史记探源》,第4、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当代有的学者因循崔氏之说,批评顾颉刚视“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为同一类型学说的观点。如蒋庆认为:“通三统说是今文说,终始五德说是古文说。通三统说是要解决新王兴起改制立法时新王之统与前王之统的关系问题,终始五德说则是要解决某一朝代兴起其必然的宿命依据问题。三统说是为孔子作《春秋》当新王改制立法作理论上的说明,五德说则是为王莽篡汉作舆论上的准备。故通三统说是改制之说,终始五德说则是意识形态,二说在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决不能混为一谈。”(注:蒋庆:《公羊学引论》,第31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我们认为这种把“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两者截然对立起来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它与两种学说的基本性质不符,也和历史上的实际情况相出入。
首先,“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之间,性质上有其一致性,即都是统治阶级思想家用来解释朝代更迭、历史变迁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的历史哲学理论形态。在汉代,则是当时儒者论证汉祚合理性,说明朝代更替现象的重要理论之一。就“五德终始说”而言,两汉又有三种基本观点,一是西汉初期张苍所倡导的汉为“水德”说:“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上黑如故”(《汉书·任敖传》)。二是公孙臣、贾谊所主张的汉为“土德”说:“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服色上黄’。”(《汉书·郊祀志》)。其他诸如司马迁、倪宽等人也从此说。三是刘向父子、班固等人所提倡的汉为“火德”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汉书·高帝纪·赞》)。王充等人也持此说。它是两汉五德终始各种说法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在思想界几乎是占了统治地位。上述三种汉德说中间,前二种是基于五行相胜原则立论的,而汉为火德说则是依据五行相生原则推衍的(注:参见拙作《两汉五德终始说种种及其实质》,《历史教学》,1989年,第4期。)。 它们都是解释历史运动表象的理论,所存在的差异在于,把五行相胜的原理用之于朝代的递嬗上,意思是下一代革上一代的命,正如五行中某一行胜某一行,它的历史依据就是夏、商、周都以征伐取得天下这一点。这观点一般体现了变革时的斗争性,富有进取精神,在政治上便是以“伐无道,诛暴君,立新王”为特征。而五行相生说的原理则是“以母传子,终而复始”(《汉书·郊祀志·赞》),这更多地反映了守成时的调和性,富有保守的意义。它的历史依据出于尧舜禅让,在政治上以“和平过渡”为基本特征。
尽管汉代“五德终始说”观点很多,其政治倾向性也存在着进取或保守的差异,但是从性质上来讲,它与“三统说”并无根本的区别,即都是按照历史循环进化的观点,说明朝代更替的现象及其动因,也就是“对于帝王兴废的解释”。因为“五德终始说”以“金、木、水、火、土”等五德为运次,终而复始,循环往复。“三统说”的基本特征也是以“黑、白、赤”三统为运次,“逆数三而复”,“各法而正色”。据统者制定礼乐、法度,“各以其法象其宜”(《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提法虽有不同,但循环进化为主导的历史哲学观却一致。说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汉代儒生受阴阳五行观的思想支配,一般都既讲“五德终始”,又谈论“三统”。今文学家与古文学家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根本的差别。不能笼统地说“通三统是今文说,终始五德说是古文说”。古文学家的情况这里姑且不论,今文学家又何尝只谈“通三统”,而不谈“五德终始”?如董仲舒固然是“三统说”的积极论证者,但是同时又以很大的精力阐发“五德”理论。其著作《春秋繁露》中就有许多讨论“五行”的篇章,计有《五行相胜》、《五行相生》、《五行顺逆》、《五行变救》、《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五事》、《五行对》、《五行之义》等九篇,既讲五行相生,又讲五行相胜。可见“五德终始说”与“三统说”一样,也是董氏历史哲学的组成部分。又如何休,“张三世”“通三统”固然是他历史哲学的主体,可是他也谈“五德终始”问题,以作自己历史哲学体系的补充:“绝笔于春,不书下三时者,起木绝火,王制作道备,当授汉也。又春者,岁之始。能常法其始,则无不终竟。”(注:《春秋公羊传解诂》哀公十四年。)这些情况表明,“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作为阐发历史循环进化运动的不同理论形态,性质没有区别,不能以今古文经学的范畴来划分其归属。
第三,“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性质虽然一致,但学说的内涵以及表述的方式却有较大的不同。从内容来说,“三统说”以自然物生长之色为“统”的载体,即黑、白、赤三色各据一“统”,循环周复。而“五德终始说”则以自然物的属性为“德”的载体,即金、木、水、火、土五物各据一“德”,或相生,或相胜,循环终始。从特征来说,“三统说”有较大的兼容性,即肯定新王“正统”的同时,保存距今最近的旧王“两统”,尊先王存二王之后。而“五德终始说”则表现出较大的排斥性,旧王在新制中不再有特殊的地位。从论述的侧重点来说,“三统说”注重于阐述历史演变现象的本身事实;而“五德终始说”则注重于通过对历史演变现象的归纳总结,为论证现存体制合理性服务。正因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才使得汉代儒生在接受“三统说”的同时,也把很大的精力与才智投入到阐述发挥“五德终始说”理论方面,使两者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互为发明,互为补充,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历史哲学体系。
二、何休“通三统”的论点与特征
何休的“通三统”思想在其代表性著作《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多有保存。和其他《公羊》学家一样,何休也认为“三统说”是解释朝代更迭、历史变迁的理论依据,应该成为《公羊》历史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通三统”的基本特征,何休在《解诂》隐公三年注文中曾有明确的说明,并指出其意义在于“尊先圣”,使“师法之义,恭让之礼”昭白于世:
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至于“三统”的内容,何休引用董仲舒等《公羊》先师的观点,认为新王受命而王,必改正朔,易服色,建立起一个新“统”,以彰明新王兴起乃是受命于天,而非继人。然而由于正朔服色三王各不相同,故有三统之别,缘此而形成“三统”的基本模式:
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法物见,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法物芽,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法物萌,色尚赤。(注:《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更深入地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何休的“三统说”至少包含了三层基本含义:
一是“通三统”为“存三正”之义,即《春秋》三正可通,新王受命而王,改正朔可于前王之正月依次择善而用之。《春秋》桓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解诂》释云:“无王者,见桓公无王而行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复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为汉制而已。”又,《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解诂》云:“河阳冬言狩,获麟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说的都是“存三正”的意思。
二是“通三统”有存二王之后的意义。何休继承《公羊》先师的成说,认为王者应存二王之后,指出这乃是“通三统”的前提条件之一。具体方法是新王封二王之后地方百里,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解诂》于其义多有阐述,今仅举两例,以明其法。《春秋》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解诂》云:“宋称公者,殷后也。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待之而不臣也。”又,《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解诂》云:“时天王居于郑,晋文欲讨楚师,以宋王者之后,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
三是“通三统”中,“黑、白、赤”三统在特定时间里地位并不平等,凡新统者必区别于他统而在三统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即新王兴起虽尊先圣,师法前王,但必须以自己一统为三统中的主导者,也就是说当以新王之一统,通王者后之二统。《解诂》对此义颇多论析。例如《春秋》隐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解诂》云:“道《春秋》通例,与文武异。”又如《春秋》庄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齐纳币”。《解诂》云:“《礼》言纳征,《春秋》言纳币者,《春秋》质也。”这都是以《春秋》为新王立一统,而进而统前王二统之义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何休阐说“通三统”之义,不仅仅是对《公羊》先师之成说的继承,也是对东汉整个社会思潮的趋同。因为在东汉思想学术界领域内,凡涉及历史观问题,都不能回避“通三统”这个命题。当时的儒生,不管他是今文学家还是古文学家,在考察社会变易,解释历史发展动因时,都以“三统说”的理论为重要依据,从而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东汉中期成书的《白虎通义》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性。它一样秉承“三统说”,并易名为“三教”,而“三教”的内容实与董仲舒、何休等人所言的“三统说”相一致:
王者设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继周尚黑,制如夏同。三者如顺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白虎通义·三教》)由于视“三正”、“三教”为循环往复的事物,所以在“改制”观方面,《白虎通义》的基本看法也与董仲舒、何休诸人的见解相同:
王者受命必改正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王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质。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积,声味不可变,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白虎通义·三正》)。在这样人人争说“通三统”的社会大氛围之下,面对传统,何休别无选择,只得以很大的精力来阐说、发挥“通三统”的哲理,并努力使之与“三世说”相结合,构筑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
当然,何休的“通三统”理论,并不是对《公羊》先师成说的简单重复,而是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这集中体现为他引申董仲舒“王鲁”的观点,系统提出了“黜周王鲁”的理论,使《公羊》“三统说”呈现出新的面貌,焕发出新的生机。
“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是何休“三统说”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精神,被列为其“三科九旨”中的“一科三旨”,“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这个“新王”,就是鲁国,所以“《春秋》当新王”便是“王鲁”,如《解诂》隐公元年所言“《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
有的学者认为,“黜周王鲁”非《春秋》以及《公羊传》本义,而是何休独创,强加给《春秋》和《公羊传》的(注:参见吕绍纲:《何休公羊“三科九旨”浅议》,《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整部《春秋》中,的确找不到“王鲁”二字,隐公元年出现过“内鲁”的提法,宣公十六年也出现过“新周”的字眼,但它们同“王鲁”的真实含义似乎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如果据此而断定“王鲁”纯属何休独创,则也不尽恰当。事实上何休“王鲁”之说的提出,是以董仲舒等《公羊》先师的观点为依据的,是对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的“王鲁”提法的引申和发挥。
考《三代改制质文》,可见董仲舒的确是以鲁国代表《春秋》而继周当新王的,“《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然而,董仲舒对“王鲁”的具体内涵并未作更多的阐述和发挥。可到了何休那里,情况却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引用“王鲁”的概念,注入自己新的理解,为“三统说”增添了新的内容。
按何休的理解,在《春秋》中周统已绝,当退为二王之后,故云“新周”,新周便是黜周,取代它的便是新王——鲁。何休的这个见解,在《解诂》宣公十六年中有最为明白无误的反映。《春秋》宣公十六年书曰:“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释曰:“成周宣榭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何休在《解诂》中据此发挥说:“新周,故分别有灾不与宋同也。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周不复兴,故系宣榭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何休明确指出周统已绝,周室已无复兴的希望,当黜为王者后,并将由新统取代之。正是这个原因,何休在《解诂》中一再强调《春秋》当新王为新统,它必须区别于周统,即必须“与文武异”,与周礼异,与周正异,以示《春秋》继周而王之义。
周统既遭贬黜,退为王者后,那么就必须有新王来填补其原来的位置,受命而王,建立新统。所以何休就在《解诂》中倡导“以《春秋》当新王”,是谓“《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注:《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二年。)。然而《春秋》毕竟是一部历史著作,不是人王或政府,于是何休又以鲁当受命的新王。这就是所谓的“王鲁”,以鲁统取代周统,其核心含义是“託新王受命于鲁”,“《春秋》王鲁,託隐公以为始受命王”:
不言公,言君之始牟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于王者,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注:《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通观《春秋公羊传解诂》全书,可见“王鲁”的提法充彻于始终。清代《公羊》学家刘逢禄在其《公羊何氏释例》中曾对此逐条加以记录,数量竟多达二十余处。此足以证明“《春秋》王鲁”之说在何休“通三统”理论中的核心地位。略举几例,以显示何休是如何用“王鲁”来支撑其“通三统”历史哲学的体系的:
《春秋》隐公七年书“滕侯卒”。《解诂》释云:“滕,微国。所传闻之世,未可卒,所以称侯而卒者,《春秋》王鲁,託隐公以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隐公,《春秋》褒之以礼。嗣子得以其礼祭。故称侯见其义。”
《春秋》隐公八年夏六月书“辛亥,宿男卒”。《解诂》释云:“宿本小国,不当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鲁,以隐公为始受命王。宿男先与隐公交接,故卒,褒之也。”
《春秋》僖公三年书:“冬,公子友如晋莅盟。”《解诂》释云:“《春秋》王鲁,故言莅以见王义。使若王者遣使临诸侯盟,饬以法度。”
《解诂》成公二年:“《春秋》託王于鲁,因假以见王法,明诸侯有能从王者征伐不义,克胜有功,当褒之,故与大夫。大夫敌君不贬者,随从王者,大夫得敌诸侯也。”
《解诂》哀公十四年:“据天子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阳,公狩于郎是也。河阳冬言狩,获麟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何休提出“《春秋》王鲁”的命题,作为其“通三统”理论的核心内容,对于《公羊》“通三统”历史哲学来说,实具有质的发展。传统的“三统说”仅仅是解释朝代更替的现象,带有明显的历史循环色彩,正如《白虎通义·三教》所说的“三者如顺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而何休“王鲁”的重点则着眼于拨乱反正,建立新统,即所谓“以见王义”、“饬以法度”、“因假以见王法”云云,是前瞻的而非循环的。它既是对历史运动法则的总结,更是对现实乃至未来生活的参与和展望。如考虑到何休提倡“王鲁”的历史背景,更可以发现这种历史哲学的内在进步性质。何休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政权日趋腐朽,面临崩溃的前夜,在这样的背景下宣传“王鲁”之说,实际上是何休寄托自己对摆脱危机、重建秩序的期望,即企图以理想中的“王”来代替现实中的王,就是假借某个历史现象,来说明一种道理,实现一种理想。
对何休“王鲁”的这一底蕴,晚清今文学家皮锡瑞曾有过准确的揭示。他指出这不过是何休“借事明义”而已:“黜周王鲁,亦是借事明义”;“止是借当时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注:《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皮锡瑞真可谓是何休的千古知音!由此可见,何休的“《春秋》王鲁”之说决非单纯的历史循环观,而是立足现实,在总结历史现象基础上面向未来的进化史观。它的提出,标志着儒家的“通三统”理论得到了革命性的改造,具有了更为完善的形态和性质。到了近代,其“损益因革”、“借事明义”、“因时制宜”、“因假以见王法”的文化精神,遂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而成为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从事维新变法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