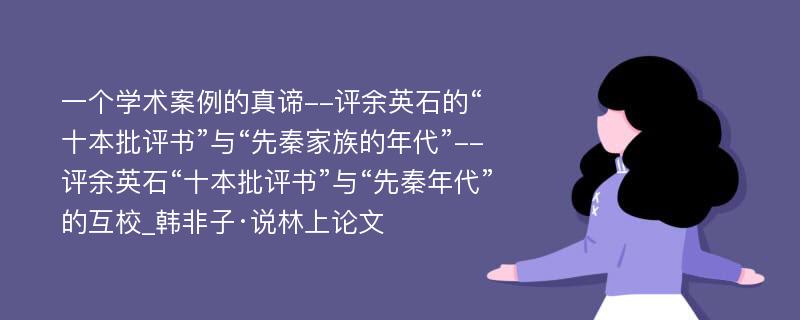
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案论文,诸子论文,先秦论文,一桩论文,真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4年8、9两月,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第6、7、8三期连载余英时先生的《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以下简称《互校记》)。作者武断地肯定《十批判书》(以下简称《十批》)大量抄袭《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据说发表时该刊主编“觉得这正是可以为《人生》增添热闹的题材”,而这也是作者求之不得的。余英时在文章中说,他对《十批》和《系年》的互校说明了郭沫若“是一个完全没有学术诚实的人。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态度了”。由于当时大陆处在与外隔绝的状态,余英时这篇文章在当时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反应,这使作者颇为失望。
事隔三十七年之后,郭沫若先生与钱穆先生已先后作古。余英时对于自己的文章没有引起轰动效应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在1991年纪念钱穆的集子《犹记风吹水上鳞》中收入了该文,只是删去了原标题,以副标题为题,“大体上是把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句删除了。整体的内容,甚至风格,则一仍旧贯”。
1992年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十月号上发表《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再次提起这桩公案,称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1994年,余英时将《互校记》收入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钱穆和中国文化》一书。
经过余英时一而再,再而三的宣传,加上他的名气已今非昔比,果然引起了一些人的鼓噪。就大陆而言,先是上海一家颇有影响的大报在《读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安迪”、题为《一段公案》的短文;接着,《博览群书》1995年第12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丁东”、题为《学术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文章。这两位作者没做任何调查研究,居然跟余英时鹦鹉学舌,诬称郭沫若抄袭。这自然是余英时期望引起的效应。
余英时标榜他的《互校记》是采用校勘的方法,“排比联络,一以贯之”,“以诸篇之抄袭证成一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这确实具有较大的迷惑性。没有读过《先秦诸子系年》和《十批判书》的读者固然容易上当受骗,即使是读过这两本书而且对先秦思想史略有了解的读者,因为没有对两书做过校勘,也难免半信半疑。郭沫若的学识和学术道德在有些人的脑海中似乎也要打上问号了。
我们对先秦思想史虽然有些兴趣,但并没有专门研究。当听说余英时有这样一篇文章后,觉得这真是一桩重要的学术公案,便借了《互校记》来拜读。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和台港地区以及国外的学术交流有了很大发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我们希望从余英时的文章中能够有所获益。但是读完《互校记》之后,觉得作者不但使用了一些通常学术批评不应该使用的恶毒的词句,而且口气傲慢武断,实在难以服人。为此,我们不惮其烦,把《互校记》和《十批判书》、《先秦诸子系年》的有关材料也互校了一番。结果发现,《互校记》对《十批》的攻击根本不能成立,其手法完全背离正常的学术批评准则。余英时在文中对郭沫若的肆意斥责和嘲讽,完全出之于他对郭沫若的偏见。
应该指出,《系年》和《十批》本来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论著,这是余英时也承认的。《系年》主要考证诸子生平活动和著书的年代,对于诸子思想内容基本上未作论述和分析。《十批》着重分析诸子思想的内容、倾向及其社会背景,对其生平活动虽也有所论及,但并不是重点。在我们这篇文章中,不准备讨论《十批》和《系年》内容的区别,也不涉及彼此历史观的不同,只是就余英时《互校记》中罗列的《十批》抄袭《系年》的证据略加爬梳和辨析。《互校记》所列凡十二条,几乎涉及所有先秦诸子。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能就几个主要问题加以论列。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根据其日记排列了他研究先秦诸子和撰写各篇文章的日期。时间起于1943年7月3日,止于1945年2月18日。这期间,1943年9月7日在杜国庠处看到书架上有一部钱穆著的《先秦诸子系年》,便借回家去翻阅。这是余英时认为《十批》抄袭《系年》的重要证据。上述时间表说明,郭沫若在撰写《十批》的过程中,确实参阅过《系年》。这一点,是应该先向读者交代的。
一、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
《互校记》说:“关于吕不韦与始皇的关系,钱先生有特别的考证,他否定了始皇为不韦子之说,否定了不韦荐嫪毐替己之说,同时还指出了不韦与始皇之间可能有政治上之冲突。郭沫若便抄袭了这些见解而大作其翻案文章。”又说:“这一节乃是《十批判书》中最严重的抄袭。一般典籍如《史记》、《战国策》之类,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其是抄袭。但论断则不然。更明显的是《系年》援引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两说,而郭氏也恰恰同引此两书,这便不是‘巧合’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讲史料征引。《系年》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嫪毐三人关系,所引史料二十余条;《十批》所引文献也近二十条,另引铜器铭文为证。两书引用史料相同的有《史记》、《吕氏春秋》和《战国策》中的有关史料。这些大概可归入《互校记》所说“一般典籍”类。问题在于《史稗》和《读书后记》。余英时说,这两书郭沫若抗战时期在重庆是“绝难看到的东西。”(《互校记》首次发表时语)言下之意,这正是《十批》抄袭《系年》最过硬的证据。我们开始也认为,郭沫若这两条材料有可能是从《系年》转引的。但是经过查对,却不是这么回事。首先,《系年》所引王世贞的书名乃《读书后辨》,并非余英时所说的《读书后记》。余英时把《读书后辨》改为《读书后记》,是从《十批》抄来的。实际上,王世贞的书名既不是《读书后辨》,也不是《读书后记》,而是《读书后》。余英时不知道王世贞有《读书后》一书,可能觉得《系年》引作《读书后辨》不通,就想当然地跟着《十批》改为《读书后记》。钱穆撰写《系年》时,是否看过王世贞《读书后》原书,我们开始不敢遽下结论,只觉得《系年》原版及增订版均作《读书后辨》,看来这个书名并不是手民误植,而是钱穆本人所定。在查阅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之后,我们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钱穆不但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而且不知道王世贞这部书的书名。《系年》有关秦始皇与吕、嫪关系的论述,大段引自《史记志疑》。其所引用《史稗》和《读书后》的材料,也都见于《史记志疑》。《史稗》和《读书后》是罕见书,而《史记志疑》则是一般学者较熟悉的常见书。为什么钱穆会把《读书后》的书名引错呢?原来,《史记志疑》中有这样一段话:“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由于钱穆并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就把《读书后辨》当作书名。这段原来无标点符号的文字,在《系年》里引用时加上“说”字并使用了书名号,成了“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郭沫若引用《志疑》的有关论述时,大概也不知道王世贞原书的书名是《读书后》,因而错改为《读书后记》。余英时在撰写《互校记》时,本来只需查一查《史记志疑》和有关的工具书,就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最可笑的是,他不知道《读书后》的书名,跟着郭沫若改为《读书后记》,还硬说《十批》抄袭《系年》,这种随心所欲的“互校”,能说是“用力较勤,所得较实”吗?
再说论断。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这个传说不可靠,从汤聘尹的《史稗》和王世贞的《读书后》到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都已作过考证,《系年》和《十批》不过是在他们论说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申述而已。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产生?汤聘尹认为是“战国好事者为之。”王世贞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吕不韦故意编造,以求自己长保富贵;另一种是吕氏的门客泄愤,骂秦始皇是私生子,使天下人都知道秦比六国先亡。《系年》对于这个问题并未加讨论。倒是《十批》提出了另一种推测,认为这是西汉初年吕后称制时,吕氏之族如吕产、吕禄辈仿照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编造的。请问余英时先生,这怎么能说是《十批》“无论在资料和论断上都全依《系年》”呢?
关于吕不韦和嫪毐的关系,《系年》说:“当时秦廷与不韦之间有猜防冲突之情而为史籍所未详者。始皇幸先发,因以牵连及于嫪毐之事。不韦自杀,诸宾客或诛或逐。”《十批》对于吕、嫪的关系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其内容与《系年》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一)《系年》认为吕不韦是“牵连及于嫪毐之事”,《十批》则认为吕不韦辅助秦始皇诛锄嫪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嫪毐发动叛乱之后,始皇“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尽得毐等。”《十批》说,“考秦只有左右二相国,于时吕不韦为相尚未废免,则昌文君应该就是文信侯的别号。”此与《系年》观点完全相反。(二)《系年》为了说明吕不韦“牵连及于嫪毐之事”,把“不韦自杀,诸宾客或诛或逐”与嫪毐被诛联系在一起。《十批》指出吕不韦假使和嫪氏果真是同党,在嫪氏诛戮之后,秦始皇为什么对他还能那么容忍,仅仅免他的相?(三)嫪毐诛戮之后,太后被秦始皇迁于雍。《史记·秦始皇本纪》云齐人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但语焉不详。《十批》认为秦始皇把太后迎回之后,便出吕不韦就国,一年后又要吕不韦与其家属徙蜀;而在前充军的嫪氏舍人在吕不韦死后即由蜀被召回。由此推论,茅焦对于吕、嫪二氏势力之一消一涨起着重要作用。《说苑·正谏篇》有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的详细叙述,《十批》认为虽属小说家笔法,不可全信,但却可推测“茅焦所以解说于秦始皇的,一定是替太后与嫪氏洗刷,而对于吕氏加以中伤。”《系年》对于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一事则完全略而不提。从上述对照不难看出,关于吕不韦与嫪毐的关系,《十批》论述与《系年》多有不合。余英时仅据《系年》与《十批》都引用了《战国策·魏策》的一段材料,就肯定《十批》是抄袭《系年》,这岂不是莫须有吗?
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对立,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作了详尽的剖析。《系年》除了提到《吕氏春秋》“抑秦与六国同例”和“讥秦政虽以武强伸于一时,犹不为民之所走”之外,可以说再别无涉及。余英时承认“不韦与始皇为政敌此点为郭沫若之《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全文的精神所贯注之所在”,因为实在无法举出《十批》抄袭《系年》的材料,就只好用一句“毋须引证”来轻轻滑过。最妙的是,余英时在强调“不韦与始皇为政敌”是钱穆的发明时说:“我们再看看钱先生的话吧:‘且不韦为秦相国,乃绝不称道秦政,……即观其维秦八年之称,已显无始皇地位’。”按《吕氏春秋》“维秦八年”之称,前人多有辨析。《系年》在援引清代学者的考证之后,认为姚文田之说“甚辨而核”,“不韦不以始皇纪元,乃统庄襄言之。”郭沫若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考证,并且得出了不同的认识。他举金文列国纪年之例,认为“维秦八年”就是秦始皇八年,“前人不明此例”,“或以为乃统庄襄王而言,都是削足就履之论。”余英时不仅对郭沫若的考证避而不谈,而且不说明钱穆赞同姚文田的说法,用一句“我们再看看钱先生的话吧”,就把姚文田的考证归到他老师的名下了。
二、关于前期法家
《互校记》说:“钱先生在《系年》中曾发现战国变法不始于商鞅,东方变法在先,西方继之于后,李悝、吴起早已为商君开路”,“钱先生认为‘至李吴商鞅,乃战国初期法家,尤不得与韩非并论’。郭沫若的《前期法家的批判》一文便完全根据此点立论,其中所列举的几个人物亦无一不根据《系年》的考证成果。”我们不妨对余英时的论点逐一加以检验。
郭沫若的《前期法家的批判》写于1944年1、2月间,但他在这之前,早已形成了李悝、吴起、商鞅具有法家思想的基本观点。1942年2月发表的《屈原思想》(收入《屈原研究》,1943年7月初版),在谈到屈原生活的时代时说:“到了战国时代,魏文侯时的李克,亦即李悝,有尽地力之教,使魏国富强,其详不可得而闻,传其衣钵的有吴起和商鞅。……这两位革命的政治家(吴起虽仅以兵家名,其实他是长于政治的),虽然同以悲剧终结,但他们的法术的行与不行,便规定了秦、楚的运命。秦国用商鞅之法而兼并天下,楚国废吴起之法而终于绝灭。”1943年8月21日(据郭沫若日记)完成的《述吴起》(收入《青铜时代》)对吴起有比较全面的论述,指出吴起“作为政治家是与商鞅并称的”;在列举吴起的政治主张之后说:“这些倾向差不多就是后来商鞅所行于秦的办法,商鞅也是卫人,说不定他们还有师弟关系吧?但至少商鞅是受了吴起的精神上的影响,我看是毫无问题的”。文中还重申了以下观点:“吴起之法结果是被楚国废了,”“假使让吴起在楚国多做得几年,使他的政治得以固定下去,就和商鞅日后在秦的一样,行了法二十二年,虽然死了,法也没有变动,那吗战国时代的中国,恐用不着等到秦国来统一了。”由于《述吴起》写作在前,所以郭沫若在《前期法家的批判》中就交代:“关于吴起,我曾经有《述吴起》一文详细论述,在这儿只想把他的面貌再画出一个简单的轮廓。”《屈原思想》和《述吴起》都是郭沫若1943年9月7日从杜国庠处借阅《系年》之前写成的。如果说余英时不知道《屈原思想》已经把李悝、吴起和商鞅并列犹可理解的话,那么,郭沫若的《十批》中已经提到曾经写过《述吴起》,余英时置而不顾,却硬说《十批》关于前期法家的论述完全根据《系年》而立论,这种不顾事实的诬罔就令人不能原谅了。
余英时说:“他(指郭沫若)所谓前期法家的概念更明明是钱先生所说的‘初期法家’,其著书之不德,弥是惊人。”“不德”之罪名,可谓大矣。但余英时在这里耍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钱穆只说过“至李吴商鞅,乃战国初期法家”,指李悝、吴起、商鞅乃战国初期的法家,并没有使用过“初期法家”的概念。而郭沫若使用“前期法家”的概念,则是有特定思想内涵的。战国初期的法家虽然也可以说是前期法家,但毕竟与“前期法家”的概念含义不能混同。余英时曲解钱穆的话为其老师争发明权,我们想钱穆先生也不会觉得坦然的。其实,郭沫若虽然把李悝、吴起、商鞅等人列为前期法家,但他并没有说这是他的“发现”。早在郭沫若和钱穆之前,有的学者已经把李悝、吴起和商鞅相提并论。如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虽然说“法家成为一学派,时代颇晚”,但已指出“自宗法政治破坏以后,为政者不能不恃法度以整齐其民”,“其在战国,则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之流,皆以法治卓著成绩”。余英时把《系年》所谓“今按重农政,则李悝、吴起、商君一也”,“重法律亦李悝、吴起、商君一也”,“重兵事又李悝、吴起、商鞅三人所同也”,说成“都是钱先生治史的重要发现”,这岂不是有些不够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吗?
郭沫若指出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儒家的子夏,是所谓“子夏氏之儒”。余英时认为“这也是钱先生早就指出来的了。钱先生既说李悝(克)、吴起是子夏、曾西弟子(《魏文侯礼贤考》页121《吴起去魏相楚考》页176)。又谓法源于儒(《商鞅考》页212)。郭氏之说实合此两条而成。”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郭沫若在借阅《系年》之前撰写的《述吴起》,对吴起的生平和思想曾作过详细的论述,其中对吴起受业于子夏和曾子就有细密的考证。吴起师事子夏牵涉到魏文侯在位年限问题,因为子夏曾为魏文侯师。《系年》说:“考魏文二十二年始称侯,子夏若尚存,年八十四”,“文侯师子夏,虽不可以年定,而其在早岁可知。”《述吴起》则肯定《史记年表》魏文侯18年“受经子夏”,并考证《史记》有关魏文侯在位年限的记载有误,认为文侯元年当是鲁悼公22年。这年子夏62岁,再过18年子夏80岁,文侯从他受经和吴起从他受业都说得过去。一个认为魏文侯师事子夏是在“早岁”,一个则肯定是在魏文侯即位18年之后,《系年》与《十批》的考证明显不同。至于吴起师事曾子的问题,郭沫若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当先解决吴起何时去鲁。《韩非子·说林上》说:“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焉。或谓起曰:‘……今季孙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吴起因去,之晋。”季孙所弑鲁君是谁?如是哀公,则其死时当在百岁以上,似无此理。郭沫若认为被弑之鲁君如非元公,必为悼公。二公虽无被弑的明文,但《韩非子·难三》说:“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则悼公和元公被弑都是可能的。据此推论,吴起去鲁在元公21年。其时曾参已卒,故其所师者决非曾参。郭沫若又据王应麟考证引刘向《别录》叙《左氏春秋》之源流言“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认为“左氏传授之说虽不足信,曾吴师承关系则较可信。”《系年》在谈到吴起去鲁年代时,对于吴起师事曾子之可能根本未作深入考证。书中虽然也引用《韩非子·说林上》的材料,但认为“考诸《鲁世家》,仅有哀公见逐,非被弑。又下距楚悼之卒,凡八十七年,吴起决不若是之寿,亦复与魏文年世不相及。盖《韩子》误记,不足信。”(见《系年·吴起仕鲁考》,余英时文章不引此条)。一个肯定《韩非子·说林上》的材料,一个认为这个材料不足信。一个认为季孙所弑之鲁君当是悼公,一个认为鲁君不曾被弑。姑不论《十批》和《系年》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但它们考据得出的结论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怎么能说是《十批》抄袭《系年》呢?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上述材料,不仅是为了证明郭沫若关于子夏氏之儒的考证与《系年》无关,而且也要让读者了解,余英时为了达到诬罔的目的,对于不利于自己论断的材料,往往采取了弃而不取的手法。就以前期法家和子夏氏之儒的关系来说,郭沫若指出:“《论语》载子夏论交,‘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正表明着法家精神。荀子骂子夏氏之贱儒‘正其衣冠,齐其颜色谦然而终日不言’,也正活画出一幅法家态度”。他对《韩非子·显学篇》言“儒分为八”,其中无子夏氏之儒,最初感到不解,后来发觉“前期法家”其实就是“子夏氏之儒”,“韩非把子夏氏之儒当成法家,也就是自己承祧着的祖宗”,自然就不“把他们当成儒家看待”。这些论述和引用的材料,倒可以说是郭沫若真正的“发现”,而钱穆《系年》于此毫无言及。余英时不顾事实,反而诬称《十批》完全抄袭《系年》,真可以说是一手想遮天下人之耳目了。
关于“法源于儒”问题还需要再说几句。《系年》说:“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顾不知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早已指出法家受儒家“言正名定分”的影响,胡适《中国学史大纲》卷上也说:“自从孔子提出‘正名’的问题之后,古代哲学家都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以后如荀子的‘正名论’、法家的‘正名论’,不用说了,即如墨子的名学,便是正名论的反响。”不知道余英时先生对于梁、胡等人的观点是否了解?
《十批》把慎到和申不害也列为前期法家,但认为其思想渊源属于黄老学派。关于慎到,《系年》于其事迹有所考证,然以今本《慎子》为伪书,谓不足信。《十批》对于慎到的事迹略而不提,着重分析他的思想,而其依据的材料,则主要是现存《慎子》残余的辑本。在郭沫若看来,这个辑本的基本思想与《荀子》对慎子的评论是相符合的。有关慎到的文献记载很少,对今本《慎子》是否可信持不同态度,这个基本事实本来已足以说明郭、钱二人对慎到的研究有很大区别。但余英时却因为《十批》和《系年》都引用了《荀子》的《非十二子》、《解蔽》和《天论》中的材料,就断言《十批》抄袭《系年》,这又一次表明他是何等的强词夺理。更荒唐的是,《荀子·非十二子》所说的“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一段文字,《十批》所引是正确的,《系年》则错误地说成是引自《庄子·天下篇》。余英时为本师讳,对《系年》的这个错误不加纠正,却还引来作为《十批》抄自《系年》的证据。试问余英时,倘若郭沫若所用的资料都是抄自《系年》,怎么又把错误的抄成正确的呢?《庄子·天下篇》没有上引这段文字,我们相信这是钱穆先生一时疏忽的笔误(初版如此,增订版依旧)。问题是,余英时既然下了很大功夫“互校”,为什么又不把《系年》的错误纠正过来,究竟也是一时疏忽,还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个错误呢?
关于申不害,《系年》和《十批》在引用《韩非子》的有关材料之后,都说申不害主张用术,与吴起、商鞅任法不同。这也不是什么新的论点。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即已指出申不害的“术治主义”与商鞅等的“法治主义”“极易混淆而实大不同”。余英时竭力要为《系年》争发明权,实在也大不必要。至于说郭沫若“所用资料亦全依《系年》的线索,”这更是无稽之谈。《十批》在分析申不害的思想时,不仅所引用的《韩非子》和《战国策》的材料比《系年》多,而且还引用了《群书治要》所辑的《申子·大体》篇,以及《吕氏春秋·任教》篇和《慎势》篇的有关材料。而《申子》和《吕氏春秋》这部分材料,《系年》是根本没有提到的。
三、关于稷下学派和其他诸子
《系年》的《稷下通考》对于稷下学宫兴衰有较详细的考证,这是钱穆先生的贡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其下。”《系年》于此据《太平寰宇记·益都下》另引《别录》说:“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又引徐幹《中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孟轲之徒皆游于齐。”这两条材料,郭沫若在《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也引用了,但把《太平寰宇记》误写为《太平御览》。《中论》并非罕见书,部头也不大。但《太平寰宇记》卷数很多,郭沫若在重庆时很可能借不到,而且从这样大部头的书中找出《别录》的这条材料,并非易事。再加上郭沫若又把《太平寰宇记》误写为《太平御览》。因此,我们不妨相信郭沫若所引的上述材料是从《系年》转引的。如果余英时只是批评郭沫若应注明材料转引的出处而没有注明,我们认为这种批评是无可厚非的。但余英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且很不实事求是地说:钱穆《稷下通考》的论证“是了解先秦学术思想的极重要之关键,其中有很重大的新发现。郭沫若在其《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一文中,竟把钱先生的精密考据轻轻巧巧地夺去了”。事实上,《稷下通考》只是考证稷下学宫的兴衰,并没有涉及这个学派的思想内容,怎么能说其论证是“了解先秦学术思想的极重要之关键”呢?《十批》指出稷下学士派别复杂,“然而这里面没有墨家,而道家是占最大多数的。”大体说来,宋钘、尹文为一派,田骈、慎到为一派,关尹即环渊为一派。郭沫若认为《道德经》是环渊所著,“《老子》其书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人又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书晚出,但其人在孔子之前是无法否认的。这与钱穆的意见相左。《十批》指出《管子》书中的《心术》、《内业》是稷下道家宋钘所著,《白心》是尹文所著,这个见解已为当今治先秦思想史的多数学者所肯定。收入《青铜时代》的《老聃、关尹、环渊》和《宋钘尹文遗著考》对稷下之学的两个重要学派作了详细的考证。这些事实说明,郭沫若关于稷下学派的研究,或与钱穆意见不同,或为钱穆所未论及,怎么能说是郭沫若“把钱先生的精密考据轻轻巧巧地夺去了”呢?
关于其他诸子,余英时指责郭沫若抄袭钱穆的手法不外乎都是:凡《十批》论诸子所引用的材料见于《系年》的,便断定《十批》关于此子的研究“抄袭”《系年》。至于《十批》所引材料不见于《系年》的,以及对于同一材料《十批》的考辨不同于《系年》的,余英时就视而不见了。郭沫若在研究先秦诸子时,参考过近现代有些学者的著作,包括《系年》。我们并不认为他绝不引用二道手的材料。处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又是被国民党官方学术机构所极力排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当时借阅图书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有些材料引自他人的著作,或从他人著作中得到线索再查阅原书,应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相信,有关先秦诸子的基本史料,郭沫若都是直接掌握而加以深入研究的。正如他在《十批》后记中所说:“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余英时存有偏见,甚至于连一些常见的基本史料或已经成为学者们基本常识的论点,都要把发明权归于钱穆名下而指责郭沫若抄袭,这实在有些无聊。如果按照余英时寻找“抄袭”证据的手法,《系年》中许多考辨的“发明”权恐怕也都要被剥夺的。例如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中用一个小注引《风俗通·穷通篇》云荀卿年十五游学齐国,纠正《史记·荀卿列传》和刘向《序录》作“五十”之说。所引材料确实见于《系年》。但在《系年》之前,梁启超也已引同样的材料考证“五十”乃是“十五”之讹;姚永朴《诸子考略》也已对“五十”说的不合理作了考证,并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五十”为“十五”之讹。又如,《十批》关于漆雕开的论述引用《韩非子》、《孟子》和《论衡》等书的有关材料,与《系年》基本相同,余英时就振振有词地说:郭沫若“从资料到判断,完全抄自《系年》”。其实,这些材料在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等书中都提到过。即以漆雕开的名字而言,《十批》引《汉志》班固注“孔子弟子漆雕启后”,认为“启即是开,因避汉景帝讳而改。‘后’乃衍文”。余英时说这是抄自《系年》(钱书引宋翔凤《论语发微》谓“后”字当衍,又引宋氏《过庭录》谓:“吾疑启字之讹。古字作启,漆雕子名,避景帝讳作开”)。《系年》有关这个问题的考辨诚然在《十批》之前,但在《系年》之前,梁启超在《汉志考释》中已经提到其门人杨树达称班固注“孔子弟子漆雕启后”之“後”字为衍文;罗焌的《诸子学述》则引阎若璩说:“开本启,汉人避讳所改”;高维昌的《周秦诸子概论》亦有此解释。如果按照余英时《互校记》的逻辑,《系年》关于“漆雕启后”的考证能说是《系年》的发明吗?《十批》肯定了“启即是开,因避汉景帝讳而改,‘後’乃衍文”;接着又对为什么会衍出一个“後”字作了分析,认为“盖‘啟’原作‘啟’,与‘后’字形近。抄书者于字旁注以‘啟’字,及‘啟’刊入正文,而则‘启’误认为‘后’,更转为‘后’也”。应该说,这对于问题的考辨又进了一步,怎么能完全加以抹煞而硬说都是抄袭《系年》呢?
关于列子、桓团与公孙龙,余英时攻讦《十批》抄袭也是用的同一手法。有关这三人的史料本来就极少,谁如果研究都是必需引用的。《十批》引用《战国策·韩策》一段有关列御寇的材料,《系年》也有此段材料。在余英时看来,这就是《十批》抄袭《系年》的证据。《十批》引用《列子·仲尼篇》桓团作韩檀,成玄英《庄子》疏称桓团与公孙龙同是“赵人,客游平原君之家”,又引用《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系年》也引用了这两句话,于是余英时就称《十批》抄自《系年》无疑。《系年》说:“扬雄《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今所传仅五篇,凡二千言,则传者无几也。”《十批》说“扬雄《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然今书仅存六篇——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就中迹府一篇显系后人杂纂,数万诡辞仅存一千八百余言而已。”尽管两书谈到公孙龙书的篇数和字数有所不同,然而余英时说,这“简直等于稍稍改写”,更证明是抄袭:“‘一千八百余言’确比‘凡二千言’为精确,但更是‘欲盖弥彰’了。”所引材料文字相同是抄袭,不同也是抄袭;你讲的比我讲的精确,更是“欲盖弥彰”的抄袭!这样说来,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四、结束语
以上我们通过对《互校记》的辨析,说明余英时攻击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是没有道理和没有根据的。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抄袭”、“剽窃”是很不道德的行为。但别有用心地随便诬蔑一个学者“抄袭”、“剽窃”,这又是什么行为呢?
根据书中引用材料相同,就轻率地断定甲书抄袭乙书,这根本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郑重态度。判断是不是抄袭,既要看引用的材料是常见的还是罕见的,又要看引用材料的文字段落是否一样,还要看对材料的考辨论证及其得出的结论是否雷同。只有经过认真的分析,才能弄清问题的真相。有些作者只是偶而引用了二道手的材料而没有注明出处,这当然也是一种瑕疵,但毕竟与抄袭和剽窃有原则区别。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常识,余英时不应该不知道。如果按照余英时攻讦《十批》抄袭的手法来查对他本人的论著,譬如说,把余英时的论著和先前出版的近现代学者的有关论著加以“互校”,看有哪些史料和论点相同或相似,以此判断有无抄袭的嫌疑,试问余先生,这样行吗?
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说,《先秦诸子系年》和《十批判书》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学术论著。应该说,钱穆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对先秦诸子的研究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至于说他们著作中的观点是否都正确,在使用材料上存在着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讨论也是可以批评的。对于前辈学者,应该尊重而不要无原则地吹捧;可以批评但不应轻薄地抹煞其贡献。而余英时对待这两位前辈学者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对自己的老师钱穆是吹捧备至并处处为之争发明权,对郭沫若则深文周纳,肆意鄙薄,使用了十分刻毒的字眼加以中伤。这难道是一个正直的学者应有的态度吗?遗憾的是,有的人对《系年》和《十批》既没有研究,又不作任何调查了解,居然对《互校记》大加喝采,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态,实在很值得玩味。为什么余英时对郭沫若这样深恶痛绝呢?余英时自己说他深鄙郭沫若之为人。他大概事先已估计到人们会联系到政治立场,因而在《互校记》的开头就先声明:“我们和郭沫若在政治上是处在绝对敌对的立场上,如果没有十分证据足以使人信服,这种学术的讨论便很可能被人们看作是一种政治性的宣传。而一切带着学术面貌的政治宣传则都不会有丝毫价值。我这篇文字有没有学术价值是另一问题,但绝不是政治宣传;因之,我希望读者也能在这种了解下来接受它。”可惜,这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互校记》的文字本身,说明它完全是在学术外衣掩盖下的一种敌对政治情绪的发泄。
余英时1991年重新发表《郭沫若抄袭钱穆先生著作考》并改名为《互校记》时,专门写了一个跋语,文中说:“郭沫若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但是中共官方学术界似乎曾注意到它的存在,并且作出了间接的然而又是针锋相对的反应。几年之后白寿彝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通篇都是用下流暴力语言,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这又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宣传和蒙蔽读者的手法。据我们向五十年代在郭沫若先生身边工作的同志了解,郭沫若并没有看过余英时1954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余英时把“几年之后”白寿彝先生批评钱穆的一篇文章说成是“中共官方学术界”对《郭沫若抄袭钱穆先生著作考》作出的“间接的然而又是针锋相对的反应”,这种丰富的想象力实在令人哑然失笑。请问余英时先生,如果白寿彝先生是代表“中共官方学术界”对你1954年那篇文章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为什么要等到“几年之后”才发表文章,而在文章中为什么又根本看不出与你的大作有什么“针锋相对”之处呢?白寿彝先生不过是我国的一位著名史学家,他写了批评钱穆的文章就是代表“中共官方学术界”,你攻击“在政治上是处在绝对敌对的立场”的郭沫若,又是代表哪个“官方学术界”呢?对白寿彝先生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尽可以反批评,但余英时并没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反驳意见,只是用“下流的暴力语言”这种恶语骂人,岂不是有失学者的风度吗?
读者从我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们并没有把《十批》当作不可批评的圣物,也无意于为郭沫若的缺点辩护。我们只是认为,学术批评应当实事求是,不能出于政治偏见而恶意中伤。余英时称自己三十七年前写的文章是“年少好事”,果真如此,倒也罢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他还要重新发表,而且在跋语中说:“郭沫若的攘窃,铁案如山,我一点也没有冤枉他,而且这一桩公案至今仍不甚为世所知,让它再流传一次还是有意义的。”这就说明,余英时是蓄意要继续对郭沫若进行诬蔑,而且进而把攻击矛头指向“中共官方学术界”的。但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毕竟不是学术。余英时以他今日的名气能够蒙蔽某些不明真相的人,然而谎言并不会因此就成为真实。余英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读者推荐《互校记》,使我们有机会得以对这桩学术公案作一番认真的了解。这一点倒是应该感谢他的。由于篇幅限制,有些问题我们并没有提及或未充分展开。如果余英时先生对这桩公案还有什么新的看法,我们是愿意和余先生进一步讨论的。
标签:韩非子·说林上论文; 余英时论文; 法家思想论文; 读书论文; 郭沫若论文; 吕氏春秋论文; 史记论文; 秦始皇论文; 商鞅论文; 吕不韦论文; 长信侯论文; 吴起论文; 钱穆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