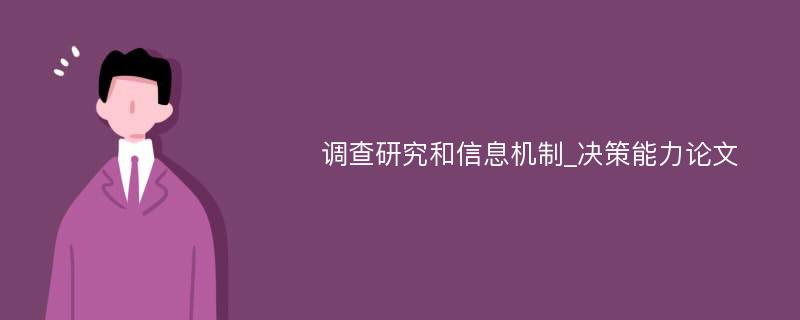
调查研究与信息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调查研究论文,机制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登载侯德础先生文章《论1961 年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新华文摘》1998年第7期转载), 读来很有感触。笔者拟就那一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所折射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信息机制的成败得失,并就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信息机制谈几点看法。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二者在信息机制、激励机制和创新机制等方面有着诸多的差别。
从信息机制来说,现代经济要保证资源配置决策的正确,必须解决信息的收集、传输和处理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要求中央计划者处理瞬息万变、浩如烟海的有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这种巨量信息在层层传递过程中,信息量是呈几何级数递增,最终必然超出计划者信息处理能力的极限,导致信息处理成本的极大膨胀。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以中央集中计划为特征的经济体制之初,都曾取得一些成绩,但也毫无疑问都遇到了不可克服的信息处理上的困难。从技术要求来看,由一个计划中心迅速收集、传递、处理和再发送全国所有的经济信息,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另外,当时信息技术的现实水平,还带来所有制上的新问题。在理论上,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对全部生产资料的管理。然而由于社会成员难以获得必要的信息来参与经济建设和资源配置的决策,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渠道让全体社会成员充分表达他们的决策意见,名义上公有的生产资料实际上产权关系并不清晰,只能由计划体制最上层的少数人来监管,这同样难以避免在资源配置决策上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我国1958年大跃进期间,正是由于中央计划的信息壅塞和决策盲目,而导致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资源配置决策的严重失误,导致了大刮共产风的侵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严重失误。
同时,在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下,由于中央利益和地方及部门利益的矛盾,也导致信息机制的混乱和失灵。中央为实现其计划的“宏伟”目标,或多或少地忽视和牺牲了部门和地方的利益,限制和剥夺了部门和地方的积极性。部门和地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信息渠道上,一方面尽可能隐瞒本地的实际情况,甚至编造虚假信息欺骗中央以邀功请赏;另一方面又尽量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资源供自己支配。由于处于下级的部门和地方在信息方面比中央具有优势,中央领导人在不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和在维护自己令行禁止权威的心态下,往往只能或者宁可听信这种虚假的信息汇报。我国1958年大跃进期间,明明大炼钢铁导致整个生产大幅度下降和资源的极大浪费;明明大刮共产风导致全国粮食库存锐减,农村灾区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猛增。毛泽东虽一贯提倡实事求是,对虚假信息也时时警惕,但是在虚假信息编织成的生产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面前,处于亢奋中的他仍由此坚信“三面红旗”成绩伟大,因而在决策上继续推进经济建设中的冒进,终于酿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巨大灾难。后来,大大滞后的经济建设中的真实信息被毛泽东知晓后,他震惊了,终于发现“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因而号召“为补课起见,我现在提倡调查研究。”于是就产生获取真实信息的重大举措,号召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摸清农村灾荒灾情,了解以“共产风”、“浮夸风”为代表的官僚主义的危害,从而为纠正大跃进错误做决策准备。
因此,1961年毛泽东发起的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实际上是在计划经济的信息机制失效、失灵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是试图在信息机制上拨乱反正,建立一个计划经济框架内的畅通而又可靠的信息机制的一种尝试。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由各级领导干部参与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作为痛定思痛的一种补救措施和作为改进信息机制的一种尝试,在当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正如侯德础先生文章所说:“1961年全党上下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中国共产党在严重的困难和挫折面前重新振作奋起的关键之举。它大大促进了当时国民经济的调整,通过调查研究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条例,确保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有效实施。”
二
1961年在毛泽东倡导下,全党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实践,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调查研究由于是以不改变计划经济的信息机制为前提的一种补救措施,因而其作用是有限的。这种深深打上计划经济的信息机制烙印的调查研究还有着种种缺陷,甚至产生一些新的负面效应。
第一,1961年的调查研究没有能够制度化。当时提倡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本人在严重困难和挫折面前,对“大跃进”以来工作失误的痛定思痛的反思。但是毛泽东所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后来没有能在全党形成制度,随着经济形势的改观,毛泽东反而把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而无人能够改变。
第二,1961年的调查研究的方法不够科学化。毛泽东号召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成员深入基层,亲身进行典型调查。这种蹲点访问式的“典型调查”或解剖麻雀式的“个案调查”,其优点是能直接了解民情,可以有效对付下级官僚主义的虚假信息。但是典型调查或个案调查的缺点是,所选择的调查对象很难具有科学的代表性,无法对现象进行精确的数量分析,因而很难发现现象之间的因果规律。其实我国解放后已经建立了全国性的行政统计机构和统计报表制度,这种机构和制度在不受官僚主义的行政干扰的情况下,可以提供比较全面的真实的信息和进行精确的数量分析。可惜在大跃进期间,左倾的狂热使这种制度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1961年毛泽东纠正大跃进错误,完全可以首先重建行政统计机构和统计报表制度在提供信息方面的权威,并辅之以领导干部的典型调查,来为正确决策服务。但是毛泽东当时并没有着手恢复行政统计机构和统计报表制度的客观公正的权威,只是强调领导干部蹲下去,因而这种经验型的信息调查形式的作用只能是十分有限的。
第三,1961年的调查研究对付官僚主义治标不治本。当时毛泽东重新提倡调查研究,是震怒于下级官僚主义提供虚假信息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但是信息机制失效的根源在计划体制本身,浮夸风、共产风等官僚主义的根源也在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不能有效地分配中央和地方的利益,不能从根本上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那么“上有决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就会经常发生,下级编造虚假信息欺骗中央的情况就不可能根除,甚至下级还会以层层设防,不让群众说真话来对付上级的调查研究。因此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虽然对官僚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有抑制作用,但总体来讲这种措施对官僚主义是治标不治本,对计划体制下信息壅塞和决策盲目也是治标不治本。
最后,1961年的调查研究未能解决决策机制的缺陷。那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许多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真实信息,可以说在信息机制上弥补了计划经济模式的很多不足。但信息机制是为决策机制服务的,若没有决策机制向民主化、科学化方向的革命性变革,信息机制所出现的积极趋向也很难发挥多大的作用。毛泽东亲自提倡调查研究,在亲自听汇报看材料时也震惊于下面情况很严重。但他又从维护“三面红旗”和个人威望的固有观念出发,对其他同志深入调查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再加上他老人家长期独处权力峰颠,因而当刘少奇等在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将来自调查、来自实践、来自群众,又与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种种政策,如责任田、包产到户等付诸实施时,毛泽东随后却将这些政策斥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加以废止,使刚刚出现恢复经济的好形势,不可逆转地发展为文化大革命那样更加惨痛的全局性错误和灾难。
三
以上分析1961年在毛泽东倡导下,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所产生的正面效应和负面影响,是为了论证由此所折射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信息机制的优劣得失,更是为了探讨在新的世纪我们如何构建新的信息机制的问题。我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正在告别计划经济体制,加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我国原有的信息机制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毛泽东所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还灵吗?
如前所说,计划经济体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化生产中信息广泛发生同集中处理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因而陷入困境。而市场经济体制则能较好地解决和处理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信息。其特点主要是,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即市场供求信息反映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从而在消费者中分配产品并在生产者中分配生产性投入。通过市场交易和相对价格的确定,每个经济活动的当事人都可以分享到分散发生在整个经济各个角落的供求信息,正如哈耶克所说,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一个庞大的信息简化场,市场不仅以对信息进行惊人简化的方式产生信息,而且还会通过自身自动的反馈体系去证实(或证伪)信息。因而市场经济的信息机制把信息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
然而市场不是万能的,发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能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而政府的宏观调控则离不开调查研究这种信息手段。调查研究作为市场经济的信息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不断提供和反馈各种信息,监测社会变化和舆情走向,并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在现代经济发展日益复杂多变的形势下,调查研究更应发挥其重要作用,传统的调查研究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手段等各个方面也应该发生深刻的变化。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社会调查研究,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先进的统计技术、抽样技术、测量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并越来越多地深入数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诸学科的方法。抽样调查的广泛运用,问卷法和访问法的精密化,多变量统计分析和统计检验的普及,实验法和心理测验方法的引入,使调查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传统的经验型的调查研究形式和方法,如不注入这些新技术和新方法,将难以再现其生命力。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调查研究的主体也越来越呈多元化的格局:有市场主体——企业自身所进行的无处不在的市场调查;有政府统计部门为获得权威的统计数据而进行的规范的统计调查;有社会中介组织、民意调查系统为把握社会舆论的变化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民意测验;当然也少不了政府官员深入基层的典型调查。在这个纵横交错的调查研究网络中,政府官员亲自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再是获取正确信息的主要形式了。按照社会分工的原则,政府退出市场后,大量的微观市场调查,政府完全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插手;而政府行使对经济宏观调控职能所必需的调查研究,又可以主要依靠专职的行政统计部门和作为中介组织的调查机构,必要时再辅之以官员亲自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在市场经济健全的信息机制下,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加强法制加大科技投入,来保证统计部门和中介调查组织的调查研究资料或结论的权威性,而不必要求自己的官员降格为单纯的调查员。
最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社会调查研究并不排斥和贬低典型调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经常进行这种深入基层、深入第一线的典型调查研究,能够使领导干部时时不忘“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通过切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典型调查向官僚主义宣战,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汲取营养,从而坚定改革的决心。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就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之前,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实地了解国有企业在推向市场的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从而为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科学决策,做了信息方面的充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