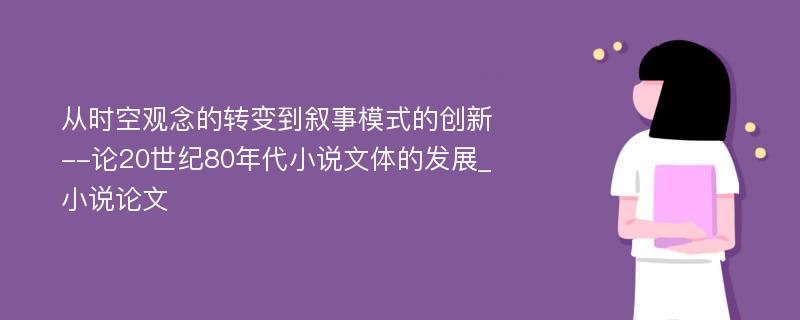
从时空观念的变化到叙事方式的革新——漫议八十年代长篇小说的文体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文体论文,观念论文,时空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全面开放的社会环境,为我国文学的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小说这个领域中,由短篇开路打开局面,继而中篇一跃而崛起,很快形成了创作上的新生面。然而由于体式本身所包括的艺术规律等多种原因,与中短篇相比,长篇小说创作的变革发展,在循序渐进的态势中却 显示出明显的滞后性。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里,它既没有象短篇那样迅疾感应出时代的变革而显现出繁荣的局面,也没有象中篇那样以文体的创造性为特征而屹然崛起。从整体上看,长篇创作是沿续着十七年史诗体式的传统观念进行的,多数作品的建构中心仍然是故事支撑下的情节因果连环。当然,从审美视角上说,经过十年浩劫,作家们的思辩色彩明显地增强,因此在构思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激情制导下的艺术思维律动,表现出一种以冷静、客观的人生态度来直面社会历史的审美趋向。由于民族文化意识的增强和时代哲学的影响,许多人力图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审视处理生活素材,使作品增强了历史的深度和艺术的力度。当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社会总体形态和人生本体意识成为作家思考和建构的基础时,长篇创作传统观念中的注重事件过程的再现和人物成长轨迹的结构框架即逐渐地开始改变。
一
在长篇小说的传统观念里,我们主要受到别林斯基“时代的史诗”的观念影响,认为长篇小说“反映生活的手段不是截取生活的片断,而是有头有尾地描绘了生活的长河。”[(1)]对生活作长河式的描绘,这在时间跨度上说,就不是某些生活断面的展示,而要作有头有尾的整体性反映。因此,以时间的自然形态为依据,对生活作直线性的描述,便形成了长篇小说常见的所谓线状时间叙事模式。表现在作品主人公命运和性格的发展展示上,一般也是单线发展、平铺直叙,在明晰流畅的话语表层结构中孕含着呆板凝滞的深层思维模式。当然,有些作家为了弥补这种叙事方式缺乏跌宕的弱点,在有头有尾的线状叙述的过程中,往往注意插入一些能够改变叙述情态的倒叙或插叙段落,或者在同一叙述平面上增添些叙述线索,造成两条或多条线索交错并行的结构,以改变单线叙事的单调艺术感受。但从整体上看,这种种手法的运用,都是在不改变时间和空间的自然形态的前提下实现的,它对于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和审美建构形不成冲击。因此,新时期最初几年的大多数长篇创作,居囿在传统时空观念下建构作品,虽然也尝试着运用了一些新的手法,但真正可喜的革新不多。开始显示出突破的,乃是在传统情节结构的基础上,溶入了意识流和生活流的构思方式。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可谓是较早显示这种突破的长篇小说之一。它的文体变革,主要表现于作者花在时间艺术上的气力。小说以主人公于而龙四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为主线,吸收了西方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和电影“蒙太奇”的剪辑方式,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和十年浩劫中的生死搏斗等颠倒交叉而又浑然相接地编织成一个瑰丽的艺术整体,压缩在两天半的时间里进行叙述。这样,自然形态的时间和生活流程便被主观地切碎,依据叙述者的构思加以重新组合。其间时序跳跃,现实与历史迭合交错,形成种种扑朔迷离的情节和腾挪跌宕的意境,更加适合对30到70年代末世纪风云变幻和历史变迁的生活表现。而这种超脱了单一线索的多层次立体式空间思维的美学结构特征,引起了读者较大的审美兴趣,因此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古华的《芙蓉镇》,则在另一种意义上改变了传统长篇观念中的时间意义。作品在农村生活的长河里截取了几个横断面,然后根据作家构思的意识流程联缀起来,形成一种既具长河式的时空历史观照效能而又富有生活片断式戏剧性审美色彩的结构形式,不但从根本上避免了传统结构平铺直叙的单调感,使作品的叙事变得跌宕多姿,而且那跳跃式的情节又给读者留下了艺术想象的空间,使长篇这种厚重的小说体式变得机杼轻灵。这方面的例子还有鲍昌的《庚子风云》等作品。
以主观意识为建构基点的结构特征,使长篇小说的整体结构支柱逐渐由外部向内部迁移,由注重主观认识、感觉和情感等意识力量的美学建构功能逐渐形成一种长篇建构的深层情绪化结构模式。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便是较早显示出这种建构体式的作品。小说不再将众多的人物头绪纳入统一的情节过程,而是让他们围绕着深沉复杂的创作动机自由地活动,表现在作品外部的情节延续性被“蒙太奇”式的跳跃性的多层次、多线索的组接所取代。具体说,作品十六部分之间已不存在长篇小说惯有的情节联接点,莫征与郑圆圆的相爱,刘玉英与吴国栋的烦恼,郑子云与夏竹筠的同床异梦,万群与方文煊的感情纠葛等等,在书中都被内在的情绪笼括为一体,而有意抹去了它们之间的形态情节关系。作家有意淡化事物和人物间的客体自然关系,通过外部松散自由形态下所透视出的内在总体情绪,引导读者思考本来就处在改革起始期的那种燎乱的生活,从多角度上形成一种客观性比照和渐进式回味的审美效果。这种超越于故事情节的独特艺术结构,虽然看似漫无章法,实质上却是以人物内在感受为轴心谋篇布局,在有限的篇幅里反映较为深广的社会生活。这种体式上的探索,对我国变革时代那种瞬息变幻、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来说,是一种艺术反映上的有益尝试,同时也为长篇小说近距离地反映生活闯出了一条新路。总之,八十年代初期的长篇小说创作,虽然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革新浪潮,但在一些作品的审美建构方面,也显示出了文体变革的迹象。自然,从整体来看,多数作品仍然是遵循传统的结构方式,而在情节结构的基础上,部分地采用意识流和生活流的描写手法,以求得人物内在展现和艺术反映的深刻。
由于作品建构的革新所带来的思维变革,在长篇小说的审美视角上,本时期也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单纯的正面地反映生活的审美习惯,而注意选择更富有审美情趣和生活内含的生活剖面建立审美中心,从而在美学意识上部分地改变了长篇即史诗的选材构思模式,使创作开始向广阔的人生和浩瀚的生活领域挺进。这方面,本时期较明显的特色即是以人的个性历史和家庭角度为审美视角来折射社会生活。王莹的《宝姑》和德兰的《求》,都是通过少女的眼光来审视生活,在生活的流动中写出时代的发展。李娜的《刺绣者的花》,通过一位普通女工的生活寄遇来反映社会变化,还有俞天白的《吾也狂医生》,通过一位知识分子成长的过程,自然真实地透视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上作品,多是通过主人公同厄运抗争的不屈精神和自强自尊、顽强奋斗的独特性格,反映出探求人生道路的性格力量,进而以一个或几个人物的生活际遇,形象地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的某些侧影。这在长篇文体意识上,算得上是一种开拓性的变革。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则较典型地表现出以家庭的角度折射社会生活的文体建构特征。小说没有侧重农村阶级范畴、采用环绕一个重大事件、设置两组对立人物形成矛盾斗争的格局,而是采用一种“家庭纪事”的结构,以一家人的命运演变为视角,透视概括亿万农民的遭遇,以一村的变化揭示农村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在描写过程中,作者避开了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的写法,虽然四姑娘的命运牵动每个人的心,但每个人胸中装的却不只是这一件事。作品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经过作者努力开掘的精神世界,小说正是通过这些精神世界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我国农村社会面貌的。稍后的《芙蓉镇》,则不但通过胡玉音、秦书田等人物所组成的家庭悲欢离合过程反映社会历史,达到“借人物命运诉时代变迁”的美学目的,而且在故事的叙述中,作者力求“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在抒情的、舒缓的、婉约幽默的笔调中传达出严峻、辛辣和残酷的故事,进而做到了在晓雾连亘、冲静淡远、浸润着馥郁的乡土气息的湖南风俗画中,映射出了中国农村十几年社会历史风云的变幻。另外,寒风的《淮海大战》,用二十二万字,俯瞰式地写出敌我双方几十名高级将领,孟千、苏鲁的《决战》,把人情味与火药味揉在一起,从过去未曾见过的视角上反映战争,等等,都显示出了长篇小说建构过程中思维模式的更新和审美视角的新探。这一切,使当代长篇小说滞重体式的旧的审美观念里,开始溶入了新的美学因素,进而开始明显的文体革新历程。
二
审美视角的变化和文体思维模式的更新,表现在人物塑造方面,是不再局囿于过去那种所谓高品位的典型塑造和强化性格闪光点的观念意识之中。在对人物进行审美观照时,冲决了先进与落后、正面与反面等两极对立模式,由关注形象自身的阶级、阶层的政治素质的典型性而转向关注人物形象本身所含蕴的历史和社会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特别是注意揭示性格的多层次、多侧面所生发出的美学潜在魅力。换一种方式说,创作开始由个体视角切入,不再热衷于表面层次的、现象式的社会冲突的描绘,而注力于个体形象所体现出来的人生内含的多角度探析,从多重组合的角度展示个性力量。如此,人物自然会摆脱二维对立的斗争格局,在哲学文化的意义上变成社会关系的总和。李准的《黄河东流去》,是在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拍摄不甚成功后创作的同一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家在总结了经验教训特别是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经验教训后,在小说创作的美学意识上作了较大的调整。在《黄河东流去》的“开头的话”中,作家告诉读者:“在这本小说里,几乎看不到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了。但它们都是真实的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还有缺点和传统习惯的烙印,但这是我故意写的,因为生活中就是那样的。”1938年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借口“以水代兵”,炸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陷豫、皖、苏四十四县于灭顶之灾中,百余万人死于非命,千余万人无家可归而流离失所。《黄河东流去》正是以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以赤杨岗七户农民的命运为线索,反映了黄泛区难民在水、旱、蝗、汤的重重灾难的打击下,迁徙奔命、辗转挣扎、重建家园的艰难历程。小说中着力塑造的李麦、徐秋斋等人物,再也不是单一性格观念的产物,而是既具有时代闪光性格特质又有某些历史局限性的活生生的个性实体。作品抓住历史上少见的大劫难、大迁徙所波及的广阔地域和不同阶层,采用多样化的艺术笔墨,努力开拓出独特时代的民族生存的艺术空间,从而在较广阔的艺术视角上,描写刻画出不同阶层的农民形象身上所含蕴的丰富的民族精神和时代内含,使小说不再停留于两种政治集团和两种军事力量斗争这一革命历史题材长期难以超越的固有的建构观念范畴,而使审美视角和思维基点上升到文化哲学的层次来透视民族斗争的革命历史。审视点的提高带来了艺术思考的深刻,作品在对赤杨岗农民身上所代表的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进行揭示描写的同时,对其中居守土地、不思变迁所养成的凝固、保守、落后等消极因素也进行了艺术的分析批判,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描绘和性格特征的刻画,让读者领悟到,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只有在发扬继承美好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同时,不断抛弃因袭的精神负担,才能轻快地前进。出版于1979年的《漩流》,是鄢国培长江三部曲之一。作品写了各具特色的遍及四川各阶层各行业的人物六十多个,其中处于全书枢纽地位的人物,是涪陵轮船公司总经理朱佳富:一个有政治野心和眼光的民族资本家,典型的西方帝国主义学文明和中国古老封建遗产的混血儿。他出身破落地主家庭,曾留学英国,获经济硕士学位,不但学习了经营、管理现代企业的知识,而且有了资产阶级观察政局的眼光,谙熟经济和政局的关系。作品中的朱佳富,有着过人的权谋和才干,为了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他搜罗羽翼,完善规章,借刀杀人,无所不用其极。作品真实地写出了处于夹缝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窘迫和挣扎,多角度地透视了朱佳富、高伦等民族资本家的形象,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人物含蕴的自身命运特征,说明了中国社会的历史选择的必然性和艰难性。这在长篇小说的结构上,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历史作品大相异趣。它对人物性格和形象内含的刻画营造,带给小说界的是非同一般的艺术启示。
适应着整体结构和人物描写的渐进性变化,这个时期的长篇创作在以写实手法为主的前提下,多种手法也开始在创作中运用。《沉重的翅膀》在对人物日常平淡无奇的生活描写过程中,叙述者的主观参与色彩使作品体现出一种新的格调。为了增强思辩性,作家往往采用大量的议论和插笔,虽然有时失之节制而造成游离于人物和情节之外的弊端,但在整体上看,它又与作品内在的对腐朽道德观念和保守专横的政治观念的批判性情绪结构相契合,而且一些不乏偏激的议论抒发本身,往往含润着别具韵味的艺术魅力。人们称《沉重的翅膀》为政论体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揭示出了它手法上的新尝试所造成的艺术效果。戴厚英的《人啊,人》,出版于1980年,是第一次在长篇小说的叙述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的作品。尽管作品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一些值得商讨的问题,但它在艺术手法上的开拓性,对于反映知识分子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三中全会二十多年的生活变化和理想转变是有益的。表现手法的创新,增强了作品反思性的艺术表现力。到了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长篇小说由结构形态变化而造成的叙述方式的变化、艺术手法的革新日益增多。李国文的又一长篇《花园街五号》,通过花园街五号先后五个主人的命运描写,反映了临江市五十年四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云变幻。作者采用了回忆、联想、交叉和时空交错、情节复迭、虚实并举等手法,仅用了23万字,就包容了广阔时空里的社会历史内容。比《冬天里的春天》在形式革新上更进了一步。从作品的整体构思上看,作家采用了象征手法,把具象描写与喻象描写交替编织,其间,人物联想、回忆甚至幻觉,情节的交迭、闪回等等,都从不同层面上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在艺术手法的交替并用中,尽管还比较明显地存在着新旧手法不够协调的问题,但它所昭示出的革新方向,却是令人欣喜和关注的。
三
八十年代中期,在经过了短篇和中篇小说创作的成功实践后,文坛上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纷纷转向了长篇小说的探索领域。特别是随着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文坛发表了大量长篇新作。不少大型刊物竞相刊载长篇,文学批评界和文艺评论刊物也纷纷组织对长篇小说创作的讨论。于是,如同建国后经过了十年时间在1959年前后形成长篇小说出版的高潮那样,在新时期文学走过了十年历程的时候,长篇小说在1986年出现了创作的新局面。无论从作品发表的数量还是从艺术形态的探索来看,都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发展的新阶段,有人干脆称之为长篇大爆炸的年头。无论人们对长篇创作的新形势作出怎样的评论,作为一种文体形式,长篇小说一旦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这对其文体意识和审美形态的研究与探求,都会造成良好的历史契机。因此说,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国长篇小说的创作实践和长篇文体的研讨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了长篇小说文体探索的社会动力。
长篇小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审美形态?它与中篇、短篇的不同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一时期的作家和理论家们结合创作实践,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见仁见智,结论不一,但有一点却体现出了时代对文学的共同领悟,即讨论长篇这种文体形式,应该超越从前那种仅从外部形体入手的局限性。从小说的形态意义上说,长篇不但不是中篇的拉长,它与短篇的区别,也不能仅限于生活的断面和纵面的不同取材特征的理解。一种文学体裁的全部内含不限于文本形式的外在呈现方面,它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反映生活和揭示世界的特征方面。如同巴赫金所说:“那些文学体裁用一些构思现实的新手法来丰富我们的内部言谈”。[(2)]作为长篇小说文体,它与中篇和短篇的不同,更多地表现于作家在对社会生活的观照方式不同而引起的艺术建构的特异。具体说,作为社会“自己的一面镜子”的长篇小说,它在对社会生活、时代发展和人生体验的反映中是大容量的载体,因此,它与中短篇的区别应该是审美反思的多层次、多维度、多视点所造成的多极空间的美学形态的具体呈现。对这种美学形态的审美效应的研究,人们经过反复讨论,逐渐趋集于对时空观念的艺术处理的认识。用传统的思维语言表述,决定长篇小说内在规定性的关键因素,是叙述时间和空间的结构组合和艺术处理。因此,众多批评和分析长篇小说的文章,都从结构入手来认识和分析文体的发展和形态革新,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人们艺术认识的自然发展。
自从八十年代初一些长篇小说开始打破传统的自然时空的直线性叙述,谨慎而又有限度地引入意识流手法和“蒙太奇”组接方式之后,长篇文体叙述的厚重风度即开始渐变,随着创作过程中时空调度的观念更新,多元视角的审美建构和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段使艺术空间得以空前拓展,叙事时间变得机智灵活,从而为作家多向度、多层次地反映日益复杂多变的生活创造了广阔的艺术天地。总之,审美视角和叙述方式的多极选择,带来了长篇小说文体的大跨度变革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改变了八十年代初长篇创作“用”变“体”不变的状况,作品无论以什么组构形态出现,都彻底改变了封闭自足的构思特征,而成为开放式的审美客体。适应着我国小说创作所呈现的多元、多向、多变的活跃局面,长篇小说虽然与中短篇相比显得尾大不掉,难于应变文学大起大落的试验,但从整体上建立一种新的审美品格、新的艺术形式已成为创作界的追求趋向。因此,冲决旧的体式规范,在中西文学思潮的交汇碰撞中进行有益于自我抒张的形式选择,便成为长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种自觉行动。当然,鉴于长篇本身体式的原因,这种选择也表现出一定的稳态特征。表现在审美思维层面,最根本的变革是从因果律的线性思维转向了多维时空的立体思维。这就使它带来的审美效应不同于八十年代初的局部手法变革所引起的娱悦,而展示出美学意识上的重建效应。
刘心武的《钟鼓楼》,较早在传达出了这种变动的信息。据作家自己说,这部作品“企图向读者展示一幅当代北京市民生活的斑澜画卷,或者说,是企图显示当代北京的社会生态景观。”而这种全方位的社会生活景观式的描写,用传统的线性结构显然是不能胜任的。作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观照模式,在结构上煞费苦心,采取了类似中国古典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法”,把自然时空按主观感觉实施改造与组合,形成一种围绕中心的放射式结构。作者所要反映的生活,就时间而言基本上都集中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这天早晨五时至下午五时的十二个小时之中,作品按时辰分为六个主要章节,即卯、辰、巳、午、未、申。就空间而言,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北城钟鼓楼一带,具体是集中在一条胡同的四合院之中和鼓楼前的“地安门外大街”上。如此使书中人物按照作者设想的放射式主观结构网活动,全书在开放式的结构模式中,主要通过文献式的叙述与心理剖析,引导读者对貌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和人物有所发现,促进读者对各种人物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深入思考,从而形成一种以思辩为主体的理论结构。为了给读者一种原生态的真实感,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作品在叙述上力求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势。在对人物言行举止的描写和心灵揭示方面,作家尽量采取比较理念化的思辩的分析和阐释语气,以不破坏事件的客观性发展形态为原则,冷静地从所述现象和心理中抽出普遍性的社会心态和规律。与散点透视对群态的关注相配合,作品基本改变了过去英雄视点而开始从个体价值身上体现出作家的艺术思考的意义。传统闭锁式结构的戏剧性效果、情节发展中的悬念、巧合等等在作品中都因结构的开放变得无足轻重。作品力求在对于自然流动感的不同时空环境中的生活“全部丰富性”的展现叙述中,呈现出北京独特的民俗风情和伦理精神、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情态。因此,文本的时空视点不再凝滞于所表现的具体生活事件与人物情绪的延展上,而是服务于主观印象的感受上。从这个层次上说,《钟鼓楼》的“花瓣式”或“剥桔式”的结构形态,标志着长篇小说从具体性与顺序性的自然时空结构原则,开始向非逻辑顺序的复现生活原始形态的多维时空的艺术结构转移。而这种转移的基本前提,即是作家以感觉时空对传统客观时空的冲击。这方面,柯云路的《夜与昼》也显示出了自己的努力。作品所创造的“散点式多侧面透视”的新的时空建构,与《新星》以李向南为中心的情节结构已完全不同。正因此,它才能通过人的主观想象的感知时空结构所带来的灵活方便的叙事情态,铺写出京都十几户人家、百多个人物全方位、快节奏跃动的场景,进而传达出社会急速变化中的那种浮躁骚动的情绪。
蒋子龙的《蛇神》所显示的结构特征,又代表了长篇的另一种时空建构特点。作家将时间拦腰夭折,以现在时的自然伸延和过去时的回溯为两个支点,交叉地向前推进,形成一种交叉性结构,使多种结构方法交错使用。现在时是过去时的延长,而过去时是现在时的延伸,两种时间交替出现,从而寻找出主人公今天的变态、扭曲与昨天的荒谬年代的内在联系。这在时空观念上来说,是摒弃了由自然时间、空间来牵引生活事物的方式,而以时空交叉、情绪脉动所构成的辐射网络来建构作品,使小说的时空呈现出回环往复的形态。它意在把读者的艺术视线集中到交错的、难解难分的意识结构上来,达到一种较之单向度折射更具审美启示力的效果。王力雄的《天堂之门》就采用了这种时空交叠的构思方式,把历史与现实这两个不属于同一时空的范畴作为作品内在律动的两极。全书以考古与改革交错出现,一是磐磨山无头国地域文化史,考古为文明史的纪录,一是当代某汽车制造厂改革生活的摹画;这两条线又分三十一个单元,各单元穿插安排、交错时空,给小说带来的是鲜明的时代感与辽阔的宇宙感。
还有《活动变人形》、《隐形伴侣》、《铁床》等等作品,都通过情节结构与心态结构的互相交叠,使传统小说的客观叙述与现代小说的感觉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作品在交叠的层次感、空间感和主体感中形成一种多向折射的意蕴,诸如人生真谛、人生意义,生命价值、历史评价、理想意识、爱情观念等等的多向审美关系,从而拓展了长篇小说的美学域区,为读者的审美反思留下了广阔的余地。张炜的《古船》,用象征性的构思来展现一个写实的世界,在小说的整体形态中,虚实两个世界互相渗透,由古船这个整体意象的象征性,造成了作品写实世界背后的虚拟世界,使洼狸镇的人事均有了象征的意义。这种变异式的时空处理,使作品在写实中采用象征、魔幻的形式,造成了作品一种神奇的艺术氛围。
长篇小说结构的变化,自然是由审美视角的变化引起的,而这些变化,又自然造成叙事情调和艺术审美方式上的更新。随着情节设置上抒情性或隐喻意味的追求,作品结构变得松散自由,象祖慰的《冬夏春的复调》,借鉴了音乐的结构形式,王蒙、莫言的系列组合音响式结构形式,王安忆《流水三十年》首次用心理分析的叙述方法来演绎长篇,陈村《从前》,以散文的章法和笔调来试写长篇,以“我”这个人物贯穿全篇,把不同地点、时间的生活情景形散神不散地连结起来;还有矫健的《河魂》,由于“我”进入小说并作为小说的结构线索,使情节淡化,主观抒情强化,从而产生一种诗意效果,亦可划入散文式结构一类。叶辛的《轰鸣的电机》,则运用多方铺叙、改换场景的方法,描写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地点在同一时间里作用于主线的起启转合。
总之,新时期长篇小说的文体形态,以结构的多样化为中心,已走向了多姿多采的领域。虽然从整体来看它的艺术革新还难令人十分满意,而作为一种体式厚重的艺术门类,作家们在八十年代所进行的这些文体创新实践,无疑为此后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可喜的基础。
注释:
(1)参见《茅盾评论文集》(上),178页。
(2)转引自《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207页。
标签:小说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沉重的翅膀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黄河东流去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美学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