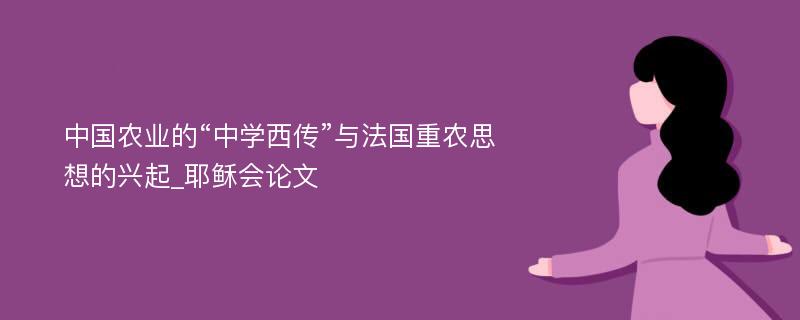
中国农业的“中学西传”与法国重农思想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中国农业论文,思想论文,中学论文,重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6-18世纪的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是欧洲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的接触及影响,而实际充当这种科学与文化接触媒介的,便是在欧洲宗教改革和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潮中应运而生的耶稣会传教士。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这两个多世纪中,随着一批又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在“西学东渐”还是在“中学西传”活动中,来华传教士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中国文化与科技的接受者,进而成为向欧洲译介中华文化与科技的传播者。通过书信往来和译介中国典籍等方式,他们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包括农耕文明,介绍到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从而对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产生了影响,同时还推动了法国重农思想的兴起,堪称中外农业文明交流的先锋。
耶稣会士“中学西传”活动加深了欧洲对中国的了解
在适应性传教路线指引下来华传教士,出于打开传教局面之需要,同时也是因为本国教会和政府的要求,有的是由于自己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希望在中国典籍中寻找到基督教教义的对接点,如利玛窦以及“索隐学派”的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和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5-1741)等人,有的则是由于天主教被禁以至于传教难以继续,因此只能一方面为朝廷服务,另一方面潜心译介中国文化,如蒋友仁(Michael Benoit,1715-1774)和钱德明等人。因此,在从事西方科技知识译介的过程中,不少人也积极投身于把中国文化科学与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情况介绍到西方世界去,是为“中学西传”。尽管西方来华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西方文化,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又成为中国文化的受熏陶者和接受者,进而成为向欧洲译介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张西平(2009:113)在其研究中以白晋为例指出,白晋撰写的《康熙皇帝传》震动了整个欧洲,直到此时欧洲人才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这么一个英明的君主,他的才能、坚毅和勤奋好学令欧洲人为之感动,他对西方科学的热情,对待不同信仰的天主教的宽容和亲善,使得不少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从中国看到了理想的国家模式。白晋对康熙皇帝和中国的介绍为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掀开了序幕。韩琦(1997:47)也认为,中西交流是双向的,从17、18世纪中国和欧洲科学关系看,我们不能忽视通过中国传人欧洲的科学,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观测和考察对欧洲科学的贡献,一是耶稣会士所介绍的中国科学对欧洲的影响。显而易见,“中学西传”活动也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加深了欧洲对中国的了解,促使中国先进科技知识和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促进了中西文化科技交流和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在他们留下的手记、图说、文献等资料中,中国的形象不断丰富起来。他们能熟读中国经书,并熟练地用中文写作,他们的中文著作达760多部。在他们笔下出现了一个‘文明中国’,改变并丰富着‘神秘中国’的形象”①。与此同时,从单纯的观察和考察到发表自己的分析评论,这些传教士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科技的时候,实际上已成为了欧洲最早的汉学家,他们的“中学西传”成果事实上奠定了欧洲汉学的基础;而由于法国传教士在其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因此法国才会至今保持着欧洲汉学重镇的地位,在欧洲汉学研究中,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所取得的“中学西传”成就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就是最好的说明。
明清之际的“中学西传”活动,就其活动方式、传播内容、成果形式与成果数量而言,与“西学东渐”呈现出明显的不同:(1)“西学东渐”的成果以著述居多,而“中学西传”的著述相对要少得多,通过传教士的书信向欧洲介绍的方式更为常见;(2)“西学东渐”的著述集中在基督教教义和自然科学这两大类,而“中学西传”的著述以儒学典籍译介为主,其次是史学著述,再次是科学知识的介绍,换言之,人文社会科学居首,自然科学居次。(3)与“西学东渐”著译迄今为止较好的统计工作相比,“中学西传”著述的统计工作虽然有人做过,但十分不易,由于史料问题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问题,这方面的统计或者是不全,或者是重复,很难说出一个比较精确的数字。比如说,黎难秋的《中国科学翻译史》对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中的外译中做了很好的统计,但是中译外的统计则几乎是一带而过。《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有“本书在传人重要译著书目”,其中也包括在华传教士的“中学西传”著述,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详细的梳理,但是,这是按照人物来华年代先后编撰的一个汇总,而不是一个量化的统计。张国刚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一书根据《列传》所做的量化统计也只是从国籍角度来比较在华耶稣会士“中学西传”著述(含刊印和未刊印的)的数量并且最终得出如下结论:1687年后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学西传”著述的数量在各国来华耶稣会士中遥遥领先(2003:319-321)。冯棠(1999)的《耶稣会士对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新局面的重要贡献》对耶稣会士“中学西传”活动及其成果做了较为详细的综述。
传教士著述类“中学西传”中的中国农业社会
来华耶稣会士的“中学西传”著述以儒学典籍为最多,历史著作其次,科学译介最少。在中国科学向欧洲传播方面,17世纪波兰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成就最为突出,他是第一个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化成果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他的科学著述是多方面的,涉及中国动植物学、医药学、地图学等,其代表作为《中国地图册》、《中国植物志》、《中国医药概说》和《中医脉诀》。18世纪法国最重要的传教士汉学家宋君荣(Antoino Gaubil,1689-1759)除撰写史学学著作以外,对天文学的研究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中国天文学史》介绍了中国15世纪之前的天文学发展历程,以及中国的星宿表,中国测算日蚀、月蚀的广泛和日蚀、月蚀表,中国测算金、木、水、火、土五行昨运行的方法等。
在传教士的“中学西传”活动中,中国的农业社会的许多成就也被译介到了欧洲,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重视不够。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72-1780)撰写了《野蚕说与养蚕说法》、《说香椿》,《说若干种中国植物》,《说娱乐庭园》,《说麝香》,《说磨菇蕈、灵之、白菜》,《说诸物》,《说桃树》,《说木树果子、構树、赤枣》,《说牡丹》,《说皂荚》,《说蜂蜜与蜜变白色之法》,《说朱砂、水银和灵砂》,《说中国毛帚》,《说马》,《说玉》,《说硫璃瓦》,《说鹿》等著作,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动植物和工艺技术产品。另外,韩国英还翻译了《康熙几暇格物论》,这是康熙在政务之余研究各门科学问题的心得之作,其内容涉及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农学和地学等诸多方面。
法国耶稣会士金济时(Jean-Paul-Louis Collas,1735-1781)撰有《中国之毛畜》和《记中国肉食》,介绍了中国的畜牧业种类、牧养方法以及病害防治技术等等。此外,他还撰有《可能移植法国的“中国植物花木之观测”》,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记载,这是金济时根据一部中国农业书籍编撰翻译的,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高度评价中国农业生产之先进,第二部分介绍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和肥料运用,其要旨大概不离“农事及时”一语,第三部分介绍了可能移植到法国的中国植物,包括产蜡树、产脂树、产漆树、桐树、椒树、樟脑、竹、柏香树等等。从目前相关研究来看,这是中国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最早被系统介绍到欧洲的著作,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但在过去的以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为对象的研究中,关于农业的“中学西传”内容则鲜有提及。
传教士书信报告类“中学西传”中的中国农业社会
耶稣会士来华之后除了出于传教的意图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外,他们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十分关心。通过写回国内的书信,他们把中国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了西方国家。其中,利玛窦的开启之功不容低估,吴孟雪、曾丽雅(2000:47)认为,首先他对中国之了解是建立在其长时间的全面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的,远非当时欧洲社会对中国的那些道听途说所能比拟,其次是他是一个掌握有一定先进科学知识的硕学之士,因此得以较为客观地向欧洲介绍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优秀之处,同时又结合自身感受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中国社会、文化、科技、礼仪、教育等方面的弊端。韩琦(1999:7)也认为,利玛窦对中国科学的评述成为17世纪欧洲人了解中国科学的主要信息来源,他对中国科学作出了总体上客观公正的评价,赞扬了中国人的良好道德修养以及古代科学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对当时中国的科学现状提出了批评。
来华耶稣会士对西方国家介绍的中国国情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提到了中国农业社会、农业生产和农村状况。比如说,《利玛窦札记》第一卷第四章利玛窦还十分详细地介绍了茶叶制作工艺及其饮用方式:“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Cia)的那种著名饮料。在这里,他们在春天采集这种叶子,放在荫凉处阴干,然后他们用干叶子调制饮料,供吃饭时饮用或朋友来访时待客。在这种场合,只要宾主在一起谈着话,就不停地献茶。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即使经常饮用也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这种灌木叶子分不同等级,按质量可卖一个或两甚至三个金锭一磅。”②
1687年之后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带着十分明确的考察中国科学和国情的使命而来,因此,他们在向本国修会和科学院提交的书信汇报中对中国科学技术介绍的频繁程度远远高于他们之前的来华耶稣会士。韩琦(1999:31)指出,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进行的科学考察活动主要包括天文、气象观测、地理考察以及对动植物、药物、中医和矿业的研究,他们通过书信向欧洲介绍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奇特世界,客观详细地描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些方面。利国安(Jean Laureati,1666-1727)神父在1714年6月26日写于福建的一封信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丝绸、茶叶、酿酒、养蚕术、纺织业、漆器、动植物、淡水和海洋渔业、黄金与铜币以及拥有的各种金属矿产资源等等,法籍耶稣会士殷弘绪(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1662-1741)神父于1736年10月8日写于北京的信介绍了中国的柿子、荔枝、槐树、柳树、扫帚草、冬虫夏草、樟树及樟脑等植物以及用羊肝治疗夜盲症等。他在1734年11月4日在北京写下的信中又介绍了中国的珍珠养殖情况、瓷器和藤器的修复方法、室内装饰和古铜器的制作方法、香料的培植、灯芯和蜡烛的制作、从植物中提炼水银、磁体知识以及炼丹术士的骗术。
1701年抵达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沙守信(Emeric de Chavagnac,1670-1717)就曾在其书信中多次描述当时的中国农业社会和农村状况。他在1703年2月10日写于江西抚州的一封信中写道:“赣州是像鲁昂那样大的城市,商业繁华。从赣州到南昌,这一带非常迷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中国人确实和国外很少通商,但作为补偿,在帝国内部的商业规模都相当大,这是欧洲无法与之相比拟的。中华帝国疆域辽阔,每一个省都是一个王国,有的出产稻米,有的生产布匹,每个省都有它们独一无二的土特产。所有这些物品不是经陆路,而是通过水路运输的,因为这里河道纵横,风景秀丽,这都是欧洲难以与之媲美的。”③
另一位法籍传教士彭加德(Claude Jacquemin,1669-1735)1712年9月1日写于崇明岛的信中对该岛的来历、地理位置、岛上的风土人情以及全岛的政治、经济、农业、商业、教育和语言活动做了十分详细的描述,其中的大量篇幅是用以描述和介绍岛上的农业社会、农业生产和农村状况的,堪称是那个时代中国农业社会的缩影,而其描述之细致完成称得上是一份科学调查报告。比如,他在描述岛上的土地种类及相应的农业生产活动时写道:“全岛土地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三种类型土地,出产也很不相同。第一类土地位于岛屿北部,自然生长于此的芦苇是一宗巨大受益。第二类土地位于上述土地以南并一直延伸到到岛屿南侧海边,岛民们在这类土地上每年收成两次;一次是收获谷物,这在当地十分普遍,通常于5月份进行;另一次是收获稻米和棉花,前者于9月份进行,后者稍晚些时候。他们的谷物有小麦、大麦和元麦,后者虽颇似黑麦,但属于另一品种。第三类土地貌似贫瘠,实际收益却比前两类还大。这是一种灰白色的盐碱地,成片地存在于岛屿北部一些沿海地区,从中可提炼大量的盐,不仅可满足全岛食用,还可供应大陆。”④更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彭加德对岛上的稻米生产过程的观察和对江南地区精耕细作农业生产的描述俨然达到了专业水准:“种植稻米是最辛苦的活。自6月初起,岛民们便抽取田地周围四通八达的沟渠的水浸泡稻田,为此使用的工具很像欧洲人排干沼泽地或围堰时所用的戽斗水车。然后,要在水田里连续翻耕三至四遍,而且双脚始终踩在水里。最初这些工作完成后,再用钁头捣碎土块,用木制犁耙平整土地,以便使稻田里的水到处都同样深浅。犁耙由一头水牛牵引,人站在犁耙上驾驭水牛。稻田整好后,他们就拔一个月前播种在另一块田里密集的秧苗,移栽于整好的稻田里,不过苗距比秧田里的要稀疏得多。秧苗返青后,还要拔除妨碍秧苗生长的杂草。”⑤
促成法国重农思想的兴起
1687年后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写回国内的书信后来大多被编辑收录到了《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系列丛书之中。该书的中译者郑德弟教授在该译著的中文版序中对耶稣会士通过书信所进行的“中学西传”活动的意义和历史价值作出评论时说:耶稣会士研究中国历史,绘制中国地图,参与中国外交,他们还深入我国各省,研究民情民俗、历史掌故、物产工艺……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融入程度以及对我国的了解的深度是以往来华的任何外国人无法相比的,他们称得上是当时的“中国通”,而这些“中国通”又长于著述,勤于写信,于是,从罗明坚和利玛窦1582年入华为肇端到1775年耶稣会在北京被解散的近两个世纪中,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便通过他们的著述、书信和报道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了西方,西方人由此才开始真切地认识中国,西方的汉学也由此得以奠基。耶稣会士因传教之需把西方各种信息和先进的科学知识引进到了中国,又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基础上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他们是16世纪至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角色和先驱者。这批书简出自身在中国切对其已有切身体验者之手,其内容大多是写信者本人所见所闻或亲身经历之事,自然就具备了某种“现场报道”的性质,它们给西方带去了中国的形象和信息,因此被反复传抄,广为流传,成了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进一步推动了欧洲的汉学热潮⑥。
张国刚、吴莉苇(2006:236-248)的研究还认为,经由来华耶稣会士传到欧洲的“中学西传”成果还促成了法国重农主义思想的兴起,因为法国自路易十三至路易十四时代奉行的都是重商政策。这一主导政策为法国带来了许多财富,促成了法国在欧洲地缘政治领域的壮大和崛起,尤其是让法国拥有了一支比当时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但也严重损害了农业利益,激化了社会矛盾,因为法国政府的重商主义行为是以牺牲农业利益为前提的,农民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为此,自18世纪中期开始,法国的一些官员和学者开始针对本国社会和经济现状寻找出路,重农主义思想开始抬头,重农主义者认为,就国内事务而言,当务之急是应该增加农产品,其途径在于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1694-1774)提出了“农民穷则国穷”这样的寓意深远的格言,认为农业人口的就业增长和农业繁荣将刺激贸易和工业。在他看来,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一个根据自然法则、自由放任的经济和贸易发展的社会,而这个社会的根本必须是农业。
显然,魁奈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重农主义社会实际上是以中国为蓝本的,因为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制度通过来华传教士发回国内的书信介绍在欧洲大陆被广泛传诵,尤其是中国朝廷对农业的态度无疑为重农主义者提供了思想材料和有力论据,甚至连孟德斯鸠这样的对中国政治制度非议多多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重农政策是善政。伏尔泰也不失时机称赞中国的重农政策并抨击法国政府对农业和农民的轻视。另一位大思想家卢梭也以中国的重农政策之成功为论据直言其重农倾向。对于中国的重农政策,来华耶稣会士在其书信中多有详细的叙述,如法国耶稣会士龚当信(Cyr Contancin,1670-1733)神父1725年12月2日写于广州的信中举例说明了雍正皇帝的亲农重农政策:“为了鼓励农民劳作,启发他们热爱有规律的生活,他下令各城市的都督每年向他禀报他们县里最勤于劳作、善于治家、和睦乡邻、俭朴节约、远近闻名的农民。根据都督的禀报,皇上封这些农民明智、积极的农民为八品官,并发给他名誉官员的证书。这个封号使他有权穿官服,拜访都督,在都督面前就座,和都督一起喝茶。他余生将受到尊重,死后还给他举办与他品位相称的葬礼,他的衔位将写在祖宗祠堂里。对于这位受尊敬的农民及其全家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快乐!这种做法除了激起农民竞相认真劳作之外,皇上还给国家必需的、在中国始终受到尊重的农作增添了新的光辉。”⑦
龚当信1727年12月15日写回国的信则详细介绍了雍正的亲耕礼:“中国人的治国箴言是,皇帝应该耕田,皇后应该织布。皇帝亲自为男子作表率,让所有的臣民都不得轻视农业生产。中国古代开国皇帝都遵循这个习俗亲自耕作,大部分后继者也仿效他们。新皇帝雍正服丧期满就宣布他每年春天要亲自开耕。在中国,二月正是开春时节,钦天监接到命令观察气象,确定阴历二月二十四为举行开耕仪式的日子。为了亲自准备牺牲祭天,皇帝预先连续三天不进食。一切准备就绪,阴历二月二十四,雍正皇帝和全体朝臣都穿着礼服到指定的地点去祭天,皇上在扶犁前先祭供牺牲。雍正皇帝扶着犁耕了好几个来回,几块地耕完后,雍正皇帝就开始播五谷种子。”⑧另根据龚当信神父在1730年10月19日撰写出另一封信,他介绍的关于中国政府的重农之道在法国大受欢迎。在18世纪中期农业、农村、农业问题日益严峻矛盾日益尖锐的法国,由传教士介绍而来的中国政府的亲农重农政策对于法国社会会带来多么大的冲击力,由此不难想象。重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魁奈更是喊出了“农民穷则国穷”的至理名言并借鉴中国政府的亲农重农经验提出了法国的重农主义思想。1768年春天,路易十六王太子仿效中国皇帝的亲耕礼而亲自扶犁,标志着法国重农学说达到其巅峰期。
在耶稣会士来华300多年后,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这段跨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作出了高度囊括性的评价:“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足以和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的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⑨。
注释:
①杨桂青、张以瑾:《汉学: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认识自己》,《中国教育报》2007年3月30日。
②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第17页。
③沙守信神父致本会郭弼恩神父的信,载《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1,第240-241页
④⑤彭加德神父致印度和中国传教区巡阅使神父的信,载《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Ⅱ,第76、76页。
⑥[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郑德弟等译,中文版序,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006-007页。
⑦⑧龚当信神父致本会爱梯埃尼·苏西埃神父的信,载《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Ⅲ,第193、264-265页。
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640-641、693页。
